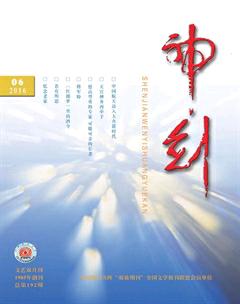要好故事,更要经典文本
对品质的追求源自对生活的体认
傅逸尘:近段时间,随着由你原著并编剧的电视剧《麻雀》的热播,关于谍战的话题又开始在网络和新媒体上流行起来。在各种讨论中,我注意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品质。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三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上,众多圈内人士共同发起了“聚焦质量,共赢未来”的倡议,也是对近年来影视剧市场乱象丛生、烂片横行的一种反拨和回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麻雀》,你有着怎样的定位和期待?
海飞:我想先说一说为什么会有《麻雀》。首先我喜欢“麻雀”这个名词,尽管麻雀在飞禽中是属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种,但是我觉得“麻雀”两字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在我眼里,一切潜伏都将是人性的潜伏,我必须找到一种不起眼却暗流涌动的符号,那么麻雀最贴切。然后我想做的是一部烧脑戏,步步为营、惊心动魄,主人公分分秒秒都命悬一线,一定要有那种悬崖之上走钢丝的味道。于是在两年多前,先有了一个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麻雀》,接着有了改编的剧本。而我心中所想的是,这个剧需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么前提就是你所说的:品质。所以细节真实、逻辑合理、情感动人,是必须做到的。
傅逸尘:品质的保障,除了以大制作为基础,还需要在基础的细节方面用心营造。现在很多军事题材影视剧,其实从资本的投入来看都是大制作,但是观影效果却并不一定和资金投入成正比,原因就在于生活质地方面出了问题。尤其是年代戏,主创们如果不下功夫去研究历史,研究当年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习惯,就会显得虚假,观众也会跳戏。
海飞:你说得很对,所以《麻雀》这部戏,就要从这些案头性、基础性的工作做起。无论是服装,道具,化妆等等,都需要力求向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一面靠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上海是一个有着众多洋人集聚的城市,所以西洋音乐,西洋味道,永远充斥在其中。当时黄包车上的车牌号码,是几位数,这个需要道具部门去查的。那时候汪伪政府用的旗,和蒋氏政府是略有区别的。电话号码是几位数,也是需要做功课去了解的。我甚至认为,民国时期的办公桌该是什么样的,就得用什么样的。那时候的旗袍,那时候的手提包,那时候的背景音乐等等,都需要符合20世纪40年代初的特征。甚至是槍械,如果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枪械,我们完全可以改掉剧本中使用的枪械。比如“掌心雷”,这就是一种射程极短的枪,便于携带,小得能完全握在“掌心”中。这十分适合沈秋霞这样一个穿呢子大衣的女特工使用。
比如特工机关的服装,只要看过电影《色戒》你就会知道,易先生从不穿军装,部下也全是黑衣特工。汪伪特工是没有制式军服的,就像我们的便衣警察一样。同样,在同一个时期的陪都重庆,军统人员配发军装,因为他们属于军人序列,但是机关工作人员和军统特工执行任务时,也是不穿军服的。比如女性工作人员,统一旗袍,而且是阴丹士林旗袍。这是我采访过大陆最后一名女军统王庆莲,她告诉我的。比如上海街头的电车,开车人是穿公司制服的,还戴着制式帽子。比如石库门,在上海是有大量石库门的,石库门是一种奇怪的房子,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也不像江南的台门屋,而且还含着那么一点儿西洋的味道。但是却有小天井,会客室,还有老虎窗。说白了,其实是中西合璧的一种房子,“亭子间”就是石库门所特有的。石库门正门门楣上一般会有砖雕的字,比如“同福里”,或者“秋风渡”。比如剧中出现的《语丝》杂志,是可以查到封面样式的。而服务员应该穿的服装,邮筒、菜场、广告墙的模样,都需要先考证,再制作。至于在剧本中出现的音乐,路名,涉及的人名和提到的事件,比如明星电影公司,比如演员白杨或者黎锦晖创办的演艺学校,比如周璇的歌曲,哪怕是咖啡馆和饭店,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都已经经过了详细考证。我的意思是,在此剧的拍摄过程中,也要如此的严谨。在我眼里,剧中的刘兰芝、扁头,说话会是带上海腔调的,但这种腔调不能过多,只适合剧本中设定的人物使用。而毕忠良和陈深,作为戏量多的重要角色,最多偶尔使用一两个上海腔的词。毕竟我们要面对的是全国观众。
傅逸尘:事实上,作为中篇小说的《麻雀》,其中也是做了大篇幅的心理描写的,对于人物情感的铺垫和描摹非常细腻。这些文学性较强的元素,到了电视剧本中,会不会被挤占和压缩呢?
海飞: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在剧中我是要尽量保留小说中的韵味,那种对于人情人性的细腻铺排。所以,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使用了许多场景描述和人物内心的描述,这是为了有助于导演和演员找到感觉。每个人物,首先是在编剧心里活起来,成长,扎根在编剧脑海里的。所以这个剧,需要的是原著小说及剧本中营造的那种氛围,换句话说,就是要具文学性的。我们盘点一下有口碑的影视剧,其实都具有文学性。一个眼神,一片落叶,街头人群密集,突然响起又突然静止的嘈杂之声,以及火车穿过了平原,晃荡的车厢里四目相对等等,是需要恰到好处的表现和表演的。甚至对白的急与缓,轻与重,从容与紧迫,都需要在故事进展中同步掌握。麻雀是需要“演”的,无论是“话中有话”,还是肢体语言,或者是情绪渲染等各方面,都已经在剧本中各有体现。也就是说,演员是需要尽力去领悟琢磨剧本,然后去达到最佳的表演状态。但是有一条,我觉得这个剧中斗智斗勇的主要角色,表演需要内敛。
总之,本剧的制作过程中,细节真实、逻辑合理、情感动人,是必须要尽力做到的。这不是枪火剧,也不是闹剧,在剧中不可能出现狗血,猎奇,血腥,感观刺激等低级的吸引观众的画面。这是一部静戏,一部充满质感的剧。情节可以是层层推进,可以是剑拔弩张,一波接着一波,节奏也不用慢下来。但是暗战双方的表象都必须是波澜不惊。仿佛我们看到的是平静的湖面,而每个人的内心,都如同湖底下澎湃而涌动的暗流。
溢出的文学支撑影视的繁盛-
傅逸尘:最早接触你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说,在整个70后作家群中,你的个人风格显明而出挑。然而从《旗袍》开始,短短几年间,《旗袍2》《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铁面歌女》《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花红花火》,一部部影视剧的接连推出,使得“海飞现象”成为横跨文学与影视两界的热门话题。正在热播的《麻雀》,在我看来是你谍战剧创作中文学性极强的一部。从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是一种极有难度的写作啊。
海飞:说到难度,首先当然来自文体的转换。但是对编剧而言,最大的难度还是来自于对品质的追求。好的谍战剧,要的是心理紧张,而不是枪声大作,所谓的含而不发。比如各种用刑以后血肉模糊的惨状,远不如在走廊上听到撕心裂肺的叫声来得让人心惊。比如主人公面临危机时的种种考验,必须在瞬间去化解,说白了是一场智力大比拼,说白了也是一场场的闯关游戏。特别要说的是,两难是最令人纠结的,在以往的种种谍战剧中,我们总是忽略了“难”的程度,所有主人公面临的问题,总会轻易地迎刃而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一种自我放低的做法。如果往左走,危险。往右走,是另一种危险。而停步或退步走,是更大的危险。这时候主人公要怎么走?那么这样的剧,才会是观众需要的。那种把人心“拎”起来的感觉,要经常性出现。剧本中对紧张和悬念的桥段已有充分表现,拍摄时就要掌握节奏了。也就是在展现危机时的“松紧”程度,是短时间化解,还是把时间和悬念、紧张感拉长,这需要恰到好处的把握。
傅逸尘:你近期的作品如《麻雀》《捕风者》《向延安》《回家》等,都是先有高品质的小说文本,再转化为影视剧产品。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视剧剧本,在故事的层面都非常精彩、扎实,似乎编织“好看”故事对你而言并不困难。很显然,你在剧本中寄寓了更大的文学抱负。
海飞:小说有无数种。小说几乎就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妖怪或者仙女。当下的许多小说,过度沉迷在自我中,各种情绪在小说中滋生,雷同得如同复印。“好看”小说,只是小说中的一种,比其他的小说更容易传播。但是,就我而言,创作过程中并未有那种为了传播而传播的意识。莫言曾把获诺奖时的演讲标题取为:讲故事的人。可见讲好故事是难中之难。四大名著,无一不是经过了数百年检验的好故事。当然,讲故事的技术有高有低,如何融合思想、语言、结构等,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就是作家会碰到所谓的瓶颈问题。我始终觉得,好小说应该是一个汪洋恣肆的故事,这故事是泥沙,但是夹在文学的“水”中,滚滚而来,瞬间击中读者的阅读神经。我觉得至少在一个时期以内,我会在这条道路中前行,像一个安静的说书人。客观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大规模投身影视编剧,成就了中国影视近三十年来的繁盛与辉煌。但这种源自文学溢出效应的支撑正在迅速衰减。
类型是呈现生活横切面的舞台
傅逸尘:整体而言,你的创作有着强烈的烟火气息,擅长在日常生活的流态中描摹活色生香却又感伤易碎的小辰光,折射出大历史的轮廓和面影;你的剧本通常都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在或明或暗的战场上检视人性的复杂和纯粹。对于个人化的风格,你有怎样的追求?
海飞:说到风格,我承认对复杂人性的解读与描摹充满热情,极度迷恋。我一直认为,小说有无数种风格及其所必须承载的使命。各种类型的小说中,我更倾向于用文字讲述人间悲欢。我喜欢把小说中的“人”放低。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焦虑的年代,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小说或者一个剧本,把主人公放得更低些,就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和虚构的可能性。我们谁也不知道,闯王李白成手下有一个音乐爱好者,如果有,他是怎么样的人生。我们也不会知道,上海起士林咖啡馆里一个厨师,他经历了怎样的跌宕人生。而那个年代发生的事件,那个年代的服装,公共设施,地名,必须真实。我认为能做到这样,创作小说的态度,就足够严谨。我们不能知道那时候的雾霾到底有多少指数,至少也得准确写出,那时候到底有没有发生某件大事。
我为什么迷恋这样的小说风格。这不是小情绪,也不是语言狂欢,是在展现让人动容和歌哭的人生,呈现一种年代风起云涌的生活画卷。每个作者的创作方向都不一样。我希望我是站在一本打开的真实纪事的书面前,幻想那个年代发生的种种悲欢。我愿意是一个复述者或者聆听者,甚至愿意和剧中人,一起细数一件大衣上细密的针脚。因此,在创作中,我首先想到的是要高度还原上海生活。我本人对上海十分有好感,是因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上海永远是一个最适合发生故事的地方。因为上海有黄浦江,还有和黄浦江交汇的苏州河,所谓大江大河,浪里有多少的恩怨情仇。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上海滩》《刀锋1937》等剧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呢子大衣、歌舞厅、叮叮响着的电车,哐当当响着的电梯,黄包车和小汽车夹杂在人群车流中,西餐厅不输于现在的堂皇与雅丽,以及赛马场、球场、影剧院等时尚场所……我们的场景不需要设置这些,但是我们在制作、拍摄、演出的过程中,每个人心中就是要装着那么一个陈旧而华丽的上海。而更进一步,如果我们着眼细节去打造一部剧,那么弄堂里其实是会隐隐地响起“栀子花,白兰花,五分洋钿买一朵”的叫卖声的,这样的声音是约定俗成的,也许网上也能搜得到这样的音频。所有的一切,会构成一种考究的“腔调”,这也恰恰是上海人最讲究的地方。上海鱼龙混杂,是一个巨大的移民城市,尤以江浙人为多。而烟熏火燎的生活,是最真实的彼时人间。仔细看旧上海照片,会发现弄堂里,一根竹竿横跨弄堂两边,其实是有人在晒着棉被或衣服的……
对谍战的探索连着对精神的勘测
傅逸尘:一段时间以来,各种雷剧横行,不仅倒了观众的胃口,也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剧本是一群人关在宾馆房间里、纯凭想象甚至“胡编乱造”攒出来的。然而在你的作品中,很多故事和人物似乎都有着原型,你怎样看待生活真实和虚构想象之间的关系?
海飞:原型和虚构并存吧,基本的人物心理、常识性的生活逻辑以及涉及史实的部分必须真实。比如《回家》这部作品,其中涉及的地名全部真实,在创作开始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张路线图,给主人公设定了一条真实的回家之路。小说中所提到的大事件相对真实,如日军从宁波登陆,里浦惨案等。在创作之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宁波姜堰敬老院的一位抗战老兵,在喝下一碗黄酒后,高唱《满江红》,这让我十分动容,仿佛在歌聲背后听到了当年的枪炮之声。而日本军人在战时的种种细节,我都是从一些日本画册、书籍中了解,我沉迷在这种对故旧事物的窥探中,并因此感到无比的快乐。
傅逸尘:谍战题材目前似乎已经进入了瓶颈,下一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你会在哪些方面进行探索或者创新?
海飞:现在的很多谍战或者推理剧,都陷入了一种模式。我想寻找一点“新”的东西,所谓不破不立,所谓不出新,宁不写。我迷恋那种舒缓之中显现的紧张。打个比方,电影《风声》中,是有那种强烈的压迫感的。就是谁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那么《麻雀》也需要是,不停地设套和解套,而且这个设的必须是双重的套,让你解起来无比困难。如果是枪火剧,十分简单,一枪就干掉了你。这并不令观众期待,他们想要的恰恰是,下一分钟是谁死
未曾闻到一点枪声,但是分分秒秒都充满着杀戮。所以《麻雀》的风格要独特深沉、镜头辽阔、画面大气、音乐洋气,让人觉得这是有品质的大片,展现的是最真实的上海滩特工精英的舐血生涯。
傅逸尘:用最通俗的故事表达最崇高的精神,创作主体对谍战剧的探索,从深层次看是对幽微人性心理和复杂精神空间的勘测,亦是对时代主流价值的建构。
海飞:你说的没错。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军旅情结的退伍老兵,每次看到军旅题材影视剧,都热血沸腾,仿佛让我回到那段军旅生涯。情怀是很重要的,很多创作者认为情怀两个字大而无当,看不到摸不着。还有一些编剧认为,情怀是空的,讲好故事就行了。其实不是,情怀是一种精神,一部戏没有情怀,会松垮下来。剧中主人公没有情怀,那就是紧张机械的故事堆砌。而创作者心中没有情怀,作品也会是苍白的。当初写完《麻雀》小说的时候,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替陈深在小说中活了一把,而且我的心中有了一种庄重感,甚至为逝去的英雄在心底里默哀。而在小说改为剧本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加强了情感纠葛,以及设计各种扣和解开各种扣。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一直都是在寻找英雄,需要着英雄。
“谍战”作为一种题材类型,会一直存在并永无止境。谍战剧不光展现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也要传达一种“唯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的崇高感,这种向上的,催人奋进并且感召着人的血火青春与瑰丽人生中,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亟须补充的精神钙质。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