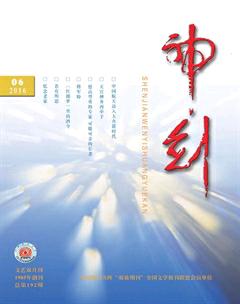一片“兵”心在玉壶
王凤英
于零散阅读随笔之印象,大抵透过碎片化、过滤式的仿日记体回忆或记录,将个人某一经历并体悟作浅浅深深的映像定格或张致。此类情况即便是在已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家那里,其所呈现的富于地域特征的系列作品仍然难祛走马观花或T台观秀之嫌,更遑论籍人生变故、进退得失、精神创伤而郁结莫白,将之诉诸笔端,似自传而失于褊狭、如日记而难以客观表达、仿游记而泛于从容,此类随笔形散意失者不少,不难看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一种高蹈、卓越、温暖人心的激越写作使命。阅读近期王嘉龙的随笔集《林中散记》,其所折射出高蹈的文学暖意和写作关切令人倍觉温暖,由此想到此类写作者所应关注领域的赅心与所深具的文学表达之间,如何达至有意义的结合,与写作者本身至关重要。
独特经历的丰沛表达
相比一般的作家,行伍之人写作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际一些社会认同上的曲折,即便其有“下马草军书”的丰沛文字作前提,也难有与文学掌控能力作有效并轨的可能性,毕竟,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两套不同的語言系统,而后者的情感强调、发声指向、灵魂震颤显然更为柔软和迷人。诚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小众,具一定的群体性,但肯定是不客观的偏见。毋庸置喙,带来这种认知上的本能质疑,与现实中的某些现象吻合度过高有必然的关系。事实上,不只在军队中,社会上亦确有不少官员学者、官员书法家、官员诗人、官员画家乃至官员歌手等所构成的特殊个体,他们的科研实力和艺术素养远不能与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学者、艺术家的能力水平与修养相提并论,这便会在相当普遍的人群中形成一种并不客观的态度,甚或齿冷:他们都不过是挂名或者附庸风雅而已。延伸开去说,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领悟力和艺术情怀,即便难得有那么一些个人爱好,也如戏台上粉墨登场的文臣武将,端着蟒袍玉带、足蹬朝靴,在锣鼓喧天中大呼小叫地走台步,动静很大,其实难有见功夫的唱、念、坐、打。这种识见由来已久,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显然以偏概全,至少是失之偏颇。
艺术从来都是留给有梦想的人的,即便官位多高、年纪多大,只要有一个契机,哪怕是一个词、一句话,就会启动一个按钮,他的心里始终蛰伏的那片独属私人的领地里,风就在那儿、雨就在那儿、花就在那儿,森林也就在那儿,疯长便在意料之中了。无疑问,如王嘉龙谦和、善良、正直、真诚等所辐射出来的人性光辉那样,结合作家的丰富阅历在众声喧哗的当下就是少见的优秀因子,当这些与文学因子邂逅之后,它们很容易就一往情深了:“军书”是他军旅生涯里演唱的高音部,文学则以低吟的方式在他的生命中持续弥漫。我注意到,这部随笔集秉承的气脉一以贯之了他在多年后仍然深藏军号声中的情感关注和精微体察,并以文学笔法和独特视角铺展了其多年森林警察的独特经历,不无清晰地使我们对早期的职业森林警察到后来森警的组建多了富于年代斑驳感的了解。
王嘉龙能够完成这部随笔集,源自他对森警前身、武警、政治的熟稔和经年的深度思考。从“打山火看林子”的职业警察到后来的军旅之路,其间的坎坷和努力、悲喜和幸运、意外和温暖等等,他不仅仅全程在场,而且是其中的重要分子。厚重的生活经历是其创作的独特的优势资源,相较于那些靠写心灵鸡汤、靠故作深沉轻薄文字的写者,他的文字厚重而不失轻盈、深刻而富有历史温度,对于过往年代的体贴和重现,他的笔墨是蘸满深深的情感和生命体温的。所以,因为他胸中自有乾坤在,笔下自然风雨骤。他丰富的阅历使他深切体会到森林警察不一样的存在感,也能够从时代的高度去思考新时期森警的职能走向,更可贵的是通过一个个人物、故事、细节去呈现官兵之间、兵兵之间、军民之间那些温暖与感动,自然地还原了那年、那事、那人,同时还把军人的使命感、光荣感、责任感与激情燃烧的岁月赋予感人至深的意义与高度。这些都是一般的作家、一般的军旅作家所难以企及和具备的。通过《1976,当森警去》《比奇乾更远的远处》《夜宿盲流屯》《安格林军号》《牲灵》《那一隅江山》《青秆子》《与野兽为邻》《从此是干部》等系列文章,试图写下这样一部个人与森警早期历史密切关联的系列作品,在我看来,除了丰沛和强大的记忆沟回的汹涌播放和存储,更要具备将碎片化的历史和人物间的关系富有光泽地串联起来的能力,还要深具独肩负荷的使命意识、文学笔力,做到这其中任何一项当属不易,更何况在繁忙的部队政治工作间隙积零拾碎地著述,委实可贵。
曾几何时,农家军歌式的题材抒写成为一种俯拾皆是的军旅文坛表达,亦成为农家子弟“光宗耀祖”的见证,个人记忆的某一瞬间常常被定格并放大为军旅生涯中的怀想底色,难见接地气、与生活合体的精细呈现,系列化构建少之又少。但王嘉龙从事务性杂乱中能够纵身一跳,便沉入那段独属于他的三维世界,而这方净土世界里他是领主,生活的捆绑远不能让其思想折翼、艺术黯淡,经历过无数俗世辉煌的他,一片兵心仍然在通透的玉壶之中,在独属于他的以“牙克石”为圆心的活动半径里丰沛地表达。可见,一个作家写作的轴心是极为重要的,那是独属于一个作家的生命根基,而那种面对同一个题材跟风似的一拥而上式,是不可能写出独特的东西并流传下去的。
情感带动的情节呈现
缺失温度的文字是支撑不起情感的大厦的,而如何为情感预留足够适合的空间并选择合适的表达渠道,是考察一个作家人格、性格、素养的有效明证。《林中散记》的书名似乎隐含着繁华之后的淡然深意。他的“林中”,从靠近中苏边境的额尔古纳右旗莫尔道嘎镇开始,围绕着牙克石展开了他在东北林区的人生起步剪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地名,还有奇乾、吉落部外站,一直到西藏那曲的戈壁风马,“由一名林业企业管理的警察一步步地转为现役军人”(《新训的日子》)的王嘉龙在多年前的森林里呼吸、成长。读《林中散记》很容易就发现,王嘉龙谦和、仁厚的性格外化在文本中是遍布的从容不迫和悲悯关怀——“立建这一开头不要紧,打草的四十天里,我没有一次不被老兵们接趟子。我的力气和技术确实比别人差了一大截”(《打马草》)。“在我们快下到山根儿的时候,果然发现山脚下有一只狍子在回头瞭望我们。山祥‘嘘的一声就把枪托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随着‘吧勾一声脆响,狍子应声倒下了。哎,真是个傻狍子啊,你不赶紧跑,回头看什么呀”(《第一次长巡》)。这些富有温情的描写展现了王嘉龙写作的特别之处,他在文章中采用小说的叙事和描写技法,摆脱了叙事散文缺少细节支撑的松散,以纯粹的情感带动着情节的自然呈现。这样做显然是成功的,细节的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温情的部分并富于现场感,使文字更好读、更精彩。如《新训的日子》中写到队长严成长搞的第一次全副武装紧急拉动,“我们”这些还没有发下来军装的“便衣警察”洋相百出:
听到队长下达“发现苏修特务,要去抓捕”的指令,有人信以为真地问,有枪没子弹怎么办?有的说,抓特务还背行李干什么?队长说,都给我闭嘴!向右转,跑步走!队伍就在深夜里黑咕隆咚的跑出去了。没多一会儿,好几个人的背包带开了,被子散了,有的就抱着被子跑,有两个人干脆把被子扔在路边不要了。有人鞋带开了,被另一只脚踩上去,一下子就摔了跟头。跑着跑着,突然由前往后一人接一人地传来口令,“往后传,叫指导员到前面来!”口令刚传下去,就见指导员“蹭蹭”地由最后面跑到前面去了。紧急拉动结束后,回到营区讲评时,队长说,看着你们的狼狈相,真是又气又恨又好笑,我下口令是往后传让队伍跟上,怎么就传成叫指导员到前面来了?听了这话,有人在队列里扑哧地笑出了声。第二天,我们见到指导员还憋不住笑,指导员摸摸这个脑袋,拍拍那个肩,也笑着说,你们这帮新兵蛋子啊,是搞我老头子吧?
这段叙述加描写呈现得有趣、形象、精彩,画面感强,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禁不住哑然失笑:队长的慈爱、队友和我的狼狈。文中活生生的人物呼之欲出,而这样极富生命场景的热度,是普通的叙事手法无法真切还原的。表达置身其中的切实感受,王嘉龙首选了小说的技法,事实证明这是不错的选择,文中的描摹刻画细腻传神,全无隔岸观望的俯视姿态,把久经岁月精雕细琢的场面比较完整地激荡出来。这归因于作家心中不停发酵的深情和不乏劲道的语言功夫,情动于衷,笔下必不苍白。其实,王嘉龙能够升温文字,使之激情四溢,与他有意识使用一些恰当的修辞手法不无关系,如形容在零下三十多度极寒天气条件下坐了五个小时敞篷车的“我們”下车时的样子是“像翻麻袋包一样从车上滚下来”(《到“俱乐部”去当兵》),并且在进入房间后,在“炉子的铁皮都烧红”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感到“五脏六腑里还流动着寒气”。这些描写选择了“侧击”手法,逼真地重现了“俱乐部”这个中队最偏远的外站艰苦的程度是多么不可想象,生命遭遇到了死亡的威胁。难得的是,王嘉龙并没有停留在那样的艰苦里不加节制地正面蔓延,相反,文中充斥着满是乐观的精神气度和对待困难时的不以为意:写冻得半死时,战友之间却是互相打趣彼此的穿着打扮像《林海雪原》里的小炉匠,写外站的狗好不容易见到有生人到来时的极度兴奋,写老兵们听到我对“吉落部”的理解时会拿着筷子叮叮当当敲碗表达高兴,等等,王嘉龙无时无刻不建设着饱满丰富的精神面目,并始终用军人乐观主义的深情爱着那些战友、拥抱着那些时光、履行着那些使命任务。这种精神面目在他的另一篇《人在路上》中也有体现:11月的大兴安岭天寒地冻,要去安格林报到,没有车,就在小旅馆里等,一星期的时间在旅馆和车道上来来往往穿梭,终于等到了一辆装载超高的车愿意拉他,他爬到车顶上,“四肢张开趴在帆布上面,两只手紧紧抓着捆帆布的绳子”,风很冷、雪很寒、路面很坑洼,要命的是货物很晃悠,一百多公里路,四个多小时在生死临界点上来来回回,文字透出的绝望令人心疼。但在他的笔下,只强调了他始终抓紧绳子,始终不松手,结尾处仅一笔带过:“一会儿听舵楼里的人下来跟另外的人说,车顶上有个你们森警的人,不知道还在不在。恍惚中,我知道到安格林了,可是我却已经没有自己下车的能力了。”语言的纯净、湿润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阅读过程中惊讶于作者在极端困难下的素朴之志的坚毅,而同时叙事又充满了平静。
语言画面感的精确组装
作家如果具备一定的美学修养,他的语言必然有不一样的气息,会穿透文字本身而呈现出独属于自己的气场,其中语言的纯净就是一种,它让人会非常舒服,这表现在字句间没有任何“端袍正冠”的拿腔作势,更无刻意的打磨装扮,只是笔随手走,手由心定,且富有画面感。我在王嘉龙在《牲灵》中读到他杀猪一节,印象深刻,文本在极为细致地还原场景时流露出富有生活经验的印痕:“我用左手丈量了一下猪心口到脖子下端的位置,再次把牙咬紧了,就把右手里的尖刀狠狠地捅进去,待刀捅到底后,我又用劲儿把刀在里头转了转,那可怜的老猪嚎叫声就由弱而衰,又吭叽了两声就没了气息了,而那猪屁股下倒拉出一摊屎来。”这是因为一个分队要庆祝归建,中队把杀猪的活儿分配给了其所在的分队,但分队的所有人都没有杀猪经验,包括王嘉龙,但他只是“咬咬牙”,赤膊上阵了。上阵后的手法全然像一个专业的屠夫,动作干净、利落。而后,他交代战友去干开膛、掏心挖肺洗肠子的事时,已然用“一个刽子手的口气”进行指挥。如果没有丰富、真切的生活淬炼,绝难勾勒出这样生动传神、用词相当准确精到的画面,他在文中把待宰老猪的绝望、宰杀中老猪的极度疼痛、老猪生命临界到死亡到来时的气息,通过一字一句精确地表达出来,并呈现出了生命终结的真实过程,文字极富画面感。令人吃惊的是,作家下笔的精准及对文字的组装能力,写老猪极度的疼痛是通过极度的冷静来传送极度的残忍的,文本中用到“丈量”猪心口、“尖刀”捅到底还用劲转了转、老猪的“吭叽”及屁股下拉出的“一摊屎”等一系列关键词,这些词汇也把读者极度的恻隐之心同时代入。这里的叙述始自矛盾,而终在有冷静有残忍,做这样的具体描绘无疑会透过坚硬暴露出他的无奈、坚强、担当,而这正是他这样的军旅作家的特别之处。他擅长在缓缓流淌中浪花飞溅,在极碎的小平淡中唱出花腔,在低回的吟咏中飙出高音部。得心应手的现代表述语言,让他的文字灵动、劲道却不暮气,尤为难得。
人物个性的鲜明印迹
无论是写散文还是纪实文学,必要的人物形象还是需要顾及的,哪怕是群像,这既是作家必要的功力,更是一种有意思地艺术呈现的维度。《林中散记》的小说印迹相当明显是不难发现的。在王嘉龙的笔下,所有的人物都是那么可爱、有情有义,但又是那么不同。他们是我的战友,都在充斥雄性的汗味儿里对抗严寒、坚守责任,在最寂寞的时光里疯长着人性的温暖和激情,他们都不卑微,更不怨怼,集体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方外世界:有困难,但无纠结;有寂寞,但无妄为;有失望,但仍坚守;有眼泪,犹自乐观;有死亡,但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如《外站的老兵们》中写到魏天昌要我代他写情书,从一开始“小声地”要求“我”帮忙,及看到情书写得意外的好,就“就高兴地大声说,哎,哎,你这个新兵写情书还有两下子”,“我”的谦和及魏的率真跃然纸上。《别了,吉落部》中写舍不得“我”离开吉落部的山祥,跑了三十多里地的筑路队踅摸回来一袋子吃的;张太平背着枪去冰天雪地的山里打猎;马福田把借来救急的两瓶子油全用于准备一桌子的酒菜上……热腾腾的战友情猛烈而真诚。他的这些小说笔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更显示出了绝对的优势,如《孙队长的故事》一文中,写了一个叫孙相武的老队长“右耳有些背,专注听人说话时,好把右手罩着耳朵侧着摸着头听”,他是一个把忠实纯朴厚道、较真和不苟言笑、文化不高、颇有功夫等复杂特征组装于一身的人,文化不高,能够不耻下问地把文件放到文书“我”的面前用“手指甲勒着印儿”问我怎么念;因为认真,非要在签署单位领导职务姓名时突出他“代理”的真实情况来;慷慨赴副镇长的“鸿门宴”,仍不失原则立场;因为儿时穷困的原因,沾上“胡子”的绰号,“文革”时候当作痛批的罪名;我复习考大学时,他却百般干扰,而我离开中队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他也在退休不久就去世了,“死讯传得不远,丧事办得简单,一个一生风风火火的人却静悄悄地走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孙队长”稳稳地立起来了。而另一个队长金春也令人印象深刻:好脾气、外人面前端点小架子,大家忘记叫他吃狗肉,他就自己带着大蒜来;下属坚持不让出驾驶室位置给他,他就蹬着车轱辘进到敞篷车厢里跟大家挤,丝毫不以为忤。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有发脾气撂脸子的时候:“那笑意盈盈的圆脸一下子就僵住了,接着两个眼角和嘴角耷拉下来,肿眼泡往上抬了抬,眼神肃然地盯着那个场长说——”(《中队部里的人和事》),想想看,紧接着肯定是一场爆发的前奏和积蓄。如此鲜明的人物个性的呈现,即使以小说的标准来衡量亦是相当成熟的,而这却是留存在王嘉龙记忆深处长长的人物画廊里的一节而已,随笔集中透过大量的人物活动、对话场景、情节转换等,聚焦了一群性格通透敞亮、豪爽大气、热力四射、真诚纯粹的军中男儿,他们活灵活现地或列队或便步或奔跑着热腾腾而来,走到我们的面前,与我们一起打狍子、喝酒、吃肉,与我们在冰天冻地里一起战斗、生活,无论是打火作业的英烈悲歌,还是在杳无人烟的大森林里苦中作乐,那群血性男儿艰苦岁月里欢声笑语的乐观精神、浓烈情感、零碎的军营生活角落,使王嘉龙倍感温暖且一直沉醉,并将一直沉醉下去。
从《林中散记》还可以看出强烈的命运感,这不难理解,尤其是像王嘉龙这样有着独特生活经历的一类人,他们有几十年倥偬岁月的丰富阅历和对此必然有的时光回顾,命运感的灌注在经意或不经意的碎片化场景中澎湃不休,所有的人生方程式都会如魔方一样快速拧转、快速组图、快速对接,一切均变得可解,一切均有了答案。《林中散记》中或深或浅的命运感无疑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他思想经历拼接的印迹。其人思、其思深、其深静,给精神的高度以格局,给格局理性的部分以暖色,他的命运感便在这些暖色里成型、发酵,并有了生命的力量和律动。基于此,那些似虚而实的故事一齐灵动起来,那些苦涩与不为人道的故事角落,经过时间善良的关照下,都留给了过去,带进记忆沟回里的都散发着美好的、温暖的、荡气回肠和欢快的音符,而这些,全部在历史的长河里真实地发生过、存在过。
一切善念终将结果。因此,阅读《林中散记》常会想到那些年代不为人知的场阈中发生的事,这除了题材有其独特性外,更要紧的是写了纯真的那群人、那个火热的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故事,链接当下,许多珍贵的东西或多已走样,或从生命中渐渐隐退,但这恰恰成了我们现处这个时代的稀罕之物、崇尚之德。这些都需要细细打捞、留意甄别。但触碰这类元素是需要小心的,需要技巧的,既不能振臂高呼有说教之嫌、露狰狞面目,亦不能雄赳赳气昂昂入侵叙事,理性所处的位置把控须前后得宜,否则,会稀释掉那些打动人心的部分,文字因而会冷峻和僵硬起来。在随笔集中有极少一部分文字理性的经纬度僭越了感性,作家负担过多对人与事件的是非判断责任,这无疑会遮蔽并冷却了情感靠拢过来的柔软度、热度,使流畅的文字顿时拘谨不少、放松有限,一旦发生拿捏失范,文字必会开始失去万种风情,代之以面如枯蒿。我倒是希望他放开一些,忘我一些,在自由的文学世界里安然、放松。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