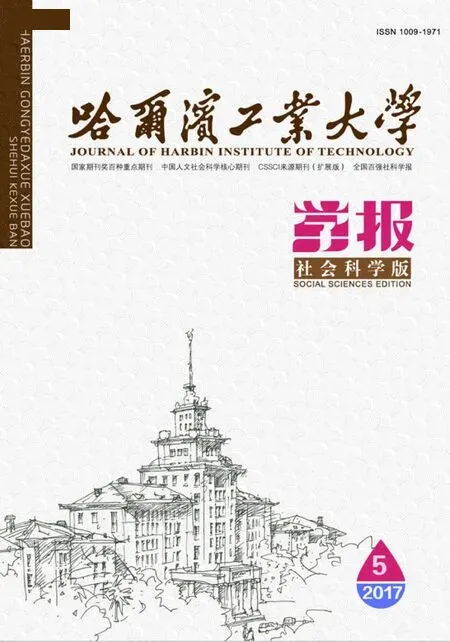以“人”为核心的表达
——李锐小说创作综论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以“人”为核心的表达
——李锐小说创作综论
翟永明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李锐的小说创作一直强调以“人”的表达为核心,自觉甚至偏执地表现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李锐所秉持的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位的人性观,是一种注重人的生存需要、强调人性的自然本性、竭力去除种种遮蔽、张扬人的生命力的人道主义,其间透露出对个体生命的呵护与关怀。但是,李锐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将人还原为动物,张扬愚昧的反智主义,这是因为他的小说反映的是真实存在的生活,其中蕴含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哲性提升。
李锐;人;自然本性;个体生命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自我观照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学自然应以表现“人”、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为最终旨归。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也表明,“文学的存在方式最终取决于人的存在方式,文学艺术领域任何根本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人的理解,任何文化都必然表现出创造者对自我的认识。人们按照何种方式生存与审美,必然与如何认识自己相一致。”[1]因此,文学即为人学这一理念在学界被广泛接受,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2]从宏观的角度看,人的本性即人性是文学的灵魂,从文学的出现到现在,文学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探讨人的性格,描写人的情绪,研究人的内心,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无一不以提示人性为最终目的。所以文学作品必须关注人类心灵的隐密世界,对道德心灵问题进行永恒的探求,实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这是文学创作不可推卸的使命。而那些优秀文学作品也正是因为对人本性的恒久表达,才使我们能够穿越久远的历史时空去领略当时人们的情感与心理状态,在共鸣中实现情感的微妙对接。
李锐的小说创作一直强调以“人”为表达的核心,自觉甚至偏执地在创作中表现“人”,表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他看来,“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3]这就是李锐对文学的理解和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坚持的准则,这种自觉使他的思考和表达始终聚焦于人,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展示人所具有的丰富本性,以自己对“人”及“人性”的独到理解构建起一个血肉饱满、酣畅淋漓的艺术世界,并在这种构建中传达着自己深刻的心理体验。
就李锐的小说创作而言,“人”的概念既不是空洞的躯壳,也不是失却了时空背景的“塑造”,更不是被涂抹了某种油彩的“非人之人”,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富含情感的个体的人,正如他所说:“人只能是人自己,人只配有人的过程。”[4]由此可以看出,李锐所秉持的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位的人性观,它与抽象的概念无关,是一种注重人的生存需要、竭力去除种种遮蔽、张扬人的生命力的人道主义,具体地说,是强调人性的自然本性,避免社会性对自然性的压抑,张扬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并以此为基点,维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表现出对生命个体的呵护与关怀。
一、人道主义的社会伦理表达
在李锐的早期作品里,即表现出了一种对“人”的关注,这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潮流相应和的。在当时人们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在痛定思痛的反省中,人们意识到造成这场灾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人”的漠视,对个体情感的抹杀,这样的反思结果使得当时产生了重视“人”及“人性”的文学潮流,这一潮流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作家,李锐自然也不例外。《月上东山》批判了古老中国的生育观念,在一个家庭里,能否生育将直接决定一个女人的命运,兰英在刘家地位的戏剧性变化实际上正折射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对女人的漠视,女人更多的是被当作生殖的工具来繁殖后代,她们生命的意义不在自身,而在她们的生育能力,尽管作者写得较为内敛,但很明显有强烈的感情蕴含在内。《丑女》中的丑女只因在长相及婚恋上与别人“不一样”,便遭到了村里人的嘲笑与指责,反映了乡村习惯势力对个性的扼杀。而《五人坪纪事》与《指望》却表达了作者在城乡问题上的思考。在当时,城乡差异已开始显现,城市的迅猛发展和乡村的相对落后使得人们的观念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李锐就是在这种变化中寻求着对“人”的表达。《五人坪纪事》中当过兵见过大世面的狗蛋渴慕过城市的文明生活,但是乡村凝滞的生活环境根本不接受他那些城里人的行径,一口普通话因为相亲问题而彻底消失,漂亮的黑塑料凉鞋与白丝光袜子也在一次滚坡后被五人坪男女老少祖祖辈辈都穿的方口鞋所取代,更富戏剧性的是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打火机最终被最原始的火镰所战胜,所有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凝滞的乡村生活中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甚至滑稽可笑,强大的乡土生存方式再一次显现出它的力量,顽固地抵制着城市文明的入侵,狗蛋最终被这种充满惰性的生活所同化,回到了千百年来重复不变的生活轨道,心安理得地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指望》则表现出了对妇女生活道路的思考,极端的物质贫困使得村子里的人都渴望走出大山,过城里人的生活,女人们实现这种愿望的唯一途径是嫁一个城里人,但是由于男尊女卑的意识的存在,她们的命运并未真正改观,嫁到城里的小玉的经历暗示,女人只有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才能在精神上与男人实现平等,才能真正摆脱前辈女人的依附命运。中篇小说《凤女》及《野岭三章》沿着这一思路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野岭三章》用传奇的笔法描写了三代女人的悲惨命运,相似的婚恋道路暗示了传统的世代相袭与永恒束缚,在那样滞闷的环境中,女人要不屈服,要不沉沦,即使竭力挣扎,结果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凤女》便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凤女由最初的屈服到大胆的反抗,在经历了数次的打击后不得不听任命运的安排,直至最后从内心里安于现状,小说最后凤女的一句“年轻人胡闹吧”直接道出了女性解放道路的曲折与艰难,传统中国文化像一张网,使得无数鲜活的生命泯灭其间。与这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同,李锐的笔触还深入到当时的现实生活。《小小》与《“窗听社”消息》皆是对官僚主义的抨击,小小的死与陈主任的被排挤都揭示了官僚主义对人的残害,进而对麻木、沉闷、愚昧的生活进行了批判。
尽管李锐早期的小说在对“人”的表达上不乏深刻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这种深刻的背后存在着当时流行的创作理念。虽然李锐并没有直接参与创作“伤痕”“反思”小说,但在李锐小说创作风格形成之前,受当时创作潮流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现实弊端的揭露都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合拍,相异的创作背后隐藏着相似的社会性眼光。传统文化、封建迷信、城乡观念、官僚主义等这些当时的主流创作话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深刻性,但它反映出的是作家们对人的社会性的强烈关注,尽管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人的吃、喝、穿、住以及性的描写,但这些描写只是为了人的社会性表达而存在,作品的关注焦点依旧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而未回到人的最本真的层面。这种对人的社会性的偏执表达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虽使当时的创作对人性的表达不乏深刻,但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漠视使这种深刻大打折扣。但是李锐的某些作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这种社会性表达而表现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存在,《丢失的长命锁》表达了人摆脱束缚走向成熟的艰难,《霉霉的儿子》中自然淳朴的生活状态显现出人的一种强劲生命力。此外,山乡农村生存方式的沉闷凝滞及对现实生活的强大制约力、人们难以压抑的欲望渴求都显现出向《厚土》凸显人性的自然本性的过渡痕迹。
二、以生命为本位的人性展示
《厚土》的出现标志着李锐小说创作风格的初步形成,这部以山西贫瘠的吕梁山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系列,真实地表现了实实在在的乡村生活与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吕梁山中的人们生活极其艰苦,物质的极度匮乏使人们挣扎在生死线上,生存成了第一重要的事情,其他与生存无关的事情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生活。于是“食”与“色”便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厚土》诸篇就是紧紧围绕这两大欲望来表现人最基本的自然性需求,展现原始的人类生存。
在《厚土》中,“贫瘠、荒芜、苍凉、干旱”这些描述生活环境的词汇随处可见,严酷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当地人的极端贫困,在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上,即使超常的劳作也仍然无法克服饥饿的威胁,人们匍伏在大自然脚下,像动物般苟延残喘地生活着。“食”的方面的欠缺,使得人在“色”的欲求上显得触目惊心。《厚土》中有很多性的描写,但人的这种最原始的本能在苦焦赤贫的乡村生活中以扭曲的形态而存在。《锄禾》《驮炭》中苦难的生活使女性成了一种物质化的存在,可以当作生产资料来交换;《篝火》中强势人物可以对女性随意欺辱与公开占有;《青石涧》《二龙戏珠》中由于性的饥渴又无力娶妻造成兄妹父女乱伦;《同行》中出于生存与繁衍的本能而忍辱负重;《眼石》中互换妻子睡觉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性的畸形存在折射出吕梁山民在最低生命需求层次上挣扎的不幸命运,一切所谓的道德、自尊在这里全是多余,贫困的生活使人们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人们只是凭着一种本能为了活着而活着。
正是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描绘中,《厚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未加掩饰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真实生存形态极富震撼力,其所带来的厚重让一切浅薄的理性认识无处现形。这样,一贯为我们所重视的人性的社会本性在《厚土》中被推成了远景,甚至只是点缀,它们的存在根本无法对“厚土”般的生活产生影响,革命、主义、理想、激情等等话语在这里都被消融,这也就是《厚土》时代背景之所以模糊的原因。《锄禾》中人们对黑胡子老汉戏文的喝彩与对学生娃所念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嘲笑形成鲜明对比;《古老峪》中小李对“她”的吸引根本不是他所念的文件,而只是觉得他“念得好看”;《合坟》中村里人对死去的知青的纪念方法居然是为其“配干丧”;《驮炭》中知青的俄罗斯革命歌曲最终被乡村略带“荤腥”的山歌取代。存在于“厚土”之外的人或事只能是呼啸来去的过客,他们的被提及往往也只是被当作谈资,面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他们的力量如此渺小,难以留下太多的痕迹。
如果说《厚土》充分凸显了人性的自然本性,表现了人的自然生存状态,并以此为基点,将人的社会性只设置为故事背景的话,到了《无风之树》及《万里无云》中,这种社会性变成了一种与人性自然性对抗的力量存在。《无风之树》中,作者建立了一个奇异的乌托邦,在这个世界里,人在物质上的贫困自不必说,世世代代都是瘤拐的生理缺陷正是贫穷生活在人们身上打下的烙印,贫穷几乎使矮人坪的所有男人都成了光棍,在这种难以排挤的饥渴中,最后只能由队上出一袋玉米买了暖玉。从道德角度讲,“公妻”是丑陋而且有违伦理规范的,但矮人坪的男人们在真挚地呵护暖玉方面又显现出对人性的尊重,在对苦难的抵制中,这种相濡以沫的情谊维护着一个自在的民间世界,这个世界按照一种奇异的法则获得了一种平衡。但是,权力者苦根儿却作为一种异质打破了这种平衡,他代表了另一种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在他身上,阶级性已占据了他所有的思想,他的意图就是要整暖玉的黑材料,打破矮人坪特有的生存方式。作者用略显夸张的笔法描述了苦根儿严厉的生活戒律和不近女色的洁癖,在无限上纲的革命美学憧憬中,他作为“人”的情感已被完全抽干,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符号而存在。因此,矮人坪社会虽不合人伦,但却充满了人味,苦根儿虽以理想和信仰为依托,却以对生命的忽视为代价,两者对照,显现出李锐对人性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态度。此外,作品中的角色多有第一人称现身说法的机会,唯独苦根儿的章节,由叙述者从旁代言,更显现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同样,《万里无云》中作为山村唯一的文化人张仲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然没有从当年的知青生涯中走出,他的独白大量援引毛主席诗词及革命口号,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另一个苦根儿。
与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不同,他的“银城系列”对“人”的表现是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强调来实现的。《传说之死》与《旧址》中李紫痕对个体生命的维护与捍卫表现得最为明显与自觉。李紫痕不懂政治,也不善交际,她行为的准则只是依据善良的天性与对待生命的态度,即使在压制生命的强大力量面前,她也是用对每一个人的爱来呵护着趋于绝境的生命。为了扛起家庭的重担,她毅然选择了吃斋念佛;为了救从事革命活动的弟弟,在最严酷的环境下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初她顶着压力收养了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文革中又以悲悯的情怀收容了冬哥。这所有的行为在那些为现实利益争得你死我活的人看来近乎愚昧,但她无疑让饱受摧残的生命获得了一丝安慰。她虽然不理解革命,但她却比更多的革命者洞察了生命的事实。正是这种质朴的生命观念,才使她蔑视一切轻视生命的“理想”与欲望,尽管她最终无法挽救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但她试图维护个体生命尊严的行为却演绎着对生命本身的敬意。与《旧址》相比,《银城故事》却以大力彰显民间世界的生存状态来表现对遮蔽与禁锢个体生命势力的抵抗。小说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表现民间社会,描写了银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不惜笔墨去展示别具银城地方色彩的牛、竹以及饮食习惯(如火边子牛肉等美味的炮制过程)。卑微却知足常乐的牛屎客,狡黠又不乏同情的蔡六娘,质朴憨厚的汤锅铺郑氏父子,低贱但又不敢小觑的乞丐势力,都构成了银城日常凡俗的生活场景。他们的存在不仅显示了李锐的民间立场,更表现出作者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正是对这些历来被理性历史遮蔽的个体的大规模展现,才揭示了历史烟云深处的诸多秘密,进而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念。
三、基于真实生存的哲性提升
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李锐对人性自然性的强调会使人产生一种误解,那就是会认为他的小说创作着重表现的是人的生物性本能,与文学艺术实现对人精神的提升、净化人的心灵、引领人类逐渐摆脱自然与社会的束缚、走向更高境界的宗旨不符,甚至还会误认为他的作品意在将人还原为动物,显示出张扬愚昧的反智主义特征。这实在是对李锐作品的一种误读,没有领会李锐小说的深刻用意。李锐的小说创作是对长期以来人性的社会性对人的自然性压抑的一种反拨,而在他笔下,并不是彻底否定人的社会本能,他对人的大部分社会性是肯定的,他所批判的是极端化的社会性,是那些为了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而无视人的自然本性的社会性。同时他的作品也不是纯粹地表现人的吃、喝、住、穿以及性这些原始的本能,而是有着更多潜在的精神性因素存在。
首先,李锐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一点上与寻根文学不同。尽管寻根文学也是从原始形态的生活中寻求灵感,但是为了揭示民族心理的深层积淀,展示传统文化的优根与劣根,往往将所表现的生活抽象化甚至怪异化,虽然这会使作品的意蕴含量增加,但现实生活的失真也会使作品失去着力点,导致文本意义只是悬浮于作品表层而未真正深入下去。李锐的作品则不同,不论是严酷的自然环境描写,还是历史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以及生活于其间人的心理状态都非常真实,展现了人本真的生存状态。这些描写足以使人心灵颤栗,却又让人欲哭无泪。《锄禾》中民间社会人与人特有的关系纠结以及与外界社会的隔膜,《选贼》中“官”本位思想在民众心中投下的阴影,《驮炭》中下层社会男女之间奇异的情感关系,《送家亲》中祭神仪式的阴冷与女人内心的悲痛,《看山》中农民对生之无奈的忧伤感触,等等,都极为真实,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半点不掺假的吕梁山”[5]。在李锐这些客观冷静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正是生命窒息的全过程和绑缚在这块厚土上的农民实出于无奈的内在心理特征。
其次,李锐小说在尽力展示底层人的吃、喝、住、行,表现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是,新写实小说在表现日常琐碎的生活时,由于作者采取的是情感的零度介入,而且在削平深度模式的叙述中小说很难有升腾的力量。李锐作品的着眼点虽也是人的日常行为,但是在其中却蕴含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这种情怀使他的小说并没有始终低徊于人的生物性本能,而是有了很多情感亮色。《厚土》中作者的叙述口吻虽极其冷峻,但却并不等同于冷漠,在对那些令人心惊的苦难和凝滞的生活展示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一种绝望与悲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直接来源于作家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人道主义关怀在《无风之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作者所建构的矮人坪的畸形世界里,拐叔为了维护某种尊严的死与村人不顾苦根儿的威胁隆重地为其送葬的行为寄托着作者不尽的同情,尽管这种同情是暗潜在作者冷静的叙述中。正是由于这种人道主义观照的暗中存在,才使李锐小说中的人虽过着动物般的生活,但他们的日常行为却包蕴着丰富的“人”的情感与意义。
再次,由于李锐是个理智型的作家,因此他的小说作品中往往蕴含着很多理性的思考,这些思考使他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从而拥有了某些哲学意味,在这一点上又与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欲望化写作区别开了。应该承认的是,90年代出现的大胆表现人的物质及生理欲望的潮流,是对长期被禁锢的人的正常生理需求的敞开,表现出在市场经济下人对自由的向往。但是由于商品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对人的欲望的表达往往会成为一种商品包装,很容易沦为低层次的感官享乐的追求。李锐小说作品中对人的欲望的表达也很多,尤其是关于性的描写存在于他的大部分小说中,但是这些描写并不是简单的生物性需求,而是蕴含着很多哲学意味。《无风之树》中暖玉与矮人坪男人们有悖于人伦的性关系中蕴含着一种救赎意义,她是矮人坪唯一的亮色,不仅满足着那些男人们的性的欲望,而且更在精神上给他们以希望,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维护着人的情感与尊严。而《厚土》系列中的《秋语》与《看山》,则在强烈的生之欲望的背后有着更多生命意义的思考,他们在那“凝冻了一般,没有一丝的生气和活力”的日子里年复一年地衰老直至消逝的感受和那生于斯、也将死于斯的无望的悲哀,传达出的正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凉情怀,那“厚土”般凝滞的古老生活方式终要以最原始的方式,涵蕴一切,然后一切重归于寂灭。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李锐是在追寻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的和谐共存,他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属性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但却并未走向极端。在他的小说作品中,人的自然本性的表达并不是完全生物性的,对人的社会属性也不是简单否定。正是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李锐创作实验的勇气,也许这种探索永远找不到答案,作品中的表达也无法达到非常完满,但李锐用他自己的方式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显现着独有的价值和魅力。
[1]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4.
[2] 钱理群.沈从文《看虹录》研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2).
[3] 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09.
[4] 李锐.厚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261.
[5] 李国文.好一个李锐[N].文艺报,1987-01-03.
Abstract: The novel creation of Li Rui is stressed continuously with expressing to the nucleus of"person", the rich nature and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What Li Ruiadhered to is a kind of human nature sight that takes life as standard, a kind of the humanitarianism to lay stress on the person's existence in the needs and the natural instincts of human nature.The humanitarianism, which goes excluding all sorts of what hides from view and makeswidely known the life-force of person,discloses the blessing and the loving care to the individual life.But the stressing of the natural instincts of person does not signify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al condition person to the animal and the ignorant anti-wisdom doctrine.The novel creation of Li Rui reflects the true life that exists, which contains one kind of the humanitarianism feelings aswell as the wise nature.
Key words: Li Rui; person; the natural instincts; individual life
[责任编辑:郑红翠]
Expressing to the Nucleus of“Person”——Survey of LiRui’s Novel
ZHAIYong-ming
(Literature Colleg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
I209
A
1009-1971(2017)05-0094-05
2017-06-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众形象’与1980年代社会转型——1985年前后的中国文学研究”(13YJC751074)
翟永明(1976—),男,山西大同人,副教授,博士,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