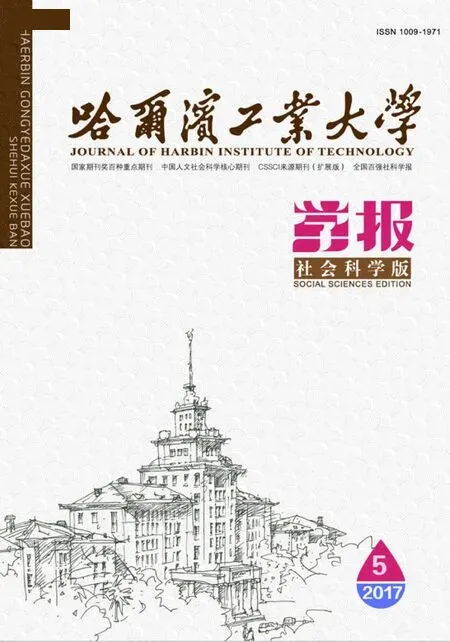“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
李占荣,魏腊云
“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
李占荣,魏腊云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杭州310018)
“多民族国家”的法治建设必须以宪法理念作为支撑,在解决出现的民族问题时,必须有相应的宪法理念回应。“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包括三个层次:首先体现在“良法之治”和“良法善治”互存的“良善法治”理念上,其次体现在“硬法之治”理念和“软法之治”理念并举的“软硬混治”理念上,最后体现在“民族自治”理念和“民族共治”理念共存的“整体法治”理念上。其中,“良善法治”理念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的核心,“软硬混治”理念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的根本,“整体法治”理念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的升华。
“多民族国家”;宪法理念;良善法治;软硬混治;整体法治
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中国具有“多民族国家”的属性。事实上,这种属性由我国《宪法》序言所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多民族国家”的法治建设必须以宪法理念作为支撑,在解决出现的民族问题时,必须有相应的宪法理念回应。“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良善法治理念,二是“软硬混治”理念,三是“整体法治”理念。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转型时期,良善法治理念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的核心,“软硬混治”理念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的根本,整体法治理念是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的升华。
一、“良法之治”和“良法善治”理念互存的良善法治理念
良善法治理念是良善和法治两者的有机结合,良善是价值追求,法治是根本目标,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良善法治理念内在地包含了“良法之治”和“良法善治”理念,“良法之治”是“良法善治”的前提,“良法善治”是“良法之治”的核心。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突出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良法善治,并且有些学者认为,良法善治的层次应该高于良法之治。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良法之治”的角度,还是从“良法善治”的角度来解读法治的内涵都没有错,良善之法是治国的重器,良法善治是治国的总目标,二者是互相包含的关系。
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理念首先体现在“良法之治”和“良法善治”互存的良善法治理念上。治理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是良法之治,而良法是那些最大程度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和关怀、确保少数民族各项权利、贯彻民族平等并且具有科学性的法律。也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认同并有效达到良善法治的目标。
(一)“良法之治”理念
“良法之治”的前提是“良法”,到底什么是“良法”?古今中外很多学者都有过自己的解读。许多法学家对良法问题也颇为关注,提出了“良法之治”的宪法理念,并且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判断“良法”的标准。第一种观点认为,“其一,良法应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法律;其二,良法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反映多数人意志和愿望的法律。”[2]第二种观点认为,“良法应具有民主性、科学性、道德性等三重标准”[3]。第三种观点认为,良法应是为人民谋取幸福、人民竭力拥护并保证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法律。“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4]笔者认为,良法至少应体现如下宪理:平等关怀、保障人民权利和具有科学性等。
第一,解决民族问题的良法必须体现民族平等的宪理。1954年《宪法》第3条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第8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宪法》还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规划地方建设和公共事业和审批预决算时,必须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宪理,民族平等的宪理为随后的宪法文本所沿用。即使是深受诟病的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也在总纲中使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表述。现行的1982年《宪法》则在序言中宣告,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应反对民族主义,包括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1982年《宪法》总纲第四条同样使用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表述,并且明确了国家要维护“民族平等关系”,禁止民族歧视。现行《宪法》第34条规定了年满十八周岁公民的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国宪法文本的历史沿革,可以大致勾勒出民族平等的宪理。体现于宪法中的民族平等的宪法观念恰恰是良法正义性的体现,只有将民族平等的宪法观念贯穿于以宪法为首的各种法律制度中,法的正义价值才能得以体现,良法之治也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第二,解决民族问题的良法必须体现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宪理。良法之治要求良法必须具有人民性的品性,即法律必须体现对权利的关怀。重视少数民族权利的宪理,首先体现在确认少数民族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平等,尤其是政治权利方面的平等。自治权是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因此1954、1975、1978和 1982年《宪法》均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规定各有关民族在各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自治机关除了行使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之外,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宪法中还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规定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的自治机关中,各有关民族都有其本民族的代表。其次,重视少数民族权利的宪理还体现在保障各民族平等的被选举权和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82年《宪法》第59条第1款规定了各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大中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第65条第2款规定了自治机关的政治权力。再次,重视少数民族权利的宪理还体现在确认少数民族的经济权利。如1954年《宪法》不仅在序言中明确国家要照顾到各民族经济文化建设需要和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的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第70条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地方的财政”。1975年《宪法》第24条则明确规定要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1978年《宪法》第40条和1982年《宪法》第4条第2款都明确了国家应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尤其是1982年《宪法》第117条和第118条明确授予自治机关财政自治权。最后,重视少数民族权利的宪理还体现在确认少数民族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1954年《宪法》第3条、第77条,1975年《宪法》第4条,1978年《宪法》第 4条,1982年《宪法》第 4条、第121条都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除1975年《宪法》外,还都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在最根本意义上被认定为属于少数民族的人的个体的权利。宪法同样保障对于这种个体的文化权利,1982年《宪法》第134条还将少数民族的整体文化权利进一步细化为对个体的文化权利的保障,细化为个体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1982年《宪法》第119条规定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
第三,解决民族问题的良法必须体现科学性的宪理。良法的科学性体现在立法必须符合国情、民情。庞德指出:“法律……是一种能努力满足众人的需要及欲望,能为众人所分享生活必需品一样的工作,这就是因为法律的目的旨在实现社会正义。”[5]1954年《宪法》序言确认了我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一国情,1975年《宪法》第4条、1978年《宪法》第4条和1982年《宪法》序言也明确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良法的科学性体现在法律体系的完备性上。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宪理在有关民族自治的法律法规中得以充分体现。《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选举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不仅确认了民族的平等权,而且为了保障民族自治权,还确定了自治区域内汉族与少数民族权利的差异性,如政治权利的差异性、公民个体权利的差异性(受教育权利、生育权等方面的权利都予以特别保障),体现了有关少数民族法律规则体系的一致性及内容上的全面性,为少数民族提供了满足个人生活意义的必要保障。
(二)“良法善治”理念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但仅有良法之治,若没有良法善治之宪法理念,也难以达到法治的目的,因而除了要有良法之治的宪法理念,重要的是需要良法善治的宪法观念。
近年来学者们颇为关注善治的概念,并展开讨论。有关善治的内涵及善治与法治的关系等,学者们的观点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善治要高于法治,是法治的目标;还有学者认为离开了法治不可能有善治,善治就是法治,法治才是核心。学者们在探讨良法与善治的关系时,能够形成共识的是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善治是良法的目标。但良法善治究竟应包括哪些内涵?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分别提出各自的见解。有学者提出:“关注民生、保障人权的法治,就是良法善治。”[6]首先,善待每一个人需要我们国家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人权,为此需要从立法上完善少数民族等少数人的权利体系,健全权利救济制度和对少数民族的法律援助制度。其次,平等关怀与尊重公民,尤其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平等关怀与尊重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作为,实现少数民族公平的机会均等。还有学者提出,“履行善治需要涵盖五大基本要素: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共治是善治的优势,自治是善治的基础,法治是善治的核心,德治是善治的保障”[7]2。有学者提出善治是“民主治理、依法治理、贤能治理、社会共治、理法合治”[8]。上述对良法善治内涵的揭示不无合理之处,善治并不是只强调德治不要法治,而是必然包含法治,或者说法治应该是善治的核心。
综上所述,良法善治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内涵:
首先,良法善治的前提是良法。如前所述,良法必须体现民族平等、人民性和科学性等特点,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治理依据上,所制定的法律必须充分符合我国的国情,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利益需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及平等保护统一于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民族概念之下的所有多元文化民族,所制定的法律在体系上必须是完整的,且逻辑上是自恰的、无矛盾的。
其次,良法善治的根本是民主之治。这就要求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事务及解决民族纠纷问题时必须充分发挥各民族参政议政的积极主动性,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政治管理的权利得到平等的关怀与尊重;“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基本原则必须在法治实践中得以落实,民主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这就要求将民主法治化。人民可以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有各少数民族的适当代表)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并通过法律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治理国家的各项管理权力。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人民的法治才是真正的善治,民主法治化还要求将民主协商引入社会的公共治理中来,尤其是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尚须注意让公共治理与民族自治结合起来,强调各少数民族共同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之中,必要时运用民主协商的机制。
再次,良法善治的基础是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是民族区域自治,要求结合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特点,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进行自治。民族自治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其最大优点在于所有的民族都能自觉自主地依法参与社会治理,这样能够有效地分散一部分政治权力,实现政治责任的转移,同时又能根据本民族特点保持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实现国家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民族自治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手段,是针对特定群体的特殊治理方式,能够彰显以人为本的精神,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
最后,良法善治的特质是共治。共治是现代治理的核心特质,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下,共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体现,反映人民的意志,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共治既包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民族事务,包括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也包括在治理民族事务的内容上的广泛性和治理方式的多元性。
总之,良法之治与良法善治是互为基石的概念,它们互相包含和互相补充,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问题,没有法治的善治有可能因善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而导致人治,没有善治的法治有可能因缺失民主共识的善的价值追求而导致暴政。“法治与善治互相保障,法治需要善治形成善政局面,善治需要法治维持社会秩序,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7]10
二、“硬法之治”理念和“软法之治”理念并举的“软硬混治”理念
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法治进程中,我国经历了从硬法之维到软硬混治即“硬法之治”理念和“软法之治”理念并举的过程。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0]进一步改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11],树立起依法治理的宪法理念,首先要树立“硬法之治”的理念,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
(一)“硬法之治”理念
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以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做到有“法”可依,并切实实施民族法律法规,确保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并运用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做到有“法”必依。这里所说的“法”,首先是指“硬法”。因此,在对待民族问题上,我国首先从宪法上对民族自治制度予以确认,随后又将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具体化,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要求各级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重视民族法的立法工作,注重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修改与完善,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但“硬法之治”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硬伤:硬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宜进行频繁的修改,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快,因而内容上有可能不适应社会的变化,出现滞后性;在调整对象上存在非全面性即无法覆盖所有的社会关系等,这些势必导致法治的真空。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又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他方面的特性,仅仅依靠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硬法来调整民族关系,解决在民族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其效果是不理想的。因此,在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时,需要借助软法等其他规则。
(二)“软法之治”理念
随着软法理论的兴起,为原本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就已经存在的软法,如广泛活跃于我国民族地区、并对当地产生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习俗性规则等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尽管至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中的“硬法”和“软法”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并没有达成普遍共识,但是随着学者们讨论的深入,软法的特征得以逐渐明晰:一是软法不具有硬法的强制性约束力,而只具有“软”约束力,在某些情况下,软法甚至具有比硬法强的实效。二是有些软法不具有完整的逻辑结构,而只具备三要素中的一项或两项即行为模式及条件假设。三是软法的制定程序不严,其产生往往通过社会的自然演绎或人为协商,不需要严格的立法程序,而不是由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来创设,其生成机制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四是软法一般不具有直接的司法适用性,但由于软法的灵活性、多样性、不断变动性等特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硬法的硬伤,适用于其他方面。如2005年在香格里拉县小中甸乡发生的“千湖山事件”,就是由于软法缺失而引发的事件,即在对被雪域藏人尊为神山的“千湖山”进行现代化开发时,未与当地藏族群众进行民主协商。因此,对民族自治地方进行行政执法、司法和社会治理时,应当适当引入软法,在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国家法与传统习惯即引入软法,往往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随着对软法认识的深入,人们已逐渐接受“软法之治”的法治理念,在解决复杂多样的民族问题时,普遍意识到“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并举的理念才是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理念。“软硬混治”的理念在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得以体现。“以软法与硬法混合治理的方式,整合民族地区国家与社会中的多种资源,发挥现代法治与传统治理模式两种制度安排的潜力,能够回应民族地区更为复杂的多种主体的多种利益诉求,能够全方位地实现民族地区的法治目标。”[13]笔者非常赞同罗豪才指出的:“法治现代化既要建设法治国家,更要建设法治社会;既要依靠国家来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更要依靠社会依据符合法治精神的软法来自我规范。”[14]有些学者认为“软法之治”优于“软硬并举”。事实上,无论是硬法之治,还是软法之治,都需要国家与社会的珠联璧合,“软硬并举”的混合治理则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软法之治”与“硬法之治”两种法治模式的潜力,全面回应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的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有效化解复杂的民族矛盾和解决民间纠纷。
三、“民族自治”理念和“民族共治”理念共存的“整体法治”理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建国以来就坚持的一项基本政治法律制度,与我国根基深厚的民族自治理念密不可分。随着西方国家“民族共治”理论的引入,出现了“民族共治”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争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持赞同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共治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后自治’民族政治的必然和合理发展。”[15]101反对民族共治的学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法律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既能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又能维护国家统一。笔者认为,虽然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政治法律制度,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民族共治。
(一)“民族自治”理念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自治”是指“民族、地区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之外,对自己的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16]。在人类社会有关自治的实践中,自治主要指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地方自治与社会自治,自治权则主要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依照宪法和法律,地方的公民作为政治主体行使相对独立的组织、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这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17]。有学者将自治权民族实现自治的形式划分为三类:“独享型民族自治权、结合型民族自治权以及融合型民族自治权”[18]。据此,中国的民族自治权属于“结合型民族自治权,即民族自治权与地方区域自治权的结合。我国建立起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其最典型的体现”[19]。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不仅聚居的民族能享有自治权利,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有自治权利,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受到法律制度和政党政治两个层面的制约,根据《宪法》第116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和《立法法》第75条的有关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要发生法律效力尚须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即实行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和批准权分开。因而我们在解决民族问题所持的民族自治理念绝不是自决权民族,自决权民族的概念属于“政治民族”的概念,民族自治理念中的民族属于“文化民族”的概念。因此,“民族自治”决不是要确立各民族的极端自治,而是以共和为目的的自治,或者说民族自治权是受到政党政治和法律制约的民族自治。区域自治权亦受到国家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制约,如在同一个自治区域内,各少数民族权利与汉族权利存在着差异性,自治机关在录用工作人员时,对少数民族予以适当照顾,从而保障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在受教育权利方面,对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加分政策等。
(二)“民族共治”理念
“民族共治”,即以各民族的和谐共存作为前提,并服务于民族共和的目的,各民族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共同平等治理国家,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促进民族权益的均衡发展,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共治是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在确认民族聚居地方的自治权时,也规定了国家与自治地方之间的权力与责任,这些实质上就是民族共治。民族共治可分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共治和民族聚居区层面的民族共治,而第二个层面的民族共治其实包含了民族自治。“自治权利:民族共治的核心。”[20]“当代国家制度下的民族自治,是少数民族参与国家管理和地方政治生活的组织保障,是以民族之间的共和为目标。民族共治有两个层面:一是各民族对国家的共治;二是有关民族对民族杂居地区的共治。”[15]95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多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活动过程的矛盾也有其必然性,因此,在治理国家各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各民族的对话与协商,这一过程其实也是共治的过程,而在处理单个民族内部事务问题时,也需要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同时,实行民主管理,民族内部的民主管理是具体化了的民族共治。民族共治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民族共治的宪法基础。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这一宪法原则,该规定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集中体现,人民通过人民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少数民族通过本民族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应当有适当比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归根结底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形式来参与、管理、决定和监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民族共治是“民族权利平等”的根本保障。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所有公民,无论其属于何种民族,只要是该国公民,不仅平等地享有公民的经济和文化权利,而且平等地享有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的政治权利。所有民族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民族自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民族共治则能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任何国家中实行自治的任何民族,不可能只是安于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同时需要协调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21]。因此,各民族之间进行充分的对话与协商,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则是民族权利平等的集中体现。
在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的关系问题上,法治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必须整体性地把握法治的规律,借助系统理论来理解民族自治和民族共治,坚持“整体法治”的理念。所谓“整体法治”,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等理论,从整体上认识法律制度,把握法治发展的规律,从而做到在整体上把握局部,在局部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与突破口,以推进法治建设的整体进步”[22]。民族区域自治只是确立政治单元,民族共治则是建立政治关系,民族区域自治是从地方的角度即部分而言的,民族共治则是从全国范围而言即整体的角度。民族自治存在于民族共治的整体方案中,并且在民族共治中体现其意义和功能。可见,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之间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我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民族自治是民族共治的前提,民族自治是有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和实现民族共治的途径和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民族共治则包含了民族自治,民族共治是现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实行民族自治的理想,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二者是和谐发展的。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1).
[2]李龙.宪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99.
[3]赵震江.法律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26-327.
[4]毛泽东早期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1.
[5] ROSCOE POUND.Sources and Forms of Law[J].21 Notre Dame L.Rev,1946,(27):71-72.
[6]张文显.民生呼唤良法善治——法治视野内的民生[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9):12.
[7]李龙,郑华.善治新论[J].河北法学,2016,(11).
[8]王利民.法治:良法与善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2):11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10]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11]王允武.民族事务法治化:民族自治地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可行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82.
[12]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9.
[13]周真刚.软法视野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J].学术探索,2011,(4):93.
[14]罗豪才.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72.
[15]朱伦.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小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745.
[17]杨成铭.人权法学[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258.
[18]李占荣.宪法的民族观及其中国意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69.
[19]任玉翠,李占荣.论民族自治权的三种类型[J].民族论坛,2016,(2):30.
[20]乌力更.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权利与少数民族[J].理论研究,2003,(4):34.
[21]朱伦.论民族共治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理[J].民族研究,2002,(2):5.
[22]石文龙.整体法治论[J].东方法学,2013,(2):49.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must be support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idea.In resolving the ethnic problems, theremust be corresponding constitutional ideas to respond.There are there levels of conceptof“multi-ethnic state” to solve the national problem:the first is the concept of“good rule of law” and “good governance”;the second is themixed governance concept of“hard law of governance” and“soft law of governance” ;the last is the“overall rule of law” conceptwhich is coexistence of“national autonomy” concept and the “national co-governance”.The concept of“good rule of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is the core of the constitutional idea to solve the national problem.The concept of“soft and hard law mix” is the fundamental idea of solving the national problem.The concept of“whole rule of law”is the subli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idea to solve the national problem.
Key words: multi-ethnic country; constitutional idea; good rule of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soft and hard law mix;overall rule of law
[责任编辑:张莲英]
The Constitutional Idea of Solving Ethnic Problem s in “M ulti-ethnic State”
LIZhan-rong,WEILa-yun
(School of Law,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China)
D920.4
A
1009-1971(2017)05-0031-06
2017-05-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回应机制研究”(15BMZ001)
李占荣(1967—),男,甘肃庆阳人,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宪法学与民族法学研究;魏腊云(1972—),女,湖南常德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法理学与民族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