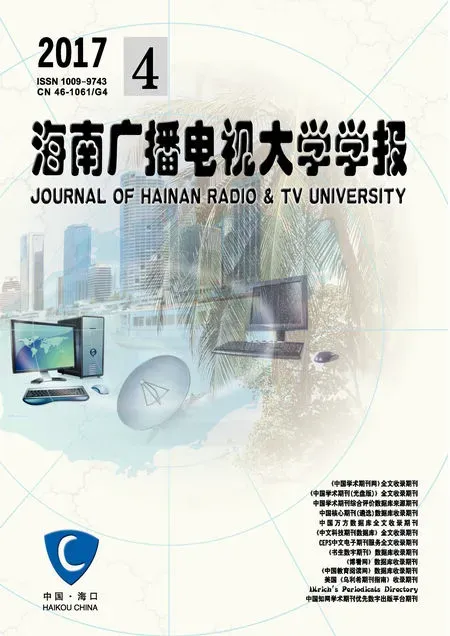文学史在等待着
——新时期以来吴组缃小说研究述评
朱超亚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文学史在等待着
——新时期以来吴组缃小说研究述评
朱超亚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吴组缃是20世纪30年代乡土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重要作家,其小说具有高度现实主义成就。因为历史原因,以及吴组缃小说创作数量并不多,在新时期之前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书写中吴组缃并未得到重视,甚至受到文学的“外部关系”影响被错误批评。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研究者对吴组缃小说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形象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叙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吴组缃小说研究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吴组缃;形象研究;文化研究;文体研究;叙事研究
正如丁帆、朱晓进所评价的:“吴组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以不多的作品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的作家”[1]166——其小说以质取胜。然而,在“十七年”的文学史书写及其他形式的学术研究中,吴组缃始终未得到重视。在极左话语影响下,不少学者对吴组缃小说作出了错误评价。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吴组缃小说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研究形式也开始逐渐多样,期刊学术论文与硕士学位论文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形式。
期刊学术论文方面。1982年,袁良骏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研究吴组缃的学术论文《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吴组缃小说艺术漫笔》。这篇论文大约代表了今后很多年学术界对吴组缃小说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作者论”。在20世纪8、90年代,赵园、魏超然、方锡德、刘勇强、谢昭新等人都发表了类似学术论文。正如袁良骏文题最后两个字——“漫笔”,这些论文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吴组缃小说特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语言风格、节奏等若干方面都进行了阐述,但是都不深入。不可否认,这些“漫笔”式的作者论也有各自特色,有些甚至为后人研究打开了局面。
这一阶段,学术界对于吴组缃小说研究的方式也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形象研究
在期刊学术论文中,所有的漫笔式“作者论”以及相当一部分专门探究角度的文章都对吴组缃小说中的形象进行了研究,大量类似研究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同质化倾向。
在人物形象性格方面,这种同质化倾向体现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吴组缃》一文的影响,大多关注人物的性格(抑或表述为“道德”,抑或表述为“灵魂”)。此外,这些文章大多将人物性格变化指向小说主题,而且他们所理解的主题并无新意,其关键词不外乎:“女性”“封建文化”“经济侵略”“底层”“阶级”“反抗”等。一如赵园认为,“对于时代气氛的总的感受,使吴组缃选择了他的人物——在内外两面的挤压下辗转挣扎的灵魂”,“吴组缃所选择的形象系列,正便于他传达对于时代气氛的总的感受——动荡不安,扰攘不宁,处处蕴藏着巨大的变动”[2]251。二如袁良骏也认为“线子嫂的被迫杀母,比起小狗子的被迫当土匪来,似乎更能揭示问题的实质。他说明残酷的经济压迫已经完全破坏了正常的人伦关系和道德规范”[3]。再如谢昭新认为“吴组缃的社会剖析小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影响下的社会变化,人心的变化,而且让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4]189。不难看出,在从总体上把握吴组缃小说人物与主题关系上,赵园、袁良骏、谢昭新以及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与夏志清在小说史中对于吴组缃的那句总结很相似——“将道德以及心理上的直觉,置放到这一论调(社会剖析与社会批判)的范畴里去”。
不能因为这些学者在人物形象研究上的“总体把握”相似而否定其各自特色,他们往往依靠自身的知识体系,将论证引向深入。
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对吴组缃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一致肯定,在从总体上概括吴组缃小说人物塑造时往往忽略了小说由稚嫩到成熟“寻找自己”的历程。在《清醒的严峻的现实主义艺术》一文中,唐沅对吴组缃小说人物塑造的内在演进过程进行了认识——吴组缃的早期小说,诸如《离家的前夜》《两只小麻雀》和《金小姐与雪姑娘》等在人物塑造的“艺术表现上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的局限,作家还不能把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从容自如地熔铸到形象的描写之中,因而出现‘理念化’的倾向”[5]6。在小说《离家的前夜》中,“故事的发展,把蝶对难以割舍的亲子之爱,处理成年轻母亲追求人生理想的主要障碍。作家显然重复着‘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作者们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在对冲突的表现和结局的处理上都反映出思想上的彷徨和困惑”[5]4。再如另一部小说《两只小麻雀》中,“小说对奶妈仁慈性格的描写流于抽象,对偶然因素的处理也未能融汇到事物运动的必然性之中而显得孤立和突兀”[5]4。吴组缃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成熟的转折标志是《官官的补品》,至此,吴组缃摆脱了“理念化”倾向,才适合这样的评价——“在不断追求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描写之中,刻画了在黑暗中挣扎着反抗着的倔强的性格”[5]6。
刘勇强认为吴组缃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实际创作中,古代小说的影响潜移默化,无处不在”[6]115,属于“典型的史传精神”。“从他的小说看,确实很出色地运用了这种暗喻褒贬的手法”[6]114-115——“在同情之余,没有袒护小秃子夫妇的愚昧;批判指瑕,也没有把官官母子写成凶神恶煞”。而这也正是当年茅盾所批判的“纯客观”倾向。另外,刘勇强也援引吴组缃本人阅读《红楼梦》的感受来论证其小说人物对话惟妙惟肖并且以语言来体现人物性格及思想变化的原因——“我们不止为小说(《红楼梦》)的内容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一部《红楼梦》不止教会我们把白话文跟日常口语挂上了钩,而且更进一步,开导我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们说话的形态、语气和意味”[6]115。
二、文化研究
正如严家炎教授在论证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时所指出的,地理意义上的地域“通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7]9。吴组缃的大部分小说属于典型的乡土小说,其文本之内蕴含着浓郁的徽州及皖南的风土人情。综观学界对于吴组缃小说的文化研究,大致分为两层——“浅层”与“深层”。
所谓浅层,即研究只关注小说文本中自然的、人文的表象。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沈琳。她在2014年发表的《台静农、吴组缃乡土小说的地域书写探析》一文中,过分纠结于吴组缃小说中“充满典型地域特征的乡土场景、具有地域色彩的日常生活和习俗”[8]168,如“在吴组缃的小说中涉及的习俗有皖南地府的妇女抱着灵牌成亲然后寡居一生(《菉竹山房》),有宗族式的管理方式(《一千八百担》)、有乡民对神灵的敬畏(《天下太平》)”。另外,在梳理吴组缃一系列小说中的“皖南地域色彩的符码”以及“地域之变”后,沈琳得出结论“地域元素在吴组缃的小说里已淡化为一种背景式的空间存在,作品更多的是对中国20世纪2、30年代的现实社会的剖析与批判,是在社会剖析视野下的地域书写”。可以说,沈琳这种研究方式未能很好地对吴组缃小说进行文化上的体认,关注表层的“变”进行主题的归纳,显然没有达到文化研究的目的,反而没有超出前文所述评的“性格研究”类型的研究范式,流于机械和肤浅,忽视了构成人文环境的诸因素,难以解读皖南文化对吴组缃小说影响的那些复杂、深刻的方面。
罗爹爹和罗四强一起过来的。此刻的阿里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头使劲地往墙上撞。阿东紧紧抱着他,哭道:“你莫这样!你莫这样!”
1997年,在谢昭新发表的《恋乡情绪 社会剖析 文化审视》中,最早地尝试了文化研究对于吴组缃小说研究的应用,研究者虽然注意到长篇小说《鸭嘴涝》(《山洪》)“与以往的写法不同,它偏重于文化审视和民族心理的分析,属于文化型、生活型、风俗型小说”,“吴组缃的文化审视是全方位的,他重点分析的是民族文化心理在抗战时期表现出来的丰富性、复杂性”[4]190,然而可惜的是,研究者并没有在文本之外进行足够的延伸,而是依然沿着“性格研究”的范式开展论证。谢昭新认为,小说主角章三官性格由三部分构成——“既有民族文化中的优质因素的生长,又有与之对立的劣质文化的充分表演,还有夹在这两种文化层面之间农民自身的文化思想弱点的显现”。研究者的论证重点在于,在抗战存亡的大背景下,这三种性格因素相互作用,最终“民族文化中的优质因素”占了上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分阶级、阶层的联合抗日的完全复兴了的中华民族”[4]191。
深层次研究能够真正走进小说所要表达的乡村文化氛围,体认小说所塑造人物的文化性格,揭示出小说所蕴含的地域的乃至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本质特征,达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目的。这一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业芸、朱菊香、穆林娟。这类文章大多对吴组缃笔下的人物类型进行了细分,然后结合文本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对某一种或多种人物进行体认。
这些形象群体被研究最多的就是女性,包括农村底层女性和知识女性。对于传统女性形象的把握,各研究者的方法、观点都趋于一致,大都分析了皖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氛围以及吴组缃童年时的个人经历,认为她们命运属于“封建礼教吃人的悲剧”,这一类研究同样具有同质化倾向,并且未见深入。在对吴组缃小说知识女性群体的体认中,朱菊香认为,“吴组缃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指向封建传统和资本主义方式,忽略了女性自身的弱点”[9]。显然,在这一方面,朱菊香对于吴组缃小说是持否定态度的。同样的问题,穆林娟也认识到了,并且她在文章中结合了“徽州文化”分析了这所谓的“女性的弱点”——吴组缃小说中的知识女性“身上所谓的‘新’更多地呈现出过渡的性质,那些充满着彻底的反叛、不顾一切奔向光明的新女性与徽州这块土地并不适应”[10]16。正如《离家的前夜》中,“传统母亲角色传递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定和期待,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融入女性自身,不自觉地实践着”[10]16,“我们体会到这个新旧参半的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过程中的艰辛苦涩,看到了她转型蜕变的困惑彷徨,触摸到了那一代女性胶着而又迷惘的心”[10]17。
其次,不少研究者以文化研究方式对吴组缃小说中与女性命运相关的男性知识群体的性格进行了剖析,具有一定的新意。吴组缃的不少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如《卍字金银花》《黄昏》《两只小麻雀》《金小姐和雪姑娘》等篇目中,“我”大多是一位受过新思想影响的男青年。有些文章将这类男性群体定义为“归乡人”,这是明显狭隘的,毕竟“归乡人”只是这类男性群体的一部分。朱菊香认为,“叙述者‘我’思想中残存的男性中心观念也是导致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但“‘我’的叙述视角也遮蔽了‘我’的男性中心观念对女性的压抑”,在这一方面,朱菊香对吴组缃的小说,同样持否定态度。但是,这也正是文化研究学者需要阐释的方面——“我”的文化性格。穆林娟认为“在徽州,不仅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女人们面临着无法摆脱的传统困境,即使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归乡知识青年同样在传统的守旧面前处于尴尬的位置”[10]18。穆林娟指出“这些归乡人‘我’回到家乡目睹或亲历一些故乡人的悲剧后,往往会犯热病中暑而昏厥几天”,这种“病状”的反复出现“蕴含着某种必然性”,具有需要挖掘的新意义。这与朱菊香的研究立场有着明显不同,穆林娟倾向于对小说中这类人物进行文化分析,而非一味地否定——“在这些归乡人的病状中把握到他们所处的徽州文化环境,这是社会病状投射在他们的映像,身体符号便是映射这一社会文化的窗口”。“在强大的礼教面前,‘我’却退缩了,忧郁不安,陷入了两难处境”,“实际上‘我’所患的热病与其说是一种身体的病,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困境,热病更像是一个道具,是‘我’所找的一个借口和托词”[10]20。
不少研究者认为,吴组缃小说中的底层男性形象是农民,如吴正一认为吴组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和抗争的旧中国皖南乡村破产农民形象,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众多具有一定社会和艺术概括性的独特的人物形象”[11]91。其实这种角色认识,一开始就与文化研究方式相疏远。王小福、祥发以及《一千八百担》中的每一个面孔,都是吴组缃刻画的具有皖南地域特色的职业类型,也就是“徽商”,虽然大部分是这一职业的最底层——店员。吴组缃笔下的店员形象被方锡德誉为“对现代文学人物画廊有特殊贡献”[12]269。张业芸就曾在文章中指出,“经过徽商们多年的言传身教、熏陶渲染,儒学和贾道互为渗透,相得益彰。尊儒的传统揉合着经商的梦想形成皖南山区共有的集体无意识的冲动,在徽商们心中郁积成一种独特的‘儒贾’情结”[13]32。研究者通过文本之外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解析了店员们身上所共有的文化基因——共同的美德,共同的宗族观念。以及在面对失业的变局时,在店员们内心中,“‘守’与‘变’的思想不断地碰撞,儒与贾紧密缠绕的结逐步松动、脱落。”[13]34。在结论上,研究者虽然也认为这些店员“程度不一地解开了心灵上的症结”,“透过对这类店员‘人心大变”的挖掘,揭示出那个时代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与传统的理念碰撞和割裂之变,从而具体细微地完成了对那个社会的深度剖析”[13]34。
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范式的重心在于以文本之外历史地理学分析的方法对文本之内人物文化性格本身的关照,而非“性格研究”中抽象地概括与演绎,所得出的结论也更能深入人心。
三、叙事学与文体学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茅盾的“纯客观”批判开始,一直到新时期,不少批评家都注意到了吴组缃小说在进行社会剖析时的叙事特色,肯定的评价不外乎“不动声色”“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否定的评价不外乎“纯客观”“缺乏热情”“不能正面表现”。且不说这些评价公允与否,它们似乎都是止于印象式的总体把握,而真正在定性与定量的高度分析与理解吴组缃小说叙述技巧的研究是以西方叙事学的使用为标志的。
和通俗的“内容”与“形式”的划分相类似,叙事学(Narratology)的“二分法”将叙事作品的文本划分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两个层次。“叙事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故事’涉及‘叙述了什么’,包括事件、人物、背景”,“‘话语’涉及‘是怎么叙述的’”[14]13。有关“故事”的讨论在前文已有充分述评,本章节不再赘述。这一阶段,研究者们对于吴组缃小说的叙事学分析最有特色的方面为“叙事交流”,涉及了“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视点”与“聚焦”等叙述学知识。
(一)李华:“叙述视点多重转换”
李华的《吴组缃小说的叙述视点》是专门从“话语”角度理解吴组缃小说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文章中,李华致力于寻找吴组缃早期(1933年之前)小说在视点上的多重转换。比如李华指出在《金小姐与雪姑娘》中通过“第一人称内视角”对“我”的内心情感进行揭示,为后来“我”与王雪姿重逢的感情波动作了极妙的铺垫。在对金家凤的叙述时则进行了视角转换,改用“第三人称内视角”叙述,“展示出一个处于社会文化嬗变时期‘被这个社会用封建传统的毒害给沦落了的’知识女性”。在叙述王雪姿时,作者再次转换视角,改用“外视角全知叙述”,写出“资本主义方式给蹂躏践踏成污泥”的女性命运[15]23-24。同样地,李华分析了《离家的前夜》与《官官的补品》中的“视角多重转换”,进而认为“叙事视点的多种转换,使叙事对象得到了多方位的呈现,也展示出这一个作家独特的叙事笔法和审美用意”[15]23。然而,在文章中李华认为“从1933年起,他减少了人物限制视角的运用更多地运用纯客观视角或全知视角”[15]24,而“纯客观视角”并非一个叙事学名词,而是当初茅盾印象式批评的用语,具有极左政治色彩。在后文的论述中,李华对吴组缃1933年之后的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忽略,所谓的研究流于情节重述和印象式分析的空洞重复,缺乏叙事学的理性。
(二)张蕾:“叙述者”的总体把握
在对吴组缃小说的“话语”研究中,张蕾有试图总体把握吴组缃小说叙述者的倾向。她认为,吴组缃的小说“叙述者‘我’的身份一般都是一位现代知识者,是作者自我经验与情感的投射”[16]113,以“我”为叙述者进行第一人称写作,可以造成叙述者、作者、甚至读者三位一体的幻象,“因为作者首先就有对小说叙事者的认同感,把自己的思想甚至经历赋予小说中的那个我”[16]114。
在对《官官的补品》进行叙事分析时,研究者并不赞成以往“自供状”“作者与叙事者同一”“反讽”这三种观点,以高度的叙事学理性思考了“这个遭人诟病的叙述者的功用何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意义是什么?”[16]115这两个问题。随后,研究者回到了前文对叙述者的“总体把握”,以叙事学的理论在小说文本中找寻到了根据,她认为“官官和这些叙述者都是‘归乡人’这一‘行动元’之下的一系列角色,官官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仅对家乡人的悲剧束手无策,而且成为悲剧的共谋者”,“所以第一人称‘我’依然把叙述者和作者牵连起来,在批判叙述者的同时,作者也鞭笞了自己”。研究者进而认为,《官官的补品》受到了狂人日记的影响,“吴组缃热爱、推崇鲁迅,他也就会自然地把鲁迅的反省思路带入自己的创作中”[16]115。
还是基于对“叙述者、作者、甚至读者三位一体的幻象”,张蕾认为,吴组缃不但熟练地使用这种幻象,而且会使用多种叙事技巧,以增添趣味。在文中,研究者以叙述学方法分析了《两只小麻雀》和《官官的补品》。研究者认为,《两只小麻雀》“呈现出一个双层叙事结构”[16]114,在这结构中,作者有意制造了两个矛盾。其一,“外层叙事者‘我’是小说主人公的好友,他交代了小说主体部分是主人公的日记。内层叙事者‘我’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可是小说内层叙事并非采用日记体”[16]114,这一层矛盾“使阅读者自然而然地与叙述者认同,忘却他是在读另一个人的日记而与叙事者间离”。其二,“外层叙事者‘我’可以被误认为作者——一位男性人物,可是进入主体部分后,叙事者变成了女性。当日记的叙事屏障被消除,阅读者迅速与叙事者认同时,幻象就会产生:内层叙事者与作者混淆起来,同时性别差异又在抵制这样的混淆”[16]114。
可以肯定,张蕾的论述具有高度的叙事学理性,在总体把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这两个反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三)其他叙述学视阈下的吴组缃小说研究
官娇英致力于叙事学工具之下的女性主义解读,审视吴组缃笔下“触目惊心”的女性命运。就批评与分析的手段来说,官娇英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李华的“多重视角转换”与张蕾的“幻象”这两种认识,她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叙述人”“人物话语”和“聚焦”。在一系列女性主义分析中,其对《金小姐与雪姑娘》的分析最具有叙事学理性。走投无路被迫靠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的雪姑娘,被人们骂为淫荡下贱的女人,其实她是最需要同情的女人,然而在小说的读者中,人们对于金小姐的同情似乎要多于雪姑娘。研究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叙事者‘我’的存在”[17]94。与张蕾的“幻象”观相似,官娇英指出“‘我’在文本中不仅是一个叙述者,也是一个参与实践的角色;不仅是一个起线索作用的人物,也是进行道德评价、价值判断的施动者”。而男性的“我”不自觉地运用了带有“严格的道德和伦理体系”的男性视角,“文本接受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无疑会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早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来看待雪姑娘的行为”[17]94。
这一阶段,张丽华于2010年也发表了一篇专门从叙事学角度研究吴组缃小说的学术论文——《吴组缃小说的叙述艺术》。文章的中心论点为“吴组缃小说多选择第一人称叙述,通过‘我’的多重角色,变换视角展开文本叙事,从而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这也在李华、张蕾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论述,不再有学术的创见性。另外,张丽华在论述《官官的补品》中的叙述人“我”时,认为“吴组缃在这里的反讽叙述时一目了然的,读者可以轻易超越反讽叙述者走向隐含作者”[18]108,这正是张蕾在2008年的那篇论文中所否定的“反讽说”——“反讽一词用得未必适当”,“只有当叙述者和作者的意志彼此具有独立性,互不干扰时,才会出现反讽效果”[16]115。“反讽说”忽略了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叙事学理性,很难将问题引向深入(即使不使用叙事学理论,也能有类似理解)。
四、结 语
八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吴组缃小说的批评与研究的总体趋势是由印象式逐渐走向理性和深入。一如20世纪30年代茅盾对于吴组缃小说的“纯客观”表述,虽然具有极左的倾向并且造成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这段时期内大陆文学史书写对于吴组缃的忽略甚至遗忘,但这表述在另一种程度上也是对吴组缃小说不动声色地冷静写实的肯定[19]。直到新时期之后,西方叙事学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应用,吴组缃小说“纯客观”的面纱才被具有高度叙事学理性的“话语研究”文章揭开;再如20世纪40年代老舍与以群对于吴组缃小说的方言应用“生动毕肖”的赞美,到了新时期之后,文化研究得以在吴组缃小说研究上展开,小说人物与吴组缃本人的“地域的乃至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本质特征”被研究者深刻读解。
可以说,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吴组缃小说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深度上,不少研究者能够与时俱进,学术质量在不断提高。当然,也是在这近三十年中,学术界对吴组缃小说的研究也出现了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十七年”间政治因素的干扰完全不同,学风浮躁,不少研究者低水平重复前人成果。例如,从总体上把握吴组缃小说的“作者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出现,这些文章为学术界开始重视吴组缃小说的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甚至新世纪之后,类似的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依然经常被炮制出来。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赵园、刘勇强等人的模仿甚至是重复,缺乏学术创见性。
“文学史在等待着”,认识到文学史书写对吴组缃及其小说的遮蔽后,赵园在《吴组缃及其同代作家》一文中如此呼唤。然而,在三十多年后,大陆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对吴组缃的评价依然未见明显进步——要么是篇幅极短,一笔掠过,不能让人引起重视;要么是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简单模仿,评语俗套,未见新时期以来“文化研究”“叙事研究”的成果。
[1] 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赵园.吴组缃及其同代作家[J].收获,1984(1).
[3] 袁良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吴组缃小说艺术漫笔[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6).
[4] 谢昭新.恋乡情绪·社会剖析·文化审视:论吴组缃的小说创作[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7(2).
[5] 唐沅.清新的严峻的现实主义艺术[A]唐沅.吴组缃作品欣赏[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6] 刘勇强.吴组缃小说的艺术个性[J].文学评论,1996(1).
[7]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创作,1995(1).
[8] 沈琳.台静农、吴组缃乡土小说的地域书写探析[J].江淮论坛,2014(3).
[9] 朱菊香.论吴组缃对女性命运的思考[J].黄山学院学报,2012(4).
[10] 穆林娟.现代作家视野中的徽州文化转型[D].苏州大学,2011.
[11] 吴正一.苦难中挣扎和抗争的人们——论吴组缃笔下的破产农民形象[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11).
[12] 方锡德.吴组缃对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A].文学传统与文学变革[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3] 张业芸.儒贾情结的生成和消解——论吴组缃对店员的心理剖析[J].南昌高专学报,2007(5).
[14] 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 李华.吴组缃小说的叙事视点[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16] 张蕾.归乡人·故事·革命——吴组缃小说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17] 官娇英.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与叙事技巧[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18] 张丽华.吴组缃小说的叙述艺术[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19] 朱超亚.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界对吴组缃小说的接受[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3).
LiteraryHistoryAwaits——Academic Research on Wu zuxiang’s Novels Since the New Era
ZHU Chao-ya
(Nanjing University,School of Liberal Arts,Nanjing 330031,China)
Wu Zuxiang,was an important writer among thirties Rural Social Analysis Novels School,with highly realistic achievement for the novels . For historical reasons,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Wu’s novels was not much,before the new era,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written and literary criticism,Wu was not taken seriously,even was wrongly criticized.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literary researchers had a new understanding on Wu’s novels,they had made some progress in characters studies,cultural and narrative research studies,but generally speaking,the research of Wu’s novel still has some room for improvement .
Wu Zu-xiang; characters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narrative studies
I206
A
1009-9743(2017)04-0026-07
2016-11-02
朱超亚,男,汉族,江苏泗洪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
10.13803/j.cnki.issn1009-9743.2017.04.005
张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