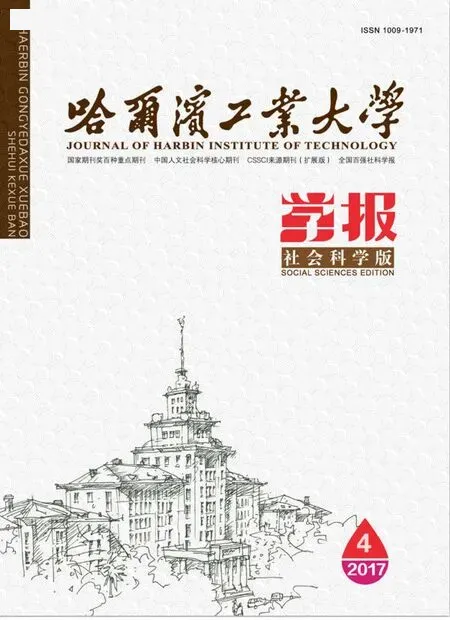由隐而显:赵翼史学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
王云燕
由隐而显:赵翼史学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
王云燕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
赵翼是乾嘉时期的诗人、史学家。早年以诗文名世,中年以后由文入史,转向史学研究。在考据盛行的乾嘉学界,时人推重他的诗文,其史学因疏于考证不被重视。嘉、道以降,经世之学兴起,赵翼史学因契合经世之风渐为世人所重。清末,他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备受张之洞青睐,借助张之洞的名人推广效应,三年内被翻刻数次,涌现出多种刊本,促成了赵翼史学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民国以来,赵翼之史名誉满中外,影响了一大批的史家、史著。综观赵翼史学生前、身后之际遇,两者形成强烈反差,其史名之显晦与时代风气和学术评价标准之转换紧密相关。探究赵翼史学在清代的际遇不仅为对比民国学术背景下的赵翼史学接受提供了有力参照,还有助于全面了解赵翼史学的传播、接受过程。
赵翼;《廿二史札记》;考据;经世;传播;接受
赵翼字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生于雍正五年(1727),卒于嘉庆十九年(1814),是清中叶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他早年以诗文蜚声文坛,“传写诗什,江左纸贵”[1]22,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中年以后,由文入史,潜心史学研究,撰成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赵翼生前,史名为诗名所掩,时人并不推重他的史学。杜维运在《赵翼传》序言中将赵翼生前史名不盛的原因归结为经世致用的治学旨趣与考据之风的不相融合[2]3-4,强调学风对赵翼史学传播造成的客观阻力。笔者进一步研究发现,除学风上的影响外,赵翼本人不擅考证的主观因素亦是阻碍他史学传播的“绊脚石”。此外,诗人身份和个别学者的负面评论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近代以来,赵翼史学日益声名鹊起,受之影响的近代史家和史著不计其数,史名超越诗名后来居上。当前学术界有关赵翼史学的研究虽不乏著述,但主要集中在文本内容的探讨,从传播、接受角度进行研究的专文则尚未见。本文致力于此,以期对这一研究有所助益。
一、赵翼史学概述
赵翼一生撰述宏富,著作等身,据时人姚鼐《瓯北先生家传》记载:除《瓯北集》外,“其他著述凡十余种”[3]。然今日所见仅湛贻堂《瓯北全集》刊本中收录的7种,包括《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簷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瓯北诗钞》《瓯北诗话》《瓯北集》。赵翼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四部著述中。
《陔余丛考》是赵翼转入学术研究后的第一部专著,撰写于归家侍母期间,①据杜维运考证,居家侍母这段时间完成的仅是《陔余丛考》的初稿,此后十余年内,赵翼反复修订此稿,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湛贻堂初刊本问世,该书的编纂才画上圆满的句号。卷首的《小引》中交代了成书经过和书名由来:“余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则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以其为循陔时所辑,故曰《陔余丛考》。”[4]全书共43卷,不分门目,以类相从,分条撰写,每条围绕一个主题单独展开,以笔记的形式对古代典籍、典章制度、历史人物、事件进行研究,涵括经、史、子、集四部。论史诸卷占一半以上的篇幅,系全书重点所在,亦精华之所在,随后问世的《廿二史札记》就是在这部分的基础上拓展而来。赵翼选题、立意角度广阔,不拘一格,书中诸多内容多发前人所未发,读之令人耳目一新。王昶诗云“清才排奡更崚嶒,袁赵当年本并称,试把《陔余丛考》读,随园那得比兰陵”[5],充分肯定了《陔余丛考》在赵翼由诗文创作转向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开创性地位。
《皇朝武功纪盛》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包括《平定三逆述略》《平定朔漠述略》《平定准噶尔前编述略》等8篇。该书以《四库全书》中前数件方略为史料来源,参酌作者亲身见闻纂辑而成,可视作当代人写的当代史。赵翼创作此书的目的在于“使观者易于披览,即不能诣阁读《四库书》者,亦皆晓然于我朝功烈之隆也”[6]2。意在彰显大清之盛世武功,文中不免有夸胜讳败、侈陈战绩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部分内容的客观性,如将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6]47,即官逼民反,可谓切中要害。
赵翼的史学代表作当属《廿二史札记》,全书36卷,补遗1卷。虽名为“廿二史”,实则囊括“二十四史”(其中《唐书》和《五代史》各包括新、旧两部)。该书延续了《陔余丛考》的写作风格,以札记的形式分条撰述,遵循“先考史法,次论史事”[7]的原则,按史书为单位编次,综合考辨历代正史之撰述沿革、编纂得失。赵翼订正史籍之外,还秉承了顾炎武倡导的经世致用精神,“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8]1。赵翼治史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史事考订,还多就关乎治乱兴衰的大事发表评论。对历代弊政的批判是赵翼治史的一大特色,譬如《两汉外戚之祸》《后魏刑杀太过》《唐代宦官之祸》等专就每一朝的典型弊政进行总结和批判,便于统治者以史为鉴。赵翼在《再题〈廿二史札记〉》一诗中写道:“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9]1024后两句明确交代了他治史的意图在于,从历代史书中探索治国之“良方”,以“古方”医“今病”,流露出明显的经世意识。此乃《札记》比同期著述高明之处,也是它在晚清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作为赵翼史学的代表作,它的传播和接受情况直接关系到赵翼史名的兴衰。
《簷曝杂记》成书最晚,为赵翼晚年回忆录与生平零散杂录的汇集,不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用力之深,各卷质量也参差不齐。
赵翼生活在考据风靡的乾嘉时代,但他治史却不局限于文字、史实的单一考证,而是多就治乱兴衰之大事发表评论,以动态的眼光研究历史发展大势,探求历代盛衰兴亡之故。乾嘉时期,学人治学崇尚考据,褒贬议论被斥为虚学,所谓“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10]王鸣盛所言代表了乾嘉学界的主流学术取向,赵翼不以考证为职志、而以经世为旨趣的撰述风格与这一学术主流有所偏离,因而不为当时学界所重。杜维运所言:“时风所趋,有如万军猝发,莫可膺其锋。瓯北(赵翼)又焉能不为时风所掩呢?”[2]3确有一定道理。
二、考据风气下的沧海遗珠
赵翼性情旷达又好交游,与当时的学界名流多有交往。乾嘉时期文人、学者的著述中有较多关于赵翼为人和为学的评论。笔者广泛浏览此类著述后发现,时人有关赵翼治学的评价多偏向诗文一隅,只有钱大昕、李宝泰等为数不多的几人对其史学作出了具体评价。
《廿二史札记》是赵翼引以为豪的作品,此书撰成后,他亲自拿给当时学界公认的学术权威钱大昕看,并邀钱为之作序。钱氏序称赞此书“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8]885。钱大昕从经世的角度充分肯定其价值。学人李宝泰为《札记》撰写的序文中也称,赵翼有“经世之才,具冠古之识”[8]887。可见,赵翼治史的经世意识确已为时人所认可。然而,当时的治学风气却并不利于这种经世史学的传播。从钱、李两人的序文来看,他们都用较大篇幅对时下的学风作了批判。钱序以经史关系为切入点,痛斥了宋代以来“陋史而荣经”、“十七史皆束之高阁”[8]885的不良风气,旨在纠正当时学界重经轻史的倾向,有意为史学正名。李序中也批评时人“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弊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8]887。钱、李二人虽不满当时的治学风气,却无力挽救时风。他们在批判时风的基础上肯定了赵翼史学,这无异于变相说明赵翼史学与时风不符。还需注意的是,从序跋的性质来看,多是应邀而作,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文字表达形式。钱、李二人又是赵翼的好友,我们并不能排除人情因素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赵翼史学的判断。在重经轻史的学术氛围下,史学的地位本来就位于经学之下,这势必会影响赵翼史学的传播。重考据的学术风气又为以经世为主的赵翼史学平添了另一道障碍。杜维运称:“当乾嘉之时,考据学趋于极盛,史学家崇尚博雅,醉心考据,耗毕生岁月于擘绩补苴纠谬正讹之中。瓯北则不趋时风,不逐潮流,飘然世外,自树一帜。其不能为时代所容,自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2]3确为解释赵翼生前史学之沉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不容忽视的是,赵翼本人不擅考证的事实也为时人贬斥其史学提供了借口。
与钱、李两人的赞赏相对,一般学人对赵翼史学持轻视态度。昭梿《啸亭杂录》中专门撰有“赵瓯北”一条,评述赵翼生平学问时称:“诗才清隽,与袁、蒋齐名,堪称鼎峙。所著议论,尚多可取,然考订每患疏漏。”[11]516他对赵翼的定位是诗人而不是史家,推崇其诗文,却无视其史学。究其原因在于,赵翼的考证水平,素为昭梿所鄙视。“考据之难”一条中,他明确将赵翼作为国朝诸儒中不擅考证的典型:“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如毛西河、顾炎武、朱竹垞诸公实能洞彻经史,考订鸿博,其后任翼圣、江永、惠栋等,亦能祖述渊源,为后学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简斋太史、赵瓯北观察(赵翼),诗文秀雅苍劲,为一代大家,至于考据,皆非所长。”[11]428依昭梿之见,赵翼虽有文采,但考据实非所长,甚至会犯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譬如《簷曝杂记》中“以汤若望、南怀仁至乾隆中犹存”之误简直是“著述中一笑柄也”[11]428。出于对赵翼考证功夫的不屑,昭梿对赵翼的史学评价不高。
与昭梿同出一辙,周中孚也在肯定赵翼诗文的同时,批评他的考证《郑堂札记》中多次针对《陔余丛考》中的考史内容发难,诸如“赵氏误也”、“如此评史真强作解事也”、“赵氏所云徒然妄生枝节耳”一类的批评屡见不鲜。周中孚最为世人称道的《郑堂读书记》中评论《陔余丛考》时称:“按云菘(赵翼)本词赋家,于经从无所得,故考论经义率皆门外之谈。惟史学颇称熟悉,曾著有《廿二史札记》,此间十一卷已得其大略,盖作于《札记》之前者,而杂论故事数卷尚多可取,余所考证,其细已甚,不足以当大方之一噱也。”[12]907周中孚对赵翼的定位仍是词赋家而非史学家,对于史学,赵翼只算是“颇称熟悉”,谈不上擅长,更谈不上精通。赵翼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在他看来亦不过是“类叙事实,毫无发明”[12]542。
昭梿和周中孚均为博学之士,生活时代也大致相同,二人评论赵翼学术时,态度和立场相似绝非偶然。有清一代,绝大多数时间内考据学占据学术主流。考据之学自清初顾炎武肇其端,至乾嘉时期臻于极盛,昭、周二人都经历乾隆、嘉庆两朝,当时的文人、学者大多以从事考证为职志。对此,梁启超曾作如下描绘:“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微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13]27考据成为一时风气,乾嘉史坛亦是考据史学独霸天下,考据功力的深浅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衡量标准。一方面,确如杜维运所说赵翼治史不以考据为旨趣;另一方面,赵翼本人不擅长考据也是客观事实。与钱大昕、王鸣盛等由经入史的正统派治学路径不同,赵翼走的是由文入史的道路。正统派学人受经学余风影响,态度严谨,史著中的错误较少。赵翼因没有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在治史严谨性方面略逊一筹,失于疏阔、粗略,由此产生的谬误构成他著作的一大缺陷。在致友人王昶的书信中赵翼坦言:“考订之事,本非所长。”[2]312昭梿、周中孚二人对赵翼的批驳,也主要集中在考证不精方面。赵翼的好友谢启昆也曾专门写信给他,就《廿二史札记》中关于《西魏书》的内容展开商榷,此信还被附入《札记》中。民国史家陈垣在辅仁大学等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上曾专门把《札记》作为教材,让学生就其史源寻找错误。陈垣本人也曾对《札记》做出考证与评论,成果主要集中在《廿二史札记批注》和《廿二史札记考正》两部分内容里。①罗炳良撰有《陈垣与〈廿二史札记〉研究》一文,详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4—97页。继陈垣之后,杜维运、王树民等也曾专门订正《札记》的疏失,经王树民整理的《廿二史札记校证》是目前该书最好的版本。生逢考据成为学术主流、考证高手如云的时代,赵翼却偏偏不擅考证,其史著中的疏失很容易被识破,再加上昭梿、周中孚等一两个较有名气学者的负面宣传,难免在时人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赵翼生前,在文学上的造诣深入人心,史学上的成就被忽视,他本人也是以诗人自居。《七十自述》诗中自称:“生当盛世身何幸,老作诗人业已轻。”[9]897从其著述在当时的刊刻、流播情况来看,诗集亦远远超过史著。赵翼晚年曾作《书贾施朝英每年就我刷印拙刻〈瓯北诗钞〉、〈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十家诗话〉等各数百部书以一笑》一诗,据题目可知,《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每年的印刷量仅在数百部。这与“四海遍传《瓯北集》,千秋重睹剑南诗”[9]1283之盛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可见,赵翼生前,史学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十分有限。
三、经世实学下的初露锋芒
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政治天然交融在一起,社会的治乱兴衰直接影响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向。清中叶文治武功达到鼎盛,考据之学执学界之牛耳,学者治学事事以学问为趋,忽视为学之价值。然自嘉庆以来,国家多故,世道衰微,时势在变,学风亦随之一变。学人不再埋首故纸堆,转而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寻求强国御辱之道,问学风气也由“考据”转移到“经世”上来。循此经世之风,赵翼史学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认可和重视。
嘉庆以后,赵翼史学的经世价值渐为学人重视。张维屏称:“盖凡先生(代赵翼)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见闻,通知时事,较之龂龂考据于无用之地者似为胜之。”[14]钱林《文献征存录》中也称赵书“较之侈谈考据,于日用事物之间毫无裨补者胜之”[15]。两人都肯定了赵翼史学与一般考据史著的区别,有意凸显它经世致用的特点。魏源亦十分欣赏赵翼史学的经世价值,在他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主持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中收录了赵翼四部学术著作中的20多篇经世文章,尤以摘自《廿二史札记》者最多。包括《籍没财产代民租》《将帅家丁》《外番借地互市》《明边省攻剿兵数最多》《用兵有御史核奏》《大臣荐举》《长安地气》《五代盐曲之禁》《汉诏多惧词》《汉儒言灾异》《明初吏治》《天主教》《唐初三礼汉书之学》《明吏部权重》14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经世文编即“经世济时”文章之汇编,赵著的诸多条目能够入选此编,无疑从一侧面为赵翼史学的经世形象作了代言。《皇朝经世文编》刊印后产生了十分深远的社会影响,晚清汉学大师俞樾曾说:“《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榘矱,几于家有其书。”[16]经世文编的风行,带动了所收录赵著相关条目的传播,为赵翼史学经世形象的确立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伴随史学声望的提高,赵翼身上除了“诗人”之外,又多了“史学家”这样一重身份,学人关注的重点也由诗文转向史学。李慈铭一度对赵翼史学评价很高,他在读书笔记中高度赞扬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周密详慎,卓然可传,最为生平杰作”[17]221。对其诗文却不甚看重,他指出:“云崧(赵翼)以诗名乾嘉间,浅率芜俗,实不足存”[17]221。李氏之前很少有人重视赵翼的史学甚于诗文者,这与乾嘉学人的一般评判形成鲜明对比。无独有偶,丁宝桢在光绪三年(1877)为《瓯北全集》所写的序言中也着重赞扬了赵翼的史学:“考据之学,至我朝诸大儒出而既精且备。盖自亭林先生为之倡,而后之踵起者,或卒毕生之精力专攻一经,或集群书之粹美,博究一艺,大抵皆大含众有,细入无间……独瓯北赵先生长于史学,著《廿二史札记》及《丛考》、《杂记》等七种。向时江南刻有全集,海内承平之士奉之。”[1]211据笔者观察,以往学者为赵翼著作撰写的序言中或多或少会夹杂一些对诗才和文采的颂扬,丁宝桢却忽略其诗文专门讴歌其史学,并指出乾嘉诸儒中唯独赵翼擅长治史,这是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嘉、道年间,渐有学人将《廿二史札记》与当时声誉极隆的《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并提。前文提到的周中孚虽曾指责赵翼考证不精,但他并不否认:“在近儒评史之书,群推王、钱两家,然惟云崧(赵翼)堪与之鼎立尔。”[12]544尚镕也称:“云崧(赵翼)经学不深,而《廿二史札记》,则多揭古人之隐,以自见其识力之深微,觉《史通》、《史纠》诸书,犹为识小忘大。同时唯钱竹汀《考异》,异曲同工;王礼堂《十七史商榷》,殊不及其精审也。”[1]156在周中孚和尚镕的推动下,时人普遍接受了三家并提的说法,“乾嘉三大考史名著”或曰“乾嘉三大史学名著”一说逐渐产生。这种现象的出现对赵翼史学的传播产生了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廿二史札记》得与学界公认的一流史著《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并称,有利于赵翼史学声望和学术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囿于“考史名著”的称号,时人往往从“考史”标准去衡定三书水平的高下。前文曾提到《札记》与钱、王两书有本质区别,它并不以考证见长。在“考史”为标准的评判模式下,学人的一般评价“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13]326。譬如周中孚对比三书时就流露出鲜明的重此轻彼的倾向:“考史之书,至竹汀此编(代《廿二史考异》),诚所谓实事求是,得未曾有者也。同时王西沚(鸣盛)《十七史商榷》,考证舆地典制,颇不减于竹汀,惟其好取事迹加以议论,仍不免蹈前人史论之辙,且于《宋》、《辽》、《金》、《元》四史未及商榷,其书究难与竹汀抗行。至赵云崧(翼)《二十二史札记》,类叙事实,毫无发明,又别为一体,尤不可与是编相提并论焉[12]542-543。短短数语将崇钱、王贬赵的学术取向表露无遗。稍后,李慈铭也称《札记》“于史事多是纂集之功,无所发明,笔尖冗沓,尤时露村学究口吻,以视钱氏《廿二史考异》,固相去天壤,即拟王氏之《十七史商榷》,亦远不逮也。”[18]420周、李二人的取向代表了多数崇尚考据者的看法。直到20世纪30年代,章太炎仍称:“三书之中,钱书当为第一,钱、王是一路,赵则将正史归类,其材料不出正史;钱、王功力较深,其实亦不免琐碎。”[19]诸如此类“钱、王为上,赵为下”的评价模式延续了乾嘉重考据的老路,赵翼史学的优势得不到有效的凸显,无疑会影响它的进一步传播。
与此种评价模式相对,也有个别学人突破“考史”程式,尝试着从“经世致用”的标准重新评定三书的价值。前文提到李慈铭推崇钱、王之书,贬低《廿二史札记》,但他为《札记》所撰的题记中又称:“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寝馈于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诚俭岁之粱稷也。其书以议论为主,又专取各史本书,相为援证,不旁及他书,盖不以考核见长,与同时嘉定钱氏《廿二史考异》、王氏《十七史商榷》不同。”[17]209李慈铭在此虽没有就三书之高下作出具体评论,却有意突出《札记》与另外两书的区别。他隐晦地对三书的性质和功能作出划分,大致将钱、王两书归为考证一类,《札记》归为经世一类。继李慈铭之后,《札记》的经世价值又为张之洞所青睐,在他为初学者指示门径撰写的《书目答问》中,专门将《札记》挑出,与《四库简明目录》《说文检字》《十三经册案》等18部著作列入“考订初学各书”一目。①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考订初学各书》一目下所收录的书籍有:《四库简明目录》《说文检字》《御纂七经序录》《皇清经解节本》《易堂问目》《十三经策案》《廿二史策案》《文献通考详节》《三通序》《通鉴目录》《历代帝王年表》《地理韵编》(纪元编)、《廿一史四谱》《廿二史札记》《翁注困学纪闻》《日知录集释》《十驾斋养新录》《骈雅训纂》,共18部。后来又在《劝学篇》中明言:“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缓。”[20]张之洞突破固有的评价模式,以“经世致用”为标准重新评判三书的高下。他不但充分肯定了《札记》的经世价值,还把它重点推荐给初学者,并极力为之宣传。借助张之洞在晚清政界、学界的名人效应,《札记》得以迅速传播。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劝学篇》对晚清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书目答问》风靡一时,李元度说,当时的读书人家几乎是“家置一编”。它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推荐书目[21],被诸多读书人视作治学指南,并按照它开列的书单去阅读或购买书籍。《廿二史札记》作为张之洞重点推荐的考订初学入门书目,自然会引起众人的重视。陈垣就是在《书目答问》的指引下阅读了《札记》,并在《札记》的引导下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②牛润珍曾言:“最初影响陈垣并引导他走上史学研究道路者,是清代学者赵翼撰写的《廿二史札记》。”详参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劝学篇》更是被作为钦定的“维新教科书”,“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22],借朝廷之力广为刊布,成为晚清印刷量最大的著作之一。《劝学篇》问世后,得益于它的宣传之功,《廿二史札记》走入更多读书人的阅读视野,在晚清有了更多的读者市场。继光绪二十四年(1898)《劝学篇》刊行后,此后的三年内《札记》不断被翻刻,掀起了一股传播热潮。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现存关于《札记》的主要版本中,有8种产生于这一时期。分别为:光绪二十四年集益学社刻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光绪二十五年湖南书局刻本、益元书局刻本、上海千顷堂石印本;光绪二十六年新化西畬馆刻本、上海书局石印本、广雅书局丛书本[23]。相比之下,《商榷》《考异》两书此时的刊刻情况远不及《札记》之盛况。《书目答问》和《劝学篇》的流传扩大了《札记》的学术影响力,为《札记》营造了良好的传播空间,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有效的促进了赵翼史学在晚清的大范围传播和接受,出现了赵翼史学传播的第一次高潮。
就在赵翼史学声誉渐隆之际,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度称赞赵翼史学的李慈铭态度发生强烈转变,甚至对《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的作者提出质疑。同治九年(1870)七月初五日,李慈铭在日记中写道:“阅赵翼《廿二史札记》。常州老生皆言此书及《陔余丛考》,赵以千金买之一宿儒之子,非赵自作。”[18]420时隔三年,他在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又说:“近代窃人之书效郭象故智者……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出于常州一老诸生,武进、阳湖人多能言其姓字。”[18]84-85由李慈铭引发的关于《札记》作者问题的争论一度引起学界关注,已有较多学者专门就此问题撰成专文,兹不细表。①详参张舜徽《论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载《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4-195页;杜维运《〈廿二史札记〉考证》,载《新亚学报》1957年第2卷第2期;杜维运《〈廿二史札记〉考证释例序言》,载《幼狮学报》1958年第1期;杜维运《〈廿二史札记〉之作者问题》,载《大陆杂志》1959年第19卷第6期;杜汉鼎《有关〈廿二史札记〉作者的问题》,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6日;谢正光《就〈陔余丛考〉论〈廿二史札记〉之作者问题》,载《新亚书院中文系年刊》1963年第1期;李金堂《关于<廿二史札记>作者问题》,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关于《札记》与《陔余丛考》的作者问题,在赵翼生前从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为何几十年后却被指责为窃攘他人之作?我们或许可以从赵翼史学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方面找到答案。赵翼生前以诗著称,其史学因不擅考据不为时人关注。嘉、道以降,伴随经世之学的兴起,赵翼史学渐为学人重视,评述和颂赞者日益增多。在此之前,赵翼向来是以诗人的形象出现的,由诗人向史家身份的转换,一时之间难以为时人所接受,不免心生疑窦。按赵翼本诗人之身,他能否写出《札记》这样一部一流水平的史学名著?李慈铭的诽谤对赵翼史学的传播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札记》一书不但得与赫赫有名的《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并称,在清末甚至掀起一股阅读热潮,刊刻、流传之广,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恰恰说明了赵翼史学确已为后人普遍接受和认可。
结 语
终清之世,赵翼史学际遇经历了“沧海遗珠”和“锋芒初露”两个阶段,由隐到显,形成强烈反差。赵翼史学在清代的命运与治学风气和学术评价标准紧密关联在一起。综观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王国维称:“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24]学术风气变化,学术评价标准亦随之变化。清初顾炎武开考据之风提倡经世致用,学术评价本之“求真”、“致用”二元标准。至乾嘉时期学风转变,治学偏入考据一门,“求真”成为主旋律,“致用”被忽视,而赵翼史学即诞生于此时。值此学术评价以“求真”为极则的时代,赵翼史学的缺点被凸显,优点被遮盖,不被世人重视也在情理之中。道光以后,世道衰微,内忧外患加剧,“经世”成为学术的主旋律,“考据”成为伏流趋向没落。学术评价渐以“致用”为标准,赵翼史学经世致用的特点渐为学界关注,史学声望也日益提高。
[1]孙星衍.赵瓯北府君墓志铭[M]//赵兴勤.赵翼研究资料汇编.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
[2]杜维运.赵翼传[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3.
[3]姚鼐.瓯北先生家传[M]//赵翼全集:第6卷.赵翼,撰;曹光甫,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9.
[4]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2:5.
[5]王昶.春融堂集[M].陈明洁,等,点校.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496.
[6]赵翼.赵翼全集:第3卷[M].曹光甫,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7]陈智超,曾庆瑛.陈垣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3.
[8]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9]赵翼.瓯北集[M].李学颖,曹光甫,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陈文和,等,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
[11]昭梿.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黄曙辉,印晓峰,标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14]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M].陈永正,点校;苏展鸿,审定.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558.
[15]钱林,王藻,辑.文献征存录[M]//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三十三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第39册.济南:齐鲁书社,2009:289.
[16]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M]//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光绪辛丑上海久敬斋铸印版:1.
[1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简端记[M].王利器,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18]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由云龙,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
[19]章太炎.章太炎讲演集[M].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100.
[20]张之洞.劝学篇[M].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5.
[21]李正辉.推荐书目源流考[J].图书馆,2011,(4).
[22]范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11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703.
[23]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06.
[24]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74.
From Concealment to Obviousness: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Zhao Yi’s Historiography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Yun⁃yan
(School of Histor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s a poet and historian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Zhao Yi was well known by his poetry in the early years and then turned to the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after his middle age.The poetry of Zhao was praised greatly and his historiography was neglected for the lack of textual research that was contrary to the pre⁃vailing historical ethos during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With the rising thought of statecraft after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the historiography of Zhao was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as i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thought of statecraft.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masterpiece Reading Notes of 22 Histories of Zhao was highly favored by Zhang Zhidong.By virtue of Zhang Zhidong's celebrity promotion effect,Reading Notes of 22 Histories wass republished several times in 3 years and many versions of the book also emerged contributing to the first climax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Zhao.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historiography of Zhao was full of fame and reputation.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are deeply affected by it.The strong contrast of Zhao Yi's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different periods indicates the historical reput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norms and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criteria.Therefore,the investigation of for⁃tune of Zhao's historiography in Qing Dynasty provides a powerful reference for the acceptance of Zhao's histo⁃riography in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Besides,this study is also greatly favorable to understand the propag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Zhao.
Zhao Yi’s historical study;Reading Notes of 22 Histories;textual research;the thought of statecraft;dissemination;acceptance
K09
A
1009-1971(2017)04-0068-07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7-05-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16JJD770037)
王云燕(1989—),女,河北沧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