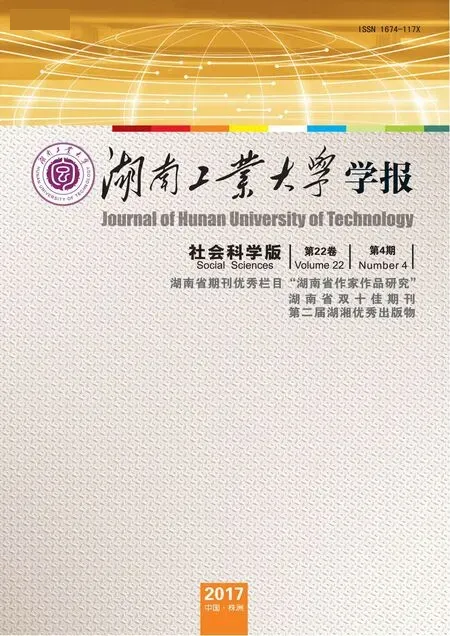网络化引起的语言变异现象研究
李 珂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网络化引起的语言变异现象研究
李 珂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伴随着全球网络的兴起和普及,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迅速转变为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进行交际的网络语言表达方式。受网络独特的虚拟交际语境、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传媒的舆论引导等因素的影响,网络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书写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网络语言变异创造了大量言简义丰、机智传神的语言符号,散发出其特有的语言魅力,引发了学界对语言变异现象的关注。
网络化;语言变异;社会文化心理;传播媒介;语言规范
Abstract: With the rise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global network, traditional language expressions have been ra-pidly transformed into network language expressions exchanged on the platform of virtual network. Influenced by the unique virtual communication context, the osmosi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the guidance of media on public opinion, network language expressions have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variations in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writing, which have created a lot of language symbols, simple in form but abundant in meaning, witty and vivid, sending out a unique language charm and triggering a wide range of attention from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Keywords:network; linguistic variations;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media; language norms
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8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1]网络交际平台逐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网络的兴起和普及,人们从传统平面媒介的语言表达方式迅速转变为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进行交际的网络语言表达方式,开启了网络语言的全新语言形式。语言反映社会的变化并为社会的发展服务,是一种社会现象。网络语言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吸收了多元文化元素的新型社会方言,是以网络作为特殊传播途径的语言系统,它已成为人们现代语言交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络语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网络语言,还有一种是广义的网络语言。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人们在网络聊天时运用各种符号组成的交际语言,如“美眉”(漂亮的女生)、“菌男”(英俊的男子)、“斑竹”(版主)等。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泛指网络时代跟网络有关的语言,如网络专业术语:网址、鼠标、联网、调制解调器、文本共享、杀毒软件等;网络特别用语:网民、挂网、网购、电子商务、第四媒体等。[2]我们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研究对象一般是指狭义的网络语言。
一 网络语言变异成因分析
“变异”最初是指语言的不同变化形式。语言层面上的“变异”主要探讨语言随社会、地域、心理等方面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变化形式。语言变异属于一种言论活动,指的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对现代汉语语言系统规则的偏离或变异。它具体可以是某些音位的组合或聚合规则;可以是某个词语,也可以是某些词语的组合或聚合规则;可以是某个语义,也可以是某些语义的组合或聚合规则。[3]网络化引起的语言变异现象我们称为网络语言变异。网络语言变异的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网络独特的虚拟交际语境、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全球网络化及传媒的舆论引导。
(一)网络独特的虚拟交际语境
网络是虚拟的世界,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里, 地缘关系、地理位置不受任何限制, 互联网成为人们实现社会参与、表达诉求的重要空间,构成完全虚拟的精神文化家园。有学者这样描述网络语言: “时空无阻碍,书写方式的更新,非语言交际主客体的统一。”[4]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也可以创造新的语言用法。不管何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均有一定的“常规”可循,这种“常规”就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言交际规范和标准,人们在相互交际时必须遵守的规则。在特定的场合或语言环境下,人们有时故意偏离“常规”创造语言新的用法,这种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就是语言变异。网络语言由于特殊的使用群体、传播手段和传播途径,在语音、词汇、语法、书写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语言新形态,变异后的语言经广泛传播并逐渐被大家认可和接受,最终成为现代汉语的一种变异形式。[5]
网络语言作为网络传播和网络文化的主要载体,人们在虚拟空间中打破常规,张扬各自的个性、差异性和多元性,争取独特的话语权,建立新秩序,网络化交际营造的虚拟世界中的个人空间使得他们摆脱了传统语言规范的制约。[6]网络语言的变异大多运用了各种谐音、缩写、杂揉的语码符号,有的还在形状上进行装饰,其灵活多变的方式体现了网民在网络虚拟世界中极力追求创新意识、追求身份认同,寻求话语平等忠诚的精神。人们在虚拟网络交际语境中尽管摸不着见不到真实的对方,但可以通过密切结合实践的网络平台,实现便捷趣味的互动、维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而且还可以不断地再扩充自己的交际朋友圈。这种方式一改网下人际关系中人情淡漠味缺失的社会现象,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现实需求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得以实现,我们称之为“数字化生存”。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
追本溯源, 从古代汉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到现代汉语的推广再到网络语言的出现,每一次语言的革命都是建立在人们的新鲜感和美学潜力不断被挑战,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不断地偏离常规的基础上而发生的。语言变异现象不断丰富语言词汇,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语言不断向前发展,有活的语言就会有无处不在的变异。陈原认为只有语言的变异才可能淘汰不适用社会需要的成分不断丰富自己。[8]换句话说,语言的变异能够使语言活力满满且富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不至于僵化。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使用传统语言(有声语言或书写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更喜欢用能直接触动人心灵的各种各样的符号进行交际。在全球网络时代的冲击下,网络语言变异成为一种社会新常态。网络语言通过语言模因的成功复制和传播形成语言变体, 为网络交际语言的语言特色及其成因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因理据。[9]语言变异体现了文化进化的规律和动态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就是承认语境变异,语言的进化。社会越进步越发展,网络语言动态性特征越发突显。纵观近十几年的网络语言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其历史动态的清晰演变路线。如“哇噻”(惊喜)一词的演变就是人们选择,接受,并被大众认可的过程。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语言这面镜子真实生动而细腻地展现了网络时代层出不穷的的事物、概念。[10]个人的经验与意识在网络互动建构的现实社会中得以呈现, 网络互动比传统互动使得人们更能够掌握主动权,网民有一定的自主创造性和话语权。这种网络互动能更好地满足网络交际的需要,全球网络化浪潮积极推动了全球多元文化的融合,网络以秒速度加快文化的传递,并迅速地广泛传播。年轻人是网络的主体,他们最有创新意识和创造力,他们有强烈的好奇心理,他们头脑中总是充满千奇百怪的思想,他们追求与众不同的个性并突出自我,他们离经叛道甚至颠覆传统,他们通过创造构思巧妙的词语来实现自身价值,以期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关注。[11]当新生事物大量涌现,人们的观念也随着新生事物不断更新,并相应形成某种社会心理或表达诉求,依靠现有的规范汉语往往不能完全表达人们的情感,语言表达系统出现暂时“缺位”现象,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变异;同时,出现了很多表达对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的态度和立场的网络变异词语,如“蜗居”“囧”“给力”“逆袭”“正能量”等词语。
(三)全球网络化及传媒的舆论引导
随着全球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网民所占据的比例持续增长, 众多的网民受到传媒的影响,独特的网络语言被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介认同、接受并借鉴。网络的传播和普及促使网络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得以彰显。各媒体纷纷对网络时事热点追踪报道,传统大众传媒中频繁出现经典网络词语,对现实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或现象进行传神解读,网络语言的广泛传播营造了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直接影响舆论导向,激发了网络语言的变异。网络传播的时效性和娱乐性为网络语言提供了很好的模仿和传播途径。在博取“眼球”效益的经济时代,网络的点击率成为媒体创新的主要指标。[12]网民从关注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发展到关注社会热点;从简单的造词恶搞发展到表征民意舆情;从对网络语言现象的追捧发展到占据掌握权力阶层话语霸权地位。
全球网络化的影响和传媒的冲击是网络语言变异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网络词语经新闻事件催生、发酵成为“热词”。如“躲猫猫”“楼歪歪”等都是来自媒体的表达。网络热词“给力”登上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网络头版头条。该稿件一经刊登,立刻引发了网民们的追捧,网民惊呼“太给力了”“给力一带一路”“给力中国足球”等词不断被模仿复制,而“给力”事件也被网民们评为“十大文化事件”。这种网络词语之所以能够被公众普遍认可,一是能够揭示社会现象,并表达民众对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的一种观点与立场;二是网民“公民意识”的觉醒,网民找不到最佳的语言来抒发自己内心压抑的不满,加上理想同现实权利之间的差距,引发了信任危机等等,如“恨爹不成刚”“被就业”等词都是在相关新闻报导中产生的。这些网络热词从新闻报导中产生,反过来又能加强新闻事件的传播和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从最初的“火星文”到而今的网络流行语,网络语言越来越被大众所接纳,人们竞相仿效与克隆,无形中加速了网络语言的流行与传播。大众媒体中的许多的言语表达形式推动了人们在社会语言生活中新的时尚趋同与流行同化,正是这种流行同化加速了语言表现形式的广泛变异。[13]网络语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在于它反映某种现实并被认同。网络语言背后隐含的网络文化体现了人们渴望摆脱平庸、枯燥、刻板的生活,追求平等的话语权。
网络语言变异的形成自有其内在与外在的原因。任何语言大体都会经历语言要发展,要鲜活、要新颖、要有生命力的发展轨迹,网络语言受到牵引与拉动,渐渐被激活类化直至同化。这就是语言变异现象产生的一条发展规律。
二 网络语言变异的特点
网络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网络语言的独特魅力来自别具一格的文字符号,网络语言中呈现的诙谐幽默、机智传神、言简义丰的变异现象比比皆是、令人忍俊不禁,是网民智慧结晶的体现。作为传统语言与网络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独特的网络语言能快捷迅速地把思维和情绪转变为语言符号。网络语言变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层面。
(一)语音变异
如今的智能监测预警技术已十分发达,若将其应用到高血压的智能分析中,可行性非常高。而且,国内已有部分社区和医院,对高血压的防治预警系统进行了相关开发与研究[9]。可见在医学领域,对高血压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其作用是巨大的。
1.汉字同音或近音谐音。语音变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汉字同音或近音谐音。语音通过汉字同音或近音的条件发生谐音变异。汉字同音或近音谐音是通过同音或近音汉字替代本字,产生辞趣的修辞格,增强汉字语音摹仿力。汉字同音或近音谐音,有普通话汉字的谐音和方言谐音两种,大多数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为了省时、省事、采用简练快捷的电脑输入模式,如使用拼音输入法交际时运用谐音字代替本字。这种为节约时间、满足语言省力原则与经济原则输入的谐音字就如雨后春笋般,随着拼音输入法的普及,遍及神州大地。如:“大虾”(大侠)、“帅锅”(帅哥)、“幽香”(邮箱)、“芥末”(这么)、“木油”(没有)等。这种语言变异表达了娱乐化、大众化、简洁化的语用原则。
2.语码混合谐音。网络语言变异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地运用各种符号,以单纯字母或数字代替原有的汉字,借用语码混合等组合谐音来表达不同效果。例如“MM”=妹妹、“PP”=漂漂、“GG”=哥哥、 “BH”(彪悍)、“596”(我走了)、“886”(拜拜了)、“995”(救救我)、“54430”(我时时想您)、“9494”(就是就是)等。
(二)词汇变异
1.派生法。派生是词法学造词法的一种,它是指在旧词的基础上衍生出新词,新词的新义和旧义有一定的联系,形式上是在词根上加上派生词缀以构成新词的方法。由派生法产生出来的词叫做派生词。派生是形态语言重要的构词方式。网络派生根据语言的语法规则以某种方式给单词增加词缀或改变它的过程,如“读+ed”“吃饭、郁闷、上网+ing”等,这些用法生动地反映了动作的状态。
2.旧词新解。旧词新解,顾名思义,就是对原有词义新的解释。网络语言中的新解往往和旧义无关甚至完全相反。比如:“潜水”(网络论坛或聊天室中只观不语的行为),“灌水”(网上发贴内容空洞的文章),“水手”(网上喜欢“灌水”的人),“菜鸟”或“爬虫”(网络交流中的新手)等。旧词新解是网络语言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也是最传神的部分,这些别有意趣的网络词语纷纷在传统媒体崭露头角,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青睐,其中很多已经成为网络语言的标识。
(三)语法变异
网络语法变异表现为语法规则被打破,语法规则的变化可以满足人们在网络虚拟的语境中情感表达的需求。
1.词性的变异。在网络用语中经常出现名词、形容词用作动词,名词用作形容词的变异现象。如,“ 我来雷一下大家。”句子中的“雷”本来是名词在这里变成了动词;“这个东西也太水了吧。”句子中的“水”本来是名词在这里用作形容词。 “好像我的博客被别人黑了。”句子中的“黑”本来是形容词在这里用作动词;“百度一下这个词”。句子中的“百度”本来是名词在这里用作动词。
2.句式的变异。网络语言变异中的语序变异和超常规句式是为了达到特定的语言效果,如,“……的说。”“……先。”“……都。”则是超常规句式的体现,“我走了先。”在语序上有悖于“我先走了。”的常规语序,如“又下班的说!”的语序超常易位,但这种语序调整并不影响交际,能满足网民们的特定的语言效果的需要。
三 学者对语言变异现象的关注
网络语言对社会的影响确实始料未及,网络语言变异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大家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人质疑网络语言变异现象,有人认为网络语言的泛滥,冲击了汉语的纯洁性,也破坏了和谐健康的语言文化环境。更多的专家学者认为网络语言变异现象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语言发展的必然,有积极的研究价值。他们认为语言规范不等于语言纯洁,应尊重目前语言文字多元化的现状。陈一舟认为:“ 网络语言表象是对传统语言规则的颠覆,实际上其背后是复杂的大众情感的表达。网络词语与社会文化现象的紧密联系正体现了网民对社会公平、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的渴望和诉求。”[14]申小龙认为“网络语言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是非常有益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表现了汉语旺盛的生命力”。[15]王先霈认为”语言不要强调纯洁,而要强调动态的、有弹性的规范。”[16]郑远汉认为特殊的言语变异现象,并非不符合或突破一般规范,而是它本身应有自己的规范标准,它和一般的语言规范属于不同层面。不能用一种尺度去评判不同层面的言语。[17]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和进化, 语言也在不断地进化,这是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同时,网络语言是社会文化生活中地位提升的标志。
网络语言变异是网民沟通交际和社会文化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语言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增强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而且,网络语言源于传统语言,不管语言形式怎样变异和突破,都不可能脱离现实语言而独立存在。网络毕竟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虚拟空间,用现实的规范去规范它,反而不大现实。新词的诞生更多的是靠约定俗成,大家共同认可,它才有生命的鲜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语言的创造性并不是对原有规范的颠覆,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更新和进步。
总之,网络语言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笼统地以“不合语言规范”“不合语法”或简单地加以排拒。依据目前这种很流行的语言现象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现实适应性、可接受的创新性等特征,也应将其视为“可能规范”的范畴,在对待网络语言变异的问题上,我们的宽容可以减少因主观判断而造成认识上的偏见并保留其所必须拥有的空间,我们应该遵循“语竞网择,适者生存”的原则。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这种独特网络语言变异现象,将会不断为语言注入新鲜血液,丰富语言的文化,并值得我们对其进一步认识与探讨。
[1] 人民网. 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6-08-03].http://it.people.com.cn/GB/119390/118340/406323.
[2] 于根元.中国网络语言词典[M].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244.
[3] 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3.
[4] 吕明臣.网络语言研究[M].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1.
[5] 樊 慧.虚拟与现实:论网络语言变异[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2):9-14.
[6] 林小董.汉语网络语言的语域角度研究[D].汕头:汕头大学文学院, 2009: 28-29.
[7] 苏新春.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7.
[8] 陈 原.语言和人[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115.
[9] 夏玉宇,李 珂.时尚网络新词的模因理据分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1):116-119.[10]百度百科.标题党[EB/OL]. [2010-12-26].http://baike.baidu.com/view/37030.htm.
[11]李 珂.时尚新词语的变异动因及其规范化[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6):111-114.
[12]李 珂.时尚“哥”族新词及其社会文化心理透视[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5):77-80.
[13]于全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研究的“非常”语言现象[J].语言文字应用,2001(1):88-92.
[14]陈一舟.所谓“保卫汉语”不过是一场虚构的战斗罢了[N].北京青年周刊,2010-01-06(10).
[15]仲伟丽.网络新语文运动:专访申小龙: 革命来了[J].e 时代周刊,2003,30(3) :56.
[16]王先霈.语言是否应该“纯洁”,是否能够“纯洁”?[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0(5):3.
[17]郑远汉.言语规范三层次[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3(3):704-709.
责任编辑:黄声波
StudyofLinguisticVariationsCausedbyNetwork
LI K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H031
A
1674-117X(2017)04-0107-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4.022
2017-06-11
株洲市社科课题“网络化引起的语言变异现象研究”(zzsk17126)
李 珂(1973-),女,湖北武汉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传播学和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