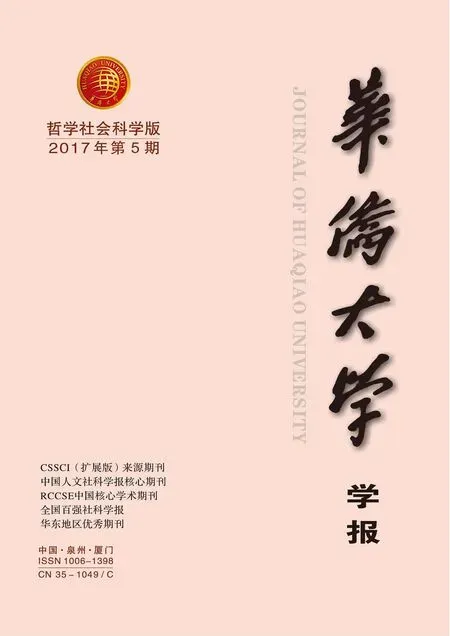论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游志强 杜力夫
论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游志强 杜力夫
家族主义是指以维护家族成员之间天然形成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为最高宗旨的社会理念,其形成有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其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主要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两大层面。进入清末之后,家族主义在“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之中逐渐式微。而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对于家族主义的因素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对此,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中,应当对家族主义采取理性的“扬弃”态度。
家族主义;中国传统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一 家族主义概述
家族主义是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概念之一,但是关于其确切的定义,尚没有一个准确、公认的概念。理解家族主义应从“家族”与“主义”两词入手。首先,关于家族的定义,《当代汉语词典》对家族的释义为:“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单位,包括同一血统的数辈人。”*《当代汉语词典》编委会:《当代汉语词典》(双色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08页。考诸中国法制史发现,在我国古代“家”的含义与范围相对确定,而“族”则多为一家几代同居或者多个家相聚而成。“一般的情形,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经济单位,为一共同生活团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单位,每一个家自为一经济单位。”*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页。结合《当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与中国古代法制史,家族是指以父为核心,血缘、婚姻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团体。在中国古代,其不仅为一共同的生活团体,而且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事业单位。*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50页。其次,关于主义的定义,主义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语言学界通常认为主义是指一种最高原则、最高理论,或为一种特定的宗旨、理念、思想、社会制度、经济政治制度等。综合上述“家族”与“主义”两者的定义,家族主义是指以维护家族成员之间天然形成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以及后天形成的婚姻关系为最高宗旨的社会理念。这种理念表现在中国传统法律上,即指中国传统法律以维护家族主义为核心任务之一,用法律的手段巩固、强化、扩展家族之中所形成的伦常纲纪。而关于家族主义的成因,主要如下:
(一)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法律最初的形成途径。探究家族主义的成因自然应当从其源头说起,即从中国传统法律的最初形成途径开始说起。中国传统法律的最初形成途径不同于西方贵族与平民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刑始于兵”。梁治平先生在对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用途进行考察之后,认为“首先,国家的产生远不是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的,相反,它保留了原有的血缘关系,把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成为国家的组织方式,从而把旧的氏族组织与新的国家形态熔铸于一。其次,国家权力严格说来并不表现为‘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是赤裸裸地族姓之间的征服和统治。”*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79页。张中秋先生亦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这个过程(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成过程)实际是它不断地对同一血缘/同族的认定和对不同血缘/异族的否定的过程。无论是在这个过程的初始还是进行之中,抑或是这个过程的完结之时,血缘始终是当时法律区分敌我、确定罪与非罪的主要标志,这意味着上古法律具有强烈的血缘性。”*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法律最初的形成途径当中包含了对于家族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的强化而非瓦解,对于家族主义的扩张而非限制。这种形成方式对于家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传统法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礼源于祭祀”亦是中国传统法律起源的另一重要路径,“礼源于祭祀”与家族主义密切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祭祀与中国传统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法律的起源。这不仅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法律有重要意义的“礼”源于祭祀,还因为宗教在中国传统法律中的特殊体现。祭祀活动在中国历代法律中都有所规定,祭祀活动是代表家族传承的重要标志,家族主义在祭祀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综上,“刑始于兵”和“礼源于祭祀”都是中国传统法律最初的形成途径,对家族主义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二)经济原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业是我国古代经济的根本,而“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页。安土重迁的传统,有利于强化家族的稳定性,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家族的封闭性。此外,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家族成员对于富有生产经验的父亲的依附,更加强化了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因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疑为家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经济土壤。
(三)政治原因—乡土政治权利的空白。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家族主义之所以能得到国家政权与法律的支持,在政治原因上源于乡土政治权利的空白。*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3-78页。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的政权体系中从来不以乡村为一行政级别,而是赋予乡村极大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即赋予乡村中的老者、族长、家长,让他们对于乡村事务进行管理。而这无疑从政治权利上肯定了家族为一基本的权利单位,进而强化了国家与法律对于家族主义的认同。
(四)文化原因—阴阳二元论的哲学观与儒家思想*陈斯彬:《儒家的良知理论和作为权利的良心自由》,《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35—43页。。中国古代特有的宇宙发生论—阴阳学说,在经过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改造之后,成为论证家族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依据。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写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夏,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16—217页。而关注人事的儒家思想,则为家族主义的存在提供了现实世界的文化支持。儒家思想向来提倡宗法制度,推崇西周的礼制,极力维护“三纲五常”,主张家国相通的理论。*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两者相合,共同为中国古人提供了家族主义的精神支撑。
(五)社会结构原因—“家国一体”。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在上文已有提及。基于这样的形成过程,中国社会发展出了特有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决定了国务以家务为原型,治家与治国相通,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相通;另一方面则决定了国家必须对家族予以保护,法律必须以家族主义为本位进行立法。
二 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法律的概念,尤其是法律所涵盖的范围,是自法律科学产生以来,法学家孜孜以求、反复探求的法学根本问题之一。面对这一问题,法学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形成了多个法学流派。“对法的定义,学者们争论不休,其中主要是自然法学和实证主义之间的对立:“自然法学认为,法(至少其‘最高原则’的核心)是直接源于自然、人的本质或者‘造物规则’。人们称这种内容随历史而变化的法为自然法。它应该存在于万事万物的本质中,而不是由国家的立法者来制定。因此,正如其定义所示,它在内容上不依靠立法者,在使用上独立于国家的立法行为。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法是权力机关根据宪法的规定所制定的法。……法制定出来之后,就只不过是统治者的组织工具和统治工具。”*[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7页。而于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法学派则立足于法律在社会之中的实际作用,从“社会控制”的观念出现,认为法律是“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8页。除此之外的其他法学派对于法律的定义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法律的定义,视角不同自然导致其定义的不同,从上述三大法学派的法学定义中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关注法律的观念与价值,实证法学派则关注法律的实际制度,而社会法学派则关注于法律的社会现实作用。由此可见,法律在存在方式上大致有观念、制度与现实三种形态,三者共同构成法律的范围,决定着法律的定义。*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总序第2—3页。基于此,关于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本文将从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观念、制度影响两个层面分别予以论述。
(一)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
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价值取向的影响—“无讼是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以“大同世界”为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为之追求、为之奋斗。《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就深深吸引着中国人,其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追求的理想社会如此,反映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上即以实现无讼为最终、最高的价值追求,如孔子所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中国传统法律之所以以无讼为价值追求,家族主义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其对中国传统法律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特有的“家国一体”的古代社会结构决定了包含司法审判在内的国政的原型即为家务。而家务的最重要任务无疑在于维护家族成员之间的和谐,使之和睦相处,安定无争。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争已是违背伦常之事,对簿公堂自然更为古人所不齿。由此可见,无讼之所以存在,家族主义为其提供了思想观念上的基础。二是在法律上实现无讼的最佳方式就是调处息争,而在古代中国进行调处息争最基本的单位即为家族。家族的存在无疑又为无讼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组织上的基础。
2.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本位的影响—义务本位。中国古代历来提倡道德至上,法律作为道德戒条最大的作用即在于为道德服务。这一法文化特征反映在中国传统法的历史进程中就是“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65—343页。其最终结果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以义务为本位,这一结果反映在立法上,就是法律成为“附加了刑罚的道德”,所有的法条即以“某某不得……若违犯……处之某某刑罚”的形式出现;反映在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之中即为权利观念的缺失。
而论及中国传统法律中义务本位的观念,不得不提家族主义在其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其一,中国古代家族主义强盛的另一面,即是个人主义的极度式微。观乎西方法律的发展史可知权利本位的兴起与个人不断脱离家族主义的束缚而倡导个人主义有着密切而直接的联系。古代中国,家族主义强盛下个人主义的式微使权利本位失去存在的社会土壤。其二,“从现代法学观念看,集团本位法实质是一种义务本位法。”*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55页。而家族主义作为集团本位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以家族主义为法本位的中国传统法律理应为义务本位法。
(二)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
法律观念通过立法的形式转化为制度上的法律。“制度的法都以具体的法典或判例作为存在的载体,或者表现为成文法,或者表现为不成文法。”*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总序第3页。在古代中国,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涉及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多个方面。
1.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民法的影响。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至今尚无定论。以台湾民法学者梅仲协和大陆法学家张晋藩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存在民法。梅仲协认为“礼为世界最古最完备之民事法规也。”*梅仲协:《民法要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5页。张晋藩教授则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为“诸法并存,民刑有分。”*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第247—277页。而学者张中秋教授则持“否定说”,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民法,“在传统中国,民事一方面被刑事化了,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数目亦是极其有限的。”*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93页。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民法是否存在尚可争论,但是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较古代西方法律体系而言,成文民法内容或存在缺失,或与刑事规范混合在一起,这尤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在这点上,家族主义的影响不可小觑。
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民法规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法存在的第一个要素为独立个人的存在。而在家族主义的束缚之下,独立的个人无从产生。“在一个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里,没有纯粹‘个人’的行为,更没有真正‘个人’的关系。”*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135页。第二,民法存在的第二个要素为法律上平等权利主体的存在。而在家族之中从来都不可能谈及平等,身份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制度长期存在于家族之中,并且通过“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扩大到中国传统社会中阶级上的不平等。如果说,中国传统法律上存在权利主体,那也只能是差等的权利主体。第三,民法存在的第三个要素为社会上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相关的人身关系的存在。而在家族主义之下,特有的血缘性、地缘性、封闭性、身份性、等级性极大地束缚了民事中财产关系的发展。*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86-94页。由此可见,家族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民法规范的影响之深刻。
2.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影响。家族主义对于中国传统刑法的影响几乎涉及我国传统刑法的方方面面,本文仅就其中最主要、最明显、影响最深刻的三大部分谈之。
第一,中国传统刑法中对于家长权的维护。探究中西古代早期法制史,发现其共通之处在于法律对于家长权的维护。家长权在罗马法中又被称为“父权”,于罗马共和国时代之前曾在罗马法中兴盛一时。对此,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父亲)握有生杀大权,对待他的子女和他的家庭就像对待他的奴隶一样没有任何限制;……子女的羊和牲畜就是父亲的羊和牲畜,父亲的财产是以他所代表的身份而占有的,而非以一个个体私人占有的。”*[英]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在人身权上父亲对儿子掌握有生杀之权,更不用说无限制的肉体惩罚权了;他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变更他们的个人身份:他可以为儿子娶妻,也可以将女儿嫁出去;他可以命令他的子女离婚;他可以用收养的方式使子女成为其他家族的成员;甚至他可以出售他们。”*[英]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第106页。但是西方的家长权在罗马帝国时期“身份到契约”*[英]梅因:《古代法》,高敏、瞿慧虹译,第130页。的社会运动之下最终泯灭于西方法制史。反观中国古代,我国传统刑法对家长权的维护可谓是从始至终,并有渐趋强化的趋势。
就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而言,中国传统刑法中对于家长权的维护大体有四点:首先,父母对子孙有除致死以外的教化惩戒之权。《唐律疏议·斗讼律》“子孙违反教令”条疏议解释:“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于事合宜,即须奉以周旋,子孙不得违犯……若教令违法,行即有愆……不合有罪。”*《唐律疏议·斗讼律》“子孙违反教令”条。另据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的相关论述,在教化惩戒子女的过程中,父母若无心致儿女死亡而导致儿女死亡的,传统刑法仅处以极轻的刑罚。若子女先有不孝之行在先,父母教化致儿女死,则可免罪。此外,父母还有权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惩戒。*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8—12页。其次,财产权上,若父母在,则儿女绝不能有私产,家长享有对家族财产的支配权。《唐律疏议·户婚律》“子孙别籍异财”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唐律疏议·户婚律》“子孙别籍异财”条。再次,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具有决定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向来是中国古代男女之间缔结婚姻的前提。而在唐朝的婚姻制度中,“婚姻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家长的统一,再经过一定的仪式,婚事便成立了。”*郑取、吉霁光、徐永康:《法典之王〈唐律疏议〉与中国文化》,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9页。最后,子女若对父亲相犯,则采取加重刑罚,不孝则是中国传统刑法中的“十恶”重罪之一。
第二,中国传统刑法中关于亲属相犯的规定。为了维护家族之中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伦常纲纪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我国传统刑法对于亲属之间的相犯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在亲属相犯的问题上,我国传统刑法“在维持家族伦常上既和伦理打成一片,以伦理为立法的根据,所以关于亲属间相侵犯的规定是完全以服制上亲疏尊卑之序为依据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42页。、“法律所重的是伦纪问题而不是是非问题。”*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48页。因此,观乎中国传统刑法,在亲属相犯的问题上,历代刑法无一例外规定了“加重与减轻”原则。此原则在西晋《泰始律》中得到了全面认可,并为后世所承袭,即“准五服以治罪”的罪刑适用原则。“所谓‘准五服以制罪’,是指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依据五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定罪量刑。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罚愈轻;以卑犯尊,处罚愈重。”*张晋藩、朱勇:《中国法制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由此,我国传统刑法在杀伤罪、奸非罪、窃盗罪中对于亲属之间的相犯均依此原则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8—62页。
第三,中国传统刑法中的“容隐”制度。中国传统刑法自汉代以来就有“亲亲得首相匿”的“容隐”制度。这一制度的由来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孔子之言。孔子曾云:“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至汉宣帝地节四年,汉宣帝正式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从此,“亲亲得首相匿”的“容隐”制度得以正式进入我国传统刑法,并为后世封建历代所扩大沿用,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唐律疏议·名例律》“同居相为容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唐律疏议·名例律》“同居相为容隐”条。其后的《宋刑统》《明律例》《清律例》中皆有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参见《宋刑统·名例》卷六;《明律例·名例》卷一;《清律例·名例律》卷五。而论及此制度的产生缘由,从孔子之言与汉宣帝的诏书中即可看出家族主义在“容隐”制度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3.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家法族规的影响。家法族规,正名定义,便可知其为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影响的直接体现之一。由于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权利的相对空白,国家便将乡村的治权托予乡村中的老者、族长、家长。而他们依何而治呢?一方面,他们依国法而行;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他们依家族伦常纲纪的直接立法化—家法族规而行。关于家法族规的内容,其一方面是对国法的细化规定,另一方面则为家族伦常纲纪的立法化。对于家法族规的内容、作用与国家的关系,张中秋先生对此有一段颇为精辟的概括:“它是宗族权贵为了维护宗族社会秩序,同时亦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国家法律、民间习惯及纲常礼教为原型,删减增补,加工整理,使其成为在宗法家族内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家法族规以宗族自身和国家的力量作为其强制执行的保证,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为直接目的,因而起到了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可谓是国法的重要补充形式,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体系主要由这两者构成。”*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53页。概而言之,家法族规实为家族主义的直接立法化。
三 家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随着清末“变法修律”的开始,古老的中国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随着此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对于法律的影响逐渐式微。自民国时期起,在全面西化的立法运动之下,家族主义在法律制度上完全失势,“虽然作为历史惯性、民间习惯和法律意识的影响依然存在,尤其在民间和乡村,但在制度上已然式微。”*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55页。这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在中国的发生时间短,但进程却极其快,而这场运动的关键之处即在于家族主义的解体、个人主义的兴起。并且,毫无疑问,这项运动将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无疑具有鲜明的进步色彩,它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确立个人的独立地位,对我国“契约社会”和民法的产生、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此外,个人创造力在运动中得到极大的解放,无疑将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与动力。但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中所具有的“形式主义倾向”和“非理性”因素,也反映出对中国传统法律中家族主义的影响有一些矫枉过正的地方。
对中国传统法律中家族主义因素的矫枉过正,主要体现在“容隐”制度上。中国传统法律自汉代以来就确定了“亲亲得首相匿”的“容隐”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大清律例》未有实质变更,前文已有论述,在此兹不赘述。“容隐”制度,就其大意而言,是指自然人犯罪,作为其亲属者可以知而不告,司法官员调查证据进行询问时享有沉默权,甚至还可以给有罪的亲属通风报信,资以财物,助其逃亡,法律对此类行为皆不予惩罚或减轻处罚。*参见《唐律疏议·名例律》“同居相为容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但是,为了防止此项规定违反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我国传统法律通常在谋反、谋大逆与谋叛等重罪上对“容隐”制度的适用作出了限制甚至禁止。*参见《唐律疏议·名例律》“同居相为容隐”条规定:“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关于“容隐”制度的立法理由,率先确定此制度的汉宣帝在诏书之中说得很明白:“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汉书·宣帝纪》。易言之,“容隐”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在于维护家族主义当中的伦理纲纪。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容隐”制度的规定已经被全面摒弃:第一,就隐匿犯罪的自然人并助其逃亡的亲属者而言,我国现行《刑法》第310条当中对于窝藏、包庇罪明确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显而易见,包括亲属在内的任何人均不得窝藏、包庇犯罪分子,否则即可根据此条论罪科刑。第二,就作证而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包括亲属在内的人均有作证义务。当代中国的刑事立法彻底废弃“容隐”制度的做法是否得当?本文认为,这种废弃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当中的家族主义因素有矫枉过正的倾向,立法有失偏颇,其理由有三:
其一,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而言,“法律秩序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它必须达到被认为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的最低限度。任何法律秩序都是以道德的价值秩序为基础的。”*[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第180页。“容隐”制度,一如汉宣帝在诏书中所言,实乃维护人间的至真亲情,保护人间最基本的伦常,实际上为“道德规范的最低限度”之一。立法上废止“容隐”制度,无疑与“道德规范的最低限度”相违背。另一方面,就当今我国刑事立法彻底摒弃亲属“容隐”制度的社会影响而言,用法律强行规定“大义灭亲”行为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亲情的彻底撕裂,此为偏颇点一。
其二,就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典”而言,其传统法律与中国大陆同出一源,但是在“容隐”制度的继受上却出现了差异很大的做法:第一,对于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亲属者,台湾地区“刑法典”第162条“纵放或便利脱逃罪”第四项明确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亲等内之姻亲,犯第一项之便利脱逃罪者,得减轻其刑。”第二,在作证义务上,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80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一、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二、与被告或自诉人订有婚约者。三、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现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诉人为其法定代理人者。对于共同被告或自诉人中一人或数人有前项关系,而就仅关于他共同被告或他共同自诉人之事项为证人者,不得拒绝证言。”由此可见,台湾地区“刑法典”在“容隐”制度的继受上采取了极其理性的态度—“扬弃”:在窝藏、包庇罪犯上,对于“容隐”并没有采取全面摒弃,而是进行了“减轻其刑”的规定;在亲属的作证上,全面继受“容隐”制度的同时又在关于“共同被告或自诉人”的作证中作出了限制。立法可资赞成。反观中国大陆地区的刑事立法,偏颇之处更趋明显,此为偏颇点二。*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刑事立法亦有关于亲属“容隐”制度的规定,参见中国香港《诉讼证据条例》第6条,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21条。
其三,就世界其他国家的刑事立法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皆有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1998年颁布的《德国刑法典》分则第21章规定的是“包庇与窝藏罪”,其中第257条规定了“包庇罪”,第258条“使刑罚无效”第6项专门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现行《法国刑法典》第434-1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了解某一重罪,在其尚有可能防止该罪发生或可以限制其后果时,或者在罪犯有可能实行新的重罪,但可予制止时,却不将此种情况告知司法当局或行政当局的,处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第2款规定:“除针对不满15岁之未成年实行的重罪外,下列人员不属于前款规定之列: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以及这些人的配偶;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配偶或者众所周知同其一起姘居的人。”1994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被指控人的订婚人;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与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证人可以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的近亲属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此外,与我国相邻的日本、韩国*参见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第3款,1953年《韩国刑法典》第151条。亦有关于亲属“容隐”制度的规定。由此可见,“容隐”制度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普遍规定之一,中国现行刑事立法彻底摒弃亲属“容隐”制度有违国际刑事立法的普遍趋势,此为偏颇点三。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在“容隐”制度上的立法存在一定偏颇。对此,本文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对古老的“容隐”制度加以“损益”、加以“限制”,而非矫枉过正之下的完全废弃。这种完全反传统的法律规定,完全违背亲情的法律规定,造成的只能是法律与道德的脱节,只能是人们的法律规避。*参见陈世伟:《“亲亲相隐”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启示》,《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2期,第23—29页;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87—104页。
家族主义当代价值还体现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可以借鉴家族主义的合理内核,以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家族主义的合理内核在于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而“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永远是法律的内在生命和基本价值之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无讼为价值取向突出体现了它对这一使命和价值的优先考虑和全面追求。即使从现代法学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价值所在。或许还可以这样认为,无讼即是理想又是对现实秩序稳定的努力,它不仅满足了人们普遍的心理欲望,也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积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属性出发,说其合理必然也是恰当的。”*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其终极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治理的和谐,“和谐”是中国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对现代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参见郑玉敏:《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37—42页。诚如此言,和谐理念始终贯彻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实践当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即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非纠纷解决机制的分裂,而是建立在统一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多元。在深受家族主义影响的传统社会中,民间社会和非诉纠纷解决体系不但不会与政府对立,反而会发挥积极作用,辅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核心价值上的一致性,这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其核心在于在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诉讼与非诉解决方式中贯彻民主、法治、保护个人权利与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秩序的统一价值观。这样才能保障“多元”服务于“统一”,才能使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共同致力于建立和谐、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参见邹亚莎:《传统无讼理念与当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法学杂志》2016年第10期,第73—79页。
四 结语
如今,依法治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曾引用韩非子“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演讲时说,“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了很多法家的经典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他在《之江新语·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就引用“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由此可见,法治建设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而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乃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都有着重大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对于传统的家族主义乃至其他中国法律的传统应当采取理性的“扬弃”态度,使之更合于民间习惯、传统,并能最终超越传统、超越民间习惯。我们应当坚信,唯有这样的法律体系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才能构建出中国特色的法治,才能构建出成功的法治。
【责任编辑龚桂明 陈西玲】
OntheInfluenceofFamilyDoctrinetotheChineselaws
YOU Zhi-qiang,DU Li-fu
Family doctrine refers to the ultimate social idea maintaining the blood relationship and relatives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embers,its formation has reasons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economy,politics,culture,social structure,etc.Its influence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ws lies in the two aspec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views and legal system.When coming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the family doctrine gradually came to weak in the movement “from identity to contract”.But there is an overcorrecting tendency to the family doctrin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o we should adapt the reasonable “sublation” attitude to i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amily doctrine;traditional Chinese law;the contemporary socialist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游志强,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湖北武汉 430072)。杜力夫,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福建福州 350117)。
D929
A
1006-1398(2017)05-0073-10
2017-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