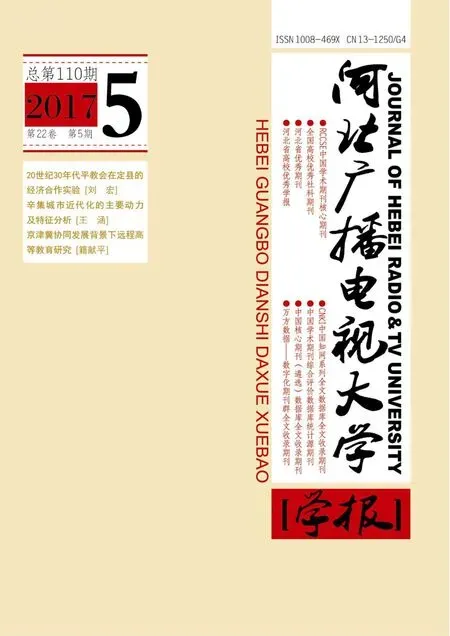团圆之思与悲悯之光
——试论《小团圆》对父亲形象的重写
曲芳莹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团圆之思与悲悯之光
——试论《小团圆》对父亲形象的重写
曲芳莹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小团圆》以对过去之事的书写重回当时的生活场景,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在早期自传散文中,张爱玲对父亲多为怨恨和批判,而在《小团圆》中却充溢着对“遗老父亲”的理解和释怀。对父亲形象的重写与其平静节制的创作心境及“向内转”的读者意识的变化有关。在对父亲形象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张爱玲也在寻求与父亲的隔空团圆,作品充溢着悲悯、温情之光。
《小团圆》;重写面向;重写原因;团圆与悲悯
自20世纪40年代凭《传奇》《流言》初登文坛,张爱玲本人及其作品一直是评论家和学者热议的对象。从20世纪40年代锋芒毕露到50-70年代由于时代政治原因销声匿迹,再到80年代随旅美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等相提并论,并提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而浮出历史地表,90年代以来随着作品和传记的出版,关于张爱玲的研究方兴未艾。2009年,其自传性小说《小团圆》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更掀起了新一轮研究热潮。《小团圆》讲述了主人公九莉童年至三十岁的家庭生活和爱情经历。从初版至今,对《小团圆》的研究集中在文体研究、晚期风格研究上,缺少将其放在张爱玲总体创作中研究的宏大视野。本文将《小团圆》与张爱玲早期自传散文中关于父亲的建构置于同一层面,探讨《小团圆》对父亲形象的改写与重构。
一、“遗老父亲”的重复书写:由怨恨到理解
1975年,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首次提到《小团圆》:“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2](P2)张爱玲坦言,《小团圆》讲的是自己,文中讲述的“被父囚禁”“港战爆发”等事件都与她自身的经历如出一辙,带有明显的自传性。作为自传小说,其与张爱玲早期散文有明显的互文性。张爱玲曾写道:“《小团圆》因为情节上的需要,无法改头换面,看过《流言》的人,一望而知里面有《私语》《烬余录》港战的内容。”[2](P6)而这两篇散文都带有自传性。在确认《小团圆》具有自传性及与前期散文有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下文将《小团圆》与张爱玲早期散文中所刻画的父亲形象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其重写的不同面向。
其一,在对“遭父毒打并囚禁”这一事件的叙述上,前后期作品有不同的表述。在《私语》中张爱玲用三千余字细致地描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到母亲家住了两星期,回家后,后母以“我”未告知她为由“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却诬陷“我”还手打她,接着,张爱玲记叙了自己被父亲殴打的过程: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2](P6)
而后,父亲用大花瓶砸向“我”并“要用手枪打死我”,后又将“我”监禁在空房里。《私语》写在张爱玲挨打后不过几年的时间里,她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并且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详细的动作、心理刻画,接近事件的真实情景。
而在《小团圆》中,对同一事件只用了两段文字来讲述,情感节制且极为精练:“翠华下楼来了,披头便质问怎么没告诉她就在外面过夜,打了她一个嘴巴子,反咬她还手打人,激得乃德打了她一顿。”[2](P112)叙述略去了激烈的肢体和言语冲突以及强烈的情感体验,用一百余字平静地将事件交代清楚,与《私语》中的详尽描写相比已极尽克制,情感也由激昂愤恨转为苍凉式的淡定。
其二,《小团圆》对父亲形象进行了明显的重构。在《私语》中,张爱玲曾说:“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父亲家里的一切,鸦片、私塾先生、章回小说,什么我都看不起。”[3](P113)父亲不复是传统话语中高大阳刚、慈爱勇敢的形象,而是落后自私、无爱卑琐的形象。而在《小团圆》中,作者将父亲定位成一个生错了时代的、无能为力的多余人。在时代变化的洪流中,作为封建遗老的父亲也曾有过努力,但终因思想的落后而无法谋生。他始终抱有幻想,渴望家庭幸福,但他的愚昧落后使他与新潮现代的母亲之间的鸿沟日渐加深。同时,《小团圆》突出了对温情父爱的刻画。父亲把九莉仿照《红楼梦》创作的章回小说认真读完,还帮她拟章节回目。“他绕室兜圈子的时候走过,偶尔伸手揉乱她头发,叫她秃子……多年后才悟出他是叫她Toots(译为:亲爱的,笔者注)。”[3](P85)在《小团圆》中,作者同情生于落后时代却被迫卷入社会转型的遗老父亲,充满温情地对其进行建构,而不仅仅是《私语》中所贬抑、去势的父亲形象,实现了对父亲形象的重构。
在《小团圆》中,对父亲形象的重复书写不只是单纯的再述事件,更多的是去冷静地“审父”,并挖掘出其可悲、可怜又充满人性温情的一面,重构了转折时代、新旧之交关于家族、人性的记忆图景。
二、重复书写原因初探
如前所述,《小团圆》对同一事件和父亲形象进行了重构。对先前经历的重复书写是去国怀乡的张爱玲创作的一大特色。现以《小团圆》为切入点,探讨其重复书写的原因。
首先,在创作《小团圆》时,张爱玲的心境由20世纪40年代的铺张宣泄转为平静节制。弗洛伊德指出:“当我们将引发症状及产生情感影响的那个事件的记忆重新追回,当病人将整个事件及其后果极尽详细地描述之后,那个歇斯底里症状便立刻、永久地消失了。”在重新回顾父亲带来的痛苦经历的过程中,张爱玲试图抚平创伤,用平静老练的姿态反思自身和理解父亲。
在讲述“弟弟挨打”一事时,张爱玲在前后期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在《童言无忌》中,作者看到父亲打了弟弟一个嘴巴后:“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3](P96)由叙述话语可知,当时作者心情激动、气愤,带有青年时期的委屈气愤和打抱不平。而在《小团圆》中则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翠华在烟铺上低声向乃德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大眼睛里带着一种顽皮的笑意。乃德跳起来就刷了他(指弟弟,笔者注)一个耳刮子。”[2](P99)中年张爱玲以旁观者的身份对这一事件进行冷静审视,不再单纯地将过错归咎于父亲,而是也看到了弟弟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面。林幸谦在谈及张爱玲创作特点的转变中说道:“整体来说,张爱玲的作品,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作品较富于张力……而后期的作品,张爱玲的书写笔格则有回归理性冷静的迹象。”[4]后期张爱玲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上放弃了感性奔放的情感,取而代之以冷静理性的叙述,还原事件的真实情景。
其次,读者意识的变化也使张爱玲在后期作品中对人物形象进行改写。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的读者定位是“文理清顺”“世故练达”的上海人,她深知这类读者感兴趣的是如“传奇”般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作品。深谙读者心理使得张爱玲在创作中刻意夸大情节的传奇性,以激烈的矛盾冲突和跌宕的故事情节支撑文章。在前期作品中对父亲的刻画强调其动作,采用诸如“打”“砸”“杀”等强烈刺激性的字眼来吸引读者眼球,从而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并使文章销路更好。
而在创作《小团圆》时,这种功利性的读者意识发生了改变。在与学者水晶对谈的过程中,张爱玲提到自己“还债”的心理动机,晚年的写作是为实现早年的心愿。这种明显向内转的创作动机使得张爱玲不再刻意取悦读者,而是注重对自己心灵的忏悔和救赎。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回到事件发生的情境中,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情境中真实的自我和他者,挖掘出父亲可悲、可怜的一面,从而以文章的形式对父亲进行追忆和忏悔,以宽容、理解的心态达成了与父亲、更是与自己的和解,清算了少年时期凝结于心的历史伤痛,最终实现了心灵的救赎。
三、重复书写的终极追求:团圆与悲悯
学者西维尔·蒙漏在研究自传这种文学形式时提出,情感相对于具体事实更具有研究价值。在《小团圆》对父亲形象的改写中,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是作者在重构父亲形象时的情绪与感觉。笔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张爱玲在写作《小团圆》时,带有明显的悲悯意识以及寻求团圆的渴望。学者王学谦提到,张爱玲早期作品带有以悲悯为底调的“苍凉”美感,而这种悲悯底调在其晚年创作的《小团圆》中表现得更为深刻。
创作《小团圆》时,由于与故人旧事有了时间上的隔断,且长期旅居海外,张爱玲能够冷静、客观地审视父亲。他的古典内蕴和奔波于生计的努力由于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进程和时代的变化而充满悲剧性,他只能是被社会抛弃的可怜人。对这个生错了时代的多余人,作者的情感由批判、讽刺变为深切的心痛与惋惜。在张爱玲笔下,时代是一种“惘惘的威胁”,生存在其中的人无法摆脱困境和绝望,只得听从于命运的安排。在这种苍凉的背景下,张爱玲的作品倾注了对人物的深沉的爱,更是一种理解和深切的悲悯。正是对时代、人性的充分认识,张爱玲完成了对父亲的重复性书写,并且不再局限于刻画其负面形象,更多的是对其温情形象的建构。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将其一生所经历的人情世故、家国之变穿插讲述,采用“草蛇灰线”式的笔法将读者带入回忆的多个面向,这些人物和事件也完成了终极见面,既是在小说中的团圆,也是一次历史的重逢。而作品中作者对人物的叙述也偏向温情、客观的零度叙事,在理解和同情中重构父亲温情的一面,最终在作品中完成了与父亲的和解和清算,也代表了后期去国离乡、深居简出的张爱玲主动实现与父亲的最终团圆的热望。正如她自己所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同时实现了对自己的救赎。
四、结语
《小团圆》自2009年出版发行以来,评论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有评论家认为,《小团圆》结构混乱、晦涩难读,已经全然失去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创作中的华美流光、灵动飞扬的气质;有评论家忽视张爱玲晚期仍笔耕不辍,改写《红楼梦》和自传冲动的事实,将张爱玲简单地归为现代作家之列。在笔者看来,《小团圆》被誉为“张爱玲的又一部巅峰杰作”着实名过于实,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实现人物、事件的历史性团圆,张爱玲与自己、与过去达成了和解,也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改写表现了中老年张爱玲的忏悔和宽容,这对她本人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父亲形象的改写研究是探讨张爱玲晚期创作心态和写法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值得深挖的文学现象。
[1]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54.
[2]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张爱玲.流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4]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9.
TheThoughtofReunionandtheLightofCompassion——OntheRewritingofFather’sImageinLittleReunion
QU Fang-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Eileen Chang’s novelLittleReunionreturns to the past through the writing back of the scene of life at that time with an obvious nature of autobiography. In the early autobiographical prose, Eileen Chang expressed much resentment and criticism for her father, whileLittleReunionis full of understanding for the old father. The rewriting of father’s image is related to the mood of calm and the change of reader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Eileen Chang is also seeking a reunion with her father, the work is filled with light of compassion and warmth.
LittleReunion; rewriting orientation; reasons for rewriting; reunion and compassion
2017-07-08
曲芳莹(1993-),女,山东潍坊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作家作品研究。
I207.42
A
1008-469X(2017)05-00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