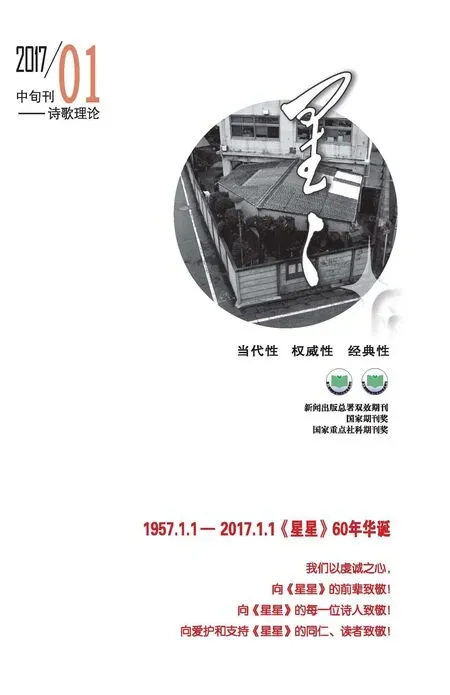对生存的深刻哲思
房 伟
对生存的深刻哲思
房 伟
在众声喧哗的诗坛,诗人散皮创制出了别样的审美空间。散皮是一位懂得生命艺术的诗人。他的诗作,既有洞察人间世相的烟火气息,又有超脱世俗的哲学思考。他不流于低俗的口语进行空洞的呐喊,也无形式实验的造作。散皮的诗,是生命的诗。高蹈独立,低调睿智,不刻意求新却处处创新。他以敏锐的洞察力,警觉于“科技万能论”带来的生存困境,警觉于个体和现代文明共谋之后的异化形态。他从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中,展现人的精神状态及其异化行为。他所要表现的,并不止于叙述表层。而是深入现实的肌理,以极为常见的场景,对人的生存位置作形而上的思辨。
一、苍白的生存景观
面对工业文明下人的生存状态,散皮有着深切的忧虑和质疑。这一点与美学浪漫主义者卢梭相契合。卢梭认为,历史的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和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的。在建设性的正值增长中,内含着破坏性的负值效应。而散皮所处的时代,正是科技理性带来巨大狂欢的时代。人们沉湎于科技文明的正值增长,迷恋于无限膨胀的物欲。却无视高度文明带来的苍白生存景观。散皮具有诗人与生俱来的敏感和警觉。他以平实而干净的笔质,将一幅幅繁华虚景定格,以此来显示人们两难的生存窘境。面对城市,散皮有着巨大的恐慌和焦虑,“笃笃的踱步排山倒海/道路逐渐合拢/街/其实空着”(《2015,街景》),身处繁华的都市,面对鱼贯而出的人群,诗人的心是空的。“新闻都是城市的腰酸腿疼/削山采石/倒下了一具风景的破旧尸体”(《不是我一个人战斗》),这是一个被谎言遮蔽的时代,新闻掩埋了城市残忍的真实。“一盘驴肉端上了食谱/查了下百度/驴/无毒”(《庆功宴》),于生存的安全隐患中,人们极力从网络中寻找安全感,并甘愿成为网络的附庸。在诗人眼里,工业文明的代价是巨大的,他试图构建另一个常态世界来影射当下现实,“那里有梦没有魇/魇的形状都被人供养/失去了梦行天下的清澈与凉爽”(《另一个世界》)。他感慨于城市噩梦对生命之种的扼杀,“他一定这么想着/这么留下来/躺在马路上/等待风生水起”(《马路上,一粒种子》)。“月亮找不到沉入湖底的空间/只好隐现在雾霾中”(《大明湖》),工业机械所带来的雾霾恐慌,淹没了人类诗意生存的栖居地。当旖旎的自然风光也只能成为记忆空间的一部分,“与虎联在一起/只因为虎啸的泉水/早已成为稀有动物”(《黑虎泉》)。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我们,究竟可以生存在何处?这是散皮留给我们的疑问。
二、畸形化的精神形态
在缺乏诗意的生存窘境中,人们畸形化的精神状态是散皮最为担忧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明的道德乃是被压抑本能的道德。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经说过:“必要劳动成为一系列本质上非人的、机械的、例行的活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工业文明的机械化劳动中,人的本能被深度压抑。在不同程度上,这种压抑可能产生两个结果。要么导致人对欲望的畸形渴望,要么导致人失去生存的诗情,变得呆滞机械。诗人散皮,以悲悯的情怀,捕捉人之精神被工具理性劫持的过程。他力图从日常生活的底色中,挖掘战栗的灵魂。不同于一般的生活化描写,散皮将生活的边缘场景和时代元素进行糅合。从而发现脆弱的精神形态:孤独、恐慌、疲惫、机械、麻木、自我分裂、多疑、敏感……在城市的尔虞我诈中,人们极度缺乏安全感,即使是在睡梦中也忐忑难安,“蹑手蹑脚进入浅睡区/并在那里不动声色观察睡姿/直到完全看不出秘密”(《清醒》)。“里面的人似乎刻意在复制我的生活/却把我的生活布置成谋杀现场”(《镜子里的影像谋杀了我》),这是人们于紧张的生活压力下,孳生的意识分裂,人们所追逐的欲望深渊正是生命的坟墓。“我的凝视使我迷失在另一度时空/对我的凝视/令人毛骨悚立”(《恐惧》),这是人们窥探自我隐秘心理的恐惧。“我发现我还是像极了某某/好像越来越想念某某/某某/反正不像自己”(《他人》),被网络所奴役的我们,正不知不觉失去了个性的独立,而成为他人“某某”。“我的疆域比心辽阔/我的睡眠比夜晚更多/但我渴望进入狼群”(《独狼》),在抒情主体“狼”的孤独中,寻而不得的归属感也正是人类的心声。面对人们因欲望而多疑敏感的神经,诗人冷眼旁观,“‘像我一样的人时刻盯着我的言语’/隐藏不够深/泄露些许春光/一定是有人告密”(《天性》)。人们为一群家雀的迁徙而惊恐不已,“行人惊慌于天象异常/疑惑的眼神相互问询”(《惊恐,抑或抗议》)。“与生俱来的宿命紧紧卡住了时间的出发地/忘记了叹息、焦虑和回眸”(《今年夏天不同》),我们奔波于现代化的陷阱,导致技术思维的单向,只知道前进却忘记了思考。面对当下精神状态的隘化,散皮以诗求证,精神应于何处安放?
三、生命意志的建构与精神家园的寻找
散皮对物质和精神双重困境的揭示,并未停留于简单的表层描述,而是极力寻找生存困境的出口。他以丰盈的生命意志建构反抗的主体,以哲理化思考寻找精神家园。首先,在他看来,只有具有强力意志的生命,才能突破机械文明的枷锁,到达自由的状态。在他笔下,万事万物都是灵性的存在。他将坚韧的生命意志赋予一草一石、一砖一瓦,并以它们为抒情主体来反抗“异化”。“再小的颤动/总得有一种方式活着/再高的飞升/也是现在”(《暴雨夜,另一滴雨》),这是一个能思考的“雨滴”,它呈现着孤傲的生命尊严。诗人对生存现状的逃离,以“石头”倔强的姿态来完成,“它们试图跳出当下生存状态/走自己的路”(《逃离》)。“水/雕刻着我/我/描绘了水/内心只剩坚韧”(《与水为敌》),这是“钟乳石”对内心坚韧的独守,也正是诗人对一片绝美风景的独守。“柏树”紧密相连的家族根系,正是作者对丰盈意志的呼唤,“只有强劲的野草四处繁衍着/陌生人看不出地下紧握的家族根系”(《邻近的痛》)。其次,作者希望从古典的人文气质和西方先哲那里寻求精神的出口。然而散皮的寻求姿态,虔诚而不恭维。在诗人恣肆的想象里,与康德把酒言欢,讨论生存哲思,“有多少虚妄被当做真实/哲学/让上帝蒙羞”(《暗夜之思》)。对夏娃与苹果的故事起因,进行新的解读,“一支小苹果竟然成就了人类,从一维爬向四维的神话”(《苹果》)。诗人以生命时间的逆行来消解崇高,“我们设计多种想象把事件还原/让掉到牛顿头上的苹果/返回到树枝”(《万有引力》)。散皮写了许多关于时间的组诗,希望从时间与存在中追溯生命的启示,如《时间的过往》、《时间之门》等。最后,诗人为颤抖的灵魂描绘了理想的精神家园,即未被现代文明染指的故乡。那是长在诗人记忆中的、干净的、神圣的存在。在《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因为穷,才有意义》、《故乡》中,诗人多次以热烈的笔触提及。
四、多元自由的艺术表达
诗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呈现和精神出路的寻找,以多元而自由的艺术方法呈现。首先,散皮的诗歌语言是自由的,消解了诗歌本身的框架,具有叙事化倾向。例如《一次午宴的再认识》一诗,以具有较强故事性的情节展开。散皮的语言是具有极强包容性的,写景诗有着古典诗歌语言的端庄,“初见面”、“长相忆”、“其声音约约/其笑貌也约约”(《途径芜湖,未晤詹声信》);叙事诗则融入时代元素,“朋友圈”、“WiFi”、“碰瓷”、“自媒体”、“春晚”、“《爸爸去哪儿》”……两种语言的底色一正一反,亦庄亦谐,耐人品察。其次,在散皮笔下,诗体也是自由的,时而散漫,时而严谨。《庆功宴》以百度说明书的体式展开,极为幽默;楼梯体式的诗歌更是巧妙新奇,不仅是在字数、节奏上错落有致,而且在诗歌题目、诗歌意象上前后对应,如《一个早晨的人生,不是人生的一个早晨》。另外,诗人擅于通过多样化的叙述视角,陌生化的比喻来塑造审美空间,如《狗眼人间》、《最后的忠诚》中,以动物的视角,来描述人类的生存状态。更为有趣的是,散皮以消解崇高的姿态,进行文本的戏仿。“春暖花开时想着姐姐/面朝大海/关心着狗粮/柴草和旅行”(《致X死党》),这是对海子诗歌的戏仿。在《2015,街景》组诗中,从“父亲的独轮车”到“山海经”、“金字塔”,这是对精英文化的解构。
散皮的诗歌以独特多样的手法,呈现他对生命的深刻感悟。活在当下,工业机械统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行动是迟缓的,精神是变形的,我们到底该生存在何处?然而只有丰盈的生命意志才能到达散皮的精神家园。正如作家王小波所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