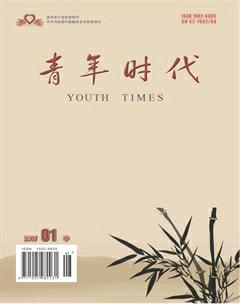戏剧视角:舞台上的英雄
李霁琨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前继卡夫卡的荒谬文学之开局,后接荒诞派戏剧的发展,加缪在荒诞题材上成为了一个接力者。面对动荡时代给予人类的困境,人们先是如K“仰望城堡而不得入”,随后又时如默索尔“对世界怀有至深的乡愁”。在尼采式的虚无命题之后,人们又面临一种归属感的空虚。或许是罪恶深重的战争抛给人的议题太过沉重。在那个仍为现代性所统摄的时代里荒诞派艺术家最先鼓起勇气以荒谬为主题,揭露世界的悲剧情景,展现人们对归属的呼唤。当荒谬被描述得日臻完备,时机变成熟了,荒谬需要上升。在《局外人》与《卡利古拉》之后,加缪决心制造一篇神话,为荒谬解说,于是,在《西西弗斯的神话》里,帷幕已经拉开,一个英雄出场了。
“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的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作为一部论集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其寓言部分仅呈现与全书的最后一小节内。加缪为这本论集加上的副题是《论荒谬》。也正是在对荒谬问题的讨论中,气氛逐渐上升,西西弗斯的面目逐渐显现,在一种类似与歌剧的回环重唱中最终的激情在西西弗斯身上得以爆发。荒谬至此达到了加缪式的超越。出于对西西弗斯力量根源的探求,我们需要回到加缪对荒谬的观念之中。
“……这种心灵的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空无成为不容争议的事实,日常连续的行为中断了,而心灵徒劳的寻求重新链接这些行为的纽带——那么,他就被看作是荒谬的最初信号。”
“有时诸种背景崩溃了。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吃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
“它的怪诞之处就在于:发现世界是“密封无隙”的,发现一块石头在哪一点上是怪异的……世界逃离我们,因为它又变成它自己。世界的这种密封无隙和陌生,这就是荒谬。”
“在人本身的非人性面前所产生的不适感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乘坐‘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谬。”
“最后,我转到死亡以及我们由之产生的感情的问题上来。”
在加缪对荒谬的阐释中,存在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荒谬概念携有本身的模糊与多义——若要试图归纳,其间至少有两种维度:在外在维度上,我们可以借用萨特所说的“脱节”或者使用加缪自己的表达“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在内在维度上,荒谬作为一种情绪的“荒谬感”在词性迁移后则进一步代表了流放,失落与乡愁。
与尼采的虚无主义情景不同,加缪作为一位剧作家,更多是发现那种“演员和布景的分离”的荒谬。这种荒谬的类型更接近于《城堡》形式的荒谬感。这也正是我们在“唐璜”“演员”“哲学与小说”“荒谬与创作”中所看到的。在基于荒谬在加缪本人以及卡夫卡的作品中已然含涉了太多话题,《西西弗斯神话》的工作是试图把其含义引向一个更为熟悉的空间。
在荒谬后续的上升中,加缪论及亚里士多德,胡塞尔,雅思贝克斯,舍斯托夫,克尔凯郭尔等一众哲学家,他在这里表现出的轻率招致了批评家的微词。但是正如加缪随后所言,“问题不再是去解释或找寻出路,而是要去经历,去描述……描述,这是一种荒谬思想最后的企望。”此时,只有遵循加缪的立场才有可能进一步理解荒谬的发展。
“在与荒谬相遇之前,芸芸众生是为着某些目的而活着,他们关心的是未来和证明(证明谁或证明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们惦量着自己的机遇……而在(意识到)荒谬之后,一切都被动摇了。“我所是”的这个观念,我把一切都看作有某种意义的行动方式(即使我有时可能说实际上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一切都被一种可能的死亡的荒谬感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揭露无遗。”
“顾忌明天,确定目标,有所偏好,这些都预先假定了对自由的信仰,即使人们有时确认并没有体验到这种自由”
“死亡犹如惟一的真理在那里存在,在它之后,一切则成定局。”
这又是荒谬的一次上升。荒谬在人的内外游离,但是作者并不计划给广泛的荒谬现象一个定义。相反,他在如上的的荒谬的类比中展示了一些趋向艰险的处境。在他的推演中,我们看到了类似默索尔的生存情景。类似的,加缪对死刑犯没有未来,“只關注纯粹的生命火焰的自由”表示出独特的“欣赏”。西西弗斯的出现至此拥有了背景。
在介绍西西弗斯之前,我们至少还需要顺着荒谬之路考察一个颇为关键的行动的十字路口:“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更关注“后果”的加缪在开篇设问,即为发现荒谬之人谋划了几种可能的方向①形体的自杀。“自杀一如逃避,根本上是一种接受。”自杀是一种最彻底的绝望。②选择宗教以求希望(哲学性的自杀)。加缪在这里特别批评了克尔凯郭尔的“信仰的飞跃”。③或者,选择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反抗者。
英雄的出场需要一个壮观的布景。在创设舞台的过程中,荒诞的处境被最终加以提升,并构成了西西弗斯的命运。舞台与背景,此处的的西西弗斯不再是希腊神话的人物,他是被加缪创作的。如果说此前的默索尔承担的是一种日常的虚无,那么当西西弗斯开始登山,他的道路本身就是带有哲学意味的——极致的荒谬。西西弗的悲剧性也就在于他命运彻底的无意义,这是也是众神权制下最可怖的一个玩笑。在这种极致的维度下,西西弗斯的处境拥有了向人间荒谬投影的权力,他的命运也成为了一切人类虚无的代言。
在这里,西西弗斯是一个胜利者,抑或说,是由加缪所确认的胜利者。我认为,或许我们应当把西西弗斯的故事理解为一个宣言。
“如果说,这个神话是悲剧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完)”
在舞台上,英雄攀至顶峰,然后面对巨石滑落。他在峰顶唱起了全篇最华丽的咏叹调。我们的作者从幕后走出来为英雄加冕。
如果我们把观赏的的地址挪移,在幕后的角落里旁观这演员与观众。那么我们将在心底默念英雄的台词,并且望见作者一直隐匿在帷幕后面的身影。
西西弗无需论述,他只是推动巨石。而在注定的命途与他的行为之间,是加缪为其填补了一段独白。在一部剧作的意义上,这一幕是一段完美的高潮,作者的意味已然明了。
“伟大的艺术作品的重要之处与其说寓于自身之中,不如说是表现于它要求一个人所遭受的经历之中,表现于它所提供的克服他的幻想并且更加接近他赤裸裸的实在的机遇。”
西西弗斯的命运是彻底荒谬的,因而也是彻底不可能的,我们及此享有的机遇正是感受西西弗斯所投射在人间的影子。若把西西弗斯与默索尔结合起来理解——加缪向我们推荐的出路是反抗。我们当然无法实践西西弗所经历的反抗,尤其当我们理解到西西弗的反抗是一种“面向无可改变的事实的自我态度转向”时,反抗的适用性更是叫人疑忌。在西西弗斯身上,与其说加缪证明了反抗,不如说他宣誓了反抗。宣言与咏叹,其内容正是反抗。
经由艺术上升后,荒谬终于逼近了哲学的课题。但是可以预料的是,作为“道德家”的加缪必定要在“自由”“激情”“反抗”之中抓住一种回归生活的艺术。加缪提供的一种解决,且不论其是否是推理的,但它无疑是令人激动的。可以理解的是,这正是一种剧作的态度,也是一个道德家的姿态。
事实上,此时观察的扇面又已集中到加缪的艺术身份上。世界再次变为舞台。在艺术与哲学的双重视角的交合之间,加缪坚持他微妙的处理。在一场形而上的讨论后,《西西弗斯神话》带着人道主义最终回归舞台。在剧院宏大的奏鸣中西西弗斯艰难登顶,面向天神与巨石宣誓反抗。一如加缪的多数创作,哲学再次栖身与艺术之中,在众人的欢呼中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