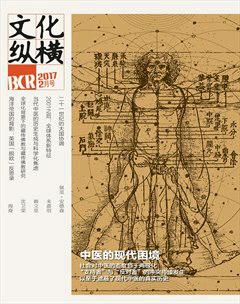“中亚”在哪里?
袁剑
近年来,“内亚”“西域”等区域议题在亚洲甚至全世界知识界掀起热潮,与之共生的“中亚”研究也愈加受到关注。新知识的生产需要建立于对历史的充分理解与思考,历史概念的形成离不开特殊的语境。今日中国如何认识“中亚”,显然不能回避“中亚”与中国历史的紧密关联。本文从报刊等文本入手,直陈“中亚”概念在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波动性与模糊性,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中亚之于当代世界的意义。
中亚如今已成为“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也正在成为中国当代对外知识视野和知识需求所日益关注的重要区域。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似乎将“中亚”当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加以讨论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再问一问:中亚这一区域究竟是什么?它又在哪里?近代中国人又是怎样认识这一区域的?可以说,了解这些,将是我们得以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亚、中国与欧亚整体结构关系的重要前提與基础,也有助于我们在古代中国的“西域”认知以及当代中国的中亚国际关系认知基础之上,更好地理解中亚及其在世界的结构性位置。
中亚及其地缘位置
“中亚”(Central Asia)位于世界最大的连片陆地——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长期扮演过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往桥梁的重要角色,在近代又转变为世界列强大博弈的舞台。正如汉布里所指出的,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通道(中亚多数大河都注入北冰洋)的缘故,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边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关于对方的有限知识。如果不是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者至少要困难得多。[1]可以说,中亚的这两种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对这一区域认知的基本前提与基础。
从目前来看,中亚可能仍然是当今世界及其历史当中相当关键,而又最被人所忽视的部分。之所以造成这种忽视,在著名的世界体系论学者贡德·弗兰克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一些胜利者的家园,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要么记述了一些历史,要么留下了一部分历史遗迹。随后,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他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又迅速在彼此之间形成关联,从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开始转移到外围、海洋和西方。[2]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上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大国力量所控制的海路运输愈发繁忙,曾给这一地区带来数千年繁荣局面的驼队贸易则日渐衰退。到了18世纪,中亚进入停滞阶段,面临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多重衰退,最终随着英俄大博弈尘埃落定,被纳入俄国-苏联的政治版图当中。[3]
随着1991年中亚五国的独立和苏联解体,这一区域又开始以新的面貌进入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当中,并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努力寻找自己的新定位,最终形成了目前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中亚现状。
中亚是什么?不是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地理区域总是充满着某种宿命的色彩,却往往又会在某些阶段扮演转变者的角色,成为触动某些重要事件或者进程的关键因素。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区域分类,背后所体现的是特定时代的独特认识观与分类观。如果说1937年出版的《房龙地理》(Van Loon's Geography)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和澳大利亚五部分,所反映的是当时美国的地缘政治构想——既谋求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同时又试图脱离由欧亚非三大陆所组成的“旧世界”体系的话,那么,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美国开始流行并延续至今的世界七大陆——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极洲的分类法,则既代表着二战之后美国的世界霸权,同时也标志着久已有之的欧式/西式分类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在整个世界的进一步拓展。
中亚由于其本身所处的地理方位和历史环境,在这种世界区域分类的结构之下,逐渐被推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长期以来,作为欧亚大陆东西段之间的交流通道,中亚由于缺乏自身稳定的政治结构与历史传承,往往作为周边文明历史的附属区而存在,该区域自身在周边诸文明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被消减掉了,可以说,中亚一方面始终在吸引着历史和现实的目光,但另一方面却吞噬着我们对于这块地区曾经的既有认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一区域内部秩序的不断变动与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这成为公众层面中亚认知的基本样态。
中亚是什么?从历史视角来看,中亚可以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视野下广阔的西域地带,可以是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内部交流的中间区域,也可以是近代俄国与英国彼此竞争的内陆亚洲区域,同样可以是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的俄国-苏联中亚区域,更可以是当代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更为广大的区域。从总体来看,它是一种经历过几个阶段变迁的文化-生态共生区域,是一种与周边文明与国家力量具有特定关联的区域,也是一块我们在思考自身社会与文明发展过程中无法全然回避的区域。比如说,当我们在思考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迁徙问题以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力量之间的南北互动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意识到中亚在这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外部因素。尤其是在我们思考匈奴与汉朝、突厥与唐朝、准噶尔汗国与清朝的政治军事博弈方面,我们就无法仅仅在中原的视角和范围内去思考前面几者之间的互动问题,而必须将观察的视角前推到更远的中亚区域,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几组政权结构间的关系逻辑问题。例如,要更好地理解准噶尔汗国在与清朝对峙过程中的相关政治军事决策问题,就必须探究其与当时俄国以及中亚诸汗国的交往过程,否则就无法从整体上理解整个关系结构问题。
中亚不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说,中亚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单独单元,它无法确立起自身的整体性话语与认同,而必须附属于欧亚大陆周边的某一力量单元方能展现自身的能量。中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它自身在经济和生态上的脆弱性使其无法在长时间内形成一致性的力量。例如,在中亚的漫长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真正囊括这一区域的并以本地区为政治中心的长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世界帝国时代,中亚也并没有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而只是整个帝国的一个部分。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俄争夺中亚的时代,中亚在英国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处于某种边缘位置,其地位无法与当时作为英国南亚战略支点的英属印度相比。
当然,随着历史的推进,近代的世界政治及其地缘政治变迁为中亚赋予了新的角色。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上世纪初曾指出,欧亚大陆内部区域,因其身处内陆以及海上力量无法渗透之故,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但在他的眼里,中亚只有在附属于俄国(以及之后的苏联)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力量。而在苏联走向瓦解之后,中亚又面临着新的抉择。而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大师布热津斯基在他著名的《大棋局》一书中更是将这块地区看成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一区域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其在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重要性更是无法估量。而建立和加强中亚地区的周边战略平衡,也就成为美国在实施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近代中国人笔下的“中亚”:范畴及其变化
正如中国的对外认知视野发生过巨大变化一样,中国对于“中亚”及其指涉地区的认识也经历着复杂的变迁过程,从而在对于“中亚”概念认知方面形成自身的特殊性,即以古代中国在“西域”认知层面的长期传统以及二战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中亚”认知中占据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中亚”认知的两种连续性;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断裂:即传统“西域”认知与二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亚”论述之间的断裂,这涉及传统的“西域”认知是如何转变为“中亚”认知的?同时也关系到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所凸显的民族国家及国家边界的日渐明晰化问题,即从一个主要包括中国西部地区在内的“西域”概念向一个基本上将中国西部地区排除在外的“中亚”具体概念的演变及语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与同一时期或在稍后时期出现的亚洲其他主要区域概念如“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相比,“中亚”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出现与使用方面有着更大的波动性与模糊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运用在很长时间内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至今尚未完全明晰。因此,回到近代中国的语境,观察当时中国人对于“中亚”范畴的认知图景,就成为一件相当必要的事情。
19世纪中叶,随着近代殖民力量的侵入,西方列强既用枪炮与商品改变了中国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同时也带来了系统性的西式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在知识和思想的层面上挑战着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并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在这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对外认知视野和世界秩序逐渐瓦解,新的对外知识视野和区域观念在曲折变幻中逐渐形成,其中就包含了中国对于中亚的认知,尤其是对其概念范畴的新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西域”认知正逐渐被更为清晰化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和“中亚”认知所取代,这也是古代中国相对模糊的对外视野向近代民族国家结构逐渐成型之后以政治边界划分为基础的认识框架转变的过程。
当然,这种近代认知转变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缓慢的演变过程。总体而言,在清末,报章和文人笔端所出现的“中亚”,更多地指涉波斯、阿富汗地带,有时甚至是指以印度为主体、并受其影响的周边区域。当时,随着英俄“大博弈”的展开,双方的势力范围逐渐明晰,因此在中国国内也开始有所报道,并在部分报刊文章里面形成对于近代意义上的“中亚”的初步认知。中国人开始逐步超越传统“西域”式的对外认知模式,转而面对更具现实性的中亚政治地缘状况。
在清末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早在1879年,位于上海的《万国公报》就刊发了关于俄国在中亚经营并进行地理勘察和地图绘制的报道,分别题为《各国近事:大俄:论中亚西亚之权力今非昔比》[4]和《各国近事:大俄:查勘中亚细亚舆图》。[5]在1898年,《时务报》第62期编译《俄国经营中亚细亚情形》一文,文中称:“俄国蚕食中部亚细亚,欲以拊英属印度之背,孜孜匪懈,思遂其雄志,其奏效之绩,颇可观焉。唯中部亚细亚之地,僻处亚洲之中央,故其事不易入人耳目,于是俄国南下之势,虽骎骎不已,世人知其情形者却少。”[6]1899年,《知新报》刊载英俄两国派员勘探中亚地理的情况,题为《亚洲近事:英俄派员测探中亚洲地势》,[7]其中以“中亚洲”指代这一区域。
1905年,清廷废科举,这标志着传统的知识观开始在官方层面被废弃。在次年也就是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中,中亚被放在第二编“亚西亚”之第五部分“亚洲俄罗斯属地”中加以说明:“亚西亚之西北大地,计七千二百六十万平方里,较欧洲为一倍半,近百年来尽入俄罗斯版图。其国之大,一时无匹,今日岁地广人稀,将来地利尽辟,人口日多,未可限量也。分三大段,在北者,曰西比利亚;在西北者,曰高嘎西亚,或曰卓支亚;在亚洲中央者,曰西域,或曰中亚西亚。”這段叙述很有意思,后来的“亚细亚”在当时还写成“亚西亚”,并将俄国所控制的亚洲部分分为三部分,其中的北部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西伯利亚,西北地区则是高加索地区或格鲁吉亚地域,而位于亚洲中心部位的,则称为西域,也被称为中亚。可见,在那个时候,中亚这一区域与我们传统历史中所说的“西域”还在混用,并没有严格区分。
1907年,张嘉森所撰《外国之部:外国半年记事:中亚细亚之政况》一文,在题目“中亚细亚之政况”下列举了阿富汗、波斯的相关情况,并指出随着日俄战争俄国的惨败,俄国在中亚被迫退让,转而同意与英国一起协同治理波斯,以防止德国势力趁虚而入。[8]同样是在这一年,《外交报》刊载《论阿富汗之关系于中亚细亚问题》一文,认为“阿富汗者,当亚细亚大陆北部及印度之要冲,自古由大陆一面,以进印度者……然自进取之俄国言之,不甚重视阿国,犹可言也,而自防御之英国言之,则阿于防御印度之关系,要不能轻视耳。”[9]次年刊发的《论英俄之于中亚细亚》一文则进一步指出,所谓的中亚地区在地理范围上非常广,以印度为主,而与之相接壤的或者与其安全息息相关的国家,以及将来在政治上受印度很大影响的区域,都属于中亚地区。而在跟印度毗邻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则是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部分(文中称为“亚细亚土耳其”),其次则是波斯,再者则是阿富汗。中亚与中国西部领土息息相关,因此对于英俄所争夺的中亚地区,我们不可轻视。[10]在这一叙述中,中亚的名称还有多种称呼,尚不统一,而其范围主要指以印度为主体、并受其影响的周边区域。
随着国内知识界对外视野的扩大,尤其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随着传统王朝认同的消解以及民族国家知识范式的逐步确立,中国国内对于中亚范围的认知开始从根本上超脱原先的王朝认知,进一步清晰起来,开始形成关于俄属中亚的一般性共识。
在1911年佩玉所撰《俄国中亚经营策》一文中,作者指出:“俄领中亚细亚之地域,北接西比利亚及欧俄,东连蒙古、新疆,南亘阿富汗及波斯,西邻戛斯卞海,广袤约当德国之七倍。至于人口,不过八百万……俄国获得中亚细亚之领域,悉为战争之结果,系最近八十年间之事。”[11]到了1912年,在孙毓修、朱元善所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地理讲义》中,在第二章“亚洲俄罗斯”部分,叙述了中亚(中亚细亚)的情况:“中亚细亚,亦称土耳其斯坦,介于西伯利亚、波斯高原之间,东邻中国,西滨里海,面积凡一千二百余万方里”。在这个叙述中,就已经把传统的西域与中亚区分了开来,而专门指称俄国中亚区域,这种叙述影响将中亚与俄国控制区域内在地联系到了一起,影响深远。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报章与教材中,有许多类似的叙述与介绍,此处兹不赘述。
但是,由于中亚地缘与历史的复杂性,即便到了对中亚范围认知较为固定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对于中亚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1940年的《译刊》曾经刊发《伊拉克:中亚的枢纽》一文,认为“摊开地图一看,伊拉克雄当波斯湾的首冲,显然地控制了中亚”。[12]文中就将波斯湾地区及周边地区看成是中亚,而这一区域在当今显然是西亚地区,与如今的中亚相去甚远。此外,在同年刊发的《苏联:中亚苏联》一文则将“中亚细亚”限定为苏联穆斯林及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也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中亚五国区域,文中指出中亚细亚(Central Asia)这一区域,人口约一千五百余万,大部分属于突厥语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其中派别甚多,北部为游牧民族,南部从事耕种。从19世纪中叶开始,沙俄即逐步将其吞并,在南部与阿富汗接壤,直抵当时的英属印度西北边境。在十月革命之后,当地由于民族关系复杂,纷乱不宁,直到1924年方才结束内乱局面,并提到了当时苏联在这一地区进行的以民族为单位的行政划分。[13]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1942年的《退到中亚细亚去》一文,该文认为“中亚细亚”这一区域位于亚洲中部,北接西伯利亚,西北与俄国欧洲部分接壤,西濒里海,南部与伊朗、阿富汗相邻,东南部与中国新疆接壤,是一块巨大的内陆地域,按政治区域来分,包括当时的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南部各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共398万多平方公里,占苏联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强,而人口仅有1540多万,不到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14]
在同一年的《中央亚细亚》杂志创刊号中,有《中央亚细亚概观》一文,作者在文中自况写作目的:“当亚洲人自决潮流澎湃之今日,余本诸亚洲人自力团结之精神,将中亚之概况介绍于国人,使国人了解此等地方而加注意,则笔者之愿即已称足”,他进而指出,所谓“中央亚细亚”的名称,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一般意义上所称的“中亚细亚”或“中央亚细亚”专指以咸海、里海为中心的亚洲中部凹地,这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狭义中亚范围,其中仅包括位于北部的吉尔吉斯草原、中部的突厥斯坦地区以及南部的土兰平原,以及中西部的咸海和里海。而广义上的中央亚细亚,则包括上面所称的狭义中亚区域,以及中国的新疆、伊犁、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可以以“中部亚细亚”来命名。该文并以(狭义上的)中亚细亚、新疆、伊犁、蒙古、西藏、青海分别加以介绍说明,并指出这片区域除了中部为咸湖、盐碱地以及沙漠之外,其余周边地区,都是肥美的农牧地,其中的河川沿岸山麓地带,则是其中最为丰饶的农牧地区。这一区域除了畜牧业之外,与高加索地区一起,同为苏联低纬度的温暖地区,并成为棉花、小麦、毛皮等国防资源的重要产地。一般人将这一地区看成是苦寒之地的观念,实际上并不确切。[15]该文可以说较为明晰地界定了中亚的范围,将中亚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上的中亚范围与国际学界的“内亚”(Inner Asia)范围类似,不仅包括如今的中亚五国区域,还包括当时中国的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等地,而狭义上的中亚范围则专指苏联中亚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一时期,有些研究者依然对“中亚”概念的指涉范围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王寒生在其《中国与中亚细亚》一文中,就认为这一区域在古代是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国,如今则是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地中海东岸克利特岛及俄属西突厥斯坦区域,而实际上这里并不是亚洲的中部,亚洲的中部应该在中国。[16]在这种情况下,中亚甚至就是一个错误的名称。
从时间轴上来看,在清末民国时期,国人对于中亚的具体范围有不同的看法,中亚这一称谓本身也存在“中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中部亚细亚”等不同的竞争性名称,而“中亚”一词在使用中逐渐胜出,成为至今广泛采用的约定性用法,而从时间轴上看,国内對中亚所指涉范围的认知存在着这样一个大致的变迁过程:在清末时期,中亚主要指波斯、阿富汗地带,有时甚至指称以印度为主体、并受其影响的周边区域。进入民国时期,知识界对俄属中亚和后来苏联中亚地区的认知逐渐清晰,这一区域逐渐成为狭义上中亚的基本范畴,当然,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着其他对中亚范围的不同看法。
概念共识:中亚认知的主体性基础
当代是一个寻求共识的时代。作为一个至今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同界定的区域,中亚在历史和当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边界的模糊性而被忽视,同时也使得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认识一直处在一种“黑洞化”的状态中,也就是说,这一区域一方面像传奇之地一样始终吸引着我们的兴趣和目光,另一方面则无情地吞噬着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美好想象,这是一块希望与失望并存之地,也是一块魅力与斥力并行之地。[17]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很难说存在着一个认识领域的全然不变的中亚形象,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所指涉的具体内涵的认知也就很自然地会出现变动,而这种变动又进一步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周边与外域的认知,并反过来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中亚认知中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既蕴含着区域层面上的变动不居,同时也涉及当时生活在这片区域上的人群的运动流散。
此外,由于中国在历史上与中亚一直存在着密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且长期以来在传统知识体系中形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西域”认知,近代随着西方知识体系的强势渗入而出现了认知领域的近代转型,对中亚概念及范畴的认知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又进一步影响着现当代中国对于中亚的整体认知。因此,在重新面对中亚与中亚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中亚认知中的语境问题,尤其是中亚认知中的中国历史关联性问题,这是中国的中亚研究与欧洲中亚研究、美国中亚研究、日本中亚研究等不同的地方。
随着历史的演进,近代地缘政治中日渐崛起的民族国家结构及其边疆-边界的明晰化,使得近代中国知识界在看待和认识“中亚”的时候,一方面往往将其与传统的“西域”认知联系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则往往较之“西域”有更明确的外域或外国的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有边界性的、中国之外的“中亚”概念和范围认知,这种认识随着对苏俄/苏联中亚政治与经济形势的介绍而日渐清晰,最终又发过来使形成了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界限的更为清晰的认识,形塑了当时和如今中国西部边疆及其社会、群体的边界与样态,影响了我们对自身内部边疆及其社会运作的认知与理解,进而更为清晰地界定了对于自身国家——中国西部范围及其西部边疆社会的认知。可以说,从历史角度而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变迁摆脱了传统的西域视野,开始纳入地缘政治的视角,成为接续后来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下的中亚主流认知的概念基础。
梳理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流变过程,是一个确立概念共识的过程,理解了“中亚在哪里”的问题,了解近代中国人的中亚视野,将使我们对于中亚在欧亚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有更具全局性的把握。这不仅是中国当代确立周边与外部认知的需要,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认识和面对这一区域时必然经历的过程,同时,这种认知也将反过来启发我们对于中国相关议题本身的思考与认知。认识中亚,也是在认识中国。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注释:
[1]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2] [17]参见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in History,no.1(1992).
[3] Denis Sinor, “Rediscovering Central Asia”, in Diogenes, no. 4(2004).
[4] [5]《万国公报》(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30期,第20?23页;1879年第11卷第542期,第22页。
[6]《时务报》1898年第62期,第21页。
[7]《知新报》1899年第88期,第6页。
[8]《政论》1907年第1卷第1期,第91?93页。
[9][10]《外交报》1907年第7卷第1期,第19?21页;1908年第8卷第23期,第13?14页。本文译自《东京日日新闻》,日本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四日。
[11]《地学杂志》1911年第2卷第11期,第18?20页。
[12]《译刊》1940年第1卷第1期,第59页。
[13]《长风》(上海)1940年第2卷第1期,第77?78页。
[14]《国民新闻周刊》,1942年第46期,第17?18页。
[15]王谟:《中央亚细亚概观》,载《中央亚细亚》,1942年第1卷第1期。
[16]王寒生:《中国与中亚细亚》,载《新中华》194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