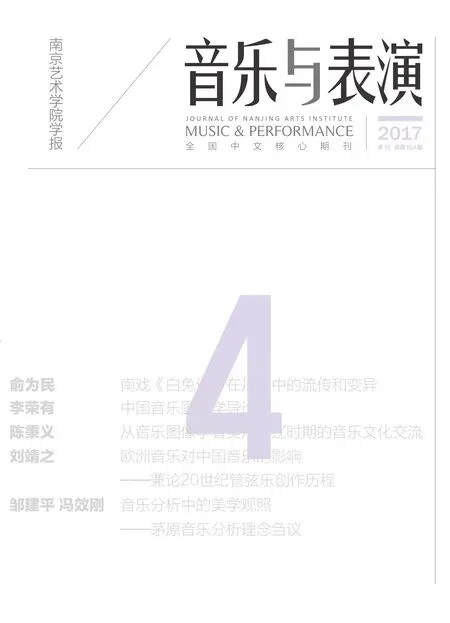中国音乐图像学导论
李荣有(浙江音乐学院 音乐图像学创意研发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4)
音乐图像学是20世纪中叶以来由西方国家传播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对于它的学术定位,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以西方视觉造型艺术中的音乐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或说是作为美术史研究之图像学的分支与交叉学科。因为在中国的古文献中,并未查阅到有关音乐图像学的定义及其相关著述,故我国以相关音乐图像为研究对象的领域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及其丰硕成果均无法找到准确的理论定位和认定依据。要从思想理论上阐述清楚这一问题,还必须借助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并从以“乐”为主体艺术文化和思想文化传统及以图文并举学术文化传统的双重视角进行探讨研究。
一、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的乐文化传统和图像文化传统同根生发,并存互惠,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其中乐、舞混称,合而为一,铸就了我国现代各种表演艺术的根脉体系。图文连缀,相映成趣,留下了历代学人探讨研究和理论著述的印迹。中国人对表演艺术情有独钟的综合性审美情趣的形成和蔓延至今,包括以图载文、以文释图和以图证文等学术研究体系一如既往的长期传承,都成为这个文明古国珍视人类早期乐舞文化和图像文化传统的重要标志。如《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1]82这里全面阐释了词语和图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和谐关系,提出了图像高于词语,变通获取最佳效益,鼓舞达到神妙境界等主张。另如《系辞下》说:“昔包牺氏(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86此说以伏羲创制八卦图为例,描述了其观物—取象—制器的全过程,明确了“观物取象”和“观象制器”的基本法则,认为八卦图具有“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功能作用。
显然,在《周易》这部凝聚着华夏文明结晶的巨著中,已经全面阐释了书籍、图像和乐舞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作用和精神实质。同时,由于作为以造型为主旨的图像和以表演为主旨的乐舞这两种文化形态之间,一直保有着本为同根生的密切血缘关系。而乐舞有着最易于接受、易于传播和易于普及的特殊功能,以至于在西周时代就形成了以“乐”为统领的(含音乐、舞蹈、诗歌、图像、田猎、宴飨等)综合性艺术文化体系。
两汉以来,虽然渐次成熟的语言文字超越了原始图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但图像作为我国远古文明的结晶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伴随着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在文化传承和学术创新发展方面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因为东汉时期兴起的“古学”热,就把古人遗存的器物和图像纳入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之中,以至于渐渐形成了“左图右书”“上图下文”“前图后文”等学术研究和著述的基本范式,并为北宋时代以钟鼎彝器和石刻造像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为宗旨目的之“金石学”的诞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金石学”涉猎范围很广,包括社会政治、历史、军事、经济、天文、地理、文化、宗教等在其范畴之内。而把贵为宫廷雅乐礼乐重器之首的“钟”的研究放在首位,足以反映出在复古之风浓郁的宋代,学者们对乐之图像和乐文化研究的高度关注。这既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又是一个学术的存在。同时,这个综合多元的“金石学”,等于开创了现代“图像学”诸学科学术研究的先河。
西方国家的图像学作为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于19世纪末叶提出,20世纪得到较快发展。作为衍生于其后被称为交叉学科的音乐图像学,在20世纪的前半叶取得相关成果,并以1971年在瑞士成立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音乐图像学分会作为显性标志。截至目前,西方学界依然以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于1939年在《图像学研究》文集“导论”中提出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主张作为指导思想。即“第一个层次为前图像志描述,第二个层次为图像志分析,第三个层次是图像学解释或文化学象征意义的阐释。”[2]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音乐图像学的理念、方法和成果陆续传入国内,在刚刚解除学术禁忌的我国学界掀起了一波涟漪,有效推动了音乐图像学事业的再度繁荣。然很快就有学者撰文指出:“音乐图像学……其名目且迟于近几年才传入中国。但其方法却早已被中国音乐史家、特别是乐器史家所谙熟。所谓‘音乐图像学’(Music Iconography),正是韩非子‘案其图以想其生也’之音乐历史学的分支。”[3]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我国学人依然保有着敏锐的文化自觉意识。
当然,仅提出这样的观点还不能够令人折服,还需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依靠大量的事实依据作支撑,全面解析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据梳理,我国金石学研究的早期成果颇丰,如“欧阳修成书于宋嘉祐六年(1061)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记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地面上的画像石资料。洪适的《隶释》《隶续》,记录了四川夹江杨宗阙、梓潼贾公阙等的画像。而吕大临完成于宋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图》,及之后的《续考古图》共10卷,首次分门别类的收录了传世和出土的钟、磬、鎛、錞于等乐器画像,精心摹绘图形、铭文,记录尺寸、重量等,成为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杰作。”[4]另如“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1086—1093),其中著录了汉画像中的乐架图像,并对古代编钟的形制与音响之间的关系作过探讨,指出古编钟皆扁如合瓦,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等基本特征。还有王黼《博古图》(1123年),薛尚功《历代的钟鼎彝器款识法贴》(1144年)等,均应属于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图像学研究成果。这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丰厚学术文化遗产,确立了‘金石学’的学理方法和历史地位,奠定了其在后世持续传承发展的牢固基础。”[5]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音乐图像研究的批量成果不断涌现,如从中国音乐研究所利用十年时间(1954—1964)编辑出版《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九辑),到由黄翔鹏、王子初先后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各省卷的陆续出版,均反映出我国音乐学界长期以来对于遗存和考古发现新材料的收集、梳理和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
经历了近30年来艰辛的探索历程,通过对我国自古至今延绵不断之图像文化传统的梳理与研究,笔者认为,从传说伏羲通过对“河图”“洛书”的描摹生成“图谱学”,到东汉兴起的“古学”对前人遗存器物和图像的考证研究,及至北宋时代“金石学”这门实证考释学问的生成,正是我国源远流长图像文化传统赖以长期传承和发展的基本动因,也是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存身之所。而西方国家的“图像学”,则可作为接通“图谱学”“金石学”这一中国音乐文化史和艺术文化史实证研究体系的重要媒介。
二、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的学理基础
近代以来,由于连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掠夺,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大国情结和文化自信全面崩溃。即从清末民初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到彻底砸烂孔家店,及至学校教育体系模式的全盘西化,包括“金石学”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的体系几乎全部被稀释和淡化。致使从小全面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一代学人,中华传统文化的素养极其薄弱,心目中几乎只有对西方国家科技文化先进标签的顶礼膜拜。基于此,笔者多年来通过图书馆、博物馆、演出厅、研讨会、田野考察和人物采访等多种途径,全面补充传统文化功底薄弱的缺憾,并把学术探研的视角从音乐与舞蹈学拓展到艺术学理论等更大范围,试图通过视野的调整和观念的提升,协调处理好古今中外各种不同学术观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彻底扭转用单一的洋理论指导中国学术实践的被动局面。
《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的最终成果。由于该领域并无前人的经验可循,当领受课题任务之后,曾有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焦虑、犹豫和迷茫,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为更加准确地把握好学术探研的走向,曾广泛地求教于诸多前辈和同仁。如针对该书的题目如何更好地突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特色问题,大家曾分别提出了“中国图谱图像学”“中国金石图像学”等参考意见,后经过一系列仔细的排比分析,笔者认为,当下我们必须严谨审慎与客观科学地正确看待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和他国他民族的文化。既要珍视和珍重华夏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又不能故步自封和自以为是地完全回归到古代传统。既要一如既往地包容吸纳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之长,又不能单纯地为了求新求异而对外来文化不假思索地全部照搬。因此,最后决定不再另起炉灶,在国际上已经通行的“音乐图像学”之前加上“中国”二字,作为本著作的最终命名。
如前述,笔者试图把我国远古时代的“图谱学”和宋代的“金石学”,以及现代的“图像学”连接融汇为一个整体,作为中国音乐图像学的理论基础。这是经过长期的思考论证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因为只有通过艰辛的历史文化的溯源过程,找到音乐图像学的原始基因,方能通过链接转化等现代手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关于中国音乐图像学与传统的“图谱学”和“金石学”之间关系问题,笔者曾指出:“音乐图像作为遗存艺术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图像一样很早以前就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如经历战国时代‘案其图以想其生’和汉魏‘古学’的长期孕育,及至宋代‘金石学’这门专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中,金类器物主要指由青铜铸造的编钟乐器。因为编钟作为十分重要的礼器(乐器),历来成为各个时代礼乐文化传承延续的基本标志和学术理论探讨研究的焦点,故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有着上千年悠久学术文化丰厚积淀的金石学学术体系中,自始至终包含着音乐图像学术研究的内容。因此,对于已经约定俗成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学术研究来说,无疑仍应回归到尊重古遗存之整体性状态,从宏观整体角度全面解析乐舞图像的内容和内涵,如若人为地破坏了其本原的基本属性,将无法全面系统地获取这些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所蕴含的原生态学术文化信息。”[6]
关于“金石学”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和学术定位,朱剑心说:“‘金’者何?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者何?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金石学’者何?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其制作之原,与文字同古;自三代秦汉以来,无不重之;而成为一种专门独立之学问,则自宋刘敞、欧阳修、吕大临、王黼、薛尚功、赵明诚、洪适、王象之诸家始。”[7]3①1981年文物出版社根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版本影印。对其研究方法概括为:“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7]20②1981年文物出版社根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版本影印。
那么,面对“金石学”这一体系完备的实证研究学术体系,若和20世纪3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学说相比较,且不说其内容和实质方面的差异,就二者之间有着近千年的时间跨度而言,一切曾经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悬念和矛盾已经迎刃而解。
据目前掌握材料,西方国家的音乐图像学研究成果,除见有多部《图片音乐史》类型的著作外,至今并未见到关于音乐图像学理论体系的专门著述。可见西方国家所谓的音乐图像学,迄今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而仅仅是借用了作为美术史研究的图像学的方法。
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图像学的理念和方法,是在原始图像的实用性功能被文字符号完全取代,作为纯粹艺术的门类发展衍变数千年之久后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回归,虽然说从其孕育发生到逐步繁荣历时较短,却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活力,且从元理论的角度来看也符合事物分合的基本规律。”[8]
同时不难发现,在以西方科技文化理念模式切块分割之后再次重组而成的诸多所谓交叉学科,其实仅仅属于科技文化模式下学科反复切块分割之后的一种局部的远端对接,特别是对于本为同根生的艺术家族之间的关系来说,则依然存在着远交近分甚或远交近攻的现象。诚如中国音乐考古学,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
比如“一是科学的考古工作有着从发掘现场到实验室等一套完整系统的工作程序,而考古工作现场又是高度封闭的,即除在编的考古工作者成员外,他人不允许进入考古发掘现场,而作为其分支学科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者,则无合法资格进入考古发掘的第一现场获取直接的研究材料,因而较多只能作为‘二道贩子式’间接研究。二是由于专门的考古工作者业务繁忙和对相关音乐文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原因,导致许多已发现音乐文物资料长期封存于库不能公开发表,亦囿于文物管理条例的特殊性,其他人不能够越俎代庖,以至于新材料却排不上新用场,音乐考古工作者则只能是隔岸观火,研究工作往往陷于滞后状态。三是音乐考古学虽号称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事实上却依然难以避免远交近分的现象。比如该领域考证研究的对象,学理上应包括遗存音乐的实物和图像两大类,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早期的音乐考古工作者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将乐器实物当成了唯一的考证对象,致使音乐图像学作为与美术史研究的图像学方法相交叉的新学科再度独立出来,即所谓的节外生枝。”[9]
同样,我国有着一以贯之的以“乐”为统领艺术文化传统和由“图谱学”到“金石学”学术文化传统,这本属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但在人类历史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扰而扭曲变形的时代,屈从于强势文化,完全仿照西方科技分割理念下的各种套路,其结果必然是大海捞针和瞎子摸象。因为遗存中国古代纯粹的音乐图像少之又少,常见的多为乐舞一体甚至于乐舞百戏混融一体的原始图像,若人为地将这些画面中完整的内容按当下学科门类史的需求切割开来进行研究,必然完全破坏了我国古代乐(舞)文化发展史的全貌。
故笔者认为:“我们虽然依旧借用国际通行之音乐图像学的名义,但具体实施中却必须以我国古老悠久的综合性历史文化传统和包容性学术文化精神为主导,如回归到歌、乐、舞本为一体的“乐文化”的研究视域,以有着千载传承发展史的“金石学”传统体系为理论基础,将遗存古代乐舞艺术的图像、书谱和铭文,以及相关器物、人物的科技成像(照片、音响、影像)等纳入研究范围,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充分融会贯通,并全面吸纳融合世界各国各民族音乐图像学的学术精华,无疑是一种具有可行性、长效性意义的做法。”[9]
在研究的过程中,许多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依然较为突出,并不时困扰着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的进程,而为使我们提出的新观点和新主张及时被学界同仁们关注和讨论,遂不断地将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即时发表,如《音乐图像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刍议》[4]①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2006年第5期全文转载。《图像与表演融合的历史与未来》[10]②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图像学的历史传统及其与现代的接轨》[6]③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等。也正由于这些即时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了不同学科广大学者和学术机构的认可,才使得这一有着较大难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课题,能够以舒缓的速度和有序的节律较为顺利地进行下来。
从宏观的思想伦理体系建设的角度,笔者也曾撰文指出:“在当今的国际文化背景下,‘综合便是创新’的理念已经被许多发达国家所利用,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者一方面必须信心十足地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坚定不移地继承与弘扬‘金石学’珍贵的综合性学术理念和方法,一方面是更加广泛地吸纳融合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新成果,客观地理解我国学人在清末民初羸弱之期提出的‘中体为本,西体为用’等主张,认真地践履费孝通先生关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高端学术命题,就能够自主创新地建立和完善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学术理论体系,这对于当今世界学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整体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也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寻求传统与现代接轨学术文化新形态的必然选择。”[6]
三、中国音乐图像学创新发展的导向
综上所述,中国音乐图像学作为宋代“金石学”的核心学术范畴,起码已经走过了上千年学术探研的历程,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类图像资料,还是历代学人持续不断探研磨砺所推出的学术成果,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积累和积淀。在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格局由单一分割模式向综合创新模式转化的背景下,协调并接通传统的“图谱学”“金石学”与现代“图像学”之间的关系,以中国乐(舞)文化的强大磁场为基础,融入当今世界全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通过对古代音乐艺术史、乐舞艺术史、表演艺术史、造型艺术史等艺术门类史的考证研究,在广泛深入的学术实践过程中积累经验、资料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打通宏观综合艺术史研究的瓶颈,以此突破艺术发展规律难以发现这一世界性魔咒,开创中国特色的艺术文化创新发展新局面应成为主要导向。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这进一步反映出,党中央倡扬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的崇高信念和决心,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与精神支柱。
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呈现两大主流趋势,一是人类共同感受到人文艺术在新时期创新发展中十分重要功能作用,出现了由科技文化分割模式向综合创新文化模式的急剧转化。二是西方国家再次高度关注到图像文明在学术研究中的珍贵价值,“图像再次战胜文字”和“图像时代回归”成为一抹主流色彩。然而,经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笔者发现,世界文化发展的两大主流趋势,恰恰应和了中华民族综合多元的“乐文化”和“图像文化”传统,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深邃隽永的中华文明和文化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在起决定性作用。按俗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自然走向,中华文化在21世纪成为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风向标当在情理之中。
鉴于此,针对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发展走向,笔者曾提出三点主张:“其一,珍视我国古老悠久的图像文化传统和实证研究学术体系的精华是立足之本。其二,在充分比较研究基础上吸纳现代图像学的异质理念和方法是必然选择。其三,加强传统艺术文化和艺术精神的研究与教育并促使其现代转化是发展之道。”[8]这三点主张,从不同的层面阐述了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一是再次强调了作为当代中国音乐图像学事业的发展,需要遵循人类文化的学理规范,首先必须寻根求源,找到其真正的根脉所在,方能建立正确的立足点,防止历史的车轮偏离轨道。如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强实力,提倡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这当然是对的。但学习西方的长处,却把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扔掉了。直到西方后现代社会到来之际,西方的哲人们开始‘屈尊’向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哲学思想学习,吸取营养,我们才有所醒悟,才开始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但真正的醒悟,真正的重视,不是靠宣传、广告,而是靠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12]290
二是阐明了如何正确看待本国、本民族的艺术文化传统,如何正确看待他国、他民族艺术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外艺术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是十分必须和必要的,因为这是双向交流与交汇的基础。包括不同艺术文化的基因,不同艺术文化的形态,不同艺术文化的历史演变轨迹和现状等,都要进行深入细致地研判分析,进而才能做出客观科学和切合实际的判断。否则,如若在病态心理支配下,先入为主地给出优劣界定之后的“比较”,将必然导致学术理念偏颇、目标含混、章法无序和漏洞百出。如有学者所言:“中西艺术之比较研究,广义地说,从20世纪初引进西方艺术和艺术批评的新观念、新方法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东方文化与西洋文化,等等,都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语境下产生的概念。但在这种意义上的‘比较’,只是凭某种直观感觉所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先入为主或人云亦云,而不是真正的比较研究。真正的中西艺术比较研究,是建立在跨文化(中西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即把中西艺术的比较研究置于中西文化语境之中,不仅比较异同,更要追根问底,找出各自特点的生命力所在及其价值取向,探出西方文化各种异质因素与我国固有文化融化出新的方法、途径。”[12]259
三是论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是要加强对于传统艺术文化的优质理念和精神实质的普及教育,然后是在进一步厘清古今中外各种繁复错杂艺术文化关系的基础上,有序实施传统艺术文化精髓的现代转化。如蔡元培先生指出:“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13]
总之,我国以“乐”为统领艺术文化与思想文化格局体系和由“图谱学”到“金石学”实证研究学术体系的并存发展,已成为华夏文明在世界艺术文化的园林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根基所在。因为他国、他民族已经丢失了的文化传统,唯独中华民族依然保有和传承着。他国、他民族需要寻求某些珍贵艺术文化传统的回归,我们却只需要一如既往地前行,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与文化的独有特色和无穷魅力。
我们当下的重要任务是,更加严谨严密地顺利实施这两大珍贵艺术文化与学术文化传统精髓的现代转化,有序突破古代乐舞文化史、表演艺术史、造型艺术史和艺术文化史研究的瓶颈和难点,进而探寻艺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旦我们攻克了这一世界性难题,就能够以中华民族固有的伟大智慧和创新创造能力,在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走向。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系辞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美)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M].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3-5.
[3]牛龙菲.音乐图像学在中国[J]//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年鉴,1990年卷[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05-113.
[4]李荣有.音乐图像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刍议[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1).
[5]李荣有.音乐图像学在中国再议[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4(3).
[6]李荣有.图像学的历史传统及其与现代的接轨[J].艺术百家,2012(6).
[7]朱剑心.金石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8]李荣有.图谱学·金石学·图像学——中国艺术文化史实证研究体系的完美链接[J].艺术百家,2016(4).
[9]李荣有.中国音乐图像学释义[J].人民音乐,2015(8).
[10]李荣有.图像与表演融合的历史与未来[J].东南大学学报,2012(6).
[11]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R]//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N].2017-10-19:1.
[12]聂振斌.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R].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90.
[1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