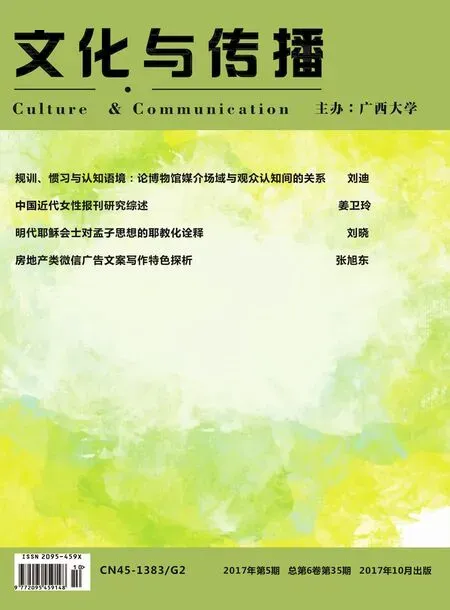规训、惯习与认知语境:论博物馆媒介场域与观众认知间的关系
刘 迪
近年来,作为媒介的博物馆的研究日渐受到学界重视,无论是基于将展品转化为学习介质的博物馆媒介化研究[1],还是在媒介视角下建构宏观博物馆学理论[2],抑或探究博物馆具体问题[3],其研究均旨在从媒介理论中获得启示转而观照博物馆领域。这似乎已成为博物馆作为当代知识传播机构属性映射下的博物馆学理论脉络的必然延伸方向。
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媒介场域(Media Field)理论下,博物馆既是社会媒介的子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内部含嵌不同层次的场域系统,其主要包括利用网络技术和人工拓展构成的馆外场域和基于陈列的馆内(教育)传播场域。从历时角度看,伴随社会与技术发展,博物馆已由一种实物展示一元化的传播媒介发展为包含实物展示、现场多媒体、网络多媒体在内的媒介系统。博物馆借助网络技术、新媒体等,其影响力已超出博物馆实体范围,努力融入广泛的社会信息传播与娱乐之中,试图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影响公众的认知。
然而,布氏媒介场域理论的缺陷之一便是未涉及受众方的研究[4],遑论受众的认知。本研究拟借助规训、惯习与认知语境三个概念来分析博物馆媒介场域与观众认知间的关系。其用意,一方面尝试较为深入地分析观众在博物馆这一媒介场域中认知发生的背景及机制,另一方面则试图以博物馆场域为例添补布氏媒介场域中受众方研究之不足。
一、博物馆媒介场域
(一)“媒介场域”:博物馆作为传播媒介的分析视域
场域是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核心概念之一,其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5](133-134)然而,布氏并未进一步对“媒介场域”作出准确定义,仅是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提出“电视场”、“新闻场”的设想[6],二者可视为媒介场域的具体化形态。博物馆作为现代知识传播机构的属性决定其也可被纳入到这一理论框架下加以考察。
因此,在对博物馆媒介场域进行分析时着眼点并不落在博物馆媒介的客观实现基础——物质上,而是去关注那些处在这一关系网络中的各种位置和占据位置的行动者以及强加于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作为媒介场域的逻辑起点,支配着不同场域的生成及其特殊运作逻辑。在博物馆中资本主要表现为以物质形态①虽然国际博协在博物馆定义中将非物质遗产纳入博物馆工作范畴,但就当前博物馆实践来看,仍以物质遗产为工作的绝对重心。和遗产意义存在的特有“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有着双重表现形式,其一表现为实体所承载的信息,其二表现为一种“符号形态”(即“符号资本”)。博物馆媒介场域的网络关系也便在文化资本的占有者、释义者、受众间围绕资本的种种权力与话语争夺而展开。博物馆文化资本的受众从被严格限制的小众逐渐演化为所有社会大众,甚至“资本”的解释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向公众予以让渡②英国的纽卡斯尔发现博物馆(The Discovery Museum)有一个常规活动“来自橱柜的衣服”,经常邀请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其馆藏中遴选展品,拟定主题,最终形成临时陈列。参见刘迪:《中西博物馆组织青少年活动之比较与借鉴》,《东方博物》2007年第2期。,这些变化更新着场域内权力关系的细节,而在场外国家权力的投影下资本占有者的位置依然未受撼动。在关系细节的不断调试中,博物馆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逻辑和行业规则,从而与其他社会场域区隔开来。
在布尔迪厄语境的抽象场域关系网络之外,博物馆的实体部分(即博物馆媒介)在福柯(Michel Foucault)思想体系中作为权力技术存在着,博物馆的建筑是权力实施的场所与媒介,空间生产则体现为对空间的规训实践,从宫殿、府邸,到以老柏林博物馆为代表的“庙宇式”博物馆建筑,再到新古典主义和奇观建筑,博物馆这些实体要素都形塑着观众的行为与认知,并生成某种传统。
以视觉为主要感知方式的博物馆媒介以符号资本为中心不断整合并重构这一场域的形态,使之与时俱进,跟进公众的媒介习惯与需求。在媒介技术上,陈列语言日趋丰富,实现了观众多感官途径的拓展,视觉以外不断开发听觉、嗅觉、触觉等多种可能。而博物馆场域中最为核心的媒介技术仍是由实物特性衍生出的“换喻”和“概念隐喻”。博物馆媒介中,实物与博物馆环境共同构筑起特定语境,展品成为某个时代、某个人物、某个事件的换喻,它既代表自身,也代表一类存在[3](119)。空间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作为概念隐喻的三种类型在博物馆的陈列中均有表现,如原中国革命博物馆“蒋家王朝覆灭”一组陈列,将陈列柜玻璃罩部分做成四坡水覆斗型,类似外国棺材盖形状,便属于实体隐喻;而将台座设计得很低,含埋葬之贬义,则属空间隐喻③实例参见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编:《博物馆陈列艺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62页。。各种媒介技术的实施均离不开公众的认知语境。
博物馆媒介与博物馆媒介场域是不同的,前者为一个实体,而后者则为抽象的关系。博物馆媒介场域是一个由资本占有者、传播(阐释)者以及公众等因素彼此结成的客观关系网络,因而具有作为分析媒介实践和媒介内部关系的工具意义。本研究便以此为框架展开,进行对观众认知的探究。
(二)图像化生存时代下的博物馆媒介场域
博物馆媒介场域作为社会的子场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之中,在既定位置作为一个结点与其他位置上的结点相联系,发生相互影响。同时,作为社会网络的组成部分也深刻地受到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法国学者雷吉斯·黛布雷(Regis Debray)将人类社会分为书写时代、印刷时代与视听时代。在书写与印刷时代中是“一幅图画迷住了我们”,而在视听时代人们则是徜徉在“图像的景观”之中,并以“图像化”的方式进行生存[7](189)。在这个时代中,“我们被各种视觉技术以及它们展现的影像所围绕,种种不同的技术和影像,提供我们看世界的视野;它们用视觉语言转述世界”[8](7)。这种“图像化生存”致使时下人们的生活经验“视觉性”空前增强,“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9](84),曾经的文本被图像所取代,文化上的“图像转向”由此产生。
博物馆作为一个视觉中心媒介诞生于前视听时代,迎合了人类对视觉认知依赖的天性,因而产生出空前的吸引力。随着时代及公众视觉习惯的变迁,博物馆由传统媒介实现向现代媒介的蜕变升级,引入大量新媒介技术,然而新的技术并没有让观众产生真正的快乐,反而使其不可遏止地沉浸其中,丧失了原本的“凝视”和深度。
如同话语一样,谁说话,说什么,怎么说,都是权力的产物,观看也是一样,看的权力就是使事物可现、可见的权力,更是一种主宰的权力[7](202)。博物馆媒介场域便是以“看的权力”为轴心构成的关系网络。作为媒介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相连接,博物馆也是通过可视化的“议题”设置扩散其(知识)权力,从而引起其他场域和潜在受众的关注,扩大影响,悄然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发展。然而,由于博物馆媒介中普遍存在议题滞后和脱离公众日常生活、脱离当下社会的情况,虽然它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控制),但其媒介的影响力总体偏弱。此外,这个图像化生存时代的整体视觉媒介面貌已远非博物馆诞生之时可比,博物馆面临与其他视觉媒介争夺公众注意力的残酷竞争,娱乐化、商业化的因素逐步渗透到这一场域之中,使之变得更为复杂。
二、博物馆媒介场域与观众认知
一直以来对博物馆与观众间互动性的简单化认识造成的理论误区之一便是忽视了权力与资本在这一场域中博弈所造就的动态博物馆场域关系,进而迷失在以纯粹的传播学对观众认知过程的刻板解读之中。媒介场域理论告诉我们,观众作为在博物馆媒介场域中具有既定位置的存在,其认知行为的发生除了内在的认识语境作为先天图式发挥作用外,还受制于外在的博物馆媒介场域规训以及中介于观众内在与场域之间的惯习。
(一)观众与博物馆场域规训
不同媒介场域因内部运作逻辑的特殊性而相互区分并获得独立,独特的运作逻辑使媒介场域也具有了分割受众的能力,受众被分割为趋于专一的群体,并发展出与之匹配的媒介接受习惯,从而进一步加深与其他媒介受众群体的区别。似乎,我们也可由此将博物馆的观众从一般公众中分离出来。然而,虽然存在“博物馆之友”这样的典型群体,但由博物馆观众的整体特征可知,博物馆是一种“群体极化”效果较弱的媒介。
观众是博物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在关注人的发展需求的新博物馆学影响下,以至可以产生“博物馆是因观众而存在的”这样的理解。而一旦将观众这一因素置于博物馆媒介场域框架之中,观众的处境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可能:他们成为透过博物馆媒介进行权力实施的对象,即博物馆场域规训的对象。
博物馆在功能、空间、形态等方面自然不同于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①圆形监狱(panopticon)理论由英国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于1785年提出,旨在揭示权力运行的微观物理学。圆形监狱是一个像圆环状的建筑,其中央建立一个观察塔,沿着圆环外沿建立许多单人牢房,牢房向外的一面不设门窗,向内的一面安装玻璃。玻璃的安装和光线的调整都经特别设计,使位于观察塔上的监视者可以清楚地看见牢房内的人,而牢房内的人却看不见塔上的人。在这样的监狱中,由于特殊空间位置的调度,囚犯所有行为总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权力/知识的威慑之下,囚犯就会因此自我控制,进而变得“规矩”起来。久而久之,囚犯习惯了,就会变得驯服。,但它们均对身在其中者实施了身体—行为的监控(控制)。博物馆从早期的准入制度①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其早期,在开放方面有诸多限制,如参观者要提供证明以示他们是“被承认的合适的”参观者,才能从守门人那里拿到票,一个小时内,游客不能多于10人,同时一组不能多于5人进行参观。参见[美]莎朗·韦克斯曼:《流失国宝争夺战》,王若星、朱子昊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到安保人员、看展员的现场巡逻,再到电子监控,从贴身到远程,从直接转为微妙,权力在这一场域中无时无刻不在规范化观众的不规范行为倾向,将观众造就成“驯顺的肉体”[10]。而博物馆对观众的规训却远不止于此,权力控制的目标并非在单纯的身体—行为层面,而是通过界定、干预场域中的实物及其秩序,产生对观众心理—认知的控制。
博物馆场域规训是历史性动态变化的,由最初对人身的直接限制(控制),逐步转变为通过对信息输出的限制控制观众,权力也从一种显露在外的暴力形式转变为隐蔽。
在博物馆媒介场域中权力通过实物和视觉化方式进行意义的生产。与对公众身体控制的变化相仿佛,博物馆陈列的形态也逐渐从“器物定位”发展为“信息定位”,不断增强着意义生产的能力。博物馆中的实物在时间之流中被孤立出来,失去了曾经的时空参照系统,失去了与原始环境的因缘勾连,意义难以驻存。实物在视觉上是反概念、反逻辑和反思辨的,致使其无法走向本质与深度,而停留于现象和表层。博物馆则利用了实物的这些性质,获得对事实和世界按权力话语需要建构的可能,在“真实”、“科学”之名下,通过注入意义的方式,弥合差异、断裂,从而使场域中的实物生成意义上的一致性。此外,权力也隐蔽在实物的情感魅惑力之中。当观众认同呈现在眼前的“常识”时,也便不知觉地接受了权力的意识形态。博物馆场域作为权力发挥作用的场所与媒介,其中意义从来都处于生产和争夺之中,利用话语对实物的界定和“改造”注定没有终点②如一匹名为科曼彻的马死后被制作成标本,意指它是一匹在卡斯特最后抵抗中幸存的马,是历史的见证。后来,这匹历史上著名的战马后来出现在博览会上,意指文明世界对凶残野蛮世界的征服与胜利。随着权力关系的演变,其意指仍会变化。参见[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福柯空间规训的思想在博物馆媒介场域中实现了意义上的延伸,“从权力话语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设计、构造与生产来完成个体的监控”[11](51)到通过实物的调度、组合等策略来实现对观众可能的认知再造,使其服从于权力的规约体系。在博物馆中,知识、真理与权力结成联盟,构成影响观众认知的基础层面。
与传统的监狱、工厂、学校规训形式不同,博物馆场域的规训是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体系。现代博物馆观众面对规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可采取规避甚或抵制,即反规训,如选择不参观博物馆、公然反对陈列内容或表面认可而暗中不屑。
(二)观众与惯习
如果说规训是博物馆媒介场域权力对观众的外在施加,那么,惯习则是博物馆观众对场域关系的主观调试,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
布尔迪厄在提出“场域”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对应的“惯习”(habitus)概念。在他看来,尽管“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但在场域中活动的行动者并非是一个一个的“物质粒子”,而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而场域并不是一个“冰凉凉”的“物质小世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5](165)。具体的场域随着社会分化过程而诞生,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中积淀并形成独特的价值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获得相对独立身份。这些潜在规则与逻辑并非一般的经验式总结显露在外,而是附着于场域结构之中,构成结构间的张力,并沉积于行动者的思维深处,内化为处理问题时体现出的惯习。
“惯习”是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理论,但它并非行动本身,而是行动者通过行动得以外在化的社会结构的前结构,同时也是行动者内心的深层化结构,持续影响着行动者的思想和行为。在博物馆场域中,行动者的身份(位置)并不相同,如包括博物馆的管理者、博物馆观众,有时甚至还涉及到为博物馆提供展品的当代艺术家。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书法家的作品均有朝大幅、巨幅发展的倾向,这便是其在博物馆场域的惯习,以适应当代博物馆陈列空间的尺度和陈列形式。博物馆场域通过艺术家的惯习也在“打磨着”展品的规格。同样,博物馆的观众也凭借着一定的场域惯习完成其博物馆实践。博物馆观众的群体极化效果较弱,观众的场域惯习并不总是表现得十分明显或典型,那些对博物馆媒介接受度与契合度较高的观众,经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实践形成了博物馆场域的惯习,即一系列的倾向:静观,而不吵闹;学习,而非观光;素描,而非拍照……由此构成一种协调的观众与场域关系。而我们在博物馆中也会看到有观众在展品前“扔钱”的现象①文刀:《当“扔钱香客”走进博物馆》,2016-08-25,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NzE4NTEwMw==&mid=2653281370&idx=1&sn=b5458ea863477d71e05463723c07aabe&scene=0#wechat_redirect,2017-02-18。,并不只发生在宗教相关的文物前,恐龙化石展品前、陈列复原场景中、博物馆园林的水池中均有此类情况发生,且投币量巨大。这种行为的发生在于那些与博物馆关系较弱的观众并未生成博物馆惯习,而是将其认为的与博物馆相近场域的惯习迁移进博物馆所产生的结果。当一个场域的惯习迁移至另一场域时,立刻会变得失当,并且产生冲突,在博物馆中类似的现象还有“摸文物”②柯欣:《传统民俗or交感巫术——人们为何热衷于摸文物?》,http://mp.weixin.qq.com/s/M0MP1lnhwI2pkeTLRyjilg,2017-02-19。。媒介场域中行动者惯习的形成,首先,来自于行动者的家庭出身与教育,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来自行动者与媒介场域的关系;再次,来自于媒介场域内部的控制,如规范、规章、引导等。
场域形塑着行动者的惯习,惯习成为某个场域结构固有属性的表达,场域的逻辑规则通过惯习在实践中表现出来。惯习又会反形塑其所在场域,在惯习的认知建构下,场域将被构造成一个充满意义和价值感的世界。当场域与行动者惯习之间吻合时,行动者惯习便体现出场域结构,并维系着整个场域结构的稳定。
场域结构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行动者惯习的改变往往滞后于场域结构的变化,惯习与结构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显现出来。在博物馆观众意识不断强化、博物馆教育理念与实践不停翻新的当下,公众仍以被动的态势、被教育者的位置参与博物馆活动,这便显现出了惯习的“迟滞效应”[12](203-208)。
(三)观众及其认知语境
在场域理论视域下,博物馆媒介场域的实质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以知识(信息)传播的形态展开的。因此,博物馆陈列语言、媒介技术与传播策略成为博物馆场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从传播客体(观众)角度来看,认知语境在传受的实现上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斯铂佰(Dan Sperber)和威尔逊(Deirdre 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的与交际认知相关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特别强调了认知语境的作用[13]。关联理论从人的认知过程及特点出发,认为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及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是因为存在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即关联性[14](39-42)。在交际行为中,为了获取最佳交际效果,说话者总是趋向于向听话者提供与认知语境相关联的信息,听话者则依据所获信息去寻找话语与语境假设之间的最佳关联,进行推理判断。就个体而言,事物进入个体认知语境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是明白的、可以感知的或可以推理的。个体的认知语境是其物理环境和他的认知能力作用的结果。它既包括已知晓的事物,也包括可知晓的和可推理的事物。前者构成个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博物馆作为媒介向观众传播信息与观众接受信息的双重过程形成了双方的交际活动,认知语境在观众认知活动中不可或缺。博物馆作为在实物基础上形成的媒介,互动性难以向纵深展开,而是依靠将空间化的展线转化为时间的流动来实现与观众的持续交流,因此,显现出较强的信息意图,而交际意图较弱。为了实现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博物馆试图建立并深化与观众的关联,建构可以共享的认知语境。从器物定位到信息定位,陈列的发展趋势已体现出博物馆在建立关联上的努力。在器物定位型陈列中,由于缺少关联的限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观众理解的困难,却也产生了在不知不觉中激活多种认知语境内容的可能;而在信息定位型陈列中,由于增加了关联限定(表明因果或其他联系),观众的认知语境内容因受到限定引导而变得明确起来。
博物馆通过陈列语言、文字语言及媒介技术建构与观众共享的认知语境。在博物馆中,实物与文字的组合是最为常见的处理方式,它们之间构成一组互文关系,文字是对实物展品的解释说明,提供具象的实物本身所不可见的必要信息;而实物也构成文字的佐证,是抽象信息的具象化呼应。陈列中的文字富于弹性,通过详尽或粗略、宏大或细微的不同表述方式建立陈列、展品与观众内化和系统化的知识结构间的联系。观众在博物馆中的观察与理解作为结果又内化为其认知语境的组成部分。此外,认知语境在对博物馆常用的媒介手段——隐喻、换喻的理解过程中也起到关键性作用。陈列隐喻的理解过程就是观众根据相关原则,以最小的加工努力在自己的认知语境中选择出最具语境效应的假设,来推导出陈列隐含的信息意图。可以说,隐喻的理解过程就是认知语境的选择过程。换喻,亦然。
三、小结
过往对博物馆观众认知的研究多局限于认知过程的分析,而缺少对观众在博物馆中认知发生的外在力量及内在心理图示的综合探讨。规训是场域权力造成的,它对观众认知来说是一种外在化的作用;而惯习对于观众认知来说则为内在化和外在化双重作用的结果;认知语境则属观众的内在结构。观众的认知和行为即发生在这样的整体框架之下。
参考文献:
[1]严建强.博物馆媒介化:目标、途径与方法[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6(3).
[2]曹兵武.作为媒介的博物馆——一个后新博物馆学的初步框架[J].中国博物馆,2016(1).
[3]刘迪,徐欣云.媒介视域下博物馆陈列的娱乐问题探析[J].东南文化,2016(1).
[4]刘海龙.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J].国际新闻界,2005(2).
[5]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曾庆香.大众传播符号:幻象与巫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8]吉莉恩·萝丝.视觉研究导论——影像的思考[M].王国强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9]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10][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1]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J].国际新闻界,2014(5).
[12]卜宇.区域性主流媒体源点的变迁与重构——基于“场域—惯习”的视角[J].江海学刊,2012(5).
[13]斯铂佰,威尔逊.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第二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4]杨莎,唐秀娟.从关联理论看认知语境与话语标记语的关系[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