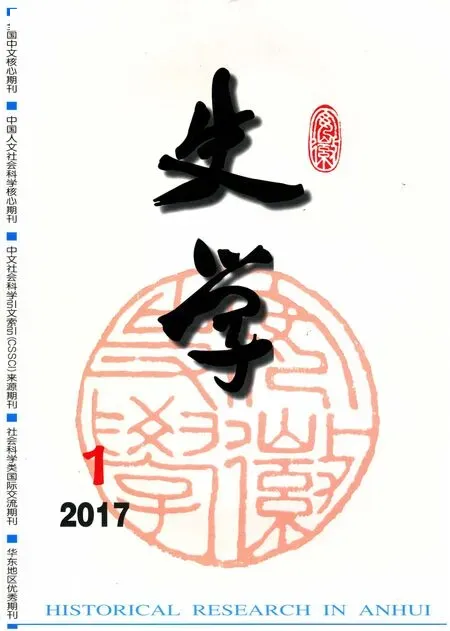由恶变善:潮神伍子胥信仰变迁新探
李金操 王元林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2)
由恶变善:潮神伍子胥信仰变迁新探
李金操 王元林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2)
涌潮形成之初,潮神信仰即随之产生。因古人将钱塘潮、广陵潮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破坏归因于伍子胥冤死泄愤,故伍子胥最早被视为潮神时,其形象乃是凶神。不过,随着两汉以来士人对伍子胥忠孝形象的强调和人们对涌潮成因认识的提高,魏晋以后,潮神伍子胥的形象渐趋正面。隋唐五代时期,由于钱塘江两岸低地的开发和人口增殖,钱塘江潮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剧。除先贤形象外,伍子胥司潮神职也为政府重视,故唐时对潮神伍子胥封号赐爵,将其纳入国家祀典。
钱塘江;潮神;伍子胥;国家正祀
古代吴越地区有两处大型涌潮,即钱塘江口的钱塘潮和长江口的广陵潮。潮神信仰随着涌潮出现而产生。已知最早的潮神是伍子胥,之后又逐渐增加了文种、石瑰、钱缪、张夏等。有关潮神的研究成果以伍子胥为多*主要成果有: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译:《伍子胥变文及其来源(二)》,《中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8期;蒋康:《试论伍子胥的崇祀习俗》,《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刘传武、何叶剑:《潮神考论》,《宗教文化》1996年第4期。。本文拟对宋代以前涌潮现象与伍子胥的关系、潮神伍子胥形象的演变及其被纳入国家正祀的原因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正之。
一、早期潮神伍子胥信仰的形成与其凶神形象的树立
史载吴王夫差浮伍子胥之尸于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史记》卷66《伍子胥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36—2637页。,可知伍子胥被杀后不久,吴人便已为其立祠。按《战国策》夫差杀伍子胥,“(子胥)入江而不改”之说*《战国策》卷30《国昌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85页。,至迟在战国时期,人们已把江水灵异现象归因于伍子胥之冤死,而此种江水灵异现象当是涌潮。古人认为,伍子胥性格易怒且冤死含恨,故将汹涌激荡的潮水视为伍子胥的惩戒*参见(汉)袁康等撰,李步嘉校:《越绝书校释》卷14《越绝德序外传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69页。。今世学者在分析潮神伍子胥的凶神形象时,往往因袭古人说法,过分强调伍子胥的易怒性格*参见刘传武、何叶剑:《潮神考论》,《宗教文化》1996年第4期;蒋康:《试论伍子胥的崇祀习俗》,《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朱海滨:《潮神崇拜与钱塘江沿岸底地开发——以张夏神为中心》,《历史地理》第3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页。。实际上,古人之叙述,只是潮神伍子胥信仰构建后的结果,而非原因。伍子胥之所以被视为潮神,与钱塘江潮形成于伍子胥被杀前后有关。


其二,古代吴越地区有“多淫祀,好卜筮”的传统。伍子胥“乃自刭死……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可知民众最初祭祀是出于同情和敬仰,应当还未被视为潮神。但因其去世与涌潮形成时间相近,伍子胥以潮水惩罚两岸居民的故事应在不久后被构建。《战国策》“入江而不改”之记载,反应了战国时期伍子胥已被视为潮神。伍子胥何以由受人爱戴的先贤变成兴风作浪的潮神?当与巫祝把持祭祀话语权有关。正如葛兆光所说,在殷商西周时代,主导祭祀秩序、规范和礼节是最重要的知识,掌握这一知识的“思想者”是垄断文化的“卡里斯玛”*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能定义神性善恶的是巫祝而非普通百姓。虽然有关先秦时期,地方巫祝构建神性善恶的记载相对较少,但我们可以从后代相似事件中推知一二。黄永年曾列举大量唐代“淫祠害民与否和成神者生前之是否贤德并无关系”的例证,并指明此为巫祝之所为*黄永年:《说狄仁杰的奏毁淫祠》,《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在唐代以前,此类情况应更普遍。将日益扩大的涌潮归因于伍子胥,即可转嫁灾害引起的诸多恐慌,又可以愚弄百姓以图利,所以伍子胥很快被刻画成了怒启涛浪以害百姓的凶神。
广陵潮形成时间稍晚,但至迟到西汉时,广陵潮已相当壮观。枚乘《七发》形容其势“疾雷闻百里”、“状如奔马”、“候波愤振”*(南朝梁)萧统:《文选》卷34,《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44册,第810页。。据《汉书·地理志》,在广陵国(治今扬州)稍东的临淮郡海陵县(治今江苏泰州海陵区)“有江海会祠”*《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0页。,当是祭潮神之祠。按《七发》“弭节伍子之山”的记载,长江口居民应接受了钱塘江流域居民的伍子胥潮神信仰。东汉初年张禹赴任扬州刺史时,曾被人以“江有子胥之神”劝阻(详后),证明两汉时长江口潮神伍子胥的形象亦是凶神。广陵潮形成之初,因临门沙坎也在不断堆积,涌潮规模同样在不断增大*临门沙坎是指河口处河床上的淤积坎,乃形成涌潮的必备条件,而两股相逆水流交汇是形成临门沙坎的必备条件,故而涌潮多发生于喇叭形河口处。两千年前长江口是一个漏斗状束狭海湾,有形成沙坎条件。参见陈吉余:《两千年来长江口发育的模式》,《海洋学报》1979年第5期。。同属吴越地区、同是不断扩大的涌潮,长江口居民接受伍子胥的凶神形象乃顺理成章之事。
伍子胥凶神形象一直持续到东汉。东汉时期,会稽(今浙江绍兴)袁康、赵晔、王充等人均对吴越民众观念中的潮神伍子胥形象有所着墨:“依潮来往,荡激崩岸”*(汉)赵晔:《吴越春秋》卷3《夫差内传》,《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58册,第263页。;“发奋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汉)袁康等撰,李步嘉校:《越绝书校释》卷14《越绝德序外传记》,第369页。;“驱水为涛,以溺杀人”*(汉)王充:《论衡·书虚》,《诸子集成》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5页。,完全没有同情之心、不顾百姓死活。不仅如此,他还携文种一同为患,“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子胥主前潮水,文种主后潮水,两人一起惩罚越人*(汉)赵晔:《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第276页。。东汉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上虞区)人曹娥以女孝尽节闻名。按《曹娥碑》载,其父曹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143年)五月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曹娥“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40《曹娥碑》,《续修四库全书》第8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页。。潮神伍子胥吞噬主持祭祀仪式的巫祝,曹娥哀慈父死于非命,怨恨潮神伍子胥残暴,投江而死,颇有生不能报父仇,死当为鬼以报之的气节。潮神伍子胥对吴越居民的压迫也引起了个别反抗。据谢昉《后汉书》载,吴郡王闳渡江遭风,“船欲覆,闳拔剑斫水,骂伍子胥,风息得济”*《太平御览》卷60《地部二十五》,第369页。。《越绝书》《吴越春秋》和《论衡》中关于伍子胥怒启波涛的记载和曹娥、王闳等人的事迹,反映了两汉及两汉以前,吴越居民对潮神伍子胥的恐惧和抵触。他们祭祀潮神的目的是“慰其恨心”,并非出于感恩。
总之,因涌潮规模的扩大和吴越巫祝的引导,伍子胥在潮神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忠正形象,而易怒、性情刚烈等性格缺点被不断凸显。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潮神伍子胥形象的改善
魏晋时期,伍子胥的凶神形象有所改变。三国东吴孙綝曾“烧大桥头伍子胥庙”,为史家非议,史书评论“綝意弥溢,侮民慢神”*《三国志》卷64《孙綝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9页。。至迟到西晋时,在会稽民众观念中,潮神伍子胥的形象已逐渐正面。西晋太尉贾充曾问会稽人夏统,会稽有何“土地乡曲”。夏统答曰:“伍子胥谏吴王,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并为贾充等王公贵族演唱,众人听后,有“子胥、屈平立吾左右”之感*《晋书》卷94《夏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29—2430页。。证明西晋时,会稽民众已将伍子胥与屈原并称,他们祭祀潮神伍子胥的原因,不再是“慰其愤心”,而是“痛其忠烈”。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中原动荡,京城倾覆,吴郡(治今苏州)人叔父欲归乡,“当济江南,风不得进,即投奏,即日得渡。”*(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5,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页。吴越民众通过投奏,得蒙伍子胥阴佑安然渡江。
当然,吴越文化区范围很大,潮神伍子胥形象转变的过程存在区域差异。会稽一向是吴越地区文教重镇,故会稽附近潮神伍子胥形象转变的时间相对较早,而其他地方则较为迟缓。如南北朝时,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百姓祈求有破产者,刺史王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呼!”王劢宣告百姓后,“自是遂止”*《北史》卷51《王劢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9—1850页。。显然,楚州附近潮神伍子胥形象转变的时间要晚于会稽。总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淫祀性质的凶恶潮神伍子胥,正逐渐向具备先贤品质的潮神伍子胥转变。据笔者分析,潮神伍子胥形象的转变,原因有二:
其一,两汉以降士人对伍子胥正面形象的宣传。伍子胥是春秋晚期声名显赫之人,虽也有“疾强谏有辞”等性格易怒的记载*韩非撰、(清)王先慎注:《韩非子集解》卷5《饰邪》,《诸子集成》下,第952页。,但总体上看,伍子胥是贤臣、忠臣的表率,典籍中不乏“子胥忠其君”*晏婴:《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诸子集成》上,第773页。、“子胥忠直”*韩非撰、(清)王先慎注:《韩非子集解》卷20《人主》,第1020页。之文,评价其“无过比干子胥之忠”*慎到:《慎子·知忠》,《诸子集成》下,第926页。。伍子胥的忠正形象甚至为敌对国士人肯定,屈原在失意时曾以伍子胥境遇自比,谓己之遭遇与“伍子逢殃兮”“皆然”*屈原撰、(宋)朱熹注:《楚辞集注》卷4《九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忠孝品质为士人所推崇,伍子胥屡被提及,扬雄认为伍子胥之贤过于范蠡、文种,“或问子胥、种、蠡熟贤?曰:胥也。”*(汉)扬雄:《扬子法言》卷10《重黎篇》,《诸子集成》下,第1139页。壶关三老盛赞伍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汉书》卷63《戾太子传》,第2745页。;刘向肯定伍子胥“尽忠极谏,诀目而辜”的做法*(汉)刘向:《说苑》卷17《杂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31册,第306页。;而何休为《公羊传》注疏时曰“子胥有至孝之致,精诚感天”*(汉)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5《定公元年至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319页。。虽然在两汉时期,吴越居民对潮神伍子胥存在误解和恐惧,但吴越地区以外士人不会受其影响。东汉初年,张禹过江赴任扬州刺史一职,“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将渡,吏固请不听。禹厉言曰:‘子胥如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遂鼓楫而过。”*《后汉书》卷44《张禹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7页。这则事例表明,吴越以外士人多以“贤人”颂扬子胥,不愿把他视为“以溺杀人”的凶神。
董仲舒“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忠孝伦理观念被不断凸显,统治阶层十分注意忠孝教化之榜样的树立,周武王封比干墓一事屡屡被儒者提及,有出于忠君教化的考虑;曹娥投江后被立庙,显然是为了推行孝道教化。伍子胥事父以孝、事君以忠的做法,同样为两汉儒者重视。在此背景下,张禹等中原士人形成迥别于吴越居民的潮神认识,实乃顺利成章之事。在两汉儒者的不断强调下,伍子胥先贤形象逐渐传播开,势必会对吴越地区的潮神形象产生影响。另外,《汉书·循吏传》中记载了大量地方长官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事例,说明以儒家伦理教化百姓是汉代普遍现象。而两汉时期,曾有多位中原士人出任吴越地方长官。如南阳宛人任延、京兆长陵人第五伦、河南洛阳人庆鸿、扶风茂陵人马稜均曾担任会稽太守。他们在任期间,应会推行以伍子胥为凭借的忠孝教化,从而帮助洗刷强加给伍子胥的冤名。
其二,对涌潮成因认识的提高。钱塘江潮和广陵潮是天体引力、江口盛行风向、喇叭形河口、河流径流量季节分布不均、河口沙坎堆积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钱塘潮成因,可参见陈吉余、罗祖德、陈德昌、徐海根、余彭年:《钱塘江河口沙坎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地理学报》1964年第2期;毛献忠、龚春生:《钱塘江涌潮影响因素分析》,《水力发电学报》2011年第4期。。东汉时期,王充已有“言其(伍子胥)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的论断。他指出,“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汉)王充:《论衡·书虚》,第1155页。,已是对涌潮成因所做较为科学的解释。东晋葛洪也反对把伍子胥视为潮神,他认为“从直赴曲,其势不懈”是江潮“隆崇涌起以为涛”的真正原因*《太平御览》卷68《地部三十三》,第388页。。王充、葛洪对涌潮成因的解释,反映了古人对涌潮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这应对潮神伍子胥形象的改善有所帮助。
随着伍子胥形象的转变,潮神信仰开始为政府提倡。两汉时,广陵国江都县(治今扬州)的江水祠是国家正祀岳镇海渎中“四渎”之一*《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38页。。南朝齐、梁时,江水祠“俗谓之伍相庙也。子胥但配食耳,岁三祭,与五岳同。”*(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等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4页。广陵潮是长江口的涌潮,伍子胥显然是以潮神身份陪祀江渎,而江渎是国家命祀,表明伍子胥的形象已为国家认可。梁元帝萧绎曾做《祀伍相庙诗》*(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38《礼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页。,对伍子胥持肯定态度,同样体现了统治者对潮神信仰的支持。
总之,汉武帝以前,儒家思想尚未成为统治思想,祭祀话语权掌握在巫祝手中,吴越地区的“科层文化(hierarchic)”和“世俗文化(lay culture)”*“科层文化”指上层文化、学者文化,与民间通俗文化对应,参见Robert Redfie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ш: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70.区分度不大。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虽然吴越地区文化发展程度相对中原滞后,但“科层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区分度已逐渐明显,巫祝只能左右“世俗文化”,即“一般知识与思想”,掌握“科层文化”或“精英与经典思想”话语权者乃为士人,他们是新的“思想者”,对民众的影响会逐渐超过传统“思想者”。随着士人对伍子胥忠孝形象的强调,吴越地区潮神伍子胥的形象逐渐改善。另外,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帮助吴越民众更科学的认识涌的形成,这有助于他们理性看待伍子胥与涌潮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士人对伍子胥忠孝形象的强调,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伍子胥信仰。据《水经注》载,成阳县(今山东鄄城县南)有一处文教重地曰崇仁乡,“乡曰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伍子胥庙也是此地众多祠庙之一,“尧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间有伍员祠”*(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等疏:《水经注疏》,第2040—2041页。。该地“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无水患威胁,故此为伍子胥立庙并非因涌潮或水灾,当是缘于官方教化。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伍子胥的先贤形象与潮神伍子胥信仰融合,潮神伍子胥已不再是以波涛惩罚两岸的恶神,而是忠孝爱民的善神。形象转变后的潮神符合国家教化要求,伍子胥开始充当江渎的陪祀,弃恶从善,逐渐走向国家正祀的殿堂。
三、隋唐五代时期潮神伍子胥的教化职能、司潮显灵与纳入正祀
随着正面形象的确立,隋唐五代时期,潮神伍子胥信仰得到更大发展。唐代对淫祠管控十分严格。武则天时,江南巡抚使狄仁杰曾毁淫祠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87页。;长庆三年(823年),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奏去管内淫祠一千一十五所”*《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503页。,而毁淫祠前后,杭州刺史白居易曾于伍子胥庙祈雨(详后),说明潮神伍子胥并未在禁毁之列。唐德宗年间,于頔任苏州刺史时“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但“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旧唐书》卷156《于頔传》,第4129页。。元和十年(815年),杭州刺史卢元甫曾专门为吴山子胥庙立碑铭并作序,他认为祭祀伍子胥乃“启忠祠”、“废淫置明”之举,盛赞伍子胥“善事父为孝”、“得死直言”为忠,并以“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诚”为结语*(唐)卢元甫:《胥山祠铭》,《全唐文》卷695,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37—7138页。。可见唐代士人认为,祭祀伍子胥是“启忠”、“废淫”,教民知礼的举措。以上事例表明,潮神伍子胥已是地方政府推进忠孝教化的重要凭借。随着潮神伍子胥信仰的发展,其信仰内涵亦在不断丰富。长庆二年(822年)夏,钱塘江流域少雨,白居易“愧无政术,既逢愆序,不敢宁居,一昨祷伍相神,祈城隍祠”*(唐)白居易:《祝皋亭神文》,《全唐文》卷680,第6956页。。可见,潮神伍子胥因阴辖水而有主管地方旱旸的神职。
隋唐五代是钱塘江沿岸低地开发的关键时期。以杭州为例: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杭州移治柳浦西凤凰山麓一代,“乃一变为江干”,为之后发展奠定基础*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包伟民主编:《史学文存:1936—2000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隋大业五年(609年)杭州(包括属县)人口有15380户;唐贞观中,杭州人口有30571户、153720口*乾道《临安志》卷1《户口》,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杭州人口多达86255户、585963口*《旧唐书》卷40《地理志》,第1588页。。随着钱塘江沿岸低地的开发和人口增殖,钱塘江潮与两岸居民的关系日益密切。唐代前期,关于钱塘江潮灾的记载还寥寥无几,唐代中后期,相关记录已然不少。诸如大历十年(775年)七月杭州发生潮灾,“海水翻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四百余人”*《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62页。;会昌五至六年(845—846年),李播为杭州刺史时,“涛坏人居不一”*(唐)杜牧:《樊川集》卷8《杭州新造南亭子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61册,第464页。;光化三年(900年)九月,“浙江溢,坏民居甚众”*《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5页。。这一时期,涌潮已不单是“以溺杀人”的个体性危害,更表现为“荡州郭”、“坏人居”式的群体性灾难。
伍子胥兼有先贤、潮神双重身份,潮灾破坏不大时,政府仅需要其先贤身份推行教化,司潮神职更多反映普通民众的需要。但随着人潮关系日益密切,伍子胥司潮神职已是官民共同需要。景福二年(893年),钱缪筑杭州罗城时,“江涛势激,版筑不能就”,因“祷之(伍子胥),沙涨一十五里余,功乃成”*(宋)范迥等:《吴越备史》卷1“唐乾宁四年八月”条,《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59册,第6页。,于是钱缪请求敕封潮神伍子胥。乾宁二年(895年)“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侯”*(宋)范迥等:《吴越备史》卷1“唐乾宁二年十一月”条,第5页。,正式肯定了伍子胥潮神身份的正统性。乾宁三年(896年)杨行密派安仁义沿“沙路”袭击湖州,钱缪忧“沙路之患”,“乃祭江而祷胥山祠,一夕惊涛,沙路悉毁,江壖一隅,无所患矣”*(宋)范迥等:《吴越备史》卷1“唐乾宁三年正月”条,第5页。,“感其灵贶,请而封之”,唐中央政府遂“敕封吴山惠应侯为吴安王”*(宋)范迥等:《吴越备史》卷1“唐乾宁四年八月”条,第6页。。伍子胥用潮水冲毁沙路助政府御叛,再次被褒奖,获得加封。伍子胥司潮神职有功于国家,筑城、御叛显灵是政府赐号的重要原因*当然,伍子胥被加赐封号也离不开唐后期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大背景。。

潮神伍子胥正面形象树立后,政府对潮神伍子胥信仰持支持态度,唐代吴越地区三次大规模禁毁淫祠,均未涉伍子胥祠庙。不过,士人推崇潮神伍子胥是因其具备先贤形象,并非因其司潮神能。因能履行忠孝教化者不止伍子胥一人,在对民间祠神封号持谨慎态度的唐代,仅凭教化之功,伍子胥的潮神身份很难被官方认可,故其长期扮演“虽非命祀,不让济渎”的地方祠神角色*(唐)卢元甫:《胥山祠铭》,《全唐文》卷695,第7138页。。随着钱塘江沿岸低地开发和人潮关系日益密切,唐末五代时,抵御潮灾已是政府日常之责。官方不仅需要伍子胥的先贤形象推行教化,更需要伍子胥司潮神职捍海御灾,故唐王朝对其封号赐爵,改变了其“非命祀”的地位。
结 语
钱塘潮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恰在伍子胥被冤杀前后,因此民众极易将涌潮产生与伍子胥被冤杀相联系,伍子胥渐被视为潮神。随着涌潮规模的扩大和吴越巫祝对民众信仰的干涉,潮神伍子胥被无端冠以凶神恶名。稍后长江口出现广陵潮,因该地自然、人文背景与钱塘江口类似,长江口居民也以伍子胥为潮神,且其凶神形象未变。两汉时,官方推行儒家教化,伍子胥的忠孝形象被士人称颂,为潮神伍子胥形象的转变提供可能。随着士人对伍子胥忠孝形象的强调和民众对涌潮成因认识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潮神伍子胥形象渐趋正面,并一度作为国家正祀之江渎的陪祀。潮神伍子胥正面形象的树立,是士人主导的“精英与经典思想”对民众“一般知识与思想”影响的结果。隋唐五代时期,潮神伍子胥信仰不断发展,在教化民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因司潮神职尚不被政府重视,其长期扮演“非命祀”的地方神角色。随着钱塘江沿岸低地的开发和人口增殖,人潮关系日益密切,伍子胥数次以潮神身份显灵,阴佑政府筑城、御叛、修堤。官方通过赐予封号,将潮神伍子胥纳入国家祀典,完成了官方“精英与经典思想”对民间“一般知识与思想”的吸收,形成了官民共祀潮神伍子胥的情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南沿海多元宗教:信仰教化与海疆经略研究”(15AZS0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郝红暖
From Evil to Good:New Approach on Development of Wu Zi-xu the God of Tide
LI Jin-cao WANG Yuan-lin
(Historical Geographic Research Center,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The faith of the god of tide come out with tide bore formed.At first,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Qiangtang tide and Guangling tide by ancients was attributable to Wu Zi-xu’s revenge because he was killed unjustly.Wu Zi-xu was regarded as the god of tide with evil image.A positive image of Wu Zhi-xu has been built up after Wei and Jin Dynasties,because the faith and filial piety of Wu Zi-xu was promoted by the scholar and people’s awareness of tide bore formation was improved since the Han Dynasty.The Qiantang tide bore has a growing impact on real life with the low lands exploitation and ever-increasing population along Qiantang river.The governments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tide-control ability of Wu zi-xu except his status of ancient sage.The God of tide Wu Zi-xu has been brought into state ritual system through given titles in the Tang Dynasty.
Qiantang river;god of tide;Wu Zi-xu;national sacrifice
K20;K892
A
1005-605X(2017)01-0033-06
李金操(1990- ),男,河南扶沟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元林(1968- ),男,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