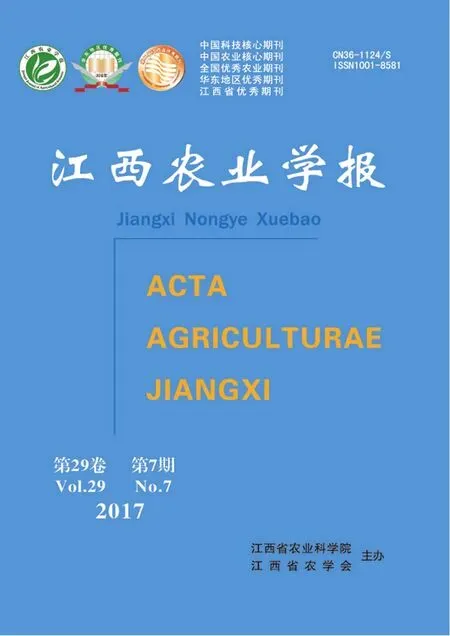2006~2016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综述
郑永兰,王宝荣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006~2016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综述
郑永兰,王宝荣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依据目前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概念及内涵、研究视角和方法、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产生的原因及其实现路径等内容进行了概括,并对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了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尽管如此,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仍十分艰难,阻碍众多,如城乡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市民化的成本昂贵等。基于此,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现代生活当中,另一方面难以回归农村的双重尴尬境地。已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乡两不融的问题,其顺利实施也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一号文件中,自此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加强了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李克强总理也多次提及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本文基于2006年至今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概念及内涵、研究视角和方法、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产生的原因及其实现路径等内容进行了概括,并对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了展望,以期对我国后续相关研究起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1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概况
“农民工”一词最早缘起于社会学。王春光教授于2001年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罗霞等[1]于2003年从代际和年龄角度,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定义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在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农村流动人口”。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一号文件第一次出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认为加之职业类别和户籍限定可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更为精准。因此,将其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2]。郑永兰[3]将其界定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近10多年来,不同的学者将“年龄”、“代际”作为重要的定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界定,但此类界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难以精确描述这一特殊群体。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并无严格的定义,基于此,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因此,研究者应对此概念不断更新、完善,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
近年来,我国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研究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目前,学界基于“过程和结果”两种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行了界定。首先就过程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并非一气呵成的,而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逐步稳健推进的,故而主要从“过程”角度进行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是:王艳华[4]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定义为“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实现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其市民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角色认同、印象管理、城市化的消费方式3个方面”。夏丽霞等[5]将“市民化”从技术和文化层面进行划分,分为狭义的市民化和广义的市民化。狭义“市民化”是指农民工依法取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与身份的过程。广义“市民化”涵盖了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如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6]。黄静等[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应当是使新生代农民由职业意义和身份意义上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得到市民资格的同时提高自身相应的能力、素质和认同。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其成败关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基于此,国家加大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学术界亦深入探讨了该问题。目前其研究内容不断发展和日益丰富,研究方法也不断更新,本文从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2个方面对学界现有的理论进行了综述,具体如下。
2.1 理论视角归纳
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2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类学者站在较为宏观视角,深度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不同情境下面临的双重边缘化困境。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视角有:(1)城市融入视角: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全面深化改革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努力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制度,以期解决市民化后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社会排斥视角:持这一视角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再生化难、市民化难及融入城市难等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市民在政治权利、体制等方面对其排斥。(3)社会差异视角:用社会差异的视角来看待市民化问题,包括制度身份差异、文化差异、就业差异等方面的社会差异带来不同的研究思路。(4)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视角:现在以工作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代替了传统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的不稳定性和安全感的缺失使其更难融入城市,应多方面共筑社会关系网络。宏观视角除了上述提到的视角,还有新户籍制度改革、社会资本、社会公正、包容性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视角。另一类学者从微观视角,基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诸如劳动权益受损、住房条件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阐述。(1)社会分层角度:学者们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特征和他们与其他的群体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述。(2)生活满意度视角:主张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设定的生活标准及其生活状况对城市生活质量做出评价。微观视角还包括代际视角、消费认同等视角。
2.2 研究方法归纳
近年来,学界主要从规范和实证2个方面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究。规范性研究方法依靠哲学思辨,利用归纳法或演绎法进行概括说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如丁静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林娣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等论文主要属于规范性研究。实证研究方法依靠实证主义对实施结果,利用感觉经验来验证理论假说的正确性。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logistics、probity等研究方法。在实证研究的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刘洪银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谢东虹的《工作时间与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2015年北京市的调查数据》等。无论是单一规范性研究(只属于理论上的假设和推断缺少验证,忽视定量分析)还是单一的实证研究(缺少理论和知识整合的能力,难排除价值判断不合理的地方,难避免个人偏好干扰)都会有缺陷,将2种研究方法结起来,以便更加全面和综合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所在,从而找到更加准确的解决办法。
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原因
本文结合学界目前已有的研究,从制度方面、经济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观念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进行了综述。
3.1 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阻碍
目前我国实施的户籍制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和融入城市的脚步,也给进一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给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邓秀华认为只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紧将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制度设计,并且在操作上具有可行性,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6]。户籍制度的衍生制度是根本原因。一是就业制度。夏丽霞等[8]认为目前的就业制度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带来了诸如就业机会低、工资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及地位低等一系列不公平问题。二是住房制度。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立足于城市并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解决住房问题,住房是新生代农民工扎根于城市的基础和重要保障。金萍[9]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就是解决了其基本的生存需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社保制度。由于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不完善使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市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四是教育制度。唐踔[10]表明,农民工子女与当地户籍人口子女就学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少学校仍拒绝接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学校收费仍存在客观上的双轨制,学籍问题使很多民工子女的升学教育受到限制,仍存在因为没有本地学籍就不能在城市上高中、不能参加当地高考等限制。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体系应尽快完善这方面内容,促使不同地区相互兼容,这必将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11]。
3.2 经济成本障碍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所需经济成本巨大,需要政府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丁萌萌等[12]按照2011年我国的外出农民工人口总数为15863万人计算,认为解决我国农民工户籍共需6408.97亿元,人均需要4024.77元。经济成本障碍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庞大的公共支出费用,目前各级政府短期内很难全部筹集到市民化所需的成本。黄锟[13]认为城镇政府将难以支付因城镇人口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的相应费用。二是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市民化的成本高昂,难以支付。张国胜[14]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包括生活成本、智力成本、住房成本与社会保障成本等,这些高昂的成本费用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支付的。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其职业的发展空间,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无法完成市民化私人成本的支付,沉重的各项成本已成为其市民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综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庞大,实现其市民化的成本巨大,是政府财政难以承受的,亦是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承受的。
3.3 身份认同偏差
新生代农民工正经历着生活环境的变迁、人口异质性增强和城乡文化价值体系差异扩大的境况,这些差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面临着自身及其城市居民的认同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自我身份认同困境。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和自我身份认同同样对市民化的意愿产生影响,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认同出现偏差及社会上对其进行排斥等原因,使得他们难以从情感上真正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长期持有偏见。王兴周等[15]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象的长期存在,致使城市居民封闭和集体排斥性较强,城市居民普遍对农民工持一种傲慢与否定的态度。也有学者把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文化异质性差异,江小容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论述。
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
基于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学术界从以下几个角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4.1 改革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制度障碍
蔡志刚[16]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我国应当尽快消除传统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区别,统一城乡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居民的真正平等。在政策层面,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加速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2016年1月1日《居住证暂行条例》的实施,使得城市落户的标准和落户的途径更为明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同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更加完善了大中城市的落户政策。改革户籍制度的关键在于消除户籍制度背后的隐形制度。一是完善劳动就业制度。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实现市民化首先要解决平等就业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应当构建平等的就业制度,首先在就业市场准入方面,应该使所有劳动者具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其次在劳动关系方面,应当使所有劳动者具有获得平等劳动报酬的权利;再者在平等就业制度方面,应当使所有劳动者具有获得平等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权利[17]。二是住房制度。由于我国体制不健全导致出现高价住宅,以及我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带来的一系列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享有城市住房福利,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市场上租用或购买商品房。“居者有其屋”方能使其在城市立足,我国政府应大力发展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三是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韩俊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离不开政策的改革,因此户籍制度、推进劳动就业、义务教育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必须大力稳步改革,逐步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制度体系[18]。
4.2 加强政府的公共支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巨大,需要政府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单菁菁[19]认为由于我国市民化社会总成本较高,应建立一套包含政府、企业、个人和市场在内的多元成本分担制度,从而确保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张继良则认为从政府、企业和个人3个方面进行成本的分担机制,同时认为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农民工分批有序地实现市民化。2016年8月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要强化地方政府特别是人口流入地政府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系。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应积极的参加职业培训,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增加竞争力,从而增加自身的收入。
4.3 转变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
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等,给人以外表脏、素质低等形象,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以从事服务业为主,其外在形象、素质与市民无异。然而,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在对身份认同中仍存在偏差。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个体需要转变观念,增加对城市的认同感。姜胜红[20]强调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归属感,提高他们的话语权。其次,城市居民应主动改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和眼光,消除对他们的误解,增强对他们的认同感,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一个尊重和谐的氛围,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转变观念,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顺利的融入城市。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领域已由先前的社会学领域逐步拓展延伸至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研究范围已从宏观层面(政府)、中观层面(社会)深入至微观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更加注重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需求和感受;研究视角从社会差异、城市融入等宏观视角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等微观视角;研究方法已完成由定性转向定量,由文献研究转到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更加令人信服。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仍然非常的复杂和艰巨,相关研究急需进一步开展。
5.1 理论视角需进一步拓展
目前学术界大多基于微观和社会群体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开展相关的研究,然而罕见其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时,结论性研究较多,全面性研究较少,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不足。因此后续研究应基于多学科、多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相关研究,以便得到更加准确的相关研究结果。
5.2 研究内容仍需深入
目前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未来趋势和走向研究等相关研究内容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过于理论化、抽象化,缺乏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5.3 指标体系仍需完善
目前国内已开展了较多的基于定性角度的相关研究,同时开展了少量的以局部性、区域性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总体而言,尚缺乏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整体考察,不能清晰地显示出存在于各个研究目标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学界尚缺乏一致的市民化指标测度体系,难以了解市民化的现状及其真实水平。不同学者的指标设置、调查方法、对象选取不尽相同,使得其研究也缺乏可信度。
因此,基于理论视角、研究内容、指标体系等多个层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后续研究仍是热门内容和关键话题,众多学者将目光研究视野聚焦、定位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现实问题,该问题的正确和妥善解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大大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1] 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3(1):109-113.
[2]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J].江苏纺织,2010(8):24-30.
[3] 郑永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9-162.
[4] 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7(5):38-41.
[5] 夏丽霞,高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J].城市发展研究,2009,16(7):119-124.
[6] 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J].求索,2010(8):71-73.
[7] 黄静,李汶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体制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成渝地区的现实分析[J].农村经济,2016(6):119-123.
[8] 夏丽霞,高君.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1):41-45.
[9] 金萍.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保障[J].社会主义研究,2012(4):89-91.
[10] 唐踔.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析[J].前沿,2010(11):116-121.
[11] 王玉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J].江淮论坛,2015(2):132-140.
[12] 丁萌萌,徐滇庆.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J].经济学动态,2014(2):36-43.
[13] 黄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 张国胜.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视角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5] 王兴周,张文宏.城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173-179.
[16] 蔡志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初探[J].理论探索,2010(2):91-93.
[1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侯云春,韩俊,等.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J].改革,2011(5):5-29.
[18] 韩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J].理论视野,2010(9):20-23.
[19] 单菁菁.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其分担机制研究[J].学海,2015(1):177-184.
[20] 姜胜红.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兰州学刊,2011(3):89-93.
(责任编辑:管珊红)
Research Summary of Urbanization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6
ZHENG Yong-lan, WANG Bao-ro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researches by relevant scholars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urbanizati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for this field, and the causes for dilemma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s of urbanization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gives a prospect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futur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Urbanization; Research summary
2017-03-0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16BZZ073)。
郑永兰(1973—),女,江苏兴化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
F320
A
1001-8581(2017)07-01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