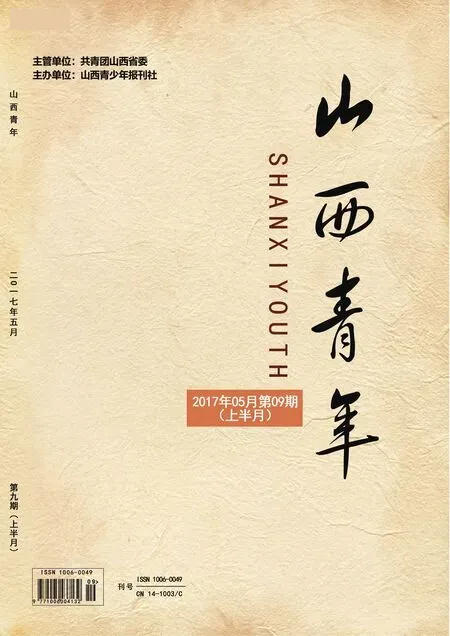试论佛教文化视阈下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周志峰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试论佛教文化视阈下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周志峰*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文学的跨领域,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方向。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方式,必然挖掘出传统批评分析中不曾发现的深层意蕴。从佛教文化视阈出发,探索沈从文的思想和创作,便不难发现他在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吸取了佛教文化元素中有益的因子,建构起了独特的艺术世界和审美天地。他以清晰自然,空寂静净的笔调书写人生,以佛教式温爱慈悲的胸怀关照万物,以此来实现对国民灵魂重塑和民族出路的终极探索。
佛教文化;沈从文;人生哲学;作品蕴藉;审美旨趣
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道一同,构成了互融互补的审美复调,并对中国历代士人生命认识、文学创作乃至生活态度的建构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就现代文学而言,对许地山、废名等人与佛教文化关系的研究颇多,但仔细研读,则不难发现一生自命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无论在人生哲学,还是在艺术风格与意蕴中,都渗透出了佛教文化的因子。然而,目前研究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甚少,因此,本文便从佛教文化的视阈入手,来探寻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以便更深入地认识这一位现代文坛上杰出的作家。
一、沈从文佛教观的成因
佛教文化体现了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和为一切众生受无量苦难的意识,因而佛教成为了受苦受难者的精神栖息地与希望的寄托。沈从文笔下“桃花源”般的湘西世界最后在统治者的压迫和残酷的现实下沦落为“田园挽歌”,蕴含了湘西人民的悲苦生活。在这样的境地下,苦难民众自然与宗教联系在了一起。原始巫文化与佛教文化等多种元素融合,形成了湘西世界独特的鬼神崇拜和菩萨崇拜。沈从文在《哨兵》一文中写到:“庙宇的发达与巫师的富有,都能给外路人一个极大的惊愕。地方通俗教育,就全是鬼话:大人们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带着进庙去拜菩萨,喊观音为干妈,又回头来为老和尚磕头。”[1]经过湘西世界长久的历史积淀和自幼的教育,形成了一种重宗教的集体无意识。出生与成长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环境中的沈从文必然在冥冥之中受到其熏陶与影响。
另外,沈从文童年时期的人生遭遇与经历也在他身上印下了佛教深深的烙印。沈从文幼年时,家道中落,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与世事的沧桑。随后,和军队同去辰州充兵,在这期间,他更是见惯了杀头与流血。正当他处在童年的苦闷时期,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走进他的生活给他情感的慰藉。沈从文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2]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与佛教“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相吻合,自然使得他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而,集体无意识下的必然性和命运无常的偶然性,建构了沈从文的佛教意识,并使得他总在有意或无意中运用佛家慈悲胸怀、人生无常的眼光来关照万千世界。
二、佛教视野下的人生哲学
沈从文的人生哲学包含了“生命”与“生活”的二元对立,包含了对“爱”与“美”、“常”与“变”的哲学思辨等等。诚然,他的这些思想意识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体验和感悟有关,但也离不开佛教因子对他的启发与诱导。本节则主要通过探讨他对“生命”与“生活”的体悟,来窥探佛教从何种意义上影响了沈从文生命哲学的形成。
佛学本是治心之学,它以慈悲喜舍之心修持六度、断绝我执、灭除幻见,从而提升人生境界,在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3]佛教认为每个人生而就有神性、清净和无我的境界,但个体被抛在尘世之中,为功名所累,为物欲牵绊,导致这种境界渐行渐远。只有潜心修行,清净耳根,净化灵魂,才能重新找回佛心佛性。沈从文在乡下与都市的不同环境下,感悟到的乡下人“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于人生的人生形式”和都市人“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命”与“生活”的哲学思辨。“生命”代表了神性,体现着自然的人性,蕴含着爱与美,是重塑国民灵魂与重建理想民族的一剂良方;而“生活”则代表着扭曲的,被阉割了的人性,是物欲横流的都市性的写照。沈从文曾谈到:“人之为人,应当还有超越单纯‘生活’的神性,一种属于人生理想与情操的精神活动,这才是区别于动物的人的‘生命’”。[4]因而,要把碌庸无为的“生活”引向体现着爱与美的“生命”,进而达到重塑国民灵魂的终极关怀。但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所谈到的神性是一种超世俗性的,而沈从文则更主张将其人间,引向审美创作与文学层面,引向蔡元培式的“美育代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在阐释生命的神性时,沈从文偏爱使用“庄严”一词。“要紧处或许还是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向深处走,多读些书,多明白些事情,了解人之所以为人……”。[5];“用那个感情去追求一种人类庄严的勇气”[6]等等。庄严一词原为佛家语,指佛家对表象事物,或心理行为的道德意义的修饰、加强。这里可以看出,无论从沈从文的人生哲学还是在阐释时遣词造句方面,都渗透着佛家文化的元素。
三、作品蕴藉中的佛教因子
由于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沈从文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用一种佛家的胸怀来审视和关照万千世界。因而,在他的审美创作中,也渗透着佛教文化的因子。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佛教经典的直接解构与重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作品中间接呈现的佛教内涵。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根据唐朝高僧道世撰写的“佛教的百科全书”《法苑珠林》中的十二篇佛经故事改写成八篇作品,加上开篇根据西南少数民族风俗虚构而成的《月下小景》,结成《月下小景》集。[7]这部《月下小景》直接体现了他对佛教经典的改编和再创作。例如:将“布施部”中的《太子须大拿经》改编为《慷慨的王子》,将“持戒部”中的《大庄严论》改编为《医生》,将《树提伽经》、《金刚经》、《长阿含经》整合为《寻觅》一文等等。
而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佛教因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的小说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特有的模式:开头不留笔墨的讴歌湘西世界桃花源般的田园牧歌世界,赞美自然美、人情美、人性美等等;而在结束则往往出现文本裂隙,将“牧歌”变为“挽歌”。用沈从文本人的话语来说即是:“一切充满了善,然而一切都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不产生悲剧”。[8]这反映了在现代化“常”与“变”的语境下,湘西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哀,是佛教中万物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反映。同时,也表现出沈从文佛教式的慈悲胸怀。翠翠、萧萧、三三是这种模式的体现。第二,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和都市系列小说的比照,体现了自然的神性和扭曲的人性。在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物的自在生命状态无论是思想基础、还是表现形态,与禅宗有了相同的价值取向:反对“异化生存”,否定虚伪的现代物质文明,回归自由不拘的生存状态。[9]进而要用神性的生命来引导物质的生活,净化人的心境,达到生命意义上的和谐,以此来实现国民灵魂的重建,拯救中华民族。第三,沈从文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观音的意象。如,在《长河》中对夭夭的描写:“夭夭长大了,一定是个观音。那会错。”再如,《一个母亲》中的大妹像观音、扮观音;《阿黑小史》中的阿黑等。观音意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深意都是沈从文的佛教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四、审美旨趣中的佛教元素
除了作品思想和蕴藉外,沈从文的佛教式的慈悲怜悯胸怀也体现在其作品的审美旨趣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趋于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带有禅宗的意蕴和温爱的色调。作为唯美主义作家,他不忍心表达血与泪,因而常常是用淳朴、自然、优美、健康的民风民俗,人性人情冲淡一切,因此在他笔下“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4]另外,沈从文的审美情趣也带有一种空无和静净之感。他在自叙其创作心理是曾说:“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5]。要除尽内心的杂念,洗尽铅华,进而达到空灵自然的审美状态和虚无静净的艺术心境。这种审美观和佛教所强调的“凡有所相,皆是虚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正是因为这种禅宗般的止观静虑,涤荡胸怀,虚纳万物心境,才使得其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美。
五、小结
沈从文不是一个佛教徒,但是他却深受佛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他吸取了佛教文化元素中有益的因子,并在自己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独特的艺术世界和审美天地。他以清晰自然,空寂静净的笔调书写人生,以佛教式温爱慈悲的胸怀关照万物,以此来实现对灵魂重塑和国家出路的终极探索。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78.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57-358.
[3]龙永干.人生体验的会通与文学创作的资鉴[J].贵州文史丛刊,2011(03):89.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59.
[7]龚敏律.论沈从文《月下小景》集对佛经故事的重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02):186.
[8]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M].花城出版社,1984:280.
[9]苏永前,汪红娟.论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禅学意趣[J].甘肃社会科学,2005(03):116.
周志峰,四川德阳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I
A
1006-0049-(2017)09-025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