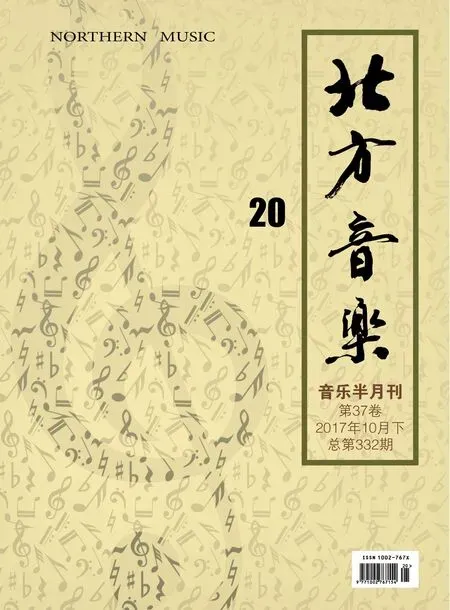从约翰·凯奇的《4分33秒》和谭盾的《鬼戏》看后现代主义音乐哲学
于 强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从约翰·凯奇的《4分33秒》和谭盾的《鬼戏》看后现代主义音乐哲学
于 强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20世纪学院派音乐多元化趋势下,后现代主义音乐代表人物约翰·凯奇和谭盾的音乐都体现出了“主体消解”的后现代音乐哲学思想。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对谭盾的《鬼戏》及约翰·凯奇《4分33秒》的创作背景、音乐呈现方式进行分析,并阐释其蕴含的后现代音乐中的音乐哲学思潮。
音乐哲学;偶然音乐;鬼戏;4分33秒
引言
在20世纪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音乐的发展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的思想差异化,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审美旨趣显著变化。后现代主义的音乐艺术创作与当时代的哲学大环境下的“主体消解说”相互应和。约翰·凯奇和谭盾的音乐创作的主体意识的消失,都寓于音乐主体的消解中。本文从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对谭盾的《鬼戏》及约翰·凯奇《4分33秒》的创作背景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后现代音乐哲学在约翰凯奇和谭盾的作品中的音乐哲学内涵。
一、约翰·凯奇《4分33秒》
约翰·凯奇作为美国著名的先锋派作曲家、偶然音乐的创始人,他的音乐创作观念深受东方神秘色彩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写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与各种意图打交道,而是与音响打交道,或者说,答案必须采取反论的形式——有意的无意义或一种无意义的游戏”。[1]
约翰·凯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渗透出出西方后现代哲学观念,音乐的偶然性与无序性被提升至空前高度,音乐不再是作为音乐单独的主体存在,而是泛生活化的存在,寄希望于听众用音乐思想去聆听“生活之声”,《4分33秒》正是这种思想的经典代表作。
“演奏”《4分33秒》的过程中,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声音”和“音乐”传达给观众,而是以“空结构”无声地表现。但约翰·凯奇认为“无声” 就是指没有意识到的声音[2],他事实上是把“演奏”过程中发出的所有声音都认为是音乐的一部分,而这些音乐却不是作曲家刻意准备的,而且是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音响,之前所有的音乐作品中观众都没有意识到的。于是乎,在凯奇这部作品中,音乐的本质意义似乎变得模糊了,人们在聆听生活中的声音即是音乐了,也是现实就是音乐了,观众在“欣赏”这一作品时也在创作这一作品,观众本身也是音乐的本身,作品展示和观众的参与成为了重点,音乐与生活的界限的消解也就是“音乐主体”的消解。
二、谭盾《鬼戏》
后现代主义者在尼采的“上帝死亡”的口号之后,提出了“主体死亡” 的口号,而人就是“世界的成分”,人与世界万物融合在一起,彼此不可分离,也可以说人融入在世界万物之中也就是“主体消解”。中国作曲家谭盾的音乐也已不再像现代主义音乐那样,试图表达“主体意识”,而直接表现“主体消解”思想,音乐大多都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表现内心世界、情感、生活作为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性”。
谭盾的《鬼戏》全名《鬼戏——为弦乐四重奏、琵琶及铁、水、纸、石头及演奏员的人声而作》,作为一部典型的综合艺术作品,整合了灯光、舞台、表演和声响、多媒体等手段和途径,是在文化、文学、戏剧、美术和音乐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音乐既是“声音”本身的艺术,又是不能单独存在,不能逃离音乐所在的生活,音乐着力模仿生活,融入生活,融入自然。
作品的表现形式也以“表演”的形式展开,音乐并非由孤立的只是由传统意义上的各种乐器产生,而这些“表演”的分量亦极为重要,演员撩动水发出的声音,人舞台上梦游四处走动的脚步声,鬼影嚎叫般词词语,扩大音发大后鹅卵石撞击牙齿,纸张抖动的声音都是音乐,都试图以这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音乐”来模仿鬼影。随后大提琴主题音乐、巴赫主题音乐与中国主题音乐(民歌《小白菜》)等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与水声、脚步声、纸声等乐音具有同等的地位,音乐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人声或者是乐器包括噪音乐器发出的声音。
谭盾以一句“因为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是完全不可能去沟通的”结束的“谭卞之争”,事实上也是由于谭盾的作品中大量采用的“自然之声”“无声”等消除音乐主体的手段,与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主体之间产生的矛盾。如果对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哲学有所了解,也就不难理解谭盾的作品意图表达的内涵了。其实谭盾的音乐所体现的后现代主义音乐哲学思想中渗透着中国传统道家哲学,只不过在近现代尚无一位作曲家以这种“道家”哲学思想表达音乐而已。陈其钢说:“如果没有谭盾,中国现代音乐的形象以及它在全世界的地位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谭盾的大跨度的、多方位的探索,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是空前的。”[3]
三、结语
谭盾的《鬼戏》和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两部作品中均投射出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消解”,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反主客分离,反主体性特征相符,两位作曲家的这两部作品通过一种行为化的展示,充分反映了人们的内心与外界,音乐与生活绝对不是泾渭分明不可融,事实上作曲家试图让观众注意、倾听、欣赏生活中的本真声音,赋予人们现实生活以音乐的“存在”。
[1]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下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
[2]余丹红.放耳听世界——约翰·凯奇传[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3]何农.陈其钢谈谭盾和现代音乐[J].北京:人民音乐,2002.
J60
A
于强(1991—),男,青岛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硕士,声乐演唱与教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