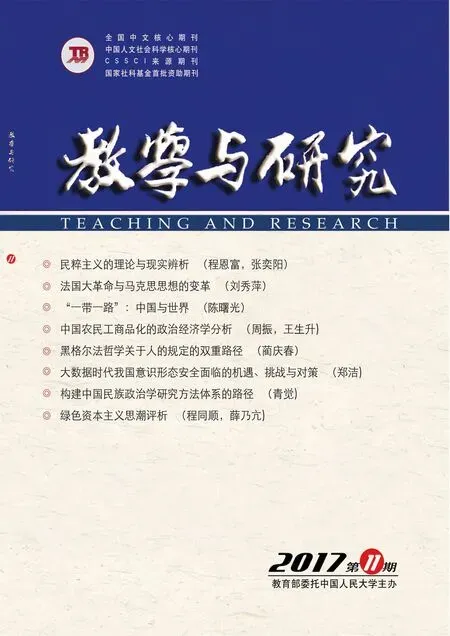中国农民工商品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中国农民工商品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周振,王生升
农民工;劳动力商品;资本积累;集体经济
在《资本论》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商品理论构成了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分析的前提。以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为参照系,波兰尼、莱博维奇等学者研究了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分析了这一过程中的去商品化或半商品化问题。以此为理论框架分析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可以看出,作为处在半商品化状态的农民工,其变化适应于资本积累在产业和空间的特定配置,所谓的农民工问题是这一过程中内在矛盾的外化形式。要解决农民工问题,不仅需要优化资本积累的产业和空间配置方式,更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以协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农民工迁移伴随改革开放的始终。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农民工一般是就地实现转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农民工向大中城市转移的“民工潮”现象,这其中70%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到城市寻找打工机会,而同时又有约1/3的外出农民工从城市暂时或永久地返回原籍地,农民工回流问题初现。[1]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工迁移的步伐仍在继续,但同时,由于劳动力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原因,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开始回流故土,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用工荒”问题。本文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分析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揭示其运动变化的规律,进而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个人理性选择:西方经济学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误区
在西方经济学观点中,人口迁徙及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英国学者雷文斯坦最早从人口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概括,并指出人口迁移的主要动机是受经济因素的支配。[2]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进一步发展了雷文斯坦的观点,并建立了二元经济结构的人口流动模式,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中,由于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在收入上存在差异,随着现代经济部门资本家利润的不断增加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现代经济部门便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至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这一部门为止。[3](P70-71)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为什么会流动的问题以及流动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目前国内学界热衷于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如用刘易斯拐点、引力模型和推拉模型等来解释中国的农民工及回流问题,但西方的诸多理论在套用到中国农民工问题时有诸多的局限性。有学者就指出,“刘易斯拐点是特定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下的现象,并不适合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要纠正用西化理论掩盖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做法。”[4]此外,还有学者引入西方经济学中的引力理论和推拉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力模型是将人口迁移与迁出地人口、迁入地人口和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联系起来,认为人口迁移与迁出、迁入地人口正相关,与两地之间的距离负相关,部分学者引用此理论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迁移越来越符合引力模型的预测。[5]现代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生活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有学者主张用推拉模型来解释农民工问题,认为该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6]
无论是引力模型还是推拉理论等,实际上都是对西方经济学新古典模型的应用,也就是运用个人理性选择来分析经济问题。农民工理性权衡成本收益,由于工业和农业收益差距,从而导致农民理性选择去城市就业。
但问题在于,农民工理性选择的历史条件才是决定他们会有何种选择的关键所在。这些历史条件,实际上就是城市的资本积累快于农村,核心问题是资本积累的产业配置和空间配置。对资本积累的产业和空间配置的分析,是和资本积累的具体形态紧密相连的,而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不过是这种具体形态的派生结果而已。因此,用西方经济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误区,就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漏掉了最关键的内容,即资本积累的产业和空间配置。
要理解农民工问题,仅仅从农民工的个人选择视角,是没有历史感的抽象分析。只有把握资本积累的产业和空间配置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才能认识农民工现象的内在规律和历史趋势。也就是说,要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而不是从个人选择的角度,去分析农民工问题。这个角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它是正确认识和分析农民工问题有效的理论框架。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商品理论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商品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乃至社会总资本运动理论的基础。
(一)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
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首次区分了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为“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的结论提供了科学基础。[7](166)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8](P197)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劳动力的彻底商品化。
劳动力彻底商品化的前提,是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即劳动者是同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是劳动者进行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就是小商品生产者不断被剥夺生产资料,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化的历史。“在出卖之前,劳动力是和生产资料,和它的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的。”[9](P37)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造就了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所谓的原始积累不过是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的历史过程。”[10](P46)
西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对劳动力彻底商品化的剖析有利于认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最重要的价值。“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抓住历史,就是因为它以一种真正资本主义关系的理想的、典型的内部组织形式科学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现实。”[11](P11)
(二)西方学者对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发展
以卡尔·波兰尼和迈克尔·A·莱博维奇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以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为参照系,结合更具体的资本主义现实条件,提出了劳动力去商品化或半商品化理论。
波兰尼强调,劳动力去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存续的条件,因为纯粹的商品化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崩溃。波兰尼的观点和马克思类似,都肯定了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但和马克思不同,波兰尼将劳动力商品与普通商品做了一个更为彻底的区分。波兰尼认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显然都不是商品;……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12](P62-63)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分析,波兰尼提出,“一方面,生产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即存在着高度的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由于福利国家和转移支付的存在,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劳动力‘去商品化’。”[13]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并不一定要建立在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前提下,或者即便丧失了生产资料,也不需要以市场作为获取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唯一途径。
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迈克尔·A·莱博维奇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做出了新解释。他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并没有完成彻底的商品化过程,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出于盈利的考虑,资本总是力图压低雇佣劳动者的工资以降低成本,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半商品化意味着雇佣劳动者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这使得工资水平低于劳动力价值成为可能,因此劳动力半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力是“自为存在的工人”(the worker as a being for self),资本面对的不是为了资本而存在的雇佣工人,而是为了自身存在的雇佣工人,[14](P99)雇佣劳动者的斗争和反抗推动了劳动力的“半商品化”。
此外,贝弗里·J·西尔弗本·法因等西方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劳动力半商品化的理论,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商品理论。
这些学者的共识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往往是多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混合,作为次要内容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提供了缓冲空间。
(三)中国学者运用劳动力商品理论分析农民工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农民工主要在私有经济部门就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商品理论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分析框架。[15]
在国内学界,有诸多学者联系中国农民工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劳动力半商品化(或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化”)的理论,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孟捷、李怡乐认为,劳动力商品化经历了不同阶段,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化与劳动力商品化的各种组合情况,并区分了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不同之处。他们认为:马克思所谈论的双重自由,可以看作直接生产者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条件,而非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条件。即便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即便还没有获得彻底的人身自由(比如迁徙的自由),仍然可以实现劳动力商品化,因为决定劳动力商品化的直接因素是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16]孟庆峰也持相同观点,“无产阶级化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半无产阶级化的阶级结构同样是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之一。”[17]潘毅结合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分析了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她认为:“阶级形成的第一步是阶级无产化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没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一个不完整的阶级主体。”[15]
三、中国农民工半商品化的矛盾
中国农民工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半商品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民工,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双重自由”。他们是劳动力的真正所有者,同时他们又是有土地的,土地和进城务工构成了农民工的双重收入来源。因此,农民工并非彻底的劳动力商品。其次,外出的农民工可以选择重新回到农村,再一次和自己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或选择就地就业,参与当地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工回流现象,正是劳动力半商品化状态实现分化的客观结果。
①②③ 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信息报》,2016年4月29日。
④ 参见《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人民政协报》,2014年3月8日。
(一)农民工半商品化的问题
从短期看,农民工的半商品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提高。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农民工劳动力成本相对廉价,由此形成的高积累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崛起。同时,与务农收入相比,打工收入增长更快,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 072元,比上年增加208 元,增长7.2%,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绝对收入增长较快,月均收入3 213元,比上年增加247 元,增长 8.3%①。
但从长期来看,农民工的半商品化则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农民工的半商品化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大关系的协调和平衡。在农民工半商品化条件下,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资本盈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由此造成的劳资关系失衡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资本积累和社会消费的比例失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职工月平均工资5 270元,而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仅为3 072元②。显然,与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相比较而言,农民工的收入远远不及城镇职工,这制约了作为消费主体的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由此加剧了社会消费能力相对于资本积累的迟滞性。不仅如此,在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农民工生活消费成本则不断提高,2015年农民工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为1 012元,用于居住的支出为475元,占其支出总额的46.9%③。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这进一步削减了社会消费能力的规模,生产过剩的程度自然更为严重。
其次,农民工的半商品化不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农民工半商品化的条件下,农民工基本上都流向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大多只需要简单熟练的重复劳动即可,对于劳动者的技术素质没有太大的要求,这就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要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关键在于人的因素。这要求农民工必须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掌握现代化的操作技术,具备较高的劳动技能等。在农民工半商品化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农民工所获得的工薪收入,是无法支付这些培训费用的,市场机制无法自发地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农民工的半商品化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农民工和一般的城市工人不同,他们没有享受到和城市普通工人一样的福利和待遇,加之其大多数从事的是简单重复劳动,并没有与技术相结合,很容易被资本所抛弃。这种状况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重了国家和社会的负担。目前,外出的农民工收入无法负担其全部的家庭生活开支,社会保障和保险依赖于土地,而一旦土地与农民工分离,则意味着这种保障难以实现,如果没有国家兜底,必然造成社会动荡。此外,农民工长期远离农业生产,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程度较高,农业收益又较少,谁来种田的问题突出。据调查显示,“目前平均每户农村家庭就有一位青壮年劳动力弃农务工,加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一些地方农地出现抛荒。”④长此以往,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农业粮食安全问题。
(二)农民工半商品化的深层根源
从20世纪90年代出现农民工向大中城市转移的“民工潮”现象,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的“民工荒”,以及大量农民工回流等现象,农民工问题伴随改革开放的始终。“民工潮”、“民工荒”和农民工回流等现象背后的支配力量,是中国市场化过程中资本积累在产业和空间上的特定配置方式。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雇佣劳动力的流动,是资本积累在产业和空间上实现特定配置的客观结果。马克思指出,“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8](P729)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同样遵循着资本积累的产业和空间配置的一般规律。中国农民工的形成与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特定模式的产物,这主要表现为资本积累的产业模式和空间模式。
农民工半商品化是资本在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迅速积累的产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发达国家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为资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积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要想变成现实,必须要有大量廉价的雇佣劳动者提供简单熟练劳动。中国农村的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正好符合这种需要,由此形成了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庞大民工潮。但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过剩不断加重,这些产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开始下降,其对农民工的需求增长也随之下降。不仅如此,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积累对简单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萎缩。这种变化导致农民工过剩问题开始逐渐显现,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过剩更为严重。因此,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变化,其背后的力量正是资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展开的积累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8](P738)
农民工半商品化,还是资本在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迅速积累的产物。改革开放首先在东南沿海等城市兴起,这里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产业集聚,产业链较为完整,因此形成显著的“外在经济”效应。[18]外在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更符合资本盈利和积累的条件,由此带动了大量农民工向这些地区流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本积累的产业和空间要求主导了劳动力从中西部等落后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四、解决中国农民工半商品化的方案
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再一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农民工是这个短板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不仅事关人民的利益福祉,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事关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农民工的半商品化状态无法长期维持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执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多年运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优势已不存在,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基础设施荒废、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农村中青年劳动力不足等问题突出。另外,在持续了多年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之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正在消失,劳资矛盾不断加剧和突出,突出表现为: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和产业配置主导下雇佣单位需要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即用人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等一些问题和矛盾凸显,回流就是劳资矛盾加剧下的一个集中体现。
继续维持农民工的半商品化状态,无法缓和上述矛盾,农民工的回流只是暂时将矛盾隐藏了起来。而且,随着回流规模的扩大,矛盾会愈发严重,对国家和农民本身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更会对当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维持农民工的半商品化状态,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长久之计。
(二)农民工的彻底商品化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失衡
有观点认为,使农民工与土地相分离,成为彻底的劳动力商品,是解决我国农民工半商品化的可行方案。在农民工彻底商品化的情况下,当地劳动力市场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空间,保证这些劳动者能够全部进入乡镇企业或者集体化的大农场,使劳动力商品与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或大农场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同时,由于这部分完全商品化的劳动力是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就必须保证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能在最大程度上归个人所有。除此之外,乡镇企业要保障劳动者享受该有的社会保障,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就地城镇化,成为当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从而解决农民工问题。
赞同此方案的学者认为,在劳动力彻底商品化的理想模式下,因为没有了城乡壁垒,可以避免户籍制度之下损害资源配置效率,抑制激励机制,形成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现象。[19](P389)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回流农民工全部成为彻底的劳动力商品涌入劳动力市场,这将是地方乡镇企业的极大负担,如若短期之内吸收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商品,而农民工本身又已经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这种情况则会出现大量的农村失业劳动力,那么回流就意味着失业,如此将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最不稳定的因素,造成失衡矛盾。因此,农民工的彻底商品化能否达到方案设计者的预期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资本积累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劳动需求。从目前的经济新常态阶段看,不仅资本积累的速度在放缓,而且还面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迫切压力,这对于吸纳农民工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将农民工彻底商品化有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失衡。
(三)依托集体经济实现对劳动力半商品化的超越
土地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得以发展的关键的生产资料,作为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工,以土地为纽带发展集体经济,是解决我国农民工半商品化问题的根本之道。
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中,“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8](P96)以土地为纽带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意味着农民工不仅可以凭借劳动者身份获得工资收入,而且还可以凭借所有者身份获得集体经济的分红收入。这种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农民工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会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面临失业和贫困;相反,技术进步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及产量的增长将惠及农民工,其生产生活条件和个人综合素质将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回流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障碍,在于如何改造“资本”的形式,以适应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从国有经济改革经验看,按照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本质属性来改造“资本”的形式,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要求的“国有资本”运营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在这方面,按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本质属性来改造“资本”的形式,建立针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农村集体资本运营模式,也一定是大有可为的探索之路。
华西村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走集体经济为主的混合型经济之路,实行“一村两制”;以及南街村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都是解决中国农民工半商品化的有效尝试,这些成功的发展模式将来自基层群众的首创与中央的顶层设计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既富有地方特色,又具有以点带面的示范性效应,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农民工半商品化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1] 张辉金,萧洪恩.农民工回流现象的深层思考[J]. 农村经济,2006,(8).
[2] RavensteinE.The Birth of the People and the Laws of Migration[J].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1976, (3).
[3]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 蔡万焕.论刘易斯拐点理论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3).
[5] 刘生龙. 中国跨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4).
[6] 金沙.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推拉模型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09,(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M].徐华,黄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3] 孟捷.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4).
[14] 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M].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5] 潘毅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6).
[16] 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3,(5).
[17] 孟庆峰.半无产阶级化、劳动力商品化与中国农民工[M].海派经济学,2011,(1).
[18] 刘光大.西方规模经济理论与应用评价[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1995,(2).
[19] Yang,Dennis Tao and Fang Ca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ural-Urban Divide[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责任编辑陈翔云]
APoliticalEconomicAnalysisofCommercializationofChineseMigrantWorkers
ZhouZhen,WangShengshe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migrant workers; labor goods; capital accumulation; collective economy
InDasKapital, the labor force becoming commodity is the premise of transformation of currency into capital, The theory of labor commodity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the analysis in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Based on Marx’s labor commodity, Bolanni, Leibovich and other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and analysed the commercial and semi commercial process of labor force. Analyzing the problem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e can see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semi-commercialization condition were adapted to the specific configuration of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the industry and space. The migrant workers problem is the external form of inner contradictions during this proces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we need not only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and spatial alloca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but also need to make system innovation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周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王生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