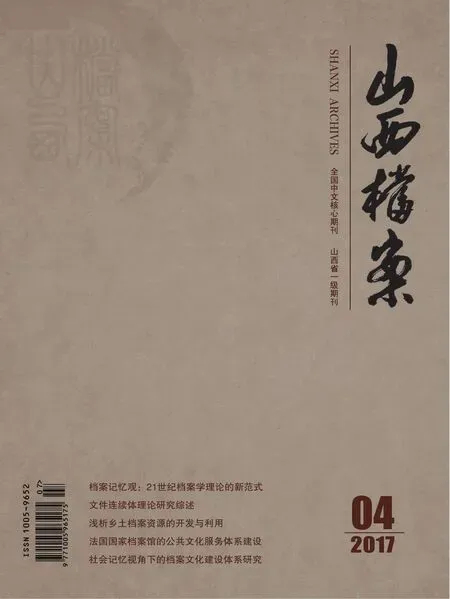社会记忆视角下的档案文化建设体系研究
文 / 马双双 吴建华
社会记忆视角下的档案文化建设体系研究
文 / 马双双 吴建华
档案文化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记忆观的兴起为我国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文章通过辨析记忆与文化、社会记忆与档案文化关系,总结出我国档案文化建设的社会性、客观性、多元性、系统性原则,分析档案文化建设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最终得出我国档案文化建设体系的基本内容,即档案记忆的构建、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档案文化的展示和传承。
社会记忆;档案文化;档案文化建设
社会记忆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20世纪末,社会记忆也进入了档案学界的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档案记忆观。对社会记忆观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有助于推动社会历史向着有利于人类持续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方向演进,这与档案文化的引导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意向殊途同归。社会记忆理论为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
一、记忆与文化
(一)记忆
记忆是个体过去所经历的事物在大脑中留下的痕迹。人的记忆无法直接观测,但能通过个体的外显行为加以研究。普通心理学将记忆定义为“经验的印留、保持和再在作用的过程”,而认知心理学将其定义为“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解码的过程”[1]43。记忆包括记和忆两个方面,“记”体现在识记和保持上,“忆”体现在再认和回忆上。记忆过程可划分为识记、保持、回忆(包括再认、再现)三个阶段。[2]45人类社会实践过程是记忆与遗忘的共存,记忆并不能存储人类主体的所有社会活动,然而档案具有原始记录作用,具有延伸人类记忆和拓展人脑记忆的功能。早在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曾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古文字档案专家布莱邦就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
(二)文化
不同学科赋予文化不同的定义。据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的统计,自从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做出明确的定义到1951年的八十年间,严格的文化定义就有164个之多。后来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尔新的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已达250多个。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人类文化创造领域和层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界定文化概念时的困难。[3]123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词义解析为:“(1)[culture]∶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仰韶文化。(2)[civilization]∶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中国文化。(3)[literacy]∶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4]1427显然,在档案文化建设体系中,文化对应的是第二层含义;文化是通过人类的创造所产生,文化的主体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可以是物质的财富,也可以是精神的财富,特指精神财富。
记忆与文化的关系具有一定渊源。德国著名的文化学学者杨·阿斯曼认为:回顾人类的过去,我们一直生活在充满记号的世界里,这个有记号的世界可称之为“文化”,甚至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记忆术”,因为它着眼于赋予精神的内心和中间世界以稳定性和持续性,取消其已逝性和生命的短暂性。[5]3-4文化学学者以及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对“记忆”的解读是,将记忆看成和文化、历史等概念紧密相连的范畴,因此选择一种唤起、建构、叙述、定位和规范记忆的文化阐释框架。这个文化框架就是所谓“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文化使记忆形态得以展示,同时,记忆建构文化。
二、社会记忆与档案文化
(一)社会记忆
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莫里斯·哈布瓦赫是最早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学者,并在此范畴上延伸出社会记忆的概念。孙德忠指出,社会记忆是指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创造性与依赖性、历史阶段性与活动连续性的统一。[6]24
社会记忆和社会变迁紧密相连,社会记忆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各种活动中留下的烙印。社会记忆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和认识活动,也具有记忆主体、记忆客体和记忆中介这三个基本的客观要素。记忆主体即人,记忆客体是记忆活动中特定的记忆对象,记忆中介一般指特定的记忆媒介,如图片、照片、物品、建筑遗物等。档案具备“记”和“忆”的统一性,既有真实的“记”,又有还原的“忆”。档案也属于记忆中介,因为它记载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是构建、了解、恢复及表达社会记忆的主要元素,具有重要的社会记忆功能。
(二)档案文化
我国档案文化的理论研究始于1989年。阿迪发表的《档案文化意识:理性的呼唤——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思考》一文,首次将“档案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此后,以文化的视角研究档案现象就成为学界、业界广泛关注的热点。[7]胡鸿杰将档案与文化的基本关系概括为“文化的档案和档案的文化”,即档案是社会组织出于自身管理活动的需要而形成的文化载体,档案的管理活动体现着管理活动的规则。[8]
档案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人类创造的文化,主要是由于其中蕴含并表现出的档案元素。档案元素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档案的实体、内容、观念、传统、经验、知识、管理、理论、技术等。档案文化一定要包含并体现出与档案有关的要素,这是档案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档案文化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一样,都是人类。档案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一部分,不应局限于档案事业或档案机构,而应该面向全人类全社会,看作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将档案文化定义为:档案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蕴含档案元素、延续人类文明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之和。
社会记忆属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形而上范畴,档案文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沉淀。因此,从社会记忆视角对档案文化的解读,能够感受档案文化真正的魅力,透视人类精神财富的深刻内涵。
三、档案文化建设的原则与意义
档案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进步和文化积累起着重要作用。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档案文化建设是指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运用档案元素构建能够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过程。
(一)档案文化建设的原则
档案文化建设原则是档案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是档案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规则。档案文化建设原则不是主观加上去的,而是对档案文化建设客观规律的揭示和概括,档案文化建设须以此为“准绳”。
第一,社会性原则。档案是不同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客观记录,具有社会性,档案文化建设要面向社会,鼓励受众参与,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客观性原则。档案具有真实性,在这一属性支配下我国档案文化建设要遵循选择公正、内容全面、尽可能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客观性原则。
第三,多元性原则。这主要体现在档案文化构建来源多样化,档案文化成果类型多样化,档案文化展示方式多样化等方面。
第四,系统性原则。这要求从资源、人员、技术、硬件、软件等多方面统筹考虑构建我国的档案文化建设体系。
(二)档案文化建设的意义
在新时期新的社会背景下,档案管理愈加受到重视。积极构建档案文化建设体系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理论价值。档案文化建设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档案文化研究基础理论,拓展我国档案文化建设研究的范围,为档案文化建设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拓展我国档案学的研究渠道和方法,丰富档案学基础理论;有助于反哺我国文化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
第二,实践意义。档案文化建设研究有助于档案行政管理活动做出对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正确决策;有助于对档案管理部门及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使档案管理行为符合档案工作的实际要求;有助于增强档案部门的凝聚力和团结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励职工干部为共同目标而积极努力工作;有助于提出科学的档案文化建设战略,不断推动档案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档案文化建设体系的基本内容
档案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以档案意识为核心,由档案意识指导下的行为方式和所形成的物化成果为组成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9]因此,我们可将档案文化建设体系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个层次:档案记忆的构建、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以及档案文化的展示与传承。
(一)档案记忆的构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的不断推进,在1996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档案记忆”成为不少主、辅报告论及的理论热点。据王德俊统计,在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10]经过近二十年的学术探讨,学界逐渐形成了档案学学科领域内的“档案记忆观”。2012年,冯惠玲将档案记忆观的基本观点初步归纳为:“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档案工作者的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对于集体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11]
社会记忆是人们存储、提取、选择社会实践经历的结果。它最后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形成了人们认同的共同记忆。在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中,各国档案学者的共识为“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知识的存储器,是知识咨询和转换的媒介,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12]档案记忆是以档案为主要表达形式的记忆。因此,档案记忆的建构也应该是一个选择、存储和提取的过程。
人类在历史活动的变迁中产生众多档案,档案的留取是人类记忆活动的澄显。弗朗西斯·布劳因指出:“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更糟糕的是它是有目的的记忆。”[13]选择是档案记忆构建的重要特征,档案记忆的选择要以能够传承档案文化和人类记忆为标准,这就需要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人员在进行传统的档案收集和鉴定等档案具体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精神文化层次要求。档案记忆的构建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档案活动过程。我们应鼓励不同层次的档案类型和种类收集进馆,扩大收集范围,紧跟时代脉搏,如将社会盛行的口述档案和各种记忆工程项目纳入收集范围;存储是一个静态概念,但是档案记忆的存储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信息化时代的技术革新对档案记忆的存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对传统的不同档案类型进行数字化,以及如何对档案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是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人员面临的新的课题和挑战;档案工作的提取性是通过档案的开发利用来实现的,社会记忆只有保证其能够有效传递,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记忆。[14]档案机构是被社会赋予了社会历史信息储存职能的机构,必然肩负着向社会传播知识信息的使命。所以,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是保证档案机构所储存的社会记忆成为有效社会记忆的重要环节。[15]此外,借助现代传播策略,有助于加快档案记忆的开发利用,宣传档案价值,发挥档案文化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功能。在实践中,档案记忆构建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城乡记忆工程、红色记忆资源的开发、企业记忆的提出等,具有多样性特征。
(二)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
记忆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被记忆,即作为记忆的客体或载体,包括人、事或物象,如图片、档案、物件、博物馆、仪式等,由这些可见的实体性符号来承载一段过去。[16]44随着社会意识和档案文化价值的提升,档案不仅仅只是一种 “组织资源”或者“管理要素”,而且成为一种表达文化方式和媒介的符号记录。[17]档案文化产品是档案文化的衍生品。档案文化产品是以档案文化为母体,通过文化艺术手段加工,再次生产演变为可供消费的产品,是与档案文化密不可分的关联产品。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是档案机构从社会公众需求角度出发,将库藏档案资源及其相关档案元素创造性地衍生出新的文化产品,改良原有产品,或开辟新的服务的工作。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正是对档案文化建设的一种符号表达。
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包含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主体、对象、方式、成果以及开发推广与营销五个方面。第一,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主体是档案机构。档案机构以公共服务为理念,以馆藏为基础,以公众需求为出发点,对馆藏档案进行深加工,生产大众喜闻乐见的档案文化产品。第二,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对象是档案资源。我国馆藏资源丰富,数量巨大,种类众多,题材丰富,覆盖面较广,特别是近年对民生档案资源的开发,使档案资源更加接地气,为开发多种多样的档案文化产品提供素材和灵感。第三,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方式为合作、授权、独立等。合作方式指档案馆馆际合作、与图书馆或者博物馆等其它公益文化机构的合作等方式;授权方式指档案文化产品开发走市场化渠道,将此业务授权给商业开发机构,寻求双方合作共赢;独立指档案机构运用自身特色馆藏开发有新意的档案文化产品。第四,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成果是带有档案元素的不同实体。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成果既可以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含有档案元素的应用品,也可以是用来装饰的艺术品,开发成果应不拘泥于形式,采用档案元素,展示不同成果。第五,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推广与营销指运用新技术和新媒体进行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档案机构要用积极开放的心态宣传档案文化产品,借鉴现代文化产品推广与营销的新手段、新方法,让档案文化产品融入人们的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典型案例,国内有江苏省档案局和扬子晚报社运用微博、微信、江苏档案信息网等多种宣传手段推出的合集《档案穿越》,国外有美国国家档案馆线上购物平台开发与展示的高质量馆藏商品。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凭借丰富的创意和先进的理念,成为文化产业的标杆。它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档案部门学习和借鉴。
(三)档案文化的展示与传承
档案文化形态需要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这就离不开档案文化的展示和传承。档案文化的展示就是将档案文化的物化形态公开展示给人们,包括实体展示和虚拟展示两种方式。档案文化的实体展示主要以传统的以纸质、照片等实体静态陈列来突显档案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价值,这是传统实践中应用较为普遍的方式。档案文化的虚拟展示指随着现代展示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展示艺术形式的不断创新,档案展览的陈列方式也得到拓展丰富,运用现代展示技术,清晰准确地呈现档案展览主题、诠释档案的历史底蕴和丰富内涵,引发观众探究档案的兴趣,拉近观众与档案的距离,达到宣传档案文化的目的。[18]目前,我国档案文化展示处在实物展示和虚拟展示交叉运用的阶段,而虚拟展示是未来档案文化展示的主要发展方向。
“记忆需要催生了记录行为,记录控制选择了档案方式,档案方式保存了历史标本——文化的历史时空系于档案传承”。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档案文化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这种历史地位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并通过凭证、传播、宣传、教育等多种作用方式表现出来。[19]档案记忆的传承机制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有意识传承与无意识传承的统一。档案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刻意制造的;第二,是储存、保护、开发与传承的统一。档案记忆传承涉及到档案形成与档案管理的全过程,包括档案形成、收集、鉴定、整理、保管、保护、开发利用等各环节;第三,是历时性传承与共时性传承的统一。档案记忆的历时性传承有三种方式或途径:档案自身(档案实体)的保存和延续;通过档案文献的编纂,使档案记忆以传统书籍文献的方式传承;通过编史修志,将档案记忆汇入历史典籍中加以延传。共时性传承可区分出两种方式或类型:同时代对共同生活记忆的传承;同代人对历史(场景、人物、事件等)记忆的传承。第四,是官方传承与民间传承的统一。与官方的强大控制力相比,民间传承是档案记忆传承的一种潜在力量。第五,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合互进。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就涉及档案记忆的传承,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依托并伴随档案记忆的传承,对文化遗产的宣传同时也促进了档案记忆的传承。
社会记忆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社会记忆对人类实践能力和经验认识的保存和传递,才使文化能够传承、传统得以延续、社会取得进步。[20]档案文化的展示与传承是档案文化建设的基本环节、特殊路径和重要方式。
档案文化建设体系中的三个基本内容是相辅相成、同向共进、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三个基本内容在档案文化建设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档案记忆的构建是重点,具有统领作用,能够引领档案文化产品开发的方向以及挖掘档案文化展示与传承的深度;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是基础,为档案文化建设提供基石;档案文化的展示与传承是途径和目的,为档案文化建设提供渠道;三者共同促进档案文化长时记忆建构观的不断发展。
[1]韩维生.设计与工程中的人因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
[2]马雅菊,蒙宗宏.心理学基础[M].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3][6]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徐海静.我国近二十年来档案文化研究成果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1(6).
[8]胡鸿杰.档案与文化[J].档案学通讯,2004(5).
[9]马仁杰,谢诗艺.档案文化的理论解读和建设探索[J].档案学研究,2013(2).
[10]丁华东.社会记忆与档案学研究的拓展[J].中国档案,2006(9).
[11]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
[12]中国城建档案代表团.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及其学术动向[J].城建档案,2004(5).
[13]弗朗西斯·布劳因,晓牧,李音.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J].中国档案,2001(9).
[14]尚东涛.社会记忆的技术向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6).
[15]尹雪梅,丁华东.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记忆建构探析[J].浙江档案,2009(5).
[16]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7]胡燕.普通公众档案利用行为对档案馆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6(6).
[18]王贞.现代展示技术在档案展览中的应用[J].中国档案,2015(7).
[19]谢诗艺.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研究[D].安徽大学,2014.
[20]何晓丽.文化传承的社会记忆探析[D].河南师范大学,2013.
G271
A
1005-9652(2017)04-0013-05
(责任编辑:虞志坚)
马双双(1989-),女,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吴建华(1964-),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企业档案管理、信息资源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