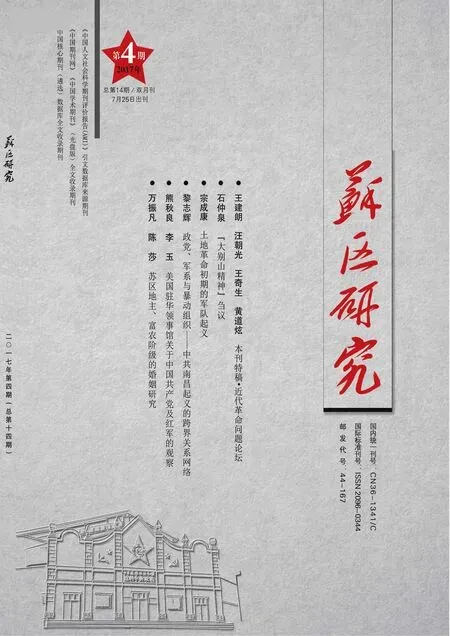从“泛阶级化”到“去阶级化”: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
王奇生
从“泛阶级化”到“去阶级化”: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
王奇生
五卅之后,各派政治势力与知识界对阶级概念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有过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在此过程中,中共的阶级话语宣传渐居强势。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的同时,也存在阶级概念被极度泛化的问题。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对阶级概念重新反思和检讨。近20年来,“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逐渐淡出中国政学两界的视野,呈现出“去阶级化”的趋势。如何从中国的阶级实情出发,对近现代乃至当代的阶级进行深入的实证的学理探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如相对非阶级的社会分化(如职业、种族、民族等),阶级分化的程度如何;相对非阶级的不平等,阶级导致的不平等有多显著;相对非阶级认同(如性别、地域、宗教等),阶级认同有多强烈;只有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与现实中的阶级实态,才不至于过分夸大或无视社会阶级的存在。
阶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瞿秋白;毛泽东
近百年来,在中国的政治与学术话语中,“阶级”无疑是一关键概念。这一概念自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后,直接运用于五四之后的革命与政治斗争实践中,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话语。文革结束以后,学术界对这一概念重新反思和检讨。近20年来,“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逐渐淡出中国政学两界的视野,甚至为国人所厌弃。本文试图结合中共革命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实践,就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过程,作一简要勾勒(难免挂一漏万),并对阶级分析的当代学术意义略述己见。
一
在西方,阶级的概念在工业革命早期即被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们广泛使用。而在中国,阶级的概念主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受到广泛关注。据瞿秋白观察:“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1926年1月29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页。确如瞿秋白所见,五卅之后,各派政治势力与知识界对阶级概念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有过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在此过程中,中共的阶级话语宣传渐居强势。而中共对阶级概念的解释和运用,虽其基本思想来源是马克思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在革命过程中又有所调整与修正,大体有这样几方面的特征:一是依贫富划分阶级,以阶级划分敌友;二是强调阶级之间的对抗与斗争,反对阶级之间的妥协调和;三是将革命视同为阶级斗争,以革命伦理、革命立场评断各阶级的政治属性;四是阶级概念的衍生,由阶级本体扩大到“阶级性”“阶级化”“阶级意识”“阶级代表”,而这些“阶级性”“阶级化”“阶级意识”与“阶级代表”经常脱离阶级本体而存在,甚至与阶级本体相错位。*如赵利栋在《“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一文中指出,将阶级意识当成与生产力没有联系的思想意识,把意识等同于阶级斗争,是五四前后阶级观念传播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6页)。这一特征显然也被中共延续下来。五是阶级概念的泛化,将一切不平等视为阶级的不平等,将一切斗争视为阶级斗争。如1925年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文中,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解释为阶级斗争,声称“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在)三方面的表现”:针对地主、资本家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是阶级斗争;全国人民反对军阀的民权主义是阶级斗争;全中国民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阶级斗争。*《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5年9月8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87-389页。这意味着在三个不同的层级上出现了三大不同阶级的对抗: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全国人民——军阀,全中国民众——外国资本主义。第一个层级是两个阶级对抗还说得通,第二、三个层级显然就不是阶级之间的对抗了。类似这样极度泛化、模糊、随意运用的阶级话语在中共早期十分常见。1926年1月,毛泽东撰写《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将中国农村民众按贫富划分为八种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者、游民,认为这八种人是八个阶级,且因经济地位各不相同,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相同。紧接着毛又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为“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分别刊载于《中国农民》1926年1月第1卷第1期第13-20页、1926年2月第1卷第2期第1-13页(原刊页码不连)。也就是说,不仅中国如此,任何国家都可划分出三等人和五个阶级。毛又分别从农村和都市找出对应的五个阶级,然后将五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划分为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革命的主力军等五种情形。当时中共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划分标准,大体是各自理解和各自表述。早期理论家之一的瞿秋白虽然指出马克思关于阶级分野的标准是根据生产机关的占有,而不是根据财产所有权,但他又强调,建立在阶级社会之上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带着阶级性,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阶级关系之上。*《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再答明致先生》(1926年3月17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574-575页。以此推演,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看作阶级关系。
中共“一大”即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下,几年之内,崇“无(产阶级)”贬“资(产阶级)”,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影响所及,国民党人亦不愿别人称他们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陈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第71期(1924年6月),见《向导汇刊》第2集,第568页。北伐时期,更有国民党左派青年欲与共产党争相代表无产阶级,声称:“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便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只知道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而不知道国民党同样是代表无产阶级。”*赞育:《孙文主义的进步性》,《现代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第57期(1927年3月17日)(原刊无页码、版次)。1927年,冯雪峰写了一首诗,诗名为《小资产阶级》,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急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语境。诗中描写他有一回和朋友喝酒时,戏称好友是小资产阶级。好友即刻满脸迸红,拍着桌子说:“你侮辱了我”,差点要动手打人。冯雪峰因此感慨说,“小资产阶级”这一名词近来很流行,我们无疑都是“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这名词是带着怎样可耻的毒刺呀。*《冯雪峰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可见“小资产阶级”这一称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即已经污名化,而知识分子从那时起即被中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那时的左翼知识青年也“听从”了这样一种安排,自我认定“小资产阶级”是他们的一种原罪。
在中共革命过程中,阶级话语表达与阶级斗争实践在不同时期虽有所不同,但一直是中共革命的核心问题。1957年毛泽东自我总结说,过去的三十几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毛泽东:《关于思想工作问题——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编:《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册,1967年8月出版,第96页。其实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据青年毛泽东的说法,他之所以选择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是因为“阶级斗争”学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可直接运用于实际革命事业中;其他主义学说,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正因为此,毛一直坚持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以及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而划分敌、友,并认为划分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辛亥革命的特质是种族革命(反满),中共革命的特质是阶级革命。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动员为目标,以扩大和激化社会矛盾为手段。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的动员策略,主要集中于“排满”宣传,专从满、汉的恶感方面鼓吹,煽动民族仇恨,激发民族感情,非常具有社会动员力。*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第93-99页。胡汉民后来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两条:一是策反新军,二是排满宣传。*《胡汉民先生自传》,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影印本,第237-238页。但刻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中共的革命擅长运用阶级斗争手段,从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到国共内战阶段的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均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大革命高潮时,中共领导下的工会会员290余万、农会会员900余万,还有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延伸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一个成立仅五六年的政党,在两三年间,能够发动如此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堪称一大奇迹。在一般社会学家看来,群众是一群缺乏同质性的“乌合之众”,要将其组织动员起来并加入到集体行动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亦因为此,中共依靠农民进行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一直成为中外学界反复探讨的问题。在众多的解读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有二:一是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农民因此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二是日本人的入侵,为中共在农村组织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黄金机会。但这两个因素也许可以解释延安时期,无法解释大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没有外敌入侵,土地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那么中共是如何将上千万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的呢?在笔者看来,阶级斗争无疑是中共早期工运、农运的动员利器。彭湃在海丰开展农民运动时,曾遇到一次“凶年减租”与“丰年减租”的选择困境。1923年夏秋之交,海丰恰遇水灾和风灾,农田完全失收,农民大起恐慌,要求农会趁机向地主挑战,实行减租运动。然而彭湃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何以凶年减租无价值,丰年减租才有意义?彭湃解释说:“减租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果然,则凶年减租虽可救死,而田主施惠、佃户感恩,有时反易没却阶级的意识,故无甚价值……反之,丰年减租,则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故有价值。”*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1923年11月7日),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119、124页。从农民切身利益来说,凶年减租最迫切、最需要,甚至生死攸关;而从党的阶级斗争目标而言,凶年减租没有价值,丰年减租才有意义。
对于“斗争性动员”的意义,中共早有认识:“因为农民团体若无受外敌之压迫,是易陷于松散,故农会之有敌人,诚为促进农民运动进步之好机会。”*《团粤区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1924年6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只有从斗争中出来的农民组织,格外有基础。”*《中央局报告》(1926年12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故中共反对“和平的农民运动理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全国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纲要》(1927年4月),载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5部(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家),大陆翻印本,时地不详,第72页。每次群众运动,中共都要首先确定斗争对象,使群众分化,争取多数,打击和孤立少数。一旦一方的声势压倒另一方,就迫使中立者必须站队,而不得犹疑徘徊于两者之间。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农民运动。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描述,狂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使那些中立观望者产生恐慌,担心被运动边缘化,甚至被裹胁成为斗争对象,而那些加入农会者自然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政治优越感和安全感。对中共而言,对农民册封这种政治优越身份,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中共正是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急速而有效地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这样一种“斗争性动员”模式,在此后直至文革的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中一直延续并发扬光大。*参见拙作《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3-94页。
中共革命成功后,至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仍然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总结说,三大改造完成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不久(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虽然承认大规模的狂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却仍强调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随后发动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毛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可以说,1949年之后,直到文革结束前,阶级斗争没有真正停止过。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革命就是阶级斗争,而革命是永无止境的,所以阶级斗争也是长期的。
阶级不同于族群,族群具有可确定性,阶级则具有可塑性、可变性和可建构性。由于认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普遍性存在,当旧的阶级敌人被镇压和消灭后,又不断建构新的阶级敌人,不断想象和寻找新生的阶级敌人。到文革时期,更推出以政治思想划阶级,以路线划阶级,以世界观划阶级,无论什么都扣上阶级斗争之名。*石谅:《批判林彪、“四人帮”按政治思想划阶级的谬论》,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1949-1979)》第3集(上),第323-328页,内部印刷,时间不详(推断为20世纪80年代初)。阶级概念被极度泛化,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二
大体上,在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国内有关阶级的纯学术性研究几乎是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曾编辑过一套《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1949-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1949-1979)》,3集共6册,内部印刷,时间不详(推断为20世纪80年代初)。,所收1976年以前的文章,几乎没有学理层面的阶级研究。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学界对阶级的学理探讨才逐渐展开。以中国史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研究为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颇为学界所关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即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主题。以此为标志,中国学界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一度兴味盎然;相继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分别就资产阶级的形成、来源、类别构成、组织状况、社会地位、思想意识、政治参与、经济活动、社会贡献等方面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论述,大体呈现出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去污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资产阶级”概念逐渐为学界所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职业性的“商人”概念。其实不限于“资产阶级”,近20年来,中国学界日益呈现“去阶级化”的趋势。对革命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泛化、滥化的反思与反弹,经过20年左右的过渡,多数学者几乎完全抛弃了阶级概念与阶级分析方法,呈现“去阶级化”的趋势。官方意识形态亦以和谐社会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学说。在此过程中,与中国史学界对“革命史范式”的告别潮流相一致,取而代之的“现代化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阶级理论。现实政治中,在“阶级”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等种种被视为负面性的东西,在“现代化”视角下成为中国人积极追求的目标。冯雪峰所感慨的带着可耻毒刺的“小资产阶级”名词,如今成为一个富有浪漫情调和品味意涵的概念。
这种趋势亦有西方学术潮流的影响。在西方学界,阶级分析传统不断受到后现代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批评家的诟病。他们认为,阶级概念在理解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不平等方面,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阶级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资本主义被认为是既存的唯一取得胜利的世界经济制度,阶级政治的重要性也随之发生逆转,“阶级的衰落”乃至“阶级的消亡”日益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主题。在概念上,西方主流研究者已不大使用“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一类名称,而用“精英”等概念来替代。
马克思提出阶级概念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历史理论,用以解释社会不平等、社会冲突、社会运动和政治过程,其理论核心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剥削产生利益对抗。马克思根据剥削定义的阶级概念,提出了对抗性利益如何形成继而阶级冲突如何产生的一整套解释机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流学界认为马克思原创的剥削概念是站不住脚的,认为这个理论依赖于早已被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摒弃的劳动价值理论。取而代之的新古典边际生产率理论认为,工人被付给与他对产品所做出的贡献相等的报酬;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够保证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不会多于也不会少于他对生产做出的贡献。*[美]埃里克·欧林·赖特主编,马磊、吴菲等译:《阶级分析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51页。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分析是理解长期性社会变革的关键;阶级关系尤其是阶级冲突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动力,对其动态变化进行研究是深刻理解历史运动的关键。而韦伯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作为席卷一切、压倒一切、贯彻一切的具有普适主义倾向的分析概念。韦伯将阶级仅仅视作社会中权力分配的一个方面。在韦伯看来,地位群体、政党,与阶级一样,都是社会中权力分配的主要现象,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甚至地位群体和政党比阶级更有可能完成这一角色,更能塑造个人的意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核心命题是激进平均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阻碍了物质资源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达成,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彻底克服这些阻碍。而韦伯则没有假设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冲突的主要来源,也不认为历史变迁的模式可以通过阶级之间关系的演进来解释。*[美]埃里克·欧林·赖特主编,马磊、吴菲等译:《阶级分析方法》,第36-37页。
在西方学界,阶级一直是一个富于争议的概念。一些人认为阶级在现代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而另一些人则坚持阶级仍然是体现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存在。当今中国学界对阶级概念与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已极为少见。虞和平的3卷本新著《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是个例外。在书的序言中,虞和平专门就“资产阶级”概念的运用问题进行了商榷。*《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包括《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3卷,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版。正如虞和平所言,国内学界对资产阶级概念的运用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资产阶级包括了资产阶级党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群体;而狭义的资产阶级则仅限于资产阶级本体——资本家或商人。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政治与学术话语中的“资产阶级”概念是广义的定义,甚至更偏向于指称“资产阶级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义的运用越来越少,狭义的研究越来越多。为了表达上的清晰起见,同时为了避免旧的阶级斗争观念与政治预设,一些研究资产阶级本体的学者转而采用了“资本家阶级”或“商人”的称谓,以代替“资产阶级”的称谓。大约2000年以后,使用“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称谓的日见减少,而使用“商人”称谓者逐渐增多。以商人概念取代资产阶级概念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是国共两党或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人所建构和想像出来的,概念范围太泛,内涵界限不清,意识形态色彩太浓,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是中国革命史观中的一个核心理论预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在近代中国,商人从来都不大称自己为“资产阶级”,而“商人”则是社会上的惯称,也是商人自己认同的一个概念。在虞和平看来,上述理由有一定的道理,有助于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近代商人或资产阶级,但他不同意以“商人”取代“资产阶级”作为唯一的概念。他主张将商人概念与资产阶级概念并存,将商人作为资产阶级的本体进行研究。虞和平认为中国近代商人即便没有达到自觉自为的资产阶级的标准,至少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群体即自在的资产阶级是客观存在的。“商人”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概念,进入近代之后它之所以被作为资产阶级本体的主要构成者,正是因为它发生了“资产阶级化”的变迁,逐渐由传统职业群体转变为新兴的阶级。在近代之前,商人作为一个职业概念,仅指从事商贸及相关之金钱、贩运等业者,不包括工业;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发展,商与工的关系渐趋密切,其界限逐渐淡化,商人的概念扩大为工、商两界的经营者。除此之外,商人的内在实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经营方式、经营规模、经营范围等也随之而变,逐渐采用股份制、公司制、银行制、经理制等资本主义商业企业制度。在虞和平看来,商人的这种近代化变迁,正是向资产阶级转型的过程,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化,是区别于传统商人的时代性所在。采用资产阶级概念,可以直接表示近代商人的这种时代性特征。虞和平承认以往使用资产阶级概念所进行的研究中,确实存有先入之见和政治预设,若注意避免和纠正先入之见与政治预设,并将资产阶级限定在狭义之内,则其概念与内涵并非不清。*虞和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第8-17页。虞和平还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存在“自为”和“自在”两种状态,引申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亦当存在“自为”和“自在”两种状态,认为这两种状态可衡量任何一个阶级的形成和成长程度,而衡量一个阶级从“自为”状态转变为“自在”状态的指标,一是看它的组织化程度如何,二是看它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的水平如何。*虞和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第230-233页。
笔者虽也是“去阶级化”大潮中的一员,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已很少运用阶级概念与阶级分析,但并不否认阶级在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的实际存在。近代中国并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阶级在近代中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不能视而不见,而必须从学理层面开展深入研究。无论当下还是未来,阶级研究与阶级分析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不能因为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国一度有过混乱与荒谬而影响今天对阶级进行严谨的学理探讨。当然要警惕过去阶级研究中存在的政治预设及阶级内涵不清等问题。从阶级的视角研究商人,与从职业的视角研究商人,两者不可完全替代。就狭义而言,资产阶级的本体是商人,但并非所有商人都是资产阶级。近代中国商人只有部分是新式工商业者,还有相当部分(甚至多数)是旧式商人。只有新式商人才能称作资产阶级的话,那么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对象必须有严格限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第1集中,附有1956年公私合营时的资产阶级统计,其总数为76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小商贩、小业主等,实际不能算作资产阶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第1集,第692页。这一统计数字没有说明具体出处,只说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根据公开和内部资料摘编。“资产阶级”只是“商人”中的一小部分,若是单一的“资产阶级”的视角,势必要将多数旧式小商贩小业主排除在外。反之,若是单一的“商人”视角,难免将新式和旧式商人一锅煮,不仅可能忽略两者之间的差异,还可能漠视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群体特征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以此观之,单一的“职业”视角与单一的“阶级”视角,各有优长,也各有其盲区。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国的阶级概念与阶级分析方法源自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是反资本主义的,主要关注阶级剥削与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且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冲突与斗争,强调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对阶级的任何理解必须放置于对经济生产和产品分配、消费及剥削过程的分析之中。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从早期现代化、市民社会等新的角度研究资产阶级,固然富有新意,实际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至少剥离了原有的阶级理论内核,甚至只余下“阶级”外壳。这种抽离了阶级内核的“阶级”术语还有多大的解释力也值得反思。比如,剥离了阶级内核的“资产阶级”与职业视野下的“商人”又有多大差别?相对于职业视野的商人研究,着眼于阶级视野的资产阶级分析的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阶级分析对历史解析与历史认知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三
在笔者看来,中国学界对资产阶级组织化程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而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的考察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中国学者大多着眼于资产阶级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参与,诸如参加清末立宪,投身辛亥革命,以及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平民主运动和抗日活动等,却很少关注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如资本家在应对工人阶级的反抗(如罢工等)时是如何集体行动的?在政府制定劳资关系与劳动立法时,资产阶级又是如何影响政府并讨价还价的?学者们多关注资产阶级的参政意识与政治文化素质,却恰恰对其阶级意识(相对于另一个对立的阶级而言)缺乏深入的实证考察。而这样一种阶级意识的考察,是最能证明资产阶级是否形成为一个“自为”阶级的。如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统计,1928-1932年间,仅上海市即发生劳资纠纷千余起,其中因资方主动停业、歇业、解雇所引发的纠纷占60%以上。*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5-6页。笔者曾探讨过国民政府时期的一起劳资纠纷。纠纷最初发生于1932年上海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民族资本企业,却最终激化为一场全上海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阵营的阶级对垒。在这场冲突中,两大阵营均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联合行动,双方均明确宣示各自的阶级立场,为各自阶级利益而战。资方参与交锋的厂商团体多达90余个,劳方参与交锋的工会亦达60多个,时间持续近两年之久,是民国时期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最大规模也最为激烈的一次阶级冲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194页。中国学界多关注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而对自发性的工人运动以及对资本家停业、歇业、解雇所引发的劳资纠纷甚少实证性研究。劳资关系是最核心的阶级关系,讨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认同时,漠视劳资关系显然是一大缺失。
由于长期受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影响,“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一直是一个负面性的称谓。故中国近代商人与资本家不愿以“资产阶级”自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客观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阶级被建构成为笼罩一切的概念,但不能因此矫枉过正而“去阶级化”。当然很多学者并非否认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存在,之所以放弃阶级概念的运用,乃认为外来概念在归纳上之合理性尚待实证,如果不能证明,那么就不如先用本土固有的称谓。尤其是在还没有论证之前就加以概念标签,然后按照这个概念标签的预设定义来理解论述主体的历史,这种研究方法有先入为主之嫌,而容易遮蔽许多史实。
在西方学界,除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之外,还有其他的阶级分析理论,如韦伯主义、涂尔干主义、托克维尔主义以及布迪厄的阶级分析等。这些西方的阶级理论可作为中国阶级研究的借鉴,但均不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作为中国阶级研究的方法视角乃至结论。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转型而出现的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现象日益突显,一些研究当代问题学者又重拾阶级概念与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经验现象。阶级分析在中国也许又有再兴的可能。笔者认为,如何从中国的阶级实情出发,对近代乃至当代市场经济下的阶级进行深入的实证的学理探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诸如宏观层面的阶级结构分析,微观层面的阶级位置对个人生活影响的考察,以及阶级关系、阶级利益、阶级形成、阶级划分、阶级意识、阶级文化、阶级冲突、阶级行动、阶级政治、阶级革命、阶级流动性等,均有深入探讨的空间。20世纪中国政治与学术话语的“阶级化”本身也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是,阶级概念与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必须严格限定,不可泛化,不可滥用,不可排斥其他概念的运用。并非一切不平等都是阶级不平等。相对非阶级的不平等,阶级导致的不平等有多显著?相对非阶级的社会分化(如职业、种族、民族等),阶级分化的程度如何?相对非阶级认同(如性别、地域、宗教等),阶级认同有多强烈?这些方面均可进行比较审视。只有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与现实中的阶级实态,不至于过分夸大或无视社会阶级的存在。
责任编辑:何友良
From "Generalized class" to "De class":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 Discourse in China
Wang Qisheng
After the May 30th movement,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and intellectuals had different views and arguments about class concept and its applicability in China.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CPC's propaganda of class discourse became stronger. While the CPC carried out the localization, embodiment and utility of the Marx doctrine in china, it also made the concept of class greatly generalize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academic circles reconsidered and reviewed the concept of clas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class" and "class struggle" discourse gradually fade out of the China'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showing the trend of "De class ". How to start from the class reality of China, to carry on the thorough and empirical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modern and even contemporary class, is an academic problem whic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omparing to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non-class (such as occupation, race, ethnicity, etc.), what is the degree of class differentiation? Comparing to the non-class inequalities, how significant is the inequality resulting from class? Comparing to non-class identities (such as gender, geography, religion, etc.), how strong is class identity?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only by properly grasping the actual state of class in history and reality can we not exaggerate or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lass.
class; class struggle; bourgeois class; Qu Qiubai; Mao Zedong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4.003
王奇生,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组织、动员与武装斗争:1925-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4JJD77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