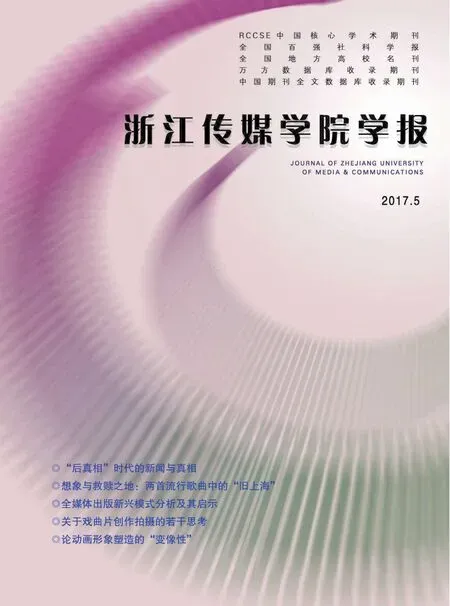“流水落花”二李词
刘晓珍
“流水落花”二李词
刘晓珍
“流水落花”是李煜、李清照词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意象,由于二人用笔的不同——李煜用笔大、健、放,而李清照用笔锁、柔、曲,造成二人词雄奇畅爽、阔大超逸与曲折婉转、微妙深细的不同审美境界。相似的“流水落花”意象上分别寄托着二人不同的思想与情感:扑面而来的落花与东流无尽的流水寄托着李煜无限的伤痛与悔恨,并进一步引发其人生皆苦、世事成空的哲理感悟,而李清照则借助一朵残花与一段流水自伤自怜、自叹流落。二人不同的身份、经历与思想是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
流水落花;李煜;李清照;笔法;寓情
“流水落花春去也”,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美丽又最苦痛的景象了吧,故而那些伤心人每每将其付诸笔端。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到“花自飘零水自流”,直到《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一段展衍,几千年的文学流变中始终能看到它们明晰而揪心的剪影,从而成为文学作品中最富于感情浓度的一类物象。而在唐宋词中,更是频频出现,尤其于李煜、李清照词中最为特出。细品二李词中之“流水落花”意象,又会有些颇为不同的审美感受。大体说来,李煜眼界开阔,气度非凡,将“流水落花”提炼为一种深具悲愁意味的载体,进行高度概括的书写;而李清照则琐碎细腻,情真意切,将“流水落花”的逝去与凋零点点滴滴咀嚼品尝,引领读者走进极度痛苦的情感世界。如果说李清照的“流水落花”寄寓了她的个人情感经历与家国情怀,那么李煜的“流水落花”大多已经超越家国,上升到了宇宙人生的高度,李煜的佛禅修为使得他的咏叹常“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
一、“流水落花”境不同
“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仿佛是站在具体时空之外,远距离观照这一人世间的整体场景,因而写得雄奇畅爽、阔大超逸;而李清照则是近距离地陪同在落花与流水的近傍,甚至身处小舟之上,目睹身边的“花自飘零水自流”,因而写得曲折婉转、微妙深细。
1.大笔与琐笔
李煜词常将“落花”置于无穷无极的浩渺时空之中,如其《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匆匆落花背后是无尽的朝风晚雨,滴滴珠泪背后是不绝的东流之水,更加衬托出此憾的沉痛之极。故而此词常被称誉“大笔”:
谭献《谭评词辨》卷二:前半阙濡染大笔。[2]
俞平伯《读词偶得》:结句转为大手笔,与“一江春水”意同,因此特沉着,后主之词,兼有阳刚阴柔之美。[2](104)
的确如此,结合论者所评,则上片之“朝来寒雨晚来风”与下片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皆为大手笔,境界极为阔大深沉。再如其《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无限江山”、“天上人间”等措辞,都极富感染力,将情感的发抒提升扩充到无限广大、无限深沉的境地。可谓极大之笔、极阔之境,寓至深之情。故李攀龙曾盛赞其结句“悲悼万状”[1](122),诚是的论。
而李清照则往往将时空锁定在庭院闺阁之内,将对“流水落花”的感叹具体落实在身边眼前。如其《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洒黄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如刘乃昌所云:“全词是用洗练、本色的语言,写出经过艺术加工的真实日常生活图景,以显示自己的内心情感。”[3]词中所写之时间非常具体:漫长的白昼,重阳节的半夜,黄昏时分。地点也非常具体:玉枕纱厨内,东篱傍边,帘内。这样就十分具体细致地写出了一位女子从早到晚、无所不在的孤独与悲伤。最精彩的是结拍将人与隔帘相望的黄花进行对比,衬托女子的消瘦形象,写得很微妙深细。再如其《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被春睡,梦远不成归。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挼残蕊,更捻馀香,更得些时。”同样写得具体细微。时间更加具体到一个夜晚,地点更加具体到卧房之内,尤其是人物动作更加具体到“更挼残蕊,更捻馀香”上。非常含蓄地将一个借酒解愁,深夜无眠,手拈残花,百无聊赖的深闺思妇形象展示出来。故而刘逸生叹曰:“事情有多么琐屑,而写来却多么细腻,表达的人物感情又何其曲折幽深,耐人寻味。”[3](151)
2.健笔与柔笔
同样是写落花与流水等偏向柔美的事物,李煜用笔每每雄健奇崛,骨干挺立,从而使其词作呈现出一种刚柔相济之美。如下面这首《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尘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遥殿影,空照秦淮。”
词中用语浑朴厚重,感染力极强。上片直接将“对景难排”之悲哀,“终日谁来”之孤寂倾吐而出。下片之写月华空照秦淮,“开”与“空照”等词汇皆警精劲健。故陈廷焯评曰:“凄恻之词而笔力精健,古今词人谁不低首。”[2](112)另一首《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同样笔力雄奇浑厚。故谭献谓其“雄奇幽怨,乃兼二难。后起稼轩,稍伧父矣。”[2](122)
而李清照在写流水与落花时,用笔相对柔婉清丽许多,如其名作《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评论者或谓其“香弱脆溜,自是正宗。”[3](51)或谓其“精秀特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3](53)柔婉秀丽乃是其最突出的特点。上片红藕、玉簟、罗裳、兰舟、锦书、雁字、西楼等词汇无不柔丽清雅,通过一系列活动含蓄地表达思妇对远人的思念。下片“一种”与“两处”相对,“眉头”与“心头”相对,非常巧妙地倾吐柔情离思,令人过目难忘。再如《清平乐》之“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诉衷情》之“更挼残蕊,更捻馀香,更得些时”,《菩萨蛮》之“风柔日薄春犹早……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等关涉落花之词,用笔皆轻柔清丽。
3.放笔与曲笔
李煜词有一种冲口而出的奔放感,同时又不失之于直白,“流水落花”类词作也不例外。俞平伯曾就李煜词的这种特点予以详细说明:
盖诗词之作,曲折似难而不难,惟直为难。直者何?奔放之谓也。直不难,奔放亦不难,难在于无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无尽之奔放,可谓难矣。……情一往而深,其春愁秋怨如之,其词笔复婉转哀伤,随其孤往,则谓千古之名句可,谓为绝代的才人亦可。凡后主一切词当作如是观,不但此阕耳,特于此发其凡耳。[2](119)
正如俞平伯所云,后主一切词当作如是观,不光其《虞美人》如此,其《望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亦如此。唐圭璋评价此词“一片神行,如骏马驰坂,无处可停。……此类小词,纯任性灵,无迹可寻,后人亦不能规摹其万一”,[2](101)可谓精当。
形成比照的是,李清照的“流水落花”词以婉曲之笔法与韵味取胜。如其《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词中写“一段新愁”,却自始至终不从正面说出,而是不断地延宕逗引,让读者猜想不断。正如沈际飞所评:“懒说出,妙。瘦为甚的,尤妙。‘千万遍’,痛甚。转转折折,忤合万状。”[3](93)其《临江仙》同样以意脉曲折取胜:“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玉瘦檀轻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又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这首照样可见女词人的善于用曲笔,如“为谁”之设问,“应是”之推测,“别到”之设想。正如周笃文的分析:“以‘应是’云云推测之词,加以摇曳,愈觉意折层深,令人回味不尽。”[3](147)王灼曾批评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4]虽是贬词,却恰说出了李清照词用笔的曲折、轻巧等特点。
二、“流水落花”寄不同
二李之词都曾被誉为善写悲愁,可谓字字血泪,流水落花类词作尤其如此。如唐圭璋评李煜《浪淘沙》词:“一片血泪模糊之词,惨淡已极。深更半夜的鹃啼,巫峡两岸的猿啸,怕没有这样哀吧!”[2](123)评李清照《武陵春》词:“通首血泪交织,令人不堪卒读。”[3](210)可以说二李在这方面是非常相似的。正因如此,唐圭璋谈到李煜时,就很自然地把他与李清照的情感与生活联系起来:
他的词说:“往事只堪哀(下略)。”“无言独上高楼(下略)。”可想见他孤独的悲哀,李易安所谓“寻寻觅觅,泠泠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生活,也正是他的写照。[2](112)
二人同样在词中借助流水、落花意象表达故国之思、身世之叹,同样善于今昔比照,凸显目前之悲苦孤寂,正所谓“伤心人固别有怀抱”[2](106)。然细品二人词中“流水”、“落花”,其中寄寓的情感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1.故国梦断与故乡何处
李煜词中“流水落花”寄寓的是他作为一代国君沦为阶下囚的亡国之悲,面对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只能以泪洗面、深自忏悔。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强烈感受到故国不再的深悲剧痛,满眼象征着逝去与消亡的“落花”成为触发他伤痛的主要媒介,日夜东流从不停歇的“流水”成为他满腹愁苦的最佳喻体:
清平乐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几首词极为相似,所谓“砌下落梅如雪乱”、“林花谢了春红”,均在突出一种触目皆是、扑面而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紧迫感与无力感。其写“落花”不是着眼于细部特写镜头,而是远距离全景式观照,增强了气势与力度。无边无际、满眼都是的落花恰恰折射出词人心境的苦痛与落寞的无可排解。“流水”也同样是大手笔,有奔涌而出不可阻挡之气势,正适合来表达他的无可排解的亡国之痛,故而陈廷焯评其《虞美人》为:“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2](117)唐圭璋也谓此词“此首感怀故国,悲愤已极……满腔恨血,喷薄而出,诚《天问》之遗也。……通首一气盘旋,曲折动荡,如怨如慕,如泣如诉。”[2](118)
这种整体关照写法李清照词中也有,如“风住尘香花已尽”、“风定落花深”等等,不过李清照词更多地是将镜头对准某一枝花作近距离关照,落花多是一枝一朵。试看下面这几首:
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
清平乐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
诉衷情
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被春睡,梦远不成归。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挼残蕊,更捻馀香,更得些时。
本研究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上腹部不适,其中观察组2例,对照组4例,其次是头痛、恶心呕吐和焦虑,对照组患者总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观察组(P<0.05)。见表2。
这几首词中均描画了一位斑白的鬓上斜插一朵梅花的思妇形象,花的形象是特定的这一朵,是鬓角的这一朵,是已经凋残、香消殆尽的这一朵,由此可见花与人的互相映衬作用。这思妇当年曾经“常插梅花醉”,而今只身“海角天涯”,故乡“梦远不成归”,夜半醒来只能百无聊赖地手揉残花,自怜自伤。由此可见:不同于李煜词中目睹落花之纷至沓来而引发无限凄苦,重在触景生情,李清照重在花人合一,以花喻人;不同于李煜“落花”之寓亡国深悲,李清照的“落花”意象更多的是表达对自我的怜惜、对故乡的眷恋、以及迟暮之年流寓异乡的孤寂之感。同样,李清照词中的“流水”也限定在自家门前:“唯有门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江楼楚馆,云闲水远。清昼永,凭栏翠帘低卷”,同样是在表达自怜自伤之意。
2.一梦浮生与物是人非
李煜“流水落花”词还特有一种对人生的自省与对宇宙的追问,呈现出博大深沉的哲理性的一面。如其《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滴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关于词中呈现之觉悟程度,俞陛云的解读颇中肯綮:“人当清夜自省,宜嗔痴渐泯,作者辗转起坐不平。虽知浮生若梦,而无彻底觉悟。惟有借陶然一醉,聊以忘忧。”[2](85)的确如此。从词中看,词人是在秋雨秋风的残夜无眠之时,发抒对人生世事的一种空幻感悟:万千世事皆随流水而逝,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梦一般。这种空尚属一般人所理解的“断灭空”,并非佛家当体即空的“第一义空”。正因对空等佛教教义的理解并不真切,故而其觉悟也不彻底。但即使如此,词中对宇宙人生的关照与思考已经使其区别于《花间词》的香艳与日常,别具一种高逸深沉的美。其《虞美人》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相见欢》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皆流露出人生皆苦、世事成空思想,颇有佛理意味。故而有王国维所谓“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33),唐圭璋所谓“气象开朗,堂庑特大,悲天悯人之怀,随处流露”[2](86)等评价。
相对来说,李清照的“流水落花”词则更多地是在表达流离失所后浓重的愁苦之情,哲理思索并不明显。她的“流水落花”词也常写到梦、写到空,但并无浮生若梦、往事成空的佛教哲理意蕴,如“梦远不成归”,“夜来清梦好”,都只是在写日常性的睡梦。试看其《好事近》:“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此词写落花,并未从雨横风狂写起,而是径直从“风定”起笔。蔡义江分析道:“只下一‘深’字,来表现花落的结果。寓动于静,静中有动。留下了多少想像馀地,让读者自由地去补足那刚刚过去的狂风无情、落红如雨的纷乱景象。”[3](189)词中处处精心营造落花时节的伤春氛围,重在表达极度伤痛之心情,并不进行哲理探寻。她写“玉尊空”,写“梦魂幽怨”,都是为了烘托极度伤春之情,空与梦都很具体日常,没有形而上意味。其《武陵春》也极为类似:“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词中也写“花已尽”之无可奈何,也写“双溪”水之载不动许多愁,但并未对落花流水进行理性关照;她虽强烈感受了“物是人非事事休”,却并未进一步上升到追问与思考的层面。
三、“流水落花”人不同
由上可见,相对于李清照“流水落花”词的工巧精细、婉曲动人,李煜的“流水落花”词境界阔大、笔力厚重。李煜词含蕴的情感更是由个人家国直通世间万法、宇宙人生,其肃穆深沉的哲理性也正是李清照所欠缺的。这当然与二人的身份、经历、思想等都有密切关系。
1.词帝与词女
李煜一向有“词帝”之称,这不仅关合他现实当中帝王的身份,更多指的是他在词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而李清照作为词坛上一位最出色的女词人,地位也是非常特殊的,大家熟知的有关赵明诚“词女之夫”的传说颇能说明问题。
在词坛上,二人皆备受推崇,并常常并称,如“男中李后主,女主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2](131)卓人月甚至戏称二人“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2](131)说明二人对词体的艺术特征把握都非常精准,写出了最具词性特征的作品。说来二李在精神气质上确有相通之处:二人皆具深情,皆具高超的艺术感悟力。二人虽身处不同时代,然际遇却也颇为相似,均承受了国破家亡的深悲剧痛。
但是二人毕竟有男与女、帝王与平民的身份区别与经历区别。虽然王国维曾盛赞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1](33),但与李清照词相比,还是显示出来一位男性尤其是帝王所特有的大视野、大手笔、畅达利落来,如前文所展示的其笔力的大、健、放上。虽然历来都不乏对李清照其人其词“脱尽闺阁气”、“有丈夫气”[4](471)的赞颂,然与李煜流水落花词对照后,不难发现李清照相对来说,还是更具细腻柔婉的女性气质,这突出表现在前文所分析的用笔的琐、柔、曲上。
从艺术修养上看,二人也有区别。通过李清照《词论》中对词体音乐性以及她词作本身的当行本色上可以推断,她音乐素养应该比较高。相对来说,李煜的艺术修养更加全面。史载其由于大周后之“善歌舞,尤工琵琶”而痴迷音律:“后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废政事。”[5](5588《南唐书》)又精通书法与绘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6]“所画林石、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7]词帝多方面的艺术修为,使其对美的感受、对素材的把握都高出常人,因而他的词作更加有一种出神入化、超凡脱俗、高度概括之美。正如谭献所言:“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4](108)
再从二人的身世经历来看,李煜作为一国之君,承受的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一向文弱的他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只是更加虔诚地求助于佛教。甚至在“长围既合,内外隔绝,城中之人,惶怖无死所”之时,也是在“幸净居室,听沙门德明、云真、义伦、崇节讲《楞严圆觉经》。”[5](5492-5493《南唐书》)面对一夜之间沦为囚徒的事实,他有的只是无力承受、无法开释的满腔悔恨,流于字里行间,便是一种如狂风骤雨般倾倒而下的愁苦。
而李清照所经历的则是一种渐变的、数十年的煎熬、伴随一生的伤痛。正如她在《金石录后序》中所写:“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矣!”[8]而她自儒道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当中接受了一种“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的滋养,使得她在遭际一切苦难之时,能较为理性地痛苦地咀嚼自己的痛苦,所以相对来说,显示出来一种较李煜更为内敛的特点。
2.莲峰居士与易安居士
李煜与李清照思想上的区别从二人的字号上即可看出:“莲峰居士”来自佛禅,而“易安居士”则来自“儒道兼综”的陶渊明。
李煜一生笃信佛禅,他曾说:“我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5](5020《钓矶立谈》)据禅典记载,他在做郑王时曾向法眼宗祖师文益禅师问法。即位后,又向其弟子泰钦文遂问法。[9]文益禅师圆寂后,后主亲自为他立碑颂德。[10]陆游《南唐书》卷三也谓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算。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5](5492-5493《南唐书》)李煜还经常书写经卷流通,籍此弘扬佛法。他曾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11]他在诗歌中也常常咏写对空门的向往与信仰。如《病起题山舍壁》中写道:“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悟无生。”[12]《悼诗》中写道: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12](72-73)《病中书事》中写道:病身坚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12](74)不同于诗歌中直接说理倾向,他词中佛禅意味的表达更具艺术性,更与抒情写景融合无间,如“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等等。故而王鹏运赞曰:“莲峰居士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芝兰空谷,未足比其芳华;笙鹤瑶天,讵能方兹清怨。……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4](109)
易安居士李清照思想上则是儒道兼综。从南渡前的作品来看,由于生活在北宋相对安定的时期,她思想上道家隐逸色彩比较明显,这可以从她对陶渊明的青睐上看出。退居青州后,她给居室起名曰“归来堂”,而自己起号曰:“易安居士”,二者均来自陶渊明。《金石录后序》中也真诚表达了她对青州闲居一段日子的心满意足:“甘心老是乡矣!”[8](178)前期词中最出色的词句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均可看到陶诗的深刻影响。南渡后,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状,她思想上儒家齐平思想更加突出,虽为一介女流,并不能真正参与治国平天下,但她积极地通过文字表达对国事的关注、对偷安享乐之辈的鄙弃:“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8](127)“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8](137-138)“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8](151)。从她这些愤激难平的诗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神传承。
由于李清照视词“别是一家”,她词中避免了上述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感的流露。她在“流水落花”词中将家国之情的表达向内转,化为一种极度愁苦的情思,如“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等,这种表达更增加了其词婉丽曲折的意味。
所以从思想上看,李煜信奉佛禅,由于其修养尚未达到佛禅的“圆融无碍”的最高境界,故其“流水落花”词中每每有一种“众生皆苦”、“浮生如梦”、“万事成空”的基本佛教意味;而李清照思想上儒道融合,词以抒情为主,思想表达不明显,故其“流水落花”词更多是在表达一种“孤苦无依”、“哀时伤逝”、“自叹流落”之情。
[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3.
[2]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3:103.
[3]陈祖美.李清照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3:59.
[4]孙克强.唐宋人词话[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457.
[5]傅璇琮等.五代史书汇编[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6]陶穀.清异录[M].四库全书本.
[7]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四库全书本.
[8]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2.
[9]道原.景德传灯录[M].大正藏本.
[10]赞宁.宋高僧传[M].大正藏本.
[11]王铚.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
[12]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72.
[责任编辑:詹小路]
刘晓珍,女,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I207.23
A
1008-6552(2017)05-01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