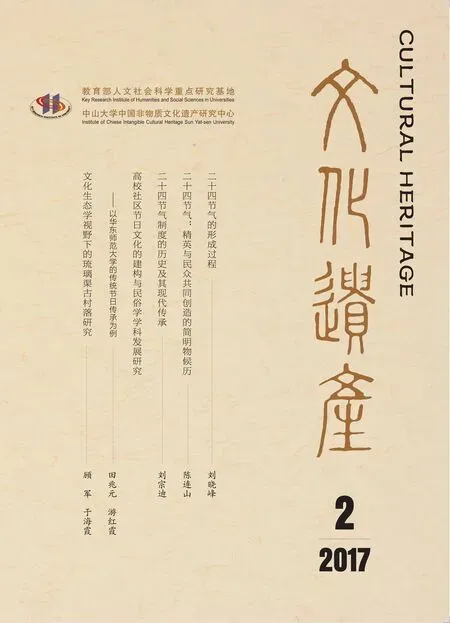尽唐卡画师的“本分”
——藏族勉萨派唐卡艺术大师勉冲·罗布斯达访谈录*
马 宁 采访整理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访谈录·
尽唐卡画师的“本分”
——藏族勉萨派唐卡艺术大师勉冲·罗布斯达访谈录*
马 宁 采访整理
勉冲·罗布斯达,男,藏族,1967年生,西藏日喀则拉孜县人,藏族唐卡艺术大师,西藏唐卡勉萨画派的代表性人物,现为西藏唐卡画院院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西藏唐卡博览会专家评审组成员。曾参与扎什伦布寺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灵塔殿、十世班禅大师灵塔殿的壁画绘制工作,负责色拉寺藏巴康赞、哲蚌寺乃琼查仓莲花生大师宫殿的壁画绘制工作,独立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红宫坛城殿珍贵壁画的修复与临摹工程,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贡献。长期钻研西藏传统艺术的研究,编撰有《罗布斯达唐卡作品精选》《藏族唐卡勉萨派传承人罗布斯达唐卡作品》《勉萨画派白描图》《藏族传统壁画绘制方法概述》《论勉萨画派的历史渊源》《勉萨画派概述》等代表性著作和文章。今年是罗布斯达从事唐卡艺术创作的第四十个年头,本刊特委托马宁博士对他进行专访,以飨读者。
马宁(以下简称“马”):罗布老师,您好!我受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文化遗产》杂志社的委托,想请您从学艺、实践和传播唐卡文化的角度来谈谈您从事唐卡艺术创作四十年来的心路历程。
罗布斯达(以下简称“罗”):好的,谢谢中山大学和《文化遗产》杂志社的老师们。
一、世家:祖父启蒙
藏传佛教格鲁派班禅活佛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该寺一直是后藏的文化中心,也是勉萨画派的发源地。罗布斯达出生在日喀则市拉孜县绒措村,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接触唐卡绘画,接受了最为传统的唐卡绘画训练,为他今后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基础。
马:听说您出生在唐卡画师世家,爷爷是您的启蒙老师,请您谈谈最初学习唐卡绘画的情况。
罗:我的家族勉冲·平康世代代都是画唐卡的,我爷爷名叫达瓦顿珠,当地人不叫他的名讳,直接称呼他为“拉日”*拉日,意思是受人尊敬的画师。,从我记事起,爷爷就一直在家里画唐卡。我们兄弟姐妹有五个,四个男的一个女的,我是家里的老大, 爷爷觉得我在画画方面有天分,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教我画唐卡。那时候村里有一个很不正规的小学,我8岁开始在小学里学习藏文,放学回家就看爷爷画唐卡,照着爷爷画的唐卡练习。学校不上课时,我就要放羊、干农活,只有到晚上休息时才能学习唐卡绘画。那时学习唐卡绘画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不想干繁重的体力活,因为我觉得干农活太累,放羊也没意思,而只要当了画师就不用干农活了,所以一心想跟着爷爷学习唐卡绘画。
马:您祖父传授唐卡艺术,一般要经历几个学习阶段?
罗:12岁时,我已经能够背诵《度量经》,就开始用最传统的方法学习唐卡绘画,第一阶段是学习制作绘画工具,先在一块高50厘米、宽40厘米、厚4厘米的木板上涂上湿锅底灰,再涂上酥油,然后用粗布包上白色的颜料“撒嘎”*白灰,一般用于涂抹藏式传统建筑的外墙。,通过抖动布包,让颜料均匀地落在涂有酥油的木板上,再找一支松木条,用小刀削出一个尖,做成一支“笔”。然后就开始画画,因为木板上有酥油,手碰到木板,酥油就会融化,所以手必须要悬空,绝对不能挨着木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既要练习绘画技巧,同时还要练习手腕的力量,达到胳膊不依靠支点就能长时间工作的目的。这一阶段的学习大约持续了两个多月。第二阶段是练习白描,用碳条在涂有白色颜料的木板上画画,这种特殊的碳条是用柳树枝烧制而成的,铅笔只有在给佛像比例打格子时才使用。我特别喜欢白描,但因为白天要帮家里干活,所以只能在晚上练习,一共练了两年半。第三阶段是学习着色和勾线,两者是同时进行的,着色的时候由爷爷先白描,然后让我上色,上色完了再由爷爷勾线和处理后续事宜,大约练了一年时间,爷爷觉得我已经基本掌握了着色技巧,才让我勾线。我跟爷爷学习唐卡绘画前后一共有6年多时间,到18岁就算完成了基本功的学习。
二、精进:大师亲授
对于年轻的唐卡画师来说,完成基本功阶段的学习只能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艺术殿堂的一扇窗户,要想使自己的唐卡作品登堂入室,就必须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进行练习。若机缘巧合,能获得参加大型绘画工程的宝贵机会、得遇名师的指点则能使绘画技艺在短期内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罗布斯达生逢其时,参加了扎什伦布寺班禅大师灵塔殿的壁画绘制工程,并以其精湛的绘画技艺得到了名师的垂青,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人脉关系,成就了自己。
马:听说您19岁就参与了扎什伦布寺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合葬灵塔殿的壁画绘制工程,当时您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工作情况。
罗:扎什伦布寺五世至九世班禅的灵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1987年十世班禅大师来西藏后着手建一座供奉五世至九世班禅灵骨的灵塔殿,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把日喀则地区18个县最优秀的木匠、铜匠、石匠、画匠都召集到了扎什伦布寺,老艺人们都带着自己的徒弟来参加这个工程,我也跟着爷爷去了,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能参加这样的工程,本身就是对唐卡画师绘画水平的肯定。我们从1987年开始画灵塔殿外面的彩绘,包括窗户、柱子。到年底时,4名高水平的老画师才开始进入大殿进行壁画的白描,我们这些在大殿外画彩绘的年轻人一有时间就进去观摩,中午吃点糌粑、喝点清茶,然后就赶紧爬到画壁画的木架上,看老师们是怎么画的。1988年4月初,白描完工后,老师们就在年轻画师里挑选水平比较高的人到壁画组进行上色,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紧张,因为大家都想做这项工作。其实在我们进行殿外彩绘工作时,老师们就通过对我们的观察来评判年轻人的水平,决定下一步谁能进去上色了。最后从90名画师中挑选了20多人进入大殿工作,我被选中了,感觉就像考上大学一样高兴,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噶钦·阿顿早期的徒弟,他们都在罗布林卡画过壁画,实践经验丰富,特别熟悉祥云、花朵的晕染技法,我们年轻画师都非常羡慕。因为画壁画和画唐卡不一样,晕染的方式也不一样,画唐卡是用特别细的笔一点一点晕染,而壁画是同时拿三、四支笔直接进行晕染,面积大,没有一定的技艺和功力是不行的,所以画壁画的难度比唐卡要大得多。为了弥补不足,我们几个年轻画师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中午休息和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在木板上练,向有经验的画师学习上色、晕染技巧,但是人家不给我们教,问问题,人家也不回答,我们只能在旁边看,下来后琢磨、练习、讨论,大家进步很快,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学会了。总的来说,当时所有的白描都是由4名老师来画的,画完之后让我们去上色,大家齐心协力,能勾线的勾线、能晕染的晕染,到1989年我们才完成了所有工作。
那时候我们学习唐卡绘画没有范本,只能利用到寺院的机会参观壁画和唐卡,自己揣摩,实地观摩名师作画的机会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不像现在互联网上什么都有,可以随时查阅。当时有90名画师在一起工作,他们各有各的画法和特点,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观摩学习的机会,就像上大学一样。当时对于和我一样的年轻画师来说,能参加这种大型工程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画的佛像本尊大威德金刚愤怒相等,绘画难度很高,但是老师们画出来特别漂亮,我们学起来很不容易。那时候学习条件很差,透明的纸很少,用普通的白纸放在画像上描画,但是透明度不够,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寺院里的清油刷在纸上,这样纸就透明了,然后就把最难画的佛像头部描出来,就像内地做的拓片一样。老师的白描画完了,我们就把纸放在上面,用铅笔描摹下来,拿回家晚上再练,这些纸张就成为我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马:听说您曾拜十世班禅大师的专职画师噶钦·洛桑平措和噶钦·阿顿为师,请谈谈您拜师的情况。
罗:我拜十世班禅大师的专职画师噶钦·洛桑平措和噶钦·阿顿为师是在扎什伦布寺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合葬灵塔殿的壁画绘制工程完工后的事情。当时噶钦·洛桑平措是壁画绘制工程的总负责人,噶钦·阿顿是扎什伦布寺的还俗僧人,但也是这个工程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噶钦·洛桑平措、噶钦·阿顿在年龄上比我爷爷年轻,但是他们见多识广,很有威望,所以我爷爷先找到噶钦·洛桑平措,说佛祖的旨意要让我再深入学习唐卡绘画技艺,希望能拜他为师,因为当时在灵塔殿绘制壁画时,我的基本功比较扎实,大师比较认可,就答应了。此后,我就一直跟随他学习,他夏天在日喀则,冬天就回拉萨,而我家在日喀则,于是当噶钦·洛桑平措冬天回拉萨后,我就在扎什伦布寺跟随噶钦·阿顿学习,主要学习勾线、晕染的方法,局部细节的处理等技巧。
马:您在跟两位大师学习的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罗:因为我在爷爷的教导下已经打好了唐卡绘画的基本功,所以拜噶钦·洛桑平措和噶钦·阿顿为师后,就不用再从白描开始学起,而是将学习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绘画技法,特别是勾线处理技巧上,点睛和白描是我们画唐卡时最重要的部分,点睛时的先后顺序、佛像和人物表情的处理,年龄悬殊的人物如何用线条来体现,唐卡中经书的特点如何表现等,两位大师都有自己秘不示人的绝技,我就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这些画龙点睛的细节上。
马:当时您拜师的时候有什么仪式?现在您收学生时还有仪式吗?您收徒有什么标准?
罗:我当时拜噶钦·洛桑平措和噶钦·阿顿为师时的仪式很简单,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的,爷爷带我去向噶钦·洛桑平措敬献哈达,送上青稞和酥油,就算拜师了。现在我收学生时的仪式也非常简单,学生一般会在家长的带领下给我献一条哈达,经济条件好一点的还会拿些水果,只有极少一些人会送红包,我的规矩是不收红包,只收哈达和食物。唐卡画师收学生是不要钱的,学生的吃住都由老师负担,还要给他们发一些零花钱,等学生出师后,如果仍然留在老师身边,老师就要给他支付工资,并且随着学生绘画水平的提高不断上涨。我不要求学生一定要有美术功底,只看他的文化程度,特别是藏文水平,通过3个月的学习来看学生有没有学习唐卡的天赋和悟性。在学制上不用学习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学生是否掌握了绘画技法,不强制规定白描必须要学习两年,着色必须要学习一年等,而是要看学生的悟性和成绩,有些悟性好的学生一年就能学会白描,悟性差一点的要两三年,也有学生学不会,主动退出的。
马:您参加了绘制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殿壁画的大型工程,有没有结识非常要好的画师朋友?
罗:当时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殿壁画绘制工程的时候,我们年轻画师之间的关系都很好。1993年,由噶钦·洛桑平措、噶钦·阿顿、格桑三位大师负责,在参加壁画绘制工程的唐卡画师中评选“乌琼”*乌琼,相当于现在的高级职称。,2名僧人、2名俗人,一共选了4人,还选出3名老师作为“乌钦”*乌钦,意思是大师。,然后将入选者报到日喀则地委行署和西藏自治区班禅大师灵塔修建办公室备案。在4名“乌琼”中,我和罗布是熟人,另外两名是扎什伦布寺的僧人,一个叫丹增,一个叫平措多杰,现在都已经还俗了。当时我被选为“乌琼”后,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在唐卡画师的传统中,“乌琼”的职位是很高的,是个人和家族的无上荣耀。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在给完工的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灵塔殿开光后,因为操劳过度圆寂了,所以又需要给十世班禅大师修建灵塔殿,外墙修了一年多,在这期间扎什伦布寺没有绘画的工作,我们又去其他地方绘制壁画,1992年末我们开始对十世班禅大师的灵塔殿进行绘画,一直持续到1994年才结束。在修建十世班禅灵塔的时候,白描、点睛大多都是由我们4个人完成的,我们商量后划分了区域,我和丹增负责东边,罗布和平措多杰负责西边,那时候干劲很大,工作再辛苦也不觉得累,我画的壁画主供的有极乐世界、米拉日巴、玛尔巴等,东边的点睛工作大都是由我完成的。在中间墙壁上主供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周围是十八罗汉,这些白描是以拓片的形式从噶钦·洛桑平措当年绘制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殿里描摹下来的,上色和点睛是由我完成的。佛祖、宗喀巴大师像是由噶钦·洛桑平措点睛的,左边的阿底峡大师像是由噶钦·阿顿点睛的,其余小佛像都是由我们4名“乌琼”来点睛,这个工程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大殿外面的彩绘和里面的壁画的水平都比当年修建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时有进步,绘画速度也比当年快。
马:您在老师带领下参加壁画绘制的工程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哪一次?
罗:1991年我进入十世班禅大师建立的日喀则刚坚公司工作,噶钦·阿顿老师是负责人,那年老师承接了萨迦寺壁画的绘制任务,带了包括我在内的20多名弟子参加。与扎什伦布寺相比,萨迦寺的壁画不是很多,大部分的白描都是老师指导我们完成的,老师亲自画的是主供的佛祖,高度在两米多。周边的十八罗汉大都是我白描的,对我而言,这比较简单。当时我们画八思巴殿的时候有点着急,因为1992年末就要开始画十世班禅大师的灵塔殿,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任务,一定要参加,所以我们就要在萨迦寺赶工,加班加点的画,还要保证壁画的质量,工作强度很大,这是我绘画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段时日。
三、历练:终成名家
通过传统的师徒相传成长起来的罗布斯达,并没有在小有名气后放松学习,而是勇敢舍弃一切、在得到贵人相助后进入西藏大学,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三年,接受了学院派的系统训练,这为罗布斯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其成为20世纪90年代西藏少有的同时接受过传统教育和现代大学教育的唐卡画师,布达拉宫坛城殿临摹工程的圆满完成更使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马:您第一次主持壁画绘制工程是什么时候?
罗:1994年我主持绘制了色拉寺的藏巴康赞大殿,藏巴康赞的僧人大多都是后藏来的,我也是后藏的,因为同乡关系,他们通过我的舅舅巴桑杰古联系到我,由我来负责这个工程,那年我24岁。我带了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画师,只带了一名徒弟,是我的表弟明琼,我们住在色拉寺里,主要画的是阿底峡大师的传记,那时身强力壮,整个白描都是我画的,其他人上色、勾线,大概用了一年时间。回想起来,早期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殿壁画绘制工程时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使我完全掌握了绘制壁画的流程,也具备了一定的统筹协调能力,所以才能够带领大家完成色拉寺的壁画工程。
马:听说1995年到1997年您专门去西藏大学学习了艺术史和藏学,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大学学习?
罗:我在色拉寺绘制壁画的时候认识了西藏大学的藏文老师嘉措,他以前是色拉寺的僧人,他没课的时候就会来色拉寺看我画壁画。有一天嘉措老师突然对我们说:“你们都年轻,绘画技术也特别好,但这些还不够,如果能去大学学习文化知识的话,以后一定会有大发展。”当时我就心动了,回到日喀则之后,就向刚坚公司请假三年,要去西藏大学学习。我当时是刚坚公司绘画组的负责人,公司不同意,我就辞职去拉萨找嘉措老师。他把自己在西藏大学上课时休息的房子借给我,我就开始了旁听生活,主要学习藏文化、藏族史,有时候也到艺术学院去听课,就这样过了三年,当时没有经济收入,家人和亲戚全部反对,认为我疯了,都不理睬我。我当时有两千多元积蓄,一日三餐就吃糌粑,嘉措老师有时会给我一些餐票,我就去学校餐厅改善下生活。我有一个叫曾智的朋友,是江孜的僧人,是我在色拉寺绘制壁画时认识的,因为当时色拉寺里有一个英语特别好的僧人叫增珠群培,我和曾智每天晚上都要跟增珠群培学英语,因为同学关系,我和曾智就成了好朋友。我在西藏大学学习时,他当时正好在色拉寺学习,经济上比较宽裕,每周六晚上他都会从色拉寺来西藏大学请我吃饭,和我讨论问题,有了他和嘉措老师的支持,我才顺利完成了这三年的学习任务。
马:您认为在西藏大学学习的这三年对您的人生影响大吗?
罗:如果没有在西藏大学旁听三年,那么现在我只是一个唐卡画师,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这三年对我综合素质的提升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现在学习唐卡绘画的众人中,大多数人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很少有人一边学画画一边还学习文化课的。嘉措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有文化,有远见,知道社会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他指点我,说唐卡传承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人才,只依靠技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习文化知识。我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才成就了自己。现在我在教学生时,不仅仅强调他们学习技法,还要求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为了给他们创造学习机会,我在2012年举办了“首届藏族唐卡传承人论坛会”,邀请区内外的专家学者来拉萨讲学,希望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化课的热情。
马:您觉得大学教育和学习唐卡绘画的这种师徒传授有什么区别?
罗:这两种学习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西藏大学唐卡专业学生的培养分为两个部分,绘画方面除了画唐卡,还要学习油画、水彩画等。文化课方面除了背诵《度量经》外,要学习藏族史、中国史、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等理论课程,知识比较系统,能够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学识,但因为绘画时间投入不够,学生的技法较弱。传统的唐卡授徒,就是练习画画技巧,背诵《度量经》,比较单纯。我个人觉得,仅就画唐卡而言,还是传统的培养方式比较好,学生付出的时间多,收获也大。
马:在您绘制唐卡的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是什么时间?
罗:我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那时国家要修复以前被破坏掉的寺庙,彩绘和壁画的工作特别多,工作量也特别大,除了扎什伦布寺以外,色拉寺、哲蚌寺、乃琼寺都请我去画过壁画,经过这些历练,我绘制壁画的经验更加丰富,技艺也日益精湛。2006年,一个叫格桑的商人请我到距离拉萨十多公里之外一个叫桑马场的尼姑寺去绘制壁画,他准备在大殿的地上贴瓷砖,墙面用水泥抹灰,我对他说:“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基础性的工作,为什么不做得更好呢,地面必须要用传统的打阿嘎方法制作,墙上要绘制壁画的话,最好还是用传统的土墙,如果你没有技术人员的话,我可以跟布达拉宫联系,那里有会抹灰的大师级工匠,我可以请他来。”格桑听从了我的建议,完全按照西藏的传统方式修建了尼姑寺,最后画出来的壁画效果特别好。那次我把15名学生全部都带了过去,吃住都在寺院里,能学习绘制壁画,孩子们都特别高兴。现在大多数寺院都已经修复完毕,实践机会特别少,唐卡画院的学生已经没有机会去学习壁画技法了。
马:您2005年的时候独自承担了布达拉宫坛城殿的临摹工作,请您给我们谈谈具体的工作过程。
罗: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于2002年6月26日正式开工,总投资为33330万元人民币,其中,布达拉宫维修工程投资17930万元,罗布林卡为6740万元、萨迦寺8660万元。布达拉宫的壁画维修工作是由敦煌研究院来做的,坛城殿里有一块比A4纸大一点的壁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掉了一块,墙的抹灰后来补上了,但是壁画就没有了。当时布达拉宫有一个叫丹增的僧人,出家前曾经是我的学生,很热爱绘画,敦煌研究院就请他去补缺失的壁画内容。坛城殿里的壁画内容特别详细,讲的都是佛教故事,他看了以后也不知道该补什么内容,于是就请我去看看,我看见图案下面有藏文解说,仔细研读后,发现周围的壁画讲的都是五世达赖喇嘛的故事,于是我回家就翻看五世达赖喇嘛的传记,认为缺失的壁画应该是五世达赖喇嘛本尊休息时所见的那些神圣事物。我就画了草图,觉得满意后,就去绘制壁画,再和弟子一起上色,达到了和周边的壁画完全对接的地步,一共用了4天时间。画完后,布达拉宫管理处的同志都来给我献哈达表示感谢,当时主持工作的强巴格桑处长说:“以前布达拉宫和敦煌研究院维修过2次的壁画现在还是脱落的比较厉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以前看过那些壁画,主要是展示龙树菩萨、途美大师等17位大成就者的功绩,还有一个单独的部分是阿底峡大师的传记,可以说是布达拉宫里的众多壁画中叙事内容最为庞杂的,就说:“那些壁画已经是文物了,不能再覆盖重画了,最好趁着壁画大部分都还在,请几名技术高超的画师,把壁画的内容画在唐卡上,遇到已经脱落的,就查阅再补充,这样以后就是那些壁画全部脱落了,也可以照着这个唐卡画。”当时强巴处长就觉得可行。大概15天之后,布达拉宫维修办公室打电话让我去一趟,强巴格桑处长说:“这段时间我们打听了全区的唐卡画师,觉得你来承担临摹、复原壁画的任务比较好,布达拉宫是我们藏民族的瑰宝,我们都有责任维护和保存它。”当时我有顾虑,壁画那么细,我一个人画工作量太大了,转念又想作为画师,我有责任去维护民族传统文化,就答应了。当时也有些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著名的藏族古建筑专家木雅·曲吉坚赞,他说“你这么年轻,这是我们西藏18世纪最顶尖的画家的作品,布达拉宫里的所有画家都画不了,你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还是以其他的方式保护或者临摹吧,用透明的纸盖住临摹的话最好。”我觉得如果壁画是完整的,那么临摹最好,并且一般的画师就能临摹,但问题是现在的壁画并不完整,所以无法临摹。我们争执了一番,最后决定用一天的时间让我临摹,作为考试,我就用一天的时间在画布上画出了一处内容比较清楚的壁画的局部,他们看了之后,一致认为我可以画,考试就算通过了。
坛城殿的壁画都是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时期绘制的,红宫本来是第悉桑杰嘉措修建的,那时本来是一个寝宫,后来七世达赖喇嘛把它变成佛堂,还亲自修建了三座坛城,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都是金身,建完坛城之后就组织拉萨和日喀则的顶尖画家来绘制壁画,内容是七世达赖喇嘛亲自设计的,他每天都来检查,画得不好的地方要现场擦掉重画,所以壁画的内容特别丰富,精细程度用巧夺天工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临摹壁画的时候,我还研读了七世达赖喇嘛的传记,想找到这些画家的名字、家乡这些信息,但是没有找到,只说是拉萨、日喀则的画师。为了复原残缺的壁画,我要不断查看周边的壁画,了解内容,还要查看经书,有时候一天一笔都画不了,所以难度特别大。
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布达拉宫是早上9点左右开门,下午5点左右关门,我刚开始画的时候,负责看殿的两名僧人跟我一起加班,我一直要画到6点左右。有一天,一个汉族画家在坛城殿里参观时,看到我一直在画,在我休息的时候就问我:“你一天这样画几个小时?”我说最少五六个小时。他说:“这样画时间太久了,这么精细的工作,会损害你的眼睛和身体,你画半个小时就应该出去活动一下,不然身体吃不消的。”我当时不以为然,就这样连续画了3个月,觉得身体发麻,去医院检查后才知道得了颈椎骨质增生和肩周炎,休息了一个多月后才有所好转,我想起汉族画家的话,就不再连续画画,每周一、周三、周五去布达拉宫画,周二、周四、周六休息。这项工作从2005年开始,一共用了8年的时间,冬天最冷的时候停工2个月,夏天要做政府安排的非遗展览工作时停工2个月,2014年画完了所有绘画,2015年补充了后续的文字。从2016年7月开始,这些唐卡在布达拉宫展出2个月,然后就要被布达拉宫永久收藏了。这项工作的完成,尽了自己作为唐卡画师的本分,也为我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四、传播:创办画院
进入21世纪后,面临鱼龙混杂的拉萨唐卡市场,罗布斯达不愿只做一名普通的唐卡画师,而是坚守传统,熬过唐卡行业的低潮期,并且以一己之力创办了“藏字头”的唐卡画院,积极与政府文化部门合作,为勉萨派打造出一个传播艺术的高层次平台,成为勉萨派兴盛的“中流砥柱”。
马:2000年的时候您成立了“堆觉百吉藏族美术室”,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工作室?
罗:之前我带的徒弟少,一般在家里画,后来徒弟人数越来越多,没有地方教。在药王山有个查拉鲁普寺,维修时请我去绘制壁画,我们关系比较好,正好寺院下面有个破房子,我就租借了这个房子,重新收拾后作为教学场所。后来我在八廓街修了座房子,开了间店铺,用于展览唐卡,顺便进行销售,为了方便就起了“堆觉百吉”*堆觉百吉,意思是生活富裕。这个名字,大概维持了四五年,这算是我创办的第一个企业。但是因为那时唐卡的价格不高,游客少,基本上没有汉族人请唐卡,我的唐卡主要还是销售给藏族人,所以收入不多,平时还要去寺院画壁画,才能支付房租,养活自己和学生。因为经济收入低,学习唐卡绘画的学生改行的很多,那是整个唐卡行业最低迷的时期。
马:2009年您已经创立了勉萨派唐卡艺术发展中心,为什么还要创办唐卡画院呢?
罗:2005年的时候,国家开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藏的唐卡绘画从区域上来讲分为昌都、拉萨、日喀则三部分,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业内一般用康吉、卫忒、藏吉来称呼,康吉是昌都绘画,卫忒是拉萨绘画,藏吉是后藏绘画,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要追根溯源,说清楚三代以上的师承关系,我进行研究后发现,藏吉可以追溯到勉萨画派,2009年我们就以勉萨画派的名字进行了申报。与勉唐画派、钦则画派和噶玛嘎孜三大画派相比,勉萨派是西藏最年轻的一个画派,创立于17世纪,已经传了十三代,与其他画派相比,以精细著称,特别注重佛像、山水风景、动物、服饰等内容的修饰,追古·曲英嘉措大师是勉萨派的代表性人物,曾担任四世班禅大师的专职画师,获得“乌钦”称号,他的绘画水平在整个后藏是最高的。曲英嘉措大师不是一个普通的唐卡画师,他精通佛教显宗、密宗,是一位有大成就的佛学大师。曲英嘉措大师不仅受四世班禅大师的器重,也深受五世达赖喇嘛的青睐,在扩建布达拉宫时,五世达赖喇嘛邀请他从日喀则到拉萨,绘制白宫里重要大殿的壁画,当时关于人类起源的壁画都是曲英嘉措大师画的,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因为曲英嘉措大师在创作时有在作品后面留诗的习惯,所以很好辨认。就我们勉冲·平康家族来说,我曾祖父土多是第一代,我爷爷达瓦顿珠是第二代,我舅舅巴桑杰古是第三代,我是第四代传人。因为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牵头单位,于是我就创办了勉萨派唐卡艺术发展中心,从那时起,国家和自治区的一些大型活动都会邀请我,2009年参加了在苏州举办的“吉祥哈达”西藏文化艺术展,2010年先后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巧夺天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名工艺美术大师技艺大展、在山东举办的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拉萨举办的首届“指尖神韵”勉萨派唐卡艺术作品展。2011年勉萨派唐卡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又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薪火相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并于当年举办了藏族唐卡(勉萨派)传承人罗布斯达个人唐卡作品展。经过两年的运营后,勉萨派唐卡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于是我又想搭建一个有利于推广西藏唐卡文化的更高平台,就开始筹建西藏唐卡画院,经过一年多的审批,2012年1月6号正式拿到批文,属于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当时注册资金是33万元,几乎耗尽了我的全部积蓄。
马:西藏唐卡画院成立之后,对您的事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西藏唐卡画院成立后,给我们搭建起了一个实体平台,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也有了可以集中展示作品的场所,能够让前来洽谈业务的人放心。我们就向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申请了项目,帮助文化厅组织唐卡艺术博览会,为画师的交流创造条件,不断有媒体、国内外参观团前来参观、学习,对提升唐卡画师的名气和社会地位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到区外参加展览,只要有唐卡类别的代表就会让唐卡画院参加。2012年,唐卡画院先后组织人员参加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浙江(义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我们带上一些唐卡的成品和半成品,在展览地现场作画,介绍和宣传唐卡文化,可以说确实很好地发挥了传播唐卡艺术的作用。现在,唐卡画院已经成为传承西藏唐卡艺术的重要民间力量。
马:听说您曾经参加了“百幅唐卡工程”,请给我们讲讲具体情况?
罗:为推动唐卡艺术的传承和创新,2012年5月,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实施“百幅唐卡工程”,我担任百幅唐卡艺术专家组的总监职务,当时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同志要我带头画一幅,我就去请教西藏美术家协会主席韩书立,韩老师说:“你就画一幅世界遗产吧,你天天去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的形状你也比较熟悉,就用唐卡的传统画法去画”。因为布达拉宫于1994年12月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大昭寺和罗布林卡也被包括进来,我就画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的草图,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又得到了韩书立老师的肯定,我就开始白描,之后又拿到药王山上色、勾线,大概用了三月时间,画成了这幅高1.8米、宽1.2米的大型唐卡《世界遗产》。我的弟子贡觉杰也画了一幅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唐卡。在所有唐卡中,我们唐卡画院的作品内容是比较传统的,同行的认可度也比较高。
马:您出过国吗?外国人了解唐卡艺术吗?
罗:我出国的次数很少,2012年第一次出国,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今日西藏当代画展”,当时是韩书立老师带队,一行5人,新加坡人信仰佛教的很多,我带了7幅唐卡,他们请了4幅。总的来说,现在唐卡在国内宣传力度很大,内地人都知道,但是美国除了专门从事唐卡研究的学者外,大多数人还是不了解唐卡,今年我去洛杉矶时带了4幅唐卡,美国人都不知道唐卡是什么,觉得太贵,没有人买。希望国家能够在这方面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唐卡艺术。
五、传承:坚守中创新
罗布斯达秉承唐卡绘画“以祖为师”的传统,并不只将唐卡绘画视为一门技艺,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承,按照最传统的方法来训练唐卡画院的学生,力求培养精通唐卡绘画及其附属技艺的全能性学生,因地制宜地申请了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到使优秀的唐卡作品传世的目的。
马:唐卡的颜料主要有哪些颜色?据说这些颜料是保证唐卡光泽度的关键,您认为市场上出现的新式颜料对传统颜料有冲击吗?
罗:唐卡的颜料比较复杂,有石矿类、土质类、植物类、宝石类、金属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矿物颜料,主要有朱砂、白珍珠、红珊瑚、黄丹、石青、石绿、玛瑙、绿松石、金、银、铜、黄蜜蜡等,主要的颜色有朱砂红、胭脂红、黄色、桔黄色、白色、蓝色、靛青、藏青色、二青、浅青色、深绿、头绿、金色等,其中,蓝色和绿色颜料单独有矿石,不用配色,其他颜色就要配色。使用天然矿石颜料是唐卡和壁画色彩鲜艳、经久不变的主要原因。现在市场上出现的新式颜料很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出现了一些用水粉在纸上画的唐卡,但是有职业道德的画师一般是不用这些颜料的。除了颜料以外,壁画墙面的处理也很重要,我们当年给扎什伦布寺十世班禅大师的灵塔殿绘制壁画时,颜料的质量是当时最好的,但是墙是水泥的,这些壁画现在开始褪色了,应该是矿物颜料与水泥发生化学反应的缘故。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大殿、四大天王殿都一百多年了,仍然色彩鲜亮。但是现在会这些传统技艺的艺人越来越少了,为了使这些技艺能够传承下去,西藏唐卡画院申报了一项名为壁画绘制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就包括墙壁处理技艺。
马:唐卡画师手中的画笔是非常重要的工具,请您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知识。
罗:画唐卡的画笔很讲究,点睛的笔,藏语叫“杰笔”*藏语“杰”是勾的意思。,晕染的笔叫做“秋笔”*藏语“秋”是涂的意思。,笔杆的材质主要有竹子、柏木、檀香木,还有一种是用草药做的,叫“杰巴”,是藏药里治疗眼疾的一种植物,它对眼睛里的血管有好处。一般用来上色的大笔,笔杆都是用竹子制成。画笔的毛用的最多的是山羊毛和马毛,马毛只用它颈部下面的那点毛,藏语叫做“察”,其他部位的不行,马毛和山羊毛一般做成大笔,上色和晕染时要用。勾线和点睛用的笔是猫毛做的,黑猫和白猫的毛都不能用,黑猫的毛太硬,白猫的毛太软,最好是选用红色和黄色的猫,用剪刀剪下毛后再一根一根挑选。这些挑选出来的毛再经过垛齐、裁剪、粘毛、削制笔杆、上杆等工序,才能做成一支画笔。我的笔都是自己做的,是小时候爷爷手把手教的。现在八廓街上出售唐卡的店铺有近百家,唐卡画师人数众多,但在那里基本上看不到我这种传统的画笔了。我认为,如果这种画笔制作技艺失传了,唐卡文化就会变得残缺不全,于是就将唐卡画笔制作技艺申报成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养了两个传承人,一个是40岁的米玛,一个是20多岁的达瓦,都是日喀则人,专门给唐卡画院制作画笔。制作画笔的毛不好找,必须要自己养猫,两个徒弟就在日喀则老家专门做这个工作,一支画笔的制作成本最少也要三四十元钱,这些画笔除了唐卡画院自己使用以外,也对外出售,因为是纯手工制作的缘故,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现在年轻人对唐卡文化不了解,都是用街上购买的一般画笔,这种笔可以画,但是毛质不好,点睛时就无法处理。为了宣传唐卡文化,今年我们专门加工了一批画笔,在西藏藏博会上以成本价出售,社会反响很好。此外,我还教学生们烧制白描时使用的炭笔。所以要当一名唐卡画师并不容易,必须要学会全套手艺。
马:请您给我们讲讲唐卡画布的处理方法。
罗:画唐卡时选用的是质地细密、厚度适中的纯棉布,将其固定在专用的木头框子上,框子尺寸最常见的为高100厘米、宽80厘米。将画布固定好后,用挑选的平滑石头打磨画布,然后用毛刷子将牛皮胶均匀地涂抹到唐卡上,然后阴干,等干透后再往画布上喷水,再用石头打磨,一共要反复打磨5次,画师用来打磨画布的石头都是老物件,一块石头可以传几代人。现在学生刚进唐卡画院,都要先从绑画布开始学起,学会后再练习打磨画布,掌握了这些基本功之后才能开始学习唐卡绘画。唐卡画布的处理要用到牛皮胶,这是唐卡和壁画能够传世的关键,日喀则老家的米玛和达瓦专门负责做胶,熬胶时牦牛皮的效果是最好的,一般不用新牛皮,而是用生活中使用过的老旧牛皮,比如牛皮船上的牛皮,现在这门技术也快失传了。虽然市场上的乳胶漆也能用,但是画成的唐卡容易掉色,存放的时间不长,对于画师来说,画一幅唐卡很不容易,如果因为胶水的缘故而使唐卡受损就太不划算了,所以我们就坚持使用传统的牛皮胶。一般使用铁锅或铜锅,加水文火熬制十多个小时,不能放其他东西,等清浊分离后,用勺子将清水一样的胶水舀出来,放在桶里晾,等快凝固时放入一个叫做“通边”的容器中分隔阴干,大约八九天以后,就会成为一块一块的固体胶,一张牛皮能熬十多斤胶。就我知道的情况,使用乳胶漆的唐卡只能保存十几年,而使用牛皮胶的唐卡如果没有进水等这些外部原因的话,能够永不褪色。像古格王朝、扎塘寺11世纪的那些壁画,没有进水的话能一直保持鲜艳的色泽。
马:西藏民族大学于乃昌先生曾说《画像度量经》《十搩手造像度量经》《造像度量经》约在13世纪萨迦王朝时期传到西藏,是藏族绘画和雕塑的依据和仪规,与《十搩手造像度量经疏》合称“三经一疏”,列为藏传佛教“工巧明”。您怎么看待《度量经》的重要性?
罗:对于唐卡画师来说,《度量经》是根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唐卡画师,必须要懂藏文,要背诵《度量经》,无论哪个画派,在培养学生时都是从教授《度量经》开始的。《度量经》是一部讲述绘画人物形象的理论著作,详细叙述了佛像、诸天金刚力士、各类世俗人物的形象塑造法。用诗体写成,分为三章,第一章“求画”叙述具有十智神通的赤降王囊扎计推从梵天那里闻习画理真传,广布人间的过程。第二章“供画”讲画像超然世俗、教化众生的作用。第三章“量度”介绍了佛陀、诸天及各类世俗人物形象身体各部位和器官的尺度、比例和量度方法。最基本的计量单位是:
微尘发尖虮与虱,以及青稞手指量。
上列依次为八倍,前物乘八后物长。
八个微尘排列起,等于一个发尖量。
八个发尖排列起,等于一个虮子量。
八个虮子排列起,等于一个虱子量。
八个虱子排列起,等于一粒青稞量。
八粒青稞排列起,等于一指宽度量。
在画转轮圣王时的规定是:“面部三分额、鼻、颚,每一部分四指量。整个面部宽几许,十四指宽是正常。面部上部和下部,各是十二指宽量。肉髻宽度为六指,长度则为四指量。头部横宽十二指,华盖为准来衡量。环绕头部尺度数,要用三十二指量。耳孔一般作半指,也有认为一指量。耳垂尺寸无一定,眉长要有四指量。转轮眉间的白毫,距离眉毛一指量。眉腰距离那发际,二指半宽是正当。眉头距离额中间,要用四指来衡量。眼的宽度是一指,眼长应为二指量。眼睛睁开为二指,两眼相距也同样。三分眼珠是瞳仁,眼长瞳仁三倍量。眼睛好似竹弓状,横宽则为青稞三。”*根据对罗布斯达的访谈内容和西藏民族大学文国根先生翻译的《画像量度经》整理而成。
因为《度量经》对人物的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佛、菩萨、护法神、本尊的画法、法器、色彩都有详细的规定,所以汉族学生如果不学藏文的话没有办法学习唐卡绘制技艺。
马:除了背诵《量度经》外,学习唐卡还有什么禁忌?
罗:要禁烟禁酒,唐卡画院对学生的第一要求就是“烟酒不沾”,这个规矩是历代唐卡画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方面跟宗教有关,就像去寺院拜佛必须要摘帽一样,在大殿里也不会看到抽烟的人;另一方面跟画师的身体情况有关,喝酒以后,对身体有影响,手也会发抖,肯定是没法画画的。
马:现在唐卡市场如何?唐卡画师的报酬和社会地位怎么样?
罗:最近这几年是唐卡市场最活跃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人们生活富裕,社会上请唐卡的人也很多,唐卡画师依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是没问题的。现在西藏,尤其是拉萨的唐卡画师非常多,一般画师的级别分为一级画师、二级画师、国家级传承人、省级传承人、一般画师等,各级别的画师报酬也不一样,一级画师的唐卡作品要卖到一万元以上。现在唐卡画院有西藏自治区一级画师3人,分别是贡觉杰、索朗、次仁,二级画师1人,名叫祖多,还有几名优秀的画师,一共有十来人,学生有二十多人。贡觉杰已经成长起来的,不光绘画水平高,理论水平也可以,今年他去青海民族大学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授课教师说他已经掌握了唐卡的历史和绘画技巧等知识,算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了。为了能够留下一些镇院之宝,现在我们画院已经不再出售优秀的作品了,而是把它们收藏起来,已经在一楼的展厅里展出了五十多幅唐卡。如果有人喜欢的话可以找我们预定,我们再重新画。我们画院有一幅画有释迦牟尼和藏传佛教各派创始人的大型唐卡,在2013年时有个上海的企业家出价250万要买,我们也没有卖。在我爷爷那个时代,本乡本土的人相互熟悉,就比较尊敬他。现在社会变了,城市里的人相互间都不认识,见了我们,最多人家会说:“你是唐卡画师,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不可能尊重我们。
马:您曾说过一副唐卡能不能传世有三个标准:第一要能让人感动,第二是能助人顿悟,第三是能教人行善,这个标准是您在学习中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老师教给您的?
罗:这是根据老师的教导和自己多年的积累琢磨出来的。唐卡的题材一般都是佛教的内容,我们画佛菩萨的时候有具体的要求,第一个是比例的要求,第二是色彩搭配上的要求,画师必须要严格按照要求去画,其他部分才能根据艺术的角度和画师的个人喜好去自由发挥,比如佛祖的画像都是用金色或黄色,不能画成白色,雪山、祥云、花鸟这些没有规定,画师就可以从艺术角度进行发挥。一幅佛像一般只能展现单纯的一种形象,或怒或喜。平时我们画佛祖都是佛祖的眼睛一直看到鼻尖,不能左右乱看。怒相从比例和形象上来说与慈相是完全不一样的,怒相的嘴巴是正的,眼睛也是正的,并且眼睛睁的比较大,怒相要呈现出让人震撼和给人一种敬畏的感觉。比如画一个人物的时候,当你把瞳孔画在眼睛中间时,不管观看者人在左边、右边还是中间,都会感觉唐卡上的人物在看着你,这种画法是可以表现出这种特点,但是当我们画一些侧面的怒相时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衡量一幅唐卡的优劣,方法其实很简单,要使不了解佛教的人看一眼就被深深打动,这是宗教上的要求。从艺术和市场的角度来说,如果唐卡画的不好,人们不喜欢,也没有人会购买。
马:现在唐卡画师的培养,您觉得还有那些方面需要改革?
罗:改革的话,还是不敢说的,我一直认为,就学习唐卡而言,还是传统的方式比较好。要创新也得先把传统的唐卡基础学好,能达到历史上唐卡创作最顶峰时期的水平,再谈创新也不迟,如果一味追求创新,就会破坏前人留下来的优良传统,给唐卡绘画的传承带来影响。我要求唐卡画院的学生学习时要按照传统方式盘腿坐,学习白描时也是在木板上练习,不在纸上画,画完之后洗一下板面就可以继续画了,白描学两三年一块木板就足够了,后面的人还能接着用,既节约,又绿色环保。如果在纸上练习白描要浪费很多纸,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把画有佛像的纸撕掉或者扔到垃圾里都是不敬的行为。
马:唐卡画院有女学生吗?您支持女性从事唐卡绘画吗?
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唐卡画师这一行男生多,女生偏少,我们画院有3个女学生,一个是23岁的仓噶,来自日喀则;一个叫25岁的尼珍,来自达孜县;还有一个叫杨真真的汉族学生,她是2012年从四川大学美术系毕业后过来的,学习了两年半藏文,然后开始学习画唐卡,现在已经毕业嫁人了。现在我女儿寒暑假时也来画院和其他学生们一起学习,以后是否从事这个行业要看她的选择。在我看来,女性学习唐卡绘制技艺,除了生育小孩时会耽误几年外,其他时间都可以画,从佛教的角度来说,画唐卡也是一件神圣的事,结婚后画唐卡,家人也不会反对。
马:听说您还抽出时间做科学研究,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罗:因为我在西藏大学当旁听生时,学习了论文写作这些课程,后来在梳理勉萨派历史时有一些心得,就写了一些藏文论文,在《西藏研究》(藏文版)上先后发表《藏族传统壁画绘制方法概述》(2009)、《勉萨派绘画源流考》(2012)、《藏族画笔制作技艺研究》(2015)等文章,在《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上发表了《勉萨画派创始人追古·曲英嘉措大师诞生地及其绘画艺术研究》(2015),还有一篇题为《谈唐卡艺术的传承与未来发展》的文章被《第二届中国唐卡艺术节高端论坛论文精选集》(2015)收录,主要对唐卡和壁画的绘制过程、各种仪式进行了论述。现在,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勉萨派的书,希望能够为西藏唐卡艺术的传承尽到自己作为一名唐卡画师的义务。
采访后记:罗布斯达老师是在布达拉宫完成坛城殿临摹壁画作品的讲解工作后,专门赶回西藏唐卡画院接受我采访的,原本计划采访一个小时,却聊了三个多小时,他那风温尔雅、谦谦君子的长者风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成长经历让人倍感振奋,虽然常年的绘画工作给他留下了一身病痛,但他却从不后悔,仍然身体力行,坚持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做创新,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恪守唐卡画师的本分,让我深刻理解了西藏唐卡艺术不断传承的生命力所在。“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罗布斯达老师能够从一名唐卡画师成长为西藏唐卡艺术的代言人绝非偶然,正是他四十年如一日的不断创作、攀登唐卡艺术高峰的远大理想、当断则断的果敢性格和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也为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责任编辑]陈志勇
马宁(1978-)男,羌族,甘肃省陇南人,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陕西 咸阳,712082)
*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号:NCET-13-0960)、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藏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项目号:12XMZ067)、2013年度西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项目“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构建”(项目号:2013ZJRW46)的阶段性成果。
G122
A
1674-0890(2017)02-0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