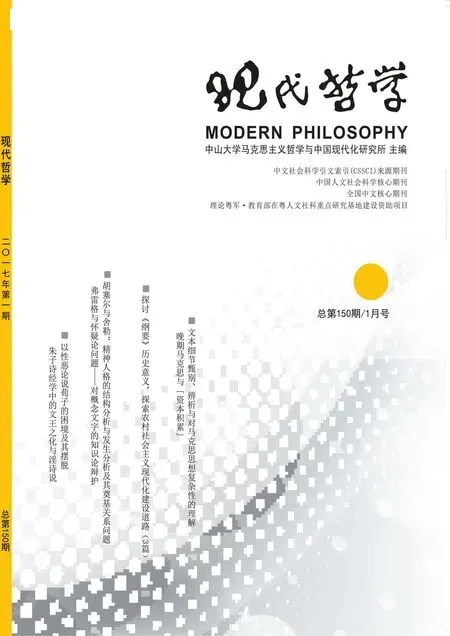以性恶论说荀子的困境及其摆脱
周炽成
以性恶论说荀子的困境及其摆脱
周炽成
表述于《荀子》一书的性恶论与荀子其人在人们心中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但是,该书并非全为他一人所写。前贤以性恶论说荀子,陷入重重困境,有人欲摆脱困境,结果又陷入新的困境。回到刘向编该书时把《性恶》夹在《子道》与《法行》之间本来的位置,不视之为一篇独立、完整的论说文,而以之为杂言杂语,这是摆脱这些困境的好方法。《性恶》不是荀子所作,而是其后学与人性有关的不同言论的汇集,它反映了后学对人性看法的分歧:有人以人性为恶,有人不以人性为恶。
《性恶》;荀子;荀子后学
以荀子为性恶论者,是一种悠久而强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形成的始因应该是《荀子·性恶》前半部分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反复申说。但是,该篇后半部分肯定“性质美”,肯定“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而且,《荀子》其他篇还有大量对性的论述,它们都无法用“恶”来概括。研究荀子人性论的人,如果只看那著名的一篇之前半部分的反复申说而不看别的,他们当然容易保持一致。但是,注意到“别的”,就会出现复杂的情形:有人明显打破一致性,有人暗中打破之,而陷入困境者难计其数。不断有人尝试摆脱困境,但是,我认为这些尝试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本文在回顾这些困境以及尝试摆脱困境的不成功努力之后,回到刘向编《荀子》时的指引,试图从《性恶》为荀子后学之杂言而非荀子本人所作之论说文的角度动摇那种悠久而强大的历史惯性,表明荀子不是性恶论者,而是性朴论者。
一、自相矛盾的困境
《性恶》在前面说了八九次“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后面又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质”和“具”难道不属于性吗?此质、此具难道是恶的吗?至于说“性质美”,那不是直接否定性恶了吗?完整读完《性恶》的人,只要有正常的理性头脑,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戴震在引用《性恶》的“涂之人可以为禹” “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等话之后,指出“此于性善之说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发明”*[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1页。。戴震这样说,当然意味着:既然极力主张人性恶的《性恶》说了那么多“发明”性善的话,它批评性善论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不过,戴震后面接着又说:“盖荀子之见,归重于学,而不知性之全体。其言出于尊圣人,出于重学崇礼义。首之以《劝学》篇,有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又曰:‘积善成德,神明自得,圣心循焉。’荀子之善言学如是。且所谓通于神明,参于天地者,又知礼义之极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在是。圣人复起,岂能易其言哉!而于礼义与性,卒视若阂隔不可通。以圣人异于常人,以礼义出于圣人之心,常人学然后能明礼义,若顺其性之自然,则生争夺;以礼义为制其性,去争夺者也,因性恶而加矫揉之功,使进于善,故贵礼义;苟顺其自然而无争夺,安用礼义为哉!又以礼义虽人皆可以知,可以能,圣人虽人之可积而致,然必由于学。弗学而能,乃属之性;学而后能,弗学虽可以而不能,不得属之性。此荀子立说之所以异于孟子也。”*[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32页。在这段话中,戴震又认为《性恶》前后不矛盾。关键点在于:在戴震的理解中,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不属于性。不学而能者,才属于性;学而后能,不学虽可以而不能者,不属于性。不过,既然戴震认为此质、此具不属于性,那么,他前面为什么说“此于性善之说……若相发明”呢?仔细分辨,不难看出戴震的困境:先说《性恶》有矛盾,后面又设法通过引入“学”的概念来消解矛盾。你认为他真的消解得了吗?
后于戴震一百多年,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之序中也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余谓性恶之说,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恶,必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在王先谦看来,荀子表面上是性恶者,实际上是性有善有恶论者。王先谦更准确的意思应该是:荀子在内心上是主张人性有善有恶的,但是,“世大乱,民胥泯棼”的现实激使他说人性恶。如果性恶之说非《性恶》的本意,如何解释该篇八九次反复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呢?王先谦以木有曲直来比喻性有善恶,这显然有悖《性恶》之旨,因为该篇非常明确地主张性之恶正如木之曲一样。本篇以曲木比喻恶之人性,绝不认为人之性有善有恶,正如木有直曲一样。木确实有曲有直,但那里文本明说天生之人性恶,一如木之曲。曲木之喻,只是性恶之喻,而不是性有善有恶之喻。鲜明、反复地说的话(“人之性恶”),不反映作者的本意,有这种可能吗?
后于王先谦几十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也陷入类似的自相矛盾:“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15页。王先谦认为“本意上”主张性有善有恶的荀子激于现实之恶而说性恶,与之相比,胡适则以《性恶》文本上的一些话来说明他的奇怪看法。胡适指出:“孟子又以为人性含有‘良知良能’,故说性善。荀子又不认此说。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此即吾所谓‘可能性’),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故说: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为‘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例如‘目可以见,耳可以听’。但是‘可以见’未必就能见得‘明’,‘可以听’未必就能听得‘聪’。这都是驳孟子‘良知良能’之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前揭书,第214—215页。紧接此话的就是前面引用过的“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胡适将《性恶》原文中的“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简化为“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简化的结果当然就是对原文的曲解。原文说的知与能有明确的对象:仁义法正。这种对象是善的,而不是恶的。原文说的当然是可以知善之质、可以能善之具,而绝不是可以知善或知恶之质、可以能善或能恶之具。但是,从胡适的上下文来看,他只有解释成“可以知善或知恶之质,可以能善或能恶之具”,才能合逻辑地得出“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的结论。非常注重逻辑方法的胡适,说出了“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并且为本话的后半部分找“证据”而不惜曲解《性恶》原文。
对胡适曾有尖锐批评的徐复观在说荀子人性论时事实上也有类似于胡的困境。徐复观认为荀子的性含两方面的内容,即官能的欲望与官能的能力,恶只是对前者来说的,而后者则是无善无恶的。从前一方面看,荀子是性恶论者;从后一方面看,他是无善无恶论者。徐复观说:“从荀子所界定的人性的内容……实与告子为近……荀子发挥了‘食色,性也’这一方面的意义,更补充了‘目明而耳聪’的另一方面的意义,这自然比告子更为周密。但正因为更周密,便更应当得出‘性无分于善恶’的结论。因为食色不可谓之善,也不可谓之恶;而‘耳聪而目明’,更不可谓之恶……荀子也是主张性无定向的。既无定向,即不应称之为恶。”“他是从官能的欲望,与官能的能力两方面来理解人性,却仅从官能欲望方面来说性恶,而未尝从官能的能力方面来说性恶。所以他的性恶论,对于他自己而言,不是很周衍的判断。”*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06、225页。《荀子》中的性含官能的能力,这是很多人忽视的,徐复观注意到了这一方面,这显示了他的慧眼独识。不过,这也使他陷入更深的困境。徐复观使两个荀子的分裂更为严重:主张性恶的荀子与主张性无善无恶的荀子。
与徐复观的说法类似,廖名春认为荀子的性是二元的,“是由恶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知能之性构成的。荀子的‘人之性恶’指的是情欲之性这一特殊,而并非具有一般意义。作为涵盖情欲知能的荀子所谓性概念,它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内涵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是与‘伪’相对的‘本始材朴’,指的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页。。廖名春所说的情欲之性与知能之性,分别就是徐复观所说的官能的欲望与官能的能力。在廖所说的荀子之性的二元结构中,一元恶,另一元无善无恶(或者说非恶)。与徐复观说荀子的性恶论不是“很周衍的判断”相似,廖名春说:“所谓‘人之性恶’,这一判断的主词是不周延的,所有的人生来就具有恶性,但这种恶性只是人性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所有方面。也就是说,性恶只是人性的内涵之一,而不是人性的所有内涵……荀子在强调性恶的同时,他还承认并且一再肯定过人性中还有非恶的一面存在。”*廖名春:《〈荀子〉新探》,第75—77页。廖名春引用了我们一开始就说到的《性恶》后半部分的一些话和《解蔽》的“凡以知,人之性也”、《礼论》的“性者,本始材朴”等来表明人性中非恶的一面。廖名春有时用“无善无恶”来说那一面,但更多的时候是用“非恶”来说它。在徐复观那里存在的两个荀子分裂的问题,在廖名春那里当然同样存在。
对荀子人性论之最具困境的话,是由李经元在近30年前说出的:“荀子强调性恶的观点是尽人皆知的……但就其所论,则不能不指出,尽管他一再力图证明人的本性是恶的, 善是人为的,然而在事实上却是把善和恶都当作人性里面本来就有的。荀子这种前后不一的矛盾,表明他只是注重性恶的一面,但很难说他就是性恶论。说的再明白一点,与其说他是性恶论,莫如说他是人性有善有恶的二重论,更为贴切。这个结语,也许不合荀子的本意,但也绝非没有根据……荀子在这里所说的普通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并非后天人为的……是人性里面本来就有的。由此可见,在荀子的思想中,善和恶实际上是作为人的二重性而存在的。”*李经元:《荀子的人学思想》,《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第58—60页。李经元明确指出荀子有“前后不一的矛盾”。不过,经过他的解释,荀子就应该是性有善有恶论者,而不应该是性恶论者了。自己指责别人前后矛盾,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指责者自身不应该前后矛盾。遗憾的是,李经元在这里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他一方面不否定传统的说法(荀子是性恶论者),另一方面又想否定这种说法;一方面认为以荀子为性有善有恶论者“也许不合荀子的本意”,另一方面又极力表明荀子的本意是人性中有善恶的“二重性”;一方面承认荀子“只是注重性恶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承认荀子主张人性中有恶和善的两面。我不想过多地指责李经元,因为他的困境事实上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说荀子人性论之困境的延续。
二、摆脱困境的不成功的尝试
只看《荀子》一书中《性恶》的前半部分,很容易得出结论:其人性论是简单明了的性恶论。但是,一看该篇后半部分和其他篇对性的论述,就肯定不会感到那么简单明了。上文所讨论的多个论者,他们都对该书的人性论有较为全面的视野,但由于把《荀子》其书与荀子其人等同,以为该书所有对人性的论述都是荀子一人作出来的,结果陷入了矛盾的困境:性恶论与性善论矛盾的困境或性恶论与性有善有恶论的矛盾的困境。戴震陷入的是前一种困境,王先谦、胡适、徐复观、李经元陷入的是后一种困境。陷入这两种困境的论者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难以一一列举。
我们也能看到,在前人研究荀子人性论的过程中,有人尝试摆脱困境。这些尝试给人以启发,但应该是不成功的。下面主要谈三种尝试: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之分的尝试、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性区分的尝试、性恶与心善并举的尝试。
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之分的尝试可以日本学者兒玉六郎为代表。他敏锐地注意到《荀子·礼论》中的“性者,本始材朴”的深意,以之为荀子对人性看法的关键,并在此指引下解读《性恶》,得出了该篇事实上主张性朴的结论。他的思路很独特:《性恶》不以先天之性为恶,而以之为不善不恶之朴,恶是对于后天之性说的。六郎指出:“荀况注意到好利、疾恶、好色等先天欲情的自身存在并不直接决定恶。但是,这些欲情的肆意放任(“顺是”)则尊致了犯文乱理之暴的恶的结果……此处论述显然乃是结果论,论述了后天性的恶……好恶喜怒哀乐即所谓天情,其自身正是‘性’,而性乃无所谓善、恶……以好利、疾恶、好色之情欲等存在作为《性恶》篇开头一段论述先天性恶论的根据,并不恰当……肆意放任性情的结果,造就了桀跖、小人等恶,这也是后天性恶的论调非其他……先天性恶、先天性善二说若皆不见于荀况思想,那么,先天性相关的论述则只能见于《礼论》篇中‘性者,本始材也’的先天性朴。因此,只能将荀况性论理解为由先天性朴发展出分为二歧的结果:即以枸木、钝金等比喻的后天性恶论与以直木、锐金等比喻的后天性善论……素朴之性,在其心(天君)与才能(天养)修为的结果作用之下,产生出文理隆盛之善性——或可称之为职业特性之矫性。此处的伪既然生于性,性之善、恶自然就一定是伪。《性恶》篇开头所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中之伪就是此处所云善的后天性、矫性。”*[日]兒玉六郎:《论荀子性朴说——从性伪之分考察》,刁小龙译,《国学学刊》2011年第3期,第94—105页。兒玉六郎区分两种性:先天之性(先天性)与后天之性(后天性)。他认为《性恶》并不主张先天之性恶,而只是主张后天之性恶。先天之性是无善恶可言之朴,后天之性才可言善恶。在兒玉六郎的解释中,后天之性的概念很重要,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具体的解释。先秦语境中的性与习相对,亦即先天与后天相对。按性伪之分的逻辑,先天为性,后天为伪。在这种逻辑之下,六郎所说的后天之性,事实上就是伪。依照六郎的解释,结论必然是:只有伪恶,而没有性恶。这种解释,很难面对《性恶》说了八九次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以性朴解释《性恶》,体现了六郎的良苦用心。他千方百计地协调《礼论》的“性者,本始材朴”与《性恶》的“人之性恶”,以前者解释后者,显然是不成功的。硬把性恶解释为性朴,无法令人心服口服。也许已意识到自己解释的问题,六郎后面又说:“比起善而言,人们更容易成其为恶。因此,将‘人之性恶’一语理解为‘人之性易为恶’更为妥当,也是秉承荀子之意的。”这里说的人之性,应该是指先天之性。当六郎认为《性恶》主张先天之性易为恶的时候,就与他前面强调的该篇主张先天之性为无善无恶之朴相矛盾了。
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性区分的尝试可以路德斌为代表。他同样也要协调性朴与性恶。他认为在荀子那里,未发之性是朴的,已发之性才是恶的。路德斌指出:“从‘人生而静’看‘性’,‘性’即朴也,天然合理,无善无恶;从‘感于物而动’看‘性’,顺性自然,贪欲无度,‘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性’乃恶矣……荀子所谓‘性朴’是从存有、本原的意义上讲的,而所谓‘性恶’,则是从发用、经验的层面说的……在‘人生而静’层面还是无善无恶的‘性’,到了‘感物而动’层面后,若顺其所是,便会自然而必然地趋向于恶。‘性朴’与‘性恶’绝不可以矛盾、不兼容视之……二者圆融无碍,逻辑一贯,可以同时成立而并存……”*路德斌:《性朴与性恶: 荀子言“性”之维度与理路——由“性朴”与“性恶”争论的反思说起》,《孔子研究》2014年第1期,第57—59页。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性区分类似于兒玉六郎的先天之性与后天之性的区分。六郎存在的麻烦,路德斌同样存在。所谓已发之性,应该是指情。路德斌的说法实际上可换为另一种说法:性无善无恶而情恶。为什么无善无恶之性会变为恶之情呢?他用“性向”来解释。性固有一种性向:“欲多而不欲寡。”正是这种性向导致恶。情欲本身不恶,但不受节制的欲望必然导致恶。欲多而不欲寡这种性向意味着性有不受节制的倾向。不过,路德斌所说的性向,是指已发之性的性向。我们肯定要问:未发之性有这种性向吗?如果未发之性没有这种性向,那么,已发之性的这种性向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未发之性已有这种性向,那么,怎么还能说它是无善无恶的呢?
虽然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性区分的尝试面临太多问题,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认可之。例如,王军说:“性朴是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认定……性恶是荀子人性学说的独特贡献……性朴与性恶之间并存在绝对的冲突,因为两者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其地位也不相同——性朴是基本认定、是性之未发、是性之体;性恶是特殊判断、是性之已发、是性之用。”*王军:《性朴、性恶与向善: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层次》,《现代哲学》2016年第1期,第106、110页。已发与未发说来自路德斌,基本认定与特殊判断说来自廖名春,而王军糅合两者,陷入更多的困境。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军一方面用不同层次说来解释性朴与性恶,另一方面又用时间先后来解释之:“荀子的思想具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前后矛盾或不一致也可理解。”这表明王军一方面认为性朴与性善没有矛盾,另一方面又认为两者有矛盾!
性恶与心善并举的尝试可以梁涛为代表。他认为《性恶》有两种的看法:性恶与心善。他把该篇分为两部分:以“涂之人可以为禹”为界,前一部分着重说性恶,后一部分着重说心善。与一般人把《性恶》中的“伪”解释为“人为”不同,梁涛据郭店竹简把“伪”解释为“心为”。他将“伪”与“心”联系起来,其目的在于说明心善。他说:“伪并非一般的作为,而是心之作为,是心的思虑活动及引发的行为……《性恶》实际揭示、说明了人生中的两种力量:以‘性’为代表的向下堕失的力量,‘心’为代表的向上提升的力量,并通过善恶的对立对人性作出考察,实际是提出了性恶、心善说。”*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73、77页。“知仁义法正之质”“能仁义法正之具”“性质美而心辩知”这些出现在后一部分的话,都被梁涛作为心善的根据。事实上,把“伪”作为“心为”不能令人信服。《性恶》之“伪”,显然是指人为、人为的作用、人为作用的结果。《性恶》前半部分明确地以后天人为的作用来说明善的由来,而不是以心的作用来说明之;《性恶》后半部分也未说到心善。“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说属于心,而“能仁义法正之具”不可以属于性吗?“性质美”之性,更明显地属于性。梁涛试图走出前人研究荀子人性的困境,但最终仍然陷入困境。向下堕失的性的力量和向上提升的心的力量之“两种力量”说,显示了鲜明的二元论,这自然令我们想起前面引用的李经元的话:“在荀子的思想中,善和恶实际上是作为人的二重性而存在的。”
三、从刘向编辑的指引出发摆脱困境
前面两部分所述关于荀子人性论的种种说法,都有麻烦。在本部分,我提出摆脱麻烦的思路是:回到刘向编《荀子》时对《性恶》的排序,视之为杂言杂语而不是论文说;它不是荀子所作,而是荀子后学与人性相关的不同言论的汇集;《性恶》体现荀子后学对人性看法的分歧。
以某子命名的先秦子书,其作者不全为某子,这是通例。例如,《庄子》的内篇为庄子本人所写,而外篇和杂篇为其后学所写。《荀子》也并非全为荀子所作。唐代为该书作注的杨倞认为,《大略》是弟子记录老师的话。虽然它体现荀子的思想,但显然非荀子所作,正如《论语》体现孔子的思想,但非孔子所作。杨倞还认为《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20页。,显然也非荀子本人所作。这几篇不是论说文,大部分是不同情境的对话,对话与对话之间没有关联。这些篇不与论说文混而单独排在一起,是很合理的。
令人惊讶的是,在汉代刘向编辑的版本中,在《子道》和《法行》之间夹着《性恶》。杨倞在注《性恶》的开头时说:“旧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议论之语,故亦升在上。”*[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34页。所谓荀卿议论之语,就是荀子所作的论说文,如《劝学》《礼论》《正名》等;而《宥坐》《子道》《法行》等则与这些论说文明显不同。杨倞的话可以让我们反推:刘向应该把《性恶》看作非“荀卿议论之语”,也就是非荀子所作的论说文。但杨倞把它看作“荀卿议论之语”,故抽离了它原来的位置,从第26篇升至第23篇。
今人总会认为《性恶》是一篇论说文,因为它主题鲜明,反复论证人之性恶。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看的,但是对它前面说性恶、后面说性质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它是一篇论说文,只能说是一篇自相矛盾的论说文。作为一个逻辑头脑非常严明的哲人,荀子可能写下自相矛盾的论说文吗?荀子在《劝学》《礼论》《正名》等论说文中有自相矛盾的情形吗?
后来,当我看到刘向编辑的《荀子》目录中《性恶》夹在《子道》和《法行》之间,于是恍然大悟:我们被杨倞误导了,它不是一篇论说文,而是与前后两篇一样的杂言杂语!它汇集了荀门有关人性的各种言论,这些言论前后不一致完全可以理解。《性恶》体现的不是荀子的自相矛盾,而是荀子后学对人性看法的分歧:有些人主张人之性恶,有些人主张性质美;有些人主张人情甚不美,有些人主张人有能仁义法正之质、知仁义法正之具……
从刘向所处的汉代到杨倞所处的唐代,经历了七八百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性恶》的杂言杂语性被遮蔽,而逐渐被人们看作是荀子自己写的论说文。性恶的说法太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且正好可以跟性善针锋相对,而性善性恶之争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人性史的主线,《性恶》这篇被刘向归于不重要的“杂言、杂事”类的荀子后学言论集,被后人看得很重要,而且被看成为荀子本人的代表作。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们忘记了其拼凑性而将它看成一篇完整的论说文。这是刘向在编《荀子》时完全意料不到的*周炽成:《〈性恶〉出自荀子后学考——从刘向的编辑与〈性恶〉的文本结构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93页。。
在将《性恶》视为论说文的视野下,面对其不同的内容,有人把它分为两部分。例如,前面已引用过梁涛的说法:以“涂之人可以为禹”为界,前一部分着重说性恶,后一部分着重说心善。关于两部分的关系,人们有种种说法,但都不能令人心服口服。如果我们将它回归杂言杂语,而不是以之为论说文,那么,很多困惑都可以豁然开解,而所谓两部分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不成其为问题了。
在我们看来,作为杂言杂语的《性恶》是由七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就是反复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部分;第二部分由“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到“以秦之人安恣睢,慢于礼仪故也,岂其性异哉”;第三部分由“涂之人可以为禹”到“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第四部分由“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到“唯贤者为不然”;第五部分由“有圣人之知者”到“是役夫之知也”;第六部分由“有上勇者”到“是下勇也”;第七部分由“繁若、钜黍,古之良弓”到结尾。
第一部分最长,占全篇内容的一半以上。如果只看这一部分,《性恶》确实很像一篇论说文。但是,全面看后面六个部分,把它视为论说文就很难说得通。第五部分说四种知(圣人之知、士君子之知、小人之知、役夫之知)、第六部分说三种勇(上勇、中勇、下勇),在论说文视野下对这两部分最难解释。设想你要作一篇以性恶为题的论说文,你在那个地方说四种知、三种勇,你是什么意思呢?你想说明什么呢?四种知、三种勇与性恶有何关系?如果有关系,你为何不说?如果无关系,你说它们干嘛?以《性恶》为杂言杂语,这两个部分就比较好解释:《性恶》编者大概认为四种知、三种勇具有先天性,故与其他关于人性的内容编在一起。三勇说可能成为后来盛行的性三品说的思想素材。
在杂言杂语视野下,《性恶》后六个部分的其他部分也好解释。第二部分与人性恶无关,其基本意思非常接近于孔子对人性的看法:性相近,习相远。曾参、闵子骞、孝己与众人,秦人与齐鲁之民,他们在天性方面没有差异,其德行之不同,完全是后天修为之不同而带来的。显然,杨倞对这部分的解释是错的:“綦礼义则为曾、闵,慢礼义则为秦人,明性同于恶,唯在所化耳。若以为性善,则曾、闵不当与众人殊,齐、鲁不当与秦人异也。”*[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42页。杨倞顺着第一部分的思路而解读第二部分,以为还是在讨论性恶。在第一部分中,“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反复出现,以作为每一段的总结。如第二部分真的还是继续说性恶,为什么不出现这样的话呢?单独阅读这一部分,不受第一部分影响,就可见用“性近习远”来概括它是合理的,而用“性恶”来概括它则不合理。
第三部分对人性的看法与第一部分的看法完全相反。“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和“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的说法已被不少人注意到。它们与性恶的说法明显冲突。第七部分以良弓、良剑、良马比喻人性,明确肯定人有“性质美”,与第一部分的冲突更为严重。在以《性恶》为论说文的视野下,第三、七部分完全解释不通。本文第一节所说的种种困境,多与解释不通相关。如果我们回到杂言杂语的视野,这些困境、这些不通就不存在了。持第一部分看法的荀子后学与持第三部分看法的荀子后学、持第七部分看法的荀子后学,是不同的人。至于持第三部分看法的荀子后学与持第七部分看法的荀子后学,可能是同样的人,因为两者都不以人性为恶,都持有相似的人性观,但更可能是不同样的人,因为两部分的侧重点有差别。第四部分肯定人情甚不美,与第一部分说性恶接近,这两部分的人可能是同一群荀子后学。
但是,第四部分之位置也进一步显示《性恶》之杂言杂语性。第三部分肯定人人皆可以为禹,人人皆有“知仁义法正之质”和“能仁义法正之具”,表明对人性的乐观态度。但是,第四部分却又回到第一部分的悲观态度。为什么第四部分不紧接在第一部分之后呢?如果《性恶》真的是一篇完整的论说文,对人性持有悲观看法的第四部分紧接在对之持有乐观看法的第三模块之后,实在难以理解。
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指出,《性恶》之篇名容易误导人们视之为论说文。表面上看,它与《劝学》《礼论》《正名》之命名方式一样,都以文之要义命名,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以要义命名之篇名很好地概括全篇的内容,而全篇的内容也无离题者。但是,“性恶”二字只概括该篇第一部分之内容,无法涵盖后面六个部分之内容。准确地说,这二字可以涵盖第一部分之内容,并也可能涵盖第四部分之内容,但无法涵盖其他部分之内容,因为这些部分都明确显示人性不恶。《性恶》之命名,应该与《子道》《法行》之命名一样,取开头二字名之。总之,回到该篇夹在《子道》与《法行》之间本来的位置,才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它。
(责任编辑 杨海文)
周炽成,广东郁南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性论通史”(15ZDB004)
B222.6
A
1000-7660(2017)01-01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