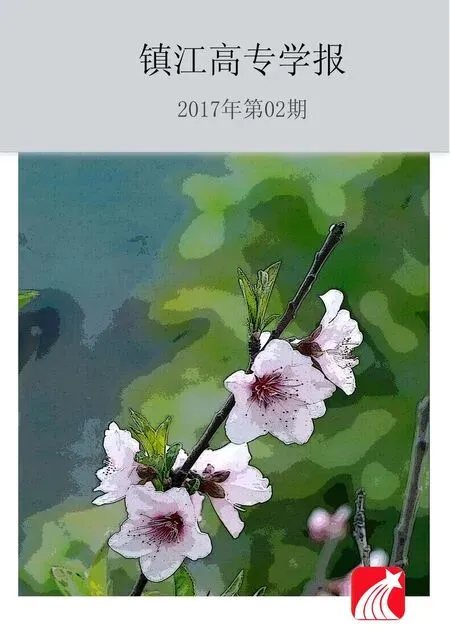司法视角下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认定标准重构
朱孟超,刘三洋
(1. 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检察院 办公室,江苏 扬中 212200;2. 江苏大学 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1)
司法视角下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认定标准重构
朱孟超1,2,刘三洋2
(1. 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检察院 办公室,江苏 扬中 212200;2. 江苏大学 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公共场所管理人和公共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风险社会中,该制度的目的是以极为广泛的注意义务形式,赋予众多潜在受害人更多的救济机会。透过学者的观点和相关司法文书,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认定标准有“要素叠加”和“行为+程度”两种标准。在责任普遍化的情形下,为平衡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对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认定,应采取司法审判中体现的“行为+程度”特定场所的可支配性标准,而非“要素叠加”的标准。
司法;安全保障义务;认定标准
1 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认定标准的意义
案例1(本文案例及判决书内容均引自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下略) 2013年8月9日,原告陈某某与家人到被告“小玲老厨房”餐馆就餐。原告步入餐馆内尚未就餐时即摔倒受伤,经先后两次医疗鉴定,其腰椎、胸椎均出现骨折等情况。事后查明,当时“小玲老厨房”餐馆内有一服务员在拖地,但事前未采取警示等行为。后法院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餐馆承担部分责任 。
案例2 2010年6月16日,原告矫利仁到百色天鹅城百货购买日用品。当乘电梯前往商场2楼至电梯尽头时,因商场的工作人员在维修电梯,在维修现场没有放置任何警示标志,导致矫利仁一只脚突然踏空,右腿陷入电梯下方致右股骨上段骨折,并因之两次就医。后法院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百色天鹅城百货对原告第二次就医的费用承担部分责任 (第一次就医的费用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未获支持)。
案例3 2013年10月6日下午18时至22时许,陈某某的父母带其参加父亲的同学聚会,聚会地点为被告陈勇军所经营的××酒楼一楼最里面的包间。22时许,陈某某从包间的一扇窗户摔出,经一次转院治疗,鉴定为头部左颈侧、左枕部、左眼眶等受伤。后法院以未尽安保义务为由判决涉案酒楼承担部分责任 。
尽管具体情节存在差异,但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了较为一致的认定: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以下简称“安保义务”)而引发的不作为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了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因未尽合理的安保义务所负担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将这一责任的主体明确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以及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并规定该主体与引起危险的第三人之间系主要责任与补充责任关系。
然而,尽管我国相关法律明文规定了安保义务,但是如何合理认定这一义务的范围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范的责任主体,大多属于经营性主体,追求效益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赋予其过高的安保义务原属不宜;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属于私法,其处理的是独立私主体之间的纠纷。故经营者的安保义务与行政主体被赋予的保障秩序的公法义务不同,具体表现为,一者,经营者不具有管理、控制其他私主体的行政职权,相应地,其所承担的安保义务应被限制在合理的时空范围内;二者,经营者们履行这一义务,不仅需要独立承担管理的费用,譬如商场内的安保费用等,还面临着因管理不当而承担一般侵权责任的风险。因此,构建安保义务范围合理的认定标准,以谋求经营主体与消费者的利益平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确立认定标准的法理依据
在对安保义务范围的认定标准展开讨论之前,应首先解决一个问题:确立这一标准的依据是什么?这需要先理解安保义务的目的,为有效构建安保义务的范围标准提供指导。
以德国相关制度的发展为例。由于注释法学派在继受罗马法的侵权诉讼体系时,为了保障一般主体的行为自由,仅规定在以下情形中追究他人的不作为侵权责任:当他未履行由先前行为引发的积极作为义务时[1]。但在1902年“枯树案”(公共道路上的一棵枯树倒塌致使一处房屋被毁损,房主对道路管理人提起诉讼)中,鉴于传统侵权理论不能在该案中满足公众的衡平情感,德国帝国法院基于社会连带理念认为:特定树木占有人对其可能引发之危险具有注意义务。若违背该义务,未采取适当手段避免危险发生,则应承担责任[2]。
德国的相关实践表明,安保义务的责任,系以判例形式出现的、作为传统侵权责任体系的补充或例外而产生的。但具体是何种例外呢?如果侵权责任体系以保障自由行为为立法宗旨,那么,该体系的规范视角应当以行为人或者以侵害人为视角而展开。假使我们承认法律规范系以权利、义务等为其调整社会主体行为的制度机制,且责任不过是违反义务产生的法定后果,则我们将承认这样的观点:侵权责任体系的初始目的,与其是为了补偿受害一方的损失,毋宁是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那么,以该观点为前提而引申出的结论就是“枯树案”中司法判决的例外,是一种关注视角的例外:从受害人的视角评判某一行为的侵害性(注意:此处不赞成使用“补充”的表述。虽然说鉴于该案中透射出的“注意义务”,相关责任主体将基于可能引发的诉讼纠纷和担责风险的恐惧而调整其行为,但从该义务产生的来源来看,至少作为“造法者”的司法机关是以“让受害人获得救济”为动机。产生于不同目的的事物之间本不应当存在主体与补充之分,只能认为系原则与例外的关系)。但是,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侵权体系呢?
笔者认为不适用于我国的侵权体系。首先,从立法目的的角度而言。《侵权责任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该条款表明,《侵权责任法》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受损害一方的利益。“侵权行为”只是该法“预防与制裁”的对象。简而言之,《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只是供给受害人获取救济的请求权基础,而非行为基础,这一点与德国的相关规定存在本质差异。其次,从本法的功能定位来看,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有学者主张,尽管该法将谋求受害人利益保障与侵权人行为自由的利益平衡作为考量的因素,但其发挥的作用在于限制这一功能的不断扩张:对受害人相关权益的救济[3]。最后,《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也表明,该法的立法视角主要是受害人的得偿视角,而非行为人。
那么,我国侵权体系中安保义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将法律规范视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那么应该考虑该条文在法律规范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条文的关系,并避免法律规范内容之间出现重合、冲突和遗漏。《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位于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中。这一章属于《侵权责任法》总则的内容,还是分则的内容呢?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立法体例,《侵权责任法》没有直接言明总则与分则的界限。有关学者在对《侵权责任法》总则内容进行解释时,没有将第四章的内容纳入讨论的范围。此外,从法律条文的平等效力出发,除非某一规范对相关案件未做明确规定,如果认为总则的相关条文不能作为审判某一具体案件而适用的某一实体规范最后列举的条文,则法院无疑认可第三十七条属于分则的内容。
既然认为安保义务责任属于《侵权责任法》分则的相关事项,那么应当认为该类行为与第五章至第十一章规定的侵权责任在外延上是并列或者至少是交叉关系。如果肯定前文对侵权责任体系的理解,那么第四章的内容应当理解为:在第五章至第十一章相关责任的基础上,对特定主体课以新的责任。从这一点来看,尽管违反安保义务之行为具有间接侵权的特征,相关主体承担责任仅因其“未切断第三人行为或物的属性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但间接侵权责任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安全保障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假设A前往B宾馆居住一晚。当夜,A所在宾馆的吊灯突然掉落,将A砸伤。事后查明,该吊灯质量合格,且已经过年检。其掉落系因为第三人的破坏行为。若该案中A起诉B宾馆,其请求权基础将不可能系《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或第六条的规定。其仅能考虑是否求助于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又假设C与朋友前往D的电影院,并购买F出售的爆米花(F与D为相互独立的经营者)。后于观看电影期间,C因食用爆米花而生病住院。若C起诉D,其仅能依据第三十七条。简而言之,安保义务就是相关主体基于对特定场所和活动的支配可能性而产生的对他人可能遭遇的潜在危险的防范义务,而从责任和受害人救济层面而言,如果承认这种支配性具有一定效力或本法推定的效力的话,则可认为系基于有关主体对特定场所或活动的支配性延伸而来的补充救济。该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受害人能于特定场合获得更多一层事后救济或事前保障。
3 现有认定标准的不足
有关安保义务的认定标准,我国学界已有所研究。有学者提出,从安保义务人是否获益、预防与控制的成本、危险控制义务的履行,以及专业人员的标准几个层面探讨[4];也有学者提出,从安保义务人获益情况、风险或损害行为的来源、预防或控制的成本、危险义务的控制情况,以及普通民众的感情等方面予以认定[5];此外,杨立新等学者提出了安保义务人的五要素:是否受益,风险或损害行为的来源或强度,安保义务人控制、防范风险或损害的能力以及受害人参与经营活动或社会活动的具体情形[6],即采用“要素组合”标准。
然而,从理论经济性和认定合理性的角度出发,笔者不认可学界普遍支持的“要素组合”标准。如果采纳学者们主张的诸要素判断标准,则需要进一步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这些要素是采用“正向一致”原则还是“反向一致”原则?如果是后者,应当遵循“阶梯式”组合还是“流水线式”组合?如果这些要素中有一二项不存在如何认定?譬如案例1中,受害人刚刚步入餐馆尚未就餐,即因地板湿滑而摔倒受伤。安保义务人尚未获利,风险仅来自于地板的湿滑程度,安保义务人对这一风险的产生可能仅有模糊的不安感。此时究竟如何认定安保义务人的义务履行?
第二,学者提出的用以确立安保义务是否履行的诸要素本身的认定即存在争议。假设采取杨立新等提出的“五要素”标准,其中最容易确定的是安保义务人的获益状况及风险的来源,至于风险的强度、安保义务人控制风险的能力及民众的情感等均属于司法人员规范认知的要素。就风险的强度与风险控制能力而言,“汉德公式”从比较法的视野对该要素的认定提供借鉴,“汉德公式”以一种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用具体的金钱数目取代哲学性的抽象原则的标准,让行为人知道自己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已善尽注意义务”,这就是“汉德公式”划时代的意义。汉德法官设定此“免责点”B=L×P(其中,B指预防事故的成本,P指事故发生的概率,L指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此公式的意思为当行为人为避免事故所支付的成本数额等于风险造成的损失与风险发生的概率的乘积时,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免责),这显然是一个很直觉式、带有道德上“道义上我做到这个地步应该说得过去了”味道的一个标准[7]。这一公式的可行性仍然存在疑问。
第三,尽管学者们力图通过若干要素的搭配,将安保义务控制在可见范围内的努力值得肯定,但这却给相关经营者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尽管经营者们通过一段时间的经营活动,能够从大量受害人抱怨和投诉中分析出风险的来源。但如果要求他们从经营行为中识别出某一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则多少有些强人所难。这些内容绝对不可能成为经营者们认识到或可能认识到的内容。如果司法者们仍然基于“社会衡平”的考虑贯彻这一标准而不论义务人能否预见得到,那么,我们只是在缔造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社会”[8]。
4 司法视角下认定标准的重构
应当选择何种标准来确定安保义务的范围呢?笔者认为,不妨从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寻求答案。正如学者所说的那样:“经由司法人员的智慧锤炼而成的实践理性是一块膏腴之地,其闪现的司法人员的理性之光既是萃取理论的富矿,也是提炼裁判要旨、形成司法规则的活水。既有利于指导司法审判,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9]
如刘海燕与青岛永旺公司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一案,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写到:“服务场所所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的义务,是积极的作为义务。经营者不采用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设施或设备、不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不设置必要的警示或不进行必要的劝告、说明等,均属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本案被告经营场所内设置的电梯存在安全隐患并且未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系导致原告女儿手被夹住、原告在施救过程中手被致伤的主要原因。被告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再如,刘子亮与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人民法院在审判理由中写到:“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本就是易湿滑场所,其管理人应该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被告门诊楼二楼卫生间设施较为陈旧,且其主要是向患者开放的公共场所,被告应当承担更为严格的维护和管理义务,进行有效的警示和维护,以防止意外的发生,被告未能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对原告摔伤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考虑到原告摔伤后,被告及时进行了抢救治疗的情况,被告应该对原告的摔伤承担次要责任。”
刘子亮案的判决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法官论证了经营者被赋予安保义务的缘由:卫生场所地面“湿滑”“设施陈旧”且属于“向患者开放的公共场所”,医院在其支配的领域内,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范患者摔伤、跌伤的潜在风险;第二部分,法官阐述了应如何履行安保义务,即被告应采取“更为严格的维护和管理义务”,并“进行有效的警示和维护”。那么,我们不妨对这一判决内容作这样的理解:作为被告的医院,当处于其支配下的、某一对外开放场所存在因地面湿滑而具有引发患者摔倒的风险时,医院应当采取更为严格的维护、管理、警示等行为,以防止意外的发生。简言之,当事后发生某一风险时,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形下安保义务人是否实施了防范风险的合理行为,以阻却安保责任的产生。笔者将其概括为“行为+效果”或“行为+程度”的标准。
不难发现上述标准与“要素组合”标准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后者从事前的立场出发,在怎样的情境下经营者应当承担安保责任;前者采用事后的角度回顾:一旦义务主体采取了适当的防范、保障或警示措施,且能够避免风险的实现,即可阻却安全保障责任的产生。
确立这一新的标准,具有两个作用:一方面,使安保义务的认定更为简便。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只需判断,经营者是否采取了保障安全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在一般意义上的有效性,即能明确经营者是否履行了安保义务。在具体案件中,保障行为的存在与否、是否有效,是相对容易判断的。另一方面,缩小了经营者所需承担的安保义务的范围。“行为+程度”标准将经营者的安保义务由秩序保障缩小为行为保障。经营者只需根据经营场所的自身情况,采取相关的警示、预防、管理和保障措施,即可将被追责、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降至最低。
哪些行为应当作为已尽安保义务的行为呢?从受害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意志自由角度出发,并且遵循责任主义原则(注意:不是分担损失的标准,那是《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关注的对象),那么,对安保义务人的保障义务应当推定是十分有限,甚至狭小的;同时,如果我们承认,一定程度上,受害人所可能遭受的风险(不是他人有意实施的行为),与其所进行的选择(譬如,是否选择进入某一家餐馆用餐)是具有一定关联的,那么,无数“潜在的”受害人自进入某一公共场所(尤其是经营性场所)或参加某一活动时,其也应当意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应进行理性的判断;此外,如果认为经营者的安保义务源于其对某特定场所或活动的事实上的支配性,当安保义务人将某些可能风险已经以合理方式作出警示,受害人依旧我行我素时,则应视为受害人“脱离了支配性”,安保义务人不再承担可能的风险。就如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如果事先以合理方式告知了缔约主体相关的权利义务,则一旦缔约之后,若无证据证明该条款存在违法事项,所订条款应推定有效。故笔者认为,安保义务主要系公共场所管理人与公共活动组织者对潜在风险的警示、告知、劝阻等义务,以及对相关设备的质量保障义务。 有关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也对这一观点予以支持。譬如案例1中,人民法院对安保义务作了如下理解:“从事餐饮业服务的经营者对前来消费的相对人负有安保义务,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作了相应的规定,从前述规定看出从事餐饮服务业的管理人因支配其餐饮环境而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包括警示义务、禁止义务、指示义务。”
再如,祁继舫与北京菜市口百货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人民法院以质量保障义务和警示义务的妥善履行而认定相关经营者不再承担安保责任:“本院认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已向本院提交了电梯维护单位和相关维护人员的资质证书、扶梯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及自动扶梯监督检验报告;经本院现场勘验,被告在自动扶梯处均设有明显标志对老弱病残孕及行动不便人员进行了提示;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亦显示,被告商场并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可直接导致原告损害后果的不当情形。综上,被告已在合理范围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程度标准事关安保义务人应尽到何种程度的义务方能免责的问题。从祁继舫案的裁判理由中可以发现,程度标准往往隐含在安保义务人实施的若干行为之中,其对行为标准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综上,被告已在合理范围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这句话表明,义务人实施的安保行为所能达到的足以防止危险发生的程度考量,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标准存在。结合前文的观点,此处亦可参照《合同法》格式条款对提供者的“合理说明义务”予以规定。一般意义上,结合告示牌的大小、显示区域、警示牌的数量等,只要能够达到一般公民视觉上的“可清晰识别性”,即可认定为履行了安保义务;若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内发生了斗殴、哄闹等现象,从自力救济的原理出发,只要经营者或活动组织者能够证明其采取的制止措施,如警告或拦阻行为,达到了分离斗殴双方或使其脱离公共场所的效果,并及时寻求公力救济,则应视为妥善履行了安保义务。
[1] 林少棠.作为请求权基础的安全保障义务:兼论合理判断标准的建构[J].时代法学,2016,14(1):52-60.
[2] 刘召成.安全保障义务的扩展适用与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发展[J].法学,2014(5):69-79.
[3] 曹险峰.侵权责任法总则的解释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9.
[4] 王楚.论侵权责任中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1):104-108.
[5] 王俊英.安全保障义务及其限度[J].河北法学,2008,26(10):198-200.
[6]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研究”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J].河北法学,2010,28(11):1-21.
[7] 林立.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88-300.
[8] 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 [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42-255.
[9] 杨海强.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刑事审判指导案例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3):25-33.
〔责任编辑: 张 敏〕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ndards in judgment of the scale of obligations for safeguard
ZHU Mengchao1,2, LIU Sanyang2
(1. Office of Yangzhong Municipal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Jiangsu,Yangzhong 212201, China; 2. School of Law,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01, China)
The obligations for security safeguarding, regulated by Article Thirty-seven in The Law of Tort Liability of China, were given to governors of several public platforms and organizers of activities. Under the risks of society, the purpose of the system is to give many potential victims more relief opportunities in the form of the extremely wide duties of care. Through the views of scholars and the relevant judicial documents, the judgment standards of the security obligation scope include “elements overlapping” and “behavior”. In the case of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judgment of the scope of the security obligations should adopt the disposable standards of “behavior and degree” embodied in justice practice in particular platform instead of “element orerlapping”.
justice; obligation of safeguard; standard of judgment
2016-12-01
2016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SJLX16_0419)
朱孟超(1984—),男,山东菏泽人,助理检察员,硕士生,主要从事刑事法研究; 刘三洋(1993—),男,江苏南京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刑事法研究。
D926
A
1008-8148(2017)02-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