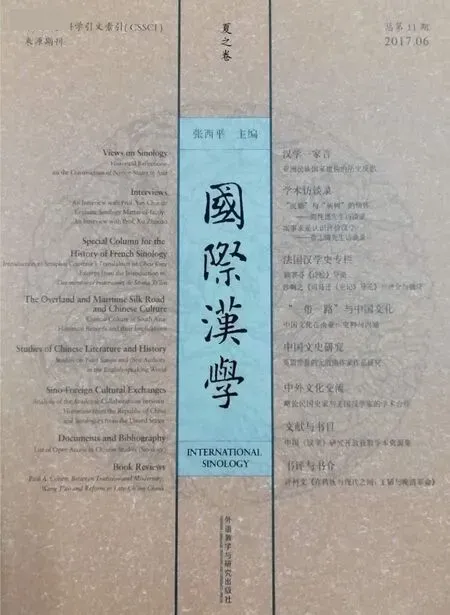鲁布鲁克出使蒙古的翻译问题研究
□
引言
13世纪蒙古人西征重新恢复了欧亚大陆之间的陆上通道,东西方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欧洲教皇和君主先后派遣使团出使蒙古。这些使团多出于传教目的,但更可能带有“窥探蒙古人动向的目的”①柔克义译注,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因为当时欧洲十字军正在和阿拉伯人鏖战,亟须在东方寻找盟军。
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教士鲁布鲁克(Rubruck William,约1215—1257)②本文中使用的译名皆以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译名为准。鲁布鲁克之译名也可见“卢白鲁克”“罗伯鲁”“鲁布鲁乞”等。携带法王致蒙古统治者的信函出使蒙古。鲁氏使团往返旅程共持续两年时间。在此期间,鲁氏先后晋谒了蒙古领袖撒里答、拔都和蒙哥。1255年,他在返回欧洲后以致法王信函的方式详细记述了出使蒙古的经历。信函被后人汇编成书,以《鲁布鲁克东行纪》(以下简称《东行纪》)③《东行纪》原为拉丁文本,近世比较常用的英文译本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1255, 2nd Series, 4.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Peter Jackson with David Morga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2nd Series, 173. London: Hakluyt Society,1990; Christopher Dawson,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ri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55, pp. 87-220。法文译本有:Claude and René Kappeler,Guilliaume de Rubrouck, envoyé de saint Louis. Voyage dans l’empire mongol. Paris: Payot, 1985。德文译本有:Friedrich Risch, Wilhelm von Rubruk. Reise zu den Mongolen, 1253-1255,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Forschungs-Instituts für vegleichende Religionsgeschichte an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II. Reihe, 13. Leipzig: Eduard Pfeiffer, 1934. 何高济中译本即以柔克义英译本为底本。闻名于世。由于鲁氏对蒙古文化与时事的详尽记述,尤其是他对“契丹”④主要指中国北方地区。的传奇描述,《东行纪》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的必修文献。
不少学者较详细地描述和考证了鲁氏的行程⑤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6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Peter Jackson and David Morgan,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ahn Möngke,1253-1255.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0.,还有研究者将《东行纪》所载内容用于历史地理考证①陆峻岭:《哈剌和林考》,《域外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也有研究者简略地提及鲁氏出使活动中涉及的语言沟通问题②丹尼斯·塞诺:《“中古内亚的翻译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Nicholas Koss, The Best and Fairest Land: Images of China in Medieval Europe. Taipei: Bookman Books, 1999; Francis Wood, The Lure of China:Writers from Marco Polo to J. G. Ballar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但其出使活动中的翻译问题并没有得到专门研究。
一、蒙古时代的语言和翻译
13世纪中期,蒙古的势力范围及于东欧诸国。统治下的民族数量繁多,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蒙古统治者在确保统治权的前提下对多元文化和信仰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③鲁布鲁克提到为他和蒙哥第一次会面担任译员的聂斯托利派教徒同时也是蒙哥一个女儿的教员,或可为蒙古统治者对多元文化接受之旁证。如刘迎胜所述:“当时的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并存着三四个大文化圈:即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与东地中海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与拉丁文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上,自东向西分别扮演着国际交际语(lingua franca)的角色”,而“横跨欧亚疆域空前的蒙元帝国……使这几个文化圈之间的联系之便利与密切超越以往”。④刘迎胜:《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76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时代对翻译人员的需求急剧增加。大蒙古国时期甚至被美国阿尔泰学者丹尼斯·塞诺冠之以翻译人员的“黄金时代”之名。对此,萧启庆指出:蒙古在版图迅速扩张过程中,“语言问题甚为复杂,对翻译人员的需求亦极迫切”。⑤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21页。仅《东行纪》中所涉及的语言就至少有:拉丁语、蒙古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蒙古统治者不仅在行政中需要通过翻译和多民族的官僚沟通,而且其公文制度也涉及多种语言文本之间的翻译。
蒙古时代的翻译人员被称为“怯里马赤”和“必阇赤”,即“通事”和“译史”,分别负责口译和笔译工作。为了满足对翻译的需求,蒙古统治者自1233年6月开始就在燕京开设国子学,有系统地培养通译人才。但培养规模不大,一直维持在四五十人左右,因此还有大量的翻译人员需要从被征服民族中征募。
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俘虏了大量欧洲男女教徒。鲁布鲁克在蒙古首都哈剌和林就见到有法国、日耳曼、匈牙利及俄罗斯等国人员,多为工艺匠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在蒙古与欧洲的沟通中发挥了译人的作用。例如,法国工匠威廉的妻子出生于匈牙利,既能说法兰西语,也能说库蛮话。另外还有一名英国人的儿子贝昔尔(Basil),也懂数国语言。⑥黎难秋据《中西交通史》提及巴西尔(即贝昔尔)“能操数国语言,为蒙古军中通译”,(方豪:《中西交通史》,第516页)推断“宪宗帝接见罗伯鲁(即鲁布鲁克)一行时,是由他担任口译的”。此推论值得商榷,因为据鲁布鲁克记载,蒙哥(即元宪宗)第一次召见他时为他担任译员的是使团成员哈莫·德依,而为蒙哥担任译员的则是他“不知道是基督徒的聂斯托利(Nestorian)”,而第二次担任双方翻译的是金匠威廉·布昔尔(William Buchier)之子。黎氏所论或由贝昔尔(Basil)与布昔尔(Buchier)相混。
鲁布鲁克使团的到访正值蒙古汉廷的势力鼎盛时期,但高质量翻译人才的缺乏却导致他在出使活动中屡屡沟通不畅。以下我们将具体考察与鲁氏使团翻译相关的问题。
二、鲁布鲁克使团的翻译问题
(一)鲁布鲁克使团的翻译
由于语言不通,鲁布鲁克在出使过程中随时需要翻译人员协助其沟通。鲁氏使团最重要的译人是随团翻译哈莫·德依(Homo Dei)。《东行纪》的英译者柔克义认为,“Homo Dei”的译意是“上帝的仆人”,它可能是阿拉伯语“Abdullah”(真主的奴仆)的译义,因此该译人是位伊斯兰教徒。鲁氏在《东行纪》中没有交代他从何处招募此人,但他却提及译人将蒙哥夫人赏赐的礼物一路带到塞浦路斯售卖。由此或可推测哈莫·德依可能是来自塞浦路斯的伊斯兰教徒。
另外一位对使团,尤其是鲁氏本人具有重要意义的译人是金匠威廉之子。他分别在鲁布鲁克第二次会见蒙哥和参加宗教辩论时担任了译员。
此外,鲁氏还不记名地提及数位服务蒙方的译员,以及对来往函件进行笔译的译人。
总体而言,除金匠威廉之子以外,鲁布鲁克对为他翻译的人员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他在《东行纪》中多次表达了对哈莫·德依的不满,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详述。而对于翻译路易九世信函的亚美尼亚译人,他则指责他们因为自身对撒拉逊人的仇恨而扭曲了原文。
(二)鲁布鲁克出使过程中使用翻译的情况
在出使蒙古以前,鲁布鲁克并没有学习过蒙文。他在长期出使途中掌握的少量蒙语远未达到与人沟通的程度。因此他与蒙古人的交流几乎全部依赖译人。
1.鲁氏会见斯克台
鲁氏使团进入蒙古人统治地区后遇见的第一名官员是拔都的亲戚斯克台(Scatay),但是首先与他们交涉的正是斯克台的译人。鲁氏与蒙古译人的首次接触并不令他满意,因为译人听说他们从未到过蒙古,就开始向他们索取东西。在得到一些礼物后,译人得寸进尺地要求一件袍子。要求被拒绝后,译人又问他们给斯克台带了什么。在使团呈上酒、饼干和各种水果后,译人却并不高兴,因为没有得到值钱的纱绢。最后,鲁氏和同伴们是“恐惧和战栗地”带着礼物前去见斯克台。
鲁氏在见到斯克台后,将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希腊语信函递交给他。但斯克台手下并没有懂希腊语的译人,因此斯克台“立刻把信函送到索尔对亚去翻译”。
当斯克台对他将要向撒里答说明的基督教义表示兴趣时,鲁氏试图“尽量通过译员向他解释教义”,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译员哈莫·德依对他所说的教义“既不十分理解,也译得不流畅”,以致对方在听到他的解释后,只是“沉默不语”,而且还“摇他的头”。
2.鲁氏谒见撒里答
离开斯克台后,使团继续前往谒见撒里答。斯克台为使团提供了一名向导和两名车夫。在路途中,鲁布鲁克试图通过自己的译员向他们传教,但令他感到苦恼的是,译人哈莫·德依却告诉他:“你不能使我讲道,我不知道该怎样说。”①《东行纪》,第227页。鲁布鲁克对此毫无办法,因为他不懂对方语言,双方日常沟通也完全依赖译人。鲁氏自言在不久后他学会了一点蒙语后发现,在他说一件事时,译人却在谈另一件不相干的事。他认为如果这样的话,通过译人来沟通有歪曲他本意的危险,因此“下定决心不说话”,不再试图通过译人与同行者交流。
1253年8月1日,撒里答召见鲁布鲁克。使团译人跟随前往。鲁氏将路易九世的信连同他在阿康(在今巴勒斯坦境内)找译人写成的阿拉伯和叙利亚译文交给他。撒里答帐下的书记将信函译成蒙古语,读给撒里答听。撒里答在听过译文后,吩咐收下鲁氏作为礼物赠送的面包、酒和水果,而把他们的法衣和书籍送回他们的住处。
鲁布鲁克没有详细描述他在晋谒撒里答时使团译人的工作情况,但却提及对法王信函的翻译。据他所述,法王信函至少经过了两重翻译才让撒里答得以理解其内容,即从法文原文到阿拉伯或叙利亚文的第一重译文再到蒙古文的第二重译文。类似这样借助于第三种语言的“接力翻译”在不同语言与文化,尤其是距离较远的文化间交流时比较常见。②比较著名的历史案例还有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双方是通过拉丁语作为接力语言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的。尽管翻译过程复杂,但至少从撒里答对信函内容的反应来看,译文还是基本体现了原文作者的意图。
3.鲁氏晋谒拔都
1253年8月3日,在撒里答的建议下,鲁氏启程跟随撒里答派遣的向导前往拔都营帐。临行前,撒里答手下的重要官员科埃克却派人强取了他们携带的马车、书籍等。鲁布鲁克对此表示无可奈何,因为他不会被允许再次面见撒里答,也没有人会为他们主持公道。此时鲁氏又提到对译人的担心,担心“他说一些和我们意思不同的话”,因为他的译人“常常想要我们给每个人都送礼”。③《东行纪》,第234页。
显然,译人哈莫·德依在此番出使过程中不是隐身的,而是有着与使团首领不同的想法和做法。这可能与他的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职业译员是直到20世纪才出现的群体。在前现代时期,译人还不具备今天所谓的“职业意识”,他们愿意充当译人的角色多半只是为了谋生。
鲁布鲁克见到拔都时,开始通过译人布道和讲述教义,拔都听后“安详地笑了”,而“其他的蒙古人开始拍手,笑我们”。此时,鲁氏注意到他的译员“惊呆了”,以致他“不得不让他别害怕”。①同上,第240页。
此段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真实的通过译员进行沟通的场景,其中有原语的讲话者、译员和译语的听众。更为重要的是,显然听众对讲话内容的反应出乎译人意料,从而导致译人对自己的翻译行为,或更准确地说是翻译质量,产生了怀疑。而此时作为讲话者的鲁布鲁克对他表示了安慰。从鲁氏同译人打交道的情况来看,他此举更多是出于为了维系沟通的无奈,而非对译人的关心。
与拔都见面后,使团回到住宿处。向导告诉他们,拔都说如果想留下传教,必须征得蒙哥汗的许可,鲁氏必须和他的译员同去见蒙哥汗,而他的同伴及其他人则须留下,并返回撒里答处等待。译人一听说还要长途跋涉前去会见蒙哥,就开始抱怨,“认为他自己遭难了”②同上,第241页。。
由此可见,哈莫·德依对此番出使任务艰巨性的预期是不足的。但问题在于,鲁氏自己在出使前向译人交代翻译任务时可能也没有预计到行程如此复杂,因此译人虽然继续跟随鲁氏前行,但他与鲁氏之间的配合越来越成问题。
4.鲁氏在前往蒙哥营帐途中
离开拔都驻地后,鲁氏使团继续前往蒙古首都哈剌和林谒见蒙哥。一路上,鲁氏常常感到“饥渴交迫、又冷又累”。而他们的向导起初又看不起他们,不愿意“给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带路”。不过不久之后,随着相互了解的增加,向导开始愿意把他们带到蒙古富人那里为他们做祈祷。这时鲁氏又感叹:“如我有个好翻译,我本应有机会带来不少的益处。”③同上,第245页。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东行纪》将此处译为:“得到大量的食物”,而原文为“bringing about much good”,结合他此处对译人不称职的感叹及前文内容,此处应不仅指从蒙古富人处获得食物,亦指向其宣传教义。是以改译。
在鲁氏使团到达海押立城(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南塔尔迪库尔干东)时参观了一些当地寺庙。鲁布鲁克由此联想到他后来在哈剌和林参观过一处佛寺中的大小偶像后,与僧众就信仰问题展开辩论时的情景。正在他满怀信心要继续与对方理论时,他的译员对他们的辩论内容“感到厌倦,不愿再译我的话,所以他叫我别再说了”。④同上,第252页。至此鲁氏只能作罢,因为离开了译人,他与对方的交流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鲁氏的此番经历,反映了译员在发挥文化媒介功能时的一个难以避免的不足,即无法左右讲话者与听众之间沟通的内容。如果沟通内容超出了译者自身的知识范围,给他造成了理解困难,那么翻译行为就很难顺利开展。鲁氏与僧众进行的是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辩论,而很可能出身伊斯兰教的译人对双方教义都不熟悉。在此情况下,仅有语言能力,而无文化知识的哈莫·德依根本无法发挥他的中介作用。
离开海押立后,鲁氏使团经过传说中有魔鬼的峡谷。向导因为害怕,请求鲁氏做祷告,以便吓跑鬼怪。鲁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想借此机会教随行的蒙古人信仰基督教,但每次他试图教说一句将永远拯救他们的“灵魂和肉体”的话时,都苦于译员不能传达他的意思。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用拉丁文给他们写下“相信上帝”“吾人之父”等句,再试图口头向他们简单解释信仰上帝的拯救的道理,同时强调尽管他们不懂得,但要坚决相信这些句子是真的。鲁氏指出自己只能这样做的原因是,“通过这样一个不懂如何翻译信仰的译员来谈信仰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且不说是不可能的”⑤同上,第257页。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东行纪》此句原译为“什么也不懂”。此句原文为:“for he did not know how”,结合前文鲁氏提及的译人对他说自己不会翻译宗教教义的情况,此处“how”应指“如何翻译教义内容”。是以改译。。
5.鲁氏晋谒蒙哥汗
1253年12月27日,鲁氏使团一行进入蒙哥的斡耳朵,并于次年1月4日首次受到召见。据鲁氏记载,在与蒙哥会面时,至少有两名译人在场,一位是哈莫·德依,另一位是蒙哥自己的译员,是一名聂斯托利派教徒。
就坐后,蒙哥首先赐酒,鲁氏小心翼翼地“尝了一点以示对他的尊敬”,但是站在对方管事旁边的哈莫·德依却对管事给他的许多酒来者不拒,“以致他很快就醉了”。①同上,第264页。对此,鲁氏再次表达了无奈。只有通过醉酒的哈莫·德依与蒙哥沟通。
在向蒙哥解释了来意之后,鲁氏恳请能够在他的营帐度过寒冬。这时蒙哥开始回答,但醉酒的哈莫·德依的翻译鲁氏只听懂了一句话即“如阳光之普照四方,我的权利,还有拔都的权力,也及于四方,因此我们不要你们的金银”。而此后的翻译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听不懂了”。而此时,“蒙哥本人看来也是醉醺醺的”,于是他只能尽力猜测蒙哥说话的意思。而且由于看到他的译员“无力翻译”,鲁氏“就不多说什么”,而只是请求蒙哥不要因为他提到金银而不高兴,因为他“只是想用尘世上和精神上的东西愉快地”向蒙哥表示敬意。②同上,第265页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不难推测,双方的译人都只负责将对方的语言翻译给本方听。因此,哈莫·德依醉酒并没有影响鲁氏向蒙哥表述自己的观点,但却严重妨碍到他对蒙哥谈话内容的理解,以致他只能依据译人翻译出的一鳞半爪的信息对蒙哥做出简单回应。至少就哈莫·德依来说,他虽然自称不擅翻译涉及宗教教义的内容,但在日常交流中进行双向翻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由此可以推断,上述做法是依循惯例,而非译员不具备双向传译的能力。即使在今天的谈判场合,这一做法也仍然屡见不鲜。
在此次会面后,蒙哥的译员告诉鲁氏他们被允在蒙哥的宫廷度过严寒。正是在此期间,鲁氏听说哈剌和林的金匠威廉·布昔尔(William Buchier)的养子是名优秀译员。向他介绍情况的是法国妇女帕库特(Paquette)。她还告诉鲁氏她听说蒙哥喜欢与他谈话,但认为“他们的译员太糟”。因此她向鲁氏推荐译员威廉。译员威廉曾有为蒙哥担任译员的经历。
鲁氏在此前的沟通中饱受译员不能胜任工作之苦,听此消息立即致信金匠威廉,询问他能否请他儿子来协助他。威廉一家当月正在忙于蒙哥的一项工作,不能成行,但答应下月前来。
1254年1月13日,蒙哥来到聂斯托利教堂,再次召见鲁布鲁克,“认真询问《圣经》、《祈祷书》中图画及其意义”③同上,第272页。。然而,因为鲁氏的翻译没有随他前来,无法回答蒙哥的问题。而只能由“聂斯托利教徒按他们的理解作答”。鲁氏此番再次错失了与蒙哥深入交流的机会。上次是因为他的译人醉酒,而此次则是因为仓促受到召见译人未随之前往,导致他无法与蒙哥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流。他的话语权只能交给他并不完全信任的聂斯托利教徒。
不过,译人的失职也可能成为一种借口。2月8日,鲁氏再次与蒙哥会面。这一次译员还是没有前往。他的同伴因为违背宫廷规矩而被拘押后,法官前来询问情况时,鲁氏就巧妙地利用了译员的缺席这一借口。他向法官解释说他的同伴因为没有译员而不了解宫廷的规矩。但实际上他们是很明白宫廷相关规定的。
鲁布鲁克再次见到蒙哥是在5月24日。此前,鲁氏向蒙哥提出如果使团返回欧洲,希望能安排在夏天。蒙哥得知后派人告诉鲁氏要跟他谈话,并提及鲁氏的译员“力不胜任”,要找金匠威廉之子来担任翻译。
于是,5月24日,鲁氏再次被带到宫廷。宫廷的大书记代表蒙哥询问使团来访目的。鲁氏表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福音,如果要他向蒙哥讲上帝的话,那就要把金匠威廉之子找来。对此宫廷书记说他们已派人去找他,但在当时只能尽量借助现场译员进行谈话。他们很懂得鲁氏的意思。鲁氏没有提及现场译员是蒙哥的翻译还是自己的译员,但是从交流结果来看,鲁氏还是认为译员不能准确传达他所要宣传的教义。于是他对书记说,如果能将金匠威廉之子派来担任翻译,他可以向蒙哥诵读上帝的戒律,以便他自己判断是否应遵行。
在鲁氏看来,此次交流由于缺少好的译人,又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效果。其实从上述三次鲁氏与蒙哥会面的情况来看,他都因为译人的原因而没有很好地表达他的本意。从沟通角度来看,他与听众之间没有实现顺畅沟通。
6.鲁氏参加宗教辩论
鲁氏在第三次面见蒙哥后的第二天,即5月25日,蒙哥的书记又来找他,要他与同在宫廷的撒剌逊①撒拉逊人系指从今天的叙利亚到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沙漠牧民,广义上则指中古时代所有的阿拉伯人。和脱因②脱因指佛教僧侣。举行宗教辩论会。
5月30日,众人在教堂聚集。鲁氏作为基督徒代表与脱因辩论。而脱因们则推举一名“来自契丹的人”跟他辩论。此次辩论,鲁氏终于有金匠威廉之子作为他的译人,而对方也有自己的译人。从鲁氏记述的他在此次辩论中的有力论证来看,他较为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点。
在对此次辩论的记述中,鲁氏没有像之前那样为翻译的不称职而困扰。与他自己的译人相比,金匠威廉之子长期在蒙古人的治下生活,浸染于多语言的文化环境中,尤其是他生长家庭的欧洲背景使得他对于鲁氏所要表达的宗教观点更为熟悉。此外,他还曾担任过蒙哥的译员,因此也具有更多的正式口译经验。
辩论后第二天,即5月31日,蒙哥再次召见鲁氏。同时还召见了与他辩论的脱因。此次进宫,担任译员的仍然是金匠威廉之子。在这次对话中,似乎是为了突出译人的作用,鲁氏在记述中至少两次提到蒙哥询问译人他所说内容。
译人的作用还不仅于此。金匠威廉之子在见蒙哥前,就提醒鲁氏说蒙哥已经决定遣使团返回,因此不要对此决定表示反对。而在交流之后,蒙哥陷入沉思时,译人又再次提醒他不要再多说话,以免导致蒙哥不快。
对比金匠威廉之子与哈莫·德依,他们虽然都充当了鲁氏使团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译人,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发挥了单纯的语言媒介作用,而后者的作用则不仅限于语言,还充当了文化中介的角色。在跨文化交流中,译员的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是相互依存、不可须臾相分的。翻译行为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它更需要文化的解码与转码。鲁氏之所以在哈莫·德依担任翻译时产生苦恼,正是因为译人的翻译行为仅停留在语言层面,无法传达语言以外的文化信息,从而导致沟通几近无效。而金匠威廉之子显然具有更多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口译经验,能够更好地传达鲁氏希望表达的宗教和文化意图。
三、鲁布鲁克对翻译作用的认识
1254年8月18日,鲁氏一行离开哈剌和林,携带着蒙哥致法王的回复及他根据译人翻译的回信大意。1255年初,使团在离开波斯统帅拜住后,使团向导便带着鲁氏的译人去见另一位波斯统帅阿儿浑。自此,可以说鲁氏与译人的合作关系正式解除。
鲁氏虽然没有提到他给予译人酬劳的事。但从他的记述来看,译人不仅分享了蒙哥夫人赠送鲁氏的布匹,并且后来在塞浦路斯换了钱,而且还在离开蒙哥汗廷前,分得了鲁氏获赠作为路费的五个艾索特③指重十马克的银锭。中的一个,“买了点可获微利的物品”,后来还“赚了些钱”。这些可以看成是鲁氏对他的翻译服务给予的回报。
此番出使经历使鲁氏深谙翻译对沟通的重要性。1255年2月2日,他来到艾尼城④961—1045年是艾美尼亚的首都。,遇见五名携带教皇信函正要前往蒙古传教的修道士。他们一如鲁氏,将请求蒙哥让他们在他的国土内居留,宣讲上帝的旨意。鲁氏根据自己出使的经验向他们介绍了蒙古的情况,同时告诉他们靠教皇的信可以在蒙古境内通行,但他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而且最好肩负传教以外的使命,因为从他自己的经历来看,“若无其他使命,只是传教,那鞑靼人会对他们缺乏理解”⑤《东行纪》,第323页。。说到这里,鲁氏特别强调,如果他们没有带翻译的话,那么就更难与蒙古人沟通交流。
鲁氏在长达两年的出使过程中,既体会到不称职翻译给他带来的诸多苦恼,也享受到高质量翻译协助他顺利沟通的服务。因此,在他致法王书信的结尾处总结此番出使经验时,也没有忘了提及翻译的作用。他告诉法王,今后再次派遣使团时,“使臣必须要有一个好翻译,最好几个,还要有充足的旅费,等等”①同上,第327页。。
鲁氏在出使过程中了解到蒙古统治者对欧洲的好奇以及对与使臣沟通的意愿。但他本人的经历却是沟通远不够充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译人不够称职。因此,他才在经验总结时不忘提及翻译的重要性。他甚至提出,最好有几个好翻译。可想而知,鲁氏从此次出使经历中意识到在不同文化交流时,译员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同等重要。一名译员的知识储备总归是有限的,而如果能有具备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名译员相助,出使任务才能够更圆满地达成。
余论
与之前出使东方的柏朗嘉宾使团类似,鲁布鲁克一行是欧洲在与东方陆路隔绝数百年后主动寻求沟通的又一次尝试。但是,与此前使团不同的是,鲁氏除携带法王路易九世信函外,并没有承担任何明确的使命。作为传教士,他本能地要传播教义、捍卫自己的信仰;而作为正在谋划与阿拉伯人战争的世俗君主的使者,他又自然而然地承担着窥伺蒙古人实力以寻求战略联盟机会的“秘密使命”。
鲁氏一行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一路东行,先后谒见了蒙古的王公贵族撒里答和拔都,并最后在蒙古大汗蒙哥的宫廷停留。从他与蒙古统治者的接触来看,沟通效果并不理想。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随团译人不称职。译人哈莫·德依是穆斯林教徒,但却担任了欧洲基督教传教士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传译工作。鲁氏与译人之间无论在宗教信仰、文化习惯还是行为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异,由此导致哈莫·德依多次不能合格地完成翻译任务也在意料之中。
在之前的《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及之后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都没有像鲁布鲁克这样多次以较大篇幅谈到翻译问题。《东行纪》也因此为我们提供了管窥中世纪译人角色与地位的一扇窗口。从鲁氏记述来看,他的译人除翻译任务以外,至少还承担了财务管理和保镖的任务。例如,在他离开蒙哥宫廷时,蒙哥赠送他旅费时,对方将旅费“放在我的译员哈莫·德依手里,叫他供给我作旅途的费用”。又例如,在他们谒见蒙哥前,门卫搜身,从译人身上搜出了匕首,显然是为防身和保护使团成员之用。
有意思的是,鲁布鲁克在《东行纪》中不仅提及了随团译人的不称职表现,同时还提到了一位在蒙古长大的欧裔译人的出色表现。金匠威廉之子长期生活在蒙古人统治区,对于欧洲宗教和蒙古文化都比较了解。早在鲁氏使团到访之前,他就曾为蒙哥汗担任过翻译。鲁氏在哈剌和林期间,坚持要求他担任他与蒙哥汗见面及宗教辩论的译人。较之哈莫·德依而言,金匠威廉之子显然是更好的译人。因为从鲁氏记载来看,翻译效果和翻译满意度都提高了不少。但金匠威廉之子显然除翻译外,也扮演着其他角色,如蒙哥的匠人、大汗的代言人等。
鲁布鲁克还提到了其他一些译人,其中有最初见到斯克台时贪小便宜的译人,见蒙哥汗时的聂斯托利派教徒,以及为达到自身目的而故意篡改路易九世信函的亚美尼亚人。
鲁氏的《东行纪》提及译人活动的记载有数十处之多,这在同时代的类似文献中是少见的。鲁氏一行在出使过程中所遭遇的沟通困难,应该也是同时代其他东西方使者的共同遭遇。虽然在没有专业训练,也没有职业标准的中世纪,译人的素质和翻译的质量无法保证,但毋庸置疑的是,译人的活动维持了东西方交流的良好态势。正是借助译人之力,才使得各色使团在在欧亚大陆通道上穿梭不息,铺下了东西方民族之间沟通交往的最初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