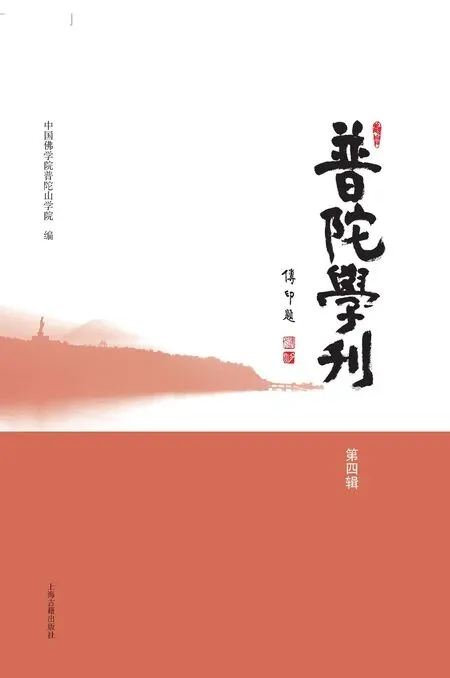从“朝圣”的演变看佛教发展
宗 慧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纵观佛教二千多年的发展,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朝圣者执著而坚定的身影。如义净大师的诗:“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时成百归无十,后者应知前者难。路远碧天惟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卍新纂续藏经》第76册No.1517《历朝释氏资鉴》,第190页a。他们悲愿宏深,为弘圣道,虽九死一生而矢志不渝。佛法之所以光被东土、后学之所以得闻圣道,实赖先贤之力。然而,朝圣之“圣”,往往名同而义异,随着时节因缘的变化。佛在世时,以佛为圣;佛灭度后,以圣迹和舍利等为圣;佛法传入中国,引起僧人西行求法、瞻礼圣迹的热忱,故以印度佛教为圣;隋唐乃至两宋,中国宗派兴起(尤其是禅宗兴盛后),往往以祖师和祖庭为圣;隋唐两宋之际,日本和朝鲜的僧人多朝礼中国,故以中国佛教为圣;明清之后,更多的普通民众加入朝圣队伍,尤其以“四大名山”代表的四大菩萨为圣。可以说,朝圣与佛教的发展相始终、互为表里,关系尤为密切。本文试图从朝圣的演变,考察佛教发展的特点。
一、 佛在世时
佛在世时,朝圣当然指对佛陀的朝拜。在巴利三藏《经集》的《彼岸道品》中,记载了住在南印度德干地方的跋婆犁(Bavarin)婆罗门的弟子十六人,听说佛陀的盛名,遂千里迢迢往中印度朝拜佛陀。他们由德干的波提陀那(Patitthana),经由阿盘提国(Avanti)的优禅尼(Ujjeni)、卑提冩(Vedisa),再经乔赏弥(Kosambi)、沙计多(Saketa)城,而到舍卫城。这条从德干到舍卫城的通道,称为“南路”(Dakkhinapatha),是自古的通商道路。但是当时释尊不在舍卫城,所以他们又经“北路”到达王舍城,在王舍城见佛闻法,成为佛弟子。*参见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台湾商周出版社,2002年,第53页。如《经集》的《彼岸道品》中说:
跋婆犁召集精通颂诗的婆罗门弟子,说道:“来吧,青年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些话,请听我说一位在这世上难以相遇的人,今天出现了,他以正等觉闻名于世,快去舍卫城,请教这位人中魁首。”十六位婆罗门弟子听了跋婆犁的话。……他们向跋婆犁致敬,施右巡礼;他们头束发髻,身穿兽皮,朝北方出发。他们先到阿罗迦的波提达那,然后经过摩希萨帝、优禅尼、瞿那陀、吠地萨、婆那萨诃耶,又经过乔赏弥、娑盖多,城中之冠舍卫城、塞多维耶、迦毗罗卫、鸠希那罗城。又经过巴婆、薄迦城、吠舍离、摩揭陀城。到达美丽可爱的石寺。犹如口渴者盼望凉水,商人盼望营利,炎热者盼望树荫,他们快步登山。这时,世尊正在僧团中向众比丘说法,犹如林中的狮子发出吼声。阿耆多看到,这位正等觉像没有光线的太阳(指和煦的太阳),像十五的圆月。*《经集》,金陵刻经处印,第156—158页。
然后,世尊面对这十六个婆罗门弟子的提问,一一作了解答。那些领会了佛陀法义的人,依法而行,就能到达生死的彼岸,因此这品被称为“彼岸道品”。从《阿含经》的诸多记载中,我们发现那个时期的朝圣,其主要内容是:为了寻求解脱而“问法决疑”。人们见佛陀后,往往先礼拜供养,而后提出心中疑问,请佛解答。闻法之后,则力行实践,修行解脱。他们因闻法而证果的,比比皆是。这种佛世时闻法的殊胜因缘,常令后世的佛弟子们自责和嗟叹。如隋代的释法充感叹:“生不值佛,已是罪缘。正教不行,义须早死。”*《嘉兴大藏经》新文丰出版社,第23册No.B122《醒世录》,第162页b。经书中把生在佛前佛后、生于边地等,皆被称为八难之一。《中阿含·八难经》说:
若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世说法,趣向止息,趣向灭讫,趣向觉道,为善逝所演。彼人尔时生畜生中、生饿鬼中、生长寿天中、生在边国夷狄之中,无信无恩,无有反复,若无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谓人行梵行第五难、第五非时。*《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No.0026《中阿含经》,第613页b。
此“边国夷狄”即常说的“边地”,乃是相对“中国”而言。中国,在佛经中指的是佛法盛行之地、佛教中心之地。这在古印度,主要是指以摩揭陀、乔萨罗为中心的区域。佛经还指出诸佛出世,唯生于“中国”(佛法盛行的区域),不生“边地”(佛法落后之区域),故值遇佛者亦以生于中国者为限。即便生在中国,又值佛世,还要排除聋盲喑哑等障缘,才能真正朝拜佛陀、亲聆佛法。
二、 佛灭度后
佛灭度后,朝圣的对象以佛陀的圣迹、圣物为主。圣迹如佛陀诞生处蓝毗尼、佛陀成道处菩提伽耶、佛陀初转法轮处鹿野苑、佛陀涅盘处拘尸那,以及舍卫城、曲女城、王舍城、毗舍离、灵鹫山等等。圣物如佛舍利、菩提树、金刚座、佛的衣钵等等。圣严法师说:
佛陀本生故事所在地、佛陀住世时的各种游历行化所在地的纪念遗迹,均有塔寺等建筑物,供给佛教徒们作供养礼敬的场所。而且不论是大乘或小乘各派,都把佛的遗骨、遗物、遗迹,视作信奉的中心……从《佛国记》中的记载所见,佛灭之后的西域印度,供养礼敬佛的遗骨、遗物、遗迹,乃至罗汉圣者的遗骨、遗迹,已是普遍的现象。*圣严:《法显大师对于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及启示》,收在《戒幢佛学》第3卷,岳麓书社2005年1月第1版,第5—6页。
佛涅槃后,由大迦叶主持荼毘典礼,烧出的舍利,由拘尸那、摩竭陀、释迦等八王,各分一份,归国供养。八王为之建塔,供佛弟子瞻仰礼敬。据《高僧法显传》载,佛入灭后一百年,阿育王欲悉数取回根本八塔中的佛舍利,然遭龙族妨害,未取得置于蓝摩国塔者。所收的其余七塔舍利,则细分至各地,立塔安置之。法显、玄奘等西行求法时,尚且目睹许多阿育王所建之塔。然此诸塔,以岁月久远,皆渐湮灭。
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朝圣莫过于阿育王的朝圣。据载,阿育王依优波毱多之劝而一起朝礼佛陀遗迹,开始“法的巡礼”。即位后第二十年,巡礼佛诞生地蓝毗尼园,初转法轮地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等圣地,以及舍利弗、目犍连、阿难、大迦叶的遗迹,并于各地布施、建塔。他在蓝毗尼朝拜之处,还树立石柱,上刻碑文。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六说: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侧不远,有大石柱,上作马像,无忧王(即阿育王)之所建也。后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东南流,土俗号曰油河。是摩耶夫人产孕已,天化此池,光润澄净,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风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No.2087《大唐西域记》,第902页b。
现该柱存高约七公尺,柱头马像已失,柱体有裂缝一道,似系雷击所致。石柱离地三公尺处,有阿育王法敕云:“天佑慈祥王于登位二十年亲自来此朝拜,因此处乃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兹在此造马像、立石柱以纪念世尊在此诞生。并特谕蓝毗尼村免除赋税,仅缴收入的八分之一。”阿育王在这里亲自举行供养,建立石柱,并下令减免此地百姓的赋税。他还在鹿野苑的石柱上刻有与诫止僧伽分裂等有关的“法敕”,其柱头雕有四匹巨大的背对背的狮子像,正下方置有法轮。这个石柱的图案如此精美、举世罕匹,乃至成为现代印度国家的徽章。*参见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台湾商周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这种对舍利(佛塔)的庄严和对圣迹的巡礼,启发和影响了“理想的佛陀观”的形成。如印顺法师认为:
舍利塔是象征佛陀的。佛法以三宝为归依处,而佛却已过去了,为众生着想,以舍利塔象征佛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香、华、璎珞、伞盖、饮食、幡幢、伎乐歌舞等供养舍利塔,佛教开始有了类似世俗宗教的祭祀(天神)行为。释尊在世时,饮食以外,是不受这类供养的;现在已入涅槃了,怎么要这样供养呢!难怪有人要说:“世尊贪欲、瞋恚、愚痴已除,用是塔(庄严……歌舞伎乐)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No.1425《摩诃僧祇律》,第497页c。括号内字为印顺法师加。?”这是不合法的,但为了满足一般信众的要求,引发信众的信心,通俗普及化,佛教界一致的建塔供养。而且,塔越建越多,越建越高大庄严;塔与僧寺相关联,寺塔的庄严宏伟,别有一番新气象,不再是释尊时代那样的淳朴了!这是释尊时代没有的“异方便”之一;宏伟庄严的佛塔(及如来圣迹的巡礼等),对理想的佛陀观,是有启发作用的。*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正闻出版社,2005年4月修订版,第33—34页。
因此,对圣迹(如鹿野苑等)和圣物(如佛舍利等)的崇敬礼拜,引发了佛教观念上的转变,迎来了佛教发展新的契机。印顺法师认为,世尊入灭了,在“佛弟子的永恒怀念中”、“世间情深”,不能满足于人间(涅槃了)的佛陀,依自我意欲而倾向于理想的佛陀,这成为了大乘佛法的兴起的重要因缘。*同上书,第84页。
佛灭后数百年间,佛弟子礼拜的对象是供奉释迦遗骨的舍利塔,并不直接出现佛像。在描绘释迦事迹的佛传图中,则以菩提树象征佛陀成道,以法轮、金刚座象征佛之说法,以足迹表示佛陀之游化,并未用人像来表现佛陀。直到贵霜王朝兴起后,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才出现了佛像的雕刻。首先用人像表现佛陀的是公元一世纪的犍陀罗,其次为摩突罗。印度早就有守护神的制作,在表现佛像的技术上并无困难,为何其早期不制作佛像呢?吕澂认为:
至于雕刻佛之行迹,则纯用象征方法,如以小鹿象征佛之诞生,以马象征其出家,以菩提树象征其成道,以法轮象征其说法,以塔象征其灭度,完全无佛本身之像。由当时雕刻之技术云,雕刻人像并非难事,而故意避开,别取象征法代之者,或系出于对佛之崇敬,以为佛之形象圆满无可比拟也。是亦一种理想主义之表现。*吕澂:《佛教美术》,收在《法音》杂志,2003年第1期,第22页。
其实不以佛像表现,这更符合佛法的精神。因为佛经说:“当观诸法皆从缘生。若能见法即见如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1册No.0316《佛说大乘菩萨藏正法经》,第814页a。。”学佛重点在佛所领悟的法,而不是胶泥某种事相。如扬之水《桑奇三塔》中说:
这里彰显的不是偶像,而是觉悟者的觉悟,他的说法以及他说的法。以不表现偶像的方法从事佛教艺术,可以更多地保存佛教的本质,使信众的敬仰之心不是落在一个具体的形象,而是这一位圣者所证悟的真理,正如佛陀不断的教诫——重要的是自身之修为。*扬之水:《桑奇三塔》,三联书店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2页。
犍陀罗佛像艺术的兴起约在公元一世纪,与大乘佛教的兴起时间相符,这印证了印顺法师的观点:大乘佛教的兴起的主要动力,是由佛弟子心中的无比怀念,这种崇敬佛陀的内心力量,事相上则表现为巡礼圣地、朝拜舍利、佛像制作,义理上则启发了大乘佛法的兴起。
三、 西行求法
由印度到中国谓之传法,由中国到印度谓之求法。传法者,如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澄、鸠摩罗什、菩提达摩等等。求法者,如朱士行、法显、智严、宝云、法领、智猛、法勇、玄奘、义净等等。传法与求法恰好成了一个回路,见证了佛法传入中国,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和繁盛的过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说:
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如支法领),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如于法兰智严),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如宝云智猛),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如支法领)。然其去者常为有学问之僧人,故类能吸受印土之思想,参佛典之奥秘。归国以后,实与吾国文化上以多少贡献,其于我国佛教精神之发展,固有甚大关系也。西行求法者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最盛。
据贺昌群先生统计:“总计西行求法有中国僧徒,见于僧录史传的,自第三世纪朱士行以至第十世纪的继业,得一百零七人。”*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第27页。中国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为朱士行,他因为读《道行般若》觉得翻译尚未尽善,感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梁慧皎:《高僧传》卷四,汤用彤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1版。遂于甘露五年(260)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至于阗。在那里,他求得《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遣弟子送归,经竺叔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经》。但他终老于阗,并未真正到达印度。真正到达印度、求法回国者,当以法显为最早。如汤用彤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下面谨以法显为例,一窥求法者的风骨。
法显三岁出家,二十受戒。他因感叹律藏残缺,誓志寻求印度律典。弘始二年(400),已是六十多岁的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一同去的,先后有十人,他们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最后只有法显一人历西域、度流沙、翻雪岭,先达北天竺,经西天竺,到达中天竺,然后经东天竺,乘船抵达狮子国(今斯里南卡),并由狮子国登商船,取道海陆归国。前后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其间他朝拜了许多佛陀的圣迹,如《佛国记》云:
昔天帝释试菩萨,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既成道与诸弟子游行,语云:“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国人由是得知,于此处起塔,金银挍饰。……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大塔,金银挍饰。……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挍饰。……城北双树间,希连禅河边,世尊于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须跋最后得道处,以金棺供养世尊七日处,金刚力士放金杵处,八王分舍利处,此诸处皆起塔,有僧伽蓝今悉现在。……阿育王坏七塔作八万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余,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城东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连初见頞鞞处,尼犍子作火坑毒饭请佛处,阿阇世王酒饮黑象欲害佛处,城东北角曲中耆旧于庵婆罗园中起精舍,请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养处。今故在。……法显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到耆阇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抆泪而言:“佛昔于此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No.2085《高僧法显传》(佛国记)。
法显在中天竺,一边学习的梵文,一边抄录经律,在摩诃衍僧伽蓝抄得最完备的《摩诃僧祇众律》,又抄得《萨婆多众钞律》(即《十诵律》)约七千偈、《杂阿毗昙心》约六千偈、《方等般泥洹经》约五千偈及《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后来在狮子国又抄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经》等。归国后,在南京道场寺,他与外国禅师佛驮跋陀,共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毘昙心》等。他取回及其翻译的经律,对中国的律学、佛性思想等影响深远。后人赞叹法显云:
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同上书,第865页c。
法显是印度求法的拓荒者,他的信心和勇气,给世人深刻的印象,鼓舞了许多后来的求法者。如玄奘说:“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能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自当继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No.2052《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第214页a。而义净年始十七即“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No.2061《宋高僧传》,第710页b。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写道:“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显法师则开辟荒途,奘法师则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莫不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俱怀旋踵报四恩以流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No.2066《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页a。其中的“咸思圣迹罄五体而归礼”,正是无数西行求法者最核心的原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僧传中可以看到许多求法者都有深刻的“边地情结”。如法显的《佛国记》云:“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No.2085《高僧法显传》(佛国记),第863页a。又如《续高僧传》记载玄奘到达伽耶山时:“奘初到此,不觉闷绝。良久苏醒,历睹灵相,昔闻经说,今宛目前。恨居边鄙,生在末世,不见真容,倍复闷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No.2060《续高僧传》,第448页b。对此陈金华分析说: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僧人(即使是像玄奘这样才具卓越者)总是油然生起一种强烈的自卑和焦虑感,因为与印度高耸的形象相比,他们的国家卑居边鄙,相形见绌。在佛教的世界观中,印度总是被置于宇宙的中心,像中国这样的“次要”国家只被保留在边鄙。当中国、日本或朝鲜的僧人涉及印度或中国时,一个深刻的“边地情结”困扰着他们。那就是:如何克服本国与印度之间似乎遥不可及的距离。这距离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相对于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印度,印度次大陆之外的亚洲各地都是边缘地带。这种边缘意识,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相互矛盾的情感集合体(complex)。首先,与佛陀出生地的距离会给予印度之外的佛教徒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可以强化为焦虑,失望,乃至绝望。同时,这种距离感也有可能转化为对作为佛教中心的印度产生倾慕之情,从而生起效仿与学习的精进之心。接着,当这种学法的热忱达到某种程度时,自卑,企慕,上进之心便会转化为自信。最后,这种自信有时会膨胀到以边缘不异中心,甚至超过中心的意识。这种“边境/边地/边国/边地情结”(Border land Complex)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东亚僧人的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影子。*陈金华:《东亚佛教中的“边地情节”:论圣地及祖谱的建构》,《佛学研究》2012年总第21期,第28—29页。
其实,这种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就像是“学习”的动态过程。古人说“学者,效也”。学习的开始,总是仿效。但随着时空的推移、因缘的转变,则“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种人与人的师弟关系,对应在地理空间上,也就是中心和边缘的转化。就如曾经的印度和中国,或曾经的中国与日本。而且学习或传授,不是一种单行线,而是“教学相长”,双向流动。悄然转化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亦所在不鲜。
四、 宗派兴起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从微至著,在国人的心中,渐渐从表象的“淫祀”、术数一类,而转入理性的深层求索。随着国人极大的求法热忱和规模宏大的译经事业,佛法的精神渐渐深入人心。义理的诠释方式,也从附和于玄学的格义而渐渐进于一经一论的系统研究。又从接受吸收,到综合消化,到把握精髓……终于中国祖师精思入神、开创宗派。隋唐之际,天台、三论、净土、华严、唯识、禅宗、律宗等相续成立。对于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关系,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近人常说中国佛教如何如何,印度佛教如何如何,好像有两个佛教似的。其实只是一个佛教之继续发展。这一发展是中国和尚解除了印度社会历史习气之制约,全凭经论义理而立言。彼等虽处在中国社会中,因而有所谓中国化,然而从义理上说,他们仍然是纯粹的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命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他们并无多大的影响,他们亦并不契解,他们亦不想会通,亦不取而判释其同异,他们只是站在宗教底立场上,尔为尔,我为我。因而我可说,严格讲,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只是中国人讲纯粹的佛教,直称经论义理而发展,发展至圆满之境界。若谓有不同于印度原有者,那是因为印度原有者如空有两宗并不是佛教经论义理之最后阶段。这不同是继续发展的不同,不是对立的不同;而且虽有发展,亦不背于印度原有者之本质;而且其发皆有经论作根据,并非凭空杜撰。如是,焉有所谓中国化?*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学生书局印行,2004年6月修订版,序言第4—5页。
宗派兴起后,朝拜祖师和祖庭,成为朝圣的一种新形式。如天台宗的道势禅师,“幼负材器,遍参知识,凡所入室莫投其机,及见智者于玉泉,*湖北丹阳玉泉寺。隋代开皇十二年(592),智者大师为报地恩而创建。次年四月,智者大师于此讲《法华玄义》。文帝原敕寺额“一音寺”,后改为“玉泉寺”,以其由洞穴出水,注凝为泉,色似琉璃,味如甘露,故称玉泉。开说止观,顿获妙悟”。*《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No.2035《佛祖统纪》,第199页c。又如陈朝尚书左仆射徐陵:“尝梦其先人曰‘(智者)禅师是吾夙世宗范。汝宜一志事之。’*同上书,第200页b。陵奉冥训,资敬尽节。参不失时,拜不避湿。每蒙书疏则洗手焚香,冠带三礼,屏气启封,对文伏读。”又如唐代的善导大师,他常依《观经》修十六观,因仰慕慧远结社念佛的高风,遂亲往庐山东林寺叩寻古德遗踪。后更周游各地,访问高德。闻道绰在玄中寺盛弘净土,即于贞观十五年(641)前往朝拜。其时正值严冬,善导风餐露宿、倍极艰苦,道绰悯其远来,即授以《观经》奥义。
这种朝圣的行为,甚至表现在信众死后。如三阶教兴起后,其祖师信行和他的终南山墓地,都成为信徒的朝圣对象。如《道安禅师塔记》:
大唐故道安禅师,姓张,雍州渭南人也。童子出家,头陀苦行,举三阶集录,功业成名,自利既圆,他利将毕。以总章元年十月七日,迁形于赵景公寺禅院,春秋六十有一。又以三年二月十五日,起塔于终南山鸣塠信行禅师塔后,志存亲近善知识焉。*《道安禅师塔记》,见《金石萃编》卷五十七,第19页。
又如,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8)的薛夫人卢未曾,生前师事大智禅师,死后建塔于龙门西冈,其塔铭云:
自宗师大智,茂修禅法……先是未疾之辰,密有遗嘱,令卜宅之所,要近吾师,旷然远望,以慰平昔。*《薛氏婆夷功德塔铭》,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十六,第13—14页。
道安禅师建塔于信行塔侧,为的是“志存亲近善知识焉”。薛夫人卢未曾“密有遗嘱,令卜宅之所,要近吾师,旷然远望,以慰平昔”。这些无疑都是朝圣祖师之心的具体体现。
尤其是到了禅宗兴盛之后,朝拜祖师和祖庭更是达到了极盛。如雪峰义存禅师(822~908)“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后仍缘契德山”。*《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No.2037《释氏稽古略》,第846页c。说他三次登投子山朝拜义青禅师,九次到江西洞山朝拜洞山良介禅师,最后才在德山宣鉴禅师那里悟道。又如圆悟克勤禅师的出川:
圆悟,西川成都府昭觉寺禅师,名克勤。彭州骆氏子,世宗儒。儿时日记千言。游妙寂寺,见佛书有感,遂出家。依师自省祝发,从文照法师通讲说,又从敏行授楞严。出蜀首谒玉泉皓,次依金銮信、大沩喆、黄龙、晦堂心、东林总,皆称美之。晦堂曰:“他日临济一派属子矣。”最后到蕲州,谒演禅师于五祖山,尽领其奥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No.2037《释氏稽古略》,第882页a。
这段话讲了圆悟克勤禅师徒步出蜀、遍参禅德的参学历程,先后参拜的祖师有:玉泉承皓、金銮信、大沩喆、黄龙慧南、晦堂祖心、东林总,最后得法于法演禅师。这种参拜祖师的盛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缘于经论中一再强调的善知识的重要,如《法华经·妙庄严王品》云:“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09册No.0262《妙法莲华经》,第60页c。《有部毗奈耶杂事》甚至把善知识称为“全梵行”:“阿难陀言:‘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办。得善友故,远离恶友,以是义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佛言:‘阿难陀,勿作是言,善知识者是半梵行。何以故?善知识者是全梵行,由此便能离恶知识,不造诸恶,常修众善,纯一清白,具足圆满梵行之相。由是因缘,若得善伴与其同住,乃至涅槃事无不办,故名全梵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册No.1451《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第398页b。(二)禅宗强调的心外无法、以心传心、当机指点。如二祖的求“安心”即是。欲求心之解脱,当然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寻求明心见性者的指点了。因为心无方所,不能在文字上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只有在那些悟道祖师的鲜活智慧中,当下求其点拨了。
唐宋之时,源于古印度佛教的“巡礼”,在中国僧人中蔚然成风。“巡礼”,就是指巡回礼拜佛菩萨、祖师等圣迹。僧人们云游参学,除了参拜高僧大德外,还包括朝拜佛教祖庭和名山。唐末逐渐形成了云游僧人汇集的四个中心:五台山文殊菩萨圣地、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大圣圣地、终南山三阶教圣地、凤翔法门寺佛骨圣地。南宋宁宗时,由于史弥远的奏请,始定江南禅寺之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以五山位在所有禅院之上,十刹之寺格次于五山。钦定“五山十刹”作为禅僧的游方参请之地。以杭州径山的兴圣万福寺、灵隐山的灵隐寺、南屏山的净慈寺、宁波天童山的景德寺、阿育王山的广利寺为“五山”;以杭州中天竺的永祚寺、湖州的万寿寺、江宁的灵谷寺、苏州的报恩光孝寺、奉化的雪窦资圣寺、温州的龙翔寺、福州的雪峰崇圣寺、金华的宝林寺、苏州虎丘的灵岩寺、天台的国清寺为“十刹”,成为禅徒游方参请集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四个中心”还是“五山十刹”,其地点皆在中国,而非印度。可见,佛教的演变中,已经由“以印度和印度祖师为中心的佛教”,转而成为“以中国和中国祖师为中心的佛教”,这尤其以禅宗的兴盛为其成熟的标志。这充分反映在从恨居边鄙、西行求法到自立自足、参拜祖师祖庭的转化上。
五、 入唐(宋)求决
公元8世纪后,印度的佛教日渐式微,而中国佛教则诸宗并弘、蒸蒸日上。此消彼长之间,中国佛教已然取代了印度佛教的中心地位,成为世界佛教的朝圣地。古人到印度求法,今人则到中国求法。不仅日本、朝鲜的佛教由中国传入,而且他们的僧人也以巡礼中国为荣。隋唐至两宋,五六百年间,大批的日本、朝鲜僧人入中国参学求法,他们回国后,开创了本国的佛教宗派。当时的中国,是真正佛教的中心。
如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的最澄大师为深究法华一乘教义,经桓武天皇的允许,以“天台法华还学僧”的身份,与空海同行入唐求法。他们从明州(今宁波)后,到达台州龙兴寺,正逢道邃大师宣讲《摩诃止观》,遂从受学天台教观,并受大乘“三聚大戒”。后又往天台山参拜,从行满大师修学,终获其法,并得天台教典82卷。他还向牛头宗翛然问禅,后又从顺晓受密法。回国时,行满大师为最澄写“印信”:
日本国求法供奉大德最澄法师……求妙法于天台,学一心于银地。不惮劳苦,远涉沧波,忽夕朝闻,忘身为法。睹此盛事,亦何异求半偈于雪山,访道场于知识,且行满倾以法财,舍以法宝,百金之寄,其在兹乎,愿得大师以本愿力,慈光远照,早达乡关,弘我教门,报我严训,生生世世,佛种不断,法门眷属,向一国土,成就菩提,龙华三会,共登初首。*行满:《付法最澄法师书》,《邻交徵书》二编卷之一,第11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台州刺史陆淳也亲自为写“文证”。其词曰:
最澄阇黎,形虽异域,性实同源,特禀生知,触类玄解。远传天台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犹虑他方学徒未能信受,所请印记,安可不以为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No.2061《宋高僧传》,第891页a。
从文中可知,最澄回国前,为了取得自己真实得法的凭证,向道邃、行满、刺史陆淳求取“印记”。无此,担心回国后人们不信。可见中国祖师的传法印可,代表着佛法的正统性、合法性、神圣性。最澄归国后,在比睿山大兴佛法,正式开创日本佛教天台宗。
又如日本的圆仁大师(794~864),十五岁登比睿山,师事最澄。后经众僧推举,获选入唐“请益”。在扬州与宗睿邂逅相遇,跟他学习汉梵二语,又跟全雅受灌顶,并得到金刚大教及曼荼罗。到达五台山以后,朝拜了文殊菩萨圣容,许愿建造文殊阁。跟五台山的志达、玄鉴,以及醴泉寺的宗颖学圆教止观的玄旨,并跟宝月三藏学习悉昙。他在长安期间,参见了元政、义真、法全、元侃、宝月、义操、法润等人。他还跟净影寺的惟谨学习密教。他在唐前后十年,归国后,他首次在食堂设置天台大师供,在总持院发起舍利会,又效仿五台山竹林寺之风,修净土院庙供,改传法华忏法,兴起不断念佛。成为继最澄创业后,集日本天台宗之大成者。圆仁把求法的经历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记》,后人将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
而且日本的僧人遇到难以解决的疑问,往往也以中国祖师的决断为凭信。如唐朝时,日本圆载持天台众疑五十科,访天台山禅林寺的广修等法师,请求答疑。又日僧源信遣弟子寂昭“入宋求决”,《四明教行录》云:
日本国师问,四明法师答。皇宋咸平六年癸卯岁(1003),日本国僧(寂照)等,赍到彼国天台山源信禅师于天台教门致相违问目二十七条。四明传教沙门(知礼)凭教略答,随问书之。(其来书云)诸方匠硕,或一披览,无吝斤削云。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恭投函丈,伏冀垂慈,一一伸释,不胜至幸。日本国天台山楞严院法桥上士位内供奉十大禅师源信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No.1937《四明尊者教行录》,第885页b。
不仅大批日本朝鲜的僧人,入唐(宋)求法,而且就如安世高、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入中国传法一样,中国的祖师如鉴真等也东渡日本传法。日本的入唐僧荣睿和普照,以日本传戒无人,故恳请鉴真律师东渡传法。然前五次东渡,皆因国人不舍高僧东游,又遭受海盗、暴风等而未能成行,其间颠沛长达十一年之久。后虽双目失明,却不稍减其赴日之志。直至第六次东渡,才获成功,其时鉴真已六十六岁。他依道宣之戒坛图经,于日本东大寺毗卢遮那佛前营建戒坛,师亲为君民上下传授菩萨戒,又为日僧重授戒法,此为日本登坛授戒之嚆矢。天皇尊以“传灯大法师”的称号。无论求法还是传法,都同样表明了中国佛教作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中心地位。佛教的中心,已当之无愧地转移至中国矣。这与初期的“边地式的自卑”,已迥然若天渊之别。
六、 明清之后
明清之后,随着佛教的式微,以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佛教越来越平民化和民间化。传统的祖师和祖庭的朝拜,虽然依然存在,但其影响已日趋衰弱。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更多的普通民众加入朝圣队伍,尤其是以“四大名山”为代表的朝圣。只是他们朝圣的目的更多是世俗的安乐,而非出世解脱。
明清以来佛教的衰微,可由师资的低落窥见一斑。对此,湛然圆澄禅师的《慨古录》的描述极具代表性:
诸方各刹,上堂普说,概之不闻。间有一二榷商者,不过依经傍教而已。其次皆世谛流布,不足听也。悬说悬谈,抽钉拔楔,举世不闻。非谓故不谈也,此事非亲证亲悟,莫之能矣。大抵丛林多有不识字者主之,其领徒不过三等:上者劝其作福;次者令其应务;再次者平交而已。其贤者不耻下问,向徒弟学经。其不贤者,恐弟子处我之上,见其习学,怒云:“你不老实修行,学此拟装大汉耶?”又云:“学此口头三昧奚为?何不老实修行!”又有一等,宗教曾不之闻,出家又且不久,便去守山,或复坐关,称善知识,诳唬人者。*《卍新纂续藏经》第65册No.1285《慨古录》,第369页b。
可见当时善知识的稀缺,丛林之主持多有不识字的。师弟授受之道亦坏,不仅自己无知无识、无修无证,还阻碍徒弟学习,甚至嫉妒他超过自己、妨碍驾驭。更有一班装模作样的、唬人的善知识。如此的佛教气氛下,原先寻师问道、参禅决疑的风气自然行不得了。很多时候,参访祖师,已经变得无师可参。缺乏了佛法研习和实践的寺院,价值取向很容易就滑向现世的、功利的追求,则寺院再怎么建得华丽,也只是招揽俗客的观光地而已。
明清佛教之世俗性倾向,必须溯源于唐代佛教思想的一场大变革,即六祖慧能的禅宗思想。原始的佛教否定现世的价值,是极度出世的取向。而新兴的禅宗,使佛教教义有了“入世”的转向。如《坛经》云:
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No.2008《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第352页b。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同上书,第351页b。
最早慧能大师的话语,只是不把此世和彼世不看做截然的二分;虽然肯定现世的价值,而它的根却是植于‘出世’的,依然以佛法的解脱和悟道为本怀。而明清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异化,变成了舍本逐末,甚至是徒有末而无本了。由慧能大师发端的肯定现世价值的转向,经五代、宋、元,不断被扭曲异化,到明清之际,这种发展已到烂熟,其弊端也展露无遗。湛然圆澄禅师的《慨古录》云:
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卍新纂续藏经》第65册No.1285《慨古录》,第369页b。
古时檀越人家有丧事,师僧往吊,必登座说法以资亡者,其次则远棺念佛,并无跪拜之礼。今之沙门,不体古规,毋论男女老少,一往拜礼。吾不知于礼是耶。夫沙门之体,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戒经有不拜父母之说。父母劬劳,尚云不拜。彼少年男女,有何恩德,一槩礼拜。可为一笑。*同上书,第373页c。
世称焰口,即相应之法。所言相应者,乃三密严持之谓也。口密诵咒,手密结印,心密观想。是以古师授受,必择行解相应,堪绍灌顶者,方为传授,如缘起文中所说。……近来新学晚辈曾不坐禅,又不习观,但学腔科,滥登此位。非唯生不可利,仍恐损己福祉耳。不可不知。*《卍新纂续藏经》第65册No.1285《慨古录》,第374页a。
这种民间化佛教的描述,在明清小说中也常常作为负面形象被人诟病。如《西游记》第三十六回中,寺院的主持,只愿意接待富有的施主,而不愿接受贫穷的行脚僧的挂单。第九十八回,甚至描写了取经的最后关头,迦叶、阿难二尊者,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贿赂)。
另一方面,明清商品经济较宋元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明代后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一是因为新禅宗、新儒家、新道教的入世转向,引起社会观念、伦理观念的转变,促进了商人地位的提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参考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259页,联经出版社,1987年3月初版。二是因为西方航海大发现,引发的全球海洋贸易时代的来临。中国虽然遥隔欧洲,依然不免卷入此一大潮。三是隆庆开关后,对外贸易的繁荣。尤其是中国有着西方孜孜以求的稀缺商品:丝绸、茶叶、瓷器等。在明朝后期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据学者全汉升统计:
在17世纪早期的好年景时,每年进口的白银总数价值在200万至300万比绍(57500~86250公斤白银),但涉及的数量可能要大得多。*《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373页。
总之,明清的小品文里,充满了对个体体验的赞美和肯定。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把个人的良知肯定,作为个体觉悟的依据。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地位提高,市民阶层的力量兴起。平民大众,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财力,从事精神追求和娱乐。同时,商品经济的网络,也使得道路交通得以进一步发展……这种种因素,都为民间化的、大众化的朝圣创造了条件。
宋朝的“五山十刹”只在教内流行,并没有被民间接纳。被民间普遍接纳的是渐渐形成的“四大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周叔迦先生说:
到了明代这些山刹(五山十刹)久已衰歇,当时佛教界中也少有可以指导群方的尊宿大德,于是在佛教徒中出现了参拜名山的习惯。一般佛教徒集中参拜的地方是四大名山:一是山西五台山,二是浙江普陀山,三是四川峨嵋山,四是安徽九华山。四山之中以五台山为最有名。明代曾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嵋,铁九华”之说。*周叔迦:《法苑谈丛》,见《周叔迦佛学论著全集》第三册,中华书局出版,第1039页。
需要注意的是,四大名山的朝拜,并非明清才有。早在唐代,五台山的朝圣就达到了鼎盛。早在宋代,峨眉山也曾盛极一时。其“名山”的声望,大致而言,五台山最早,峨眉山其次,普陀山其次,九华山最后形成。本文只是说明:(一)“四大名山”格局,直到明清才真正形成。“四大名山之说,出现较晚,是在九华山佛教达到鼎盛时才见诸文字的,时间大约在清代康熙(1662~1722)年间。”*参见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三卷下,2010年11月第一版,第790页。(二)民间化、大众化地朝拜名山,是在明清时期才形成。这种朝圣的路线,有着中心向边缘流动的趋势:在地区内香客的流动往往与商业活动的流动方向相反。商人从农村地区收货沿河下行运至地区中心,而香客则从行政治地转向圣山所在地的半外围地区。*参见《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601页。
这种朝圣的人员,有僧侣,有士绅,更多的是平民大众。这种朝圣的形式,有个人的,有团体的:对大部分俗人来说,朝圣被组成集体,而不是个人的宗教活动。这些群众性朝圣活动在村一级组成,以共同认捐的钱财预付费用,所去之地是某一重点朝圣地。朝圣活动似乎常常由妇女率领,其实它就是妇女能享受长途旅行的唯一机会。*参见《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601页。
当然,四大名山的形成,还与帝王支持有极大的关系。其中,除了信仰的因素,还有着地缘政治的考虑。如印顺法师云:
又如四大名山:普陀山兴起于日本之慧锷,九华山兴起于新罗之地藏,五台山地接北胡,峨嵋山则处西南夷,历为蒙、藏信仰重心。我国佛教得力于外族同化及边地民族,亦即有助于民族间之协和同化也。*印顺法师:《妙云集》下编之十《华雨香云》,第199页。
普陀山之于日本(梁贞明中,日僧慧锷开山);九华山之于新罗(唐高宗时,新罗僧地藏开山);五台山之于北狄(五台久为名德所居。后宋太平兴国五年——九八〇,往毘邻大辽之五台山,造金银铜文殊像及万菩萨像,于五台重修十寺,并意在抚边);峨嵋山之于吐蕃、南诏。*印顺法师:《妙云集》下编之九《佛教史地考论》,第73页。
边地民族和国家,多数都信奉佛教。而圣地既然在中央王朝的地域,自然可以增加民族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平抚边地民族和国家的敌对性。同时也得以提升中央王朝的威信和声望,中央王朝得以恃佛而重。
对于朝拜四大名山,祖师们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虽然,很多的祖师强调真正的观世音道场,其实是在每个人的内心,而不必一定要去普陀山。认为出家之初,信念不固,不宜多涉外缘。但也有很多祖师认为,朝圣是参师访友、忏悔身心、澡雪精神、砥砺信念的极好的修行方式。莲池大师认为“心地未明,正应千里万里亲附知识。何得守愚空坐,我慢自高?”*《卍新纂续藏经》第68册No.1319《御选语录》,第593页c。应先行万里路,交天下有识之士,才能心志豁然开朗。心志豁然开朗,才能与菩萨道、大乘智慧相应。否则,坐守顽愚,虽筋疲力尽,也未必有益。
结 论
通过对上述六点的综合比较,我们可以由朝圣的演变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佛教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心可以变为边缘,边缘也可以变为中心。此消彼长,悄然兴替。无论中心还是边缘,都在因缘的法则下,无常变迁。没有永恒的中心,也没有永恒的边缘。二是中心向边缘的辐射,如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如涟漪效应。如印度(一级中心)——中国(二级中心)……越南、朝鲜、日本(边缘)。而且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不可能是单向单线的。同一时期,有多种方向。同一方向,有多种线路和渠道。而且不仅有中心向边缘的辐射,还有着边缘对中心的反方向运动(如天台教典之回归)。三是除了中心向边缘的运动,还有从上层向下层的运动,尤其是在上层的精神沦丧的时候(义学衰微和宗师匮乏),就表现为民间化和底层化。这一方面是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但另一方面则是丧失了中心精神的明确和清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