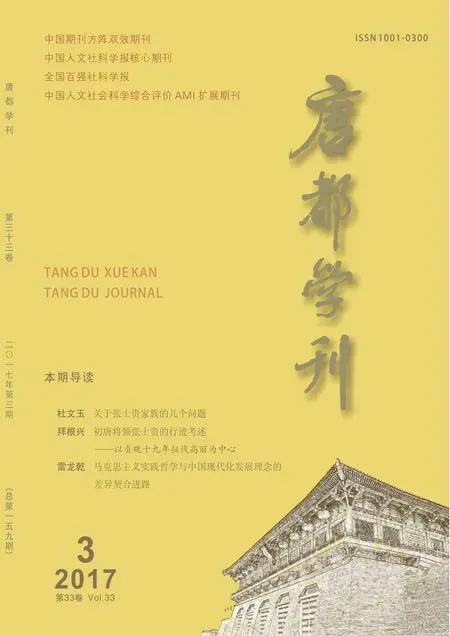竺法护的佛经翻译与汉地女性佛教信仰的发展
周玉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宗教研究所,西安 710065)
【历史文化研究】
竺法护的佛经翻译与汉地女性佛教信仰的发展
周玉茹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宗教研究所,西安 710065)
佛教传入中原内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以竺法护为首的佛经翻译者对大乘佛教典籍的翻译和弘扬促进了汉地女性思想解放,为她们提供了新的心灵空间。公元4世纪初,汉地出现了第一个比丘尼教团,标志着中国女性宗教信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竺法护;比丘尼;佛教女性;法华经;大乘佛教
公元3世纪开始到公元7世纪(即两晋南北朝直到初唐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女性贞节观念淡薄,积极追求与男性的平等、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现象,这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影响密切相关[1]。佛经翻译家竺法护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竺法护翻译的佛经不仅数量大、部类广,而且思想广博,其佛学思想涵盖了本体论、现象论、心性论、实践论等多个方面[2]。对竺法护的成就与贡献,世人多有论及,本文试图通过他的佛经翻译看他在汉地女性佛教信仰推动方面的影响。
一、竺法护的生平
竺法护(228—306)*有关竺法护的生卒年,史籍记载不一,经李尚全考证,法护生于曹魏太和二年(228),卒于西晋惠帝永兴三年(306),见李尚全《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载于《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梵名昙摩罗叉,是我国著名佛教翻译家,他的翻译开启了中国佛教的新时代,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很大,当世人对之评价很高。梁代高僧僧祐和慧皎都留下了他的传记,其中,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第七》记云:
竺法护,其先月支人也。世居炖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常介于视听也。
是时晋武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古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赍胡本,还归中夏。自炖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以晋文所获。大小乘经、贤劫、大哀、法华、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译写,劳不告惓。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护以晋武之末,隐居深山,山间有清涧,恒取澡漱。后有采薪者,秽慢其侧,水俄顷而熇。护乃徘徊叹曰:“水若永竭真无以自给,正当移去耳。”言终而泉流出满涧,其幽诚所感,皆此类也。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时有沙弥竺法乘者,八岁聪慧,依护为师。关中有甲族,欲奉大法,试护道德。伪往告急,求钱二十万,护未有答。乘年十三,侍在师侧,即语客曰:“和上意已相许矣。”客退,乘曰:“观此人神色非实求钱,将以观和上道德何如耳!”护曰:“吾亦以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余口,诣护请受五戒,具谢求钱意。于是四方士庶,闻风向集,宣隆佛化二十余年。后值惠帝西幸长安,关中萧条,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昆池遘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后孙兴公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以护比山巨源。其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其见美后代如此[3]。
法护的远见卓识和贡献,使他在僧团内部和朝野名士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名僧支道林为法护作的“像赞”云:“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倾拔玄致。”[4]23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并将他与“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媲美。
二、竺法护佛经翻译的贡献
竺法护生活的时代,兵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在颠沛流离中致力于佛经翻译和传法数十年,翻译了大量佛经。法护译经的数量,《出三藏记集》和《开元释教录》等史籍说法不一,《出三藏记集》记为154部309卷,《开元释教录》则记为175部354卷。根据吕澄先生的研究,法护译本存在的凡91部、208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74部、177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10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2卷、《般若三昧经》1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1卷、《温室浴洗众僧经》1卷、《迦叶结经》1卷、《楏女耆域因缘经》1卷、《大六向拜经》1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1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1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1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5]。法护的译本覆盖面广泛,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佛教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时人赞叹道:“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6]僧祐也对法护的翻译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法)护之力也。”[4]518竺法护的佛经翻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了前人。他在长安青门外建立的敦煌寺,被当代学者誉为中国最早、最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场所[7]。
三、公元3—4世纪时期汉地女性宗教信仰
竺法护在中土的译经弘法开辟了中土宗教信仰的新时代,更是为汉地广大女性精神信仰打开了新的一页。在大乘佛教经典精神的影响下,妇女突破了两汉以来经学对女性的精神控制[2]。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比丘尼教团,在社会政治和各种公共事务领域都有较大影响[8]。
早在佛陀时代,以大爱道为首的释迦族妇女建立了最初的女性僧团,此后,随着佛教在各地的传播,女性僧伽组织也开始在许多地区发展起来。公元2—3世纪的西域地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比丘尼僧伽,鸠摩罗什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史籍记载,这些尼寺皆用法自整,大有检制[9]。两汉之际佛教初传汉地,最初只有来自西域的沙门,曹魏嘉平(249—254)中,朱士行自行剃发出家,成为第一位汉人僧侣。建兴元年(313)出身官吏家庭的种令仪依止西域沙门智山剃度出家,禀受十戒,法名净检,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建立了竹林寺,从此开始了汉地女性僧伽的滥觞。佛教史家对净检的出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宝唱在《比丘尼传》中就写道:“像法东流,净检为首”,并详细记载了净检出家受戒的情况:
净检,本姓种,名令仪,彭城人也。父诞,武威太守。检少好学,早寡,家贫,常为贵族子女教授琴书。闻法信乐,莫由咨禀。后遇沙门法始,经道通达,晋建兴中(313—317),于宫城西门立寺,检乃造之,始为说法,检因大悟,念及强壮,以求法利,从始借经,遂达旨趣。他日谓始曰:“经中云:比丘、比丘尼,愿见济渡。”始曰:“西域有男女二众,此土其法未具。”检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宁有异法?”始曰:“外国人云,尼有五百戒,便应是异。当为问和上。”和上云:“尼戒大同细异,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但无和尚,无所依止尔。”检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立竹林寺[10]。
继净检尼之后,女性出家者日益增多,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佛图澄弟子安令首尼就领导了二百多人的尼众教团,在南北朝时期,僧团内部出现了在数量上“僧众尼亦众”的现象[11]。出家女性不仅数量大,而且修行和持戒上都有相当大的建树。
四、竺法护的译籍对女性的态度
古代印度社会贬低妇女,妇女虽然有种姓高低之分,但都是男子的附属品。如《摩奴法典》规定:“妇女不当独立,她童年时受父亲的保护,青年时受丈夫的保护,老年时受儿子的保护。”[12]印度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有着种种缺陷,所谓“女人身有十恶事”,在男子眼里,女性只有两个指头的智慧,即“二指智”。
佛教虽然提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并允许女性进入僧团,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古代婆罗门教对女性的贬抑态度。特别是部派佛教悲观厌世,提倡“无生”,将性欲和性行为视为大罪,多部广律都将须提那比丘与妇行淫作为佛陀制戒的直接原因*事见《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等。。女性的身体被视为男性的欲望对象,是男子修行的最大障碍,此外还要求比丘尼严守“八敬法”,严格僧团伦理秩序*又作“八重法”或“八不可过法”,规定比丘尼无论年龄、辈分、学养都须受比丘的教诲、管制,对比丘表示礼敬等。。
大乘佛教赋予女性与男子同样成佛的权利,事实上也就解除了三事隔、五事碍对女性的束缚,赋予了她们成为转轮王、成就佛果的权利。大乘佛教突破小乘部派佛教的种种局限,对妇女态度相当宽松,这在竺法护所翻译的经典有充分表现。法护的译籍中涉及女性的非常多,如《超日明三昧经》《大净法门经》《宝女所问经》《海龙王经》等都对部派佛教执著于男女相的分别,女身不能成佛等进行了反驳。如《超日明三昧经》中讲到一位名叫慧施的长者女向佛要求以“女身”受“佛道”,遭到一位名叫上度的比丘的反对,上度比丘提出了女人有“三事隔”(即“少制父母,出嫁制夫,不得自由,长大难子”)、“五事碍”(即女人不得作帝释、梵天、魔天、转轮圣王、佛),并有八十四种丑态,因此“女人不得作佛”。慧施女对比丘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她说,世间万法“譬如幻师化作日明、帝释、梵天、转轮圣王、天龙鬼神、人民、禽兽,随意则现,恍惚之间则不知处”,一切都是“本无处所,随行而行”。既然“一切无相,何有男女?……既无男女,吾取佛者,有何难也?”这一论证得到了佛陀的认可:“一切无处随行而成,不合不散不兴不衰,无见无闻无念无知无言无说,乃成正觉。”*参见《佛说超日明三昧经》卷2,大正藏第15册,第541~542页。又该经虽署名为聂承远译,但聂作为法护最重要的弟子和译经助手,主要是对该经整理删减,主要意旨还是竺法护的。慧施女的论辩,在理论上为女子争取了成佛的权利。
竺法护在另一部译籍《宝女所问经·问宝女品》中,宝女提出佛法“无男子法”“无女人法”,进一步否定女身是一种恶报的观点,驳斥了舍利弗坚持的“女身是恶报”的观点*参见《宝女所问经》卷2大正藏第13册,竺法护译,第458~460页。。
《诸佛要集经》通过离意女与文殊师利菩萨的对话,批驳了文殊师利对“男相”“女相”的执著。文殊师利问离意女“何故不转女身”?离意女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问:达诸法者有男女乎?计于色者有男女乎?受想行识有男女乎?地水火风有男女乎?虚空旷然,无有边际,不见处所,有男女乎?所说文字本末有处所,得男女乎?对离意女这一连串发问,文殊师利难以招架,一一回答:“无也”。离意女乘势反问:“一切诸法悉如虚空,当以何因转于女像成男子乎?”*参见《诸佛要集经》卷2大正藏第17册,竺法护译,第763~769页。
法华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影响,早在隋唐时期就形成了对该经受持、读诵、讲解、为他人说等各种修行方法[13],此经最早的译者就是竺法护(译名为《正法华经》10卷27品),太康七年(286)法护将该经译出,以后的五六年内,一边校对一边为众弟子讲授这部经,在长安和洛阳僧俗中广受欢迎[14]。
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卷6《七宝塔品第十一》记载了溥首菩萨(即文殊师利菩萨前身)在海中宣说《正法华经》,他认为八岁的龙女“聪明智慧与众超异,发大道意志愿弘广,性行和雅而不仓卒,便可成佛”。智积菩萨对此表示怀疑,问龙女“汝虽发意有无极慧,佛不可得。又如女身,累劫精进功积显著,尚不得佛。所以者何?以女人身未阶五位:一曰天帝,二曰梵天,三曰天魔,四曰转轮圣王,五曰大士”。龙女不愠不恼,以一价值连城的如意宝珠献给佛,并说:“今我取无上正真道成最正觉,速疾于斯。”瞬间,龙女变成“男子菩萨,寻即成佛,相三十二、众好具足,国土名号众会皆见,怪未曾有,无央数人、天、龙、鬼神,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三千世界六反震动,三万道迹得不退转,皆当逮成无上正真道”。看见这个事实,智积菩萨和舍利弗都“默然无言”*参见《正法华经》卷6大正藏第9册,第106页。。八岁龙女既是女身,又是旁生,但她“智慧利根”,不仅没有受到“女身污垢,不是法器”不能成佛的限制,即刻转女成男,还得不退转,成就佛身,从而突破了小乘佛教关于女身不得成佛的限制。
五、竺法护所译弥勒类经典与女性信仰
竺法护还翻译了一系列弥勒类经典,据相关经录和藏经所载,包括《佛说弥勒成佛经》(又名《弥勒下生经》一卷)、《弥勒为女身经》(又名《弥勒菩萨为女身经》一卷)和《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等三部*分别见《佛说弥勒下生经》,收入大正藏第14册,第421~423页;《大周勘定众经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第374页;法经:《众经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第116页,又此部经收入大正藏第12册。。这三部经典对促进两晋时期佛教在女性中的传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其中《弥勒为女身经》早已佚失,但从现存《六度集经》和《经律异相》所收录的《弥勒为女身经》相关文字仍可窥知其主要内容和倾向。《弥勒为女身经》记载了弥勒菩萨在过去世中曾化身为女性,受佛度化。
中古时期流传着各种净土信仰,除了广为人知的弥陀净土(即西方净土)以外,还有观音净土、药师净土、阿閦佛净土、弥勒净土等。阿弥陀佛净土和药师佛净土都没有女性的存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寿终之后复为女像者,不取正觉”*参见《佛说无量寿经》,大正藏第12册,康僧铠译,第268页。。因此“(众生)但论生彼国,无女人即无盲聋喑哑人”*参见智说《净土十疑论》,大正藏第47册,第80页。。药师佛则发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众苦之所逼切,极生厌离,愿舍女身,若闻我名至心称念。即于现身转成男子具丈夫相。乃至菩提”*参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义净译,大正藏第47册,第413页。。因此“彼佛土,一向清净,无有女人,亦无恶趣,及苦音声”*参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正藏第47册,沮渠京声译,第405页。。弥勒净土在五代以前拥有较大的影响,道安、玄奘都是弥勒净土的信仰者和追随者*道安和玄奘都希望往生弥勒净土。“(道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高僧传》卷5《道安》,大正藏第50册,第183页;玄奘在取经途中多次遭遇危险以诵念弥勒名号得以解脱,临终时更告知门人弟子,(死后)“决定得生弥勒前”。《续高僧传》卷4《玄奘》,大正藏第50册,第458页。。与其他几种净土不同的是,弥勒净土唯一有一个女性的净土世界[15]。经典记载“(兜率天中)阎浮檀金光中,出五百亿诸天宝女,一一宝女住立树下,执百亿宝。无数璎珞,出妙音乐,时乐音中演说不退转地法轮之行……(八色琉璃渠中)水出华中如宝花流,一一华上有二十四天女,身色微妙如诸菩萨庄严身相”*参见《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大正藏第14册,沮渠京声译,第419页。。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无论是弥陀净土还是药师净土,对女性的身体形象都是否定的,女性需要累世功德才能转身成男具备往生此方的资格,接纳女身的弥勒净土更容易获得女性的认可,更何况弥勒过去世中曾多次以女身得到佛的度化。弥勒类经典的翻译和广泛传播,使得弥勒及其所在的兜率净土成为隋唐以前广大妇女共同推重的对象,北朝时期北方出现了一批女性为功德主的弥勒造像[16]。如“永平四年(511)十月,人止和寺尼道僧造弥勒像一躯”,景明三年(502),佛弟子维那尹爱美……等二十一人为七世父母等造弥勒像一躯;永平二年(509)四月,比丘尼法文造弥勒像一躯,永平四年(511)比丘尼法兴造弥勒像一躯……;延昌元年(512),清信士弟子刘洛真兄弟为亡父母敬造弥勒像二躯,使亡父母托生紫薇安乐之处。兜率净土成为江南比丘尼念佛发愿往生之乐土,《比丘尼传》记载了多例南朝时江南比丘尼发愿往生兜率净土(兜率天)的事例[17]。吴太玄台寺玄藻尼“诵《法华经》,菜食长斋,三十七载。常翘心注想,愿生兜率”。广陵中寺光静尼“属念兜率,心心相续,如是不断”。建康禅林寺尼净秀“告诸弟子,我生兜率天”*参见《比丘尼传校注》,第63、83、166页。。
从这个意义上看,竺法护翻译的弥勒经典对广大妇女佛教信仰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得力于经典的翻译。佛典翻译和佛教在汉地传播进程基本同步,但直到公元三、四世纪,佛典的流传和翻译相当程度上还只是个人和部分小团体自发自觉的行为,翻译者个人的水平和喜好决定了佛典翻译的质量和倾向*自后秦鸠摩罗什在逍遥园设立译场,中国佛典的翻译开始进入官办阶段,一直延续至北宋初年。。公元4世纪以后,汉地女性得以突破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和男子一样剃度出家修行,获得与男子一样的灵性解放的权利,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妇女来说是巨大的进步。对此,任继愈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佛教史上,很少有这样集中地关注妇女问题,而且如此为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译家。可以说,竺法护在很大程度上提炼了佛经关于妇女观念的精华。”[18]
[1] 张勇.论魏晋南北朝大乘佛教对妇女精神风貌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62-67.
[2] 李尚全.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J].敦煌研究辑刊,2004(1):77-82.
[3]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3[M].北京:中华书局,1995:518.
[4] 释慧皎.高僧传: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 吕澄.竺法护[M].中国佛教:第二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1.
[6] 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9[M].北京:中华书局,1998:332.
[7] 李利安.中国最早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场所:敦煌寺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9-62.
[8] 周玉茹.六朝建康比丘尼参政现象探析[J],人文杂志,2010(6):138-141.
[9] 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98:411.
[10]王孺童.比丘尼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
[11]白文固.中国僧尼名籍制度[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22.
[12]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9.
[13]释圣严.中国佛教以《法华经》为基础的修行方法[J].中华佛学学报,1994(7):8.
[14]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97:304.
[15]唐嘉.《弥勒为女身经》探微[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04-108.
[16]释见证.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弥勒造像与信仰[D].成都:四川大学,2006:341-342.
[17]周玉茹.六朝江南比丘尼禅修考论[J].人文杂志,2014(12):14-20.
[18]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3.
[责任编辑 贾马燕]
Dharmaraksa’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Development of Han Women’s Buddhism Belief
ZHOU Yu-ru
(InstituteofReligions,ShaanxiAcademyofSocialSciences,Xi’an710065,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the Central China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patterns and beliefs. Translators, led by Dharmaraksa, by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Buddhist Scriptures, promoted the Han women’s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provided them new inner space. At the 4th Century AD, the first Buddhist Nun Mission was established in China, which symbolized a new stage in the Chinese women’s religious beliefs.
Dharmaraksa; Buddhist nuns (Bhikkhuni); Buddhist women; Lotus Sutra (Saddharmapundarika-sutra); the Mahayana Buddhism
B948
A
1001-0300(2017)03-0083-05
2016-10-26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2016年度院级重点课题:“早期佛教性别观研究”(16ZD02)阶段性成果
周玉茹,女,四川邛崃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佛教性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