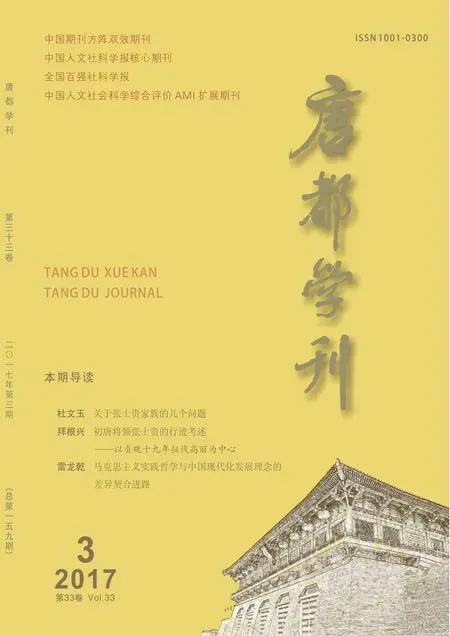生存极地的生命蛮力与乡土边缘的人性光晕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
郭茂全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20)
【西部文学研究】
生存极地的生命蛮力与乡土边缘的人性光晕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
郭茂全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20)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表现了中国西部偏远乡村中农民的苦难生活,呈现了他们在极地生存中的生命蛮力与人性光晕。乡土书写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审美理想之一,《极花》不仅传达了作家对卑微的乡土生命的深切关注,还表征着作家对乡村凋蔽的深沉思考。
贾平凹;《极花》;生命蛮力;人性光晕;乡土书写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是其继长篇小说《老生》之后的又一力作。乡土书写对贾平凹来说是“宿命的呼唤”,《极花》则是作家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凋敝”这一社会问题的审美创造。该小说在描绘生存极地文化景观、表现乡土边缘的生命蛮力、反映底层生命的人性光晕等方面深具特色。
一、“前现代”:生存“极地”的文化景观
《极花》呈现了一幅具有“前现代”特征的边地农民的生存景观,小说中的“高巴县圪梁村”就是边远乡土生活空间的缩影。圪梁村人居住在窑洞里,祖祖辈辈靠天吃饭。这里土地贫瘠,只能种植荞麦、土豆等农作物,村民一日三餐不离土豆,吃的最多的就是荞面与土豆,吃白面馍则需要坐车到较远的镇上买。因村里没有通上电,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照明,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只有村长家里的一部电话。圪梁村偏远而又闭塞,从县上到镇上坐车需要一天,从镇上到圪梁村坐拖拉机需要多半天。手扶拖拉机是村民去镇上唯一的现代交通工具。由于落后、贫穷,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到圪梁村,圪梁村因此成了一个“光棍村”。“黑家的日子虽然在圪梁村算是好的,但也只是饭没有断顿,零花钱没有打住手罢了。”[1]“这些年来,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而光棍却越来越多。”[1]圪梁村人卑微又顽强的生活理想就是娶妻生子、给老人送终和箍几孔窑。为了延续香火,许多男人在娶不到媳妇时,只能从人贩子手里高价“买”女人,然后将其锁进窑洞,暴力强迫成婚。《极花》不是表现原始、纯朴、美好的乡村文化走向式微的挽歌,而是表现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处在贫困、蛮荒甚至残酷生活境遇里的农民的悲歌。
《极花》延续着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对独特地域文化的重视。小说中的“圪梁村”文化世界中充满了古朴、奇特、神秘的文化风俗,有观星象、观年历、看风水、招魂灵、剪纸花、凿石像、闹婚礼、戴花绳、井里吊鞋、补粮拜寿、接生、哭丧、拜神、祈雨等各种乡土习俗。小说中的老老爷“浑拙又精明,普通又神秘”,他在村里辈分最高,会观星象,知节气,懂时令,为村里出生的孩子取名,村里人凡遇到大事都会向他询问,其言语之间常常充满玄思。老老爷是圪梁村里民间的智慧者与文化传统的延续者。圪梁村的“村长”利用手中的权力“硬吃硬压”,以“权”入股一些村民的血葱生产,以“权”长期霸占着村里的几个寡妇,是一个扭曲的基层权力的拥有者。黑亮爹、瞎子叔、半语子叔、黑亮、三朵等圪梁村的村民既淳朴善良又蒙昧野蛮。小说通过女主人公胡蝶的视角写村民的动物般的生态状态:“这个村里的人我越来越觉得像山林里的那些动物,有老虎和狮子也有蜈蚣蛤蟆黄鼠狼子,更有着一群苍蝇蚊子。”[1]小说《极花》是一个“前现代”的寓言,它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古老、凋敝、蛮荒的偏远农村的生存景象,绘制了一幅中国西部偏远乡土文化的基因图谱。
地球上的“极地”终年白雪覆盖,几乎没有植物生长。从生存条件的严酷来说,小说中圪梁村可谓人类生存的“极地”。圪梁村极其贫困的物质条件、极其顽强的生命形态、极其独特的乡土文化就共同构成了一幅具有“前现代”特征的农民生存图景。“圪梁村”不是作家对前现代“乐园”的怀旧性建构,而是对前现代“绝境”的创伤性表达,它似乎遥远地回应了鲁迅小说中“萧索的荒村”的“前现代”乡村叙事。与当下纷繁的城市生活书写相比,圪梁村则是“乡村生活”的“一极”;与中国当代农村“离城镇近的、自然生态好的、在高速路边的地方”的“新农村”的美好景象相比,圪梁村则是“边缘化”的“一极”;与中国的现代化、城镇化的社会建设蓝图相比,圪梁村则是“前现代”的“一极”。《极花》中的“极地”生存世界体现了贾平凹对那些被主流话语、城市话语、现代性话语遮蔽的偏僻乡村的深切关注,小说以钢凿般“极端”叙事的方式凿开了现实生活厚厚的岩层,錾落了乡土生活的乌托邦想象,刻镂出饱受苦难的、卑微又顽强的边缘农民群体的生命样态。
二、“集体暴力”:乡土边缘的生命蛮力
个体生命在无法找到改变生存困境的正当途径时,常常会选择“暴力”的方式。中国当下的城镇化不仅是城乡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是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的变化,在偏远的乡村,女少男多的性别失衡已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极花》中,圪梁村的男人只能通过“买”“抢”“囚禁”“强暴”等方式得到传宗接代的“媳妇”。婚姻行为在圪梁村变成了“集体暴力”,圪梁村的村长与村民共同组成拐卖妇女的“联合阵营”。家里的各个成员也是防止被拐卖者逃跑的中坚力量,甚至家里的狗、驴都参与了监视、看守。黑亮花了三万多元“买”来胡蝶后,便以铁链、铁环等将胡蝶锁在窑洞里。为防止胡蝶逃跑,黑亮爹、瞎子叔、黑亮组成一个监视群体。由于胡蝶死活不从,家人便请来村里的小伙子将胡蝶绑在板凳上,黑亮便“强暴”了胡蝶。胡蝶寻机逃跑时,被人发现并再次囚禁于窑洞。当胡蝶的母亲与派出所所长解救胡蝶时,全村男人在村长的带领下拼命追打解救者。防止村里的媳妇逃跑,成为圪梁村的“集体责任”。当端午媳妇的家人来寻找被拐卖的女儿时,圪梁村人拿着榔头锨把将解救者赶跑了。小说中,马角把她的媳妇一买回来就打断了一条腿,以防止她逃跑。“家暴”在圪梁村比较常见,麻子婶因给胡蝶送苦楝子被发现后,她的丈夫半语子就将她一顿暴打,还打掉了麻子婶的两颗牙。非常严酷的现实处境与极其强烈的生存欲望将圪梁村的男人们锻铸成了一个个野蛮的“施暴者”。
《极花》一方面描述了圪梁村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他们对女人“疼爱”、失去女人的“悲痛”与“疯癫”及渴望女人而不得的“梦呓”。黑亮一家虽然处处限制胡蝶的自由,但也时时尽其所有地让胡蝶吃好。黑亮按时去遥远的镇上买白面馒头给胡蝶,也不让她干农活、干家务。当胡蝶有病时,黑亮一家竭尽全力改善胡蝶的生活,黑亮也悉心地照顾胡蝶。能够守护住女人成了圪梁村男人最大的愿望,也成为他们最大的责任。没有女人,圪梁村的男人或因拐卖妇女而变成“罪犯”,或因媳妇亡故而变成“疯子”,或因未能尽到看护女人之责而“自杀”。金锁在他的媳妇被葫芦豹蜂蜇死后就疯了,一直给人说她的媳妇还活着,四年来经常坐在媳妇的坟头嚎哭;顺子在进城打工时,媳妇与收购极花的城里人跑了,顺子爹因愧疚未能替儿子守住儿媳而喝农药自杀身亡。一些娶不到媳妇的光棍们便让人凿一个石头女人放在家门口,甚至死后化作鬼魂后还常托梦给家人给他安排“阴婚”。
圪梁村男人的“暴力行为”源于生命本能无法正常疏泄时的蛮性力量,但并不一定完全是邪恶丑陋的。圪梁村的男人是粗暴又细心、冷酷又热情、懦弱又顽强、善良又凶恶的“混合体”。从小说中,读者时时都能察觉到叙述者在呈现这种“集体暴力”时的激愤与悲哀、焦灼与忧虑、迷茫与无奈。圪梁村农民只能靠挖越来越少的“极花”谋生,城里来的人不仅收购“极花”,还“拐”走了乡村的女人;圪梁村人靠种“血葱”向城市人的“输血”,换来的“血汗钱”却只能“买”女人。叙述者通过人物黑亮之口“控诉”城市对乡村的“暴力”:“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1]谁能否认,边缘乡土社会的“集体暴力”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城市社会掠夺乡村财富与农村劳力的灾难性后果呢?像胡蝶一样的农村姑娘向往着城市生活,但常被挤压于简陋的出租大院,有时还被拐卖到更为贫困偏僻的乡村。当被她们被解救回“家”时,又陷入城市“舆论”的“囚禁”与“围观”之中,连原有的拾荒者的生活都无法继续。胡蝶们“有”故乡无法回、“在”城市又无法“居”的“悬浮”命运难道不是城市“施暴”的结果吗?面对偏远乡村的凋蔽与底层生存者的苦难,叙述者不断地叩问:谁夺走了乡村的幸福?
三、“星辰”与“花朵”:生活绝境中的人性光晕
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中不仅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还关注其精神层面的追求。“辍学进城—被拐卖到乡村—反抗逃跑—接受现实”是《极花》中女主人公胡蝶的人生轨迹。漂亮的乡村女孩胡蝶在父亲去世后,因生活所迫而辍学,和母亲一起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最底层,依靠捡破烂维持家人生计,供给弟弟读书。单纯的胡蝶对“城里人”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喜欢穿“小西服”与“高跟鞋”,对出租大院中的大学生青文怀着朦胧的情愫。胡蝶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成为“城里人”,却在城市应聘酒店服务员时被人拐卖,从城市底层的“出租大院”陷入非常贫穷的“乡村窑洞”。尽管胡蝶对自己的“城里人”的身份认同有着不切实际的方面,但胡蝶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就是小说中一缕缕美丽的人性光晕。
如果说《极花》中的“血葱”象征了乡土世界中男性的原始生命蛮力,那么“星”与“花”则象征着乡土世界中女性的宿命。被拐卖到黑家的胡蝶被囚禁在窑洞,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她只能通过窑洞上的小小窗户望“星辰”,正如小说中的老爷爷所说“总会有星的”。“白天里我等着天黑,天黑了就看夜里的星,我无法在没有星的地方寻到属于我的星,白皮松上空永远是黑的。”[1]胡蝶寻找自我的过程,就是通过寻找夜空中属于自己的星辰来实现的。《极花》中的“星辰”与“花朵”就是生活绝境中的人性光晕的象征。《极花》的叙述起于“夜空”,终于“夜空”,“胡蝶”在小说的结尾已经成为一个被巨大的“黑夜”包围的女性“共名”。“花”在《极花》中同样是女性的象征,“花”与“蝶”相互指涉,将女性的宿命交织在一起。胡蝶认为自己的“前世”也许就是“极花”,“被拐卖”到圪梁村也许就是来寻找“极花”的。黑亮妈生前将“极花”供于中堂,希望未来的儿媳像“极花”,她挖极花从未空手过,但却在挖极花中不慎坠崖而死。黑亮说,如果胡蝶生下个女孩,就取名“极花”。经过近十年疯狂的挖极花,圪梁村的周围的极花变得越来越少,正如村里越来越少的女人。“极花”是女性的象征,“剪纸花”同样是女性的象征。“剪花娘子”麻子婶在剪“花”,也在剪女人们的“梦”。她在教胡蝶“剪花花”时,也教胡蝶如何在剪纸花的过程中忘却生活的苦难与减少内心的痛楚。乡村夜空里的“星辰”、贫瘠土地上的“极花”和农村窑洞上的“窗花”均象征着乡村女性的宿命。在小说的结尾,没有等到母亲来解救自己的胡蝶宛如“剪花”被风吹到了窑壁上,这无疑是胡蝶将会永远生活于圪梁村的隐喻。
《极花》中,胡蝶盼望母亲能够来解救自己的心理描写是小说中最富含人性温暖与最蕴含人性关怀的部分。作为女人,胡蝶既是妈妈疼爱的女儿,又是在乡村生下的孩子“兔子”的母亲。她在遭受折磨时一次次呼唤母亲的到来,又在生下兔子之后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母爱。《极花》也表现了女人们在男性暴力包围中的“姐妹情谊”。善良的麻子婶将苦楝子偷偷地送给胡蝶,以便让她堕胎、逃跑;当她感觉到胡蝶逃跑无望,麻子婶教胡蝶剪窗花以慰藉她内心的痛苦。訾米进城后沦落风尘,嫁到圪梁村后成为立春的媳妇。尽管她与立春的弟弟腊八也有些瓜葛,但并非人可尽夫。当立春和腊八被山崖滑坡压死后,訾米一直守孝至七七祭日,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村支书的逼迫。当訾米发现圪梁村的光棍思谋着要抢那些挖极花的外地女子时,便连夜悄悄地将她们送出村外。从这些行为中,读者不难发现訾米在逐渐抖落“风尘”之色后透出的人性光晕。
贾平凹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精神是丰富甚至混沌的,这需要我们的目光必须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写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坚硬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身处污泥盼有莲花,心在地狱而向往天堂。人不单在物质中活着,更需要活在精神中。”[2]336在《极花》中,圪梁村的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对姐妹命运的关切、对母性温暖的眷恋等成为不断消解“暴力”和祛除“残忍”的“柔软”的力量,成为生活绝境中温暖的生命灯烛所衍射出的美好人性光晕。
四、“自述”与“唠叨”:女性悲剧的话语建构
以“拐卖妇女”事件作为小说题材,叙述者可以选择的叙述方式较多,如“失踪寻亲”模式、“被拐解救”模式、“犯罪侦破”模式等。与上述叙事模式不同,《极花》采用的是亲历者“我”的“自述”与“唠叨”的叙述方式,以此展开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呈现与对边缘乡土生命样态的描绘。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说:“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1]“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1]“唠叨”叙事其实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喃叙事”。“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人个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3]在被苦难的生活撕裂的伤痛时刻,个体生命不需要理性的分析与阐释,而需要的是陪伴与倾听,“唠叨”叙事或“呢喃”叙事的意义正在乎此。
在小说的开头,胡蝶已在窑壁上刻下了第一百七十八条道道儿,叙述者在清晰而又混沌的时间“标记”中制造了一个故事“开局”,也制造了一个“自述”与“说话”的起点。被囚禁的胡蝶只能在窑洞中默默地给极花说话,在自言自语中,“我”不时沉浸于昔日的生活片断。“我给极花默说着话,说累了,又坐在了窗前往夜空里看。”[1]“我”回忆着昔日城市底层生活中的“自由”,又咀嚼着被拐卖后的“痛楚”。值得注意的是,因遭受极大的创痛,使“我”灵魂出窍,“我”的视角有时表现为一种灵魂与肉体被“撕裂”的叙事模式,“我”的“灵魂”站在窗格子上看到“胡蝶”的“肉体”被强暴的情景,后来还看到胡蝶分娩时的情景。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个体生命只有在“极痛”状态下才可能有的叙述视角。
圪梁村人的生活景况是通过“我”“说”给读者的。“我”唠叨着窑洞外的天空、树木、院落、磨盘、牲畜、行人,也唠叨着村里邻里发生的有关村里人生死、买卖的谈话。胡蝶在回忆自己在城市底层的出租大院中的生活与偏远乡村窑洞生活中建构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话”。“我”的叙述成为城乡文化交汇与对比的场域。胡蝶是城市生活的知情者与介绍者,也是边远山村生活的观察者、体验者。胡蝶实际上成为一个被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双重铭写”的“文本”,“我”既是“言说者”,又是“被言说者”。胡蝶的“自述”与“唠叨”,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女性苦难悲剧的聆听者与女性心理脉息的探触者。可以说,“自述”与“唠叨”的话语方式不断向读者发出吁请,让读者不得不走近叙述者,细心聆听“胡蝶”的诉说,细心聆听“花朵”的呐喊。
《极花》的叙述结构可分为三个向度。首先,《极花》所讲述的是一个女孩被拐卖后不断逃跑直到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情节故事,这主要体现在被囚禁的胡蝶不止一次地想逃走。即使胡蝶在后来逐渐适应了圪梁村人的生活,但偶然听到有人寻找“胡蝶”时便满怀期待。其次,《极花》叙述了一个女性的母性意识与心理逐渐生成的过程,这一点集中体现于胡蝶对孩子“兔子”的情感态度的变化过程中。胡蝶经历了“我不能怀孕”、“我不会认你是儿子,你也别认我是娘”、“这是我儿子,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天是让我的儿子来陪我的”、“我有娘了,可兔子却没了娘,你有孩子了,我孩子却没了”的心理渐变过程。其三,《极花》叙述了一个女性对乡土文化从讨厌、反抗再到接受、认同的心理故事。胡蝶对乡村的态度经历了“我要回城市去”“我厌烦着村里人”“我不爱这里”“我不再有想法了”的心理嬗变。“知道了心理有多健康身体就有多健康,心境能改变环境也能改变容颜。”[1]胡蝶最后对圪梁村文化的接受并不是乡土文化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胡蝶的接受心态发生了变化,她已经完全习惯了圪梁村的“味道”,学会了做搅团、荞面饸饹、蒸土豆等乡村饭食,学会了伺弄鸡、骑毛驴、采茵陈、编草鞋、做笤帚等农活,也认为自己能从乡村走到城市,也可以从城市回到乡村。《极花》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是一个个体生命如何遭受不幸、如何吞咽苦难、如何忍受痛苦、如何回归平静的精神旅程。贾平凹在对中国乡土的小说想象中既有温情与留恋,也有沉痛与无奈,作家在《极花》中流露出的感情是复杂而微妙的。
《极花》依然延续了贾平凹在创作关注现实乡土、关怀底层生命的价值取向,是作家对他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经验的审美表达。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延续性上,《极花》中的胡蝶母亲等城市拾荒者的生活与《高兴》中进城农民拾破烂的生活有相通之处,《极花》中的“剪花娘子”麻子婶与《古炉》中蚕婆有相似之点;在表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衰落与农耕文明的式微方面,《极花》与《秦腔》《带灯》《老生》等小说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表现“前现代”的乡村生活方面,《极花》与《浮躁》中所表现的乡村生活有着相似之处。
《极花》的创作既调动了作家对昔日故乡的记忆,也调动了作家对当下农村的观察。贾平凹说:“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4]正如《土门》中的对“城市拆迁”的表现和《极花》中对“拐卖妇女”的展现,贾平凹能够从看似平常的“新闻事件”背后敏锐地发现丰富的人生意蕴。“真正的作家取决于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什么?作品的维度有多大?提供的困惑有多少?”[2]287尽管《极花》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部,但无损于作品所蕴藏的艺术力量。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凋敝”,直面现实的小说《极花》无疑是贾平凹“救救边远乡村”的“呐喊”。
[1] 贾平凹.极花[J].人民文学,2016(1):4-94.
[2] 贾平凹.访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55.
[4] 贾平凹.关于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10.
[责任编辑 张 敏]
Life’s Brute Force under the Worst Surviving Conditions andHuman Nature’s Brightness of Villagers inPrettyFlowerby Jia Ping-wa
GUO Mao-quan
(SchoolofLiteratur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20,China)
PrettyFlower(JiHuain Chinese) by Jia Ping-wa describes villagers’ miserable life in the remote countryside in the west of China, displays their life’s brute force and human nature’s brightness under the worst surviving condition. One of Jia Ping-wa’s aesthetic ideals in his novel writing is to write for the fate of rural areas. Through this novel, Jia Ping-wa not only expresses his deep care about the humble rural life, but also represents hi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poverty-stricken countryside.
Jia Ping-wa;PrettyFlower(JiHuain Chinese); life’s brute force; human nature’s brightness; rural writing
I206.7
A
1001-0300(2017)03-0064-05
2016-11-12
2015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丝绸之路的文化记忆与文学想象”(15LZUJBWZY001)
郭茂全,男,甘肃武山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