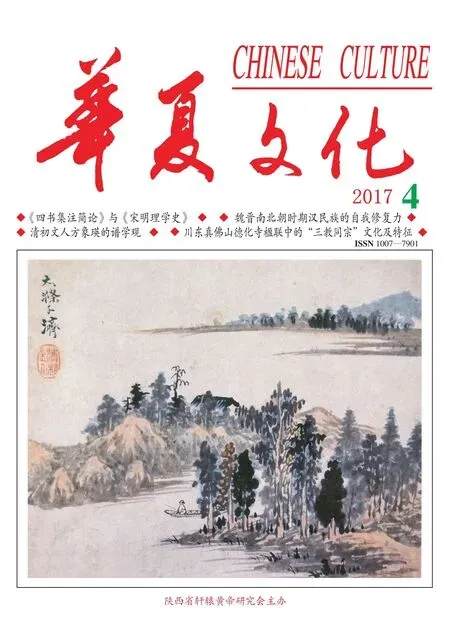从《尚书》到《论语》的“明德慎罚”观念
□黄 熙
从《尚书》到《论语》的“明德慎罚”观念
□黄 熙
“明德慎罚”是《尚书》中主要的治国理念之一,它直接被提出是在《尚书·康诰》中:“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在《尚书》中,不难发现,“明德慎罚”的观念在上古及三代的政治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明德慎罚”的观念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从《论语》中不难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深受“明德慎罚”观念的影响。本文试图从《论语》中的相关言论,论述从《尚书》到《论语》对“明德慎罚”这一观念的变化和发展。
一、《尚书》中“明德慎罚”观念的表现
在《尚书》中,“明德慎罚”的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它随着上古及三代的历史而不断变化。直到周公“在探讨如何治国的问题时,便天才地提出了影响了我国数千年的两个根本大法——德治和法治”(钱宗武、杜纯梓:《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最终,在《尚书·康诰》中明确提出“明德慎罚”。
(一)上古及三代明德观念的发展
上古时期的统治者,如帝尧,能够做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尧典》),到了舜时,也知道“惇德允元”(《尚书·尧典》)的重要性。意思是说尧舜都能明白“明德”的重要性。然而此时人们的认识有限,宗教观念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如禹的征伐都需要借助神意才能进行。此时的统治者是天在人间的代言人,也只有选拔出有德的人,才有资格向天帝报告。如尧选拔禅让对象时,就特别看重候选人的德。因此,舜才有资格“受终于文祖”“肆类于上帝”(《尚书·舜典》),成为天在人间的新一任代言人。
到了商朝统治者,他们能够认识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尚书·盘庚》)。即广布德教,用德来维系民心,获得支持。此时“德不仅作为思想出现,更作为了一种范畴而出现”(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这个时候的德,与民联系在一起,不再是尧舜时单纯的对统治者的要求了。此时的德增添了与夏桀之德相对应的善德。即满足人民利益,收获民心。此外,商朝统治者祭奉的上帝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玄鸟的传说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商朝统治者认为,他们的德是天德直接赋予的,是继承了上帝即祖先的意志从而直接管理人间。因此,敬天德即敬君德,从而承认殷商统治者的合法性。
周朝的建立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夏商的历史经验。如《酒诰》中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另外《召诰》中也明确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些便是周初统治者认识到夏朝和殷商灭亡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天命会随着统治者的“德”而转移,夏桀、商纣的败德导致天命的转移。此时,德也不再是天生赋予统治者的,而是君王修德,从而去配天命。只有“敬德”才能够“祈天永命”(《尚书·召诰》)。如周文王,能够“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尚书·康诰》)。尤其是孔子推崇备至的周公,“开始把明德、敬德作为政治口号提了出来”(何发甦:《孔子与〈尚书〉》,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周公还告诫成王“王其疾敬德”(《尚书·召诰》)。除此之外,这种德不仅仅针对天子,对于处在统治阶层的大臣来说,也强调德的重要性,如周公告诫康叔“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康诰》)。这种君德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德,范围扩大到整个统治阶层。
(二)上古及三代由刑到罚的转变
在舜时,刑的种类繁多:“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唯刑之恤哉”(《尚书·舜典》)。可见当时对刑的重视。除此之外,还能看出那时虽然重视刑,但是并不严酷,即使这样,在使用起来,也要小心翼翼。这说明尧舜时期,不仅看重刑,而且也注重慎刑。可以说,从治国层面看,此时刑和统治者的德是并重的。用刑来约束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
《商书》中虽不多见刑罚,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此时不注重刑罚的作用。相反,“商朝具有成套的暴力机器和精神统治的武器”(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到了商纣时,愈加严重和残酷,“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尚书·泰誓》),简直是残忍至极,以致“皇天震怒”(《尚书·泰誓》)。商纣不仅不“慎刑”,反而滥刑,出现了“用乂雠敛,召敌雠不怠”(《尚书·微子》)的情况,即国君用杀戮和重刑横征暴敛,招致民怨。而“凡有罪辜,乃罔恒获”(《尚书·微子》),一些真正有罪的人,却不能受到惩罚,这样的结果最终使天命转移。
如果说夏商治国的手段主要是刑,那么周朝统治者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罚。刑是用刀割颈,一旦犯法,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而罚是指轻微的犯罪行为。在还未触及到重大的法律时,就以罚的形式,对其警醒和惩罚,从而避免了刑的使用。因此,周朝统治者重视罚的作用。即使罚,也不能乱罚滥罚,而应该慎罚。如:“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尚书·康诰》)。即对于犯人的证词也要慎重审查。并且“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尚书·立政》),要十分谨慎地依法行事。此外,虽然周做“吕刑”,但是其目的仍旧“非讫于威,惟讫于富”(《尚书·吕刑》)。从而为民谋利,“以成三德”(《尚书·吕刑》)。用这些方法引导人民向善,从而维系国家稳定。最终才能够“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
(三)“明德慎罚”观念的提出
明德与慎罚的结合,在周公时才明确提出,在《周书》中,有大量的诰文阐发“明德慎罚”的思想。如他告诫康叔姬封要“敬明乃罚”(《尚书·康诰》),如此才能够“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尚书·康诰》)。才能够使人民不犯上作乱,危害统治。从而形成了西周“明德慎罚”的统治观念,其根本在于保德保民,从而延续王命。
而在《康诰》中,周公更是道出了“明德慎罚”的具体方式,即“庸庸,祗祗,威威”,任用应该任用的人,尊敬应该尊敬的人即是“明德”,而“慎罚”则去镇压应该镇压的人,惩罚应该惩罚的人。那么哪些人才是应该去镇压和严惩的人呢?
从《尚书》中,大概可以总结出四种人是应该重罚的。首先,“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之人,对于这类不孝不恭不慈不友之人,就应该“刑兹无赦”,严惩不贷。其次,就是对于“不率大戛”,不遵循国家大法的官员,也应该按照国家法律杀掉。而在前一个朝代——商,对于这类官员,“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尚书·盘庚》)。甚至连后代都会殃及,这也是《尚书》中出现的最严酷的惩罚了。再次,就是针对殷商遗民,如果“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尚书·多士》)。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民众不能够敬事周国,服从命令,那么也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从《尚书》中几篇誓文可以看出,在战场上的惩罚是特例,无论哪个朝代,战场上都不会“慎罚”,如果在战场上不听从命令,不完成使命,不奋力杀敌,则会“孥戮汝”,或者遭到大刑。
德,构成了施政的核心理念;而罚,则成为维系政权的必要手段。“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尚书·盘庚》)。实际上,上古及三代时期既是“明德”又是“明罚”的。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控制人民。而所谓的“慎罚”、保民,“充其量不过是使百姓能够活下去,而不会超过这个限度”(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第216页)。孔子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继承“明德慎罚”的观念的同时,不仅要慎罚,甚至认为应该不存在罚。
二、《论语》对“明德慎罚”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生在动荡的春秋社会,西周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与思想遗产,对孔子的影响非常大。《尚书》作为已有的思想材料,孔子不仅从中了解到上古及三代时的政治观念,更通过“诠释尚书,形成了儒家所信奉的理想典范”(严正:《王道理想与圣贤意识——论儒家〈尚书〉诠释的理论价值与影响》,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一)《论语》对《尚书》中德的继承
孔子在阅读《尚书》中记录的历史故事和讲话时,无不对先代圣贤们流露出崇敬之情。有关孔子对尧、舜、禹、周公等先代圣贤的溢美之词,在《论语》中频繁出现。孔子从《尚书》中吸取到许多经验,这些都对他及其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谈到周朝的德时,孔子说:“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周朝之德是“至德”。他又说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又继承着周朝的礼乐遗产和思想观念,并且始终践行着周朝的政治理念。他渴望通过《尚书》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从而实现他心中文、武、周公时的政治环境,恢复礼乐制度。将“德治”推行于天下,从而改变春秋时期的纷争局面。
孔子不仅继承了“明德”的观念,并且发展了“明德”的思想。
(二)《论语》对《尚书》中德的发展
首先是根据《尚书》的德,将德具体化,具体到仁的核心观念上。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和礼,表现于内的则主要是仁的思想,礼也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特别突出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将仁具体地解释为五种德,以仁概括恭、宽、信、敏、惠等具体的德行,视仁作为德政的基础,并且对统治者做出要求,只要统治者掌握了这种仁,行为符合仁,德政便能实现。
其次,将《尚书》中的“明德”范围下移,使人人有德,从而形成了早期儒家的修养论思想。在《尚书》中,德主要是统治者或者统治阶层应该去“明”的,去拥有的。也只有这样才可以“配天命”。而在孔子这里,德不仅仅是统治者应该拥有的,作为普通大众也应该拥有这种德。他“扩大了德的使用范围,把统治者之德发展为人人之德”(邢广伟:《试论〈论语〉中“德”的思想》,华北电力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3月,第21页)。孔子认为“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有道德的人是不会感到孤单的,必定有和他相同道德的人。而仁这种德也是很容易就能够得到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此外,《论语》还有大量关于君子以及修养方式的言论,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尚书》中德的观念下移到普通人民之中,下移到社会大众之中,从而使社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德治社会”,实现孔子心中的政治理想。
(三)《论语》对《尚书》中罚的继承和发展
在孔子那里,“明德”成了最主要的部分,而“慎罚”则相对来说变得不被重视了。在《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到“慎罚”,纵观整部《论语》,可以发现,只有两个例子孔子谈到了刑罚。一是“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二是孔子认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第一则材料提到了要赦免小的过错,这继承了《尚书》中“慎罚”的观念。第二则材料谈到了刑罚的“中”,即刑罚要合适,也体现了“慎罚”。虽然孔子很少谈刑罚,但是孔子并非不重视刑罚,只不过在他看来,刑罚应该是从属于礼乐之后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礼乐才是刑罚的前提。孔子提倡的礼乐制度,特别是礼,就已经包含着刑罚的作用了。
在谈到治国的理念时,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应该主要用道德和礼来使人心归服,而不是使用刑罚。从这一点来说,孔子将《尚书》中的“慎罚”观念进一步淡化,突出礼的作用。礼是道德活动规律,是人应该为的,而刑罚则是一种管束,是强制性的礼。相比较而言,礼更具有生命力,这是因为礼更有人性,更有道德修养的导向作用。除非到万不得已时,才会用到罚,用到刑。然而,在孔子构想的人人有德的环境中,只需要人人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监督从而成贤至圣。只要人人都有德,那么“罚”也就失去了必要性。
因此在《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刑罚。而更多地谈仁谈礼谈君子之道。在孔子那里,以仁这种德为核心,使人人修养自身的德,以礼作为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别说“慎罚”了,甚至连罚都不再成为社会的需要。毕竟在人人都是君子的社会,是不需要刑罚来加以惩治的。这样才能够达到孔子的“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
三、结论
从《尚书》到《论语》,对“明德慎罚”观念变化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孔子。孔子从《尚书》中吸取了众多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对自己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启示。孔子在继承“明德慎罚”观念的同时,进一步将“明德”与“慎罚”分开而论,在两者关系中,孔子更注重德的一方面,将德进一步发展为“仁”的核心思想,并且将德的范围扩大,下移到普通人民群众之中,使人人都有德。而对于罚,孔子不仅淡化罚的作用,而且突出“礼”的约束作用。从而形成了孔子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孔子对“明德慎罚”的发展,构成了孔子政治论的核心部分,在其政治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孔子进一步突出仁、礼的观念和作用,也对其修养论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丰富了其人学思想。他对“明德慎罚”的继承与发展,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打破了德在春秋之前统治阶层的专属。在春秋时代,满足国民阶级的需要。此外,也正因为春秋时代的动乱,孔子才渴望用“仁”和“礼”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恢复先代的稳定繁荣,从而结束混乱的局面。此外,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的这种思想对后代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上熠熠生辉。孟子继承了孔子“以德治国”的观念和仁、礼的核心思想,进而提出“仁政”。将孔子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的便是宋明理学家们。不仅如此,随着儒家思想的独尊,历代帝王也非常注重德的修养,重视民众之德,除此之外,更加注重礼对民众的约束。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刑罚也是历代帝王所看重的治国手段之一,然而由于孔子对刑罚的淡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模式下,外儒内法的独特形式。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