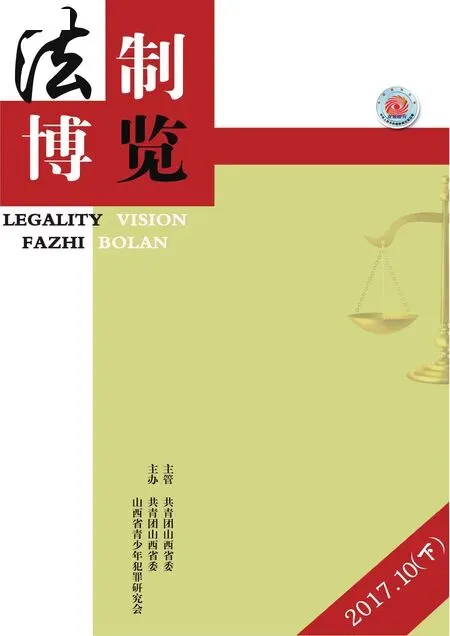强制猥亵、侮辱罪立法再完善思考*
薛陈陈 张思卿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强制猥亵、侮辱罪立法再完善思考*
薛陈陈 张思卿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强制猥亵他人罪指违背他人的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该罪虽然经过了《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正,但是仍然存在主观故意内容不明确、法定最低刑过低、猥亵儿童单独定罪已无必要等不足。应该在主观方面增加主观故意为满足性欲、提高法定最低刑、取消猥亵儿童罪以及将强制侮辱罪的对象扩大至他人。
强制猥亵;强制侮辱;侮辱;男性
一、强制猥亵、侮辱罪的立法沿革
1979年,我国刑法没有对强制猥亵和侮辱妇女进行定罪量刑,但其行为包括在流氓罪中。流氓罪属于典型的“口袋罪”,它主要是指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公共秩序等恶劣的破坏行为。其中包含了侮辱妇女这一行为。
1997年刑法废止了流氓罪这一罪名,将其改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斗殴罪以及寻衅滋事罪四个新罪名。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从流氓罪到如今单独定罪,从之前的妨碍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罪名到被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章节之中,体现了对公民人身权利,尤其是妇女的性自由权的重视。然而遗憾的是刑法的此次修改并没有对男性遭受猥亵的行为做出具体的规定,使得男性的性自由权无法得到法律上的保护。
男性遭受猥亵的案件不断增多,法律对于此方面的空白导致男性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是相违背的,故该条罪名的修改刻不容缓。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其中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加以修改,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改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并且将“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改为“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增加“其他恶劣情节”作为法定刑升格的事由。
强制猥亵、侮辱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从被规定为流氓罪到被单独定罪,再到《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将强制猥亵的行为对象扩大至他人,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不断重视,加强了男性性自主权的保护。但笔者认为其还是有存在缺陷、不足的地方,在此,笔者针对强制猥亵、侮辱罪的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强制猥亵、侮辱罪仍存在立法缺陷
(一)主观故意内容不明确致该罪与侮辱罪难区分
两种罪行的区分是我国理论界的一个传统话题,传统观点日益受到抨击与质疑,《刑法修正案(九)》没有对强制猥亵、侮辱罪与侮辱罪的主观故意内容作出修改,使两种罪行依旧难以区分。强制猥亵、侮辱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的,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本身的作为侵害了妇女的性自由权,而仍旧强制实施。学术界对此意见一致。然而,我国学者对于犯罪是否需要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是激发或满足欲望,却充满争议。倾向犯指行为人作出的行为必须体现内心的某种倾向,当这种内心的特定倾向被发现时,就具备构成这种罪名的要件。[1]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该罪是倾向犯,即行为人要有兴奋和性心理满意度的追求,它才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为强制猥亵,侮辱,但不寻求刺激和满足内心的欲望,则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强制猥亵、侮辱罪的要件。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将主观目的当做本罪的成立条件,这使本罪与侮辱罪在主观故意上很难区分。例如甲男跟乙女因爱生恨,乙女对甲男拳打脚踢,甲男气氛之下,在地铁站当众扒下乙女的衣服,使其赤身裸体。本案中对甲男行为的认定,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甲男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第二种观点认为甲男构成侮辱罪。两种观点不同的关键在于强制猥亵、侮辱罪是否需要行为人具备追求刺激、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如果需要,则构成该罪,如果不需要,则构成侮辱罪。[2]实践中关于这种案例不胜枚举,争议的核心就在于是否把主观故意内容当做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构成要件。
(二)法定最低刑过低致该罪责不均衡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款:“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从该条款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即使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符合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加重情节,法定最低刑仅是五年,这种量刑,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看,强制猥亵罪是故意的行为,人们实施强制猥亵、侮辱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性欲、性刺激,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损害别人的权利,仍然为之,充满恶意,若对行为人的处罚力度较小,行为人接受法律的制裁之后,悔改可能性性较小,则再犯可能性较大;从社会危害性角度出发,行为人的行为破坏《世界性权利宣言》中宣扬的性自由权,威胁他人人身安全,使受害人对社会充满不安感,实践中,多次出现少女被强制猥亵后自杀,少女被当众强制侮辱后不堪羞辱、跳楼自尽的案件,种种事件说明强制猥亵、侮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加害人应当承担较大的刑事责任。但是现行法中,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法定最低刑过低,使罪责刑失衡。
(三)猥亵儿童行为单独定罪无必要
猥亵儿童罪,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之外的方法对儿童(包括男童和女童)实施的淫秽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刑法条文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了强制猥亵妇女罪,第三款规定了猥亵儿童罪,“妇女”和“儿童”的区别是两罪名的重大区分。
通过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婚姻法》等,可以看出我国注重对儿童权益的保障,所以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之后,仍然保留了猥亵儿童罪,只是把强制猥亵的对象由“女性”改为“他人”,“他人”包括十四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儿童。由此可知,“他人”已涵盖了儿童,猥亵儿童罪对象与强制猥亵他人罪对象重合。此外《刑法修正案(九)》取消嫖宿幼女罪,将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行为以强奸论,按照刑法条文内部体系完整,对猥亵儿童行为单独定罪已无必要,完全可以按照强奸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升格法定刑即以强制猥亵罪结果加重犯的方式解决。
(四)将强制侮辱的对象仍然限定为妇女不妥当
强制侮辱妇女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妇女的人格尊严和性的不可侵犯权,目的是寻求精神刺激。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鉴于妇女在生理、身心方面的特殊性[3],人们一贯重视保护妇女利益。但是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男性遭遇女性强制猥亵、侮辱和有男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强制猥亵、侮辱,因为刑法的不完善,导致男性无法像妇女一样受到《刑法》二百三十七条同样的保护,只能以其他罪名对加害人进行定罪量刑,这对受害的男子来说是及其不公平的。[4]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后,将强制猥亵妇女罪改为强制猥亵罪,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相符,也符合《国际性权宣言》中对性平等权的尊重,但是《刑法修正案(九)》仅仅只是对强制猥亵罪的对象进行了修改,强制侮辱罪的对象仍然是妇女,这就相当于回到了《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男子遭遇强制猥亵却无法适用正确条文的阶段。若男性遭遇强制侮辱,由于缺乏法律的规定,只能适用其他法律加以解决,但是其他法律的处理结果往往轻于《刑法》第二百三十七的结果,比如法官会以侮辱罪对加害人进行定罪量刑,通过对刑法条文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侮辱罪的法定刑低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对强制侮辱的对象也可以是男子的忽视造成了刑法条文内部不统一的局面,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时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由于强制猥亵、侮辱罪存在上述缺陷,笔者将针对上述缺陷,综合我国司法实践和各国立法,对该罪的不足作出完善。
三、强制猥亵、侮辱罪立法再完善思考
(一)增加主观故意为满足性欲
从中外学者对强制猥亵、侮辱的理解来看,大多数学者承认行为人主观目的是为了追求性刺激和满足性欲。[5]笔者支持该种观点,对强制猥亵、侮辱罪是否是倾向犯持肯定意见,即认为强制猥亵、侮辱罪主观故意为满足性欲。从司法实例出发,例如医生出于为妇女治疗身体的目的,对妇女进行一系列抚摸行为,如果仅仅只是因为医生实施了猥亵行为,而判决医生犯强制猥亵、侮辱罪,这对医生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而从倾向犯的角度出发,因为医生不是出于满足性欲的目的,那么就不可认为医生做出了强制猥亵、侮辱行为。笔者认为对于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理解,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将行为人是否具有刺激性欲、发泄感情的主观目的作为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判决要件,我国可对条款进行修改,增设主观故意为满足性欲这一主观要件,将主观目的正式确定化。
(二)提高法定最低刑
罪责性相适应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基本原则,贯穿于刑法的始终,对刑事立法、司法及定罪量刑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强制猥亵、侮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源于性的不可侵犯性,当代社会关于性自由权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不管是强制猥亵还是强制侮辱行为,对于心理防线比较薄弱的人,对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人来说,加害人一时的行为会给受害人带来一生的伤痛和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刑法条文将该罪的法定最低刑规定为六个月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定最低刑是法官据以给罪犯定罪的法律依据,即使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但是对罪犯的定罪也不可低于法定最低刑,法定最低刑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为了使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更加完善,使法官对触犯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加害人能够受到本该有的处罚,使民众更加信服,使立法公正与司法公正能够实现,立法者应该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可以以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为蓝本,将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法定最低刑提高到一年有期徒刑,保护性自由权不受侵害,增强刑法的威慑力和社会警示力。
(三)取消猥亵儿童罪,将猥亵儿童行为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
笔者认为,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他人”包括14周岁以上的男性女性和14周岁以下的儿童,猥亵儿童行为单独定罪已无必要,所以,为了使刑法的第二百三十七条更加完美,漏洞得到填补,应按照《刑法》二百三十六条取消票数幼女罪,将该类行为一律适用关于强奸罪,但是属于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的立法模式,将强制猥亵罪和猥亵儿童罪两罪合并为一罪,保留强制猥亵罪,取消猥亵儿童罪。鉴于儿童的身心不成熟,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侵害,并且受到侵害后造成的后果比一般人更加严重,呼应社会加强对儿童权益保护的要求,应当把强制猥亵儿童作为强制猥亵罪的结果加重情节,即将猥亵儿童行为作为强制猥亵罪的法定刑升格情节。对于强制猥亵儿童的加害人,加大对他们的惩罚力度,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儿童受到来自外界侵害的次数。
(四)将强制侮辱罪的对象扩大至他人
随着妇女权益的不断扩大,女性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因为受男权主义思想长期的压迫,女性在地位平等之后,渐渐不受世俗的约束,在现实生活中也会主动地对男性进行强制威胁、侮辱,并且同性恋现象的明朗化,男性对男性的性行为再也不是那么难以启齿了,所以男性受到来自男女方双重压迫,该现象的出现使男性再也不是处于强势地位,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也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话题。[6]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为了使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更加完善,能够全面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立法者可以参照《刑法修正案(九)》关于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将强制猥亵妇女罪改为强制猥亵他人罪的规定,将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将强制侮辱罪的对象扩大为他人,全方位地扩大对男性权利的保护,这样做更加公平合理,也是顺应时代发展。
四、结论
《刑法修正案(九)》对强制猥亵、侮辱罪的修改是我国对男性性权利保护的一大进步,表明了立法者的态度。这一立场的明朗化使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很多难以判断的难题都迎刃而解。但是这一次的进步是有限的,关于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很多方面都没有考虑进去,在接下来的立法中,应当继续坚持这一立场,继续完善强制猥亵、侮辱罪,削减实践中无法可依局面的涌现。
[1]陈家林.<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后的强制猥亵、侮辱罪解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8-75.
[2]丁友勤,胡月红.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争议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1).
[3]刘德法,彭文华.刍议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评刑法第237条规定之缺陷和不足[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1,16(2):55-59.
[4]金泽刚.由男性遭受性侵害案看性犯罪的法律变革[J].法治研究,2015(3):39-47.
[5]玉品健.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的再讨论[J].法制与经济月刊,2007(10):65-66.
[6]李银河.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1-31.
*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编号:201610370532)。
D924.3
A
2095-4379-(2017)30-0037-03
薛陈陈(1996-),女,汉族,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张思卿(1997-),女,汉族,安徽池州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