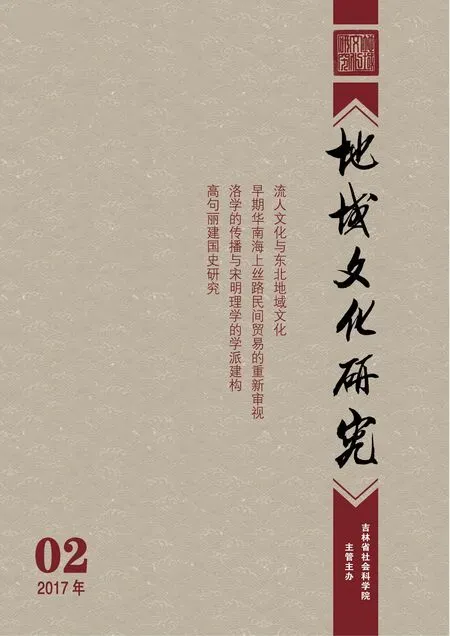内藤湖南与“满洲”①的文献搜集事业
林志宏
内藤湖南与“满洲”①的文献搜集事业
林志宏
内藤湖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学者,尤重“满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内藤中国史研究之盛期处于20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关系既密切又对立的时刻,这使其成为一个在学术与政治上无法分割的典型,学界因此对内藤湖南的历史定位颇具争议。而如何看待内藤湖南在“满洲”研究中的地位及对“满洲”文献搜集事业之影响,从而探讨内藤湖南与“满洲国”文献工作的关系,论究内藤对“满洲”的观察以及其学术思想发生的转折,将有助于深刻认识内藤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内藤湖南“满洲”文献搜集 历史定位
直到今天,要了解近代日本汉学界乃至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内藤湖南依旧系无法回避之人物。他代表着日本对中国研究之典型,是厘清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汉学或中国研究实况之关键。身为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内藤身处于20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关系既密切又对立的时刻,同时他也是一位在学术与政治上无法分割的典型。对此傅佛果(Joshua A.Fogel)曾形容内藤湖南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张地拉扯,②Joshua 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ō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这也使得对他的评价直到战后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差异。③那些盛赞内藤史学的研究贡献者固不必论,而给予严厉批判的人,可见[日]五井直弘《近代日本东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第135-138页、第154-155页;[日]增渊龙夫:《历史家の同时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第49-82页。譬如,增渊龙夫说内藤观察中国时局,系以“文化中心移动说”来确立日本侵华的正当化,缺乏尊重中国本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主体性。④“文化中心移动说”指的是每一民族各有其文化中心,随着时势推移,文化中心则不断地移动,且不受国界限制。内藤湖南认为,日本充分吸收中国文化,犹如中国之内的一省份;而历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吸收中国、西洋文化后,将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化体系的中心。见[日]增渊龙夫《历史家の同时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第77页。对此,已有学者提出反省,见[日]谷川道雄《戰後の內藤湖南批判──增渊龙夫の场合》,收入內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第364-391页。
然而,人们对内藤湖南的历史定位产生争议之际,不该忘了他对东北亚历史的研究和言论应放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中解读。伴随日本帝国“大陆政策”之展开,内藤踏上东洋学术研究的历程。他带领着一批批继起者探究中国东北史地领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据内藤女婿鸳渊一形容:将近40年期间,内藤湖南对“满洲”具有相当的研究,非惟孜孜不倦地为日本政府献策,甚至直到最后临终之前,仍与其关系密切。①[日]鸳渊一:《北平奉天故宫所藏の蒙古源流に就いて─并せて故内藤博士遗业の一斑に就いて─》,《史林》第19卷第4号(1934年10月)。换言之,这不但是内藤终生备受瞩目的转折点,也是人们经常提及之处。
本文经由论究内藤对“满洲”的观察以及其中发生的转折,重新思考他对学术与政治的坚持。此外,如何看待“满洲”研究中内藤湖南的地位,尤其是他对文献搜集事业的影响。笔者认为,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并非止于内藤湖南的有限生涯内,而是要持续到其身后“满洲国”的文化问题上。这个经由日本扶植的伪政权,历14年之久,直迄二次大战结束为止。除了成为日本战时“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一员外,②Louise Young,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它也积极发展所谓“满洲”的地方特色。可是我们又该怎么审视其“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所带来的历史遗产呢?内藤湖南应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
一、对“满洲”的观察与论点
1932年3月“满洲国”建立以前,内藤湖南对“满洲”的学术工作和活动情况就已展开。分析内藤的思想变迁,有必要追溯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之发展状况。如众周知,内藤的祖父、父亲都是幕末时的汉学家,对其汉学兴趣的培养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这并非是关键的影响因子。近人曾指出内藤思想中具有历史辩证法的观念,“恐怕与德国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有关”。③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6页。尽管这一点极难获得证实,不过应非空穴来风。至少在面对经世实学的思维上,日本各界对传统汉籍经书的各种学问,已承认不敷现实与时代需求。19世纪末内藤湖南以革新江户汉学自命的同时,特别强调要重视历史学本身的特殊性。李庆分析日本近代汉学历程时,认为内藤“史学观念有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④李庆:《日本汉学史:起源和确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41页。,系指类似脉络的理解。至少从1900年起,内藤湖南认为学术调查重点不应以“经、子二部之学”为限,还要兼顾“清朝以来的掌故、实录之类”资料,并且留意金石、塞外碑刻乃至铜器金文等等。⑤[日]内藤虎次郎:《支那調查の一方面(政治學術の調查)》,原载《日本人》第111号(1900年3月),收入吉川幸次郎、内藤干吉编《內藤湖南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2卷,东京:筑摩书房,1969-1976,第162-165页。细思其主张,多少呼应当时世界上历史主义(Historicism)风潮,也可能受到清代史家(如赵翼)著作之影响,与同期中国思想界摆脱经学而强调史学⑥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341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到20世纪后,内藤开始留心朝鲜、“满洲”等地情势,并多次往赴考察。1902-1912年,他曾实地探查“满洲”有6次之多。开始是以记者身份前往,后来系为学者之名义。①参见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滿州帝國──橘樸の思想との比較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內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第220-221页。1902年10月,内藤任《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被派至“满洲”观察,并对官方提供诸多建言。那次经验让内藤目睹了俄国势力在辽东半岛的统治,特别是有关兵力的集中、煤矿的发现及开采、森林采伐等。日本国内颇有以经济因素来主张非战者,高唱要以强硬态度对俄国宣战。②[日]内藤虎次郎:《追想雜錄.日露戰爭の前後》,《全集》第2卷,第745页。又见内藤虎次郎《满洲撤兵》,原载日期1903年4月28日,《全集》第3卷,第527-528页。其后,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最终日本获胜,获得“南满”的特殊权益。就在战事大致砥定、双方签署休战协定的前夕,内藤湖南接受了外务省的委托,再度前往“满洲”调查实况,此后仍有3次。
内藤湖南之所以能深获日本官方支持,并且得到政府经费,绝非毫无凭借,实际上跟他屡屡针对现况发表言论有关。在担任记者尚未来到“满洲”以前,他已公开呼吁:有必要对中国进行学术调查及研究工作,同时希望工商业的资本家们给予资助。③[日]内藤虎次郎:《支那の學術的調查》,原载日期1902年4月24日,《全集》第3卷,第413-414页。直到日俄战争期间,他还积极献策,主张对占领地施行民政调查。对此,内藤似乎抱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强调日俄战争的后果与中日甲午之战的性质有所不同,不仅须先有军事调查的准备,更该留意民政问题;特别关于殖民台湾带来的经验中可知,“满洲”有其特殊背景,颇值得注意。首先,内藤说此处是清帝国的发源地,有必要留心那些过去的历史文献资源。其次是这里的情况发展殊异,乃“旗地民地,犬牙相错”,既有关内各种杂税的存在,又有“满洲”旧俗,因此先实施民政调查之后,才得以进行有效统治。④[日]内藤虎次郎:《占领地の民政調查》,原载日期1905年1月15日,《全集》第4卷,第142-143页。相关讨论可见陶德民《日露戰爭前後の「满洲经营论」─內藤湖南の满洲军占领地民政调查をめぐって─》,收入氏著《明治漢學者中國─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论策─》,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第151-196页。显然内藤湖南的大声疾呼,既引人注目,也符合了日本官方的需求,故受到委托来调查“间岛”问题。⑤“间岛”是1880年以后,朝鲜人大规模越境开垦图们江及以北地区的创名,最初只是指图们江中的一小块岛地,后扩展至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己保护条约》,视间岛为朝鲜领土,乃于龙井村设“统监府出张所”,派官员管理之,故间岛问题又成为清日两国的外交问题。参见李盛焕《近代东アジアの政治力学─间岛をめぐる日中朝関系の史的展开─》,东京:锦正社,1991年,第41-94页。至于内藤湖南对间岛问题的前后经过与言论,进一步可见名和悦子《内藤湖南の国境领土论再考:二〇世纪初头の清韩国境问题「间岛问题」を通して》,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在此期间,他辞去了《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工作,随即转换身份成为京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讲师,并开始进行东北亚的学术调查。
1910年8月“日韩并合”期间,朝鲜、日本舆论界反响激烈。⑥韩国学者就当时所搜集大量的日文报纸社论、杂志论说来看,发现许多文字支持合并主张,从诉求“日鲜同祖”、强化朝鲜李氏恶政、殖民地开化与负担等加以正当化,见姜东镇《日本言論界と朝鲜,1910-1945》,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4年,第7-8页。不久,随着“大正民主”时代的来临,许多日人思考对外殖民可能带来的扩张及其弊端,不少自由民主派在面临国内经济恶化及社会风潮等问题丛生时,提出所谓“小日本主义”(亦即坚守日本本土,无须向外殖民),借此批判军国主义的发展。朝鲜因为距离日本仅有一海之隔,特别得到各方关注,其中更牵涉到有关“满洲”的占有及统治与否等问题。如知名的法学博士末广重雄积极主张放弃论,引起政坛之注目。①譬如东洋经济新报社记者石桥湛三,便是大力引用末广的论点。见宇都宫明《石桥湛山の生い立ちと人物像》,《圣学院大学总合研究所纪要》第39号(2007年9月),第542-543页。而内藤湖南则恰恰相反,坚持保留。他认为日本对待中国东北的统治问题,至少还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之经营,故在经济资源方面无须担忧;而抱持放弃殖民地的念头,至少对于“满洲”来说,实无必要。②[日]内藤虎次郎:《南满洲问题》,原载《武乃世界》第2年第7号(1913年7月),《全集》第4卷,第495-499页。
为何坚持要保有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这应是所有研究内藤湖南的学者所深感兴趣的。当我们留意到内藤多次发表对“满洲”言论与想法之际,更应体认与他自身处境有关。简单地说,是对当地各种历史文献的关注,鼓动了内藤公开强调日本与“满洲”的关系。
内藤湖南不止一次传达自己对“满洲”历史资料之兴趣。在1905年3月发表的《东洋学术的宝库》一文中,他提醒读者要特别留意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意义。尤其在北方三阁(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热河文津阁)藏书均有散佚的疑虑之下,文溯阁本特别值得珍惜保护。另外,奉天西门的喇嘛寺内藏有藏文、蒙文、满文等佛经,均该力求图存。除典籍之外,内藤还倡吁要重视“满洲”原来的文化实物,包括兴京故城的遗址,无论是史迹还是古碑等。③[日]内藤虎次郎:《东洋学术の宝库》,原载1913年3月8日《全集》第4卷,第177-178页。然而,这样的主张对清季东北微妙的局势来说,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尽管内藤后来饱览了《满蒙文藏经》、文溯阁《四库全书》《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等,可一度向盛京将军赵尔巽要求观看史料时,却被拒绝。④这可从内藤湖南与当地差役的笔谈中可略知倾向,见陶德民《内藤湖南の奉天调査における学术と政治─内藤文库に残る1905年笔谈记録をめぐっ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1号,2006年3月,第131-143页。
尽管内藤个人无法完全达成搜罗“满洲”文献的工作,不过这项理念却暂在另一机关建置下获得落实,且短期施行了一段时间。1907年4月,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筹设调查机关,以“文装的武备”论作为核心概念,其中辖下的“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委任由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主其事。⑤有关满铁调查部初期创立的概况,见小林英夫《满铁调查部の轨迹,1907-1945》,东京:藤原书店,2006年,第27-54页。“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直到1913年野村隆太郎担任总裁后,改由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负责,正式切断关系。这个调查部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结合史料分析与实地调查同时进行,同时以“集众之力”来完成史书编纂工作。它先后延揽了松井等、箭内亘、稻叶岩吉、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等学者,共同为研究满蒙史建立基础,并促进了日本的“东方主义式”想象。⑥黄福庆:《论后藤新平的满洲殖民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究所集刊》第15期上册(1986年6月),第393-395页。有关白鸟库吉与东洋史学所带来的影响,见S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顾名思义,该调查部主要以“满洲”、朝鲜地域为范畴,虽然强调的是纯学术层面之工作,但仍期待能对实际统治产生助益。⑦[日]伊藤武雄:《满铁に生きて》,东京:劲草书房,1964年,第25-27页。1910年,此刻正传授东洋史学的内藤湖南即对此一现状深表信心,表示白鸟等人能够关注到朝鲜地区金石拓本的搜集,一定可以补充朝鲜《李朝实录》不足之处,甚至还能填空日朝关系史等相关课题。有意思的是,他对扩展到“满洲”史迹方面的研究,也认为指日可待。⑧[日]内藤虎次郎:《东洋史学の现状》,原载《大阪朝日新闻》1910年1月8-9日,《全集》第6卷,第19-21页。
就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进而激发了内藤湖南思考自己的学术生涯及志向。此时他关心与着墨的部分,并非纯粹来自书本上知识,而是跟时势密切有关之事,亦为对现实的反映。例如,当革命潮流风起云涌之际,内藤曾提醒日本读者为何还要持续学习中国历史。就在1911年革命前夕的短文中,他说:除了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外,中国历史无疑是“东洋全体的记录,也丰富了邻近日本、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①[日]内藤虎次郎:《支那史の价值》,原载《朝日讲演集(一)》1911年8月7日,《全集》第6卷,第42-47页。。从这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内藤湖南关心的是他所谓的“东洋”,中国历史的功能系在提供“东洋”之内容。同样秉持类似态度,内藤则是将关怀触及“满蒙”地区的历史。他的改变既是受到清中叶以来蒙古研究风气的影响,又与辛亥革命后与罗振玉的交往密切相关。②[日]内藤虎次郎:《支那學問の近状》,原载《朝日讲演集(一)》1911年8月8日,《全集》第6卷,第48-50页;内藤虎次郎:《支那历史家の蒙古研究》,原载《学艺青年》第2卷第5号(1915年11月),《全集》第6卷,第92-95页。相关讨论亦见渡邊健哉《內藤湖南によるモンゴル時代に關する史料の蒐集》,《中國─社會と文化》第25号(2010年7月),第211-229页。在1915年为稻叶岩吉的《满洲开发史》写序时,内藤湖南又说:要了解今日“满洲”,自然须从历史上的“满洲”得悉;知晓古代“满洲”的历史,才能对今日“满洲”如何开发有通盘的了解。因为随着历史之脉动,过去不单是死的事实,而是显然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③[日]内藤虎次郎:《「滿洲發達史」序》,原文撰于1915年4月29日,《全集》第6卷,第292页。
因此,虽然进入大正时期,内藤湖南对“满洲”的观察及思想,仍不乏深具时代与政治互动的面向,特别是其借学术所达之目的。这可从1918年他在为满铁读书会至东北各地进行讲演之际,仍不忘面会张作霖,甚至描写张氏“精悍之气飘于眉宇之间”,对学者亦表尊重的印象之中得悉。④[日]内藤虎次郎:《余が見たる張作霖氏》,原载《周刊朝日》1922年7月30日,《全集》第6卷,第220-222页。此外,1925年日本外务省有意借庚子赔款进行文化亲善工作,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来结合中日两方人士,内藤也代表日方委员,负责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有关史部、集部之编纂。⑤[日]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
二、“满洲国”建国前后的心境转折
1932年3月伪满洲国的出现,不惟造成国际舆论之争议,也引起日本国内社会各层面许多冲击和影响。⑥譬如对帝国外交政策来说,论者以“二面的帝国主义”(一面从属、一面侵略)进行相关探讨。见[日]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研究史论》,东京:校仓书房,2001年,第9-39页。尽管身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内藤湖南已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术课题上,但针对东北刚成立的政权,带有强烈评论时事记者性格的他还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综观这些文字的内容,与其说是内藤对“满洲国”一事发表观感,不如说是有意展现自己关于日本政局的立场。只不过,内藤个人是把目光投射到久已熟悉的中国东北地区,并借此抒发己见。这三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分别是:《关于建设满洲国》(滿洲國建設に就て)《关于满洲国今后的方针》(滿洲國今後の方针に就て)以及《大阪每日新闻》上的谈话报道。
有关“满洲国”建设的意见中,内藤湖南特别针对新建立的政权抒发己见,强调秉持以下的几项主张来进行。首先,他认为要贯彻“满洲国”成为“和平乐土”的精神,以作为世界民族共同的乐园;至于该国所援用共和政体,内藤则认为似乎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次,由于中国本身历处不安之局,建设“政权”须是在日满双方合作的前提下;既要把过剩的日本人口向“满洲”进行开发,也要运用日本的资本及能力对当地人民施行教育。最后内藤湖南以偌大篇幅,诉说“满洲国”应该如何加以组织及运用人才。他的主要思想乃透过教育方式培养专业人才,一方面使其具备国际观,另一方面则是采取“自治”、尊重旧习的方针,而非仅一味地受到日人(尤其是军部)之控制与指使。①[日]内藤虎次郎:《滿洲國建設に就て》,原载《大阪每日新聞》1932年3月1、5、7、8日,《全集》第5卷,第170-180页。
就这篇名为《关于建设满洲国》文章来看,内藤的想法似与当时关东军之立场南辕北辙。而他的不满及其批判声音之代表作《关于满洲国今后的方针》一文更显直截了当。他公开宣称:“人为国家”将来会朝向怎样的发展,其实很难预测,姑且不论;且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有很大的距离。然对“满洲国”实际情况来说,目前的情形反倒是比较缺乏足够的治理人才,尤其是那种能体认现状、熟悉历史,乃至思索未来应具备何种组织等方面的人才。更确切地说,内藤湖南在该文中意识到“满洲国”真正领导者,并非属于该国之内人士,反而全由日本官僚来负责。对他而言,如此先建立的政权,无疑缺少统治主体性,根本无视乎自身的历史渊源,结果等于是画虎类犬,错把“满洲”复制成为日本的殖民场域。②[日]内藤虎次郎:《滿洲國今後の方针に就て》,原载《大亚细亚》第1卷第3号(1933年7月),《全集》第5卷,第181-185页。这篇与日本政府国策并不同调的文字,写于“日满文化协会”大会召开前夕,也充分展现出他对建立“满洲国”的期待与思考。
谈到内藤与“满洲国”的联系,就不能不论及“日满文化协会”。根据报载,“满洲国”建立后不到一年,日满双方有意设置教育文化方面的机关,目的为了达到“亲善融合”“相互视察恳亲”“助长调查研究”等工作,并开始关注境内古迹文物的调查。③《设立日满教育协会,经日满两国要人发起》,《盛京时报》1933年1月11日,第1版;《国内古迹古物出现有待,文教部已令各省调查》,《盛京时报》1933年6月10日,第2版。它的出现乃源自两项因素。首先是20世纪20年代中叶,为了培养亲日人士,日本对华推动“东方文化事业”,而“满洲”政权的建立使得中国东北有了新的变化,迫使文化工作必须区隔,另外尝试单向“对满洲”活动。④[日]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第668页。内藤湖南曾经担任“东方文化事业”的日方委员,加上长期对“满洲”有所研究,所以再合适也不过。其次,除了强化“满洲国”与日本关系、达成“文装的武备”功能外,该协会还有一项主要目标,即体现“满洲”存在的渊源及价值,借此诉诸建立“满洲国”的合理性。在此准则上,一面强调“满洲国”步入安定之局,另一面则要“消化”军事侵略后的果实。最先谋立文化协会的人,系担任关东军临时顾问的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为了能够继续先前开展的各项调查活动,联系内藤湖南等京都学者,起草了成立儒、佛研究机构的请愿书。该项建议在日本广获回响,尤其是得到东京方面研究满蒙问题专家以及官员的支持,决定设置“国立文化院”,最后演变为“日满文化协会”。⑤关于这段曲折过程,见[日]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歷史──草創期を中心に》,京都:作者印行,2006年,第25-30页。
内藤湖南虽非“日满文化协会”发起者,却系当中的关键性人物。当时有几项考古活动、文献整理的工作陆续开展,亦可看出内藤居间扮演的角色。譬如1933年7月末,位于奉天城东的靖安军兵营发现“满洲”正蓝旗人达海的墓碑三通。①分别为:康熙四年诰封达海碑、康熙九年敕建达海碑及与达海密切关连的钮祜禄氏碑,见[日]佡俊巖《达海墓考证》,《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第52-54页。达海系满文的创成者,据传精通满汉文,为清朝关外时期利用蒙古文编成满文的硕学之士,惜年仅36岁。此一考古消息经由传开后,立即吸引内藤女婿鸳渊一前往探究。鸳渊氏时为广岛文理大学教授,以访契丹辽文化之迹为名而来,并访问奉天满铁图书馆长卫藤利夫,且在报纸上发表谈话:
达海为清朝太祖、太宗时代之学者,由蒙古语编出满洲语,为元音之完成,诚可谓清朝文化之恩人也。达氏36岁逝世,实可痛惜之壮学者也。不料该氏之碑,在数百年之今日且在“满洲国”成立后而被发现者,诚为吾等后学之莫名欣快者也。②《清朝文化之祖达海之墓碑在靖安军兵营发见》,《大同报》1933年8月15日,第4版。个别标点偶有更易。该则报道稍早还在奉天地方报纸及日本报纸之中呈现,唯内容较为简略,见《满语鼻祖达海墓已发现地址判明在城东五里地点,各考古家来奉共同研究中》,《盛京时报》1933年8月10日,第4版;《満州语、创生者の墓発见清の太祖时代の达海》,《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8月10日,第3版。
强调古坟挖掘与“满洲国”之成立相互呼应。此则消息也透露了内藤相当留意“满洲”境内对于清代文物的考古活动。另一件事是罗振玉将昔日从天津携来旅顺的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假借肃亲王善耆的旧邸设置“库籍整理处”,并“招处员十余人从事整理”。罗氏能够饬理旧籍,据其后人所称乃因“1933年秋天得资”缘故。③罗继祖撰,萧文立编校:《永丰乡人行年录校定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收入罗振玉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附册,卷下,总第111页。目前尚无从获悉所谓“得资”之来源,但显然与留居在“满洲”的日人有关。根据金毓黻日记可知,④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4册,总第3016页,1933年3月23日条记曰:“松崎君函言:罗雪老携水野梅晓于午后到奉。三时到站迎迓,雪老未来,仅晤水野君。晚饭于鬫宅。水野君提倡影印《清实录》及《四库全书》,又雪老存《清内阁大库老档》,亦拟整理之,其愿颇宏。”当中呈现的相关人物松崎鹤雄、罗振玉、阚铎、水野梅晓等人俱参与“日满文化协会”,可知其关系。时任满铁大连图书馆汉籍部主任松崎鹤雄以及进行宗教文化活动的西本愿寺僧侣水野梅晓,都积极主张参与罗振玉之整理文献工作。可能透过两位日人的关系出面协调,日本外务省愿意出资帮忙。所以等到后来终于在成立“日满文化协会”之际,罗振玉被举为常任理事,倡议集资影印清代列朝实录。内藤湖南时为日方理事,立即“首附议赞同,乃得印行”。⑤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校定本》卷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收入罗振玉撰,萧立文编校《雪堂类稿》附册,卷下,总第111-112页。
由此推知,重视“满洲”文献与史料传承,毋宁成为内藤湖南面对伪满政权时所思索的课题,也是他托付参与“满洲国”之旧友所期待的使命。因此,他在临终前一年,尽管冒着身体微恙之虑,仍风尘仆仆地赴中国东北,结识的旧雨新知,筹备各项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尤其是“满洲国”方面的清朝遗民旧臣,因为有共同学术兴趣为基础,内藤非常乐意同他们交流有关文献典籍的意见,留下附庸风雅之迹。现存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有封书信,是由“满洲中央银行”总裁荣厚(后任“日满文化协会”会长)所写。其中便叙及两人相见,一共长谈八时,并饱览了内藤家中的藏书,甚至废寝忘食,以至于内藤夫人“笑为书痴”。值得留心的是彼此交谈的内容,仍止于学术研究上。①《湖南宛荣厚书简(昭和9年[1934]1月26日)》(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湖南文库”馆藏),编号:25,各种关系资料(10)日满文化协会关系书类2-1。
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内藤湖南最后还有一篇关于“满洲”的文字报道,乃为介绍“满洲国”实施帝政特辑而撰。这篇文章主要进行了如下的阐述:伪满政权建立之历程中,帝政已成无可抗拒之势;因此,在推动巩固“皇帝”成为领导中心的同时,寄望“皇帝”能够有所作为,发挥像是历代贤君那样的才能。在字里行间,我们甚至发现内藤投注更多的笔触,刻画所谓的“贤君”的形象。例如,他把众所熟知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比附成东汉光武帝,说溥仪“喜好学问,人格高尚”,虽然期待完成“中兴”大业,但应该要眼光更加长远,追效清朝康熙帝的德政,这样方始“满洲国的将来可充满希望”。除此以外,内藤湖南个人更建议“满洲国”要考量自身传统与日本有所不同,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治国方针。换句话说,即使是招募日本的顾问,也应该寻求熟悉明治维新后那些身怀杰出见识的人物,而非照搬现今那些在日本壮年行政官员的各项做法。②[日]内藤虎次郎:《国家创立当时から事实上既に皇帝 今日この结果は宁ろ当然 亲み深い执政の人德》,《大阪每日新闻》1934年1月21日,第4版。细思全篇,仍有意借此讽喻日本国内官僚。由于这篇文字实在太多属于应酬性的内容,后来并未收入于其全集之中。
从上述三篇文章可以洞察内藤湖南对“满洲国”具有矛盾交织的心态。他一方面期待其政权要能维持“自治”局面,并从历史中来找寻学术根据,进而达成合法性基础所在;另一方面,又不愿日本军方过度以武力介入“满洲”问题,采取“人为”方式打造一个新国度,甚至沦为类似殖民地的“傀儡”。但是内藤湖南的“异议”声音并未获得当时伪满国家当政者的重视。当权者选择了他为日满文化合作所规划的“蓝图”,却避开了正视关于日军或日本的自我反省那一部分。
三、“满洲”文献与知识的再生产
诚如前述,内藤湖南关注“东洋”的思维,显然以整体的方式来观察东北亚史,而环顾“满洲”正是其中构想之一。他的学生稻叶岩吉曾形容:内藤极力主张要研究辽东史实,最好先从掌握朝鲜的资料入手。原因是中国史书本来对辽东的记载甚为简略,而朝鲜则因近在咫尺,过去由于朝聘往来之故,殆无虚日,所以“彼邦悉纪载之”。犹可论者,辽东和朝鲜的历史经过相互比对后,不但彼此毫无失据,反而还能充分得到补充与印证;亦即“在辽东不能得者,在朝鲜则往往得之,在辽东所得而定其究竟者,在朝鲜则得其旁证焉”。稻叶自己即是采取类似的办法研治东北亚史,而且受益颇巨,因此笃信地说:“近十年来,依其指示求之,果多有所获,乃知湖南先生之言为不刊之论也。”③引文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总第2839页,1932年7月11日条。稻叶氏能运用朝鲜史料,特别对入关前的清朝历史带来更多创获之见,也可从夏鼐比较萧一山《清朝通史》一书里得悉。见夏鼐《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册,总第183页,1933年7月28日条。其实稻叶岩吉所谈的史料典籍“互证法”,大抵成为当时研究满鲜史的日本学者所共同抱持之研究态度,类似见解也出现在晚年内藤湖南为今西龙遗著《百济史研究》撰写的序文中。根据内藤的说法,过去探讨朝鲜古史时,不免过度倚赖日本古书,但今西龙则是另辟蹊径,反从朝鲜的记事资料着手,甚至还比照中国史籍,重新恢复朝鲜古史的面貌。①[日]内藤虎次郎:《〈百济史研究〉序》,原载于1934年3月《全集》第6卷,第319页。据此扩大可知,对于厘清东北亚历史的情况,内藤等人是将“满洲”、朝鲜、日本等视为一体来衡量,至少反映在史料中即是如此。
经由上述研究东北亚史的构想,我们才能了解内藤在“日满文化协会”之主要工作目标。就在“文化协会”成立后不久,内藤湖南向金毓黻“谈满洲文化事业,颇具条理”,其大略包含研究、保存、出版三方向。这段谈话的篇幅相当长,后来纳入到金氏日记,显见重视;其中也呈现出不少内藤自己对此项工作的蓝图。以下分述之。
有关“研究”规划上,主要系指主题而言,大致涉及了历史、地理、制度、经济、语言、民俗、宗教、考古、艺术、建筑、艺文等各项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注之中,内藤湖南强调“往日之研究偏远文献,而今日之研究兼重事实”,尤其关于日本学者先前业已着手部分,“此后更当趋重实地之研究”。至于其他地区,诸如朝鲜、日本、欧美等皆有关联于“满洲”的史料,更该等量其观地加以重视,“朝鲜史中尤多满洲史料,欲彻底研究满洲史,非先从高丽史入手不可”,呼应了前述环顾东亚史的构想。此外,内藤认为这些课题仅仅包括“人文学方面直接之研究”,而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他认为自然科学“则让专门学者为之”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出版社,1993年,总第3170-3171页,1933年10月24日条。。
内藤湖南的经营“满洲史”理念,更重要凸显在“保存”与“出版”两项。他认为:保存不单只有留存原物的功能,进一步还要编列造册目录,方便日后的人们查阅,才能进而达到保护古物之目的。出版则主要借由官方力量,将大部头的书籍加以印行,如《清实录》、文溯阁《四库全书》等。此外,内藤认为评估各项文献搜集工作,还要注意其他地方图书馆有关馆藏,如英国藏《五体清文鉴》;又如《蒙古源流》有汉、满、蒙文三体,“闻德国已将蒙文《蒙古源流》用罗马字译出印行”;其他如日本宫内省图书馆保存蒙文书、由罗振玉在旅顺所清理之档案等,均有刊行之必要。③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出版社,1993年,总第3172页,1933年10月24日条。因为意识到保存和出版的重要,内藤湖南指称中、日、俄学者应互相提携,甚至利用科学方法——考古学来进行,特别是当地的“辽、金时代之宝藏极多,现正待开发”。④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出版社,1993年,总第3172页,1933年10月24日条。
综观上述描述可知,内藤的有关活动虽由金毓黻转述,然约有几项特征:第一,进行“满洲”研究应该要重视有关实地的考察。第二,所谓“满洲”历史,不应局限于当地文献,而是要兼顾在外的资料,如日本、朝鲜等地方。第三,强调史料的保存必须多元,包括了古物遗迹之保护,还有珍稀典籍之出版。第四,结合新学术分科来进行工作,如考古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发展。第五,学者应该协力,不分畛域,共同来深化研究。最后,辽金等朝的历史文物,其实是代表“满洲”文化之特色,亟待开发。
这些整饬“满洲”文献的构想,后来陆续展开,也促成了知识如何转化与再生产的过程。以下要略举几项跟内藤湖南相关的研究、保存、出版事宜,进行论述。首先是在研究上,譬如内藤的女婿鸳渊一,1943年便以奉天市立图书馆、伪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所藏的谈迁《国榷》进行比对,同时发现要比《崇祯实录》更为详尽,且事涉满蒙方面的材料尤多。①[日]鸳渊一:《奉天の国榷に就て》,《东洋史研究》第8卷第2号(1943年6月),第92-114页。鸳渊氏还有《满洲碑记考》一书,亦详述自己多年对“满洲”史料的心得。②[日]鸳渊一:《满洲碑记考》,东京:目黑书店,1943年。此外,文物考古调查工作更在“满洲国”时期此起彼落地发展,像是水野梅晓伙同杉村勇造从奉天出发,历经15日抵达热河承德,在避暑山庄珠像寺发现世界孤本满文《大藏经》,并见到雍正敕版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③[日]杉村栋编:《八十路——杉村勇造遗稿集》,东京:编者印行,1980年,第115页。另一个案则是在1935年9月,安东省发现新的高句丽时代壁画和古坟,池内宏、滨田耕作、梅原末治等学者前往调查,④[日]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歷史》,第126页;滨田耕作《旅の女の話》,《滨田耕作著作集》,第7卷,京都:同朋舍,1993年,第354页。后来更出版《通沟》,又组织“辑安古迹保存会”。⑤“满洲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满洲国史·各论》,东京:满蒙同胞援护会,1971年,页1121。
至于保存与出版方面,前述水野梅晓发现的满文《大藏经》,即在北平特务机关松室孝良派兵“保护”下,以两昼夜的时间完成目录,之后又带回北京进行自费印刷。⑥[日]杉村勇造:《滿洲文化の追憶》,收入社团法人国际善邻协会编:《滿洲建國の夢と現實》,東京:编者印行,1975年,第289-290页;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歷史》,第184页。罗振玉的出版事业,更体现了内藤湖南的志趣。伪满政权建立后,罗氏即在内藤的启示之下,开始陆续拓印有关东北史之金石碑刻。1935年,黑田源次、竹岛卓一前往内蒙古林东调查辽代庆陵,⑦此次调查活动经纬,事后还写有报告书;见三宅俊成编《林东辽代遗迹踏查记》,满洲事情案内所,1944年。其中发现辽代诸帝后的国书汉文哀册,广受瞩目,于是伪满洲国官方决定移置奉天的“国立”博物馆保存。罗氏不仅拓印了此一契丹国书,更将箧中多年所藏诸拓毕备,命子罗福颐创编《满洲金石志》6卷。另外,还将非属于东北金石,如清代热河行宫所藏古彝器,还有邺下、洛中石刻之流入东北者,则统为《别录》2卷,先后成书。⑧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校定本》卷下,沈阳:辽宁出版社,2003年,总第116页。不仅于此,早在寓居京都期间,罗氏经内藤湖南介绍,结识小川简斋。小川本人富于收藏,以古本《华严经音义》出示,罗、内藤两人“皆以为惊人秘籍”,商榷有意影传艺林。小川虽慨然许诺,但以事故未果;嗣后小川、内藤均捐馆。直逮1940年前后,罗振玉始经由羽田亨转借,得以向小川家人借书影印。⑨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0集下,《贞松老人外集补遗》,《日本古写本华严音义跋》,总第910页。
知识的再生产甚至还包括设置博物馆机构与举办展览会。伪满中央博物馆最先构想源自对清代热河离宫、寺庙有关文物离散及荒废情形提出因应之道,嗣后再加上几位清朝遗老所收藏的旧籍文献以及外务省所添购的墓志铭文,存放地点初以汤玉麟公馆进行修筑,⑩对热河的建议为日本沟口祯次郎视察时提出;旧籍文献系指荣厚、宝熙整理的数万册书籍资料以及罗振玉整理的大库资料目录。另外,墓志铭为外务省的文化事业部以45,000元购入陶湘所藏六朝、唐代部分。俱见[日]冈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歷史》,第120页;“满洲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满洲国史·各论》,东京:满蒙同胞援护会,1971年,第1118页。1935年6月1日,该馆正式于奉天开馆;直到1939年1月1日,伪满新京的博物馆成立,为配合调整职务,改称为“国立中央博物馆新京本馆”,原奉天之馆改称为奉天分馆。博览会事业最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9月10至25日,由“日满文化协会”常务主事杉村勇造居中牵线,在东京上野的帝室博物馆举办“满洲国国宝展览会”,展示奉天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满文《大藏经》、缂丝刺绣、陶瓷等。该次博览会的目的乃为纪念伪满洲国政权建立10周年,表彰所谓的“文化合作”,连上海地区也有所报道。①《东京举行满皇宫展览会》,《申报》(上海)1943年5月13日,第2版。
简言之,透过“文化协会”建立一套“合作”机制,使得日满双方各具名义参与其中。对“满洲国”而言,一方面积极发展所谓“满洲特色”,另一方面则致力确立继承清朝的事实;至少站在经由获得清室的文物之际,强化自身的地位上。②论者分析“满洲国立博物馆”收藏品的内容,认为初期“日满文化协会”的考古工作与活动,大抵以呈显“清朝色”为主,1937年后则出现转向。见大出尚子《日本の旧殖民地における历史.考古学系博物馆の持つ政治性─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及び「满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馆を事例として─》,《东洋文化研究》第14号(2012年3月),第12页。至于日本方面,在符合国策的需要下,参与的日方学者陆续于返国后开设考古讲座,③[日]吉村日出東:《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講座の開設─國家政策と學問研究の視座から─》,《日本历史》第608号(1999年1月),第93-108页。并讲演各处搜罗的心得。④譬如1935年4月9日至30日,因应“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的机会,在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与“日满文化协会”共同催生下,举办“东方文化春季讲演”,先后由鸟居龙藏、常盘大定、关野贞、原田淑人、白鸟库吉、小柳司气太等,分4次进行,见《近頃の歷史學界(一)》,《历史学研究》第3卷第6号(1935年4月),第66页。对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之历史来说,日本的用意颇与“满洲国”有所不同,是处于解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建立“东亚史观”。譬如华北“沦陷区”的一份杂志在描述“满洲国国宝展览会”时,特别列举到当中最为珍贵古物系一辽代三彩砚台,并说“由里面残存之契丹之文字一点观之,实可供为东亚陶瓷器之历史研究资料”。⑤《文化纽丝·满洲古物将运日展览》,《国民杂志》第2卷第8期(1942年8月),第69页。
结 语
内藤湖南于1934年因胃癌去世,终年68岁。内藤去世后,日本、中国学界诸多名士皆深感惋惜。日本汉学界将其誉为“东洋史巨擘”,其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著”和“日本思想家”之列。中国学者罗振玉在其逝后也写下悼文,称其“为山方始,鸿图未申”⑥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0集下,《车尘稿》《祭内藤湖南博士文》,总第583页。,对其文化之事业未能全面展开而抱憾。王古鲁则形容内藤一生“遭遇最奇”,盖“以重视阶级制度的日本”,有不凡之际遇,确是难得。⑦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常熟:作者自刊,1936年,第177-178页。
诚然,内藤湖南因日俄战争胜利而得以发展对东北亚史地的研究,其学术发展与日本的外向扩张紧密相连。对于兼具记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内藤而言,其学术研究与政治环境的关联度可谓史上罕有,因而多数学者在研究内藤湖南时多以侵略和批判的视角斥责其侵略行径。比如,为达成目的,内藤处心积虑,调用了一切手段,如1912年,内藤在奉天为搜集“满洲”相关史料遭到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拒绝后再出一计,声称要为研究满族语言而拍摄史料,赵尔巽遂准之。内藤“此计获售后,在二十日左右最短期内,摄得《五体清文鉴》影片五千数百张;满文老档四千数百张,平均每天须摄五百余张”⑧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常熟:作者自刊,1936年,第178页。。显然,如果不以纯粹之目的论和侵略角度看内藤湖南对中国的研究,其对中国文献的搜集、整理、编撰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纯从学术层面上来看,内藤治史之勤,搜书之多,考察之广仍有后世学者可鉴可资之处。正如王古鲁所言,“其行为可议,其辛苦耐劳亦值得我人注意的”①王古鲁:《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常熟:作者自刊,1936年,第178页。。对此,也有学者谓:“十数年来,日本占领东北……注意这些残破的纸片,还价以搜集,分类整理、保管。这不但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全面化与深入化,同时也可以知道日本这个民族的确是可怕的”②安志敏:《日人在华之考古》事业,《益世报》(天津)1946年9月3日、9月17日,第3版。。
总而言之,内藤助推有关“满洲”的各种文献之出版乃至透过博物馆对其进行保存与展览,虽无不尽显其“殖民现代性”之倾向,但亦为后继的中日学者积累了大而全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文物资料,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研究与知识的再生产。
责任编辑:赵 欣
K107
A
2096-434X(2017)02-0074-12
林志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学术史;台湾:台北,11529。
①“满洲”一词,本为族名,作为区域名称因满族发祥地而得名,系指今辽、吉、黑三省全境,再加上内蒙古东四盟及河北部分地区。
—— 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品集》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