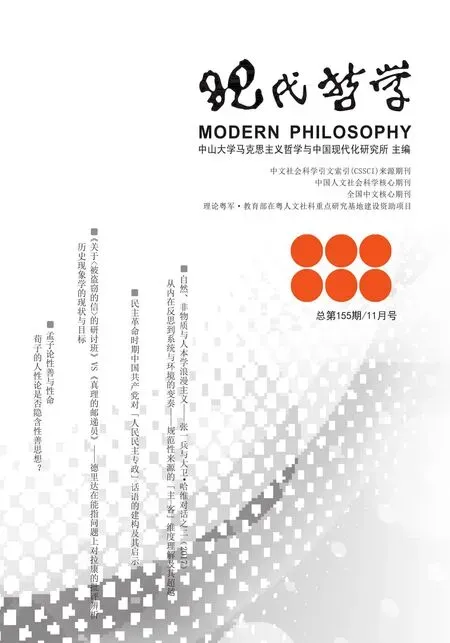《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VS《真理的邮递员》
——德里达在能指问题上对拉康的批评辨析
黄 作
《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VS《真理的邮递员》
——德里达在能指问题上对拉康的批评辨析
黄 作
拉康在《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中详细阐述了其独特的能指理论,德里达从原子论、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出发对之进行了猛烈批评。不过,从各自不同体系的书写理论即结构性书写(能指结构)与源初性书写(延异)出发却不难发现,正是不同的理论路径造就了各自在能指问题的不同姿态,同时也说明了德里达在此对拉康的批评更像是某种类似于“越界错误”的情况。
能指;结构;书写
一
在1955-1956年度的研讨班,拉康在1955年4月26日研讨会上就爱伦·坡《被盗窃的信》的短篇小说做报告*报告的原貌记录在1978年出版的这第2期研讨班《弗洛伊德理论之中和精神分析技术之中的自我》上面世。而早在1956年的5月和8月,拉康实际上重写了这一报告的内容,以《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为名首次发布在1957年第2期的《精神分析学》杂志的第15-44页中,又在前面的第1-14页加了个长长的《导言》。拉康1966年编辑《文集》时把这篇正文和《导言》都收录其中,不过他把正文放在最前面(第11-41页),之后是新加的“序列介绍”(第41-44页),再后是原来的《导言》(第44-60页),其中(第54-57页)插入了1966年新加的“各种括号的括号”(parenthèse des parenthèses)。,其独特读解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拉康把小说的故事场景总结为两个盗信场景,这两个场景具有相似的三元结构,第一个场景由国王(小说中的另一位高贵的人)、王后(小说中高贵的“她”)和部长D三者构成,而第二个场景由警察局长G、部长D和杜邦探长三者构成。国王和警察局长G处于第一种看(regard)的位置中,即他们“什么也看不到”;王后和第二个盗信场景中的部长D处于第二种看的位置中,即第二种看“看到第一种看什么也看不到且被诱骗着认为它所隐藏的东西是受到保护的”;第一个盗信场景中的部长D和杜邦探长处于第三种看的位置中,即“出自这两种看的第三种看,看到这两种看让需要加以隐藏的东西展露开来,以便它将要攫取这一东西”*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15.。拉康后来又称“什么也看不到”的国王和警察局长G处于“实在的情形”(situation réelle)中,他们“被看到却看不到什么”;王后和第二个盗信场景中的部长D处于“想象的情形”(situation imaginaire )中,他们认为人们不能看到他们,他们不知(méconnatre)“实在的情形”而且看不到“象征的情形”;第一个盗信场景中的部长D和杜邦探长处于“象征的情形”(situation symbolique),他们自身能够很好地去看,能够看到处于“实在的情形”中的主体“什么也看不到”,以及看到处于“想象的情形”中的主体自以为人们看不到他。*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p.30-31, p.31, p.16,p.29,p.29,p.29,pp.59-60.当然,主体所处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譬如第一个盗信场景中的部长D处于“象征的情形”中,但一旦“在此被看到者感到自己没有被看到”②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p.30-31, p.31, p.16,p.29,p.29,p.29,pp.59-60.,他就掉入“想象”的陷阱,于是在第二个盗信场景中处于自以为人们看不到他的“想象的情形”中,这是因为真正决定位置的不是主体或角色,而是在各种位置上进行流转的能指以及由能指所构成的象征结构。
其二,在拉康看来,整个故事的发展体现为信(lettre)的流转,当然这不是具体的信件的流转,而是作为“lettre”(字母)功能的“信”的流转,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能指的流转,“被盗窃的信就是纯粹的能指”③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p.30-31, p.31, p.16,p.29,p.29,p.29,pp.59-60.。为此,拉康批评波德莱尔通过把爱伦·坡这一短篇小说的原文题目“The purloined letter”不切当地译为“La lettre volée”而“背叛了”④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p.30-31, p.31, p.16,p.29,p.29,p.29,pp.59-60.原作者,因为原文题目中的英语动词“purloin”是一个罕见的词汇。根据牛津字典的说法,“purloin”是一个英语与法语混合而成的词汇,由英语前缀“pur-”与古法语的词汇(loing,loigner,longé)构成,意思应该与英语动词“prolong”(延迟)相当,由此“the purloined letter”用邮局词汇来说就是“la lettre en souffrance”(待领的信)的意思,而不是“la lettre volée”(被盗窃的信)的意思⑤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p.30-31, p.31, p.16,p.29,p.29,p.29,pp.59-60.。当然,拉康还是在行文中保留了波德莱尔法译文的这一标题即“La lettre volée”,并没有加以更改,也称自己的研讨班就是“关于‘La lettre volée’的研讨班”,本文由此也把“lettre volée”通译为《被盗窃的信》。正是从“purloined”一词应该得到的这一正确译法出发,拉康认为爱伦·坡小说中警察局长G所说的盗窃案件的“简单和古怪”其实就表现为“信的奇特性”,而后者就像“The purloined letter”(被延迟的信)这个题目所指出的那样,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题”,因为信能够经受一种“迂回”,那就是信“具有自身固有的一种路径”,在这一线路之中“信的能指影响显现出来”,其中能指“只能在这样一种置换(déplacement)之中维持,即,与我们的带状的各种发光广告牌或我们的像人类一样的思维机器的各种轮转的记忆的置换可比较的置换”⑥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p.30-31, p.31, p.16,p.29,p.29,p.29,pp.59-60.。拉康在研讨班之后加写的《导言》中解释了思维机器(machine-à-penser)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是由于缺乏人类意识的效能才拒绝用思维机器来形容我们赋予如此奇妙的各种语言行为的这种效能,而是仅仅因为,这种效能只会思考如下,即,如果就此并没有被能指的各种呼唤所折磨,人就不会具有其公共身份”⑦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p.30-31, p.31, p.16,p.29,p.29,p.29,pp.59-60.。从1978年出版的1955-1956年度的第2期研讨班内容中不难看到,这一时期的拉康热衷于把“象征界”解释为一架庞大自动装置机器,这是能指的大机器,机器的运作就是能指的流转,能指的流转服从机器的自动性原则*参见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四章第二节。。而关于能指流转的自动性问题,拉康把它与弗洛伊德后期在《超越快乐原则》一文中所提到的“强迫重复”(Wiederholungszwang )*“Wiederholungszwang”一词,英文一般译为“compulsion to repeat”或“repetition compulsion”,法文一般译为“compulsion de repetition”,而拉康主张译为“automatisme de repetition”,他认为自动性(automatisme)一词更能形象地说明强迫重复现象。(参见Lacan , Séminaire II , p. 79.)现象联系起来。在《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正文一开头,拉康就直言“自动重复扎根在我们称之为指称链的坚决要求或坚决主张(l’insistance)的那种东西之中”*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11, p.44, p.29.,而且在后加的《导言》一开头明确指出,这一研讨班内容是“我们整个这一校历年[1955-1956年度]致力于《超越快乐原则》一文所做的评论其中一个时刻”。
拉康在重写的文本中添加了大量的图式来说明能指在“象征界”大机器之中流转的自动性原理。同样,借着爱伦·坡这一短篇小说的奇妙结构,他进一步论证了处于“象征界”大机器之中流转着的能指的特性:1.能指优先于且决定所指,“能指相对于所指的优先权”,就如拉康在对列维-斯特劳斯1956年5月26日在法国哲学学会中所做的《关于神话与仪式之间的关系》报告的长长的介入评论中直言,这一观点是对列维-斯特劳斯在《马塞尔·莫斯著作导言》中“能指先于且决定所指”观点所欠的理论之债*Cf., J. Lacan, Intervention sur l’exposé de Claude Lévi-Strauss : “Sur les rapports entre la mythologie et le ritual” à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le 26 mai 1956; Paru dans 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1956, tome XLVIII, pages 113 à 119; C. Lévi-Strauss, “Introduction à l’oeuvre de Marcel Mauss”, dans M.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un document produit en version numérique par Jean-Marie Tremblay, dans le cadre de: “Les classiqu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une bibliothèque numérique fondée et dirigée par Jean-Marie Tremblay, en collaboration avec la Bibliothèque Paul-émile-Boulet de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Chicoutimi, p.28. 中译本参见[法]毛斯:《马塞尔·毛斯的著作导言》,《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导言》第15页。;他甚至幽默地说,之所以保留波德莱尔所译的标题,“更多地”正是因为考虑到“能指相对于所指的优先权”,而非“能指的约定特征”*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9, p.24, p.32, p.32,p.41, p.32.。2.能指就是象征系统中最小或最后的差别性元素,能指“只有以一种缺场的方式才由于其性质而成为象征符号”,是“具有独一无二性质的单元”③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9, p.24, p.32, p.32,p.41, p.32.,因此也是哲学史上所谓的最后的不可分者。当然,能指并不是任何原子主义意义上的“不可分者(atom)”,因为能指的“本性”恰恰以缺场的形式表现出来。拉康不仅用“en souffrance”(悬而未决的,待领的)来形容作为能指的信,而且信的“这一未使用”(non-usage)④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9, p.24, p.32, p.32,p.41, p.32.,或信的使用“只能是潜在的”而且“不立即消失”⑤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9, p.24, p.32, p.32,p.41, p.32.这一事实,反过来正好说明了作为能指的信的缺场性。3.拉康在《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正文最后声称“因此,‘被盗窃的信’、甚至‘待领的’信意味着,一封信总是到达目的地”⑥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9, p.24, p.32, p.32,p.41, p.32.,然而,既然信对拉康而言并不是指具体的信件,而是指纯粹的能指,那么这里的目的地也并非具体的目的地,而是代表一种能指的分配,“信只有通过纯粹能指的各种最终的分配才能作为权力手段而实存”⑦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9, p.24, p.32, p.32,p.41, p.32.。
可以说,多亏爱伦·坡这一短篇小说的奇妙结构以及其中的信的奇特性,拉康的能指理论在此找到了绝佳证据。正是由于这一解读对发展其能指理论的有利性,使得拉康把《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一文置于《文集》(1966)的首篇,不仅独立于录入《文集》的以前各篇文章的编年排列,而且享有特权地位来安排这些文章的序列。*1970年《文集》在瑟约出版社以口袋本的形式分两卷本再版,拉康写了个《介绍》,一开头就讲“多亏了某个人,这个东西(ceci)就是甚于一种语言符号(signe)的东西……”而能指恰恰就是比语言符号更为基本的东西,然后以几近一半的篇幅来谈论爱伦·坡这一《被盗窃的信》。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参见J. Lacan, Post-face à l’édition de poche des Écrits, Coll. Points Seuil 1970, pp.7-12, p.7.)
二
正是因为《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一文在拉康理论中的独特地位,它成了对手攻击拉康的集中点。聪明绝顶的德里达显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在1972年声称要向拉康宣战后,在3年后的1975年,兑现了在《多重立场:与让-路易·乌德宾、居伊·斯卡培塔的会谈》一文收入《多重立场》一书时所加的长注释中,要在3至4年对拉康的《文集》做出回应的承诺(他尤其感兴趣的是真理与言语问题以及《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Cf J. Lacan, Positions. Entretiens avec Henri Ronse, Julia Kristeva, Jean-Louis Houdebine, Guy Scarpetta,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pp.112-119 note 33.中译文参见德里达:《多重立场(与亨利·隆塞、朱莉·克里斯特娃、让-路易·乌德宾、居伊·斯卡培塔的会谈)》(以下简称《多重立场》),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07—112页注释34。,在《诗学篇》(Poétique)21期中,他发表《真理邮递员》(“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一文,以《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为靶子,试图全面、系统地清算拉康的“错误”理论。
我们根据德里达在文中对拉康的主要批评论述,逐一进行辨析。首先,德里达批评拉康的能指(字母)理论是一种原子论的理论,“这种原子论的能指拓扑学”*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Collection La Philosophie en effet, Paris: Flammarion, 1980, p.453.,认为这一原子论基于拉康在文中所谓的“能指的物质性”*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4.理论。德里达把这种物质性排除在经验的物质性之外,“不是可感性能指的经验的物质性”,同时把它限定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属于“某种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é)”,另一方面属于“某种场所或局部性(localité)”*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52.。
在能指问题上,拉康不仅用“matérialité”(物质性),而且用过“matériel”一词,譬如称能指为“听得见的物质性东西”(le matériel audible)*J. Lacan, Séminaire I , éditions du Seuil, 1975, p. 272.,能指就是“指称性的物质性东西”(matériel signifiant)*J. Lacan,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379, p.427, p.511 etc.等。这里所谓的物质性东西就是语言的物质性东西,就是说能指是语言的物质性东西,“能指之网就是语言的物质性东西(matériel du langage)的共时结构,就每一个元素在此所获得的确切使用就在于它与其它各元素有别而言”*Ibid., p.414. 拉康有时也称“matériel de la langue”(语言的物质性东西)。J. Lacan, Séminaire III, éditions du Seuil, 1981, p. 66.。能指作为这种物质性的东西,一方面是语言本身的支撑,所谓“听得见的物质性东西”,从“audible”(听得见的,可听见之物)一词来讲,属于哲学史传统的“可感之物(sensible)”的范围(德里达在此断言拉康的能指“不是可感性能指”,实际上并不确切),可感之物对应感觉,但有别于感觉本身。因此,拉康把能指这一“听得见的物质性东西”与“躯体性的和心理性的各种不同功能*Ibid., p.495.”区别开来,也正是在这一物质性东西的意义上,拉康的能指概念与索绪尔的听觉形象(能指)实质上也是不同的,因为听觉形象是“心理痕迹”是“表象”,是两面的“心理实体”其中一面,表现的无疑是心理功能,是“感觉的(sensorielle)”*F.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ublié par Charles Bally et Albert Sechehaye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Albert Riedlinger, é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e par Tullio de Mauro, postface de Loui-Jean Calvet, Payot, Paris, 1985, p.98.中译文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1页。而非“可感的(sensible)”。另一方面,这种物质性的东西是言语或具体话语的支撑,它是“具体话语从语言中借入的这一物质性支撑”*J. Lacan,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495.,因为“当主体说话时,他有全部语言的物质性东西供他使用,正是从此出发,具体话语得以形成”*J. Lacan, Séminaire III , p. 66.,换言之,如果得不到这种物质性的支撑,具体话语是无法形成的,由此可见能指这一物质性东西对具体话语或言语(对语言也是一样)的基本性。
当然,把能指视为“物质性的”并非拉康首创,而是索绪尔。索绪尔一边否认听觉形象是一种“物质性的声音”(son matériel)和“纯粹物理性的东西”(chose purement physique),一边却说“我们有时称听觉形象为‘物质性的’(matérielle)”,当然他紧接着解释道“这仅仅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而且是跟连结的另一术语即更为抽象的概念相对而言的”*F.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e par Tullio de Mauro, op.cit., p.98. 中译文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01页。。拉康在能指的物质性问题上一向备受争议,原因还在于如何理解物质性。尽管索绪尔的“听觉的(形象)”与拉康的“可听的(物质性东西)”可以视为相对应的两种不同东西,就如感觉与可感者,但在我们看来,索绪尔的上述说法恰恰是说明拉康的能指的物质性问题的钥匙;索绪尔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他是在“具体”(相对于抽象而言)这一意义上使用“matérielle”(物质性的)一词的,同样,拉康归根到底也是在“具体”这一意义上使用该词汇,他称能指是具体话语的物质性支撑,正好说明了物质性以具体性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德里达用“localité”(局部性)一词来说明能指的物质性的具体性一面无疑也是正确的。明白了这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索绪尔和拉康都没有称能指(听觉形象)为一种“物质”(matière),因为能指不是任何哲学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例如它不是物质的声音,也不是任何自然的或物理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能指的这一物质性不是传统感觉论意义上的经验的物质性,无疑也是正确的。
索绪尔把能指(听觉形象)归于感觉表象,从而否定了它是一种物质(如自然的声音),其观点清晰易懂。相比之下,拉康的观点就要复杂多了,他一方面否认能指是物质或自然性的东西(如声音),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能指表现为一种心理(或生理)功能。我们还需要从能指的结构性(或系统性)这一特征出发来理解。能指不仅是系统或结构中的元素,只作为系统或结构的元素而存在,而且还是系统或结构中最小或最后的差别性元素,是元素而非不可分的原子。能指既具有结构性又是系统的元素,恰好是说明能指并非原子的利器。德里达从拉康的能指的物质性出发来说明能指的不可分性的路径,实质上是借道于原子论来实现的,即从能指的物质性推导出能指的原子性,再从后者推导出其不可分性。这一推导无疑是错误的;德里达没能看到拉康有时也说“文字原子”(atome littéral),但他指的是“音位学元素”和“指称性单元”这些结构性元素*J. Lacan,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816, p.690, p.823,p.710.,而不是原子论意义上的原子;最主要的是,反复强调能指的奥古斯丁传统的拉康,不能不视结构性(或系统性)为能指的首要特征,而绝不会承认原子论意义上的能指。同理,所谓能指的不可分性也并非指“atome”(原子)的“a-tome”(不可分),在这一问题上,德里达同样误读了拉康。德里达在上述《真理邮递员》一文中引用拉康在《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中的表述,“然而如果我们强调的首先是能指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在很多方面是奇特的(singulière),其中第一方面就是并不支持划分(partition)”*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4. Et cf. 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52.,试图说明拉康正是从不可划分性来说明能指的物质性。但这里拉康所谓的“不支持划分”其实并不是“atome”(原子)意义上的“a-tome”(不可分)。拉康文本中紧接着说“你们把信变成一些小小碎片,信还是它所是的信,与格式塔理论(Gestaltheorie)用潜伏性的活力论来考虑其整体观念是完全不同意义的”*Ibid., p.452.,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不支持划分”不同于格式塔完形理论的整体观,不属于“想象界”范畴,不属于把整体分割直至不可分割的原子为止的传统的整体与部分理论。德里达引用包括前句话在内的大段的拉康引文时,中间故意省略紧接着的这句话,非得从“atome”(原子)意义上的“a-tome”(不可分)特性来解释拉康所谓的能指的物质性,动机非常可疑,同时其论证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
其次,德里达批评拉康的能指理论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上菲勒斯中心主义,称之为“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e)*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510.。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至于菲勒斯中心主义,可以说是德里达专门批判拉康理论(甚至扩展到弗洛伊德主义)的术语。从其理论构成上看,拉康是在谈到母婴关系时引入菲勒斯(phallus)概念的,后者作为第三者是构成母婴关系必不可少的一方,换言之,母婴关系不是一种单独的简单的二元想象关系,而是一开始就涉及一种想象三角形(le ternaire imaginaire),这是拉康理论的独特之处。他称想象三角形中的这一第三者为想象的菲勒斯(φ),后者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阴茎(penis),而是婴儿与母亲的欲望的共同对象,而且处于想象三角形的核心地位,“如果不把菲勒斯当作一种第三者的元素……那么,对象关系的概念不可能被理解,同样也无法被操作”*J. Lacan , Séminaire IV , éditions du Seuil, 1994 , p. 28.。当然,就欲望的真正对象是一种缺乏而言,菲勒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就是一种能指”⑥J. Lacan,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816, p.690, p.823,p.710.,它就成了“Ф(大写的phi),不可能拒绝的象征的菲勒斯,享乐的能指”⑦J. Lacan,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816, p.690, p.823,p.710.,这一能指“具有缺乏于存在的那种能指功能”⑧J. Lacan,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816, p.690, p.823,p.710.,它就是关于缺乏的能指*1997年,萨福安(Safouan)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开办的讲习班上清晰而又生动地用“a signifier of lack”(一种关于缺乏的能指)与“a signifier that is lacking”(一种缺乏的能指)区分了菲勒斯与对象小a,认为菲勒斯已是一种能指,欲望的能指,欲望作为一种缺乏有自己的能指菲勒斯,而对象小a则本身不是一种能指,或者说,它连一种能指都不是,关于这种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表示它。(Safouan, “Direction of the Cure, the End of Analysis and the Pas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oct. 1997, inedited.),由于“能指越不指向什么,它就越不可被摧毁”*J. Lacan , Séminaire III , 1981 , p. 210.,就越纯粹,菲勒斯(象征的菲勒斯Ф)可以说就是最纯粹的能指。这一特殊的能指也正好说明了能指的本性,“能指是具有独一无二性质的单元(unité),从其本性上说只是一种缺场(absence)的象征符号*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4.”。爱伦·坡上述小说中的“被盗窃的信”本身作为能指,“将在且不将在它所在、它会去的地方”*Ibid., p.24.,完全不服从传统逻辑规律,恰恰说明了它从其本性上说是在场与缺场的合一(présence/absence),因为其价值不在于它的存在(在场),而在于它与其它能指(元素或单元)的差异之中。*《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的英译文作者马勒曼(Jeffrey Mehlman)在此有个注释,把拉康此处的“将在且不将在”与索绪尔的“语言之中只有各种差异”以及“语言之中只有各种差异,无需各种肯定项(sans terms positifs)”的表述联系起来,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参见F.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réparée par Tullio de Mauro, op.cit., p.166. 中译文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167页;J. Lacan ,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 traduit en englais par Jeffrey Mehlman, Yale French Studies, Issue 48, French Freud: Structural Studies in Psychoanlysis, 1972, p.54, note 24.)
德里达无视拉康把能指视为一种缺场(或缺场与在场的合一)的事实,固执于他上述有关能指的物质性的观点,坚持把拉康的能指视为一种在场,试图通过一种文字游戏来根本地改变拉康所称的能指是关于缺乏或缺场的理论:爱伦·坡上述小说中的“被盗窃的信”本身作为能指,并不像一般的事物一样存在于某个地方,具有某个场所,相反,它并没有它自己的场所或地方,“我们对着信/严格地(à la lettre)只能说,这个东西并没有它的地方,这属于那种能够加以改变的东西,换言之,这属于象征秩序”。就像图书馆里一本书找不到了,它躲起来了,图书卡片显示的它不在它的地方,它很有可能就在旁边的柜子上,它“如此显见地显示着”,可它却是“隐藏着的”,这只有象征的东西(信作为能指)才能做到,相反,实在的东西总是有它自己的地方或场所,无论你怎么移动它,它总是要占据一个地方,它“总是且无论如何就在那里”,“它以紧贴着基底而获胜”*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5.。聪明的德里达绝对不会读不懂拉康这些文本的含义,但为了坚持他在拉康的能指问题上的错误己见(从原子论的不可分的能指原子说到能指的物质性、能指的固有场所,再到能指的在场性),不惜使用低级的文字游戏,即用“(le) manque a sa place”(缺乏有它的地方或位置)来取代拉康文本中的“manque à sa place”(没有它的地方或不在它的地方),试图强行给拉康的能指扣上在场的帽子,“在短语‘manque à sa place(没有它的地方或不在它的地方)’之中,引入一个书写的‘a’,换言之,没有重音的‘a’,或许足以改变一个字母,或许改变不如一个字母的东西,以便使之显现出,如果缺乏在能指的这一原子论的拓扑形态中有其位置(le manque a sa place),如果缺乏占据着一种外形都受到了限定的、被决定的场所,那么,秩序就将永远不会被打乱:信总是将重新找到其固有的场所,即一种被欺骗的缺乏(当然不是经验性的,而是超绝的,这更好且更确定)”*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53.。一方面,德里达认为拉康的能指“甚至总是语音的”*德里达经常引用的“音位学的且甚至总是语音的”(phonématique et même toujours phonétique)这句话严格说来并非拉康的原话,而他其中所说的“刚刚所引用”的句子在德里达上述文中前面一点地方已经出现过,即“像梦本身一样的一种书写,是能够用形象来表示的,它总是像语言一样是象征地分节的,就是说,它完全像这一语言一样是音位学的(phonématique),而且从它被读时起它实际上就是语音的(phonétique en fait, dès lors qu’elle se lit)”,两者并不一致。这一“刚刚所引用”的句子来自《文集》,与发表在1956年第4期《哲学研究》杂志上的原文也有出入。简单地说,拉康在1966年把该篇文章收入《文集》时用“而且从它被读时起它实际上就是语音的”这一表述取代了原先的表述即“而且它终究是语音的”,但这两种表述都不是德里达所说的“(音位学的且)甚至总是语音的”,都没有德里达所谓的“甚至总是语音的”的意思,可以说这是德里达的误读。,由此认定拉康的能指是语音中心主义的产物,从而必定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理路指导下,德里达坚持认为拉康在上述《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中所论及的作为缺乏的象征符号、作为能指(或字母)的信(lettre)具有在场性,“这一有声的‘字母/信(lettre)’因此同样会是不可分的,总是与它自身相同一,不管它的物体的各种分块会是什么”*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93.,与自身相同一,“在场于自身”*Ibid., p.493.。另一方面,德里达把拉康的菲勒斯理论作狭义的理解,尤其把它作性欲化理解。德里达这样说:“信有它固有的意义,一种固有的路径,一种固有的场所。哪些意义、路径和场所呢?在三角形之中,只有杜邦看起来知道这点……为杜邦所知的这一固有的场所,就像我们将看到以游移不定的方式占据其位置的精神分析师所知一样,就是阉割的场所:女人作为被阴茎之缺乏所揭开面纱的场所,作为菲勒斯的真理(vérité du phallus),换言之,作为阉割的真理。”*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67.他认为菲勒斯的真理就是阉割的真理,这就曲解了拉康的理论。拉康在名为《对象关系》的1956-1957年度的研讨班中曾经明确讲,对象之缺乏有三种基本表现形态:象征之债(阉割)、想象的损害(挫折)和实在之洞(剥夺),各自对应的对象分别为想象的对象、实在的对象和象征的对象。就阉割而言,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阉割并不是《曼努法典》中所列出的真实的阉割,“任何阉割,在一种神经症的影响之中所涉及的那些阉割,它们决不是一种真实的阉割。阉割只是就它在一种针对一种想象性对象的活动的形式之下、在主体之中起作用而言,才开始起作用”*Lacan, Séminaire IV, 1994, p.219.。根据拉康在表格上所列,阉割的对象是想象的对象即想象的菲勒斯,而不是真实的阴茎,阉割行为的行动者是实在的父亲,而阉割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象征行为。而就剥夺而言,虽然剥夺可以视为“阉割经验的如此可感的和可见的一种经验”,但拉康是“在实在中引入剥夺概念的”,“就是在实在之中引入象征的简单次序,以便覆盖实在以及挖掘实在”,所以剥夺的对象是一种象征对象,如象征的菲勒斯,剥夺“包含对象在实在之中的象征化”*Ibid., p.219.,剥夺行为的行动者是想象的父亲,剥夺本身表现为一种实在之洞。需要指出的是,说女人被剥夺了阴茎或女人没有阴茎时,并不意味着女人被剥夺了真实的阴茎,而是说这会造成一种实在之中的恐惧,“我们力求定义的阉割,以女人缺乏阴茎这一实在之中的恐惧为基础”*Ibid., p.219.,作为阉割经验其中一种的剥夺无疑也以这一恐惧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被剥夺了真实的阴茎或女人被阉割了真实的阴茎。坐拥精神分析师娇妻的德里达,并没有深入体会拉康的这些精神分析术语,听从习惯把拉康理论中作为根本维度的缺乏简单轻率地视为“阴茎之缺乏”,或者说把菲勒斯视为“阴茎之缺乏”,同时又不恰当地把菲勒斯、“阴茎之缺乏”与阉割等同起来,进而在把拉康的能指理论视为一种语音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把它视为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拉康在《文集》中曾经讲到过“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辩证法”(Écrits, p.554 et p.732),但不是生理意义上。,并且从生理的角度出发,错误地把后者等同于“雄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e)*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510.。
四
再者,德里达批评拉康的能指理论和真理理论都属于在场形而上学范围。德里达不仅用“不可分性”来说明拉康的能指的“物质性”,而且用“localité”(场所)来说明后者,当然,他紧接着指出,这一“场所本身并不是经验性的也不是实际的(nonréelle),因为它招致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在它所在的地方,‘没有它的地方’,并不位于它所位于的地方,或者还可以说(但这会是同一回事吗?)位于(setrouve)它不位于(nesetrouvepas)的地方”*Ibid., p.452.。就如前面指出的,这种东西就是拉康所说的“它将在且不将在它所在的地方”的那种东西,它代表着在场与缺场的合一。熟悉20世纪前期哲学的人都知道,拉康所谓的“在场与缺场的合一”理论正是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显/隐”理论的翻版,一向敏锐的德里达不可能看不到这点,而且正因为如此,德里达也把拉康的缺场——那种没有它的地方(manque à sa place)的缺乏(manquer)——理论归于一种根本上的在场理论,就像他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归于在场形而上学一样。他还进一步指出,拉康的这种以缺乏面目显示出来的能指场所的在场性,背后得到了一种更为根本的在场理论的支持,那就是作为能指源头的言语对于自身的在场性,“语声自行地引发这样一种解释:它具有自发性(spontanéité)的各种现象性特征,具有在场于自身的在场性(la présence à soi)的各种现象性特征,具有返回自身的循环性返回(retour circulaire à soi)的特征”*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93.。由此,德里达把能指的物质性和不可分性、能指场所的缺场性以及能指的言语性(语音性)与一种根本上的在场理论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指出在拉康的这一《关于〈被盗窃的信〉的研讨班》中,能指的这一在场性理论与真理理论(作为能指的信的真相)紧密联系在一起。德里达紧紧抓住拉康在上述研讨班中有关“信具有自身固有的一种路径”*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9.的表述,尤其是在研讨班正文的最后关于“因此,‘被盗窃的信’、甚至‘待领的’信意味着,一封信总是到达目的地”*Ibid., p.41.的表述,认为作为能指的信实际上处于返回自身的循环性返回之中,或者说,虽然信是流转的,但它的路径是固有的,从而最终还是要回到它固有的场所,这再次说明能指(信)的不可分性和不可摧毁性,“信将位于此,即,它通过固有的(propre)且确切地说是流转的(circulaire)路径的迂回总将是不可触及的和不可摧毁的,总将应该是不可触及的和不可摧毁的”*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53.。从信的“固有路径”和信“总是到达目的地”这两点出发,德里达概括了拉康上述研讨班中“被盗窃的信”的真相(真理),“我们已经看到,真理价值的两种意义在拉康研讨班上被呈现出来”,那就是:
1. 在循环的返回和固有的路径之中,从起源到终点,从能指的临时出发地到能指的再次连结的相符(Adéquation)。相符的这一循环保卫(garde)和注视(regarde)约定的循环,契约的循环和宣过了誓言的信任(foi jurée)的循环。相符的这一循环重新建立起后一种循环以反对威胁且把后一种循环重新建立为象征秩序。在菲勒斯的卫士(lagarde)被委托为缺乏的卫士(garde du manque)的那一瞬间中,相符的这一循环构成了。从国王到王后,由此出发,处于一种没完没了的交替游戏之中。2. 作为缺乏结构的带着面纱-揭开面纱(Voilement-dévoilement):阉割,能指的固有场所,它的信的起源和目的地,没有显示任何东西来揭开面纱。因此阉割以它的揭开面纱的方式(en son dévoilement)来带着面纱。但是真理的这一运作有其固有的场所:成为了缺乏于存在的那种缺乏的地方(étant-la place du manque à être)的各种外形。*Ibid., pp.491-492.
当然,就如德里达随后指出的那样,这两种真理价值无疑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从菲勒斯应该被保卫,应该重新回到它的出发点,应该不在路途中撒播那时起,它们就需要言语和字母/信(lettre)的语音化”*Ibid., p.492.。而要想能指(包括有关缺乏的能指即菲勒斯)在它的字母中得到保卫,要想能指这样返回,就需要能指在它的字母中不遭受被划分的命运,即能指必须是不可分的。为此,德里达还调侃起拉康,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不能说部分的信/字母(dire de la lettre),而只能说一封信/一个字母(un lettre),一些信/一些字母(des lettres),信/字母(la lettre)”*Ibid., p.492.。可见,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被盗窃的信的奇特性(singularité),正是能指(信、字母)的不可分的特殊性(singularité)。能指的这一特殊性,所谓能指的物质性,在德里达看来,“从人们并不能在任何地方发现的一种不可分性中演绎出来的这种‘物质性’,实际上对应于一种理想化(idéalisation)”。为了说明能指的这一理想化或理想性,德里达还引用了拉康的表述“你们把信变成一些小小碎片,信还是它所是的信”*J. Lacan, “Le séminaire sur ‘La letter volée’”, repris dans les Écrits, p.24.,不过这一次不再从原子论意义上的可分性出发来解读拉康的表述,相反却正确地指出“这一点不能用经验的物质性(la matérialité empirique)来说”*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92.,同时希望以此为范例,得出一种能指的理想性,“就如这一点不能用经验的物质性来说那样,一种理想性[无更改地进行置换着的对于自身的一种同一的不可触及性(intangibilité)]应该被包含其中”*J. Derrida, “Le facteur de la vérité”, repris dans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492.。这毋宁是说,能指的循环性的相符是一种理想性,而且能指的不可分的物质性也是一种理想性。
上文已指出,德里达从原子论意义上的不可分性出发来理解拉康的能指的物质性(实质上是系统论意义上的单元或元素的具体性)的做法并不确切,在此基础上得出拉康的能指的不可分的物质性是一种理想性,同样也是不确切的。德里达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试图为了自己的永远可分的、延异的、撒播的能指理论考虑而扫清一切障碍。同样,德里达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拉康的表述“你们把信变成一些小小碎片,信还是它所是的信”不能用经验的物质性来说明,但是他把这一表述作为证明能指在流转或循环中相符的理想性的范例的做法并没有说服力,因为拉康的这一表述蕴含着显而易见的索绪尔主义的意义,那就是信的价值在于它在系统中的差异性,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实在性或实体性。德里达没能明白这一意思,反而把它当作能指在流转或循环中相符的理想性的例证,这是不可取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在批评拉康的“信(能指)总是到达目的地”观点同时,提出自己的能指观即能指(信)是永远延异的、撒播的,“与拉康研讨班最后一句话所说的意思(‘被盗窃的信’、甚至‘待领的’信意味着,一封信总是到达目的地)相反,一封信能够总是不到达目的地”*Ibid., p.472.。事实上,无论德里达冠以拉康的能指的物质性以理想性,还是冠以拉康的能指的循环性的相符以理想性,其目的都是为了批判这一理想性背后的在场理论,而在能指领域中,语音(语声、言语)对于自身的在场在德里达看来无疑是最终的在场形式,上述第二种真理价值“带着面纱-揭开面纱”(隐/显)也必然隶属于这一最终的在场形式。然而,“能指甚至总是语音的”并非拉康的完整表述,而是可以视为德里达的一种改写。相反,虽然语言学中的能指在其产生上来说是一种听觉能指,但一旦能指产生(无意识是言语作用的产物),能指就成了系统的元素或单元,成了能指函数,不得不服从系统的法则,至此,这已是类似于音位学法则的法则,而非语音的法则或语音学的法则。与此同时,拉康凭借弗洛伊德在梦方面的伟大临床发现,看到了文字与书写的重要性,发现能指函数正是书写的表现形式,发现无意识结构中的能指服从的其实正是书写的法则,至此,能指彻底告别了语音或言语,脱离了德里达所谓的语音或言语对于自身的在场性,同时也摆脱了语音或言语或逻各斯的纠缠,从而也不可能滑向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五
拉康和德里达都受惠于弗洛伊德文本,前者受益于《释梦》尤其有关“梦是一种图形谜语(rébus)”的论断,后者则受益于《“神奇的便条簿”笔记》小文和《科学心理学纲要》“(手稿)”。他们把能指的根本问题最后推进到书写(écriture)层面来进行讨论,各自发展出两种著名的书写理论:结构性书写(能指结构)与源初性书写(延异)。正是不同的理论路径造就了各自在能指问题的不同姿态,同时也说明了德里达上述对拉康批评更像是某种类似于“越界错误”的情况。
B565.59
A
1000-7660(2017)06-0067-09
黄 作,浙江宁波人,(广州 510006)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拉康《〈父亲的姓名〉翻译和研究》(16BZX070)
(责任编辑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