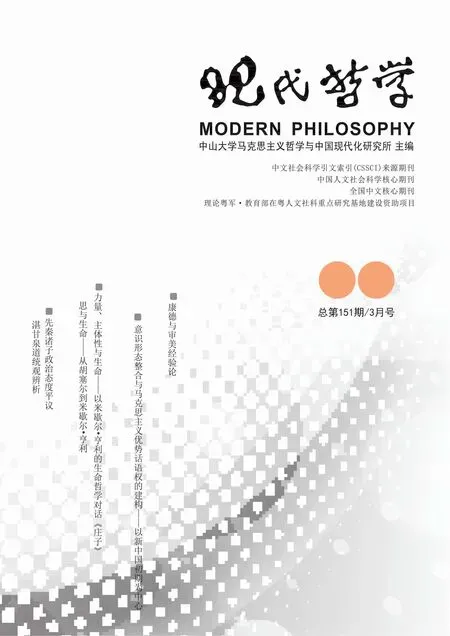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向世陵
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向世陵
宋儒倡导的道统,在元明时期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甘泉以“大道为公”批评宋元人的道统观,以此为自己的道统论说留下地盘。从默识之道到随处体认天理,心与事应然后天理现,这是甘泉道统论的理论真谛。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圣人之学是心学,天理则是千圣传心之要法。他敬象山却不愿接续象山的学脉,因为象山学“独立高处”“主内太过”,违背了程学内外体用合一的中道。他所认同的,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
道;道统;天理;心学
儒家的道统,自宋儒大肆倡导以来,在明代已成为学者们回避不了的问题,而不论其是否认同或进一步的选边站队。就后者来说,它是与不同学者各自的理论主旨和学术倾向密切相关的。
一
道统的内涵及其传承,可以《宋史·道学传》的元代官方论断为定准。其言曰:
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宋儒”的概念,在这里是以程朱为中心的濂、洛、关、闽,而朱子之“闽”学则是集其大成。所以,《道学传》在陈述朱学时,概括出了“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的为学“大抵”,将格致论与修身说作为了朱学亦即宋儒之学的中心。以此为据,宋儒跨越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上千年昏暗,终于接续起先秦孟子之学,儒家道统于是得以发扬光大。
元人信奉朱学,所以他们的“复天德王道之治”,本身就意味着对朱学道统的自觉承接。在此之后,所有有志于传承道统的学人,都必须要回答对宋儒道统的是否认同,并以此来彰明自身的学术谱系与正统地位。相形之下,不认同濂洛关闽而以为直承孟子的陆九渊之学,尽管可以关联“明善诚身为要”,并同样关注朱子阐释道统的人心道心问题,但由于非“以格物致知为先”,故被元人排斥在道统之外。
然而,由朱学造就的理学道统论,到明代中叶的湛甘泉这里却产生了质疑。在他与学生之间,就此专有一番讨论。学生问:
近科圣制策问,有道统之传尽归臣下之旨。然道统二字自宋儒始,前此未之闻也。夫道岂人所得私耶?宋儒乃有《道学传》,近又有《理学名臣录》,恶同喜异者乐有是名,遂互相标榜,而道统之名立。大道为公,似不如此。愚谓吾人道学之实不可亡,道统之名不可有也。何如?*[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1《问疑续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30页。
既然是科考的圣制策问,说明统治者对“道统之传”高度认同。但是,作为学生提问基点的“前此未闻”和“宋儒始发”,并不是新的问题,《道学传》自己就对此进行了说明,即道统本来就是先王“既没”和孔孟之后才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此之前的“大公”并不能否定在此之后的“得私”。不过,学生的后一问有些意义,即认为道统是“恶同喜异”而互相标榜的门户之见的产物。倘然若此,它就根本违背了“大道为公”的原则,所以是不妥当的。
事实上,《道学传》的逻辑是利用道学的价值来宣扬道统,道统是随着道学的创立才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挺立起来。但在学生这里,却要求将“道学”与“道统”进行区分,肯定求道之“学”有必要、传道之“统”不可有。
甘泉认可了学生之说,答之曰:“大道为公,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流行宇宙,何尝论统?只为立《道学传》后,遂有道统之说。其指斥至人者,则以此二字加之而摈弃之,而斯道亦未尝不流行于天地间也。”*[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1《问疑续录》,前揭书,第630页。
既然肯定了“大道为公”是一般的原则,并不以人或宋儒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所谓传道的专门之“统”就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由《道学传》带来的道统论说,却以自定的“道统”为依凭去指斥他人,将不属于其“统”的摈弃在外,就完全是门户之见。其实,道流行于天地之间,人人都可以体道修道,凭什么要为程朱的专门之统——“道统”所统呢?如果坚守这一逻辑,即求道之“学”并不受道统有无的影响,甘泉就不应该再谈论道统的传承,可在不少时候,他事实上又是认可和维护道统的传承的。只是他所言说的道统要推重白沙,并再上溯到程颢,以标示出甘泉自己有别于他人的道统旨趣。
二
自明初开始,朱学成为了统治思想,但心学亦逐渐孕育成势。按黄宗羲所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白沙学案上》,沈之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作为白沙的嫡传弟子,甘泉在明代追溯学术谱系,自然就把白沙放在了宋儒的继承者的地位上。甘泉在为庐陵黄氏宗族谱作序时,肯定其受同郡欧阳修的影响,但其成就又超越欧阳氏,因为他们能够“惓惓然思以大振白沙先生之学,追濂、洛、关、闽之轨,以入孔、孟、禹、汤、文、武、尧、舜之大道”*[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7《庐陵黄氏总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730页。。这里虽然是评价他人,但仍可看出甘泉自己的道统思想,即他是认可濂洛关闽的宋代理学正统的,而其师白沙则是最恰当地传承尧舜以至孔孟的“大道”之人。甘泉说:
先生之道即周程之道,周程之道即孟子之道,孟子之道即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即文、武、禹、汤之道,文、武、禹、汤之道即尧舜之道也。*[明]湛甘泉:《甘泉先生文集·内编》卷14《白沙书院记》,董平校点,《儒藏·精华编》第25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尧、舜、禹、汤、文、武直至孔孟之道,作为道统论的基石和发端,宋明诸儒都是予以认可和维护的,关键的分道是在宋以后。尽管濂洛关闽是官方认定的理学正统,甘泉对此也不回避,但他更多的时候是舍去了关、闽而只讲濂、洛,濂、洛往下,便直接跳到了白沙。而他本人则是白沙之学的继承者,故又说:
孟子之道在周、程,周、程没,默识之道在白沙,故语予:“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何患不到圣贤佳处。”阳明王公扣予曰:“天理何如?”应之曰:“天理何应?廓然大公。”阳明曰:“唯唯!”初无不同也,后门人互失其传。*[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8《默识堂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10—11页。
甘泉所谓默识之道,作为“孔门之本教”,体现的是道的真传。“默识”之所以必要,在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随处体认天理,则是对默识之道的进一步发扬。在甘泉这里,不论是称赞文王的“维天之命,於(wu)穆不已”还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以及到《中庸》称引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或者孟子要求的“勿忘勿助长”,都是默识之道的现身说法。孟子之后,直到周敦颐、程颢,此道才得以发掘和弘扬*[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8《默识堂记》,前揭书,第10页。。周、程之后,正是白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担当起了传承道统的重任。
可以说,在道统成为既定的情形下,学者要想成为圣贤,“默识”性与天道或随处体认天理就成为必须。阳明询问甘泉的“天理何如”,话语比较简便。从甘泉的回答来看,可能是问既然主张默识和随处体认,天理在其中是如何因应呢——或许它只是一种被体贴的外在对象?这多半与阳明批评甘泉之说是求理于外相关。甘泉以“天理何应?廓然大公”做答,意味天理流行,无处不在,日用间随处体认,就是我心与天理相互应和。他并以为阳明认同了自己所说,湛、王两家学问本来一致,其差别对立乃是后人的门户之见。
尽管如此,阳明对甘泉的质疑和批评并不能忽视。甘泉也需要做出辩解,他说:
或疑随处体认恐求之于外者,殊未见此意。盖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理矣。所云“看来宇宙内,无一事一物合是儒者少得底”,此言最当。更不若云“宇宙内无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犹见亲切。盖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宇宙内即与人不是二物,故少不得也。*[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答聂文蔚侍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573页。
天理本体的显现需要心之主体“默而识之”,此种主客或心物(事)相应的工夫,是甘泉工夫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故对阳明批评他的“随处体认”说走的仍是朱学格物穷理的路径即所谓“求外”,并不以为然。在甘泉,由于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前提,人与事物相互应和。心与事应,事来而心感。 心感应事本是体贴天理的工夫,但是,天理不是确定的物则或客观的本体,而是心在与事的相应中达到的中正不偏的心境和状态。从此去看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蕴含,即是人与任何来事的相互应和。因为所谓“宇宙内”,正是人心体贴的结果,不然无所谓内外。故宇宙与人,不得有任何一方有缺。
这就是说,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本相,就是心与事、理的相应。但这相应的发生,是主体自觉参与亦即体认天理的结果。这是甘泉所认为的由周、程经白沙再到他自己的道统传承的真实内涵。甘泉在向白沙请教的信函中说:
自初拜门下,亲领尊训,至言勿忘勿助之旨,而发之以无在无不在之要。归而求之,以是持循,久未有落着处。一旦忽然若有开悟,感程子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李延平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愚谓“天理”二字,千圣千贤大头脑处。尧舜以来至于孔孟,说中,说极,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该括在内。若能随处体认,真见得,则日用间参前倚衡,无非此体,在人涵养以有之于己耳云云。*[明]湛甘泉:《甘泉先生文集·内编》卷17《上白沙先生启略(拾遗)》,董平校点,《儒藏·精华编》第253册,第387页。
甘泉从白沙那里承接下来的“勿忘勿助之旨”,既是无时无处持续地做工夫,又是无忘无助长而循守中道的精神。但是,他接下来按此去实践,却始终未落到实处,没能有所得。直至他豁然开悟而体贴到天理。
“天理”二字,程颢说是自家体贴出来,它作为宋儒的理论结晶,实际上整合了尧舜周孔以来的儒家智慧。甘泉也因之将天理视作了道统传承的精神内核:“呜呼!天理二字,乃千圣传心之要法,修身格物之大端。周公发之于此,真圣学大头脑处也。”*[明]湛甘泉:《圣学格物通》卷27《进德业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76页。这个圣学的“大头脑”,已把仁义礼智、中、太极等概念集中进来。随处体认天理,也就意味着接续了这个道统谱系。当然,要“真见得”天理,不可能坐等其成,人需要提高自己的涵养境界,延平的“默坐澄心”也因之成为了体认天理的条件。甘泉此信,获得了白沙的高度认同,并最终使白沙将江门衣钵授予甘泉*参见陈白沙《江门钓濑与湛民泽收管(三首)》。《陈献章集》,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44页。。
“默坐澄心”能够“体认天理”,天理必然不离于心,“天理者,即吾心本体之自然者也”*[明]湛甘泉:《圣学格物通》卷27《进德业二》,第1075页。。以心体自然来描述的天理,在宋儒的范畴里属于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相对应,甘泉亦谓它“未发即性,已发即情,即道即事之得其中正者也”*[明]湛甘泉:《圣学格物通》卷27《进德业二》,第1075—1076页。。即道即事都是人之活动,天理便是心在此活动中得知的中正不偏之则。这虽是后天的行为,但所得者也关联着先天未发。联系到宋儒的未发已发之辨,延平追求未发境界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之功,与明道看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都属于体认未发的工夫。甘泉称:
明道看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延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象山在人情事变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为而发,合而观之,合一用功乃尽也。吾所谓体认者,非分未发已发,非分动静。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盖动静皆吾心之本体,体用一原故也。*[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答孟生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574页。
甘泉将明道、延平和象山放在一起讨论颇有些意味。从明道经延平到朱子,正是标准的宋儒道统。朱子便曾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南宋]李侗:《李延平文集》卷3《答问下》,《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页。一句“龟山门下相传指诀”,体现了程学一系体认先天未发的心法传承。但再加上象山,情况则产生了变化。象山所谓在人情事变上用工夫,显然进入了后天已发的范畴。不过,甘泉的目的可能正在于此,即要求合先天后天、未发已发为一。由此,他体认天理的“随处”,就既包括了物理性的时空过程,也指心灵的不同存在状态。天理既无处不在,未发已发,或动或静,自然都不会成为体贴的障碍。这可以说是从工夫论的角度维护了“体用一原”的原则。
三
象山是宋代心学的代表性人物。甘泉接续白沙,传承的同样是心学,但讲求和弘扬心学的甘泉,却并不愿意延续象山的学脉,实际上又影响到心学道统论的成立。当然,这不是说甘泉不尊敬象山,事实上,他与象山还有着颇深的渊源。他后来回顾青年时的情景说:
象山书,三十时常手抄本读之,见其一段,深得大意。近日学者虽多谈之,每每忽此。象山可信,决知其非禅者,此耳。答稿二通录奉,览之可知矣。然以比之明道内外体用一贯,参之孟子知性养性,考之孔、颜博文约礼,若合符节。乃所愿,则学明道也。近于《庸》、《学》二书愈见“易简”之学,并录一览。其来劄中间节目,难以尽答,敬疏于别纸,惟聪明裁之。*[明]湛甘泉:《甘泉先生文集·内编》卷16《答太常博士陈惟浚(六条)》,董平校点,《儒藏·精华编》第253册,第355页。
甘泉对象山学的尊崇,从其“三十时常手抄本读之”便可见,而且他自认为能“深得大意”。可在象山与明道之间,他承接的学脉是明道而非象山。这又是为何呢?除了“答稿二通”不详而无法评说外,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甘泉是能明白象山书的“大意”的,不同于那些被象山词句所吸引而不能明白其究竟者。正是凭借对象山学的了解,所以他坚信象山学绝非禅学。另一方面,象山与明道相比,则当学明道而非象山。明道学术的特点在内外体用一贯,而体用一贯正是甘泉判定道统承接的根本标准,这与孟子的既知性又养性、孔颜既博文又约礼是完全相合的。易简之学虽由象山倡导,却也需要从《中庸》《大学》的研读中得来,即它是通过读书而悟出的,所以又有别于象山“先立乎其大”和“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参见《语录上》《年谱》,[南宋]陆九渊:《陆九渊集》,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0、491页。的心学进路。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大量使用象山心学的类似语言,只是他也认为这一问题不是简单几句就能说明白的。
事实上,明道确是主张内外体用一贯的,如他言“须是合内外之道, 一天人, 齐上下, 下学而上达, 极高明而道中庸”*《河南程氏遗书》卷3,[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9页。便是如此。内外体用不能够分割开来,因为“道”本身就是一个统一整体:“盖上下、本末、内外, 都是一理也, 方是道。”*《河南程氏遗书》卷1,[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页。然而,道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概念,中国哲学家无论谁都不否认道处于最高的逻辑位阶,关键要看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体系中具体所指。这在甘泉哲学,主要有两方面的蕴涵:
其一,道从存在的状态看,指天理的浑沦一体。“天理,一而已矣。自其天理浑沦而言,谓之道。”*[明]湛甘泉:《圣学格物通》卷3《立志上》,第227—228页。从浑沦合一或整体的层面看,道就是天理。所以是浑沦为一,在于它将儒学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境界整合为一体。如称:“道也者,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非他,即吾心之中正而纯粹精焉者也。是故曰‘中’,曰‘极’,曰‘一贯’,曰‘仁’,曰‘仁义礼智’,曰‘孔颜乐处’,曰‘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皆天理也,尽之矣。”*[明]湛甘泉:《甘泉先生文集·内编》卷14《白沙书院记》,前揭书,第318页。道与天理同一,而天理不离吾心,儒学尽管内容宏大,资源丰富,但都可以概括到道或天理的范畴中来。换句话说,人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正是道之存在状态的现实发明。
其二,道从流通的作用看,意味着传道之统。但甘泉言道统的传承,是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的。学生曾听他教导说:“周公思兼三王,思道也。道也者,群圣同然之统也,求在我者也。禹之恶好,汤之执立,文之视望,武之不泄不忘,与周公之思兼,皆心学也。不合者,心未一也,思而得之,则其心一矣。”*[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3《雍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538页。甘泉所说,是对孟子当年追溯前代圣王事迹的概括*孟子语见《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圣王所做虽是事,但相应者却都在心,所以谓之“心学”。而“道”本指前圣后圣同然之统,只是这个“统”是需要我心去求的,在我有所得方能与圣王心合,故道一实质在心一。
甘泉以“心一”和“求在我者”接孟子,实际延续了象山的学脉,象山谓自己的学术乃“因读《孟子》而自得之”*[南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71页。,本身传承和弘扬的正是孟子学。而按朱子的归纳,象山的学术可以经由张九成上溯到二程大弟子谢良佐*参见《宋元学案》卷24《上蔡学案·附录》,第931页。。全祖望后来进一步明晰了此“心学”的道统:“程门自谢上蔡(良佐)以后,王信伯(蘋)、林竹轩(季仲)、张无垢(九成)至于林艾轩(光朝),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清]全祖望:《象山学案·案》,《宋元学案》卷58,第1884页。如果按照思想的发展而非严格意义的师承次第看,全氏的说法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甘泉既不愿意接续象山,象山往上的学脉对他便没有意义。
从当时的学界看,甘泉不认同由象山而下的心法传承,其实颇有些不合时宜。可以说,自元代朱陆和会到白沙倡言心学(暂不谈阳明),到甘泉讲学之时,象山之学已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他说:
仆昔年读书西樵山时,曾闻海内士夫群然崇尚象山。仆时以为观象山宇宙性分等语,皆灼见道体之言。以象山为禅,则吾不敢;以学象山而不至于禅,则吾亦不敢。盖象山之学虽非禅,而独立高处。夫道,中而已矣,高则其流之弊不得不至于禅,故一传而有慈湖,慈湖真禅者也,后人乃以为远过于象山。仆以为象山过高矣,慈湖又远过之,是何学也?伯夷、柳下惠皆称圣人,岂有隘与不恭者?但其稍有所偏,便不得不至于隘与不恭也。仆因言学者欲学象山,不若学明道,故于时有《遵道录》之编,乃中正不易之的也。若于象山,则敬之而不敢非之,亦不敢学之。*[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寄崔后渠司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581页。
按照甘泉的说法,他开初在西樵山建书院聚徒讲学时,“海内士夫多宗象山”,可见象山心学一脉在当时的影响。然而,甘泉追溯心学的源流,却不愿接续在象山的名下,原因不外是象山之学的禅学色彩,即甘泉所指称的其“独立高处”的流弊。所谓“独立高处”,甘泉也叫作“主内太过”,从而违背了程氏内外合一的中道*参见[明]湛甘泉:《甘泉先生文集·内编》卷17《寄陈惟浚》,董平校点,《儒藏·精华编》第253册,第374页。。此弊发展到慈湖,便由“假禅”变成了“真禅”。既如此,甘泉就不愿学宗象山,而是心仪明道传下的中正不易之学。
不过,从甘泉的具体论述来看,他称赞象山的“宇宙性分”等语是灼见道体之言,说明他仍是肯定象山心学的理论内核的。不论象山还是甘泉,他们事实上都坚守以心为本这一心学的共有立场。甘泉曾明确断言:“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如何谓心学?万事万物莫非心也。”*[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20《泗州两学讲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57页。甘泉在给其学友、阳明弟子方西樵的信中,正是将“性分”与“本心”界定为同一的概念。其曰:“愚意吾所举象山‘宇宙性分’之语,所谓性分者,即吾弟所举本心之说耳。得本心则自有以见此矣。本心,宇宙,恐未可二之也。”*[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答方西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565页。结合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等语来看,宇宙、性(己)分、本心正是相互发明,可以说典型地揭示了心本论的宇宙观和直抒胸臆的精神气象。其中的关键在自己能否有真实的体验,故而又有“先发明人之本心”之说*参见《陆九渊集》中《杂著·杂说》和《年谱》等的记载。见该书第273、491页。。这在甘泉,实际都是能“见得头脑”的见教,故又不乏维护象山之学的意味。
当然,象山学在甘泉因过高而有偏,可敬而不可学,所以要从道统传承的选项中排出。至于对慈湖的批评,甘泉显然要严于象山,但下手处也留有余地,即他虽以慈湖为“真禅”,却又未直接摈斥其为异端,而只是责其远过于中道。其实,甘泉以为象山灼见道体的宇宙性分以及诸如东西南北海同心同理等语,有可能正赖于慈湖在《象山先生行状》中的记载而得以传承*慈湖在《象山先生行状》中所言与《陆九渊集·杂说》的相关记载完全一致且有背景,或许《杂说》是取自《行状》亦未可知。参见《陆九渊集》,第388页。。
回到象山,由于诋象山学为禅学者首先是朱子,朱子学在当时又有官方的地位,甘泉不以象山学为禅学,对此就必须有所交待,所谓“抑亦以文公一时以为禅,后人因以为禅,遂以为禅乎”*[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寄崔后渠司成》,前揭书,第581页。。甘泉的交待或反驳,利用了象山学与朱学的交集,他实际是从朱学的角度去反证象山学不为禅学的。他认为象山所云“于人情物理上锻炼,又每教人学问思辨笃行求之”,正可以说是朱门之“规矩”*[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7《寄崔后渠司成》,前揭书,第581页。。象山是能见“大头脑”即前圣后圣相传的天理的,问题只在于其功夫未深而“客气时时发作”耳*[明]湛甘泉:《湛甘泉先生文集》卷10《问疑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626页。。“客气”本是朱学的概念,系指一时之意气,乃气血所使的产物,与变化气质是密切关联的。气质未变化,则客气未除,所以象山与朱子论辩多意气用事。正是因为如此,“遵道”就不应相随象山,而当直承于明道。就此而论,甘泉论道统不接象山,要害其实不在于象山自身,而在不能把象山置于明道之上。这或许也表明了对其时尊崇象山的学术风气的某种调和。
(责任编辑 杨海文)
B248.99
A
1000-7660(2017)02-0141-06
向世陵,四川仁寿人,哲学博士,(北京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