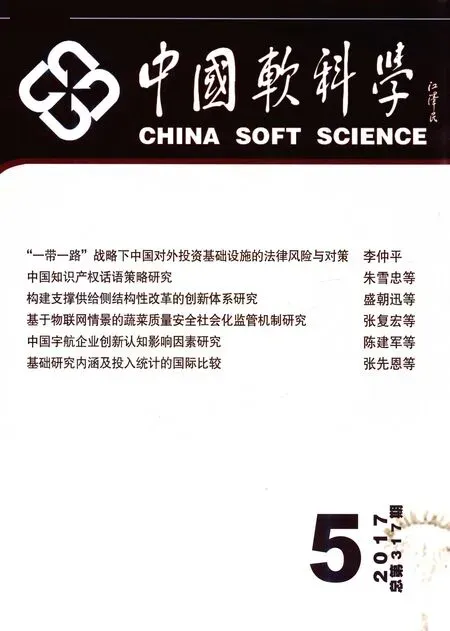“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投资基础设施的法律风险与对策
——基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视角
李仲平
(广东金融学院 法律系,广东 广州 510521)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投资基础设施的法律风险与对策
——基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视角
李仲平
(广东金融学院 法律系,广东 广州 51052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应注意将基础设施分为“一般基础设施”和“非一般基础设施”。其中,“一般基础设施”可以借助公共物品理论予以识别,努力使之不受反补贴措施的规制。“非一般基础设施”则可能遭受上游补贴调查的法律风险,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小心防范。一旦此类风险发生,中国应特别重视补贴“利益传递”的抗辩,明确要求调查机关“证明”而非“推定”利益传递。此外,中国政府还应侧重选择以对外援助的方式建设“非一般基础设施”,确保享有反补贴税法的豁免。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反补贴
一、引言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2015愿景与行动》”),将基础设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先发展领域。如何既能有效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亚欧经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又能成功规避可能的法律风险,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之一。基于中国与绝大多数沿线国家均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有关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下简称“《反补贴协议》”)的规制。为此,本文将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成员方的国内实践,探讨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法律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二、基础设施判断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实践
《反补贴协议》第1.1条(a)(1)(iii)明确规定,政府提供“一般基础设施”不构成财政资助,从而不受反补贴规则的约束[1]。将基础设施分为“一般基础设施”和“非一般基础设施”,《反补贴协议》试图指出政府可能将基础设施视为提供补贴的特定方式,但却并未就“一般基础设施”和“非一般基础设施”之间的区别做出任何说明,致使其成为“美国与欧盟互诉对方影响大型民用飞机措施案”(以下分别简称“欧盟空客案”和“美国波音案”)中的主要争端之一。
在“欧盟空客案”中,美国与欧盟分别就德国米尔博格湖改造、不莱梅机场跑道拓展和法国飞机场及机场进入道路是否构成“一般基础设施”产生争议*美国诉称,德国米尔博格湖改造、不莱梅机场跑道拓展和法国飞机场及机场进入道路,不构成“一般基础设施”,因为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均被限于空客公司使用。欧盟辩称,争议所涉基础设施虽然在事实上仅限于空客公司使用,却是欧盟为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履行的公共职能和有权选择的政策工具,因此构成“一般基础设施”。。该案专家组认为:“‘一般基础设施’指不是为了一个实体或有限一组实体的利益,而是对于所有或几乎所有实体,都可以使用的基础设施。”由此,基础设施的使用不存在准入限制,是“一般基础设施”的主要特征。尤其,此类准入限制既包括法律限制,也包括事实限制[2]。
基础设施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本质,决定了其通常无法由市场提供,因此世界各国都将其视为政府公共职责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排除某些政府将基础设施视为向特定接受者提供利益的手段,从而引起资源错配和贸易扭曲的不利后果。将“一般基础设施”解释为“不是向单个实体或有限一组实体提供的基础设施”,恰恰表明专家组的此类担忧及对违背公共利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所持的否定态度[3]。因此,《反补贴协议》在“基础设施”前面加上“一般”这一限定词表明,仅仅实际上具备公共利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才不受反补贴措施的规制。
值得关注的是,在澄清“一般基础设施”的特征后,该案专家组强调:“抽象地界定‘一般基础设施’,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非常困难。”考虑到即使经济学界也尚未就基础设施的概念达成共识,专家组的谨慎值得肯定。尤其,《反补贴协议》第1.1条(a)(1)(i)和(ii)都通过枚举示例的方式,阐明某一类型财政资助的概念。比如,《反补贴协议》第1.1条(a)(1)(i)通过提及“赠款、贷款和股本投资”及“贷款担保”,分别说明“资金直接转移”和“资金或债务潜在直接转移”的含义;《反补贴协议》第1.1条(a)(1)(ii)通过提及“税收抵免”,说明“政府放弃或未征收本应征收的税收”的含义;而《反补贴协议》第1.1条(a)(1)(iii)在规定“一般基础设施”时,却没有提及任何示例来澄清“一般基础设施”和“非一般基础设施”之间的区别。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似乎表明,《反补贴协议》的起草者也认为,“一般基础设施”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以至于无法举出具体的示例予以说明。在此情形下,“一般基础设施”的判断,不得不依据个案具体情况予以具体分析。“欧盟空客案”专家组的上述法律解释,得到“美国波音案”专家组的认同[4]。
本质上,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断“一般基础设施”的不确定,源于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此类模糊反映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原则上已就“一般基础设施”不可抵消达成共识,但究竟何谓“一般基础设施”,尚待进一步谈判的现时博弈结果。“一般基础设施”含义及其判断标准的这一建设性模糊,恰恰赋予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方通过国内规则或实践,解释或澄清此类模糊的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各成员方根据各自价值判断和理解所设定的行为模式或规则标准,不得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的基本原则和明文规定。
由此,在遵循《反补贴协议》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前提下,中国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创设明确的规则来确定合作的成本收益,借此降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的潜在法律风险。然而,囿于当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谈判陷入困境,中国澄清“一般基础设施”含义及判断标准的任何努力,均无法忽视美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可能施加的规则羁绊。在此情形下,中国不得不关注美国和欧盟判断“一般基础设施”的国内实践是否符合《反补贴协议》的相关规定。
三、基础设施违法性判断的美国实践
美国是世界上首个对政府提供基础设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并基于专向性概念能够揭示基础设施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本质,从而将其作为判断基础设施可否抵消的基本标准。
美国对基础设施进行抵消的最早实践,可追溯至1984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碳钢盘条反补贴案”。在该案中首次提出专向性标准后,美国商务部在1986年“沙特阿拉伯碳钢盘条反补贴案”中对其进行改进[5]。在同期“马来西亚纺织品和纺织厂产品反补贴案”、“波兰液压硅酸盐水泥和水泥熟料反补贴案”、“泰国大米反补贴案”和“加拿大大西洋底栖息鱼类反补贴案”中适用这一标准后[6],美国商务部于1989年修订《反补贴规则拟议条例》时,将这一行政实践上升为法律规则[7]。历经1993年“韩国钢铁反补贴案”的进一步完善[8],专向性标准作为判断基础设施可否抵消的基本方法得以正式确立[9]。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反补贴协议》吸纳美国的专向性标准,将其作为识别可抵消性补贴的构成要素之一。这意味着美国在判断基础设施能否抵消时,不得不另辟蹊径创设新的标准。在“欧盟空客案”中,美国根据专向性标准的反面——非歧视的可获得性,提出“普遍使用”是识别“一般基础设施”的唯一方法。本文将其称为“普遍使用检测法”。然而,仅仅依赖“普遍使用”,美国的新方法仍然无法与之前的专向性标准相区别,并在事实上将财政资助和专向性混为一谈。
《反补贴协议》明确规定,政府措施必须同时构成财政资助和专向性,才属于可被抵消的补贴。当且仅当其属于《反补贴协议》第1条范围内的财政资助时,才需要判断其是否构成第2条意义上的专向性。质言之,财政资助和专向性是两个彼此独立、但又前后相继的法律问题。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是否构成“一般基础设施”,属于财政资助层面的判断;此类基础设施的使用资格是否受到限制,则属于专向性层面的判断。仅仅着眼于基础设施是否被限于特定企业或产业使用,美国的“普遍使用检测法”实际上是用专向性标准判断财政资助存在与否,必将导致分析上的冗余与体系上的失衡,并不可避免地承继了专向性标准固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反补贴协议》并未就专向性判断给予任何说明或解释,致使其存在大量模糊之处。比如,第2.1条(a)规定,授予机关或其运作所根据的立法,是法律专向性的分析边界。但在授予机关或其运作所根据的立法,构成另外一项更为宽泛的、整体补贴计划一部分的情形下,法律专向性判断究竟以争议所涉措施为界,还是拓展至更为宽泛的整体补贴计划?此外,第2.1条(b)所涉事实专向性的判断,更是存在大量的不确定之处。比如,“某些企业主要使用补贴计划”,何谓“主要”?“有限数量的某些企业使用补贴计划”,如何界定“有限”?“给予某些企业不成比例的大量补贴”,如何量化“不成比例”?在专向性判断的规则和技术缺陷不得不借助调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予以克服的情形下,据此标准来识别“一般基础设施”无疑会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
尤其,美国的“普遍使用检测法”,与《反补贴协议》第2.2条的地理专向性相悖。地理专向性这一概念表明,授予机关向管辖范围内指定地理区域的企业或产业提供的补贴构成专向性。但是,基础设施具有固定的地域性。适用专向性标准来识别“一般基础设施”,意味着只要补贴提供经济体没有平等地发展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寸土地”,争议所涉措施都会被视为可抵消性补贴[10]。
最后,美国的方法可能导致裁决的随意与不公。比如,基础设施的第一个使用者是补贴利益的获得者,那第五个使用者呢?在其他使用者开始使用基础设施时,最初的补贴水平会下降吗?多少个企业或产业使用基础设施,可被视为“一般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为满足特定使用者需求而建的情形下,直到大量企业或产业开始使用该基础设施之前,是否构成“一般基础设施”[11]?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决定了某些类型的基础设施不可能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
意识到“普遍使用检测法”与《反补贴协议》中的专向性标准直接冲突,美国商务部在20世纪末对基础设施启动反补贴调查渐趋克制的同时,竭力通过扩大解释“货物”概念的方式,抵消给予基础设施的补贴[12]。与美国的自我克制相比,欧盟的相关实践却随着基础设施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不断扩展的势头。
四、基础设施违法性判断的欧盟实践
《欧共体条约》并未就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制定任何规则。实践中,欧盟委员会通常认为,政府以平等和非歧视条件向使用者提供的基础设施,不会授予其优势,从而构成“一般基础设施”[13]。由此,补贴是否向基础设施的使用者提供了其竞争者无法获得的优势,是欧盟识别“一般基础设施”的主要标准。本文将此方法称为“优势检测法”。
欧盟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基础设施”,仅限于对基础设施使用者层面的考察,强调基础设施在使用上的非歧视性[14]。比如,在“法国佛兰德港口案”及大量道路基础设施裁决中,欧盟委员会认定争议所涉港口和道路构成“一般基础设施”[15];而在“荷兰鹿特丹到德国鲁尔丙烯管道案”、“巴伐利亚州乙烯管道案”和“雅典国际机场航空燃料管道案”中,则否定争议所涉管道构成“一般基础设施”[16]。随着基础设施理论的发展和私人介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普及,欧盟委员会逐渐将优势的审查范围,扩展至基础设施的所有者/管理者及其股东层面,并分别创设了国家职责原则[17]、公开招投标原则[18]以及低利润原则来识别“一般基础设施”[19]。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欧盟官方和学界使用不同的单词(如,advantage、favoring或benefit)表示“优势”,但其含义与《反补贴协议》中的“利益”相同,均指企业收到了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原本不会获得的好处[20]。而且,欧盟委员会认定成员方政府授予“优势”的形式,如企业收入超过正常市场条件下的利润率[21]、免除股息[22]、税收[23]及销售或租赁货物、服务和财产的收入或租金[24],均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认定的利益授予方式相同。尤其,与《反补贴协议》第14条相同,欧盟委员会对优势是否存在的判断,也是以正常市场中的竞争条件作为比较基准。由此,不考虑成员方政府提供补贴的原因、目的或意图,仅仅探究补贴的效果,欧盟的“优势检测法”,本质上是《反补贴协议》中的利益标准。
但是,《反补贴协议》并不试图抵消所有授予利益的补贴。当且仅当此类补贴采取了第1条范围内的财政资助时,才受到反补贴措施的规制[25]。质言之,《反补贴协议》特别将补贴形式(财政资助)和补贴效果(利益)视为判断可抵消性补贴的不同要素,旨在确保并非所有授予利益的政府措施,都属于可被抵消的补贴的范围[26]。就此而言,“财政资助”和“利益”的相互独立,是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方之间利益博弈和立场妥协的结果。正是在此意义上,欧盟的“优势检测法”用补贴效果判断补贴形式,有破坏《反补贴协议》目的之虞。尤其,将补贴效果和补贴形式混为一谈,无视补贴在经济学和法学意义上的分野,欧盟的“优势检测法”,极易陷入矫枉过正的境地。
美国与欧盟关于“一般基础设施”判断标准的既有不足,恰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留下了余地。尤其,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斯里兰卡港口城项目、墨西哥高铁项目及中国—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等的搁置,再次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的核心,是通过澄清“一般基础设施”的含义及判断标准,制定“互利共赢”的合作和激励规则。
五、规避基础设施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的中国对策
《反补贴协议》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实践表明,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既可能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一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又可能作为补贴手段,引起资源错配和贸易扭曲的不利后果。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两面性,决定了中国应对基础设施进行二元划分,也即,事实上可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的基础设施,构成“一般基础设施”,通常不应受到反措施的规制;仅限于特定使用者使用的基础设施,构成“非一般基础设施”,有被采取反措施的可能。
(一)明确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对“一般基础设施”进行分类识别
基于“一般基础设施”是本质上具备公共利益属性的公共物品,中国可运用公共物品理论来识别基础设施的“一般性”。
公共物品指使用兼具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前者指某人对某物的使用,不会减少或阻止他人的使用;后者指某人不能因自己的使用,而排除他人的使用。同时具备这两种特点的物品,构成 “纯公共物品”。仅具备其中一个特点的物品,则构成“准公共物品”。其中,仅具有竞争性的物品构成“公共池塘资源物品”;仅具有排他性的物品构成“俱乐部物品”。
基础设施根据其在使用上是否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被相应地分为“纯公共基础设施”和“准公共基础设施”。“纯公共基础设施”通常由政府提供的固有性质,使其自动构成“一般基础设施”。“准公共基础设施”又可被细分为“俱乐部基础设施”和“公共池塘基础设施”。此类基础设施虽可由市场提供,但由于私人投资者无法收回全部成本,因而需要政府直接提供或委托私人提供。“准公共基础设施”的特殊性表明,其是否构成“一般基础设施”,需要谨慎判断。
根据《2015愿景与行动》,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主要以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为重点。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港口、管道等的建设,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的突破口;跨境输电、输气、输油通道及跨境光缆等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则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保证。无论交通基础设施还是能源基础设施,在使用上虽然不具有竞争性,但却具有不完全的非排他性,从而构成“俱乐部基础设施”。由于有限排他性是“俱乐部基础设施”的特性,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政府是否限制此类基础设施的使用资格,作为判断其是否构成“一般基础设施”的主要标准。
本质上,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均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因而政府不得不以特许经营的方式限制此类基础设施的使用范围。就此而言,政府赋予某些企业独占性的使用权利、某些企业是基础设施主要使用者的事实,或者某些企业以不成比例的方式使用基础设施,均不足以直接否定其不构成“一般基础设施”;而那些被临时限于某些企业使用的此类基础设施,如果在可预见的将来重新开放,仍然可能构成“一般基础设施”。
(二)明确上游补贴调查机关的利益传递证明责任
根据前述“欧盟空客案”和“美国波音案”,政府将基础设施作为补贴手段,向特定接受者提供利益,本质上构成上游补贴。由于《反补贴协议》并未规定投入产品接受的补贴必须是出口最终商品的制造国给予的,致使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有遭受上游补贴调查的法律风险。
试举一例予以说明。A国政府以提供无息贷款的方式资助B国建设一条高速铁路线,借此帮助B国运输制造汽车所需的零配件。B国的汽车产业因获得低成本的零配件,得以在C国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销售汽车。在C国汽车产业因此受到损害的情形下,按照现行《反补贴协议》的规定——受损害产业的产品必须与实际受补贴的进口产品是同类产品,C国既不能对A国也不能对B国采取反补贴措施[27]。
基于上述“通谋合作”行为通常发生在AB两国组建的各类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其他类似性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中,美国商务部在《1997年反补贴拟议条例》(以下简称“《拟议条例》”)中规定,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一个成员方补贴本国投入产品,目的是为了在另一个成员方生产最终商品,则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所有成员方可被视为一个单一成员方。通过这一规定,美国成功地防范了投入产品补贴国利用中间国规避最终商品进口国反补贴税法的行为,并得到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默认[28]。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组成自由贸易区建设基础设施的情形下,“非一般基础设施”有遭遇上游补贴调查的法律风险。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反补贴协议》关于可抵消性补贴的定义,只有给予投入产品的补贴向最终商品传递了利益,方可对最终商品征收反补贴税。这意味着,对上游补贴进行规制,必须判断并量化给予投入产品的补贴,是否向最终商品传递了利益。由于投入产品补贴和最终商品获益之间构成必要不充分关系,中国应明确要求补贴调查机关必须“证明”而不可“推定”利益传递。
鉴于利益是否以及如何传递具有高度的事实依附性,因此量化利益传递程度的“证明”方法,需要视个案具体情形而定。“美国波音案”的被诉方——美国曾主张,证明利益传递的唯一方法是实证分析,但却遭到该案专家组的否定。专家组明确表示,其并不试图限制可被成功用来证明利益传递的任何潜在方法,在合适情况下,该方法可能包括使用精确反映所涉市场情况的商业基准价格或理论模型。
考虑到“证明”利益传递需要搜集繁多的市场数据并进行复杂的数理推导,“美国波音案”专家组对“证明”利益传递方法所持的开放态度,无疑加大了上游补贴调查机关认定上游补贴的难度和成本。如果调查机关未能以肯定性证据完成利益传递的证明义务,中国可主张其调查行为违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6.3条、《反补贴协议》第10条脚注36、第19条和第32条的具体规定[29]。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要求调查机关承担利益传递的证明责任,是中国应对上游补贴调查的有效方法,但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可能是中国杜绝此类风险发生的重要举措之一[30]。
(三)加大“非一般基础设施”的援助性投资
中国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资金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政府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二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对外援助。与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采取市场运作,通过吸引社会、私人和国际资本,主要投资经济性基础设施不同,中国既有的对外援助资金通常以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低息贷款的方式,投向低利润或者无利可图的基础设施[31]。
基于中国投资目前在非洲、东南亚甚至拉美国家面临的困境,中国应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援助力度。由于此类援助通常旨在帮助受援国调节收入分配或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32],因此即使投资对象是“非一般基础设施”,也能获得国际社会最大限度的容忍。事实上,美国现行《拟议条例》,已经明确豁免国际贷款或开发机构提供的类似跨国补贴[33]。尤其,中国以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基础设施对外投资模式,本身就具有对外援助的性质,事实上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反而被某些经济体以“中国倾销过剩产能”为由,启动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因此,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范围、规模和额度,不仅与中国既有实践相符,而且得以最大限度避免贸易摩擦。
本质上,“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最终实现各国经济政策的有效协调。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基于现实主义利益诉求与传统地缘政治纷争,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贴上“新殖民主义”和“资源掠夺”等标签[34]。即使是印度这样的金砖国家成员,也不乏存在“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增强中国在印度洋的软实力,有助于中国解决“马六甲困境”及推进“珍珠链战略的言论”[35]。因此,强调中国以对外援助方式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非一般基础设施”的力度,有助于缓解此类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忧虑和担心。
六、结语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与相关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而基础设施投资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引擎。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法律风险,中国应通过创设具体的规则安排来确定参与各方的成本收益,藉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而澄清《反补贴协议》关于“一般基础设施”的界定和判断,中国需要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中国智慧”,积极倡议“二元划分”的“中国方案”,竭力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1]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机构专家组. 加拿大诉美国软木案[OL]. 世界贸易组织网, https://www. 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257_e. htm, 2015-09-10.
[2]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机构专家组. 美国诉欧盟及其成员方影响民用大型飞机措施案[OL]. 世界贸易组织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 dispu_e/ cases _e/ds316_e.htm, 2015-09-10.
[3]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机构专家组. 巴西诉加拿大影响民用支线飞机措施案[OL]. 世界贸易组织网, https://www.wto.org/ 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 _e/ ds 316_e.htm, 2015-09-10.
[4]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机构专家组. 欧盟诉美国影响民用大型飞机措施措施案[OL]. 世界贸易组织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 tratop_e/ dispu_e/ cases_e/ ds353_e.htm, 2015-09-10.
[5]美国商务部. 美国对特立尼达、多巴哥和沙特阿拉伯碳钢盘条反补贴案[OL]. 美国贸易执行网, http://enforcement.trade.gov/frn/index.html, 2015-01-10.
[6]美国商务部. 美国对马来西亚纺织品和纺织厂产品反补贴案、波兰液压硅酸盐水泥和水泥熟料反补贴案、泰国大米反补贴案及加拿大大西洋底栖息鱼类反补贴案[OL]. 美国贸易执行网, http://enforcement.trade.gov/frn/index.html, 2015-01-10.
[7]林惠玲. 美国反补贴法中的专向性标准及其适用问题[J].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0, (1): 47.
[8]美国商务部. 美国对韩国钢铁反补贴案[OL]. 美国贸易执行网, http:// enforcement.trade.gov/frn/index.html, 2015-01-10.
[9]美国商务部.反补贴税:最终规则[OL]. 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网, http://www. gpo.gov/fdsys/pkg/FR-1998-11-25/html/98-30565.htm, 2015-03-08.
[10]Lehmann, Christoph. Definition of Domestic Subsidy under United States Countervailing Duty Law [J].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87(1): 53-86.
[11]Ragosta, John A. Specificity of Subsidy Benefits i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untervailing Duty Determinations [J].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994(2): 671.
[12]美国商务部. 美国对泰国热轧碳钢盘条产品反补贴案[OL]. 美国贸易执行网, http://enforcement. trade.gov/ frn/ summary/thailand/01-24753-1.txt, 2015-01-10.
[13]Nicolaides Phedon, Kleis Maria. Where Is the Advantage [J]. European State Aid Law Quarterly, 2007(4): 617.
[14]Christian Koenig, Andreas Haratsch. The Logic of Infrastructure Funding under EC State Aid Control [J]. European State Aid Law Quarterly, 2004(3): 394.
[15]欧盟委员会. 法国佛兰德港口案、英国爱尔兰地区机场案和希腊高速公路案等[OL]. 欧盟委员网, http:// ec.europa.eu/ competition/elojade/ isef/index.cfm? Fuseaction=dsp_result, 2015-06-18.
[16]欧盟委员会. 荷兰鹿特丹到德国鲁尔丙烯管道案、巴伐利亚州乙烯管道案和雅典国际机场航空燃料管道案[OL]. 欧盟委员会网, http://ec. europa.eu/ 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 2015-06-18.
[17]欧盟委员会. 英国货运设施案[OL]. 欧盟委员会网, http:// ec.europa.eu/ competition/elojade/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 2015-06-18.
[18]欧盟委员会. 英国伦敦地铁案[OL]. 欧盟委员会网, http://ec.europa.eu/ competition/elojade/ isef/index.cfm?fuseaction=dsp_result, 2015-06-18.
[19]Christian Koenig, Kuhling Jurgen. EC Control of Aid Granted through State Resources[J]. European State Aid Law Quarterly, 2002(1): 11.
[20]欧盟法院. 法国国际快递工会及其他方(Syndicat français de l’Express international and others)诉邮局和其他方[OL]. 欧盟法院网, http: // curia. europa .eu/jcms/jcms/j_6/en/, 2015-12-20.
[21]欧盟法院. 奥德特公司(Odette Nicos Petrides Co. Inc.)诉欧盟委员会[OL]. 欧盟法院网, http://curia. europa.eu/ jcms/jcms/j_6/en/, 2015-12-20.
[22]欧盟法院. 西德意志州银行和北威州土地局(Westdeutsche Landesbank Girozentrale and Land Nordrhein-Westfalen)诉欧盟委员会[OL]. 欧盟法院网,http://curia. europa.eu/ jcms/jcms/j_6/en/, 2015-12-20.
[23]欧盟法院. 拉德布莱克赛车有限公司(Ladbroke Racing Ltd )诉欧盟委员会[OL]. 欧盟法院网, http: // curia. europa.eu/ jcms/jcms/j_6/en/, 2015-12-20.
[24]欧盟法院. 万德尔库伊(Van der Kooy)诉欧盟委员会[OL]. 欧盟法院网,http: // curia. europa.eu/ jcms/jcms/j_6/en/, 2015-12-20.
[25]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机构专家组. 加拿大诉美国出口限制措施案[OL]. 世界贸易组织网, https://www. wto.org/ english/ tratop_e/dispu_e/ cases_e/ ds194_e. htm, 2015-09-10.
[26]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机构上诉机构. 加拿大诉美国软木案[OL]. 世界贸易组织网, https://www. 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 / ab 257_e. htm, 2015-09-10.
[27]甘 瑛. 国际货物贸易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问题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28]李仲平. 美国上游补贴规则视域中的利益传递检测——在法律规范与自由裁量之间[J].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12(1): 113.
[29]李仲平. 模糊与澄清:上游补贴利益传递分析的法律依据探析[J]. 国际经贸探索, 2015, (1): 101-114.
[30]佚 名. “一带一路”不能忽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OL]. 参考消息网, http:// ihl.cankaoxiaoxi.com/ 2016/ 0202/ 1069132.shtml, 2016-01-02.
[31]白云真.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1): 61.
[32]托达罗·史密斯. 发展经济学[M]. 余向华, 陈雪娟,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33]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 联邦纪事汇编第35l部分[OL]. 中华税务网, http:// www. chinesetax. com. cn/guojimaoyi/ shimaobutie/meihzou/ 200508/255531. html, 2015-04-05.
[34]王明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J]. 东北亚论坛, 2015(6): 81.
[35]林民旺.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5): 47.
(本文责编:辛 城)
Legal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 under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Perspective of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greement
LI Zhong-ping
(DepartmentofLaw,GuangdongUniversityofFinance,Guangzhou510521,China)
China should divide infrastructure into “general infrastructure” and “non-general infrastructure” when invest in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of “One Belt One Road”. Among them, “general infrastructure” can be identified with the help of public goods theory and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 of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Non-general infrastructure” may cause the legal risks from upstream subsidies investigations, which China need to be carefully to guard against . Once such risks actually occur, China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lea of “benefit pass-through” and request investigators have to “prove” rather than “presume” the pass-through of benefit.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should also choose the form of foreign aid to invest “non-general infrastructure” and make sure it enjoy the exemption of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e belt one road”; infrastructure; anti-subsidies
2016-11-05
2017-05-09
李仲平(1976-),女,山西原平人,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DF96
A
1002-9753(2017)05-0001-08
- 中国软科学的其它文章
- 中国知识产权话语策略研究:基于话语与秩序相互建构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