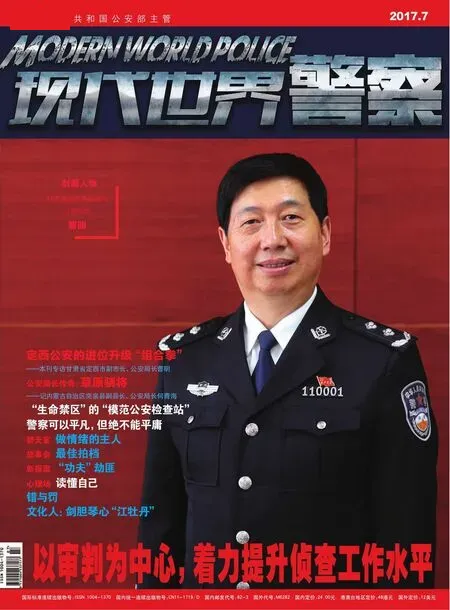郅都的遗毒
文/王志祯 高逸凡
郅都的遗毒
文/王志祯 高逸凡
在中国历史上,郅都的名气不算大,但争议却颇多。有人说他是一个忠臣,甚至把他与战国时期赵国的廉颇、赵奢等名将并列,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谷永说:“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幕。”陈寿的《三国志》说:“郅都守边,匈奴窜迹。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的“宋四大书”之一《册府元龟》说:“汉拜郅都,匈奴避境;赵命李牧,林胡远窜。”可见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太史公司马迁却说他“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把他归入酷吏行列,并排在历代酷吏之首。这是为什么呢?
就让我们从他的生平事迹说起吧。
郅都是西汉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汉文帝时做了郎官。郅都为人勇武有力,公正廉洁,从不看私人求情的信。送礼,他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他常说:“已经背离父母来当官,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决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汉景帝时,郅都当了中郎将。他敢于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很多时候能够当面使人折服。他曾经跟随景帝到上林苑,景帝的妃子贾姬去上厕所,一头野猪突然闯了进去。景帝用眼神示意郅都前去救护,郅都不为所动。景帝想亲自拿着武器冲进去救贾姬,郅都跪在景帝面前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其他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缺少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看轻自己,可是江山社稷和太后怎么办呢?”景帝回转身来,所幸野猪也离开了。窦太后听说了这件事,非常高兴,赏赐郅都黄金百斤,景帝从此也开始对郅都另眼看待。
西汉初年,朝廷倡导“无为而治”,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有的居然横行地方,蔑视官府,不守国法。济南郡的大姓宗族共有三百多家,强横奸滑。如瞷氏家族,仗着宗族户多人众,称霸地方,多次与官府作对。地方官循于常法,“莫能制”,济南太守也拿他们没办法,于是汉景帝委任郅都为济南郡太守。
郅都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手段,到任就痛下杀手,把瞷氏等几个大姓家族的首恶分子全家都杀了,其余的大姓坏人都吓得魂不附体,不敢再与官府对抗。过了一年多,济南郡被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郅都打击济南豪强,影响极大,周围十多个郡的郡守畏惧郅都就像畏惧上司一样。
公元前150年(前元七年),郅都晋升为中尉(武官职位),掌管京师的治安警卫,亲领北军。他执法公正,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看权臣脸色行事。丞相周亚夫官高傲慢,而郅都见到他也只是作揖,并不跪拜。
当时汉景帝一心要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实行“减轻徭役、降低赋税”的政策,因而人民安居乐业,极少有百姓触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郅都施行严酷的刑法,不畏避权贵和皇亲,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和皇族之人见到他,都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汉景帝庶长子刘荣,公元前153年(前元四年)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0年(前元七年),因为刘荣的母亲栗姬失宠,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之母王娡暗中唆使大臣向汉景帝请求立栗姬为皇后,汉景帝大怒,废刘荣为临江王。
公元前148年,刘荣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罪,汉景帝召刘荣觐见。
刘荣被召到中尉府受审,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郅都给他纸笔,要直接给汉景帝写信,表示谢罪,郅都却命令官吏不得给他纸笔。窦太后堂侄魏其侯窦婴派人暗中给刘荣送去纸笔。刘荣向景帝写信谢罪后,便在中尉府自杀身亡。
窦太后得知长孙死讯后大怒,深恨郅都执法严苛不肯宽容,准备用严厉的刑罚处置郅都。汉景帝不得已将郅都罢官还乡,随后却派使者持节任命郅都为雁门郡太守,不必到长安领旨,直接赴雁门上任,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处理政事。
汉景帝时期,匈奴铁骑连年南侵骚扰边境,边境数郡久不安宁。匈奴人一向敬畏郅都的节操威名,得知郅都就任雁门太守,惊恐万分。郅都刚抵达雁门郡,匈奴骑兵便全军后撤,远离雁门。
匈奴曾用木头刻成郅都的人形木偶,立为箭靶,令匈奴骑兵射箭击之,匈奴骑兵因畏惧郅都,竟无一人能够射中。直到郅都死去时,匈奴人还一直不敢靠近雁门。
窦太后得知汉景帝再次重用郅都,盛怒之下,立即下令逮捕郅都。汉景帝替郅都辩解,说“郅都是难得的忠臣”,准备释放郅都。窦太后忘不了孙儿刘荣之死,说:“临江王难道就不是忠臣吗?”在她的干涉下,郅都终于被杀。郅都死后不久,匈奴骑兵重新侵入雁门。
考察郅都的一生,除了严刑峻法似有滥杀无辜之嫌外,确乎是一个正直廉洁、忠勇无私的 “干才”“能吏”,甚至可称为一代名将。但太史公司马迁却坚持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酷吏,其功业皆是建立在酷吏的基础之上的,即使再大的功绩,也不能掩盖他作为酷吏的本质。这一方面因为司马迁本人就是当时严刑峻法的受害者,对酷吏一类角色深恶痛绝,另一方面,这也是与司马迁的治国理政理念分不开的。
他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的治政思想。孔子说:“用政治法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改正错误,走上正道。”老子说:“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表现在形式上的德,因此才有德;道德低下的人,虽然执守着形式上的德,却没有实际的德。”“法令越是严酷,盗贼反而越多。”太史公说:这些话是可信的呀!法令只是政治的工具,而不能从根本上抑浊扬清。从前天下的法网是很密的,但是奸邪诈伪的事情却产生出来,这情况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官吏和百姓竟然相互欺骗,致使国家衰败,一蹶不振。在这个时候,官吏管理政事就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只能适得其反、愈演愈烈,如果不用强有力的人和严酷的法令,怎么能胜任呢?如果让倡言道德的人来干这些事,一定会失职的。所以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一样;一定要有不同,那就是要让诉讼的事不再发生。”老子说:“愚蠢浅陋的人听到道德之言,就会大笑起来。”这些话并不是虚妄之言。汉朝建立后,破方就圆,对秦朝法律作了较大变动,如同砍掉外部的雕饰,露出质朴自然的本质一样,法律由繁苛而至宽简,就像可以漏掉吞舟之鱼的渔网。然而,官吏的治理政策宽松仁厚,不做奸邪之事,百姓也都平安无事。由此可见,国家政治的美好,在于君王的宽厚,而不在法律的严酷。
高后时代,酷吏只有侯封,苛刻欺压皇族,侵犯侮辱有功之臣。诸吕彻底失败后,朝廷就杀了侯封的全家。孝景帝时代,晁错用心苛刻严酷,多用法术来施展他的才能,因而吴、楚等七国叛乱,把愤怒发泄到晁错身上,晁错因此被杀。这以后就有了郅都和宁成之辈。
总的来说,司马迁是反对用严刑峻法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他崇尚一种君王宽厚、官吏清廉、百姓淳厚的政治氛围,类似于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但这只能停留在理想阶段,现实却远非如此。即便如此,他依然用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希望能借此扬此斥彼,警醒后人。郅都虽然忠君、清廉、功绩卓越,但他执法严酷,无所不用其极。先是不分青红皂白诛杀济南瞷氏等几个大姓家族的首恶分子全家,后又逼得废太子刘荣自杀,其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刑罚严酷却有目共睹,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匈奴人都闻风丧胆,可见其手段的极端与残忍。在司马迁看来,严刑峻法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效果,但长期来看,却贻害无穷。
果然,在郅都之后,有人似乎看到了做一个酷吏的好处,争相效仿,迎合统治者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奸吏,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陆续出现了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其中张汤尤为残忍酷烈,其恶名甚至超过郅都。
汉武帝重用酷吏,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使得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实际上多为官逼民反的起义者)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极其不利的。
而酷吏本人也因得罪众多、上下怨声载道,最终大多没有好下场。他们只是统治者手中的棋子而已,一旦无用,或者危及自身利益,马上就会被弃之如敝屣,甚至被推上断头台。这也算是酷吏们命中注定的悲剧人生吧。(高逸凡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汉景帝对梁国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