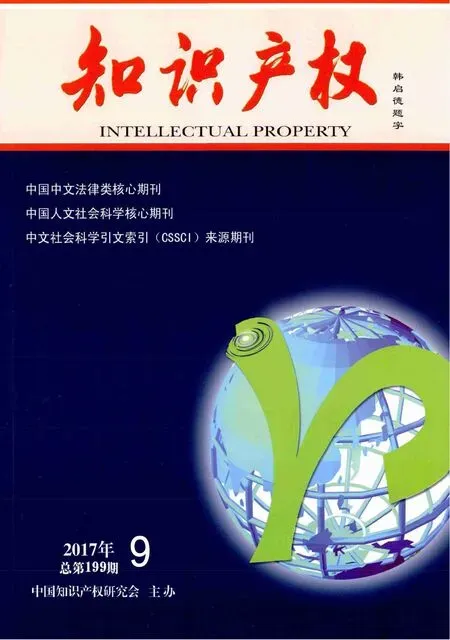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初探
刘 影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初探
刘 影
根据人工智能创作过程对人的依赖程度,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类型化为来自于人类的生成物(第一类生成物)和非来自于人类的生成物(第二类生成物)。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第一类生成物可以受到现行著作权法的保护,而第二类生成物不满足构成作品的要件。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应基于激励理论来考虑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但存在一些制度设计上的障碍。出于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考量,在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到一定阶段时,有必要打破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给予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上的保护。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生成物 知识产权 著作权法
一、问题的提出
图灵在1950年发表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首次从行为主义角度提出“机器能思考吗?”这一问题。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缩写为AI)概念在1956年美国的一次夏季会议(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经六十余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经历了从概念到不断发展的成长历程。伴随2006年深度学习概念的提出,人工智能成为未来技术发展的新趋势①阿尔法狗围棋(AlphaGo)是一款围棋人工智能程序,由谷歌(Google)旗下DeepMind公司的戴密斯•哈萨比斯、大卫•席尔瓦、黄士杰与他们的团队开发,其主要工作原理是深度学习。2016年3月,该程序与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选手李世石进行人机大战,以4:1总比分获胜,引发世人关注与热议。,甚至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②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将人工智能列为“互联网+”11项重点推进领域之一。。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人类有望通过人工智能从重复性脑力活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一旦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则存在发生自我进化的可能性。具言之,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对人和动物大脑进行仿生模拟,在大数据支持下,可以具有逻辑和思维,进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为此,有人(如霍金、比尔•盖茨等)担忧人工智能未来可能会脱离人类的控制范围而成为人类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③李桂花著:《科技的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只要科学技术发展坚持人的主体性,技术本身就只能作为客体而存在。因此,为保证人工智能技术在人类可控范围内发展,需要前瞻构建出一套从技术到产业、从社会到伦理、从政策到法律的监管规则。
知识产权制度对人类智力成果提供保护。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自然人创作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人工智能亦可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不同于传统计算机的创作过程,人工智能是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学习训练,未来可能不再依赖于硬件和事先定义的规则。换言之,未来的人工智能创作不是开发者告诉程序如何创作,而是算法本身通过数据训练,自己学会如何创作。日本公立函馆未来大学松原仁教授组建的人工智能团队通过人工智能创作出小说《电脑写小说的一天》,并入围“星新一奖”比赛初审。这部小说的创作,人的贡献度为80%,人工智能的贡献度为20%④《人口知能は小説を書けるのか~人とAIによる共同創作の現在と展望》:参见http://pc.watch.impress.co.jp/docs/news/769364.html.。可以看出,目前人工智能创作还依赖于人类,扮演人类创作道具的角色。而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技术兴起之后,各国即已对机器创作作品的法律属性进行过讨论,并在计算机仅作为协助创作的工具而存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⑤美国有关讨论See Register of Copyrights,6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1966),p.4.转自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3页注释⑫。日本有关讨论参见平成5年11月文化厅发布的《著作権審議会第9小委員会(コンピュータ創作物関係)報告書》:参见http://www.cric.or.jp/db/report/h5_11_2/h5_11_2_main.html#1_1.。因此,对于依然不能脱离人类控制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可依照计算机衍生作品的逻辑。但是,人工智能创作对人的依赖程度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不排除在不久之未来人工智能可独立进行创作的可能性。因此,在讨论人工智能创作生成的作品(以下简称人工智能生成物)时,有必要根据人工智能创作过程对人的依赖程度对其类型化,由此就会产生如下问题: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如何评价类型化后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从立法论的角度来看,是否有必要对类型化后的人工智能生成物(非直接来自于人的创作)进行保护,如有必要,应如何保护。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而展开,并在文末给出本人就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这一问题进行论证后得出的初步结论。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类型与特征
智能是人类所特有的区别于一般生物的主要特征,通常被解释为人类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⑥张仰森著:《人工智能原理与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的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⑦同注释⑥,第4页。。深度学习是一种需要大型神经网络的深层次结构,是对人和动物大脑进行仿生模拟的过程,通过特定算法并以大数据作为模型不断训练,进而发现规律并形成经验⑧孙志军、薛磊、许阳明、王正:《深度学习研究综述》,载《计算机应用研究》2012年第8期。。制约人工智能发展的限制条件有神经网络、大数据和算法⑨同注释⑧。。神经网络在深度学习过程中充当模拟人类大脑的角色。目前大型神经网络的技术发展已经可以为深度学习提供支撑,一旦数据和算法这两个制约条件也被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很快会发生自我进化。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创作通过不断从案例和数据中训练学习的算法,无需再像传统计算机一样依赖于硬件和事先定义的规则,进而实现独立创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发生自我进化前,人工智能创作依然依赖于人类,也即人工智能仍是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创作物可视为传统的计算机衍生作品。而人工智能一旦发生自我进化,将不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进行创作,这时就出现了如何看待人类主体和智能机器主体之间关系的难题。本文以人工智能创作是否发生进化为界限,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类型化为:1.来自于人类的生成物(以下简称第一类生成物),可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计算机衍生作品,人工智能仍作为人类创作的辅助工具;2.非来自于人类的创作物(以下简称第二类生成物),人工智能创作无需人类事先定义规则,作为独立的创作主体。
如果从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来看,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是经数据解析后再根据算法而创作出例如音乐、绘画、小说等作品的,无论是人工智能生成物抑或人类创作的作品,在本质上都属于信息的范畴,其外部表现与人类创作物并无明显区别。其次,得益于摩尔定律的发展,计算机硬件计算能力大幅提升,例如,2016年单张英伟达游戏显卡就有了2002年之前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拥有的能力,特别是通过云服务和神经网络,极大地提升了神经网络生成结果的速度和准确率,进而确保人工智能可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习后作出更具效率的判断,有此作为保障,人类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创作完成的作品,人工智能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批量完成。可以看出,相较于人类创作物,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主要特征为,在外部表现上与人类创作物难以区分,而在产量上又远高于人类。
三、现行著作权法下的解释论
前面已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类型化为第一类生成物和第二类生成物。事实上,第一类生成物与计算机衍生作品类似,由人类事先定义规则,计算机作为提高人类创作效率的工具存在,关于计算机衍生作品的可版权性等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并已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⑩例如,计算机软件的可版权性问题,具体参照崔国斌著:《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214页。。因此,在对第一类生成物进行讨论时,本文仅就一些传统计算机衍生作品的既有结论作一简要梳理,除此以外,不予过多探讨。对于第二类生成物,从技术发展来看,人工智能目前还未达到完全脱离人类控制独立进行创作的阶段,但是从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前瞻考虑第二类生成物的可版权性等著作权法问题,这也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
(一)第一类生成物
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作品,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指人的思想或感情的独创性表达。在这一点上,计算机衍生作品曾经备受争议,所幸各国讨论的结果已就该问题达成一致。如美国“新技术时代作品使用方式考察委员会”于1978年发布最终调研报告,认为计算机程序仅作为被动性协助创作的工具存在,未直接参与创作行为⑪同注释⑤,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5页。。又如日本文化厅1993年发布的“著作权审议会第9小委员会(计算机创作物关联)报告书”中,认为计算机系统作为人创造性表达的“道具”而被使用⑫同注释⑤,《著作権審議会第9小委員会(コンピュータ創作物関係)報告書》,第9页。。计算机衍生作品最终被认定为来源于人的创作而非计算机,进而认定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可版权性。这一结论可以适用于本文类型化后的第一类生成物,也即未发生自我进化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仍属于直接来自于人类的创作物,属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范围。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发布的报告书中亦提到,目前人工智能和各领域自动化不能完全代替人类的创作行为,通常只是将计算机作为道具而使用,但对技术的把握仍在进行中,随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角色从辅助工具转换为创作主体,则有必要重新审视计算机衍生作品的可版权性问题。如果第一类生成物属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范围,那么在作者的认定上,仍可遵循计算机衍生作品的一般逻辑。综言之,从解释论的角度看,第一类生成物具有可版权性,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权利主体的认定与计算机衍生作品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受到现行著作权法的保护。
(二)第二类生成物
人工智能依赖于神经网络,神经网络通过多层感知器实现点与点的连接,多层感知器可分为三层:输入层(input layer)、隐藏层(hidden layer)以及输出层(output layer)。输入层接收输入模式,输出层包含一个分类列表或输入模式可以映射的输出信号,隐藏层提取输入数据中的显著特征,具有有关输出的预测能力⑬[加]西蒙汉金著:《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申富饶、徐烨、郑俊、晁静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根据神经网络的工作机理,可将人工智能创作理解为数据收集、提取特征量进行加工、输出的过程。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构成著作权法语境下的作品需要具备如下要件:1.思想或情感的表达;2.具有独创性的表达;3.属于文学、艺术或者科学领域的作品。前面已提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特点之一在于外部表现上与人类创作物难以区分,鉴于这一特点,第二类生成物和第一类生成物与人类创作物一样,均属于表达,因此不属于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范围。人工智能生成物所属领域问题,第二类生成物并未超出文学、艺术或者科学领域,因此第二类生成物也未违反要件3。在解释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时,最具争议的问题要集中在要件1和2,也即第二类生成物是否属于思想或情感的范围,以及是否具有独创性。
关于要件2,独创性要求作品是独立完成且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但独立创作不应是作品是否应该受到保护的理由,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才是,独立创作是权利归属或侵权认定的判断要素⑭乔丽春:《“独立创作”作为“独创性”内涵的证伪》,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7期,第35-38页。。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只是一种质的要求,并没有准确的定量或定性标准。一般来说,偏向人格权说的学者强调作品应该通过可感知的形式体现个性。但是,作为功能性作品的计算机程序、数据库等作品,未必包含作者个性,由于职务需要而完成的作品中也很难说是反映了著作权人的个性。在著作权人是法人的情况下,强调法人个性这种观念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对此,日本学者中山信弘从确保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对独创性要件的意义进行了重新解构⑮[日]中山信弘著译:《软件的法律保护》,郭建新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二类生成物在外部表现上与人类创作物并无太大区别,又鉴于著作权法对创作物独创性只要求最低标准,如果从确保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考虑第二类生成物的著作权法保护,不能绝对排除其属于作品范围的可能性。事实上,对于机器是否具有创作天赋这一问题,有著作认为,计算机富有创造力,却缺乏人类拥有的现实世界的经验,因此它们的思维具有不连贯性⑯[美]雷·库兹韦尔著:《机器之心》,胡晓姣、张温卓玛、吴纯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05页。。一系列旨在测试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系统和人类智商之间的胜负关系的试验表明,人工智能的智力目前已经达到4岁儿童的水平⑰http://tech.163.com/api/15/1010/09/B5IBVLOE00094P0U.html.。在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下,4岁儿童的作品并未被排除在保护范围外。换言之,作品创作主体思维的缜密性或连贯性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作品不受保护的结论。
关于要件1,思想或情感的表达这一要件的判断往往会变成对思想和表达进行二分的过程,其主要目的在于排除对于思想或情感这类抽象的思维方式的保护,而只保护人类演绎、联想后形成自己观点、立场后的表达。对于第二类生成物,其主要基于大数据分析、内容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等技术实现,基本创作流程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自动创作等环节。从第二类生成物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计算机可以完成逻辑性较强的工作,因为逻辑建立在清楚而简单的规则之上,但是思想或情感却很难用机械的方式解释,因此对于第二类生成物来说,很难想象其可以像人类一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事实上,如何让一台机器人拥有一颗人类一样的心灵,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们最为艰难的课题。即使第二类生成物可以脱离人类独立进行创作,但在文义解释上,也很难认定其是思想或情感的表达。
综上所述,第二类生成物在解释论上很难构成现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也不存在作者认定的问题。但是,第二类生成物的产生是技术进步带给人类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不久之未来,第二类生成物可能会存在于甚至是大量存在于人类社会,起到繁荣人类文明的作用。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保护创作者的权利、促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来实现促进文化创新的目的,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论的角度来审视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能性。
四、人工智能生成物立法论上的探讨
(一)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知识产权正当性依据主要分为自然权论和激励理论两种观点。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自然权论中贯穿一个最朴素的逻辑,因为有劳动,所以要保护。暂且不论洛克的自然权论所受到的诟病,其至少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信念:每个人的劳动成果都应该得到尊重。另一方面,激励理论内在逻辑是,如果过度宽容免费使用,对于模仿者太过有利,从而可能导致意欲对创作活动进行投资的先行者的数量减少。为防止这种问题发生,应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禁止免费使用⑱[美]Robert P.Merges et al,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2-24(4th ed.,2006).。将两种主要理论进行比较可知,洛克的自然权说针对已经发生的劳动成果而言,也即知识由智力创作者生产,如不尊重作为知识产权源泉的智力创作者,则知识之源可能面临枯竭的危险。但从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目标来看,相较于自然权论,面向未来的激励理论更为符合社会整体价值。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这一点来看,激励理论作为说明知识产权正当化的根据更具说服力。这是因为,如果对搭便车行为不加以制止,则不能确保投资者的投资回收机会,会导致致力于知识创造的人的创作意愿减弱,公众会因为知识总量的萎缩而蒙受不利。
从立法论的角度来考虑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时,基于自然权论进行解释存在一定难度。这是因为,洛克的自然权论是以人生而为人的自然权为出发点,而现阶段人工智能显然还不具有可与自然人等同的人权,因此很难将自然权论作为赋予第二类生成物一定期限著作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当然,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类人模仿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性”,是否应赋予人工智能以“人权”,这样的讨论已出现⑲[美]库兹韦尔著:《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田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但是,即使存在赋予人工智能人权的可能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将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人类创作物等同视之,但也只能将自然权论作为解释第二类生成物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消极理由,而非积极理由⑳日本学者田村善之认为,人们创造了某种物这一命题,通过以实现效率为目标的知识产权,成为使制约他人自由获得正当化的消极根据。。那么,基于激励理论来解释是否妥当呢?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未来所能带来的利益不可估量,但其产业化过程又需要耗费相当大的投资。因此,从确保相关人员获得投资回报机会的角度来看,应该肯定给予第二类生成物制度上保护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如果不给予第二类生成物制度上的保护,可能会导致僭称内容问题㉑[日]福井健策:《人工智能和著作权2.0——机器人创作的扩大如何改变著作权制度》,载《コピライト》2015年第652期,第16-17页。。具言之,人工智能生成物外部表现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难以区分,这一特点容易诱使一些人对第二类生成物主张权利的投机行为。僭称内容问题更容易存在于对于一些有价值的第二类生成物的二次利用上。例如,人工智能独自创作的小说,其作为第二类生成物而存在,有人想要将此小说拍成电影,如果这部小说本身不享有任何权利,那么最后拍摄成功的电影也将由此失去享有电影著作权的权利基础,而一些投机者会因此对原本不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主张权利。僭称内容问题直接导致本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受到保护,实际不存在的著作权人或本来不具备资格的人享有作者的权利。这会带来如下后果:第一,在权利人实际不存在的情况下,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存续期间变得半虚构化;第二,一旦相关业者觉察到僭称内容问题的存在,会对内容相关许可业务风险有所顾忌,而第二类生成物与人类创作物难以区分,业者则不得已只能在风险之下进行许可业务,由此一来会给整体内容许可业务带来萎缩效果;再者,由于很难从外部表现上鉴定一个作品是第二类生成物还是人类创作物,因此只要知情者不告发,僭称行为被揭发的可能是很小的。综合以上考虑,有学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对策是从根本上灭杀僭称行为的诱因㉒[日]奥邨弘司:《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著作权——以著作物性为中心》,载《Patent》2017年第2期,第15页。。也即赋予第二类生成物与第一类生成物同样的著作权保护,这样就可达到祛除病灶之效果。
(二)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立法上的主要问题
以上从积极理由和消极理由两方面来说明了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性。从结论来看,基于激励理论来讨论是否赋予第二类生成物财产权更具合理性。从确保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回报机会的角度看,有必要给予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上的保护。但是,如果给予第二类生成物以著作权法保护,在立法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作品的要件认定。前面已提及,即使人工智能发生进化脱离人类控制进行独立创作,但是鉴于思想或情感为人类所特有,在这个意义上,第二类生成物很难突破其可被认定为是思想或情感的表达的藩篱㉓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发布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2016》对该问题亦持否定态度。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kettei/chizaikeikaku20160509.pdf#search=%27%E7%9F%A5%E7%9A%84%E8%B2%A1%E7%94%A3%E6%8E%A8%E9%80%B2%E8%A8%88%E7%94%BB2016%27,参见第8页。。因此,如果给予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首先需要修改作品的认定要件。让机器主体具有思想、信念、欲望、情感等这些自然人才有的特征进而使其成为真正的智能主体,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愿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试图设想如下场景:一台机器人给我们发来“今天很开心”这样一则消息,以此来表达他/她的情感,并试图与我们进行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或情感将不再是人类的特权。如果实现这一技术愿景的可能性不完全被排除,结合著作权法促进文化创新的立法目的,再来考虑作品认定要件,思想或情感的表达主体则无需桎梏于自然人,因为生物大脑所能产生的信息和人工智能所能产生的并无本质区别。虽然这与洛克的自然权论相违背,但在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产业利益面前,重新进行制度设计显然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福祉。
第二,权利归属。如果人工智能具有人类一样的思维,可以通过独立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心智创作的主体则不再限于人类,因为人工智能一样可以做到。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同自然人一样可以成为其生成物的权利主体,也即如何认定人工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这一问题自然就成了立法论探讨上的逻辑归属。虽然在技术上的确存在“智能代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从人类主体与智能主体的关系来看,我们并不愿看到二者最后发展成竞争关系或对抗关系的结果,而是期冀着一个人机协同的美好未来。在人机协同的策略设计中,为避免机器失控,有必要打破算法黑箱,引入机器算法的“伦理审计”,厘清其中的价值、利益、权利、责任与义务,并在规则制定上确保人类的绝对控制权。对此,英国《机器人和机器系统的伦理设计和应用指南》中提到,人类是负责任的主体,而不是机器人,应确保找到某一机器人责任人的可能性㉔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Guide to the Ethica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Robots and Robotic Systems, BS 8611:2016, British Standards Inst.,2016; shop.bsigroup.com/Product Detail?pid=000000000030320089.。因此,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否可能带来权利主体转移这一问题时,我们也应克服拟人思维所带来的陷阱,不应将人工智能想象成为同人类并列的法律主体。
如果人工智能不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而出于产业发展的政策考量,又有必要给予第二类生成物以著作权法保护,那么应如何对权利归属做出现实安排呢?现行《著作权法》确定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是作者享有著作权㉕现行《著作权法》第11条第1款。。作为一般原则的例外,还存在职务作品这种著作权人并非原始创作主体的制度安排㉖现行《著作权法》第16条。。一般来说,职务作品的创作事实上代表单位的意志而进行。熊琦教授认为,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法上也可视为代表设计者或训练者意志的创作行为,将人工智能的所有者视为作者在制度上不存在障碍㉗同注释⑤,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第8页。。但是第二类生成物的创作并不依赖于人类事先设定的规则,将此过程解释为代表设计者或训练者意志的创作行为未免有些牵强。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电影作品的权利归属亦是出于政策考量而做出的制度安排㉘现行《著作权法》第15条。。立法者之所以选择了一种对投资方也即制片人最为有利的规则,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确保投资者的回报机会;二是考虑参与到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人员较多,避免权利被过度分割而影响市场化㉙崔国斌著:《著作权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2页。。这两点理由对于第二类生成物的权利归属规则的设计同样适用。首先,确保投资者的回报机会已经在前面重点论述过,理应予以考虑。第二点理由也适用,这是因为第二类生成物的创作是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人工智能系统的所有者、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者等众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第二类生成物的权利也存在被过度分割的风险。有基于此,应将第二类生成物的权利设计为归属于对第二类生成物的创作负有责任的一方。这样一来,人工智能的所有者便成为最具可能性的选项。但是,一般来说,著作权分为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格权。在上述人工智能的所有人是非自然人而是法人的情况下,第二类生成物存在著作人格权没有享有主体的问题。鉴于第二类生成物原本不存在人格利益,因此可以将自然人享有的发表权、修改权以及保持作品完整权用著作财产权来替代。另外,关于署名权的问题,可考虑将作品原始归属于发表第二类生成物的责任人,也即人工智能的所有者。
第三,国际保护。作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国际公约,《伯尔尼公约》并没有直接规定作品一定为人类所创作,但是第3条第1款确定了国民的概念,也即本条约所保护的作品,其作者应是能够成为权利义务主体的国民。换言之,第二类生成物并不在公约的保护范围内。《伯尔尼公约》于1886年签订,其滞后于一百多年后人类所关注的新技术进展,实属当然。但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技术发展,制度设计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变更,因此有必要在国际条约上也给予相应的回应。
(三)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的风险
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立法,不仅存在上述制度设计上的问题,还可能因为前面提及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自身特点,而产生如下风险:第一,反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㉚See Michael A.Heller,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111 Harv.L.Rev.621()1998, Michael A.Heller&Rebecca S.Eisenberg,Can Patents Stifle Innovation?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280 Sci.698(1998).。该理论来自于公地悲剧(Commons Theory),如果牧草地任人使用,则会导致滥垦或滥捕,其结果是造成土地荒废。相反,反公地悲剧是指权利的过多存在会阻碍利用,进而导致创新停滞。人工智能在产量上远高于人类,假设现行著作权法冲破权利客体上的制度障碍,给予第二类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将直接导致著作权大量存在的问题。大量碎片化权利的存在,会增加知识产权许可的交易成本,进而阻碍作品的使用,这与知识产权法促进使用的立法初衷不符。同时,大量人工智能作品的存在会导致表达的选择范围受限,创作者出于对著作权人权利行使的担忧,创作活动也会由此而受到影响。第二,过剩保护问题。著作权法对独创性标准的要求不同于专利法,只需要达到最低的创造性即可。由此,第二类生成物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这些人工智能作品很可能是类似或相近作品,如果给予这些作品同样的著作权保护强度,会导致一些独创性不高的作品享有过剩的权利。
结 论
人工智能有望替代诸多人类脑力劳动,除可以进行作为本文讨论对象的小说、音乐、绘画等创作活动,亦可进行发明创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人工智能发明的可专利性及权利归属等问题,本文暂不予涉猎,留作日后单独讨论。而根据本文的讨论,作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第一类生成物可遵循计算机程序的著作权法保护的逻辑,其属于现行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范围,可以受到现行著作权法的保护。另一方面,作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第二类生成物在解释论上,很难认定其满足现行著作权法受保护的要件。但是,出于对促进产业发展的考虑,应确保人工智能相关人员能够回收其资本投入和智力投入的机会,因此,当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人工智能可实现独立创作时,有必要修改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给予这类生成物以制度上的保护。但是,在制度设计上应确保人的主体性与控制权,避免陷入拟人思维的陷阱。此外,应考虑到反公地悲剧问题,应赋予第二类生成物相对排他权,也即在碎片化权利大量存在的情况下,限制第二类生成物的著作权人肆意行使停止侵害的权利。再者,为防止过剩保护问题,应充分利用现行著作权法中独创性标准这一政策杠杆,仅给予高于一定创作高度的第二类生成物以著作权法保护,而非一刀切式的保护。
国际上也存在为人工智能单独立法(sui generis)的讨论㉛同注释㉕,《知识产权推进计划2016》。2016年5月,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JURI)发布《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的报告草案》(Draft 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同年 10 月,发布研究成果《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European Civil Law Rules in Robotics),推进人工智能法律研究,包括可能的立法和监管措施,未来将成为欧盟立法议程的一个核心,是否会为人工智能单独立法仍属未知。。但是,回顾过去国际上对计算机程序、DNA相关发明及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的讨论,从结果来看,都没有采取单独立法路径。这是因为,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发展依赖于知识产权的全球化保护,如果当初美国对计算机程序采取单独立法,而他国并未对计算机程序单独立法,或者即使单独立法但并未采取与美国同样的保护标准,会导致计算机软件仅在美国域内可以得到有效保护,随之带来的是美国计算机软件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被削弱的后果。我们在探讨是否为人工智能单独立法时,既要考虑到本土化问题,也应考虑到全球化背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问题。根据高盛的研究报告,中国和美国将是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如果中国对人工智能单独立法,则可能会导致中国保护标准与国外不相接洽的问题,进而造成人工智能产业在国内固步自封的后果。因此,在现行知识产权法框架下讨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问题,对中国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reliance on human be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produc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kinds: the product originated from human being (the first category product)and the product not originated from human being (the second category produ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ve theory, the first category product is protected by the existing Copyright Law, and the second category product are not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on theory, the necessity of giv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the second category produc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centive theory, but there are some obstacles in system design. Considering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the second category product should also be given copyright protection when necessary.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pyright Law
刘影,法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