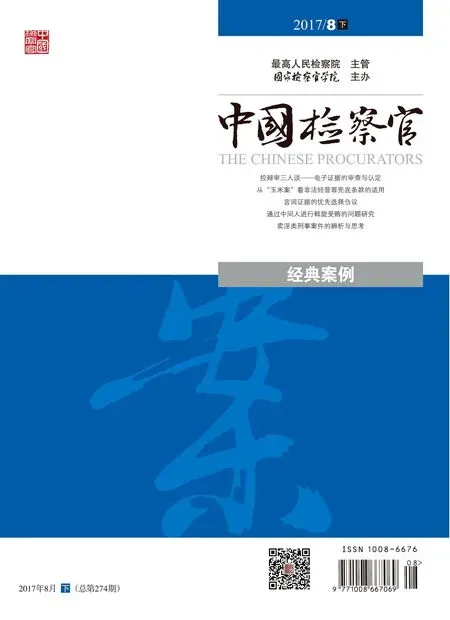在非机动车道上放置“黑心钉”的行为定性和量刑均衡
文◎周 浩
在非机动车道上放置“黑心钉”的行为定性和量刑均衡
文◎周 浩*
一、基本案情
熊某某系电动车修理铺的店主,为了增加收入,熊某某与张某某合作,通过在非机动车道上投放钢丝钉扎破过往行人电动车和自行车轮胎的方式,增加店内补换轮胎的生意。二人约定由张某某负责制作和投放钢丝钉,熊某某在店内负责补换轮胎,每补一个轮胎收费人民币5元。熊某某和张某某供述称,2014年3月底至2015年3月24日期间,张某某每隔3至4天就在H市S区W路东向西沿线的非机动车道投放钢丝钉,致使过往大量电动车和自行车轮胎被扎破,由此二人增加非法收入达到人民币2万余元。现查明,部分被害人电动车的轮胎在同一路段多次被扎破,部分被害人向市长公开电话反馈情况44次,向区长公开电话反馈投诉12次,向公安机关报案79次,多名被害人均报案称至少有3次轮胎被扎破,部分被害人报称累计被扎破轮胎就达到100余次。案发期间,公安机关使用自制的推钉器起获了涉案赃物钢丝钉15枚。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熊某某和张某某在公共道路上设置“黑心钉”,致使过往的不特定车辆处于危险状态中,且客观上造成了不特定对象的大量财物受损,应当将二人的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熊某某和张某某设置“黑心钉”所针对的犯罪对象是途径W路段的过往车辆,属于不特定对象,应当认为是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且情节严重,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具体分析如下:
(一)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未达到危险方法的相当性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是危险方法,而危险方法必须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典型行为具有同质性。在司法实践中,危险方法多基于结果危险性进行判断,即从行为造成的结果倒推行为当时对公共安全所造成的危险程度,且危害结果多为“多人伤亡”或者“财物遭受重大损失”。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的危险犯,应当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行为是否达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而危害结果只是行为危险的具化后果,不应作为危险方法的判断标准。结果倒推模式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刑法的误区,造成客观归罪。因此,应将行为当时的危险性作为判断是否属于危险方法的标准。
“行为危险性”应当将一般的社会大众作为判断主体,由社会大众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以法律事实作为当时行为的基础,从生活经验法则出发作出行为危险性质的判断。而生活经验法则实际上可以归纳为行为“具有足以使公众难以防范和抵御而行为人本身又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属性。”[1]具体到本案中,以熊某某和张某某行为当时的情况来判断,二人实施的行为不是危险方法。第一,行为基础。熊某某和张某某选定W路段作为作案地点,并在夜深时分由张某某每次投放一颗钢丝钉。在钢丝钉被消耗完毕或者被公安机关推平后,熊某某和张某某再次投放。这是判断行为危险性的行为基础。第二,客观条件。熊某某和张某某制作的钢丝钉取材自店内的自行车钢丝圈,将钢丝钉磨成尖头针,用胶水固定在道路上。熊某某和张某某在放置钢丝钉时,选取的位置在W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上,且在该固定的路段每次设置一枚钢丝钉,并非在道路上密集设置钢丝钉。熊某某和张某某选择在修车店骑行500米之内的路段为作案地点。第三,判断主体。应当以社会大众为主体,而不应该将具有法律素养或者科学知识的人作为预设主体。无论是具有法律素养还是具有专业科学知识的人,判断危险性时难免受到认识能力因素的影响,而过早带入规范、价值判断,混淆不法与责任。实际上被害人群体即可以作为判断主体。虽然被害人属于偏见方,但即使在本案偏见方的言辞证据中,也没有看到被害人指控行为的公共危险性,因此可以将被害人作为参照主体。结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普通的社会公众,即使是偏见方也能够判断,在非机动车道上设置并不密集的钢丝钉,可能会随机扎破过往自行车轮胎,但不可能导致低速行驶的非机动车辆倾覆的危险。放置“黑心钉”的行为显然没有达到危险方法的危险程度。
从反面来说,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也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的表述。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虽然使骑行人员难以防范和抵御危害后果,但二人将钢丝钉放置在低速骑行的非机动车道,避免大面积设置钢丝钉,且在距离修车店不远处选择作案地点,保障及时维修车辆。因此,熊某某和张某某在有意预测结果并将危害结果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符合危险方法的行为属性。
(二)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在本案中,熊某某和张某某的客观行为表现为损毁财物,且损毁的财物均为随机的过往车辆。尽管二人的行为在客观方面具有寻衅滋事的表象,但从寻衅滋事罪的特征来分析,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一,动机不符。熊某某和张某某并不是出于流氓动机。虽然犯罪构成理论对于犯罪行为的主观要素的要求是罪过,犯罪动机和目的不是主观方面的必然构成要件,但鉴于寻衅滋事罪脱离于流氓罪的特殊历史原因,且具有鲜明的立法特征,因此通说认为要认定寻衅滋事罪,仍然要求行为人具有流氓动机。犯罪动机多是指行为人所追求、所希望的最终结果,反映的是行为人的内心倾向。而寻衅滋事罪的动机是逞强争霸、寻求刺激、发泄不满,是一种畸形心理。但在本案中,二人的动机就是以非法的手段进一步增加店铺的收入,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并非是欺行霸市、无事生非的流氓心理,因此熊某某和张某某的犯罪动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
第二,对象不符。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复杂法益,按照不同的客观行为所侵犯的复合法益也不同,而本案所侵犯的法益应当是社会公共秩序和公私财物双重法益。“任意损毁型”的寻衅滋事犯罪应当是随心所欲地损坏公私财物,从这一点上来说寻衅滋事罪所针对的犯罪对象是不特定的公私财物,不限定财物的种类、价值,对于所损坏的公私财物不加选择和甄别,都予以损坏。但本案中犯罪对象是特定且明确的。从张某某和熊某某二人选择作案地点、方式来看,主要有几个特点:其一,熊某某和张某某将钢丝钉放置在非机动车道上,将范围限制在非机动车;其二,钢丝钉放置的数量少,将数量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其三,钢丝钉在放置后三、四天内就损耗,且将对象限制在电动车或者自行车轮胎。因此,笔者认为熊某某和张某某对犯罪对象是加以甄别和选择的,明确犯罪对象就是他人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轮胎,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不特定公私财物特征。
(三)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二人主观上有使用钢丝钉扎破他人电动车和自行车轮胎的故意,客观上二人分工合作具体实施犯罪,已经具备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该当性。但在这一点中需要论述的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量刑均衡问题。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要求为3次以上或者财物损失5千元以上,但数额巨大及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没有司法解释。在上位法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律允许地方司法机关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相应的标准。以Z省H市的地方标准为例,数额巨大的规定为5万元以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规定为毁坏公私财物10次以上。具体到本案中,如果以被害人所报称的次数来计算,熊某某和张某某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将达到近千次;如果计算犯罪数额,根据侵权法的规定,侵权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而熊某某和张某某应当将扎破的轮胎恢复原状,因此从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出发,熊某某和张某某非法收取的补换轮胎费用等价于犯罪数额。显而易见,不同的计算方式将导致截然不同的量刑待遇——如以次数计算,本案的量刑将在法定刑期内顶格量刑,即7年有期徒刑;如以犯罪数额计算,本案甚至达不到3年有期徒刑的门槛。
法律应当在个案中实现公正。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目的犯理论以实现量刑均衡。第一,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犯罪体系地位决定其隐含法律的漏洞。故意毁坏财物罪规定于刑法的第五章,其所侵犯的法益是公私财产的合法权益。根据法益侵害说,不能单纯通过客观行为来对违法性进行判断,而应当兼顾主观和实害后果来对行为作出是否具有违法性的实质性判断,这与我国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同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从侵害的法益出发,来判断行为的违法性。故意毁坏财物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犯罪处于同一法益体系下,所侵犯的法益都是对他人占有的财物进行破坏或者非法转移。但侵财型犯罪体系下均存在着法律漏洞,即所有罪状的表述均是客观行为的表述,没有明确表明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区分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此罪与彼罪。如行为人非法进入他人家中,但未取走财物即离开,则无法通过客观行为表现来认定该行为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还是盗窃罪。因此,在侵财型犯罪体系下,单纯的行为表述是隐含法律漏洞的。
第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律漏洞补充应当进行目的性限缩。侵财型犯罪的罪状规定是存在法律漏洞的,但属于可以补充或者说是可以解释的法律漏洞。虽然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司法者严格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适法,但允许司法者在不违背文义解释的涵义射程范围内,基于刑法目的对法律文本的漏洞进行补充——即刑法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法益,更应当保护行为人的人身权利。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补充和完善,但对法律漏洞的补充不能随意和扩大,否则导致法律适用的恣意。因此必须对法律漏洞进行目的性限缩,防止超越法律的框架。目的性限缩的基础是立法目的,具体到侵财型犯罪中,立法目的是实现对财产占有的保障。而侵财型犯罪的罪状表述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未超出法条条文的隐含涵义,故不属于扩大或者类推解释。因此,通说认为盗窃罪、抢夺罪、诈骗罪等典型的侵财型犯罪具有非法定的主观超过要素——以非法占有的目的,故均属于非法定的目的犯。作为同一个犯罪体系下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当然包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同属于目的犯。需要说明的是,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对财物占有状态的非法变更,其中非法占有意思既可以包含利用、处分,也可以包含长期控制或者毁灭,只需要达到剥夺占有人的占有的目的即可。如行为人以盗窃方式取得财物,后将财物毁灭,如何区分盗窃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关键就在于两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尽管在占有意思上,故意毁坏财物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等不相同,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仍然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第三,目的犯行为次数的认定以“目的”为基准。无论从目的犯的性质,还是从刑事政策角度出发,行为人出于同一犯罪目的,并实施终了一次犯罪行为,在计算次数时,视为一次犯罪行为。具体到本案中,应当将二人以破坏占有为目的投放钉子的行为视为一次行为。笔者认为应以张某某放置钢丝钉的次数来认定故意毁坏财物的次数,即每一次放置钢丝钉导致他人财物多次损毁都算作一次。虽然熊某某和张某某都供称放置钢丝钉的时间间隔以及非法所得情况,但以时间间隔和犯罪数额进行推算均不符合证据裁判原则。而公安机关在案发期间,用推钉器起获了15枚钢丝钉。因此,虽然无法完全还原客观事实,但根据法律事实,熊某某和张某某毁坏他人财物的次数至少在15次以上,故应当在法定刑期最低刑期3年有期徒刑对熊某某和张某某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注释:
[1]李炜、张勇:《认定其他危险方法不应只注重结果危险性》,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21期。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3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