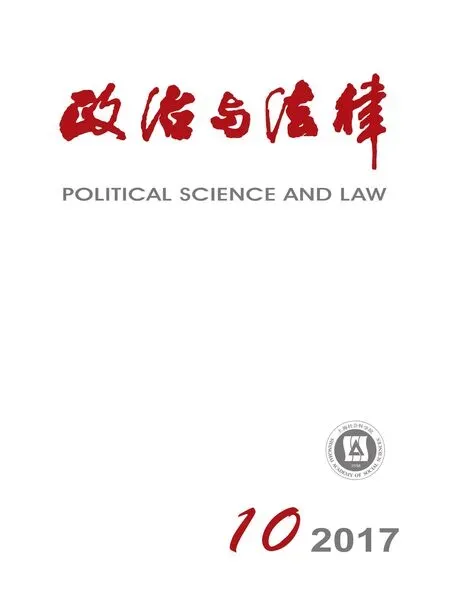被害人教义学在德国:源流、发展与局限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被害人教义学在德国:源流、发展与局限
车浩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德国的被害人教义学肇始于刑法分论若干具体罪名的研究,从被害人自我保护和刑法辅助性原则的视角研究个罪,主要集中于诈骗罪中的被害人因素。之后被害人教义学持续发展,从最初涉及的诈骗罪和侵害私人秘密罪出发,不断地向越来越多的构成要件扩展和蔓延,并试图在分则体系与总则体系之间架起桥梁。与此同时,被害人教义学也面临着各种争议,比较基础性的争议集中于对刑法辅助性原则的不同理解及这种思想在刑事政策的导向上是否正确。目前德国的刑法教义学仍处于不断深化、渗透、传播及争取共识的进程中。从被害人视角切入刑法问题,将传统的行为人单维视角的理解模式,改变为“行为人-被害人”双维视角的理解模式,这才是被害人教义学的概念应当承载的使命和理论目标。被害人教义学能够在规范层面上理解并规范化地处理被害人的行为对行为人的影响,通过一般性的理论构建回应被害人的规范需求。一个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被害人教义学理论体系将给未来的刑法理论革新带来深刻的影响。
被害人教义学; 刑事辅助性; 刑事政策;“行为人-被害人”双维视角
笔者于本文中所称的被害人教义学,是从被害人角度展开的刑法教义学。它以被害人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落脚点是合理有效地回应被害人的规范需求。传统的刑法理论都是从行为人出发,单向度地沿着行为人的行为这一方向去思考刑法问题,展开不法与责任的判断。被害人教义学试图打破这一传统的理解模式,构建一种“行为人-被害人”双维视角下理解刑法的思考模式。它的最初灵感来自于犯罪学领域中的被害人学研究,特别是在一些犯罪人与被害人有互动关系的场合,被害人的行为在事实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行为人的行为。如何在规范层面上理解这种事实性的影响?如何在法教义学的领域中规范化地处理这种影响?如何通过一般性的理论构建,回应被害人的规范需求?这些就是被害人教义学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追求。
笔者于本文中将要完成的工作,是对于德国的刑法学同行们所界定的“被害人教义学”的源流、发展和局限,做一个尽量简明的梳理和评价,这样也有利于分析、回应上述问题。被害人教义学在德国的状况(或者说)德国版的被害人教义学(既对笔者以往的思考构成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借鉴,也让笔者感到不能满意,由此推动笔者以此为基础,努力构建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被害人教义学理论。
一、首次亮相:“错误”的登场
当德国学者阿梅隆于1977年发表论文,讨论诈骗罪中受骗者的错误与怀疑这个问题时,他并不会想到,由此引发的,不仅是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热衷于从被害人角度展开讨论的倾向,而且激发了一种被德国同行中的批判者称之为“被害人教义学”的一般性理论的风潮。这种理论将行为不法的判断与被害人联系在一起,野心勃勃地想要在众多构成要件的限缩性解释中发挥作用,并在刑法总论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阿梅隆最初的论文中,他只是把目光盯在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几个行为特征中的“错误”这个要素上。*Amelung, Irrtum und Zweifel des Getaeuschten beim Betrug, GA, 1977, S.在他看来,只有那种不包含任何具体怀疑的认识偏差,才能认定为错误。如果一个人已经对他人言行的真伪产生了具体怀疑而仍然处分财物,此时,这就不再是陷入错误的财产处分,而是一种带有冒险性质的投机行为。对于这种自冒风险的投机行为,刑法没有保护的必要性。
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社会中的交往行为。在一个匿名化的、高度复杂化的经济交往的环境中,整个社会交往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应当对自己与他人的财产交易安全抱着谨慎小心的态度。换言之,带着审慎甚至怀疑的眼光去从事交易,是一个交易者必备的品质。例如,通过各种渠道去验证交易条件是否属实,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担保,发现有不确定、不安全的或者其他值得怀疑的因素时停止交易等等。在阿梅隆眼中,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交易者可以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只有在这些措施无效之后,交易者才可以去寻求国家的保护。然而,如果交易者已经对交易产生了具体的怀疑,却仍然置这些本可以轻易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于不顾,而在投机未遂的情况下,完全依赖国家的救济,这样只会催生一群懒惰的投机者。因为这相当于是把消除交易风险的任务一股脑地交给了国家,只想着利用刑罚的强制力来威慑潜在的欺诈者,却不肯在自己能够消除风险的情况下去自我保护。对此,阿梅隆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刑法不应当承担对所有的受骗者进行全面保护的任务,那些已经产生具体怀疑却仍然交易的人并没有陷入错误,而仅仅是在投机,对此,应当将其排除出刑法保护范围。*Amelung, Irrtum und Zweifel des Getaeuschten beim Betrug, GA, 1977, S. 7f.
为了准确理解阿梅隆的观点,这里用另一种从被害人本身特点入手研究诈骗罪的观点进行对比。比阿梅隆更早,瑙克在1974年提出,对于简单、拙劣、易于识破的欺诈行为,应当排除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在这些骗局中上当受骗者,往往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无助者,但是这样一来,刑法就要承担着全面培训公民交往能力的任务,这对于刑法而言,是过于奢侈的工作。因此,刑法不应当给愚笨者或缺乏经验者提供帮助,而是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去自我训练自己的决断能力。一言以蔽之,刑法并不是用来训练智力和弥补安全感的工具。*Naucke, Die kausalzusammenhang zwischen Taeuschung und Irttm beim Betrug, FS Peter, 1974, S.117f.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人们去信任那些明显拙劣和虚假的骗术,刑法就不应当保护这种信任;相反,只有那些复杂的、不易被识破的骗术,才具有刑事可罚性。只是,由此必然会引出的争议是,轻信的受骗者不受刑法保护是否符合诈骗罪的立法价值。与此相联系的结论是,面对一个拙劣的骗术而轻信上当者,可能是愚蠢和智力缺陷者,但是,对这种社会意义上的不保护弱者的歧视性立场是有争议的,这涉及非常复杂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与瑙克的观点不同,阿梅隆自认为,他的观点并没有陷入上述价值判断的泥潭中。在他看来,对存有具体怀疑者不予保护,不是一个是否值得保护的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需要保护的问题。因为轻信的人未必就是愚蠢的人,他们之所以受骗上当,往往不是由于愚蠢或智力缺陷,而是由于不积极运用自己的智力进行审慎的判断。因此,对已经有了具体怀疑但仍然不进行自我保护的被害人而言,不提供刑法保护,排除的不是被害人的应保护性或者说值得保护性,而是需保护性或者说保护必要性。排除的根据,也不是根据被害人的愚蠢或道德方面的价值判断的理由,而是根据他在处分财产的心理事实。*Amelung, Irrtum und Zweifel des Getaeuschten beim Betrug, GA, 1977, S. 9f.那就是,交易在客观上存在足以令人怀疑的事实,被害人主观上也对交易的真实性产生了具体怀疑,但仍然处分了财产,这就是放弃了本来可以实施的自我保护。从构成要件特征上讲,此处排除了德国《刑法》第263条中“错误”的要素,行为人不构成诈骗罪。于是,为后来那些支持或反对“被害人教义学”的德国学者们共同认可的该理论的核心原则,在阿梅隆的这篇文章中就雏形出现了:如果被害人有适当的手段可以自我保护却不使用,那么以辅助性保护为原则的刑法就没有必要介入。
阿梅隆的文章是被害人教义学正式亮相的开山之作。从一开始,被害人教义学就从刑法分论而非总论的舞台上登场,奠定了从被害人自我保护和刑法辅助性原则的视角研究个罪的基调。在此文发表之后的几十年中,德国刑法学界涌现了大量从被害人的角度分析诈骗罪构成要件各个特征的文献。诈骗罪中的被害人因素,成为一股学术潮流,当然也引发了此起彼伏的激烈争论。
二、纵深发展:鏖战于诈骗罪的主战场
诈骗罪,向来被认为是验证和演练被害人教义学的最佳场所,是“一个深入检验被害人教义学效能和极限的例子”,因为“迄今为止被害人教义学在德国刑法第263条的构成要件上面被说明得最详尽”。*[德]许乃曼:《刑事不法之体系:以法益概念与被害者学作为总则体系与分则体系间的桥梁》,载许玉秀、陈志辉等编译:《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6年版,第221页。可以说,在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各个要素上面,都集中了大量的从被害人角度展开的讨论。
首先,是关于“错误”的研究。在阿梅隆前后,哈赛默、赫茨伯格、库恩、弗里希等学者都曾经对“错误”展开过研究。例如,赫茨伯格主张用被害人同意的意思瑕疵理论来解决诈骗罪中的错误问题。通过与德国刑法中的侵占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进行对比,赫茨伯格认为,诈骗罪中的错误范围,与在侵占罪或毁坏财物罪中,认定那些足以影响被害人同意效力的瑕疵标准是一样的。*Herzberg, Funktion und Bedeutung des Merkmals “Irrtums” im § 263 StGB, GA, 1977.按照这种观点,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是一种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同意的内容就是财产损失。如果这种同意是在没有意思瑕疵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被害人就没有陷入错误,就应当排除诈骗罪的既遂。诈骗罪的解释能够与其他财产中的同意瑕疵的解释在体系上保持协调一致,这是赫茨伯格自认为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优点。至于错误这一要素的功能,赫茨伯格认为并不像阿梅隆所说的那样,是有助于刑法辅助性原则的实现,而是将那些被害人没有意思瑕疵的情况下处分财产而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从诈骗罪的既遂中排除出去。*在赫茨伯格1977年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阿茨特已经在1970年的著作中提出了“法益错误说”的理论。他将被害人同意中的错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益(相关性)错误, 另一类是与法益无关的错误,主要是指动机错误。 前者会使同意无效,后者并不影响同意效力。Arzt, Willensmaengel bei der Einwilligung, 1970.其后,等到这种理论成为德日刑法学界的通说之日,就被有心的日本学者如山口厚拿去,用在了对诈骗罪的错误的解释上面,成为山口厚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实际上,将被害人同意瑕疵理论与诈骗罪中的错误联系在一起,这个思路的始作俑者是赫茨伯格,他当时在文中也提到了法益相关的认知缺陷(rechtsgutsbezogene Fehlvorstellung)。只是,山口厚对法益错误说在诈骗罪中的引入更为彻底,那些与法益无关的错误,都不属于诈骗罪的“错误”,由此,实现了这一要素的排除功能。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页。赫茨伯格对阿梅隆的批评遭到了哈赛默的反驳。在哈赛默看来,在德国刑法规定的侵占罪和毁坏财物罪中,立法者并没有要求以“错误”为构成要件特征。诈骗罪中被立法者明确规定的“错误”与同意是两回事,不应该扯在一起。这样反而会使得“错误”这个要素的功能变得模糊不清。*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124.
又如,尽管弗里希赞成阿梅隆从被害人角度探讨错误要素,因为“目前德国刑法理论对被害人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关注太少,没有清晰的说明”,*Frisch, Funktion und Inhalt des “Irrtums” im Betrugtatbestand, FS Bockelmann, 1978, S. 657.但是,其对于阿梅隆由此与刑法辅助性原则相联系的做法却大不以为然。刑法辅助性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为什么它仅仅在阿梅隆所说的诈骗罪这种关系型犯罪中凸显出来,却在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沉默?在弗里希看来,这种“在一个独特的、个别的概念(错误)身上赋予普遍性原则的功能”的思考方式是错误的,因为个别的法律概念的功能仅在于指向和确定特定的事实,而类似于刑法辅助性这样的普遍性原则,正好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限制的作用。*Frisch, Funktion und Inhalt des “Irrtums” im Betrugtatbestand, FS Bockelmann, 1978, S. 656.在批评阿梅隆将错误概念的功能与刑法辅助性不当关联之后,弗里希提出了他所理解的错误的功能。作为自我损害型的财产犯罪,被害人的财产处分处在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中心。弗里希眼中的错误,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处分行为的预备状态。处分财产的预备行为范围宽泛,而错误的功能,就是标志着一种会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后果的特定的、危险的预备形态。*Frisch, Funktion und Inhalt des “Irrtums” im Betrugtatbestand, FS Bockelmann, 1978, S. 660f.这就为诈骗罪的处罚限定了范围。
与阿梅隆的观点相呼应,这个领域中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哈赛默,进一步把德国《刑法》第263条规定“错误”的立法任务与自我保护可能性联结起来。哈赛默在著作中通过“危险强度”的概念来引入被害人的作用。立法者规定构成诈骗罪需具备“错误”的特征,就是在描述一种典型的被害人缺乏保护可能性的状况,它与立法者规定的另一个构成要件特征“欺诈”一起,在法律上共同设定了诈骗罪的危险强度。按照哈赛默的划定,诈骗罪属于一种关系型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互动关系,犯罪的成立需要一方对另一方行为的配合,对诈骗罪而言就是处分财产。这同时也意味着,被害人在这种侵害模式中发挥着共同作用,他对于阻止这种侵害完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54, 55.简单地说,在诈骗罪的结构中,一方面是来自于行为人的危险行为,另一方面是来自于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只有当前者的强度达到了足以让后者无效的情况下,诈骗罪的刑法保护才是必要的。
可以看出,哈赛默尝试在诈骗罪的欺诈行为的特征与错误特征之间,建立起一种功能性的关联。正是由于危险强度足够狡猾和欺骗性的欺诈行为,让被害人陷入到无法进行自我保护的错误状态之中,才处分了财产遭受了损失。相反,如果行为人的骗术没有对被害人产生那么强的效果,却让被害人产生了具体怀疑,*哈赛默把被害人的主观状况区分为三种形态:主观确信、模糊怀疑和具体怀疑。主观确信是指被害人确信自己得到的信息完全是真实完整的;模糊怀疑是指被害人对于交易的不安全性有模糊的感觉;具体怀疑是指被害人的怀疑程度超过了模糊的感觉,而是对特定相关事实的真实性产生疑问。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132ff.此时,被害人就有充分的能力并且也被期待去进行自我保护,因为他并没有陷入一个错误,从而也不需要刑法的保护。*对于产生具体怀疑却不自保的情形,哈赛默列举了两种类型加以说明。一种是懒惰的被害人,另一种是投机的被害人。这两种被害人在有具体怀疑的情况下都有自保的可能性,但是基于自身原因而仍然处分财产,这就属于未陷入错误。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162.由此,哈赛默就把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错误”特征,功能化地诠释为刑法辅助性原则的实现。这在思路和结论上与阿梅隆保持了一致性。不过,与阿梅隆一样,哈赛默的观点也遭受了不少批评。麦瓦德认为,按照哈赛默的理论,恰恰会把那些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排除在诈骗罪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有违社会伦理的基本底线。*Maiwald, Literatur Bericht zur R.Hassemer, ZStW96(1984), S.70ff. 按照哈赛默的表述,处于愚笨、缺乏考虑和经验而处于确信或模糊怀疑的人群,应当保留其应保护性。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165. 所以,麦瓦德的批评有对哈赛默的观点曲解之处。这些人,而不是哈赛默所说的懒惰者或投机者,可能更符合麦瓦德所说的弱势人群。
其次,关于“欺诈行为”的要素,也有不少学者从被害人角度展开研究,如前述瑙克的观点。根据理性的、有正常生活经验的一般人的标准,那些通常情况下根本不会上当受骗的低级、拙劣、易于识破的骗术,应当被排除在诈骗罪的欺诈行为之外。*瑙克认为,下面案例中的被害人就不应当受到诈骗罪的保护:一个厨师做广告,谎称自己是一个性工作者,只要有人按照指定的地址付款,就会上门提供服务。瑙克认为如此拙劣的骗术,根本没有达到欺诈行为所要求的狡猾的标准,被害人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Naucke, Die kausalzusammenhang zwischen Taeuschung und Irttm beim Betrug, FS Peter, 1974, S.112.当然,瑙克也为精神病人和儿童的保护留下了余地。这些人虽然可以被归入愚笨或缺乏生活经验之列,但是这种状态的出现,并非他们自身不努力去学习和适应,而是由于不可改变的原因,因此,这些人也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只是在瑙克看来,这种欺诈行为已经不属于诈骗而是盗窃或者侵占。*Naucke, Die kausalzusammenhang zwischen Taeuschung und Irttm beim Betrug, FS Peter, 1974, S.116.埃尔默赞成瑙克在诈骗罪构成要件层面考虑被害人共同责任的想法,同时认为,应当在个案中仔细考察欺诈行为是否属于一般人眼中的简单、拙劣的低级骗术。*Ellmer, Betrug und Opfermitverantwortung, 1986, S. 148f.
还有一些学者从被害人角度讨论诈骗罪各个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瑙克认为,通过改变欺诈与认识错误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则,使用相当因果关系说而非条件说,可以对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行限缩解释。相当性的因果关系意味着进行规范的判断,由此可以评价欺骗行为的强度以及对骗术无力抵抗的被害人。在瑙克看来,在诈骗罪中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就是将被害人共同责任的思想融入诈骗罪教义学的表现,由此可以限制刑法适用,让交易者增强财产安全意识。*Naucke,Die kausalzusammenhang zwischen Taeuschung und Irttm beim Betrug, FS Peter, 1974, S.118f.又如,布莱认为,在被害人对行为人所说情况产生怀疑的场合,并不是像阿梅隆那样从否定“错误”的角度来排除可罚性,而是因为,这种怀疑与财产处分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过,布莱在原则上也同意阿梅隆关于被害人自我保护的想法。他之所以否定错误与财产处分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因为产生了怀疑的被害人原本能够自我保护,或者说,本来有机会避免自己的财产遭受损失。*Blei, Strafrecht BT, 1978, S. 199.不过,布莱的观点也受到了希伦坎普的批评。被害人在产生怀疑时仍然处分财产,恰恰说明骗术的高明。怀疑并不能直接否定错误,而只是说明,这个错误因为可避免而危险性较小而已。Hillenkamp, Der Einfluss des Opferverhaltens auf die dogmatische Beurteilung der Tat, 1983, S. 25f.
比这种因果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规范化,也更加具有总论色彩的分析,是库尔特将客观归责理论引入到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分析之中。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是客观归责的下位规则之一,它意味着,如果风险实现的类型并没有包含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或者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就不能将此归责给行为人。库尔特将此一般原理引入到诈骗罪中。*Kurth, Das Mitverschulden des Opfers beim Betrug, 1984, S. 171ff.按照他的观点,在被害人共同负责的情况下,虽然行为人通过实施骗术创设了一个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但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这个风险的具体实现,而是由于被害人自己的疏忽所导致的,因而不能轻易地将此结果归责给行为人。还需要进一步判断的是,在共同负责的场合,究竟是行为人的欺诈还是被害人的过失对整个风险实现有支配地位。如果是后者,即被害人在共同责任中占统治地位,就不能再把结果归责给行为人,而只能由被害人自己承担。
综上所述,在诈骗罪的领域,从被害人角度展开研究可谓是应者云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刑法学的语境中,“被害人教义学”这顶帽子,只戴在了其中部分学者的头上。换言之,并非上文评述的与被害人相关的诈骗罪研究,都被德国学界称之为“被害人教义学”。这个被部分德国学者抢注“商标”的一般认定的理论符号,包含了特定的内涵,因而也只有部分德国学者愿意用在自己身上。
三、开疆拓土:向其他构成要件延展
“被害人教义学”的说法,几乎是在一面世,就遭遇了“新瓶装旧酒”的指责,认为这个概念只不过是把早在它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工作,归入这个名目之下而已。*S/S/Lenckner, vor 13 Rdnr. 70b.令人尴尬的是,就连被许乃曼引为同道的埃尔默,*在许乃曼的划分中,自己和阿梅隆以及哈赛默属于一派,埃尔默、库尔特属于另外一派,但都属于被害人教义学的阵营,只是路径不同而已。Schuenemann, Die Schwindel in der Dogmatik und die doppelte Weishei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Beulk, 2015, S. 543.也并不愿意被归入“被害人教义学”的阵营中,他不无讥讽地指出:“被害人教义学只是一个盖上印戳的‘流行词’,古老的认识被贴上了新的标签就作为新产品出售了。”*Ellmer, Betrug und Opfermitverantwortung, 1986, S. 268.与之相似,研究主题多与被害人相关的阿茨特,则把“被害人教义学”的观点,淡化成是“理所当然之事的重新发现”,*Arzt, Rezension Raimund 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 und Strafrechtdogmatik, GA 1982, 522. 观点类似的,还有米特胥,他也质疑所谓的被害人教义学究竟是新发现还是重新发现?“就像带有欺骗性的波特金村庄一样,在用涂料粉刷上了一层新的语词外表之下,是被尘埃遮盖的古老的思想建筑。”Mitsch, Rechtfertigung und Opferverhalten, 2004, S.13.并且不同意罗克辛把他称之为“被害人教义学之父”。*Roxin, Anm. Zu BGHSt 31, 915, JR 1983, 335, Fn.12. 阿茨特的反对意见,Arzt, Viktimologie und Strafrecht, MschrKrim 1984, 113.
与上述质疑声相反,在被害人教义学这个概念正当化的过程中,许乃曼以一种当仁不让的姿态出现,“他把重要的角色分配给了自己”。*Mitsch, Rechtfertigung und Opferverhalten, 2004, S.14.从许乃曼自己的角度来说,标志性的文献是他在1986年发表的《被害人在刑法保护中的地位》。*Schuenemann, Zur Stellung des Opfers im System der Strafrechtspflege, NStZ 1986, 439.然而,实际情况是,就被害人教义学这个名称而言,既不是来自于许乃曼,也不是来自于他的追随者,而是来自于最重要的反对者希伦坎普,他在自己1981年的著作中创造了这个名称。“被害人学(Viktimologie)和教义学(Dogmatik)的融合产生了被害人教义学(Viktimodogmatik)。”*Hillenkamp, Vorsatztat und Opferverhalten, 1981.这个概念一经问世,立刻成为一面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下努力证明其价值,并且始终站在回击反对意见的第一线的,是许乃曼。在整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评价体系中,许乃曼以持续的热情积极评价被害人教义学的地位和作用,例如像“教义学的新发展”、“最重要的立法者格言”、“刑事政策的指针”、“刑事政策的格言”、“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成熟果实”等等。*这些评价来自于许乃曼不同时期的一些文章。Schuenemann, Einige vorlaeufige Bemerkungen, S. 413.; Schuenemann,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von Privatgeheimnissen, ZStW 90(1978), 11ff.; Schuenemann, GA 1985,352 Fn.32.; Schuenemann, FS Faller, S.362.;Schuenemann, FS R. Schmitt, S.129.总之,这些来自于许乃曼的表述,一直在提供关于被害人教义学价值的论证。*Mitsch, Rechtfertigung und Opferverhalten, 2004, S.14.
作为被害人教义学的旗手,许乃曼在这个领域中的开端性文献,是其于1978年发表的《刑法对于私人秘密的保护》一文。*Schuenemann,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von Privatgeheimnissen, ZStW 90(1978), 11ff.该文是许乃曼1977年向德国刑法学会提交的报告。在这篇讨论私人秘密的刑法保护的报告中,许乃曼显示出了与同年发表的阿梅隆的论文讨论诈骗罪相似的思路。德国《刑法》第203条规定了侵犯他人秘密罪。根据该条,医师、药剂师、心理师、律师、婚姻家庭咨询人员等人士,无故泄露因该身份而受托付或以其他方法而知悉的他人秘密,特别是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秘密或经营业务秘密的,构成侵害他人秘密罪。许乃曼认为,泄密行为人的主体身份应当限定在特定的受托人范围之内。因为只有特定的负有义务保守秘密的人泄露了秘密,才属于刑罚的对象。第三人可因他人泄露秘密而免于处罚,因为只有针对那些秘密所有人无法避免,必须吐露个人秘密且必须信赖的特定人而言,秘密所有人才是需要保护的。第三人也能够经由他所委托的人来泄露秘密而免于处罚。因而也免除听第三人泄露秘密之人的保守该秘密的人。同样的,秘密所有人保守特定秘密也是如此,因为需要或期待特定利害关系人的保守秘密的意愿,也属于秘密概念的一部分。
这篇文章中举了一个如何看待患者秘密的例子。一个患者在治疗期间主动向医生透露自己与某官员夫人有暧昧关系。许乃曼认为,由于这一信息与治疗行为毫无联系,医生没有保守这一隐私的义务。如果医生向其他人透露了这一信息,不违反德国《刑法》第203条的规定。因为这里法益主体能够保护自己的秘密,具有自我保护的可能性,却放弃了对自己秘密的保护。德国《刑法》第203条保护的不是法益主体在非紧急状况下泄露的信息,而是保护那些有价值的、如果不告诉他人就无法实现巨大利益的秘密。只有那些在面对特定的信赖对象不得不吐露的秘密,秘密所有人才是需要保护的,所以说,那些听第三人泄漏秘密的人,也应当免除其保守该秘密的义务。而且,期待特定的利害关系人为自己保守秘密的意愿,也属于秘密概念的一部分。总之,在许乃曼看来,只有个人无法也没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的秘密,才受刑法保护,泄密行为才能犯罪化。*Schuenemann, Der strafrechtliche Schutz von Privatgeheimnissen, ZStW 90(1978), 34ff.显然,许乃曼通过对非法侵害他人秘密罪中的“秘密”进行了限缩解释,而限缩是通过评价被害人有无自我保护可能性来完成的。
在诈骗罪的问题上,许乃曼赞成和坚持阿梅隆的观点,认为“只有具体的怀疑才能阻却构成要件,这个具体怀疑正好使被害人的错误不能满足构成要件,并因此基于被害人教义学的诠释,适当限缩欺诈的可罚性”。此外,在许乃曼最新的于2015年发表的论文中,其专门讨论了神秘的、超自然的骗术。在他那愤青般的笔触下,德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充斥神秘主义的、集体痴呆症烙印其上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Schuenemann, Die Schwindel in der Dogmatik und die doppelte Weishei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Beulk, 2015, S. 543.从占星术到足球比赛预言再到超自然的精神治疗,存在着一个非常广泛的神秘主义的、超自然的市场。然而,在许乃曼看来,今天的人们已经过启蒙洗礼,其对于可能的超自然的神秘主义爱好或兴趣,刑法不需要再介入其中。那些信任神秘主义的、超自然的骗术的被害人,不应该得到刑法的保护。在构成要件层面的处理方式是,那些神秘主义的、超自然的陈述或情状并不属于作为欺诈行为对象的事实,因此,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欺诈行为的特征就没有得到满足。
被害人教义学的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它从最开始涉及的诈骗罪和侵害私人秘密罪出发,不断地向越来越多的构成要件扩展和蔓延。
例如,在性犯罪领域,德国《刑法》第177条第1款第3项规定了行为人利用被害人所处的一种无助的、无保护的(schutzlos)的状态。许乃曼认为,要比较理性地限缩这个构成要件,只有排除那些行为人只有一点点优势或者被害人只有一点点无助的情况才能办到。因为在那些情况下,可以期待被害人采取绝对能够采取的抵制行为,那么,行为人为了压制这种反抗,就必须使用明显符合构成要件的暴力手段。*同前注⑤,许乃曼文,载同前注⑤,许玉秀、陈志辉等编译书,第211-212页。又如,在财产犯罪领域,在德国刑法针对盗窃行为规定了不同程度的可罚性的问题上,许乃曼认为,这也反映了被害人教义学的思想。德国《刑法》第246条、第242条、第243条,规定了从侵占到普通盗窃到加重盗窃由轻到重的等级,其中的区别始终在于被害人保护自己的财产的程度不同。这种情况直至德国《刑法》第243条的规定出现时达到顶峰,因为行为人必须要侵入被害人受到特别周全保护的领域中,此时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力度是最强的。此外,德国《刑法》第242条规定了盗窃罪,在对“取走”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展开解释时所使用的“占有”的概念,德国多数意见主张要考虑社会意义的归属。对此,许乃曼认为,在考虑是否因为社会生活的类型、类型的必要性以及普遍性等因素以后,会导致要大为放松支配地位,并且因此无论如何还要留下一个所有人都要尊重的权利人的支配这些问题的时候,明显是在使用一个被害人教义学的标准。对于这一点,应当适用德国《刑法》第243条规定的通常情形,在那些情形中,刑法之所以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是因为被害人自己采取了特别的保护措施。*同前注⑤,许乃曼文,载同前注⑤,许玉秀、陈志辉等编译书,第214页。 类似的观点,即在从盗窃罪到抢劫罪之间体现出一个被害人需保护性逐渐升级的状况,布莱也在他的论文中明确表达过。Blei, Strafschutzbeduerfnis und Auslegung, FS Henkel, 1974, S. 122.
以专著形式将被害人教义学的理念纵深推广的,是哈赛默。他的著作深入阐释了被害人自我保护可能性及需保护性等被害人教义学的基本概念,并尝试将这些理论适用于包括诈骗罪在内的多个构成要件。哈赛默认为,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包括对称与非对称的两类。前者对法益实行全方面的防御,后者的规定体现出特殊的、具体的保护。在非对称的构成要件中,有一部分属于关系犯,例如诈骗罪,就要求行为人与法益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需要另一方的配合,才能完成犯罪。相反,不以这种互动关系为前提的,例如杀人罪,就是单方的干预犯。在哈赛默看来,被害人教义学的主要场域是在关系犯中。*Hassemer, Schutzbeduerftigkeit des Opfers und Strafrechtsdogmatik: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Auslegung des Irrtumsmerkmals in § 263 StGB, 1981, S.52ff.由此,他讨论了德国刑法中的计算机诈骗罪、信贷诈骗罪以及救助金诈骗等。
阿梅隆在1977年从诈骗罪着手启动被害人教义学研究之后,也将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构成要件。在他看来,被害人教义学的思想,至少可以适用于各种轻微犯罪领域。*Amelung, Kommentar zur Hillenkamp, GA 1984, S. 582f.例如,以被害人的心理影响为前提的犯罪,立法者对于被害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反抗有一个预期的设定。以强迫罪为例,既然要求达到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那么在被害人放弃反抗的情况下,就可以运用被害人教义学的观点限缩构成要件的解释。又如,涉及个人秘密的犯罪,包括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侵害言论秘密罪、泄露个人秘密罪等,这些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被害人首先自己要把所谓的秘密或者隐私当回事儿,此时受害的就是以自我保护为基础的人际信赖。相反,如果被害人自己都无所谓,不保护自己的隐私或秘密,那刑法就更没有保护的必要。
尽管涉及刑法分则中不同的构成要件,但是,在讨论问题的分析思路和结论上,上述这些学者文章相互呼应,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在评价行为人的行为不法时,他们都把被害人的自我保护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自我保护的可能性对于刑法是否保护被害人,进而是否惩罚行为人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发挥影响力的根据,被追溯到刑法的辅助性原则之上。这些思想,成为他们讨论分则问题的概念工具,构成了所谓“被害人教义学”的核心内容,使得它与其他从被害人角度切入的研究区别开来,这也是它引起众多争议甚至成为批判的靶心的原因之所在。
四、遭遇阻击:法理基础的质疑
被害人教义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是一直在努力把在刑法分则中发展起来的被害人自我保护的概念,与刑法总则层面的刑法辅助性原则或者说最后手段性原则链接起来。
作为一种解释准则,被害人教义学自我设定的功能,是将被害人不应当也不必要受到刑法保护的行为方式,排除在刑事可罚性范围之外。它的主张者们坚称,被害人教义学是从刑法辅助性原则推导而出的,或者说,是最后手段性原则的具体化。*Schuenemann, Das Verbrechensopfer in der Strafrechtspflege, 1982, S. 407.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法益主体也要承担自我保护的任务。相对于刑法保护而言,被害人的可期待的自我保护,就属于其他前置于刑法的手段。一个具有自我保护可能性也被期待去自我保护的被害人,却放弃了自我保护的措施,此时,他就丧失了应保护性与需保护性。与之相应,行为人的刑罚也欠缺刑事可罚性,由此,显示出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的实现。*Schuenemann, Zukunf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Faller, 1984, S. 357ff.于是,从分论研究出发的被害人教义学,按照许乃曼的表述,是要“在分则体系与总则体系之间架起桥梁”。*同前注⑤,许乃曼文,载同前注⑤,同许玉秀、陈志辉等编译书,第207页。
然而,这个理论雄心遭到了各种形式的阻击。也正是在与各种批评意见不知疲倦的论战中,许乃曼的观点成为在被害人教义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声音。
比较基础性的争议,首先来自于对刑法辅助性原则的不同理解。批评者认为,从辅助性思想中,并不能直接地引导出与其所支持的认识相违背的被害人教义学原则。刑法是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这仅仅是在说,在国家能够使用较轻微的手段解决社会冲突时,就不允许处以刑事惩罚,而不是意味着,在公民能够自我保护时,就必须放弃刑法保护。把辅助性原则扩展到公民的自我保护可能性上面,会与历史事实相悖。因为公民正是为了解除自我保护的责任,而将刑罚权赋予国家行使。*Roxin, Strafrecht AT, 2006, §14, Rn.20.在被害人的法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刑法不予保护,意味着一种刑事法网的回撤。因此,批评意见认为,被害人教义学所主张的刑事法网应当在被害人能够自我保护之处回撤的观点,是对刑法辅助性的误解。刑法的辅助性,是认定刑法作为最后手段,是与其他的公权力救济渠道相比较,而不是与公民自我保护的手段相比。*Hillenkamp, Vorsatztat und Opferverhalten, 1981, S.177ff.在希伦坎普看来,辅助性原则的正确指向,是用来反对那种极度压缩个人自由的国家主权行为,而不是用来反对释放个体力量的行为。*Hillenkamp, Der Einfluss des Opferverhaltens auf die dogmatische Beurteilung der Tat, 1983, S. 13f.国家之所以承担保护公民的义务,正是因为公民不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Hillenkamp, Der Einfluss des Opferverhaltens auf die dogmatische Beurteilung der Tat, 1983, S. 12f.在被害人法益受到损害的地方,恰恰说明不存在有效的自我保护,此时最需要国家的保护。
笔者认为,关于刑法辅助性原则的争议,实际上关联着一个法哲学层面的疑问,即公民订立社会契约,向国家交出部分权利,形成刑罚,这究竟是为了要减轻自我保护的负担而由国家来承担,还是由于个人的力量不足以自保因而才求助于国家?
在被害人教义学的批评者看来,答案是前者,“公民接受国家行使刑罚权,真是为了将自我保护的责任委托给刑法,从而能够更好发展自己的人格”。*Roxin, Strafrecht AT, 2006, §14, Rn.20.然而,在主张被害人教义学的学者看来,答案是后者。因为根据国家哲学和宪法学的一般理论,当社会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时,国家就不必介入;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的公民,当他可以自我保护自己的法益时,就是在社会层面有效地发挥作用,此时,并不需要国家通过刑法进行保护。相反,只有当他的力量不足以或者难以期待去自我保护时,国家的力量才有必要出场。“辅助性原则终究植根于社会契约论,人民只想在保护彼此自由的必要限度内放弃自由,这倒是早已由贝卡利亚几乎逐字地写在刑法上。最初市民本身也必须保留他对于法益的支配,并且当他的力量不是完全足够自保时,他才需要国家。”*同前注⑤,许乃曼文,载同前注⑤,许玉秀、陈志辉等编译书,第210页。因此,在被害人教义学的主张者看来,批评被害人教义学的学者才是误解了刑法辅助性原则。按照许乃曼的说法,这种基础原则与概念或历史上的问题无关,而是与所谓的实践理性相关。“反映在国家最后原则上面,就是在社会本身不愿也无法支配自己的自由时,才托付给国家。”*同前注⑤,许乃曼文,载同前注⑤,许玉秀、陈志辉等编译书,第211页。
由此可见,被害人教义学所理解的最后手段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与其他较为轻微和温和的国家手段相比,二是与法益主体能够且可期待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相比。当这两方面手段均不具备时,才应当将刑法作为最后手段予以启用。显然,传统刑法观念对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理解,是坚守在第一个层面,被害人教义学则想要开拓出第二个层面的内容。从被害人教义学的角度看来,可能且可期待的自我保护,是在刑法上相比较民法而言更为有效的选择。民法的强制机制是在事后才启动的,严格来说已经太晚,因为法益损害已经形成,相反,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却可以在法益损害发生之前就有效地避免这种损害。这样看来,最后手段性的双重含义,有助于加强法益的保障。
除了刑法辅助性原则和最后手段性原则之外,关于被害人教义学的另一个基础性争议,是这种思想在刑事政策的导向上是否正确。
批评的声音认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被害人教义学导向的后果是不可欲的。因为它将会取消对轻信人的刑法保护。这样一来,不信任、怀疑和谨小慎微的自我保护思想会成为社会共同生活的法则。由此导致的,是公民基于对法律的信赖而充分展开的自由,相反,那些想要非法干涉他人专属领域的人的行动自由,却得到了扩大。罗克辛认为,这在刑事政策上是不正确的。国家在利益衡量时,应当站在支持被害人一边而不是犯罪人一边。*Roxin, Strafrecht AT, 2006, §14, Rn.21.即使按照被害人教义学的说法,可以期待被害人在能够自我保护的时候去自我保护,这点要求并不过分,但是,在被害人不进行自我保护的时候,国家就置之不理,这种不作为是过分的。在刑事政策的导向上,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通过惩罚被害人来打击犯罪人的斗争”。*Ebert, Verbrechensbekaempfung durch Opferstrafung, JZ 1983, S. 633ff.进一步而言,批评者认为,被害人教义学对构成要件的限缩性解释,会导致一个面对犯罪不断退缩而暴力盛行的社会。因为随着国家对被害人保护的整体性收缩,被害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自我保护,于是,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出现一个以暴制暴、私力解决的“拳头法”社会。
针对不合理的刑事政策导向的批评,被害人教义学的回应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拳头法”的想象,只是出现在暴力犯罪的场合,但是,在这个领域,本来也不是被害人教义学深入展开的地方。仅仅是在那些涉及非暴力的强制性行为的问题时,被害人教义学的思想才会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资源。“在暴力犯罪领域中,目前没有任何人曾经主张过,由于被害人不进行自我保护而对构成要件进行限缩性解释。”*Schuenemann, Zukunf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Faller, 1984, S. 368f.; Schuenemann, Zur Stellung des Opfers im System der Strafrechtspflege, NStZ 1986, 440.因此,在被害人教义学的辩护者看来,这是批评者对于被害人教义学适用场域的误解或扭曲。既然被害人教义学并不适用于暴力犯罪,那所谓的退缩性保护和“拳头法”社会就不会出现。另一方面,被害人教义学的主张者声称,被害人教义学导致的限缩性解释,是应对刑法“肥大症”和“通货膨胀”的良药。许乃曼认为,刑法犯罪圈的不断扩大,导致实体法膨胀和司法效率的低下,而当前刑法教义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设定一个有意义的标准来解决“刑事可罚性的肥大症”,进而实现最后手段性原则。*Schuenemann, Zukunft der Viktimodogmatik, FS Faller, 1984, S. 368f.而被害人教义学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标准,在那些被害人欠缺需保护性的地方,也正好取消了行为人的需罚性,由此形成了对构成要件的限制性解释和国家刑罚权的克制性适用。
此外,在形成针对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双面激励这一点上,被害人教义学也能找到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因为如果损害是由被害人自我放弃保护造成的,那么他对于自己利益的否认,就不会再得到刑法的保护。换言之,如果法益主体不认真对待和积极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在出现法益损害的场合,也可能得不到国家的保护。由此一来,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反向激励的效果,激励每一个公民认真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法益,面对风险积极预防,采取可能的自我保护手段去回避危害结果的发生。
以上笔者只是简单地勾勒了被害人教义学的核心思想所遭受的争议。直至今日,这些批评与反批评也未能真正地达成和解。因为,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触及如何看待被害人,如何理解刑法的手段和任务,如何为刑法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准确定位等基础性问题。围绕着这样一些基础性观念的争论,注定难以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可以预见,由被害人教义学引发的观念冲突,还将长久地持续下去。
五、休养生息:论战之后的渗透与传播
尽管曾经遭受过猛烈的批评,也在各种争论无果后淡出了学界的聚焦范围,不过,在以许乃曼为代表的部分辩护者的持续论述下,被害人教义学的思想还是在德国刑法学界顽强地存活下来,逐渐从阐述性的专著和论战性的论文,走进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和注释书中,以被承认或被批判的形象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那本影响广泛的刑法教科书中,罗克辛赋予了被害人教义学一个值得专门讨论的章节地位。一方面,罗克辛承认,被害人教义学的观点不仅对于讨论分则中的诈骗罪、侵害个人秘密罪、伪造货币罪以及强制罪等构成要件时提供了符合目的论的解释方法,而且对于处理总论的构成要件理论和不法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也能够提供说服力资源。例如,在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风险以及挑唆防卫等问题上,被害人教义学还是可以说得比较清楚的。另一方面,罗克辛又认为,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基础,即因为具有自我保护可能性而排除刑法保护,特别是与刑法辅助性原则的链接这一点,则是难以被接受的。最后,罗克辛“和稀泥”,表示被害人教义学不能作为一般性和绝对性的原则,但是可以提供一种角度,使得由此在各种特定利益的权衡中综合性地考虑刑法的保护范围。
在2006年的第四版教科书中,罗克辛在保留先前各种批评的基础上,最后增加了一段(相对于1997年的第三版),算是比之前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承认许乃曼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地为被害人教义学辩护和论战的不易。然而,针对许乃曼表示和罗克辛之间没有本质区别的说法,罗克辛灵活地回应,他认可被害人教义学是一种解释准则,针对构成要件进行目的限缩的解释,将那些被害人不具有应保护性也没有需保护性的情形排除出可罚性的范围。简言之,“是一个关于个别构成要件的解释问题”。*Roxin, Strafrecht AT, 2006, §14, Rn.25.按照罗克辛的这种表述,他把自己对于“被害人教义学”的支持划定在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他仅仅是赞成在考虑被害人的应保护性与需保护性的情况下去解释构成要件,但是,在最后这段总结性的表态中,罗克辛完全没有提及对于所谓“被害人教义学”至关重要的核心论点即自我保护可能性与最后手段性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罗克辛的立场是清楚的:他仅仅是同意在构成要件的目的性限缩中考虑被害人因素这个解释方向意义上的“被害人教义学”而已,但是对于被阿梅隆、哈塞默、许乃曼等人所主张的“被害人教义学”,他根本不像许乃曼所说的本质上观点相近,而几乎是完全回避了。
在德国最权威的刑法注释书之一,由舍恩克和施罗德主编的注释书中,在讨论法益概念的部分,艾希尔(Eisele)提到了被害人教义学的原则,将其定位在一种选择性概念,功能在于对于法益保护原则的“非决定性的调节”。*Eisele, in: Schönke/Schröder, Kommentar StGB, 2014, vor §13, Rn.10b.对被害人教义学更具体的展开出现在该注释书的不法论部分。被害人教义学被承认为一种限制构成要件解释的原则。“如果被害人有可能并且被期待在损害出现之前,自己采取保护措施去避免其发生,被害人就不具有应保护性和需保护性,那么就可以在构成要件解释允许的范围之内消除可罚性。……这种被害人教义学,并不是重新制造一个独立的修正的构成要件,……是对解释空间的一种限制,是一种一般性的调节性原则。”*Eisele, in: Schönke/Schröder, Kommentar StGB,, StGB Kommentar, 2014, vor §13, Rn.70b.应当说,“调节性原则而非一般性的推演前提”这个理论定位对被害人教义学而言,已经是得来不易了。而且,这个评价离被害人教义学主张者自己的描述,也相去不远。
此外,在其他注释书中,被害人教义学的观点也开始在刑法总则或刑法分则部分出现,篇幅上或多或少,态度上或赞成或批评。作为莱比锡注释书的作者之一,许乃曼自然是在莱比锡注释书中不遗余力地鼓吹被害人教义学,此处不再赘述。在另一部重要的注释书(慕尼黑刑法注释书)中,弗罗因德(Freund)明确表达了对被害人教义学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被害人教义学的辩护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想要作为一种特定的构成要件的限制准则的观点,即“损害可能性的形成单独地以被害人是否有自我保护可行性为基础,因此缺少了国家的特别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是不可接受的。弗罗因德认为这首先是源于对必要性原则的误解。作为比例原则的要素之一,刑法上的必要性原则意味着,“当国家有数个同样适合的手段去达到目标时,应当使用其中最温和的手段。至于说公民个人是否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在所不问”。*Freund, in: MK StGB, 2017,vor § 13, Rn. 426.相反,也是在慕尼黑注释书中,黑芬德尔(Hefendehl)则对被害人教义学表达了肯定的态度。他从诈骗罪作为一种被害人共同负责的犯罪的角度,评介了被害人教义学的观点。“当法益主体明明有行为选择可能性,却在明知的情况下提升了危险强度,此时,就有必要对构成要件做出限缩性解释。此时,不存在歧视那些有特殊保护需求者的问题,而是把那些能够独立负责的有意识进行风险决定的法益主体,从刑法的适用范围中排除出去。因此,进一步地出现了这样的建议,即那些轻信或者有重大过失的被害人,不再受到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保护。”*Hefendehl, in: MK StGB, 2014, § 263, Rn. 28.从黑芬德尔的论述来看,尽管他主要还是从他所说的支配原则出发,认为被害人教义学不过就是支配原则的具体化表现形式而已,但是,在基本观念的层面上,他还是站在了被害人教义学的这一方。在黑芬德尔看来,关于被害人教义学会违背社会契约论和不当地解脱国家保护功能的担忧,是不能自我证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教义学在德国学界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核心刑法的领域,例如,在最新的著作权法的注释书中,斯滕伯格-里本(Sternberg-Lieben)在介绍了被害人教义学的论点(在有可能且可期待自我保护的情况下,缺乏需保护性与应保护性)之后,将其作为讨论下列情形的基础:著作权的权利人长期对某些侵权活动不提出诉讼请求,这使得侵权人信任权利人将继续容忍他的相应行为,从这种容忍中可以推导出一个合理的(隐含的)同意。*Sternberg-Lieben, in: BeckOK Urheberrecht, 2017, § 106.
近年来,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也漂洋过海,传入了中国学界。在论文方面,笔者于2008年在《法学》上发表的《从华南虎照案看诈骗罪中的受害者责任》一文,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正式地使用“被害人教义学”的名称并运用该理论讨论诈骗罪的个案问题。这篇论文简要地介绍了德国刑法学界从被害人在量刑阶段发挥作用到在不法判断中发挥作用的观念转变和理论争议。特别是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限缩性解释中,对于有具体怀疑的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以及简单、拙劣的骗术是否构成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这两个被害人教义学的代表性问题,此文分别介绍了阿梅隆和瑙克这两位德国学者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从两个方面用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分析了当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华南虎照案。作为结论,笔者在该文中认为:“如果能够证明受骗者已经对照片的真假产生怀疑,但是最终还是舍弃本可以充分使用的自我保护手段,而基于投机心理贸然投身风险,从而遭受损失的,国家就没有必要再大费周折对其保护了。这种投机的心理不宜再被看做是‘陷入错误’。”*一方面,从欺诈行为的要素来看,基于当时社会上对虎照真假的讨论之广泛与对抗之激烈,很难将周正龙的行为评价为一种对普通人而言是“特别简单、拙劣、易于识破”的骗术,也不能由此来否定本案中存在欺诈行为。另一方面,从作为被害人的陕西省林业厅官员的情况来看,承认虎照为真又会为其带来获批国家自然保护区资源的巨大利益。在客观上完全具备严格审查的时间和条件下的情况下并没有仔细审查。车浩:《从华南虎照案看诈骗罪中的受害者责任》,《法学》2008年第9期。
尽管笔者最早在学术论文中引入并运用了德国学者表述的被害人教义学理论,但是,现在看来,当时笔者还没有对这种理论本身进行全面的审视和分析,而仅仅是作为一种舶来品引入到国内,然后将其运用于国内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解决。简言之,对于德国版的被害人教义学,笔者当时的态度是“拿来主义”,主要是引介并应用到个案中,但对理论本身的展开和批判都不够充分。一年之后,缑泽昆在《清华法学》上发表的《诈骗罪中被害人的怀疑与错误》一文,对被害人教义学在诈骗罪中的理论空间,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此文主要是引用了许乃曼的理论资源,为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优势辩护。*缑泽昆:《诈骗罪中被害人的怀疑与错误》,《清华法学》2009年第5期。如果说笔者之前的论文是直接将被害人教义学应用于国内个案分析,那么,缑泽昆的论文则是针对理论本身,更加详细和全面地介绍德国学者特别是许乃曼眼中的被害人教义学,增进了国内学界对于被害人教义学的了解。然而,这篇论文与之后的很多一样,基本上对被害人教义学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也同样缺乏足够的反思。此后,国内学界中又有多篇关于被害人教义学的学术论文陆续面世。于小川的《被害人对于欺骗行为不法的作用》一文,明确指出“被害人的谨慎义务落实在被害人教义学原理上,即为对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可能性和需保护性的评价和判断。”*于小川:《被害人对于欺骗行为不法的作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5期。黎宏和刘军强在《被害人怀疑对诈骗罪认定影响研究》一文中,仔细探讨了被害人教义学在诈骗罪认定中的作用。他们在该文中认为,当根据被害人有具体怀疑而限缩诈骗罪成立范围的基础上,再根据谨慎注意义务的有无,将诈骗发生领域划分为无需谨慎注意义务的一般生活领域与应当具有谨慎注意义务的市场、投资、投机和违法领域。“对前者实行无差别的、严格的保护,对后者适用被害人自我答责,从而在限缩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诈骗罪的处罚范围。”*黎宏、刘军强:《被害人怀疑对诈骗罪认定影响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王骏在《论被害人的自陷风险——以诈骗罪为中心》一文中认为,对于被害人自陷风险时行为人是否需要对结果负责的问题,被害人教义学不能给予妥适的解答。*王骏:《论害人的自陷风险——以诈骗罪为中心》,《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此文从几个方面对被害人教义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在文献翻译方面,许乃曼的一篇关于被害人角色的论文,最早于2001年被王秀梅和杜澎翻译发表在《中国刑事法杂志》上。*[德]许乃曼:《刑事制度中的被害人角色研究》,王秀梅、杜澎译,《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此外,罗克辛的刑法教科书(1997年第三版)由王世洲翻译,于2005年在我国出版,该书中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了所谓“被害人信条学”对于实质不法的影响。真正全面地引介德国学者的被害人教义学观点的,是2011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申柳华博士的《德国被害人信条学研究》。这本出版于2011年的博士论文,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德国被害人教义学理论研究最为深入和广泛的一本专著。这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德国被害人教义学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容,并对围绕这些理论产生的广泛争议,进行了批评和反批评的理性思考。不过,申柳华基本站在了重述许乃曼观点的立场上。针对一些关于被害人教义学的批评,用许乃曼的观点回应之后,就很少有申柳华本人的反思或进一步的展开了。此外,这本著作也存在着选择性论述甚至夸大己方阵营影响力的疑问。有些德国学者虽然是从被害人角度展开的研究,或者讨论被害人行为对行为人不法的影响,但是其核心思路与许乃曼等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例如,米特胥关于正当化领域中的被害人行为的著作,就是以对许乃曼等人的“被害人教义学”的批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Mitsch, Rechtfertigung und Opferverhalten, 2004.但是,申柳华的著作也把他归入到所谓“被害人教义学”的名目之下,用来说明这一理论的研究规模的扩大,*参见申柳华:《德国被害人信条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这就有误导之嫌了。不过,瑕不掩瑜,该书仍然是一本难得的学术前沿之作,对于德国版的被害人教义学思想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六、结语:被害人教义学的重新出发
本文的主题,是被害人教义学在德国的源流和发展。这就意味着,在笔者看来,目前在德国被部分学者主张的所谓“被害人教义学”,仅仅是被害人教义学发展的一个支流,或者说形态之一。部分德国学者将“被害人教义学”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个概念在德国的发展。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疆域,应当得到更加宽广的定义。
笔者认为,从被害人视角切入刑法问题,将传统的行为人单维视角的理解模式,改变为“行为人-被害人”双维视角的理解模式,才是“被害人教义学”的概念应当承载的使命和理论目标。由德国学者许乃曼等人主张的所谓“被害人教义学”,显示出追求这一目标的雄心,但是,这种从被害人自我保护可能性以及最后手段性原则出发的理论,其法理基础、所遭遇的各种批评以及发展现状足以说明,它无法单独地实现这一任务。它的确是从被害人角度理解刑法的一个重要进路,但远远不是全部。很多从被害人角度对刑法问题展开过深入研究的德国学者,包括阿茨特、米特胥、库尔特等等,他们的研究与许乃曼、哈赛默等人的主张完全不同,甚至对后者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为了与后者相区别,他们也只能与已经和后者捆绑在一起的“被害人教义学”划清界限。被害人教义学在德国遇到的这种”注册商标“式的瓶颈,是一种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的悲哀。
然而,对具有理论后发优势的中国刑法学界来说,这些人为设定的限制都不存在。笔者在2013年的《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一文中,对被害人教义学做出了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定义。德国学者主要在诈骗罪中主张的那种被害人教义学,与被害人自陷风险以及被害人同意,都属于一个以自我决定权为共同基础的、广义的被害人教义学的下位理论。“德国学者所发展的被害人教义学,其思考原点必然要追溯到自我决定权和自我答责的思想。……德国刑法学语境中的所谓‘被害人教义学’,与被害人同意中的自我决定权以及被害人自陷风险中的自我答责原则,在强调被害人的自由意志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三者之间在教义学理论模型上的差异,既是德国刑法理论精细化的产物,也是学者试图从新的视角去创设新的概念表述,进而树立自身学术个性和标签的结果,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教义学层面的差异而遮蔽或忽视了它们共通共享的思想基础。”*车浩:《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被害人教义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可能构建出更宽广的理论基础,挖掘出更丰富的可能性,也会给未来的刑法理论革新带来更深刻的影响。
(责任编辑:杜小丽)
DF61
A
1005-9512-(2017)10-0002-13
车浩,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