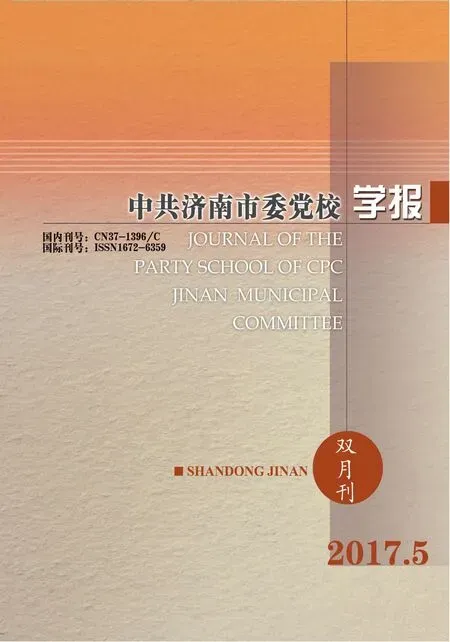“文化硬实力”场域下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之缘由
令小雄
“文化硬实力”场域下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之缘由
令小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基因,熔铸蕴含着民族前进的力量。文化正是坚守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根和魂所在。中华文明能够数千年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其内在的文化场域“硬实力”架构是值得崇仰审思的。从历史文化的视域而言,中华民族是最有底气讲“文化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与魂,中华文明五千年赓续不绝就是靠着它的光芒和力量。
中华文化;文明古国;文化自信;文化建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基因,熔铸蕴含着民族前进的力量,而“文化软实力”是表征国家综合实力的灵魂。文化作为软实力其实也有硬结构支撑,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可以称之为“文化硬实力”。把这个视域导入五千年文化场中,审思“文化自信”的根与魂,可以发掘这种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并对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未来导向。 “文化软实力”是从精神文明层面对应物质文明的“硬实力”,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热切预言,文化的根脉“正像活的种子一样,伸展它造福的树枝,开花、结果。”
一、地理环境塑造民族文化性格
地理环境在文化内质的衍生与发展变迁过程中呈现非常重要的作用。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硬件结构的“硬文化”状态决定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民族精神的产生与自然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其民族精神气质中投射“人文地理”的特质,二者互为体征。黑格尔强调:“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1]孟德斯鸠主张,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气质和性格,而民族气质性格决定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所以地理环境决定政治制度。这个逻辑推导过程的起点就是地理环境作为硬文化场对民族性格及其法治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地理环境通过它对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
(一)水域与文明的发源
人类的繁衍离不开水域的灌溉,水对文化繁衍及文明的滋养是不言而喻的。
河流与文化的发展脉息有着先天的关联。古老的世界四大文明体系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等。“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国家不过是河川流注的区域。”[2]古巴比伦主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间。尼罗河由南向北、倾泻而下,它源于乌干达,经苏丹、埃及注入地中海,成了埃及唯一的水源,很好地诠释了“古代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黄河是中华古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和发祥河。水成为国域的滋养源和文化的灌溉者。
(二)历史文化的地理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将地理环境视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初期,“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某一地理环境对成长于其中的那个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进而决定那个人类文明的类型及其发展进程。
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一直孕育在一个广阔的避风港中,东面临海、西北有广漠戈壁,西南则多横断山脉,东北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整个地理形势呈现“负陆面海”的架构,如章太炎所说,是一个“右高原,左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度。中国东南濒临的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这对于古代中国人绝对是难以超越的。在太平洋的东亚海域,中国大陆与朝鲜、日本以及琉球群岛隔海相望,形成一个不甚完整的内海,被人称其为“东方地中海”。这种半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以“隔绝机制”孕育并持续发展着一个统一、独立的文明体系。正是这种地理环境塑造了中华文明在起源上的本土性和独立性,易守难攻的保守性同时赋予到文化的内质,“中国似乎自发地和没有外助地发展了他们的文化”。这种地理结构给外侵者也设下了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当然也自我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历史学家汤因比强调气候等自然因素对文明产生的作用。五千年以来,中国的生态处于地球上适合人类生存的良好区间,中国人口居世界之首位表明怡人宜居、生生繁衍的特点。长江、黄河是东西向的流域,比其他国家南北向的河流更有利于民族生存。每逢灾荒,虽有流民潮出现,但国家地大物博就回旋余地大,灾民可向非灾区转移,也不致因地域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中华文明在“东方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中及世界范围内长期领先,属于“高势能文化”,如大唐盛世,万国来朝,文明远播,享誉世界。
中国在东亚,处于欧亚大陆相对封闭的位置,没有受到西亚或欧洲的大侵扰,华夏文明所承载的这种人文地理的保守格局,促其文化传承自成一体,易守难攻;加之地广物博利于文化的物质支撑,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整合,其兼容并包、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态势和文明风貌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历史环境”与“地理环境”是相对接内合的,从初级社会也可以进入较高级社会形态,“历史环境”理论是“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依据。
二、农耕文明奠定的“层序社会”
农耕文明必然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接起来。据研究表明,我国稻作农业文化可推进到1万年前。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耕民族有向心力、亲和力、群体观念,建立在宗族基础上的群体观念较强,以相对静止的状态保存和发展文化,而儒家学说在凝聚农耕民族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农耕文明的这种文化早熟现象内生了社会结构上温和的、保守的层序社会。守土有责和故土情结是农耕文明奠定的社会心理结构,这建立在祖先崇拜及对家庭宗族重视的深层文化意识中。农耕民族必然形成宗法文化,这种社会心理模式体现惜土守土情结的层序稳态社会结构中,保守性强,社会的整体流动性低。出乡“入仕”是一种上升渠道,社会的向上流动始终没有脱离底层关怀的视阈,出则为仕,退则为绅,形成良性循环系统。士农工商是社会层序的政治文化界定,带有身份政治考量。背井离乡被看成是迫于无奈的生计选择,到一定年龄就讲求叶落归根。
长期的共同生活,就形成宗族的纽带,非常牢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民族性格勤劳朴实又稳定保守。这些因素就促成我们民族超强的稳定性,其他外部势力很难打破这种稳定。即使一段历史界域中短期打破了,很快又会得到恢复,民族传承的稳定也就保持了文化上的黏合力、凝聚力。尽管历史大势演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政权迭换,但中华文化状态的主体功能延续不断。
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外向型文化,属于动态文化,而中华文明则是一种建立在自足基础上的内向型文化,属于“静态文化”。这种实践取向深刻地影响到文化的内核,以至于成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标志之一。而譬如在商业竞争中,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希腊人很早就学会了用合同或契约的形式来约束和规范双方的行为,以保护商业信用。在这一过程中,希腊人也形成了组织、联合的观念和法的精神。而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契约是以道德担保的,这个传统延续到现代生活,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借钱一般不会在书面上体现出合约来,这种契约精神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在这样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独特农耕文化以追求稳定、和平、和谐为目标价值取向,强调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安土重迁,抱常守静,重视反身向内审视、向后看,倡导实践上的节俭勤劳、仁爱忠信等精神,传承持守克勤克俭,隐忍平和,重视教育,讲求信用,看重血缘,尊敬权威的文化诉求。
三、政治结构中的文化特质
传统农耕文明的经济结构中男耕女织是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主体模式,这种自足自给的产业形式建立在宗族层序的一个范式中,这个超稳定结构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对接中,包含祖先崇拜的血缘宗族礼序、乡贤文化与乡村自治文明的接轨。
(一)乡贤文化与“双轨政治”
宗族血缘传承的祖先崇拜文化外放推移为差序格局,建构为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其抗风险能力强大,这塑定了其社会模式的超稳定结构。这种文明传承就是以孝文化价值治理为根本导向的,于家为孝,于国尽忠,政治结构的双轨制对社会的治理与疏导功能在正面上发挥着非常强劲的价值引导力。“皇权不下县”与乡贤乡绅形成的乡村自治模式千百年来孕育了深厚的乡贤文化。这种政治治理模式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力是深远的。一代代乡贤达人行为示范,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乡贤是传统乡土中国最基层的管事,集政治文化于一体的担当者,是担负乡约的领袖者。“他们是村庄的道德典范,是村庄的精神领袖,并因此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护者。”[3]出则为仕,退则为绅。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双轨制对文明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今天,我们提倡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丰富当下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郡县治天下安”和乡村自治的政治文化生态的对接,这种治理的双轨制对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的传承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二)“选举社会”
选举制度是社会政治文明的集中表征。“选举社会”,亦即从一种封闭的等级制社会转变为一种流动的等级制社会。中国两千多年来从荐选(察举制的“他荐”)到考选(“科举”制度)的演进,构建了从“世袭社会”到“选举社会”,体现了一种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平等的“单渠道流动”发展。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始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的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科举制塑造的文官制度对政治文明和文化传承的促进作用是深远的,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政治先进性的引领作用。“士大夫多出草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及其更远的察举制度在制度层面保证了社会人才供给流动性。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社会的政治结构呈现一个从草根阶层到精英阶层开放向上流动的状态,这对社会层序架构的改善疏通及其文化的弘展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得到激发延续。
(三)士文化传承
“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及历史进程。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知识分子阶层,是自战国以后逐渐取代没落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领导的新中心”。[4]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士”的精神性存在确实是历史发展中的火光和丰碑。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礼记·儒行》)。孔子的“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敬其在己”(《荀子天论》),曾参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钱先生认为,“由士之负担人文理想,由士之共同精神,即可见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完整性的人格。能十足表现中国文化传统的完整性,中国人即称之曰士”(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士的完整人格与承载文化的完整性有效对接起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与抱负,到晚明顾炎武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铁肩担道义,士的担当精神与社会价值或道统的承传。宋儒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重道轻仕”、“宁退不仕”的政治态度与观念所直接显示的乃是“他们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场”。钱先生所谓“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常传于天地间”。[5]修己以敬,君子人格与圣贤气象,内向超越是“士文化”的特征,也映射着中国文化的内化特质。
(四)政教分离的文化取向
政权与宗教的距离保证了政治文明的连续性,改朝换代是在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循环,并没有烙印上宗教政权的痕迹。中国版图整体上是统一的国度,政治文化、政权的统一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政治和宗教保持一定距离也是一种文化优势,政教合一是很多西方政权的运行模式,政教合一,容易因为宗教的冲突而发动战争,撕裂文明,摧毁文化,中国历史上没有因为宗教冲突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这一点值得反思。宗教的冲突,是深层次的,难以弥合的灵魂断裂,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却是儒释道融合,百家争鸣,竞相开放。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以文化“硬实力”积淀传承,历久弥新、淬炼前行,成为世界文明长河的璀璨之光。
[1]黑格尔(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2.
[2]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134.
[3]赵法生.再造乡贤群体重建乡土文明[N].北京:光明日报,2014-08-11(2).
[4]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1.
[5]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82.
(责任编辑 胡爱敏)
令小雄,中共定西市委党校讲师,硕士(邮政编码 743000)
G122
A
1672-6359(2017)05-00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