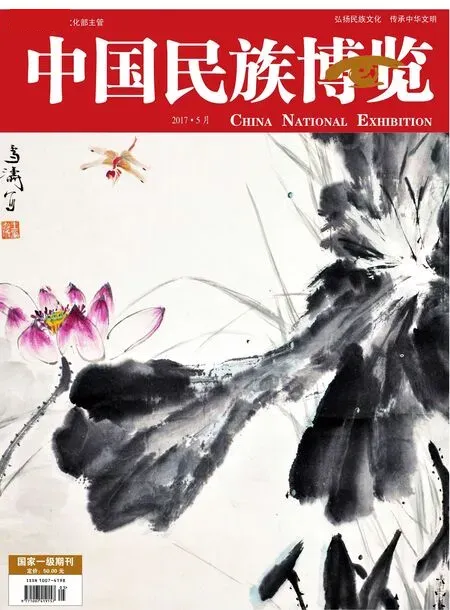环珠江口海洋文明中的树皮布文化浅释
冯游游
(贵州医科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环珠江口海洋文明中的树皮布文化浅释
冯游游
(贵州医科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树皮布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明之一部分,记载和传承史前人类衣食住行之“衣”,透露着人类文明的演变信息。这种制衣文化在今天的保存更说明了它的生命力与实用性。本文以环珠江口为切入点,探讨环珠江口地区海洋文明孕育之下的史前树皮布文化,以期对史前时期南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树皮布文化;环珠江口;海洋文明
引言
史前环珠江口地区的海洋文明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树皮布文化,这不仅是地域差别引起的文化差异,更是中国历史“我者与他者”角色的不断转化和儒家文化包容性的显现,也是史前时代起中华文明的起源就呈“满天星斗”状发展模式的多元文化特征。而“岭南制布文化,是以土著南越‘蛮夷’制布文化为根基,博采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制布文化精华, 经过漫长的融会、整合、创新、升华而形成的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体系。”据科学碳十四年代推测,出土“石拍”公元前三千年至七千年不等,其中“深圳咸头岭遗址”出土的“石拍”约公元前七千年,为考古发现之最早,这不仅说明“树皮布文化”作为中国史前文明之一部分,记载和传承史前人类衣食住行之“衣”,透露着人类文明的演变信息,这种制衣文化在今天的保存更说明了它的生命力与实用性。201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海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艺技”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使环珠江口的树皮布文化备受关注。树皮布文化散布于整个南中国、东南亚、两河流域乃至中美洲地区,并与两河流域的树皮纸与中美洲的无纺织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石拍与树皮布
经考古研究发现,石拍作为树皮布制作的主要工具,隐含着史前树皮布制作的信息,虽然史前树皮布没有在今天的考古中发现,但大量出土石拍证明了树皮布作为史前文明之一部分,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且这种技艺今天仍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今天的云南、海南等地方都还有树皮布的制作,这与出土之石拍实物不谋而合,在考古材料、传世文献与田野调查“三重证据”的力证之下,树皮布文化研究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石拍文化的研究中,《衣服的起源与树皮衣展览图录》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石拍与树皮衣的相关问题,对石拍与树皮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野。“石拍作为制作树皮布的工具,虽然是小小的出土文物,但却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南中国考古发掘中,“云南大墩子”“广西革新桥”“广东丰沙坑”“香港屯门涌浪”等考古遗址中都发掘了大量的石拍,在经过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之后,发现石拍与树皮布制作有很紧密的联系。
“树皮布是一种由拍打技术制作成的布料, 与纺织布的经纬织造技术系统完全不同。”而在树皮布的选材上是有要求的,一般选材于“构树”、榕树、见血封侯、楮树等,这些都是生活在热带或者靠近热带的亚热带地区,除见血封喉外都可入药,这可以说明在经过一系列加工之后制作成衣布是可以的,它不会伤害人的身体,而见血封喉在经过加工之后对人体也没有伤害。下面简单介绍树皮布的制作过程,以期更为清晰地说明树皮布文化传承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选料
根据植物生长的特点,一般在夏秋之际砍取制作树皮布的原料,这样做的原因是树木水分充足,易于脱落,而且这些乔木都生长在热带或靠近热带的区域,这体现了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民的地域概念,也符合史前生产力不发达的生产水平。
(二)浸泡
选取原料之后,一般放在流动的水里面浸泡,而且要经常翻滚浸泡,这样才能均匀,这种方式有利于驱散乔木中不利于人身体的液体,也为剥削树皮做好准备。
(三)剥皮
剥取树皮在刀或利器的帮助下完成的,需要的是“内层皮”,而不是外面粗糙的那一层树皮,在这一过程中要用木头或其他东西拍打,而且要不断地浇水,这样既有利于树皮脱落,又有利于将树汁排除。在有经验者手中,对什么时候可以脱树皮和拍打的程度把握得很好。
(四)拍打
剥下树皮之后就要将之不断拍打,这时候跟现在考古发掘的“石拍”有了联系,石拍分为“棍棒型”与“复合型”,这只是根据石拍的外形来分的,重要的是石拍上的凹凸不平“槽”,它具有着重要的作用,槽面与槽沟的高低不平正是发挥作用的关键,因为凹凸不平的槽面才能使被拍打物(树皮)受力不均,一方面可以将树皮本身内部的纤维组织折损,这样有利于树皮向“树皮布”转换,且让人使用起来比较“活软”;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往上面洒水不易将树皮拍坏和有利于将树汁排除,就如见血封侯虽然适合制树皮布,却是有毒的,这一步非常关键。
(五)“煮”和“晾晒”
在制好树皮布之后,要进行的是“煮”(有利于破坏树皮本身的组织结构)和“晾晒”,这一步也非常重要,这样有利于杀菌和消毒,亦有益于使树皮布更加柔软。在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加工之后,最后的工作就是将这样一块一块的树皮布缝制为树皮衣或者其他的日常用品,这一技艺一直从史前延续到现在,今天虽然只有极少数的地方保留这种祖先的技艺,但它却见证了一种文明的延续和祖先的智慧,海南省黎族现在保存的制作树皮衣的文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云南省的诺基族、佤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树皮布制作方式,这也证明了树皮布的现实意义。
以上只是树皮布制作的一种工序,或许不同的地方会有所差别,但总体思路是这样的。总而言之,根据对出土石拍的研究和今天民族学的调查,从现在还保留的树皮布制作工序中窥见史前制作树皮布(树皮衣)十之一二,这不仅有利于研究现在少数民族文化,更从现实的角度与考古材料互证,从而说明南中国文明也是中国文化魅力的一部分。
二、结语
“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从以兽皮为衣到以树皮(树叶)为衣再到以丝绸为衣见证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树皮衣制作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而将考古出土的“石拍”材料与现在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结合,更进一步挖掘这种存在身边的文明,“树皮布文化历史从考古学角度而言,必须首要解决的是,如何论证出土遗物、遗迹与树皮布关系的难题”。随着对树皮文化的研究和对考古材料相互证明,邓聪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了树皮布的起源乃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尔后传播至台湾以及东南亚,因为“环珠江口一带大湾文化里所发现为数不少的树皮布石拍,是中国大陆目前所知唯一年代最早,且科学性最强的与树皮布技术有关的资料”。当然,也有其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如台湾学者凌纯声先生就认为树皮布应该起源于长江流域。尽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观点,但树皮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无可争议的,苏秉琦先生的中华文化生长“三模式”(原生型、续生型、次生型)发展模式对于树皮布的研究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无纺树皮布起源、发展的中心在华南、东南亚至太平洋群岛,是百越先民和南岛语族共同的文化遗产”。这种树皮布的制作工艺与中国乃至两河流域的造纸工艺都有紧密的关系,因为“中国传统的各类造纸工艺无不如此, 其工艺流程均大同小异, 主要是原材料的差异而已。它们都脱胎于树皮布工艺”。可见,海洋文明孕育出的树皮布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就在现实的生活之中,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将这一文化保留至今,是有它的意义的,传承与运用这种文化不仅是历史的要求,更是现实保护与运用的需要,将之发扬光大,不仅作为“树皮布文化”传递着史前文明的信息,对中华文化也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据Tolstoy统计,迄今在中美洲发现最早的树皮布石拍,出土于玛雅文化的范围,其中尤以西南中美洲太平洋沿岸平原Guatemala与El Salvador的地区,年代约在距今2500年前。在此以后,树皮布文化徐徐由西而东向中美洲全局扩散”。这证明了对环珠江口树皮布文化的研究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
[1]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向安强.树皮布•蕉布•竹布:古代岭南土著社会“蛮夷”制布文化考述——从环珠江口先秦“树皮布文化”说起[J].农业考古,2010(1).
[4]邓聪.古代香港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浅释.[J].东南文化,1999(1).
[5]周伟民.树皮布石拍的民族学解读[J].寻根,2004(2).
[6]王翠娥.略谈海南黎族树皮布制作技术[J].南方文物,2006(1).
[7]刘玉璟.树皮服饰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学文论文,2006.
[8]邓聪(编).衣服的起源——树皮衣[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11.
[9]吴春明.“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证[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0]刘志一.纸的发明与革新(续二)[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1(1).
[11]邓聪.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J].东南文化,2000(11).
K232
A
冯游游(1988-),女,贵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比较与公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