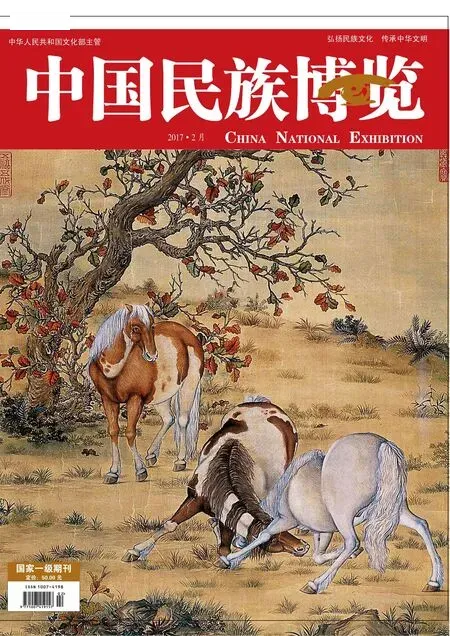贵州西部苗族烧灵仪式音乐中的族群认同
——以兴仁县大山镇尔期村坪子上组为个案
罗义翔 常艳丽
(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贵州西部苗族烧灵仪式音乐中的族群认同
——以兴仁县大山镇尔期村坪子上组为个案
罗义翔 常艳丽
(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族群认同是一种多维立体的理论,强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中去探索族群文化内涵。兴仁县大山镇尔期村 坪子上组作为当地少有的苗族村组,尽管与周边民族(主要以汉族为主)文化交融过程中接纳了部分外来文化元素,但在族群内部仍有“倔强”的一面。而烧灵仪式音乐则是该族群所要强调的文化元素之一。本文以族群认同视角为主线,旨在探索出烧灵仪式音乐、社会、文化认同的内涵。
苗族烧灵仪式音乐;音乐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
“大山乡东邻营上乡,南接公德乡,东南与启白乡相邻,西抵晴隆县栗木乡,北界田湾乡。面积41.36平方公里,人口约11980人。设……9个村委会,辖86个村民组,59个自然村。”[1]尔期村下辖23个村民组933户4121人。该村主要民族成份有汉族、苗族及布依族,而坪子上组则是其少有的一个苗族村组,约52户。
苗族烧灵仪式是当地苗族丧葬习俗的一部分,通常被视为最后的仪式。仪式中的音乐包含有古歌、芦笙乐曲等,是当地人与亡灵沟通的主要方式,也是整个仪式活动的核心。本文以族群认同视角为主线,旨在探索出烧灵仪式音乐、社会、文化认同的内涵。
一、族群认同理论概述及烧灵仪式过程
(一)族群认同理论概述
族群认同理论在学界“大致可分为‘原生论’和‘建构论’两种。”[2]其中,“原生论强调从族群的客观属性出发来定义族群,认为族群的文化特征在族群认同的塑造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建构论认为,族群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的主观特质,无法单独经由族群文化特征导出,它一定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它的边界不与地理文化边界必然重叠,而常与社会政治的利益形态相结合。”[2]总之,两个理论之间实际是围绕着历时性与共时性来开展。本文唯有将两者相互结合,才能揭开当地苗族烧灵仪式音乐文化的内在特质。
(二)烧灵仪式过程
当地烧灵仪式主要有三个过程:请灵—祭灵—送灵。其中,请灵是当地人以芦笙吹奏为主,通过音乐“召唤”亡灵归位;祭灵是当地人在祭祀物品时,须木鼓与芦笙的配合,把交代的“话”带给亡灵;送灵也是同样通过芦笙音乐来给亡灵交流、引路。三个环节当中,还有诸多仪式细节也涉及到音乐,本文将不一一列举。总之,烧灵仪式音乐贯穿于整个仪式活动,是其主要的一部分。
二、烧灵仪式音乐认同
“音乐认同,是指人类以音乐符号形式表达自己独特的创造力,将人的个体音乐思想和行为与其他个体或社会群体进行交流和融合,也是主体进行个人阐释与实现社会功能— —个体对于宗族、族群、民族,甚至国家的归属、凝聚和认同的过程。”[3]换言之,烧灵仪式音乐作为当地苗族文化系统中的一份子,是其内在的一种反映,也是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界限区分的标准之一。
首先,当地苗族强调对音乐的认同是基于历史的缘故。当地苗族与周边民族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文化冲突”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地苗族特别强调自我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差异。
其次,近些年随着全球化快速发展,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当地苗族不论精神文化或物质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当地丧葬文化体系由于其信仰空间的“稳固”仍得以完整保留。烧灵仪式作为当地丧葬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固然被强调。那么,烧灵仪式音乐在整个过程中作为与祖先沟通的主要方式,自然在当地苗族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当地苗族社会中,对于烧灵仪式音乐的认同实际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判断与周边民族之间存在差异的辨别方式之一。
三、烧灵仪式音乐中的社会与文化认同
(一)烧灵仪式音乐中的社会认同
1.烧灵仪式音乐中社会地位的认同
烧灵仪式音乐所体现的社会地位认同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音乐的难度,使得能够掌握它的人被族群内部视为较有“能力”者。烧灵仪式音乐本身的复杂,使得能够驾驭的人并不多。以芦笙乐为例,根据笔者实地调查所知,全组能够完全掌握的不超过10人。另一方面,烧灵仪式一旦没有人能够掌握,则无法与祖先进行沟通。
2.烧灵仪式音乐中社会地位的提升
仪式的神圣则赋予了音乐的神圣性,而音乐的神圣性则给予操作的人一定的权威性。因此,能够掌握仪式音乐的人在仪式过程中享受与常人不同的待遇。如:仪式过程中他们只需要吹芦笙即可,不用参与其他劳动;仪式举办的主人需要拿出额外的肉来感谢专门唱古歌的人等。当然,他们在仪式过程中享受的地位并不会因为仪式的消失而消失,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也有所体现,并逐步成为族群内部具有一定威望的群体。如:当地遇到纠纷或议事皆会尊重这类群体的意见或建议。总之,烧灵仪式音乐不但在仪式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还成为族群内部社会地位提升的条件之一。
(二)烧灵仪式音乐中的文化认同
“一个族群, 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加强集体记忆, 仪式的‘重演特征’对于塑造和维持族群的共同记忆和族群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4]仪式在当地历史过程中不断地上演,仪式音乐不断再现的实质是:族群内部不断地由加强集体记忆到实现自我文化巩固与认同的一个过程。首先,仪式音乐作为仪式当中核心的部分,在其历史族群内部是视为不可变也不能变的事象。换言之,烧灵仪式音乐的改变意味着其族群内部无法与祖先正常交流。因此,烧灵仪式音乐得以在族群内部不断地巩固,而这一巩固的过程就是其族群核心文化强化的过程。其次,当地人往往会借助仪式音乐在不断地述说着亡灵及族群的历史。而族群文化往往就是在这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得以强调。而在当地苗族社会,他们以烧灵仪式及仪式音乐作为区分我者与他者的标准之一。
四、结语
纵观整个仪式过程,实质就是当地通过音乐—社会—文化逐步实现自我认同的一个过程。由于音乐所具有的神圣,使得音乐行为在整个过程中被约束,而行为的约束是对族群观念的一种反映。由于观念得以巩固,使得族群社会也因此得以稳固发展,而社会的稳固发展既是当地族群自我认同的过程,也是其文化体系得以延续的基础。
[1]贵州省兴仁县编史修志委员会.兴仁县志[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2]李志农,廖惟春.“连续统”云南维西玛丽玛萨人的族群认同[J].民族研究,2013(3).
[3]黄灵智,周显宝.“音乐认同”:一种哲学人类学解读[J].学术界,2016(4).
[4]高源.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J].青海民族研究,2007,18(3).
J607
A
罗义翔(1990-),男,布依族,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常艳丽(1992-),女,汉族,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本文为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16yjsxm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