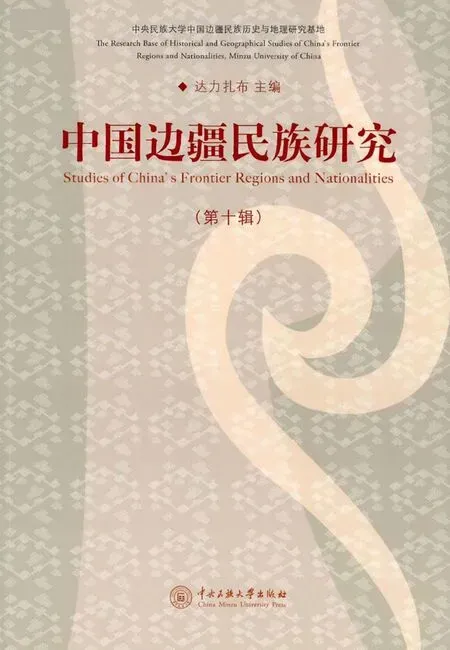清代迁入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的卫拉特诸部
[日]柳泽明著 吴 刚译
内容提要:18世纪,原属于准噶尔的一些卫拉特部落,被清朝从西蒙古和阿尔泰山迁到今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地区。清朝的主要目的是:第一,防止他们逃走或反叛;第二,救济贫穷的他们。迁移后,一些部落被安插在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成为今天中国该地区现有族群的基础,而另外一些部落则被编入八旗驻防或发配为奴,并很快融入周围的部落。
1.引言
2.每一部落的来源和迁移过程
2~1 第一阶段:1720—1722
2~2 第二阶段:1728—1733
2~3 第三阶段:1757—1758
3.迁移的几个侧面
3~1 清朝的目的和管理体系
3~2 安置后的困难
4.迁移的卫拉特诸部与现有民族的关系
1.引言
目前,今中国东北与呼伦贝尔①在本文中,我们在音译专有名词和历史术语上基本采用满语罗马字转写,而有时则采用其他语言,比如蒙语和汉语的拼写和音译。地区的人口来源,包括一些卫拉特部落的后裔,是清政府从西蒙古或阿尔泰山地区迁来的。他们的迁移主要集中于清朝与准噶尔汗国之间长期战争出现重大转折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720—1722年、1728—1733年和1757—1758年。1720—1722年,战争重新爆发后不久,清军深入到蒙古西部和阿尔泰山。1728—1733年,雍正帝决意出征准噶尔,但因准噶尔的反攻,使双方最后陷入了僵局。1757—1758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重建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这三个时期里,曾属于准噶尔的诸多部落进入了清朝的管辖范围,一些部落被迁到了遥远的今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地区。
从迁入的这些地区来看,仅有少数部落至今仍保留一定的民族特征,例如,对富裕县的柯尔克孜人、伊克明安蒙古人和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厄鲁特人深入的研究(桥本重雄1943,那顺乌力吉 1990,道尔吉 1990,吴元丰 2004,柳泽明 2005,胡振华 2006,敖乐奇 1987,波·少布、何日莫奇2001)。另一方面,在已经融入到其他民族和民族识别停止后,我们缺乏对这些部落的了解。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对这些卫拉特人的迁移过程和改编作了相当全面的考察,包括在今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地区的重新安置,但是她并没有详细指出迁到这些地区的所有部落(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2009)。
本文主要依据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方档案,首先论述每一部落的来源和迁移过程,然后探讨清朝迁移他们的目的、他们重新安置后的情况和他们与安置地现有族群之间的关系。
2.每一部落的来源和迁移过程
2~1.第一阶段:1720—1722
① 特楞古德
1720年8月(农历),康熙帝下令,把傅尔丹将军辖下的400多“厄鲁特人”集中起来迁到呼伦贝尔地区(MZZJB 11-08,HJYD 1-1720:206-217)。这是有关卫拉特人迁移到今呼伦贝尔和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记载。在诏书里,他们被称为“厄鲁特人”,但是后来考察证明,他们都是“特楞古德人”。1721年3月,他们到达黑龙江地区后,黑龙江将军陈泰为其提供了食物、牲畜及安家物品,然后把他们安插在从西面流入嫩江的诺敏河与其支流格尼河交汇处的周围,使其耕种土地。他们离开军营时有305人,因途中死了一些人,到达目的地时剩68户293人(HJYD 1—1721:39—41,91—100;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2009:42—43)。
② 塔奔和科尔撒哈勒(Ker Sahal或Ker Sakal)
1722年10月,从傅尔丹和祁里德将军等处遣送塔奔和科尔撒哈勒643人给呼伦贝尔附近的黑龙江将军代管。然后他们穿过大兴安岭,12月到达布特哈地区,人口减到640人。黑龙江将军决定把他们安插在从西面流入嫩江的雅尔河沿岸,把他们与特楞古德(①部)一起编入佐领(HJYD 1—1722:128—137;3—1722:213—214;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2009:42—43)。在一些档案里,统称他们为“乌梁海”。
在布特哈总管辖下,①②两部部落最初编为6个佐领,但是后来,在1731年,把他们都编到齐齐哈尔、黑龙江(瑷珲)和墨尔根(今嫩江)等三城的八旗驻防(MZZ580:卓尔海,民族,蒙古族)。
自1715年后,卫拉特诸部的迁移,与清朝和蒙古军事联盟在萨彦岭和阿尔泰山地区的活动紧密相关。要详细弄清楚这些部落最初居住于何处以及他们是怎样进入清朝统治下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根据各部在这些地区的总体情况,可以发现一些信息。
A)1708年,清朝抗议俄国在黄郭罗依(萨彦岭北方的叶尼塞河沿岸)处修建城堡,并指出最初居住该处的吉尔吉斯、乌梁海和莫多尔为根敦(喀尔喀王公)所辖,但是后来在1702年,准噶尔汗带走了大部分,仅留有少数莫多尔在那儿(《选编》No.140)。
B)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在1725年3月上奏中提到,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声称,生活在克木克木齐克(今图瓦)和黄郭罗依地方的吉尔吉斯、明阿特、特楞古德及乌梁海一直属于准噶尔;并在1715年,当清军行进到此处时,准噶尔汗把他们带走了,但是有一些归顺了清朝。另外,属于准噶尔的特楞古德仍然居住在阿尔泰诺尔湖(位于阿尔泰山北面,今捷列茨科耶湖)周围(MZZ928:策凌,民族事务,蒙古族)。另一喀尔喀副将军丹津多尔济也在1728年的上奏中提到,属于准噶尔的特楞古德居住在阿尔泰诺尔湖周围(MZZ359:丹津多尔济,民族事务,蒙古族)。
C)1720年,色布腾(见下④这兄弟俩父亲为厄鲁特扎萨克多罗郡王阿喇布坦,1702年归顺清朝。他死后,清政府承认他们统治乌梁海的一部分(《表传》卷77:《阿喇布坦传》)。)在阿尔泰山南麓投降清军后说道,在其管辖下,最初有乌梁海、特楞古德和科尔撒哈勒,但他投降后,根敦的继承者博贝把乌梁海带走了,特楞古德也分散迁到了其他的地方(YZD 1(1):320—324)。
仔细分析这些零碎的信息,我们推测特楞古德在归顺清朝前,应居于阿尔泰山处,而据上述B可知,他们是从叶尼塞河流域①部落①的直接来源可能是色布腾提到的分别迁移的那批人。迁来的。另一个事实也支持特楞古德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关系:清军平定准噶尔后,被编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内的人们自称为“特楞古德”(吕一燃 1991),并且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区的阿尔泰人中仍有一支群体叫特楞机特(Levin and Potapov 1956:329—330)。②我们发现在清朝征服准噶尔之后的一些文献里有名为“特楞古德”的词,如《准噶尔全部纪略》和《准噶尔部旧官制》,作为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的“新十二鄂托克”之一。据说这个部落有4000人。据小沼孝博的研究,“新十二鄂托克”是“准噶尔在其扩张过程中吸收其他部落的基础之上改编而成的” (小沼孝博 2009)。如承认这个提法,他们可能在从叶尼塞河迁到阿尔泰山后被编为一个鄂托克。
关于塔奔,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然而这个事实却值得关注,18世纪,在叶尼塞的吉尔吉斯人(今哈卡斯族)有一部落被称为Taban(Butanaev,Khudyakov 2000:157),并且在今富裕县柯尔克孜族中,有一族姓为“达本” (胡振华 2006: 144)。至于科尔撒哈勒,除在上述A里稍有涉及外,我们没有关于其来源的详细资料。我们仅知道,他们是说突厥语的人,因为“ker”可能与今土耳其语“kīr”(“苍白的”)有关系。③“Sahal”或“sakal”在突厥语和蒙古语里都称为“胡须”。
2~2.第二阶段:1728—1733
③ 乌梁海
1728年12月,雍正帝指出博贝所辖的一部分乌梁海在生计上已陷入困境,故下令把他们迁往齐齐哈尔地区,据皇帝旨意,429名乌梁海人被护送到布特哈地区,然后再前往通肯河和呼裕尔河流域(MZZ733:那苏图, 民族, 蒙古族)。在布特哈地区,他们被编为两个佐领(HJYD 4–1730: 535–537, 625–630;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2009:45)。然而,在1731年,清政府决定把他们分配到吉林和盛京一些八旗驻防地,因此把104名成年男子及其家庭迁了过来(MZZ580: 卓尔海, 民族, 蒙古族; 733: 那苏图, 民族, 蒙古族)。
1726年,据副将军策凌奏,当时博贝辖有乌梁海1082户,车棱旺布和色布腾旺布④这兄弟俩父亲为厄鲁特扎萨克多罗郡王阿喇布坦,1702年归顺清朝。他死后,清政府承认他们统治乌梁海的一部分(《表传》卷77:《阿喇布坦传》)。辖有736户。前者主要居住于以下区域: 1)唐努山南面向西流入乌布萨湖的特斯河沿岸;2)位于图瓦东部Toji和Cisgit河沿岸(MZZ925:策凌, 军务, 人事)。迁到今中国东北的那些人可能便是从这些乌梁海中选择的部分。
④ 厄鲁特
此处我们仅对厄鲁特作一简单的概述,因为在另一篇论文里曾对其有所详细论述(柳泽明 2005)。1720年,他们在阿尔泰山南麓投降清军。后来把他们编入以前的首领(扎萨克)色布腾管辖下的两个佐领,位于察哈尔地区。1732年2月,雍正指出,因靠近他们居住的另一群卫拉特人最近逃跑了,周围的人对他们有所怀疑,故认为应把他们迁往呼伦贝尔(HJYD1–1732: 113–118)。八月,到达呼伦贝尔地区,即把他们安置在海拉尔河南面的一个大牧场。原有的两个佐领迁徙后也保持不变,任命色布腾为总管来管理他们。当时他们有217户771人(HJYD 2–1732: 289–293)。正如上述C所述,他们最初包括乌梁海、特楞古德和科尔撒哈勒,然而一些史料却统称他们为“乌梁海”(HJYD 1–1732:113–118)。
⑤ 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初为色布腾旺布所辖,但是其有强烈的叛逃倾向(YZD3(3): 184–186)。1732年,当色布腾旺布将要向东迁往喀尔喀河时,①色布腾旺布和他的牧民们,在喀尔喀河流域生活了好几年后,又把他们迁到蒙古西部地区,编入科布多附近的旗。(见岡洋樹1994)。打算把他们一起带走。然吉尔吉斯不愿与其一同居住,且在途中,一些人就分散了。然后色布腾旺布提议把他们交与皇上(YZD6(2): 262–266;5:2(2): 158–161)。雍正帝接受了他的提议,下令将他们迁往齐齐哈尔地区。1733年,吉尔吉斯276人到达齐齐哈尔,分别把他们编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瑷珲)和墨尔根等三城的佐领(MZZ734: 那苏图, 民族, 吉尔吉斯;YZZ9:261–269;吴元丰 2004;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2009: 45–48)。
据上述A和B知,他们最初居于叶尼塞河流域,且在1710—1720年,分别受到准噶尔和清朝控制。②我们发现一个名为准噶尔的“新十二鄂托克” 之一的“奇尔吉斯”(见注释③),他们有4000户。一些学者认为生活在今天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与叶尼塞河流域的哈卡斯在语言和族姓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胡振华 2006:102-144),故可能来源于这一部落。
2~3.第三阶段:1757—1758
1755—1756年,随着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原已归顺清朝的许多卫拉特部落又先后叛逃。清朝镇压叛乱后,屠杀了大量可疑之人,把其余的为奴,而把可以酌情的一些部落没有分散地迁到呼伦贝尔和其他地区。尽管笔者在另一篇论文里注意到了这些部落(柳泽明 2005),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也对他们的迁移过程作了考察,现在笔者根据一些新材料作一补充说明。
⑥ 明阿特
1757年3月,当乾隆帝下令处罚那些可疑的部落时,明阿特的一部分也作了奴隶。但是在得木齐③得木齐是准噶尔的官衔。清朝认为他们的地位相当于佐领。见马大正、成崇德(2006,p.83)。巴苏台辖下的一个部落,清朝决定把其迁到呼伦贝尔地区,而不让他们为奴,因为他们“真心归顺”和“配合我们捉拿乌梁海叛军”。初有26户120人,但是,在同年十一月到达呼伦贝尔时,人口减到105人。然后把他们安置在呼伦贝尔东部的乌兰布尔噶苏台河沿岸(HJYD4–1757: 236–265, 576–583)。①巴苏台,最初为得木齐,在到达呼伦贝尔之前就死了。Yangtemur,被任命为得木齐代替巴苏台,但他也不久就死了,故Korima为第三任得木齐(HJYD 4–1757: 1102–1103)。
明阿特也是准噶尔“新十二鄂托克”之一,有3000户。据上述B知,他们可能居于叶尼塞河流域,后迁到阿尔泰地区。他们可能是操蒙古语言的人,因为策凌在一次上奏中提到:“明阿特并不等同于乌梁海。他们是蒙古骨(Monggo giranggi)。”
⑦ 噶勒扎特(Galjid)
自1756年以来,得木齐达木拜和根敦率领辖下的噶勒扎特人,相继归顺清朝,清朝暂时把他们编入扎哈沁。然而清朝对他们曾有所怀疑,但最后决定把他们迁到呼伦贝尔而没有使他们为奴,因为他们“自归顺以来,一直忠顺,没有任何问题。”1757年10月,当他们到达呼伦贝尔时,离开时的147户578人减到532人。然后,把他们安置在呼伦贝尔东部的Dulimbai Eyur河沿岸(HJYD4–1757: 374–383, 755–762)。
噶勒扎特也是准噶尔“新十二鄂托克”之一,有4000户。其居住可能位于今和布克赛尔地方,据《方略》一段记载:“噶勒雜(雜为扎——译者注)特部落在和博克等处”(《方略》卷29: 乾隆二十一年秋七月己巳)。②冯锡时(1990)指出他们的牧场可能位于伊犁河流域。顺便提一下,在1757年初,乾隆下令追剿噶勒扎特部的另一部分,因他们叛离清朝并留在了额尔齐斯河(《方略》卷38:乾隆二十二年春三月戊申)。
⑧ 杜尔伯特-1
杜尔伯特曾是“四卫拉特(DörbenOyirad)”主要成员之一,兹不赘述,但是在1753年,车凌率领很大一部分归顺了清朝(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2006)。然而,一些贵族(台吉)布图库、班珠尔带着属民后来又归顺,不愿同车凌居住,请求迁移。乾隆下令将其迁到呼伦贝尔或通肯呼裕尔(HJYD1–1757: 145–148)。后来,因有人报道呼伦贝尔环境更好,清政府决定把他们迁到那儿(HJYD3–1757: 286–291)。离开时大约有70户,但是在这一年里他们没能到达目的地——乌兰布尔噶苏台河,而且在那一年里,一些人(9户41人)在路上落后了(HJYD7–1757:295–301, 4–1757: 961–967)。
1790年,⑥—⑧这几个部落编入到④部落的两个佐领,故得到了类似八旗驻防的待遇。
⑨ 伊克明安
他们可能属于四卫拉特另一主要组成部分的辉特。1754—1756年,两个贵族阿巴达什和巴桑各自带领其所属属民归顺清朝后,他们被安置在塔米尔河沿岸的牧场。当大部分辉特人叛离清朝时,巴桑和阿巴达什并没有参与(《表传》 卷115:《巴桑传》和《阿巴达什传》;敖乐奇 1987, 1990)。因此,在镇压叛乱后,把他们迁到通肯呼裕尔地区,没有受任何处罚。1757年9月,该部落的52人与明阿特(⑥部)到达呼伦贝尔,然后继续前往通肯呼裕尔。刚到该地,即将其编为一旗,任阿巴达什为扎萨克。
之所以称他们为“伊克明安”,是因为巴桑和阿巴达什的族姓。“伊克明安”这个姓可以在《准噶尔全部纪略》和《准噶尔部旧官制》(见302页注②鄂尔楚克可能与阿尔泰山处的一部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发现,准噶尔被清朝征服之后,OortsaG作为阿尔泰乌梁海的一小部,被编入七个旗内。见Bi Batuba (2004)。,英文原文见注③——译者注)中找到,是构成辉特九个昂吉(蒙古语为anggi)之一(冯锡时 1990;小沼孝博 2009)。被清朝在不同地区编旗的辉特其他部落的所有首领,都源于这个族姓(《表传》卷86:《贡格列传》,卷99:《达玛琳传》和《罗卜藏传》)。
⑩ 杜尔伯特-2
伯什阿噶什,除车凌外的杜尔伯特主要首领,1756年归顺清朝(《表传》卷95: 杜尔伯特总传)。但他很快便死了。然后,他的亲属试图与车凌合流,但是他们陷入了“没有可吃的或喝的”的困境。因此,清朝决定把博东齐、达瓦济特——伯什阿噶什的弟弟与儿子——及其属民迁到通肯呼裕尔地区。他们离开时有47人,1757年12月,到达呼伦贝尔时减到39人(HJYD7–1757: 315–322, 4–1757:1094–1099)。虽然我们尚未发现直接提到他们到达该地后的情况的相关资料,但他们似乎加入了伊克明安(⑨部)。
⑪ 明阿特, 绰罗斯, 特楞古德, 吉尔吉斯和鄂尔楚克
如上所述,1757年3月,乾隆帝下令解散那些参与叛离清朝后又归顺清朝的一些卫拉特部落,并把他们分赏给布特哈和呼伦贝尔地区的官兵为奴。虽然在诏书里仅提到三个部落,即特楞古德、吉尔吉斯和乌尔罕济兰①乾隆评论道,这三个部落是“古尔班和卓的帮凶”。这个评述是反映部分特楞古德一部和柯尔克孜人在古尔班和卓的率领下叛逃和试图与阿睦尔撒纳合流(《方略》卷29:乾隆二十一年秋七月壬申)。,但是后来经详细调查发现,他们是由明阿特、绰罗斯、特楞古德、吉尔吉斯和鄂尔楚克的181户636人组成。他们分三队迁移,由于相当多的人死在了途中,7月到达呼伦贝尔时只剩176户570人。其中346人(60%)被派到布特哈地区,颁给当地的官兵为奴,224人(40%)则留在了呼伦贝尔(HJYD4–1757:236–265;《方略》卷38: 乾隆二十二年春三月乙巳)。
在这些部落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包括准噶尔“新十二鄂托克”中的特楞古德、吉尔吉斯和明阿特。乌尔罕济兰也和鄂尔楚克共同组成准噶尔“新十二鄂托克”之一(冯锡时 1990;小沼孝博 2009)。②鄂尔楚克可能与阿尔泰山处的一部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发现,准噶尔被清朝征服之后,OortsaG作为阿尔泰乌梁海的一小部,被编入七个旗内。见Bi Batuba (2004)。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乾隆最初提到的乌尔罕济兰为什么后来不见了。绰罗斯不是部落名,而是准噶尔和杜尔伯特统治家族的族姓。
除上述提到的诸部落,清政府也暂时计划把准噶尔又一杰出首领达什达瓦的属民迁到通肯呼裕尔(HJYD4–1757: 236–265),但后来改变了目的地,将其迁到了热河(承德)地区(敖其尔·乌云扎尔噶拉 2009: 99–115)。
3.迁移的几个侧面
3~1.清朝的目的和管理体系
对上述言及的诸部落,清朝将其迁移的主要目的,不必多言,是消除清政府担忧他们从前线逃跑。1720年,当康熙皇帝决定迁移最早的那一部落时,说道:“从现在起,很多(卫拉特)人将不断地被俘虏或投降。如果成百上千的人来归顺我们,怎样安置他们在我们的军营?营地如此靠前,以至他们容易逃跑” (MZZJB11–08; HJYD1–1720:206–217)。雍正皇帝迁移厄鲁特(④部)的直接目的是因为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另一卫拉特部落逃跑。从色布腾旺布处单独迁吉尔吉斯(⑤部)到齐齐哈尔地区,是因为他们有叛离他的倾向。至于噶勒扎特(⑦),他们迁移的背景则是清朝怀疑“他们不值得信任。我们不能消除对他们反叛的担忧” (HJYD 4–1757: 374–383)。
在一些资料里,我们也发现了另一个因素:清朝迁移卫拉特人的目的是为了救济他们。如乌梁海人(③部)出发去今中国东北之前,雍正皇帝下令解释道:“今贝勒博贝牧场周围的动物都逃走了,故你们无法狩猎。你们靠打猎为生。若缺乏动物,你们将陷入困境。……林木繁茂和禽兽颇多的齐齐哈尔地区是适合你们的地方。”有序迁移杜尔伯特(⑩),乾隆帝表达了他的忧虑,如果他们一起生活,极端的贫困可能对车凌及其属民产生消极的影响(HJYD 7–1757: 315–322)。
对于这样的目的,在今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地区有着充足的条件。首先,有八旗驻防的存在,便于监督新迁来之人。此外,对新来的人而言,这些地方有足够的空间,因为此处没有太多的人口。①除呼伦贝尔和中国东北地区之外,清政府也经常选择察哈尔——在这个地区也设了八旗制度——作为移民的目的地。然而,在18世纪50年代,要在察哈尔地区找到一块空的土地已经很困难了(HJYD: 1–1757: 145)。
在重新安置移民问题上,清朝的管理体系可分为三种类型。最基本的类型便是把一个部落安置在一大块土地上,而不分散他们(①—④,⑥—⑩)。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往往选择嫩江支流流域像通肯和呼裕尔,或呼伦贝尔地区作为他们的目的地。我们找到一些关于对这些地区环境的描述:“诺敏河和格尼河交汇处是一块肥沃的土壤。附近林木繁茂,有充足的土地耕种、畜牧和游牧” (HJYD 1–1721: 91–100);“呼裕尔河与通肯河有各种大小的鱼,周围平原广阔,水草丰美。森林里禽兽颇多。” (HJYD 4–1730:535–537);“呼伦贝尔和喀尔喀河位于广阔的平原上,这儿水草丰美。林木繁茂,也有众多动物和鱼类。这是适合你们游牧生活的好地方” (HJYD1–1732: 113–118)。
第二种类型是把一部落分散并把他们分别编入八旗驻防。关于①—③部落,由于最初采用第一种类型,几年后,清政府决定“把他们编入到固山(旗)和牛录(佐领),让他们披甲并给其补助”,因为在重新安置后,他们生活一直不稳定。关于吉尔吉斯(⑤),可能鉴于前者的失败,清政府从一开始就采用第二种类型,说道:“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置于可观察的状态,我们将会担忧他们反叛或逃跑。如果我们让他们在八旗驻防里面披甲,不仅将有监督者,而且他们还能过着每月领着钱粮和饷米的舒适生活” (HJYD 2–1733: 635–640)。
第三种类型是把他们作为奴隶(⑪)分赏给八旗驻防的官兵。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而且还是为了惩罚他们。
3~2.安置后的困难
这些移民在新的地区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问题,即不适应新的环境。虽然嫩江流域经常被描写为一块“美好的土地”,其实该地似乎并不是他们理想生活的场所。如特楞古德(①)到达指定的区域格尼河的第二年,就向清地方政府呼吁,他们的牲畜皆死于感染,而且已无食物可吃(HJYD3–1722: 199–201)。我们也发现有乌梁海(③)一例,他们重新安置后不久,牲畜因感染而死了(HJYD 4–1730: 628–621)。如上所述,在1731年,清政府不得不把①—③部编入八旗驻防,因为:“自从先前来的和后面来的乌梁海重新安置后,他们的马和其它牲畜并无增加,且周围的野生动物也被其驱至远处。如果继续让他们在该地待下去,这对他们的生活是不利的(MZZ580: 卓尔海, 民族, 蒙古族)”。当迁徙卫拉特诸部的第三阶段时(1757—1758),清政府就已经开始把通肯呼裕尔地区视为“牧场如此之差,夏则有大量牛虻和蚊子”(HJYD6–1757: 262–267)这样的地方。相反,对呼伦贝尔地区的较高评价基本不变。我们发现在1790年有关移民的一份档案中这样记载:“自陛下青睐我们以来……安置我们在呼伦贝尔,在广阔的牧场上,水草丰美,享受了多年” (MLZ3277–028/147–2337)。然而,在第三阶段,我们也了解到牧场拥挤已成为严重的问题,呼伦贝尔索伦、巴尔虎八旗的总管们曾就噶勒扎特(⑦)的迁移而抱怨:“(如果他们来了,)索伦和巴尔虎的牧场将变得更狭窄” (HJYD 4–1757:374–383)。
重新安置的部落有时可能面临与当地居民间的冲突或麻烦。当特楞古德安置后不久,即遭受上述饥荒,黑龙江将军责备布特哈总管,他有照顾他们之责,说道:“你没有为特楞古德提供可吃之食物,也没派官兵去照看他们,因此丢下他们,无任何的帮助”(HJYD3–1722: 199–201)。当乌梁海遭受感染时,将军再次批评了总管,并指出:“尽管乌梁海饲养的动物因染疾病死去而失去了生活资料,但是你却没能提出一个明确解释这个事实的报告” (HJYD 4–1730: 618–621)。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布特哈地方的官员至少没有关心移民们的生计。关于厄鲁特(④),1731年迁到呼伦贝尔,他们的首领色布腾很快便仇视与厄鲁特同时从嫩江地区迁到呼伦贝尔的索伦总管博尔本察(柳泽明2005)。总而言之,尽管我们不应该过渡高估这样的个例,但是本地部落,像索伦和达呼尔,似乎并不欢迎新来的卫拉特人。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被安置部落的内部矛盾,可以发现有乌梁海(③)一例。1730年,他们到达通肯呼裕尔地区之后不久,一个叫Gajarak的长老来到布特哈的总管衙门,呼吁道:“自我们集中在一个地方以来,在我们内部经常发生矛盾,相互视为敌人。不能和平相处。我惟恐担心我们在未来会互相残杀或逃跑” (HJYD4–1730: 293–295)。这一呼吁,直接导致了他们被编入到齐齐哈尔八旗驻防。关于呼伦贝尔的厄鲁特,1739年,在副总管那木扎(Namja)和佐领扎木布(Dzambu)的领导下,许多人控告他们的首领(总管)色布腾(柳泽明 2005)。
据此推测,在卫拉特诸部调整适应今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的环境这一过程中,除上述所举例子外,卫拉特诸部还遇到了其他许多的困难和曲折。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问题上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4.迁移的卫拉特诸部与现在的民族的关系
总的来说,清政府给予一些卫拉特人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并维持了很久,这为他们保持或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例如,呼伦贝尔地区的厄鲁特(包括④、⑥、⑦、⑧等部落),在他们自己的总管下保持着两个佐领,直到清末也未变;而在呼裕尔河流域的伊克明安(包括⑨、⑩)仍是他们自己的执政者(扎萨克)管辖下的一个旗。这些行政组织成为了现有族群形成的基础。虽然厄鲁特和伊克明安都是由不同来源的部落构成,但是今天看来,这些小部落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是那么突出。然而,他们却没有完全忘记自己最初来源的小部落。关于厄鲁特,源于④部落的氏族被称为“旧厄鲁特”,而源于⑥—⑧等部落的氏族被称为“新厄鲁特” (柳泽明 2005)。
相反,那些被编入八旗驻防和分配为奴的人,可能已迅速融入了周围的部落,因此要识别出他们的后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却发现一个另外——今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由于五家子村是他们大多数生活的地方,他们的来源可能是在⑤部落中编入齐齐哈尔驻防的部分。尽管当时他们被分配给不同的佐领,但为什么会生活在同一个村庄,并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元素?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缩写
HJYD: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编号:页码)
MLZ: 《满文录副奏折》(编号:档案号/缩微胶卷号:胶片号)
MZZ: 《满文朱批奏折》(编号:人,分类,条)
MZZJB: 《满文朱批奏折机构包》(编号:缩微胶卷号:初始胶片号)
YZD: 《月折档》(编号:页码)
《表传》: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四库全书》)
《方略》: 《平定准噶尔方略》(《四库全书》)
《选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