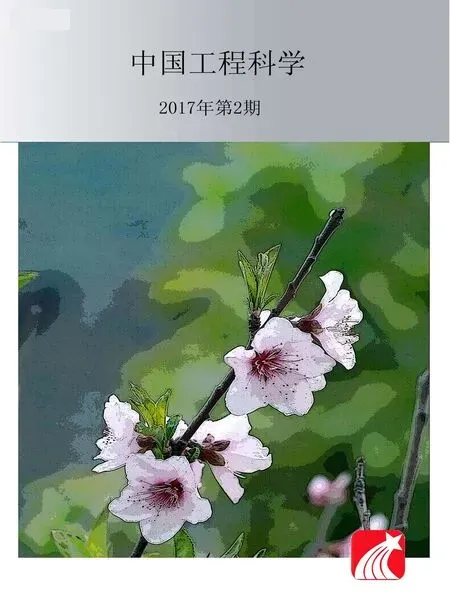我国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生物工程研究现状和应对策略
谢立信,周庆军,徐海峰,林萍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山东青岛 266071)
我国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生物工程研究现状和应对策略
谢立信,周庆军,徐海峰,林萍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山东青岛 266071)
我国现有盲人1 200多万,是世界上盲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寻找可用于恢复视功能的生物工程材料,尤其是使用干细胞技术和生物芯片技术重建视功能已成为生物工程领域最有前景的研究方向。本文介绍了我国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生物工程研究的发展现状,分析了角膜和视网膜领域生物工程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情,针对研发方向、审批制度、成果转化和研究平台建设提出了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
眼科学和视觉科学;生物工程;现状;对策
一、前言
跟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肿瘤、心血管疾病、眼病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前三位疾病。研究资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约有1 200万盲人,占全世界盲人的18 %。我国每年约有45万人失明,几乎每分钟就会新增1例盲人,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的负担[1]。引起致盲的主要疾病有白内障、角膜病、眼外伤、青光眼、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美国国立眼科研究所(NEI)资料表明,美国每年用于眼科疾病治疗的费用约为600亿美元;英国每年的治疗费用也高达88亿英镑。中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中国人口约是美国人口的4倍,因眼病造成的伤害与损失无法估量。中国政府已在WHO发起的“视觉2020,全球行动消灭可避免盲,享有看见的权利”行动上签字并做出庄严承诺,承诺2020年以前在我国消除可避免的盲症。我国政府在白内障领域的防盲工作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角膜病及视网膜、视神经疾病等领域的研究与欧美国家相比尚存在差距。
目前,世界各国致盲性疾病研究的重心都在根据国情或发病率的变化逐渐转移,欧美国家主要针对神经性致盲病,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虽然目前有很多药物或手术能延缓病程发展,但最后都会因为视网膜神经细胞的损伤,对视力造成不可逆性损害。在角膜病方面,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与其他国家不同,角膜移植供体材料的来源受限是阻碍我国角膜盲患者复明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寻找可用于恢复视功能的生物工程材料,尤其是使用干细胞技术和生物芯片技术重建视功能已成为最有前景的研究方向。生物工程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成为眼科领域研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二、我国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生物工程的研究现状
(一)角膜领域
角膜病是我国重要的致盲性眼病。由谢立信教授组织的我国10省市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单眼或双眼角膜盲人301.5万,其中80 %可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实现复明,但我国角膜捐献率低,供体材料严重匮乏,每年角膜移植手术量不足10 000例,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2~3]。因此,开发组织工程角膜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人工角膜、组织工程角膜和生物活性羊膜是目前临床常采用的角膜替代材料,组织工程角膜上皮和基质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展[4]。
1. 人工角膜
人工角膜是用异质成形材料制成的一种特殊屈光装置,植入患眼取代混浊的角膜组织,以达到取得一定视力的作用。1947年,Stone首次使用高分子材料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制作人工角膜,大大推动了人工角膜研究的发展。近年来的进展主要体现在材料选择、处理和设计方式上的创新。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证并应用于临床的有AlphaCor和Dohlman-Doane (Boston)两种人工角膜,其中Boston人工角膜在1992 年获得美国 FDA 的批准可以临床使用,AlphaCor 人工角膜在2003年被批准使用;Boston人工角膜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疗效最可靠的人工角膜之一。我国还没有自主研发的人工角膜产品应用于临床治疗。
2. 组织工程角膜
全层组织工程角膜应包含角膜上皮、基质和内皮三部分。早期,研究者利用病毒转染永生化的人角膜上皮细胞、基质细胞和内皮细胞,结合戊二醛交联过的胶原材料作为支架,构建了全层组织工程角膜替代物,透明性及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接近正常角膜,但目前仍未有进入临床研究的报道[5]。基于永生化细胞的安全性和支架材料的长期效果尚未阐明,临床深板层角膜移植和角膜内皮移植的技术尚待完善,全层组织工程角膜的开发和应用价值仍需探讨。
构建组织工程角膜上皮必须包含合适的上皮干细胞和载体材料,形成重组上皮细胞膜片。目前,采用体外扩增形成的角膜缘上皮细胞膜片、口腔黏膜上皮细胞膜片移植治疗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症已被日本、意大利、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批准应用于临床,短期和长期的效果显著[6~9]。对于其他干细胞分化为角膜上皮干细胞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可能为组织工程角膜上皮的构建提供新的种子细胞来源[10]。
角膜基质占角膜整体厚度的90 %,是维持角膜透明性的主要结构基础,寻找具有天然角膜基质透明性的替代物是组织工程角膜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在保持角膜基质成分、结构和透明性的同时,尽可能地去除其细胞和抗原成分。国内已有多家单位对脱细胞猪角膜进行了研究,2015年4月,我国自主研发的脱细胞角膜基质产品“艾欣瞳”正式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临床试验的脱细胞角膜基质产品[11],随后也有类似的产品获批或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但临床应用长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12]。
人角膜内皮细胞体内再生和体外扩增能力差,获得具有正常功能的角膜内皮种子细胞是组织工程角膜面临的最大难题。近年来,研究者一方面优化成人角膜内皮细胞的体外扩增方法,另一方面诱导胚胎干细胞或其他成体干细胞分化为角膜内皮细胞,但前者难以实现产业化,后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待阐明。同时,限于角膜内皮细胞没有特异性的检测方法,分化细胞的性质和功能鉴定还存在问题。
3. 生物活性羊膜
羊膜是目前角膜病治疗中被广泛使用的生物材料之一,美国已有专门的生物活性羊膜产品应用于临床治疗,我国目前还没有生物活性羊膜的产品上市,只有一家公司开发了冻干型生物羊膜,其临床应用效果明显弱于生物活性羊膜。
(二)视网膜领域
在视觉产生过程中,视网膜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由于视网膜色素变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眼外伤等原因造成的视网膜结构不可逆性破坏,药物治疗已无能为力,视功能永久性丧失。视觉假体是一种可取代视网膜,使失明患者恢复有用视力的人造器官[13]。根据植入部位的不同,视觉假体可分为视皮层视觉假体(cortical prosthesis)、视神经视觉假体(optic nerve prosthesis)和视网膜视觉假体(retinal prosthesis)[14~16]。
1. 视皮层视觉假体
视皮层视觉假体研究历史最长,迄今效果最好的是瑞士科学家报告一例因外伤失明的患者,植入视皮质假体后能够看到1.5 m处10 cm宽的字母,植入的假体在患者体内存留已长达20年[13]。但视皮质假体研究进展缓慢,这一方法不被看好的原因是刺激强度难以控制,刺激过强会诱发癫痫;另外,电极的植入过程本身及进行刺激时均有可能损伤大脑组织,因此虽早有计划进行人体试验,但尚无结果报道。
2. 视神经视觉假体
视神经视觉假体是直接在视觉信息进入大脑的必经之路——视神经上安置微电极阵列,刺激视神经形成视觉感受。国际上,除基础研究外,比利时科学家先后报告了3例因视网膜色素变性完全失明的患者通过在视神经周围植入电极,刺激视神经而产生视觉感受[17,18],认为这一现象证明了视神经假体的潜在可行性,除此之外尚无其他人体试验的报道。我国“973”首席科学家任秋实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经过前期研究,已经在视觉信息处理、图像获取与处理、微电极阵列与视神经相互作用机理、微电极阵列及其表面修饰、相关基础医学问题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且进行了动物试验,通过植入的电极刺激视神经,在视皮层成功记录到电位响应,证实其植入的视觉假体能引起视觉感受[19]。下一步的目标是在完善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寻找视网膜和局部视神经功能尚完好的盲人完成3~5例人体神经假体植入试验,期望视觉假体能让盲人产生光感、动感、轮廓感,并能识别简单的文字。
3. 视网膜视觉假体
视网膜视觉假体是所有视觉假体中研究最成熟、最广泛的一种[20~22]。
(1)视网膜芯片领域
国际上,如德国、美国均有产品上市,美国第二视觉公司的产品——Argus II已在欧美上市,该产品是美国能源部的人工视网膜项目组,包括6个国家级实验室、4所大学及1家私有公司,进行长达20余年研究和改进,又历经世界范围内10个临床中心、4 年多的临床观察最终推向市场的。Argus II为第二代产品,共有30位视网膜色素上皮变性患者参与了临床观察,这些患者治疗前仅有光感视力,使用Argus II后绝大多数患者视功能有所改善[23]。德国的Alpha-IMS视觉假体也于2013年在欧洲上市。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国内的研究仅仅是视网膜芯片技术最初始的研究。
(2)组织工程视网膜领域
组织工程视网膜是近年来随着干细胞研究的发展而形成的一项新的治疗方法,由种子细胞及支架材料组成。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国内还处于基础研究阶段,阴正勤教授、葛坚教授以及徐国彤教授团队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原始创新成果,证明了干细胞移植对视功能修复的可能性。在临床试验方面,目前国外正在开展多项临床试验,将干细胞用于治疗萎缩型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Stargardt’s病、视网膜色素上皮变性及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24]。
4. 蛋白类生物药
目前主要是针对视网膜疾病开发的抑制新生血管的抗体类药物的研发和临床应用。国际上已有Lucentis,Avastin等药物获批上市;国内四川康弘药业集团资助开发的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已经上市,临床应用效果显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也是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制品I类新药。
(三)晶状体再生领域
一些哺乳动物的晶状体摘除后,在囊袋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再生出新的晶状体[25]。目前普遍认为囊袋内不能被完全清除而残留的晶状体上皮细胞是晶状体再生的来源,我国中山大学眼科中心与美国加州大学合作研究,通过刺激内源性干细胞再生出功能性晶状体,并对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进行了临床试验[26]。但是,哺乳动物的晶状体再生并非晶状体发育的简单重复,特别是后发性白内障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三、我国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生物工程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角膜领域
脱细胞角膜基质产品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但对于含细胞的组织工程角膜产品,尤其是组织工程角膜上皮,以及难度更大的组织工程角膜内皮还需要企业与科研院所、临床医院的紧密合作,这也是解决我国角膜供体匮乏的关键难题。此外,人工角膜仍依赖于国外进口,我国尚无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实现临床应用。
(二)视网膜领域
视神经假体的研究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但要实现临床应用,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组织工程视网膜研究领域,我国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与国际差距不大,但临床前的研究仍面临许多问题,这也是最可能有突破、有原始创新的地方,临床试验方面与国际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我国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生物工程研究的应对策略
(一)结合国情开展研究开发
以组织工程角膜为例,目前欧美国家角膜捐献率高,美国捐献的角膜中约1/3用于临床移植,1/3用于实验室研究,1/3用于出口到其他国家。虽然我国角膜捐献在逐渐增加,供体角膜的利用率也在提高,但目前大多数角膜盲患者还不能通过角膜移植复明。因此,组织工程角膜是目前解决我国角膜供体匮乏的主要途径,尤其是组织工程角膜上皮和角膜基质是最有可能率先应用于临床的生物工程材料,风险也明显小于其他组织工程产品。建议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在经费支持、政策导向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缓解我国角膜供体严重不足的局面。
(二)制定国家层面的审批制度
目前我国干细胞和组织工程方面的基础研究与国外基本保持同步的水平,但在相关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方面明显处于落后状态。严格的国家政策对于治理目前干细胞移植混乱的现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或政策不明确,导致对我国干细胞和组织工程眼科产品方面的开发工作影响较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一直在尝试制定政策引导干细胞临床试验,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和规范。基于组织工程角膜的基础和临床技术要求较高,探索通过建立干细胞临床试验研究基地,开展相应的临床试验研究十分必要。虽然通过第三类医疗技术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品转化方面的劣势,但是其应用和将来转化的规模仍无法与产品转化的规模相提并论。因此,建议卫生主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能尽快制定并出台规范化的审批政策和制度,不应单纯跟踪模仿国外的制度。
(三)制定积极的成果转化政策
目前,我国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的生物工程研究多依赖于国家的经费,多数的研究成果也仅停留在实验室和发表论文阶段,进入产业化和临床阶段的成果偏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目前的成果评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化和临床应用的进程。如“973”课题多数强调发表论文的层次,并未对下游的过程进行评价,5年的研究周期对于成果转化来讲也过于仓促;另一方面,目前国家在成果转化方面的政策还不够积极,也阻碍了研究人员进行产业化和临床推广的积极性。日本在干细胞产业化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在产品的研发阶段就引导公司介入,随后有风险投资的跟进,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相关成果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因此,建议科技主管部门尽快制定并出台规范化的审批政策和制度。
(四)建立工程技术研究平台
建议国家科技部组建一个国家级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工程技术研发平台,面向国内患者和医疗机构的实际需要,注重资源整合和转化医学,致力于研发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组织工程眼用产品。通过新的工程技术产品、创新手术技术的开展和推广,减少可避免盲的致盲率,使更多的患者复明,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可避免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1]新华网. 国际盲人节: 我国每年新出现盲人大约45万人 [EB/ OL]. (2006-10-16) [2016-10-25]. http://news.xinhuanet.com/ health/2006-10/16/content_5207677.htm. Xinhua Net.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blind: China increases about 450 thousand blind person each year [EB/OL]. (2006-10-16) [2016-10-25].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06-10/16/ content_5207677.htm.
[2]Song X, Xie L, Tan X, et al.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the burden of infectious keratitis in China [J]. PLoS One, 2014, 9(12): e113843.
[3]谢立信. 我国角膜手术的现状和发展策略 [J]. 中华眼科杂志, 2005, 41(8): 702–704. Xie L X.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corneal surgery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2005, 41(8): 702–704.
[4]周庆军, 谢立信. 组织工程角膜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现状 [J].中华细胞与干细胞杂志, 2014, 4(1): 1–4. Zhou Q J, Xie L X. Tissue-engineered cornea: New progresses and challenges [J]. Chinese Journal of Cell and Stem Cell, 2014, 4(1): 1–4.
[5]Griffith M, Osborne R, Munger R, et al. Functional human corneal equivalents constructed from cell lines [J]. Science, 1999, 286(5447): 2169–2172.
[6]Pellegrini G, Traverso C E, Franzi A T, et al. Long-term restoration of damaged corneal surfaces with autologous cultivated corneal epithelium [J]. Lancet, 1997, 349(9057): 990–993.
[7]Tsai R J, Li L, Chen J. Reconstruction of damaged corneas by transplantation of autologous limbal epithelial cells [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0, 343(2): 86–93.
[8]Nishida K, Yamato M, Hayashida Y, et al. Corneal reconstruction with tissue-engineered cell sheets composed of autologous oral mucosal epithelium [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4, 351(12): 1187–1196.
[9]Kaghad M. Limbal stem-cell therapy and long-term corneal regeneration [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0, 363(2): 147–155.
[10] Ouyang H, Xue Y, Lin Y, et al. WNT7A and PAX6 define corneal epithelium homeostasis and pathogenesis [J]. Nature, 2014, 511(7509): 358–361.
[11] Zhang M C, Liu X, Jin Y, et al. Lamellar keratoplasty treatment of fungal corneal ulcers with acellular porcine corneal stroma [J].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2015, 15(4): 1068–1075.
[12] Fagerholm P, Lagali1 N S, Merrett K, et al. A biosynthetic alternative to human donor tissue for inducing corneal regeneration: 24-month follow-up of a phase 1 clinical study [J].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0, 2(46): 46–61.
[13] Dobelle W H. Artificial vision for the blind by connecting a television camera to the visual cortex [J]. ASAIO Journal, 2000, 46(1): 3–9.
[14] Troyk P R, Bradley D, Bak M, et al. Intracortical visual prosthesis research–approach and progress [J].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 Biology Conference, 2005(7): 7376–7379.
[15] Veraart C, Raftopoulos C, Mortimer J T, et al. Visual sensations produced by optic nerve stimulation using an implanted self-sizing spiral cuff electrode [J]. Brain Research, 1998, 813(1): 181–186.
[16] Humayun M S, Cruz L D, Dagnelie G. Interim performance results from the second sight® Argus™ II retinal prosthesis study [R]. ARVO, 2011.
[17] Duret F, Brelén M E, Lambert V, et al. Object localiz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grasping with the optic nerve visual prosthesis [J]. Restorative Neurology & Neuroscience, 2006, 24(1): 31–40.
[18] Sakaguchi H, Kamei M, Fujikado T, et al. Artificial vision by direct optic nerve electrode (AV-DONE) implantation in a blind patient with retinitis pigmentosa [J]. Journal of Artificial Organs, 2009, 12(3): 206–209.
[19] 任秋实.视觉假体的研究进展与面临的挑战 [J]. 生命科学, 2009(21): 234–240. Ren Q S. Bionic vision: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challenge [J]. Chinese Bulletin of Life Science, 2009(21): 234–240.
[20] Yanm D, Weiland J D, Mahadevappa M, et al. Visual performance using a retinal prosthesis in three subjects with retinitis pigmentosa [J]. Americ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2007, 143(5): 820–827.
[21] Behrend M R, Ahuja A K, Humayun M S, et al. Resolution of the epiretinal prosthesis is not limited by electrode size [J].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2011, 19(4): 436–442.
[22] Nanduri D, Fine I, Horsager A, et al. Frequency and amplitude modula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percepts elicited by retinal stimulation [J]. 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 2012, 53(1): 205–214.
[23] Ahuja A K, Dorn J D, Caspi A, et al. Blind subjects implanted with the Argus II retinal prosthesis are able to improve performarice in a spatial-motor task [J]. British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2011,95(4): 539–543.
[24] Mathieson K, Loudin J, Goetz G, et al. Photovoltale retinal prosthesis with high pixel density [J]. Nature Photonics, 2012, 6(6): 391–397.
[25] Grogg M W, Call M K, Okamoto M, et al. BMP inhibition-driven regulation of six-3 underlies induction of newt lens regeneration [J]. Nature, 2005, 438(7069): 858–862.
[26] Lin H, Ouyang H, Zhu J, et al. Lens regeneration using endogenous stem cells with gain of visual function [J]. Nature, 2016, 531(7594): 323–328.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Ophthalmology and Visual Science Bioengineering, and a Development Strategy
Xie Lixin, Zhou Qingjun, Xu Haifeng, Lin Ping
(Shandong Eye Institute,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blind patient in the world, China is home to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who are blind. The most promising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bioengineering field for the treatment of blindness involves searching for bioengineering materials to restore visual function, particularly using stem cell and biochip technolog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hina’s bioengineering research in ophthalmology and visual science, an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ffecting current bioengineering research in corneal and retinal areas. We also present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he approval system, achievement trans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search platform,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ophthalmology and visual science; bioengineering; current situation; strategy
R77
A
2017-01-08;
2017-03-01
谢立信,山东省眼科研究所,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为眼科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E-mail: lixin_xie@hotmail.com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我国眼科学和视觉科学领域生物工程研究现状和应对策略”(2012-XY-20)
本刊网址:www.enginsci.cn
DOI 10.15302/J-SSCAE-2017.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