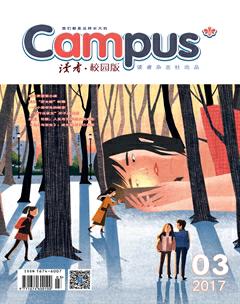如何成为一个浑然不觉的人
陈思呈
我特别喜欢邻居郑姐来我家做客。因为她每次来我家,总是一边与我聊天,一边帮我把家里收拾一遍。我们谈房价时,她帮我摘菜;我们讨论装修时,她在擦厨房的墙;我们讲各自家乡的美食时,她教我如何用收纳法整理冰箱;当我们开始讲起家人的坏话时,我家里已经窗明几净了。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去郑姐家做客。在她自己家,她也是一边与我聊天,一边操持家务。当我们谈房价时……好吧,好像我们天天谈房价一样。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习惯谈文学的人,之所以与郑姐谈房价也能谈得这么开心,是因为我喜欢看她边聊天边干活的样子。而她似乎没觉察到自己在干活,一切轻松得仿佛毫不费力,像严歌苓笔下所写的王葡萄,“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刚认识郑姐时,想象着她应该很累——连聊天时都在不停歇地干活,怎能不累?后来我发现,她一点儿也不累,反而是我,一个懒得让人怜悯的人,很累。因为对于我来说,在干一件活之前,要先调动“我要干活了”这样一个意识,然后开始付出“那么我一定很累”的心理成本,把以上心理活动进行了一遍,才硬着头皮去干一件小活——活还没开始干,我就已经累坏了。
郑姐则刚好与我相反,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活,就已经把活干完了,轻轻松松,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她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干活,甚至不耽误她和别人聊天,不耽误她谈论房价和装修。她是一个在干活时浑然不觉的人,不管是在她自己家还是在朋友家,这都是她的常态,她既不觉得自己有多勤劳,也不觉得自己有多热心,当然更不觉得自己忙和累。
就在我几乎要用“禅意”之类有文化深度的词来概括郑姐的生活状态时,我又想到另一个浑然不觉的人——我的伯父。伯父浑然不觉的方向与郑姐不同,那就是他对物质环境的感觉。
他们这代人的节省习惯是很普遍的,无须我多说,读者自能想象。我特别想举的一个例子是,在广州炽热而漫长的夏天,他竟然可以不用空调。
因为他的子女皆经济状况良好,他本人更是早早实现了财务自由,不存在买不起空调的问题。而他看起来近乎自虐的节省,简直就是陷子女于不义。
但是伯父这人脾气极倔,子女强行给他购买的东西,他坚决不用,既不惮辜负了子女的一片好心,也不在乎显得子女对他无情。出于对这种个性的欣赏,我好奇他对空调一事的真实感受。很快我的调查结果出来了:他确实真的不觉得热。
他好像对热无感。在最热的那几天中午,他会用清水擦一遍竹席,拖一遍地板,再打开一把落地扇。我在炎热的午后拜访他,只见他怡然自得、愉快清爽,并不是在强忍炽热。他只是觉得“没你们说的那么热”,他不需要“更凉快”,即使这个“更凉快”很容易实现,他也不去刺激自己的这个欲望。
我于是猜想,自己之所以觉得热不可耐,是因为我已经唤醒了这种欲望。我没有伯父那种浑然不觉的精神。
一个浑然不觉的人是多么幸福。他轻松放弃,不需要经历我所揣测、所设想的困难。他也可以不以别人的感受为参照物,因为他自己的浑然不觉就可以另设坐标——没必要因为别人都说热,所以自己就真的觉得热。
我们从小听到的那句老话“无欲则刚”,我总以为是在形容牺牲者,其实它是在形容享受者。他们享受了自己因为无欲而变多的自由。
你会说:“要是人人都像你伯父这样,那我们的社会经济怎么发展?文明怎么进步?”我的一位研究生物学的朋友说:“要是不肯定人类的物欲,人类现在还在树上趴着呢。”但人类是多么复杂、内心多么丰富的生物,人类的魅力就在于其欲望和思想的双重发达。
与其说我在为节欲者辩护,毋宁说我在赞美钝感。经济发达使我们敏感,我们因为体会更多、见识更广而不断地提高自己对生活的要求。敏感使人丰富,可以让人感受更多、看到更多;但钝感也令人拥有另一种丰富,可以让人因为浑然不觉而不受外物阻挡。
我也珍惜自己幸存的浑然不觉的精神。郑姐浑然不觉的方向是干活,伯父浑然不觉的方向是物质环境,我则对脏、乱、差有着令处女座朋友抓狂的适应性。
有一次,我与一个处女座朋友旅行,她不但能一眼看到垃圾,还能想象出看似卫生的食物可怕的来路。我觉得这份敏锐和想象力很有趣,一切感受丰富的人都令人欣赏。但与此同时,我也默默庆幸我尚未触发自己的洁癖,它使我能轻松地吃下各种可能被苍蝇叮过的饭菜,毫无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