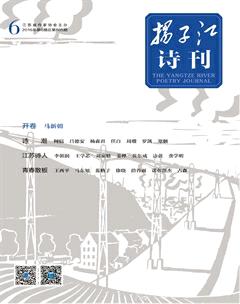心灵疼痛的“白纸黑字”:庞余亮诗歌印象
在与众多熟悉或陌生的写作者的精神交流和对话中,渐渐结识了文学领域的“全能选手”庞余亮。他自如而有力地穿梭于各种文体之间,小说、散文、童话故事样样来得,并且均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在细读过他大量诗歌文本之后,我发现他本质上更是一位诗人。这种“认定”并非对庞余亮诗歌之外作品的贬损,而恰恰产生于其他文类中栖居的诗性深度和感染力,在它们那里无法宣泄和表达的情感,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诗中寻找到答案。所以不妨说,诗歌是庞余亮文学创作的策源地,深入解读其诗歌作品,将会带来对他整个创作认识的本质性飞跃。
在一定程度上说,庞余亮的诗不是那种能够一目了然的愉悦类型,而属于一种难于解读的“困难”之诗。它从不放纵情绪,也不刻意制造阅读的快感,甚至不向大多数读者敞开心扉。潜心于艺术本体的沉稳打造,和流行、时尚趣味的自觉性疏离,使庞余亮虽然不像许多“大红大紫”的诗人那样耀眼,但他诗歌的品位却绝不比他们逊色;而且在情思的深度、心灵的内视性和文本的寓言色彩等方面,有着他人难以模仿和企及的独到之处,在诗坛上有着相对理想的辨识度。
一、疼痛的心灵内视
新世纪近二十年的新诗创作和批评,事实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某种不大不小的误区。即我们在评价一位诗人的创作时,往往急于确定诗人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一方面来自于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习惯和水准,另一方面则关乎着诗人传情达意的方式。客观地讲,这样的寻找标准和方式无可厚非,它或许是我们厘定一位诗人在诗坛位置的基本手段。然而这种通常十分有效的方法,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诗人的思想深度、高度及与情感、语言的融合程度。其实,那种克制而又具思辨力的内在意蕴,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诗歌风格,一位诗人的思想往往决定着其作品质量的上限,这种上限既指思想层面,也包括艺术表现因素。庞余亮的诗歌有着不凡的思想魅力,只是这种魅力并不容易领略,甚至许多读者始终无法参悟到其深意,其原因可能缘于它从不直接袒露情思;而是十分注重思想层次的递进和跳跃,思想、情感和形象三位一体的浑融,这种追求虽然在客观上提升了诗歌的阅读难度,把一批读者挡在了诗歌的门外,却也拉长了文本的理解过程和距离,生发出了更开阔的审美再造空间。所以,找到庞余亮思想的切入口,也就成了俘获其诗歌魅力的关键所在。对此,“空对空”的冥思苦想是靠不住的,逐字逐句的“拆解”似乎也很难奏效。从诗歌文本的阅读效果看,庞余亮诗歌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一个是无处不在的“疼痛感”,一个是经常出现一些身体性意象,我们只有从这两方面入手,才能精准地体会到诗人神奇深邃的情思世界。
说起文艺作品的“疼痛感”,难免让人联想到那些能够刺激人体感官神经的文字和画面,然而这种疼痛虽然具体可感,却因为过分追求生理刺激,终究要落下成。庞余亮诗中的“疼痛感”则主要来源于诗人的内在心灵,诗人用语言传递的并不真的是感官意义上的“疼”,而是对于自身、人性、世界深思熟虑的某种主观经验,这种经验使得读者在接受的瞬间能够触摸到诗人内心的苦恼、疼痛乃至愤怒。并且,根据读者理解能力、感受能力和人生阅历等阅读准备因素的差异,诗人的“疼痛”经验在读者的审美过程中,完成或减损或增强的二次加工,从而使诗人的“疼痛”经验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思想意蕴,和因人而异的多重启发性。比如《吞针记》一诗:“拔根头发做根针/已是传说。/这年头,梦不到/低头磨铁杵的母亲/仅可感到沉默的铁杵/在焦灼之洞里/慢慢下沉。越来越少的耐心/已遮不住/日渐荒芜的身体。/还可继续表演吞针/缝棉被的1号针/比纳鞋底的2号针勉强/在吞下3号钉衣针之后/还佐了一口残茶。/更短小的4号绣花针和5号串珠针/竟也吞咽了许久。/好在傍晚的风突然转向/吹干了额头上的汗水/子夜时分/还有余力在一张纸上/吐出藏在舌下的/那根锈蚀之针”。诗人描写的显然不是一场真正的吞针表演,读者自然也不会真能感受到吞掉一根1号针的痛苦,但读过全诗依然会有如鲠在喉之感,诗中身体的荒芜、情绪的焦灼自不待言,诗人吞下的五根针粗细大小各异,应是生命中诸种烦恼苦痛的化身,“额头上的汗水”足见忍耐之艰,最后“藏在舌下的锈蚀之针”,恐怕是指那些不吐不快却又无人问津的情愫,化而为诗略抒愤懑。在这里,诗人把人生的种种苦闷具象化为“疼痛感”十足的吞针表演,明知艰辛却只能默默承受,于灯火阑珊处稍放悲声,人生悲凉可见一斑。比起这种比较明显的“疼痛”,《苦嘴》可以说笑中带泪,作品以三种语言讲述一场暴雨灾害,一种是农民的语言:“二哥说,在芒种后再下雨多好啊/可老天爷从去年秋天/就用这雨水搓绳子/越搓越长,越搓越来劲/算起来,这雨绳子做成的鞭子/应该算到去年秋天/雨鞭子推迟了晚稻的收割”;一种是气象部门的专业用语:“受高空低槽和切变线影响”,一种是诗人的语言:“麦田的新衣服”。二哥说天气预报的话听不懂,“新衣服”早已成了“烂衣服”,泡烂了庄稼,看似如饭后闲谈的诗句,细细品味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感觉,身为农民的二哥面对暴雨灾害无能为力而又不失风趣地调侃,内心的焦虑和无助在短短数语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诗歌语言在切实的灾难面前简直成了某种讽刺,诗人此刻的尴尬也就可以理解为文学悲观命运的象征。诗中人物的痛楚无以名状,但诗人依然以形象化的方式将其客观地记录下来,这种“疼痛”书写不是想单纯地引发读者的同情,而是对于命运的捉弄在逻辑上无计可施、难以逃脱的那种“疼痛”。还有经常在庞余亮诗中出现的“行军的蚂蚁”“翻滚的落叶”和仿佛会说话的“白纸黑字”等意象的设定等,都与一般的痛苦展示有所不同,也能给读者带来一种超越感官的思想“疼痛”。
庞余亮诗歌在意味探索上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就是不断闪回着嘴唇、眼睛、额头等有关身体的意象。按照西方新批评派的理论,一个意象在一个诗人的一篇作品或多篇作品中反复出现,就渐渐积累了成一种象征的含量,上升为“主题语象”。庞余亮诗歌让这些身体意象复现的行为,在深层心理上透露出诗人比较执着的建立、反思自我形象的欲望和诉求。它也决定了庞余亮的诗有着较为强烈的内视倾向,更为注重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出现频率较高的嘴唇意象就特色十足,“我所盼望的曙光总是最先看见/那疲倦的屋顶,之后才是那些惊恐的额头/以及粘满粥皮的嘴唇(《疲倦的屋顶》);“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厚嘴唇/命运也是厚嘴唇”(《那么多那么多》)“还有被碎瓦逼成凹形的土豆/它在坚忍中长出了一张泥嘴唇/——多好啊,我已经活过,我终于说出”(《小札记》)……诸多“嘴唇”意象可谓匠心独运,它承载了多种内在情绪的表达之责,同时它的细微动作和变化,也成为诗人内宇宙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某种缩影。在这些作品中,嘴唇有时飞速地表达情感,有时只是苦涩时微微颤抖的微笑,有时则是对人生或世界的嘲弄,这些无不在隐约间标示着诗人对于自我的哲学认知,其中又不时掺杂着对于从生活琐事到人类命运的深远思考。当“嘴唇”出现时,诗人的情绪与思想往往不期而遇,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定这种表现方式是诗人写作技巧的戛然独创之处,但从诗的情与思的高度融合中可以断定,独特的心灵内视已成庞余亮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本能,普通的嘴唇意象也被诗人纳为外化精神疼痛的有效途径。
二、生活内外的寓言故事
诗歌文本总是或隐或显地凝聚着诗人的情绪信息和人生态度,阅读诗歌的过程,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感受诗人精神世界的过程,一首好诗,不仅仅是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表达,更是对宇宙、世界和人性中某些问题的形象解答。一首有意义的诗,应该像一扇神秘的门,优秀的诗人不用也不会告诉读者门后有什么,而是通过特殊的情感和形象,引导读者去寻找打开那扇门的钥匙。如果把这种功能隐喻为好诗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庞余亮的大部分诗作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精品,因为他善于在诗作中,以相对诗化的方式,自如地传达自己直接或间接、与众不同的人生体会与经验。
在感受了庞余亮诗中俯拾即是的生活“痛感”之后,有必要搞清楚庞余亮诗中究竟隐含着诗人怎样的“生活”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从诗中的“疼痛”想当然地推导出诗人的悲观,因为能够正视和挖掘“疼痛”,以一颗平常之心面对创伤,本身就是一种乐观、通达的表现。在人生观的表达方面,庞余亮的诗歌并不拐弯抹角,有时甚至是直抒胸臆的,像“一场生活过后,就像一场麦收后/母亲总是领着我们弯腰拾麦”(《 一场生活过后……》)、“月光是日子的灰烬/未燃尽的是对生活的热情”(《遍地是心灵的碎银……》)、“最疼痛的十二点/我们要做生活的好儿女”(《弃婴》)。这样平实直白的诗句,把诗人面对平坦抑或坎坷生活那种积极向上的心绪抒放出来了。庞余亮更善于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去攫取诗意,这让他的诗具有明显的亲切感,同时因其高超的诗化能力而获得了某种艺术审美的光晕。如《哗啦一声……》:“哗啦一声,倒塌的家具店里/那些沙发背上倚过的头颅/椅面上烙过的屁股印/统统移开了/他们的占领……老灰尘老木头的味道里/多了一些类似/青春骨折的伤口/其实,那也是缺了钙的陈腐/哗啦一声,木头腿/哗啦一声,木头手/哗啦的木鼻子,哗啦的木尾巴/还有哗啦的小木凳/早不明去向”。由家具店里老旧家具的倒塌开笔,联想到同样衰老的自己,“哗啦一声”具有十足的生活气息,甚至不无幽默感,但当写到诗人的手脚都已经“哗啦一声”的时候,又让人难以释怀。生活中的小细节、小声音,在这里成了诗人诉说衰老感受的突破口,看似简单易懂,实则需要极强的审思生活经验的能力方可进入。另一篇《淮河》则又有一种样态,诗人在淮河边看到“那些船不仅会运煤/还会输石子、钢筋、面粉和性”,目送它们“吃水线很深地向北驶去”,以这种近乎于白描的手法来叙述直接经验其实只是铺垫,诗人的意图在诗的后半段才逐渐表露,直到诗人说:“那条黑暗中发着幽光的淮河/看见痛苦的幸福的我/它就会鸣笛致意”,观察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开始突然调换,诗人自身反倒成了一幅风景,这不仅是情景辩证关系处理的高超技艺渗入,更是对日常生活经验诗意提升的超拔能力外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寂寞时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在玉米地的中央》《龟》《小团体之歌》等直接从日常生活经验土壤中生长出的精神花朵之外,庞余亮还有不少作品源于诗人的想象机制。相比于有些诗人故弄玄虚的想象方式,庞余亮这类诗歌依然保持着真诚自然、朴实无华的抒情风格,它们一方面带着真的功能和形态却并非实有的面貌,验证了韦勒克、沃伦任何作品都是作家“虚构的产物”的理论,具有艺术的真实,另一方面又具有某种意蕴高深的寓言性质,情趣别出。比如《红字》:“在狱中,第一年是痛,第二年是痒/第三年就成了顽固性的癣/必须镇压,必须在黑暗中用力抓挠/必须把皮肤抓破,必须溃烂/必须学习别的犯罪方//第四年我不得不努力减刑/第五年我的癣已遍布全身/第六年我学会手谣和装病/第七年我已经可以控制另一部分新犯人/第八年我终于忘记了我是谁/第九年词语们和我一起刑满释放∥我终于放弃了写日记的习惯/但脸上的红字再也不能抹去”。生活中的诗人并没有经历过牢狱之灾,所以文中之狱应为一种隐喻,或许是指人生中某些难以承受的困顿危局,整首诗仿佛是一个寓言故事,写故事的主角在狱中逐年堕落最终失去本心的过程,而这恰恰暗合了生活中良知和人性的逐步沦丧。再如《我听见了骨头》,全诗凭借诗人的想象铺就而成,“我听见了肋骨的手风琴穿过了我的胸膛/我听见了指骨的笙抚摸了我的双手/我听见了髋骨与脊柱的吉他指挥着我的步伐/我还听见肱骨的笛声”,幻象思维的跳跃中,使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可能出现的“骨头交响曲”被奏响,路向纷纭,神奇异常,赋予了诗歌一种梦真交错之美。相似的作品还有《土豆喊疼》《废柴记》《蓝光》等,这些作品在看似荒诞而无逻辑的语言外表下,传达的多是对深刻复杂的生命本质问题的思考,有些颇具神秘的色彩和朦胧的旨趣。
三、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调试
思想层面的深刻挖掘和生活经验的精准把握,有赖于庞余亮的文坛“多面手”身份,这种身份决定他能够在创作中使各类文体汇通,形成一种具有良性文本互涉结构的创作体系,成为一名风格特殊的诗人。同时,这种身份也使庞余亮更加清楚,不论是文体间的结合,还是每种文体的独立打拼,都必须以创新为最高旨归,像有个性的人才可爱一样,在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调试中,练就、确立属于自己的风格型范。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他是成功的。
庞余亮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推出了几组高度个人化的独特意象,它们在用法和含义上都具有着较强的辨识度。其中,出现最多的当属嘴唇、额头、眼睛等身体意象,这是诗人心灵自视的一个必要途径,前文已有交代,这里不再赘述。另外像“兔子”这个动物形象出现的次数也比较多,并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它总是以独孤、寂寞、无助的身份出场,然而又从来都充满活力。在纪念海子的诗作《比目鱼》中,诗人写到:“诗歌之兔已被复制成小说之肉/我已被复制成我们/相同的生活,相同的人在死去。/在拥挤的浑浊的车厢里,/十一年一晃而过。”这里的“诗歌之兔”应该指喻着生命中的诗意和美感,“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诗意的化身。庞余亮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不让“兔子”以洁白无瑕的慵懒的玉兔面貌走进读者的视野,而是把它描述为在原野上奔跑的灰黄色的敏捷的生灵,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耐人寻味。再有诗人钟情的“白纸黑字”意象,也频繁在诗中光顾,“把这些有恩于茫茫雪地的黑字/扫到一起,就是一个/不便说出的窟窿”(《白纸黑字》)。在奇绝的想象力敦促下,平日里普通的白纸黑字在这里获得了不在普通的品性,它看上去庄重、醒目,仿佛带着可贵的思想重量,它既可视为精神疼痛的烙印,也是诗人作品孕育和创作过程的写照。这些个人化的意象已经成为庞余亮诗歌的标签,具有着相对稳定的内涵和作用。
庞余亮善于也乐于在诗中添加、经营色彩,这往往成为庞余亮某些诗歌的点睛之笔。其实庞余亮诗中的绝大多数句子,是没有色彩属性的,诗人也常说自己写的诗就是“白纸黑字”,这可能源于诗人不饰辞藻的习惯,因为诗句中修饰成分有限,庞余亮的诗也从不以浓墨重彩示人,于是诗人仿佛“妙手偶得之”地赋予诗句色彩的神来之笔,就会让整首诗焕发出新的生命气息。如在《多少亡灵在安详地散步》中有这样一句:“最终它们还得像我一样回来/坐在一只无名坟包上/学习一朵野菊花羞怯的蓝”。“蓝”作为诗的结尾,也成了全诗最出色的一句,只用一个“蓝”字,就把全诗沉郁的格调凸显得更加鲜明,而且这里的“蓝”绝不仅仅是色彩上的蓝,于是与之前的文本内容相呼应的意蕴,也由此一字延展开来,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妙笔,颇有古人“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妙趣。再如《瓷寿星》中的一句:“有时,伊就是真理/就像伊的白胡子、红嘴唇/惟有一知半解/才可滔滔不绝地说”。一白一红两种颜色,就把寿星的形象勾勒出来,然而与前后文配合后,白红两种颜色就拥有了代表公平慈祥的意思,可阅读它时也不难感受到诗人对寿星品德的些许质疑和思考,这样,红和白两个颜色在一句诗中,事实上就可能具有了三重不同的意味,诗人庞余亮超强的语言操控力由此可见一斑。
良好的语感、成熟的思想和冷静克制的情感,共同铸就了庞余亮诗歌语言显豁的连贯性。他的诗几乎不可以从中间的任何位置断开,语词之间既有强烈的相互附着性,每个语词又能在必要处跳脱出来,这种有“弹性”的诗歌语言难于模仿,煞是奇妙。因为它兼有小说语言的连贯和诗歌语言的跳跃,其背后是诗人自由穿行于两种文体之间的挥洒自如的语言逻辑。如“我不能不拒绝随之而来的夏天/我们曾经的爱,我们曾经的死亡/悬满了枝头//而生活是一只巨大的苹果虫/在我的身体里不停的咀嚼、排泄和生产/为了宽恕它,我们砍下了整整一座疼痛的苹果园”(《弯曲下来》)。仿佛从命泉里直接流出的语汇和句子,不扭捏造作,不拐弯抹角,它和朴素的拟人、比喻手法对接,把生命的疼痛和无奈和盘托出,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冲击力。再如“活着并倾听——阔叶林的落叶就像男人坠地/细叶林的落叶就像女人坠地/整整一夜,无数个男人和女人/不停的坠地。//就像一夜秋风。我看见的枝头上都空空如也/一场生活结束了/必须用死来纪念——之后是寂静,未亡人的寂静”(《活着并倾听——》)。不能再平朴的语言,不能再简单的比喻,经诗人的灵魂梳理后缓缓、轻轻地道出,但却有如胁迫,生活和生命的滋味令人动容,平静而沉重。庞余亮诗歌的语言自然简洁,极少使用欧式长句,多用内容的奇特来体现诗歌文本的跳跃性和陌生化气氛,几乎不在语言层面上使用生词、偏词与怪词。同时与生俱来的良好语感,让庞余亮诗歌在语词运用上走笔自然,读者能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层层递进的语言动势,这股跳动的趋势会引导读者不自觉地完成阅读过程,获得多层次的审美享受。
不可否认,庞余亮的诗歌创作虽然已经进入了一种相对成熟的境界,但并不是说没有缺憾。他的某些作品如《蓝光》等,就过分追求意义指涉的含混和朦胧,即便用专业的眼光分析和打量,也存在着过于复杂难懂的嫌疑,这样的作品如果多到一定的数量,就会严重阻碍读者的接近、阅读和接受。其次,庞余亮的多数诗歌在气度上沉稳克制,在思想性和情感表达方面超人一等,但是如果能够再增加一点儿艺术的洒脱,底蕴的大气,或许会更有震撼力和可读性。总之,作为一位优秀的诗人,庞余亮博得的声誉和位置可谓实至名归,他写作态度的内敛沉静、严谨端正,和诗歌文本的扎实深邃、自然从容,已然对当下浮躁喧嚣的诗坛构成了一种绵长的启示。作为至今尚未谋面的读者,我相信,有坚实的基础作为依托,在诗歌的路上他会走得更远,更稳健,更精采。
罗振亚(1963-),黑龙江讷河人,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与先锋对话》等专著九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三百余篇。曾获天津市、黑龙江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扬子江诗学奖,《星星》年度批评家奖等多种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