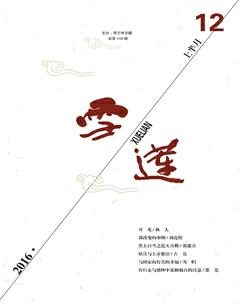一个人的森林公园
卓美
确切地说,清晨六点半从玉舍森林公园宾馆出来的时候,我忍不住一阵窃喜,这窃喜就像小市民占到某种便宜一样。独自一人漫步的森林公园,太过奢侈珍贵。
顺宾馆后的山路蜿蜒而上,一路走,一路回头流连远处万山之中的云海。泛着亮光的云海表面平整无比,像深不见底的银水。喜鹊、乌鸦、酒醉鸟、翠鸟的声音不绝于耳,稍不留神,惊扰一只喜鹊从松树的顶上扑棱棱飞出径直朝着云海而去,我不由得担心,这懵懵懂懂的家伙会不会掉进那云海深处。
路边的斜坡上长满葱茏的橛草,在高大的松树底下有金色的萢,那诱人的小东西上挂满水珠,只懊恼手掌不够宽大,无法承载一大把的回忆。甜滋滋的味道太过熟悉,这原本是童年的风物。阔别已久,再与这萢果相见时,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几十年前的放学路上,我也是这样因为一蓬金色的萢而欣喜若狂的,也是这样迫不及待将萢往嘴里送的。只是,相对于童年,如今的我已经不再将解决温饱作为理想,已经不再坚信金钱和地位有万能的力量,可事到如今,我却偏偏缺失儿时的那份无畏与坚强。就像现在,内心越是孤独,就越钟情于一个人的山河。岁月落满脸庞,一份前所未有的脆弱无端衍生。越来越依赖一道体贴的目光,越来越害怕被亲情、友情所辜负,害怕被挚爱的人敷衍。联想到这些,在风徐徐而来时,有莫名的眼泪滑落。
我决定不再往山上走,停步于松树下看一幅大气磅礴的丹青水墨画卷。云海较刚才更亮,像苍白的心事沉在晨曦中,那些从云海中露出来的山顶是深深的灰,而云海边沿的云却泛着灰的浅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颜色与之相争。
沉思的瞬间,一些深灰的雾一抹抹地朝侧面的山上悠悠而来,就像一种撤退,在放弃原来的阵地去追寻高远的梦想,也像一种升华,将生命中的浅薄之处留在了旧地。在故乡的草原上,每当傍晚天气变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雾,那草原上的雾用野蛮一词来形容都不算为过,它们有铺天盖地的气势,有覆盖一切明媚的决心和力量。小时候,总爱在那些朝山下倾泻的大雾前面狂奔,也总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大雾撵上并严严实实地包裹其中,以至于每每都要到天黑才能摸进家门。森林公园的雾大不相同,它们身姿曼妙,从容优雅,朝山顶漂移的时候,像一群文采出众的诗人去参加一场高端的笔会。森林公园的雾还有一种通达和坦然、有一种能放手昨天迎接未来的洒脱。我好像得到某种启示,我是不是应该向一片雾学习,在天地之间,走好自己的深浅。
天空与大地依然是深灰与浅灰相辅相成的画面,原来,水墨画不是丹青手自创的着色技巧,丹青色,是江山原本的基调,是乾坤真实厚重的底色。在森林公园,我站在一幅丹青水墨的画卷里,我生平第一次成了画中之人,成了景中的一棵树、一朵花、一根草、一缕透明透亮的风。
云海开始动荡,开始瓦解,我不知道是阳光掩盖了消沉,还是那些数以万计的云片已经在悄然间融化在了初升的光芒里。看来,这世间没有解不开的心结,也没有挪不走的苍然。自然如此,生命亦是。
太阳出来了,大地一派生机。耳畔传来文友高声模仿乌鸦的声音,模仿得很地道,可这模仿声略显粗糙和嘶哑,缺少圆润与干脆。再过后,乌鸦一度保持缄默。我不禁莞尔,看来,关于学习与模仿,关于对万事万物的理解,我们还需要好好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