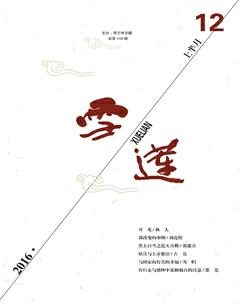怀想水磨坊
茹孝宏
水磨坊是人类由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驿站,是中国乡村渐行渐远的风景。故乡的水磨坊伴随了我的少儿时代,是我记忆深处的一道风景,也是我时常怀想的一道风景。
我的故乡在湟水谷地东部的一个小镇上。溶溶湟水千百年锲而不舍地切割,将故乡小镇抬升到一个高出河床许多的台地上。水磨坊要因地以造,依水而建,水流磨转,水止辄歇,所以故乡的水磨坊建造于小镇南面较远的湟水河河滩的树林旁。
那片很大的河滩里,有一条人工开凿的约2米宽的水沟,水沟上游与湟水衔接,引来湟水推动磨轮,因此称这条水沟为磨沟。这条磨沟顺着湟水的走势,上半段自西向东流,下半段则折向南淌,临了又涌入湟水的怀抱。就在磨沟下半段流水落差很大处,一座水磨坊凌空而架。水磨坊所在处磨沟宽而深,称之为磨塘窝。这座水磨坊共有4间,其中3间悬悬地横跨在磨沟之上,称之为“水间”;只有磨沟西岸的一间连着通向小镇的道路,称之为“旱间”。磨坊的梁柱檩椽都是木质的,下面铺的是木地板,“水间”的墙体也是用木板镶成的,这主要是为了减轻“水间”的重量和保持坊内的干净;“旱间”的墙体是用树枝编成的篱笆,上面抹了一层厚厚的泥,表皮抹得很光很细。“旱间”中盘有板炕,还修有锅灶等。在“水间”中,装配有磨盘,由上、下两扇组成,直径约2米。上扇磨盘用4根粗绳固定在梁木上,各绳中间插1根撬杠,以调节上下扇磨盘吻合的松紧度。下扇磨盘用“Y”形木墩固定,并通过木质磨轴连接到磨坊底下的磨轮上。磨轮也是木质的,形似旧时骡马拉的大木车车轮。利用磨坊所在地这段磨沟水头高落差大的地势,斜置着一个上宽下窄的木质水槽,称之为磨糟。磨槽上口衔磨沟,下口悬空于少半扇磨轮之上,以其流速之快、冲力之猛来冲动磨轮转动,进而带动下扇磨盘转动。磨槽下口设有闸板,绑着钢丝绳直通磨坊,从磨坊提起绳子开闸,磨则转动;放绳闭闸,遏制住磨槽下口处流水的冲力,磨则停转。水磨坊里共有两盘相同的磨。
磨面时,将粮食倒进上扇磨盘上面的木质大方斗里,磨盘转动时粮食经磨眼摇落到下扇磨盘上,再经磨齿粉碎成齑粉,从上下磨盘的罅隙里喷洒到地板上。其中磨眼口处有调节下注粮食粗细的活动装置,俗称搅曲把。磨盘转动前就要往大方斗里倒进粮食,且要及时续上,以防空磨转动时损坏磨齿。从磨盘罅隙里喷洒到地板上的齑粉尚未将面粉和麸皮分离开来,所以在“水间”还有罗面设备和工具。将两根上面取平的约3米长的椽木,两头用约1尺长的比擀面杖稍粗的木棍连接固定,组成一个长方形木框,再在四角各按上约1尺多长的木腿,就是一个罗面架。罗面时将从上下扇磨盘罅隙里喷洒到地板上的粮食齑粉,揽到两个大大的面罗里,置于罗面架上,罗面者坐在罗面架前的小木凳上,两手各捏住一只面罗边框,拉动两只面罗一撞一离,如此反复拉动,面粉就不断地被筛在了木架下面的地板上;如此反复拉动数十次,两只面罗里的多数面粉就被筛下去了,剩下的麸粒又要倒入磨盘上面的大方斗里重新磨粉,重新罗筛;如此反复三四次,才能将粮食里的面全“磨”尽。磨粉和罗面比较来看,磨粉以水为动力,具有一定的机械化功能,人做好协助工作就行了。而罗面则纯粹是手工的,是颇费些力气的。
水磨坊是富有诗意的。夏秋两季,站在磨槽上口处的磨沟沿上观望,但见高悬水上、凌空而架、杨柳掩映的水磨坊显得空灵飘逸、古朴典雅,独具风格。若逢多雾天气,那仄仄斜斜的水磨坊恍若浮动在雾岚之中,飘忽于烟波之间,又恍若一只轻轻舞动、款款飞翔的硕大无朋的风筝。从磨槽飞泻而下的那股粗大的湍流,冲动着磨轮急速旋转,哗哗作响,加上点缀其间的清脆婉转的鸟叫雀唱或蝉噪蛙鸣,便组成了一部悠闲而恬美的管弦乐曲。那从磨轮上溅起的水花像雪粒、像碎银、像珠玉一样溅洒在四周,既给人以视觉的快感,又引人以美好的遐想。倘或步入磨坊,那磨盘的转动则少了磨轮转动的雄风和气势,而多了些阴柔和细腻,那圆圆的磨盘转动时发出咿咿呀呀、嗡嗡呜呜的声音,仿佛一首始终强调着一个主旋律的乡村歌谣,从上下磨盘罅隙里喷洒着的粮食齑粉俨然是和顺的春风鼓起的乡村少女的素裙。倘或闭闸,磨轮停转,水磨坊则显得异常静谧、格外安宁。因为她远离了市井的纷扰、避开了众人的喧闹,间或听到的清脆响亮的鸟叫雀唱或蝉噪蛙鸣,使水磨坊显得更静谧、更安宁而已。南朝梁诗人王籍诗《入若耶溪》中“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句子所咏叹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
水磨坊是充满乐趣的。那时候每年家里要磨七八次面,尤其是夏天家里常常断口粮,父亲想方设法从这里找来一些,从那里弄来一点,去磨面的次数则更多。多半是父亲拉着架子车去磨面,我去给父亲做帮手。水磨坊离我家远,加之那时农家孩子在家干的活儿多,平素绝少有专门去那里玩耍的机会,而水磨坊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每当要去磨面,我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不亦乐乎。尽管水磨坊里有两盘磨,但由于故乡小镇户多人众,加之周边村庄的一些水磨多建于沟壑溪谷上,常因动力水源不足而停转,所以赶骡子、驾驴车、拉架子车来故乡水磨坊磨面的农人常常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在“磨务”(即待磨粉的粮食)很多的情况下,我跟父亲去磨面时按照前来后到的惯例要等待好长时间,有时得等上半天时间。这段闲暇时间便由我和小伙伴们自由支配了。我们钻进水磨坊旁边的树林深处追野兔,爬到树上在雀窝里捉雀儿,跑到磨沟上游捞鱼儿,其实雀儿捉住的机会很少,鱼儿因无工具捞着的概率更小,至于野兔根本就没有捉住过,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感到其趣也多多,其乐也融融。因为由快乐天趣兴之使然而激活的生命过程本身就是美好而亮丽的。
磨面过程中最主要的有两样活,一样是将地板上拌有少许水的粮食揽在“升子”(即小型木质方斗)里倒在上扇磨盘上面的大方斗里,磨盘转动过程中干这活有一定的危险性,磨主(即由大队委派的守磨人)和父亲根本不让我干,而只能由父亲来干,有时磨主帮着父亲干。另一样是坐在罗面架前拉罗罗面。本来拉罗罗面是一件稍带有技术性的体力活,但在我的心目中,拉罗罗面不仅很有趣,而且有一种干技术活的荣耀感和满足感。每当开始罗面,我就要和父亲争着罗面,虽然罗一阵就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仍旧不愿休息,最后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才不得不交给父亲去罗。但稍歇一阵,乏气消解,就又从父亲手里夺回面罗,愉愉快快兴致勃勃地罗面了。而在现实中,有很多“上班族”嘴上老喊着乏透了,累死了,真的就那么乏、那么累吗?我想肯定不然,乏不乏累不累的关键在于是否在所从事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以及是否遇到了一个能够激活心灵与生命状态的环境与氛围。
水磨坊是温馨的。磨主姓刘,父辈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刘三爸,我辈则称呼他为刘三爷。刘三爷个头不高,须髯稀少,脸上堆满了慈祥。每次我跟父亲去磨面,为确保粮食的出面率和面粉质量,刘三爷都操心得很周到很细致,诸如拌水的多少,粮食注入磨眼的粗细,上下磨盘吻合的松紧度,他都时时掌控着。刘三爷待我非常好。夏秋时节我跟父亲去磨面,他就会笑吟吟地从水磨坊旁侧小园子的杏树或果树上摘几个杏子或软梨给我吃,有时会拔一个花缨萝卜或胡萝卜给我吃。有时杏梨或萝卜尚未长足成熟,但在那时能吃上如此食物也算是享受了一顿口福。
为了尽量不耽误父亲出工挣工分和我的上学,有时我跟父亲晚上去磨面。这对我来说更是心之所仪求之不得的,因为晚上去磨面的人少,刘三爷也闲一些,磨完面后能在磨坊里美美地吃一顿刘三爷做的“夜晌午”,还能听刘三爷弹三弦。那“夜晌午”多半是做杂面干拌,抑或是揪一锅面片,但绝不是一顿普通的杂面干拌和面片。那时家里常常缺吃少喝,要不是年头节下或贵客临门,吃食多半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面条饭,且缺少油水,味道寡淡。而水磨坊与村里的油坊较近,刘三爷的青油瓶子里总是有油的,又有刚刚磨下的面粉,所以这“夜晌午”是一顿油油的杂面干拌或稠稠的油面片,还有供就饭的一大盘子菜。那时根本吃不上现在常吃的什么细菜,纵使贵客临门,水汆甜菜或洋芋丝,拌上蒜屑,炝上极少的一点油,就是招待客人最好的菜。有道是“甜菜拌蒜,皇上没见”,“洋芋丝拌蒜,城里人没见”。而水磨坊里的甜菜拌蒜或洋芋丝拌蒜炝着汪汪的油,比家里招待贵客的菜更香更美。所以吃油油的杂面干拌或稠稠的油面片,就着油汪汪的甜菜拌蒜或洋芋丝拌蒜,那感觉比现在吃大鱼大肉美馔佳肴不知要强多少倍。
吃完饭后,刘三爷就给我们沏上茯茶,敬我们喝,然后从板炕上方的墙面上取下那把三弦,嘣楞嘣楞地操拨起来。记得那把三弦很古旧,琴杆已被岁月的风尘剥蚀得斑驳陆离,三个琴轴的形貌和色泽也不尽相同,这显然是修补后留下的痕迹。刘三爷不会弹奏太多的曲子,每次都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首庄严中带有忧怨色彩的《满天星》,但我那时听他弹奏这支曲子,总是百听不厌,还始终有一种非常甜蜜、非常温馨的感觉。他将《满天星》弹上几遍后就会停下说:“这是一首从南凉王国宫廷里传下来的曲子啊。”他说这句话时脸上洋溢着无比的自豪和自信。后来我知道刘三爷的青年时代是在旧中国度过的,身世坎坷命运多舛。因此我常想,在那艰难困苦祸不单行的岁月里,刘三爷是否就因为会弹奏一段南凉王国宫廷的曲子而增加了生活的勇气?进而凭借这种勇气扼住命运的咽喉而顽强地活了下来?
刘三爷弹罢三弦后就帮我们往架子车上装好面袋、麸袋,绑好绳子,并看看我提的马灯里煤油有多少,如不多了,便续上些煤油,将马灯点亮后递给我,并在磨坊的一个墙旮旯里立着的大小木棍中挑一截铁铣把大小的木棍赛在架子车上捆绑面袋麸袋的绳子下面,以供父亲和我在回家的路上碰上狼时防身用,回家后作铁铣把用。然后父亲驾车辕,我提着马灯拉帮套,刘三爷在后面搡车,要帮着父亲和我拉的架子车走完磨坊门前那个长长的慢坡,并看着我们在马灯的光亮里缓缓行走,直到我们在一座小桥上拐弯了,他便远远地将手电筒朝我们一晃,表示他折回磨坊了……
我上初中三年级那年,故乡小镇安上了电磨。不久,水磨坊被撤了,没过多久,刘三爷也过世了。
今年仲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去故乡小镇南面的湟水岸畔漫步,走着走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故乡水磨坊的遗址。但见30多年前的水磨坊已了无痕迹,只有磨沟沟道依稀可辨。在水磨坊的遗址,生长着一片杨树,婆婆娑娑,郁郁葱葱,近旁刘三爷种植过果菜的园子里,长满了野草,密密丛丛,离离萋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