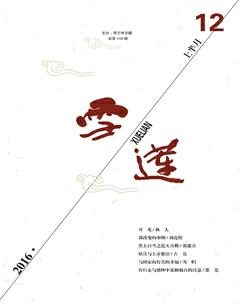耳 光
一
太平村治安特派员老鼓爬了三十多里山路才找到麻叔。他看到麻叔正光着油光黑亮的背壳在林子里嘿哟嘿哟砍杂草。老鼓想喊一嗓子,但是他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嘴一张竟发不出声音。他在一棵松树的荫凉下面一屁股坐下来,喝了一口随身携带的凉水润了润嗓子,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麻叔,派出所叫……叫你去一下。”
麻叔是太平乡自然保护区护林员,经常参加乡里的护林工作会议,也经常与乡派出所联系。以往开会,都是乡里打电话通知他,这次改成派出所派人来找,而且找他的是村治安特派员老鼓,麻叔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他停下来,拄着砍刀站在那里等老鼓走近,问他是不是派出所捉到偷树贼了。这段时间毛贼频繁盗树,派出所正在侦破此案。
麻叔的砍刀是一把长柄宽刃的弯头刀,刀身沾满了泥土和杂草。麻叔不擦自己的满头大汗,却用一块破布仔细把沾在刀身上的泥土和杂草抹干净,刀身立即在阳光下闪烁出蓝色的寒光。
特派员老鼓被刀光刺得眨了一下眼睛,神色有些不自然,回答也很云遮雾绕:“不太清楚,你回去一趟就晓得了嘛。”老鼓并不姓鼓,只是因为他患了一种全身长疱的怪病,脑袋和手脚都长满了鼓鼓凸凸的肉疱,像一个吓人的怪物,大人小孩都怕他,所以人们才叫他老鼓。乡政府和派出所都一致推荐老鼓当太平村的治安特派员,说老鼓不仅说话像打雷声音大,他的形象也吓人,这样的人做综治工作最合适不过了。
麻叔说:“老鼓,这天荒地远你还爬山越岭跑来干啥,打个电话讲一声不就得了?”
老鼓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抱怨道:“嘁!你那宝贝手机还不如一块破砖头,要能打通我还像被鬼追似地来回跑吗?”
麻叔不相信老鼓的话,老鼓平时为了好做工作经常讲一些吓人的怪话,于是他从腰间取下他的老年手机来看,果然没有信号,知道这回错怪老鼓了,马上抱歉地对老鼓打了一个拱手:“对不起,累你跑路了,进屋喝口水歇一下吧。”麻叔说的屋是松林里的一间茅草树皮屋,临时歇脚的,也可以住宿。
老鼓摇摇手:“不啦,派出所催得紧,叫你马上下山去呢。”老鼓这一路累得够呛不说,还一惊一乍地差点把魂都吓掉了。这一路三十多里,从山下到山上只有一条巴掌宽的茅草路,两边全是苍天古树和荆棘乱藤,密密匝匝遮天蔽日,阴森恐怖。老鼓不明白麻叔为啥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荒山野林里面生活几十年。换成是他,恐怕一天也呆不下去。现在这世道不太平,人为了利益和生存啥事都干得出来。另一个林区的护林员老王,就被偷树贼乱刀砍死了。麻叔还不晓得这事,因为他管辖的林区和老王管辖的林区离开几十里,两人平时很少碰面。派出所通知麻叔下山,就是与这事有关,老鼓不敢提前把这个消息告诉麻叔。老鼓本人也因为治安工作的问题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就放出话来说要灭老鼓全家。老鼓的家人就劝老鼓别再干这份差事,打算借着到大城市去治病让他辞职。
麻叔于是和老鼓一起下山。到了派出所,正碰上马所长值班,麻叔劈头就问是不是捉到偷树贼了?麻叔是乡里优秀的护林员,护林几十年,那些珍稀树种比如油松、罗汉松、红豆杉、铁杉等都是他亲手从幼苗护理成参天大树,一棵棵渗透着他的血汗,他对这些树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感情深厚。这些树被毛贼盗砍,他的荣誉和辛劳都被毁了,气得他像一只眼睛冒火屁股冒烟的老猴子,抡着大手啪啪搧自己耳光责怪自己失职。打过自己之后他又恨那些毛贼,发誓要狠狠踹他几脚,搧他几个耳光,以解心头之恨。
马所长见麻叔一来就问捉贼的事,便用复杂的眼神看了麻叔一眼,点点头。
麻叔攥紧了砍刀在地上一扽,扽得地板砰砰响,气鼓鼓地问:“贼在哪里?”
马所长被那刀的寒光刺得眨了一下眼睛,不乐地说:“老麻你拄着把刀在这里吼啥?也不嫌累。”
麻叔这才发觉自己有些失态,赶忙把刀放在屋角,搓着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嘿嘿憨笑。
马所长让麻叔在凳子上坐下,倒了一杯水给他,然后眼睛看着窗外,声音低沉地告诉麻叔,贼是抓到了,但是老王死了。
“老王死了?”麻叔大吃一惊,端在手里的水有一半洒在了地上。老王虽然和麻叔离开很远,但是一年总有几次和麻叔在一起喝酒,两人好得没谱,像同穿一件衣服的左右手。现在听到老王死了,麻叔未免有些兔死狐悲的伤感。“老王是怎么死的?”他紧张地问。
“怎么死的?总不会是自己在歪脖子树上吊死的吧?”马所长瞪了麻叔一眼,好像他是明知故问。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眼睛一翻说老王是被毛贼搞死的。
麻叔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嚯地站起身来,习惯性地伸手去抓砍刀:“老王是被哪……哪个狗日的搞死的?”
马所长被麻叔的动作吓了一跳,赶忙伸手做了一个拍篮球的动作,示意麻叔坐下。麻叔虽然坐下了,但是已经焦躁不安,好像凳子上长了刺,屁股不停地挪动着,没抓着砍刀的手习惯性地捏成拳头端在胸前,瞪着眼睛紧张地看着马所长。
马所长突然不吭声了。他点燃一支烟,吐出浓浓一口烟雾,他在考虑是否要把这个杀死老王的毛贼告诉麻叔。
“你讲呀,到底是哪个嘛?”麻叔被马所长的沉默搞得不耐烦了,他像一个看着热粥不能下口的饿汉,急不可耐。
马所长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毛叔,慢吞吞地问:“你真的想晓得?”
麻叔被马所长的眼神看得浑身发冷,怀疑是不是那刀的寒气传给了自己。他为啥这样看我?他平时审犯人就是用这种眼神的吗?可我又不是犯人。“你这样看着我干啥?”麻叔惴惴不安地问。
“我问你是不是真的想晓得是哪个杀伤死了老王?”马所长再一次问麻叔,语气像十二月下雪,冷冰冰的。
麻叔已经没有回答的勇气,只是机械地点点头。
最终,职业警察的冷酷性决定了马所长的回答,只是他的回答太重了,一句话就把麻叔敲木桩似地敲矮了半截,他说:“凶手就是你儿子。”
麻叔身子晃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所……所长,这……这个玩笑开不得哟。”
马所长黑着脸说,哪个和你开这种玩笑?我们叫你来就是通知你,这段时间你先在家休息,林区我们另外派人去看。
麻叔这才明白马所长为啥用那种寒冷的眼神看他。他脸上一阵刺痒,伸手啪地搧了自己一耳光,一只蚊子在他手掌上留下了一团腥红的血迹。
二
麻叔在派出所办完护林移交手续,步履踉跄地回到家里。
出了山麻叔才晓得,外面已经把毛贼杀人事件都传疯了,可他却呆在山里像聋子和瞎子,听不到也看不到。这事的经过是这样的:麻叔的儿子麻国民和几个毛贼去老王的林区盗砍油松,被老王发现,双方发生争斗。毛贼仗着人多势众,残忍地杀死了老王。随即,麻国民等人被警察拘捕,其他毛贼却负罪在逃,目前警察正在继续侦破此案。
麻叔下山后,一直呆在家里不敢出门,他怕外面人看他的目光,那目光像刀,比他的砍刀还要锋利,一下下戳在他的心上,流的是看不见的血;他怕听外面人的议论,那议论像一记记耳光,啪啪搧在他的脸上,搧得他头晕目眩。他想,都是自己平时惯坏了这狗日的,不该因为他是麻家的独苗指望他传宗接代而放松了对他的管教,这是报应呢。派出所叫他到县城去给麻国民送衣服和被盖他都一直没有动身。他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分不开理不顺,不晓得该怎么办。
麻叔不出家,却有人到他的家里来找他。先是司法干部来和他谈心,劝他不要有思想负担,护林移交是履行法律程序,要配合政府作好他儿子的思想工作,尽快说出其他罪犯的下落,争取宽大处理;接着是街坊邻居来看他,大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起,同过甘,共过难,说那狗日的再不争气也是他的亲儿子,打断骨头连着筋,千万不要丢下他不管,如果这样他就更加自暴自弃了。再说现在案子还没有完全侦破真相大白,万一要是麻国民讲江湖义气替别人背黑锅,那岂不成了冤大头?所以劝麻叔得赶快进城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麻叔考虑了很久,虽然觉得街坊邻居的建议有道理,但他对要不要到县城去看儿子的事还是犹豫不决,晚上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合上眼睛,忽然听到有人叫他:“麻儿!麻儿!”麻叔爬起来一看,见是他爹拄着拐棍站在他面前。麻叔想,爹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怎么忽然回来了呢?他急忙上前想搀扶爹,可是爹却拨开他的手,说:“麻家已经大祸临头,马上就要断香火了,你还在这里高枕无忧蒙头大睡?”
麻叔诚惶诚恐地说:“爹,您不晓得,您孙子成了罪犯,他不仅偷砍了千年古树,还杀死了我的老朋友,犯了王法,把祖宗的脸也把我的脸丢光了,这是麻家的报应啊。”
麻叔的爹把拐棍一扽,怒道:“胡说!就算是报应也是你造下的,谁让你对他从小就娇生惯养不教育好他?如果麻家的香火断在你手里,你就是麻家的罪人,你也无脸去见列祖列宗。”说着狠狠地打了麻叔一耳刮子,麻叔一激愣醒了,原来是做了一个噩梦。他赶快爬起来,到列祖列宗的牌位前跪下,磕头烧香,答应想办法救儿子。
坐在去县城的客车上,麻叔听到满车人都在议论这件杀人案,说是麻国民自己承认他就是杀人凶手,而且拒不交代其他逃犯的下落,把审案的警察都气得都拍了桌子。
麻叔也不清楚这些人是怎么晓得警察审案的内幕的,但是他觉得他们讲得像那么回事,因为他了解儿子的底细,这狗日的性格从小就像一头犟牛,认准了一条歪道会走到黑。按他自己的话来讲,这叫讲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下倒好,刀真地插到他的肋上了,可是痛的却是麻叔。这些话像冷水似地浇得麻叔背皮阵阵发凉。他习惯性地把手端在胸前,但是握的却是空拳。他头上几乎冒出火星子,连骂了几声狗日的,惹得左邻右座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他。
这时,只听有乘客说:“现在的年轻人真邪,啥事不能干就偏干啥事。”
另一个乘客说:“都是受了坏影响,电影电视上总是打打杀杀,明明是教人犯罪嘛。”
“千不好万不好,都是做爷娘的没有把自己的儿女教育好。”
车厢里一片唏嘘声。
麻叔觉得这些话都是车上的人故意讲给他听的,好像他们都认得他是麻国民的父亲。他感到无地自容,觉得众人在轮流搧他的耳光。噼里啪啦,耳刮子一记比一记响亮。麻叔尽管抱着头,但还是感觉到了疼痛和灼热,他在家里被干部和乡亲刚刚鼓起的一点勇气和自信被搧落得干干净净,恨不得从车窗口跳出去。车到县城还未进站他就下了车。
三
这段时间正逢严打,县公安局的刑警们白天查案,夜晚审案,忙得车轱辘似团团转。麻叔推门进屋的时候,几个刑警正围着一张图纸在研究什么。
麻叔咳嗽一声,说:“同志们,忙啊?”
他出现得很突兀,刑警们都有些惊讶。
“哎!”门卫在后面追上来,一把拉住麻叔的胳膊,说:“你这人是怎么搞的?这地方也是你能乱进来的吗?
“你刚才干啥去了?”一个刑警责备门卫,“现在才来补漏水桶啊?”
门卫摸了一下秃头,自责地说:“都是我的错。昨晚打牌熬夜,刚才眯了一会,没看见他溜进来。”
“你这是失职,晓得吗?”刑警黑着脸说,“看你还比较诚实,下次可要注意了。”
“是是。”门卫连连点头哈腰,“下次注意,下次注意,我这就把他撵出去。”
麻叔把胳膊一甩,挣脱门卫,说:“我有话要讲。”
门卫想不到这老头还这么犟,当立即火了,说:“吔!反了你了?”
那刑警对门卫说:“你先出去。”
门卫说:“行。”走了几步,又回头对麻叔说:“老头,出来别忘记补个登记啊。”
门卫走后,那个黑脸刑警用锥子似的目光打量着麻叔,见这个提着蛇皮袋的老头头发几乎脱光,下巴仅有几根稀疏的黄胡须,布满皱沟的脸如霜打过的秋苦瓜一样。他光着膀子,肌肉像烤焦的红苕皮,肋骨历历可数;背骨如一段弯曲的竹节;肩上、臂上都密布着暗紫色的疮疤;赤足蹬着草鞋,齐膝的黑布灯笼扎裤,腿肚上爬满了藤状的青筋。
刑警大概起了恻隐之心,叫麻叔坐下,为他倒了一杯水,问:“你有啥事啊?”
麻叔说找儿子。
刑警说你找儿子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这里是公安局啊。
麻叔说我就是到公安局来找儿子的。
刑警困惑了,他瞧瞧他的几个同事,知道这老头不可能是他们几个人的父亲,因为他们看到这老头除了惊讶之外都没有其它啥反应。他只好问:“你儿子叫啥名字?”
麻叔却不说话了。他胀红了脸坐在那里,像憋了一泡拉不出的屎,非常难受。
刑警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麻叔,催问:“讲啊,你儿子到底叫啥名字?”
麻叔吭哧吭哧张不开口,麻国民这个姓名像一块骨头卡在他的喉咙里,咽不下又吐不出。这小狗日的让他一张老脸没地方放呢,他想自己是不是就不该来这县城,不该来这公安局?这个想法一冒出来,他的脸就隐隐犯疼,这是被爹在梦里那一巴掌打的。他不敢怠慢,于是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地说:“我儿子他叫……叫……麻国民……”
刑警们听到这个名字,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一齐看着麻叔像看外星人。
一个浓眉刑警走过来,气呼呼地夺过麻叔手里的水杯,啪地放在桌上,凉水溅了麻叔一脸。
那个给麻叔倒水的刑警瞪了浓眉刑警一眼:“小李,你这是干啥?”
小李说:“刘队,这样的人就不配给他水喝。”
麻叔委屈地问:“同志们,我啥地方得罪你了?”
小李问:“你是麻国民的老子吧?”
麻叔说是啊。
小李说:“这就是了。养不教,父之过。你儿子不是好东西,我看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麻叔张了张嘴,一时无话可说。他觉得小李这句话比刚才溅在脸上的冰水还要凉,比他爹那一耳刮子还厉害,便用左手捂住脸,右手端在胸前握着空拳,低头无语。
刑警们大概在想,那个又臭又硬像茅坑里的石头似的麻国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父亲呢?
那叫刘队的刑警告诉麻叔,这里是刑警队,而麻国民被关押在看守所,他找错地方了。
麻叔说他想见见儿子。
刘队告诉他恐怕见不到。
麻叔又问他儿子到底是不是凶手?
刘队板着脸说:“别问了,我们正忙着呢,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麻叔出了刑警队,一路打听找到看守所,在接待室被一个肥头大耳的警察敲木鱼似地问了一通姓名、年龄、地址,最后问:“你来干啥?”
麻叔说看我儿子。
肥头大耳问他儿子是哪个。
麻叔说叫麻国民。
肥头大耳一听这个名字,像吞了一只苍蝇似地马上变了脸色。他把抽了半截的纸烟扔在地上,用脚使劲碾碎,说:“不行。”
麻叔哀求道:“好同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求你让我看他一眼吧。”说着眼角溢出两滴老泪。
肥头大耳呸了一口,说:“快走吧,别让我看见你恶心。”
麻叔又握了一下空拳。他非常郁闷,心里无比纠结:是我儿子犯罪又不是我犯罪,这些警察为啥都这样讨厌我?忽然,他想起了在刑警队时那个黑脸刑警说的那句话:“子不教父之过。”顿时又像挨了一耳刮子,脸上火辣辣地发烫。他想了一下,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于是厚着脸说:“那麻烦您送几件衣服给他行吗?”
肥头大耳从麻叔的蛇皮袋里把衣服抖出来,仔细检查了几次,然后开了一张收据给他。
“我儿子到底有没有杀人?”麻叔突兀地问,“他是不是替人背黑锅?凶手是哪个?”
肥头大耳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你走吧,不由分说把麻叔推出接待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麻叔从看守所出来,腰一下子又弯了许多。
四
麻叔在家等候破案的消息,等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晚上睡觉总是梦到爹在骂他,一次比一次凶恶。他想起在车上听到的议论,幻想儿子真是在替别人背黑锅,这样他就不至于绝命,麻家也就不至于绝后。抱着这样的希望,麻叔等了差不多一个月,啥消息都没等到,便又跑到派出所去打听。所里的人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只叫他去县里打听。于是,麻叔便又来到县城。到看守所一问,才晓得麻国民的案子已由检察院起诉转交到法院准备开庭审判。麻叔又找到法院,法院给了他一张传票,通知他马上就要开庭审理此案,叫他去找辩护律师。
麻叔在县城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啥辩护律师?时值仲夏时节,三伏天气,上面的日头往下晒,下面的热气往上熏,人在中间就像被蒸煮的饺子,热得不可开交。街道旁边有两棵树上的蝉也被折磨得受不了了,嘶哑着嗓子不停地叫:“死了——死了——”
麻叔在城里像陀螺似地转了几圈,流了一身臭汗,心里火烧火燎地烦。走到一个街角,那里有几棵樟树,正好挡住日头,是一个乘凉的好去处,那些打牌的、搓麻将的、看相算命的、卖凉茶的和看热闹扯闲篇的都拢在那里,聚了一大堆子人。
看到卖凉茶的,麻叔立即感到口干舌燥。他拖着酸胀的双腿走过去,那卖凉茶的摆了一个冰柜和一张小桌,在一张纸板上写了几个字:冰凉茶,一元一杯。
麻叔说:“老板,我要一杯凉茶。”
卖凉茶的说:“好嘞。”拖过一张小凳,热情地招呼:“您请坐,凉茶马上就好。”
麻叔在小凳上坐下来,掏出用红色小食品袋装的烤烟丝,用裁好的旧报纸卷了一支喇叭筒,在舌尖上舔一舔,叼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猛吸一口,很久才从鼻腔里喷出两股白色的浓烟,接着眯上眼睛,从嘴里“咝”地吐出一口很享受的气息。
坐在凉茶摊旁边摆摊看相测字的白胡子老头一直注目观察着麻叔,这时咳嗽一声,说:“这位老哥可要看相?”
麻叔一看,原来旁边有一个测字的先生,立刻肃然起敬。麻叔相信宿命,于是毕恭毕敬地起身深揖一恭:“先生可会测字?”
白胡子老头连忙欠身答礼:“会啊,老哥请说一字。”
这时,一位买菜的中年妇女正提着装了韭菜的篮子从麻叔跟前走过。麻叔眼前一亮,随口说:“韮。”
白胡子老头提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韮”字,捏须沉思,良久方说:“下为地,上为草,中藏非,此乃不吉之兆,怕有血光之灾啊。”
麻叔一听,吓得连烟都掉在了地上,战战兢兢地问有不有化解灾难的办法。
“欲知明日果,还看今天因。”白胡子老头沉吟一会,说:“解是有解,不过还要看你平时有没有行善积德呢。”
“那是那是。”麻叔连声说,“就请先生为我一解。”
“那好。”白胡子老头说,“烦请报上姓名和生庚八字。”
麻叔就报了儿子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时。
“啥?”白胡子老头瞪大了眼睛,“麻国民?他是你儿子?”
麻叔说:“是啊!你认识他?”
白胡子老头把毛笔在桌上重重一拍,说:“这灾我解不了。”
麻叔不解地问:“先生这是为何?”
白胡子老头摇头长叹一声:“子不屑,父之过。”说罢闭目不语。
那卖凉茶的刚端了一杯凉茶要递给麻叔,听说他是杀人犯麻国民的老子,气得把茶往地上一泼,说:“我这茶就是喂狗,也不给你喝!”
那些打牌玩麻将和看热闹的人听说杀人犯麻国民的父亲在这里,都一起把目光投过来,像看怪物一样盯着麻叔,叽叽喳喳地议论:“看这人一副熊样,怎么会养出那样坏的儿子?”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打地洞。儿子是个人渣,老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嘛。”
“听讲他还在到处找律师为他儿子辩护。那样的人救他干啥?干脆一刀劈死他算了,死一万回也不冤呢。”
噼里啪啦,又是一阵耳刮子打在脸上,麻叔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他这才晓得儿子麻国民已经像过街老鼠一样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引起全民公愤的声讨对象。他习惯性地想伸手握刀,却握了一个空,只好握着空拳发抖。他如芒刺在背,再也无脸呆在这里,于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想要离开。
麻叔再也无力说出“我儿子不是杀人犯,他是代人受过”这句话,也许这件事情真的与他教子无方有关。他手里还捏着准备用来买凉茶的一元钱,这时看见旁边蹲着一个捧了一只破碗讨钱的乞丐,猛地想起了测字先生叫他要行善积德的话,于是便把那一元钱丢进了乞丐的破碗里。
“呸!”乞丐竟然把那一元钱扔回给麻叔,“谁要你的臭钱?”
麻叔如同挨了当头一棒,连一个乞丐都在痞视他,他已经颜面扫地,连忙拔脚就走。
“喂!”麻叔突然听到有人叫他,“老头,你不是要找律师吗?我告诉你去找啊。”
麻叔停步,见叫他的是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说:“你往前走,再往左转,到法院对面就有一家律师事务所。”
麻叔心里略感安慰,他想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痞视他。但他这时已经对去找律师失去了信心,儿子已经臭名昭著引起公愤,律师会帮这样的人吗?可是如果不去爹会饶过他吗?他咬了咬牙,硬着头皮决定去找一次律师。法院他已经去过一次,只是没有留意到对面有律师事务所。他轻车熟路地来到法院,见到对面果然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挂着一块牌子“正义律师事务所。”
麻叔走进这家正义律师事务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接待了他。
中年男人就是律师,开门见山地问他要为什么人打官司。
麻叔说为儿子打官司。
律师问他儿子叫啥名字。
麻叔说叫麻国民。
律师一听,立即收起笔,合上笔记本,说这个官司他打不了。
麻叔诧异地问:“为啥?”
律师说:“我是为受害者主持正义的,不为罪犯辩护。”
麻叔慌了,低声下气地哀求道:“律师,求求你了,我就这一个儿子……”
“你走吧。”律师不耐烦了,“我还有事,别在这里影响我的工作。”
麻叔这才明白,原来那个好心指引他找律师的年轻人也是在耍他,他带着满腹的委屈灰溜溜地离开了正义律师事务所。
五
麻叔再也不敢去找律师。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他在一个小店喝了碗凉粥,找了家小客栈住下,满脑子都想着白天遭受屈辱的事,哪里睡得着?
麻叔睡的是通铺,一个房间七八张床。这晚客少,房间里除了麻叔外,只有对面床上睡了一个客人。这人三十七八岁年纪,脸上有一颗豆大的黄痦子,痦子上长着一撮灰毛。一撮毛见麻叔在床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便主动过问:“大叔身体不舒服吗?”
“没事。”麻叔见打扰了别人,忙直挺挺躺着不敢再动。
“没事就好。”一撮毛说,“有事只管开口,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点小忙呢。”
这句话提醒了麻叔,自己在县城一个熟人都没有,瞎子摸鱼到哪里去找人帮忙?如今遇到这么个热心人,何不投个石头探探深浅?想着,便问一撮毛,在啥地方能找到帮犯人辩护的律师。
“找律师?”一撮毛若有所悟,说:“原来你要打官司呀。”
麻叔说是他儿子惹了官司。
麻叔想接下来一撮毛肯定要像别人那样问他儿子的名字的,他在考虑要不要把儿子的名字说出来。可是没等他想好,一撮毛就一拍大腿说:“你这是叫化子遇到了舍粥的,我表哥就是律师啊。”
麻叔半信半疑,问他表哥肯为犯人辩护吗?他怕一撮毛的表哥又是一个正义律师,岂不是自讨没趣?
一撮毛让麻叔别急,他先出去打个电话和表哥联系,若表哥愿接这个案子,那么就是刀架在麻叔儿子的脖子上也没事。说着,便披衣趿鞋,出去打电话去了。
过了好一会,一撮毛领着个戴眼镜穿西服扎领带夹着黑色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回来了。一撮毛说:“算你儿子有救星,我表哥一接到电话就立即决定来见你了。”
麻叔慌忙起身相迎:“律师,全指望您了。”
律师说:“我姓周。你详细讲讲你儿子的事吧。”说着,拉开公文包,掏出笔和记录本。
不知为何,麻叔一见这周律师就对他产生了好感,这人特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大律师架子,老百姓最喜欢的就是这类人,更何况麻叔现在正是病急乱投医的时候。于是,他便开始讲述儿子的犯罪过程,周律师则认真地在本子上记录着。记完,周律师合上本子,对麻叔说:“情况确实对你儿子不利,这事比较难搞哟。”
麻叔一听急了,忙问该怎么办?周律师劝麻叔别急,说天总是要亮的,办法总是会有的,关键是要找出证据来证明你儿子不是杀人凶手。麻叔明白这是翻案,那可比推石头上岭都要困难。周律师自信地笑笑,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当律师的就是专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情的。麻叔一听差点要给周律师下跪,答应如果他儿子得救,他愿给周律师立长生牌甚至当牛做马。
“那倒不必。”周律师微笑说,“不过,有句话我必须讲清楚,我们当律师的帮人打官司是要收代理费的。再讲,现在没钱也办不成事,大叔你讲对不?”
麻叔忙不迭地把头点得像鸡啄米,说:“那是那是,周律师您开口,要几多钱?”
周律师告诉麻叔,要打赢这场官司,不会少于千儿八百,就看他愿不愿意破财消灾。
麻叔愣了一下,说:“我也晓得花钱才能消灾,可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
周律师问麻叔身上到底有多少钱?麻叔说只有六百元。周律师便让麻叔先交六百元,余款以后再补交。麻叔提出先交五百元,好给自己留点生活费。周律师不高兴了,告诉麻叔自己这是在救他儿子,不是在和他做生意,不能讨价还价。
一撮毛这时说话了,他说:“表哥,我看这大叔确实可怜。哪个人没得落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当是替天行道做善事,先收他五百元怎么样?”
周律师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哪个让我遇上了你这样的人呢?”
麻叔感恩不尽连说谢谢,就解开了缠在身上的腰带,从裤裆里掏出一个臭熏熏的布包,一层层打开,用指头蘸了口水,抖抖地数了五百元交给周律师。周律师接过钱,说忘了带收据,让麻叔明天上午随他表弟去他办公室取,然后就像来时一样,夹着皮包从容不迫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麻叔一觉醒来,不见了一撮毛。问店老板,说是天不亮就走了。麻叔这才明白他被人骗了,却连一撮毛的姓名都不晓得。再问店老板,回答客栈从不登记客人的姓名和地址。麻叔暗暗叫苦,这真是叫化子被狗咬,祸不单行啦,当时就握着空拳发抖,脸色苍白,双腿发软。店老板一见吓坏了,这老头要是闹起来或死在客栈里,他这个鸡毛小店就别想再开了,当下急忙把麻叔扶到一边坐下,又是倒茶又是敬烟,差点没打拱作揖了:“大叔,您蚀了多少钱,我一分不少赔给您,求您千万别把这事讲出去好不好?”
麻叔叹了一口气,说:“这不关你的事,我不报案,也不要你赔钱。要怨,就怨我自家不中用。”
店老板听了,感激得唏嘘连声,掏出二百元钱塞给麻叔。麻叔坚执不要,说:“你这是撵我呀,我走就行啦。”
店老板这才把钱收起,说:“您住,住多久我都不厌烦。”
麻叔说:“行了,你不撵我也该走了。”
店老板苦留不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麻叔离开了客栈。
六
麻叔一个人在大街上转游,心里骂一回儿子,又骂一回骗子,手一直握着空拳发抖,那抑制不住的愤恨和悲凄涌上心头,禁不住老泪横流。这时,一个人与麻叔擦肩而过,瞧了麻叔一眼。走几步,停住,又回头再瞧。麻叔也心怀戒备地瞧他。这一对视,那人便折回来,试探着问:“这不是麻叔吗?”
麻叔瞧着这人好生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他是哪个,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人握住麻叔的手,激动地说:“麻叔,我是德发呀!”
“你是德发?”麻叔愣了一下,突然想起来,德发是他远房侄子。麻叔远房大哥早亡,德发母子生活艰难,麻叔经常接济他们。德发后来考上了大学,又分配到外地工作,几年后母亲也过世了,德发就再也没回过家。“你如今在哪里工作?成家了吗?”麻叔还像对待小时候的德发一样关切地问。
德发说:“我刚调回县里,在公安局工作。”说着眼里有泪光闪烁,“我早成家了,爱人也有工作,还没调过来哩。”
“那就好,那就好。”麻叔高兴地说,突然眼珠发直盯住德发问:“啥?你在公安局工作?”
德发微笑着说:“是呀,您老人家到县城来办啥事啊?”
麻叔哽着嗓子叫了一声贤侄,已是老泪横流,那万般的屈辱和悲愤早就堵塞了喉咙。
德发一愣,忙问:“叔,您哭啥啊?”
麻叔就告诉德发说他兄弟国民犯了命案,怕是连脑壳都保不住了。
德发大吃一惊,说他刚调过来没多久,情况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要麻叔讲给他听听。
麻叔便讲了案件的经过,德发听后许久没有作声。麻叔以为德发为难了,便说:“德发贤侄,你可千万要救救你兄弟呀。”
德发沉思良久,说:“叔啊,不是我讲你,国民兄弟走到今天,你也是有责任的啊。”
麻叔低头叹道:“唉!连你都这样讲我,看来我真的是……”他想,别人讲他宠坏了儿子也许带着很多主偏见,但德发却讲的是实话,因为德发是和国民从小一起玩大的,他看见麻叔对独苗儿子万般宠爱,百依百顺,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想做啥从不阻止,即使国民把别人的孩子打了,麻叔也会找个借口护着自己的儿子,就像现在有些官僚,下属犯了错误,千方百计地包庇和保护,为的就是要保住自己的面子和地位,祸根也就是这样种下的,就像俗话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如此,麻叔仍然忍受着别人对他的谴责和痞视,想方设法要挽救儿子。
德发见麻叔难过的样子,便转了话题请麻叔到他家里去。德发把麻叔领到他屋里,摆好烟和茶水,又开了电视和空调,让麻叔在屋里等着,就出去了。
麻叔以为德发出去买菜去了,没想到一等就等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德发才醉熏熏地回来。
德发抱歉地说,一出去就遇到了几个朋友,非要请他吃饭不可,就打开为麻叔买回的一大包熟牛肉和烧鸡,又从酒柜里取出一瓶白酒,叫麻叔吃,然后就进卫生间洗澡去了。
麻叔想,当官真好,有权有钱有吃有喝。你看这屋子里摆的东西,哪件不都是和玻璃镜子一样亮堂堂的?再看看自己,寒酸得还不如一个老叫花子。正当麻叔在自卑时,德发已洗好澡出来,见麻叔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便说:“叔,您吃呀。”
麻叔答应着,呷了一口酒,又苦又辣,呛得眼里泪光闪闪;再吃菜时,竟品不出究竟是啥滋味了。
德发过来挨着麻叔坐下,说:“叔,别急,天塌下来有高个子撑着呢,没啥大不了的事嘛。”
麻叔从德发的话里听出了希望,就问国民是不是有救了?德发就笑了,说国民不是凶手,因为真正的凶手已捉获归案了。麻叔喜出望外,激动得连拿筷子的手都在簌簌发抖,忙问国民是不是就没事了?德发摇了摇头告诉麻叔,犯罪是要被判刑的,只不过判重判轻而已。
麻叔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国民若是被判个无期徒刑,那和死又有啥两样?德发看出了麻叔的心思,就开导麻叔:“国民兄弟能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至于判刑嘛,是为了使他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会不会被判无期徒刑呢?”麻叔终于问了憋在心头的这个问题。
德发大笑,说:“叔啊,有我在,您担啥心呢?”
麻叔问德发到底是个多大的官?德发说不大,也就是个副局长吧。麻叔便无限感慨。说实在的,他并不奢望儿子被无罪释放,只要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就行,让他蹲几年大牢好改邪归正。这种矛盾心理,说不清是出于对儿子的恨还是爱,就像儿子偷了人家的东西,总希望失主在不太过份的前提下适当对他责罚一下,不然心里总会留下一份遗憾。
七
事情的发展既符合麻叔的愿望又出乎他的预料,儿子麻国民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实行监外执行,提前释放出狱。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舆论,人们气愤得不行,都说这叫啥判刑,还不如叫无罪释放得了。麻国民并不在意这些议论,相反倒像个扬名立万的英雄一样大言不惭:“老子能进出自由,这才算本事呢。”
村里人晓得他是个敢把脑袋挂在裤腰上玩命的角色,又有人在“朝廷”为他挡风,犯不着与他过不去,便都躲着他。人都喜欢捡软柿子捏,就把气撒到麻叔身上。那天,麻叔到地里去锄草,从河边经过,听到几个洗衣服的女人在议论。一个说:“老麻子大概在前世做了缺德事,所以在今世要遭报应。”另一个说:“老麻子想保住香火,可他这样的儿子哪个女人会嫁给他?所以老麻子终归要断子绝孙,就是有个孙子也会没屁眼的。”
麻叔实在听不下去了,急忙拐进河边的一片柳树林里。这时候已经是秋天,秋剥皮,天气又热又闷。麻叔像中了暑一样,身子瑟瑟发抖,一会冷一会热。一棵柳树上有一只蝉在叫:“死了——死了——”麻叔向树上看了一眼,连蝉都在取笑我,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那几个女人洗完衣服,经过柳树林往村里走。麻叔急忙躲到草丛后面,听到一个女人说:“你们晓得吗?德发为了救老麻子那个不争气的儿子犯错误了,被啥双管(规)了。”
麻叔像被挨了一闷棍,眼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他也不去地里了,半路上折回家,正碰上儿子在家里和几个年轻人玩纸牌赌钱。麻叔一见,气就不打一处来:“你狗日的真不是东西。”
麻国民斜了麻叔一眼,说:“你也别骂我,我晓得德发哥出事了,我也在外面呆不了多久了,你就让我痛痛快快地玩个够吧。”
麻叔说:“识相你就自己快点滚回看守所去,别让警察来抓你。”
麻国民说:“你好意思骂我?你以为你就是啥好东西?你晓得别人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不是你和德发这狗日的想方设法把我弄出来,我在里面呆几年兴许还能成个好人。现在想让我自己回去,门都没有。”
麻叔被彻底激怒了,所有的愤怒和屈辱都爆发出来。他这一次不再是手握空拳,而是抢了砍刀在手里,把麻国民他们赌钱的桌子一脚踹翻:“你狗日的给我滚!”
麻国民他们被那闪着寒光的砍刀吓得面无人色,屁滚尿流逃出了家门。
麻叔没脸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天天以酒浇愁。邻居怕他想不开出点啥事,就来敲门。敲不开,就隔着门劝他,麻叔也不理睬。喝醉了,就迷迷糊糊地睡。麻叔想再见到他爹,问他自己该怎么办,可是爹再也不露面了,可能连这个麻家的老祖宗也无脸见人了。忽然,他看见了老王,老王站在被偷树贼砍得七零八落到处都是断树桩的树林里,浑身血淋淋的。麻叔和他打招呼。麻叔说:“老王兄弟,你这是怎么啦?”老王也不答话,只是睁着血红的眼睛愤怒地看着麻叔。麻叔猛然明白过来,老王已经死了,是被他儿子麻国民他们杀死的。麻叔扑过去抱住老王哭道:“兄弟,是我对不起你,你死得冤枉啊。”这时候他忽然发现,不单是老王,连老王身后面那些露着白森森树茬的断树桩也变成了血淋淋的无头躯体。麻叔吓得扑通跪下,给老王和这些树桩叩头:“我错了,我错了,求你们原谅我。我再也不听我爹的话了,我给你们报仇,我这就去给你们报仇。”麻叔从噩梦中惊醒。他爬起来,扛了砍刀,出门踉踉跄跄往林区奔去。
他离开林区很久了,只见满山荒芜,乱草丛中露出一茬茬白骨似的树桩,足见盗贼猖狂之极。麻叔不知道,自从他离开林区之后,接替他的人只在山里呆了一段时间,就被山里恶劣的环境和偷树贼的恐吓吓跑了,此后再也没有谁愿意来这里当护林员,正好给了偷树贼可乘之机。见此惨状,麻叔像一头被激怒的老熊,提着砍刀在松林里踉跄奔走,他在寻找泄愤的目标。
麻叔正寻找着,突然发现林子深处有一堆燃烧的篝火。麻叔借着草树的掩护,悄悄摸过去,只见五六个野人一样的男人,正围着火堆在狼吞虎咽吃东西,旁边是一堆已经砍倒的油松原木。这时,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离开火堆,正对着麻叔撒尿。麻叔睁眼一看,正是他儿子麻国民。
麻叔怒火中烧,睁着血红的眼珠大吼一声:“畜牲!看你往哪里逃?”横刀拦在了儿子面前。
麻国民一激愣,尿水洒在了裤子上。其他人见被人发现了,也都跳起来,纷纷操起家伙,将麻叔团团围住。
麻国民吃惊地瞪着父亲:“你……?”
一个像红发鬼似的后生问麻国民:“你认识他?”
麻国民余悸未消地说:“他是我爹……是……护林员。”
听麻国民这样说,那些人都稍稍吐了口气。大家都晓得麻国民是他爹历尽千辛万苦才从牢里救出来的,想来他也不会对儿子怎么样。
红发鬼想缓和气氛,便从身上摸出烟来,递给麻叔:“老伯,抽枝烟吧,民哥是你儿子,我们不也都是你的儿子吗?”
麻叔把刀一横,将红发鬼的烟打掉:“放屁!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狗日儿子。”
麻国民挥挥手,让那些人退开。他说:“看在你抚养我长大的份上,我叫你一声爹。不过你不要太过份,今天你就当没看见我们行不?”
麻叔说:“放屁!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回去自首。”麻叔现在对儿子已经彻底失望,他只想把他抓回去交给政府处理,不管法院判他死刑还是无期徒刑他都没有怨言。就像人们说的,这样的社会垃圾不除,天理不容。
麻国民冷笑说:“你不要倚老卖老。按照江湖规矩,我给你行个大礼,我俩的父子关系也就不存在了。”
麻叔气得胡须乱颤,握着砍刀的手在微微发抖:“我再讲一遍,你跟我回去!”
麻国民说:“做梦吧你。”
麻叔大吼一声:“你回去不?”
麻国民说:“我不回去,怎样?”
麻叔说:“好!你有种,你就给我行礼吧。”
麻国民真的跪下,伏地给麻叔磕了三个响头。这时,麻叔突然抡起砍刀,大吼一声朝儿子劈了下去……
【作者简介】伍秋福,笔名秋人,男,1963年出生,广西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上海故事》《广西文学》《小说月刊》《北方作家》《南方文学》《天池》《精短小说》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120多万字,小说《青冈木》获漓江日报小说奖;散文《佩环叮当》获广西文学奖,小说《意外》获冯梦龙杯全国短篇小说奖和广西小小说奖并入选《冯梦龙杯全国短篇小说集》,小说《重灾户》获第一届浩然文学奖和“登沙河”杯全国短篇小说奖,小小说《意外》和《青冈木》方便入选《2015年中国年度微型小说》漓江版和现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