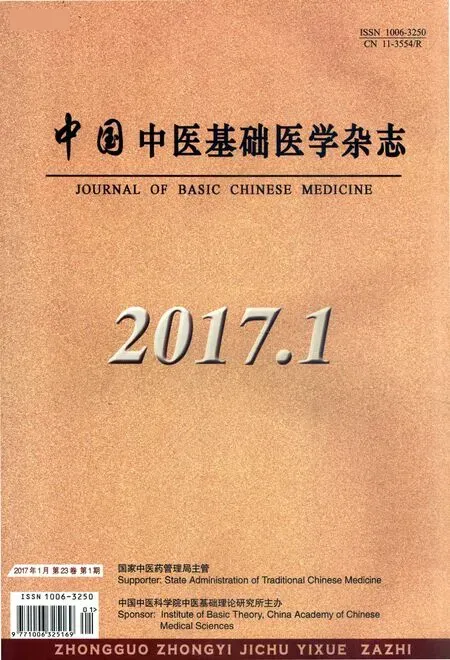王亿平辨治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湿热证临证经验*
张 磊,金 华,王 东,王亿平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合肥 230031)
王亿平辨治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湿热证临证经验*
张 磊,金 华,王 东,王亿平△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合肥 230031)
王亿平教授认为慢性肾衰竭的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兼证,多以脾肾亏虚为本、湿热内蕴为标。在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阶段,湿热证是其主要的中医证候;临床上根据湿热之邪程度不同(湿重于热、湿热参半、热重于湿)应分阶段辨证论治。在组方施治中应攻补兼施、寓攻于补,同时在清热利湿之中勿忘宣肺护阴,并将化瘀通腑贯穿始终。
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湿热证;辨证论治
慢性肾脏病基础上的急性肾衰竭(acute renal failure on chronic kidney disease,A/C)是指在原有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基础上由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短期内肾小球滤过率迅速下降的1组临床综合征[1],临床常称之为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阶段。我国急性肾衰患者中 A/C的发生率为33.17%,其中A/C患者的病死率达11.59%。而74.88%的患者肾功能不能恢复至原来的水平,其中35.48%的患者最终只能接受永久的肾脏替代治疗[2]。由此可见,积极有效地治疗慢性肾衰竭基础上的急性加重,对于延缓患者的疾病进展、减轻经济负担具有重要意义。A/C常见因素包括劳累、饮食不节、感染、原发病控制不佳、血容量不足、梗阻等,临床多以发热、乏力、头身困重、纳差、恶心呕吐为主要症状,属于中医学“湿热证”范畴[3]。王亿平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医药防治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现将其辨治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湿热证的临证经验总结如下。
1 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阶段的病因病机
1.1 脾肾亏虚为本
慢性肾衰竭主要是由于各种慢性肾脏疾病逐渐进展而致。在我国,慢性肾小球肾炎是导致患者进入终末期肾脏病的首位因素。慢性肾小球肾炎属于中医学“水肿”“尿血”“阴水”“肾水”“肾风”等范畴。王亿平课题组前期研究证实,脾肾亏虚不仅是其主要病因,亦是其主要本虚之证[4]。肾为先天之本,《素问·六节脏象论》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
肾藏精,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也是人体生长发育及各种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素问·逆调论》称“肾者水脏,主津液。”故肾气对于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作用。《素问·通评虚实论》云:“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肾气虚封藏失司,肾气不固则导致精微下泄,可出现蛋白尿;肾主水,肾气虚不能主水以致水湿泛滥而水肿。脾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精微,升清降浊、统血。正如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所说:“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素问·厥论》:“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沈目南《金匮要略注》说:“五脏六腑之血,全赖脾气统摄。”脾气虚则饮食物中营养物质无以运化,气血化生无源;清阳无力以升,浊阴无源以降,津液输布失常,无力统血,则见乏力、倦怠、水肿、尿血等。故《素问·至真要大论》有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李东垣在《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中云:“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因此王亿平认为,慢性肾衰竭的发病是以脾肾亏虚为基础,无论标实之邪的夹杂与否,治疗都应注意固本之法,即健脾益肾为之根本。
1.2 湿热内蕴为标
但慢性肾衰竭患者尤其是急性加重阶段患者临床表现多以湿热证为主。王亿平基于《素问·生气通天论》“病久则传化”的理论,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分析慢性肾衰竭患者湿热证是由于邪气入里,患者素体本虚,正不胜邪,久病入里,化湿化热,甚至化火化燥并夹有气滞血瘀。正如《素问·皮部论》云:“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脉络,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素问·调经论》云:“有所劳倦,行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
《素问·水热穴论》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薛生白《湿热病》曰:“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即在脾肾亏虚的基础上,水湿内停再感受外邪,内外相引而致湿热内生。这里的内伤主要指引起慢性肾衰竭的各种基础疾病导致患者素体虚弱,外邪主要指各种因素诱发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的各种因素,主要包括感染、饮食不洁、劳累等。外邪入里,邪不胜正,如《湿热病》云:“湿邪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入鼻者十之八九。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多阳明太阴受病。”临床上患者以发热、头身困重、胸痞、腹胀、纳差、恶心呕吐、小便短少或无尿、口中秽臭或有尿味、舌红苔黄厚腻等湿热证表现为主,故见头身困重、腹胀、纳差等症状。《湿热病》曰:“阳明太阴湿热内郁,郁甚则少火皆成壮火,表里上下充斥肆逆。”而见恶心呕吐、小便短少或无尿、口中秽臭。“湿蔽清阳则胸痞,湿热交蒸则舌黄”。故王亿平认为在脾肾亏虚的基础上,病邪蕴结于内,化湿化热是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的主要病理因素,若湿热蕴久不祛亦将成为慢性肾衰竭的加重因素。对于急性加重期患者当以祛邪为主,尽早祛除肾衰加重因素。
2 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期湿热证辨证论治
《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王亿平结合《素问·调经论》“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标”,辨证论治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湿热证。
2.1 湿重于热
肢体浮肿,按之凹陷,脘腹痞闷,口腻纳呆,口淡不渴,便溏,头身困重,小便短少,舌质淡胖,苔白腻或白滑,脉沉缓或濡细。因素体虚弱,湿浊内生,困阻中阳所致,治宜运脾行气、利湿化浊,以胃苓汤加减。方中白术健脾运湿,桂枝通阳化气,助膀胱气化;猪苓、茯苓、泽泻通利水道,使水湿下输膀胱。再加苍术苦温辛燥,除湿健脾;厚朴苦温行气消胀,助苍术以温运脾阳;陈皮芳香化浊,理气和胃;甘草调和诸药,合而为温通脾阳、利水消肿之剂。
2.2 湿热参半
眼睑或全身浮肿,退而复发;脘腹痞呕闷,纳呆恶,大便溏泻不爽,肢体困重,渴不多饮,身热不扬,汗出不解,口苦,舌尖红,舌质白微黄腻。因久病体虚,正不胜邪,邪气入里化热,湿热内蕴脾胃所致,治宜清热化湿,以黄连温胆汤加减。生大黄解毒泄浊化瘀;黄连清热燥湿除烦;半夏燥湿化痰,降逆和胃;竹茹清胆和胃,止呕除烦;佐以枳实、橘皮理气化痰,使气顺则痰自消;茯苓健脾利湿,脾湿去则痰不生。
2.3 热重于湿
神昏谵语,烦燥不安,小便短少黄赤或无尿、恶心呕吐,大便闭结或口有尿臭,面赤身热,鼻衄、牙宣、紫斑、呕血、便血等;舌质红、苔黄腻或燥,脉滑细数;湿浊内生,郁久化热,上逆蒙蔽心窍,热入血分,迫血妄行;热结胃肠,传导失司,治宜清心开窍、利湿通腑,以清营汤加减方。用犀角清营解毒,玄参、生地、麦冬甘寒清热养阴,黄连、竹叶心、连翘、银花清心解毒,丹参清热凉血活血。若呕吐甚加半夏、石菖蒲降逆通窍。
3 经典病案
罗某,女,45岁,因双下肢水肿2个月,恶心呕吐1周入院。症见胸脘痞闷、肢体困重、口有尿味、纳差、大便干结、舌质暗、苔黄腻等。既往有慢性肾小球肾炎病史10年,24 h尿蛋白1.40~2.20 g/24 h,3年前发现肾功能异常,血肌酐167 μmol/L,后长期于我院门诊辨证口服中药治疗,血肌酐波动在203~158 μmol/L之间。本次入院查血肌酐302 μ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15.44 ml/min。西医诊断慢性肾脏病4期,中医诊断关格,辨证属湿热内蕴,治以清热化湿、健脾益肾,佐以化瘀泄浊之法。处方:黄柏10 g,知母10 g,栀子10 g,六月雪15 g,土茯苓15 g,厚朴10 g,菖蒲10 g,砂仁6 g(后下),姜半夏10 g,茯苓10 g,白术10 g,薏苡仁30 g,大黄10 g(后下),桃仁10 g,丹参20 g,当归10 g,水煎服每日1剂。上方服用14 d后患者水肿消退,饮食改善,无恶心呕吐,舌质淡、苔白微腻。上方去栀子、六月雪、姜半夏,加山茱萸10 g、苍术10 g、益母草10 g,继服7 d后复查血肌酐253 μmol/L。
4 辨证体会
4.1 攻补兼施,寓攻于补
《素问·标本病传论》云:“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为独行。”慢性肾衰竭急性加重期患者以脾肾亏虚为本,湿热内蕴为标。患者素体本虚,若一味清利攻伐易耗伤正气。王亿平基于李东垣“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认为元气虽然禀受于先天,由先天之肾精所化生且遣藏于肾,但必须依赖后天脾胃精气的不断滋养。在组方施治中,于清热利湿化瘀行气之品中,常配以薏苡仁、白术、扁豆、茯苓等益气健脾之药。调理脾胃以后天滋先天,既可培土固本又可扶正祛邪,共达攻补兼施之效。王亿平强调慢性肾衰竭患者之补益,外可攻邪内可扶正,并能增加攻伐之效,寓攻于补。但其补益非一日之功,投药切勿峻猛性烈而致伤阴耗血。应徐而图之,易用生黄芪、太子参、枸杞子、生地等性平清淡之品。
4.2 清热利湿勿忘宣肺护阴
慢性肾衰竭患者以湿热为标,素体本虚,大量苦寒、苦燥之品极易伤阴伐胃,故清热利湿之中常佐以知母、生地、当归等甘寒养阴补血之品,使其清热而不伐胃,利湿而不伤阴,滋阴而不碍湿。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言:“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肺为水之上源,气化则湿化,肺宣则水道畅,正如薛生白治湿四法中的“宣湿”之法。故常配以升麻、桔梗等升散之品。一是与清热利湿方中苦寒沉降之药相配,一升一降,调畅气机,行气化湿;二是取其清宣透热之性,有“透热转气”及“火郁发之”之意,可促使湿热之邪外达气分而解,內清外宣,祛邪而不恋邪,表里同治;三是湿热内蕴,津不上承,且肺失滋润,升散之品可载液上行,既可解渴又可润肺,防止湿热化燥伤肺,有“培土生金”之意。
4.3 化瘀通腑贯穿始终
慢性肾衰竭患者随着肾功能的减退,尿量逐渐减少,肾脏排泄能力下降,使其利小便而泄热之力下降,需从肠道增加毒素排泄。同时久病则瘀滞,气虚则血停,故化瘀痛腑应始终贯穿于治疗始终。一则取“以泻代清”之意,二则取“以通为用”之法,一为通畅气机,二为血脉通畅。王亿平常以大黄配以桃仁、红花、益母草,大黄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化瘀通络;益母草活经调血,利水消肿。二药相配使湿热从下焦而去;红花辛、温,增加活血化瘀之功,以制大黄苦寒之性,防止大寒伤阴;桃仁甘、平,破血行滞而润燥且能降肺气,与方中宣散之品相伍调畅气机。
[1]李晓玫.慢性肾脏病基础上急性肾衰竭的诊断与防治[J].中华肾脏病杂志,2006,22(6):652-654.
[2]王琴,牟姗,严玉澄,等.院内慢性肾脏病基础上急性肾损伤207例临床调查[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2,32(11):874-877.
[3]李文娟.湿热证与慢性肾衰竭病证关系浅析[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4,23(2):58-59.
[4]王亿平,戴昭秋,王东,等.清肾颗粒对慢性肾衰竭湿热证患者血清纤维连接蛋白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3):872-875.
R692.5
A
1006-3250(2017)01-0127-02
2016-07-17
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12010402117)-基于免疫炎症介导机制探讨清热化湿祛瘀法对慢性肾衰湿热证患者的干预作用
张 磊(1990-),男,安徽合肥人,住院医师,从事中医药防治肾脏疾病的临床与研究。
△通讯作者:王亿平(1963-),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wypwyp54@aliyun.com。